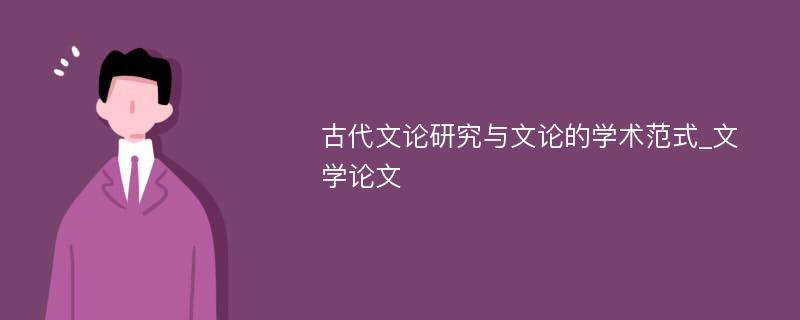
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学术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范式论文,古代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1-0022-06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在库恩看来,“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科学研究模型或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范式的不同显示出研究模式的不同,范式的不断更新显示出研究模式的发展变化与更替。借鉴库恩的范式理论审视人文社会科学,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及其研究规范、研究方法,人文社会学科的每种理论形态都有自己的研究模式、学术范式。从宏观的角度看,中西传统的文学理论具有不同的学术范式。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范式的变异,采纳了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1]从微观的角度审视,众多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涌进国门),改变了我们研究文学的视角、途径、方法。这种研究范型的改变导致了传统的断裂,先是引发了“失语”的痛苦和“身份”的质疑,继而在对西方范式的深刻反省中回溯祖先的智慧,探寻建设当代文学理论的新途径,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继承日渐成为当下文论建设的主导话题。
中西文论的研究范式截然不同。(由于当代文论的研究范式已经西化,谈中西文论的比较都是指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从总体上看,思维方式、思想基础、理论范畴、理论表述都不同。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是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西方文论的思维方式是科学主义的认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基础是儒、道、佛三教合一,西方文论的思想基础则融合了西方的哲学、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是体验与概括统一、具象与抽象统一的既有确定性又有包容性的范畴,西方文论的理论范畴是剥离了表象的明确的抽象概念。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表述多是直觉感悟式的审美经验、审美现象的类比类推,西方文论的理论表述则是抽象概念的演绎归纳、逻辑推理。具体说来,其研究的运行大致有以下诸方面的不同。
第一,研究文学的视角不同。西方文论是“以我观物”,中国古代文论是“以物观物”。王文生先生曾运用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诸坐标的角度和方法,从总体上比较中西文论的特点。[2]他认为在宇宙与作者,即宇宙与文学的关系上,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以“自我”为中心,即以人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以我观物”,即以人所制造的抽象概念去说明宇宙和它的发展规律。人与宇宙万物是分离的、对立的。而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人置身于其中,与天地万物不可分离。老子和庄子反对用语言、概念对宇宙加以界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得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与万物置身宇宙这个浑然的整体之中,人与万物同一,当应和万物,“以物观物”。“以我观物”,趋向“分”。“以物观物”,趋向“全”。反映到文艺思想上,古希腊注重对对象的摹仿,强调艺术的创造,提倡结构的和谐。而老庄主张“涤除玄鉴”(《老子·第十章》),“虚而待物”(《庄子·人间世》),以空明的心境感应、体悟天地万物,提倡自然的自由呈现、物象的浑然天全,反对一切人为的造作。“以我观物”影响文艺创作,摹仿常常使用解说、叙述、象征。“以我观物”影响文艺理论批评,以剥离表象的具有明确指称的抽象概念论析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以物观物”则要求物象的呈现浑然天全,或以近似自然的方式去表现自然现象。所以中国古代诗歌常常以物象自然呈现、互不联属的方式来串联情意的链条,并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生发出艺术的虚境来表现自然的“全”之美,这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意境。而中国古代诗学的意境理论对意境特征的总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则体现了对物象的自然呈现和对自然的“全”之美的追求。“以物观物”影响文艺理论批评,则以不剥离表象的范畴描述文艺的特征与规律。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常常建立在体验、感悟的基础上,在审美体验中生发出来,是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概括与体验的统一,既有确定性又有包容性。如情景、风骨、滋味、形神、意象、气象等等。
第二,研究文学的途径不同。“以我观物”,趋向“分”。西方文论习惯于将研究对象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剥离表象,径取本质,以概念、判断、推理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来演绎和阐述文学的性质、特征与规律。“以物观物”,趋向“全”。中国古代文论则强调对对象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不脱离具体表象去作抽象的推理论证,对文学的研究往往通过直觉感悟、体验体味来把握,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和诗文评、小说戏曲评点以随笔和点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品评作品的高低。或者联系文本具体描写,点到即止,言简意赅,诉诸读者的直觉领悟;或者以意象、诗语描绘评论,甚至以诗论诗。这些表述方式虽然显示出本质分析的不足、理论系统的不够严密,但却往往紧密扣合文本实际,有对艺术形象深入的体味、精湛的见解,将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经验与逻辑相结合,融审美鉴赏与理论生发于一炉,避免了脱离艺术实践、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空疏议论。
第三,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同。“以我观物”,趋向“分”。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是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分门别类地“解剖”对象,侧重于对审美客体结构、本质的研究,从而取得了理论体系(学问)的建树。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众多理论家标新立异,从社会历史、精神分析、神话原型、符号结构、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各自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以物观物”,趋向“全”。中国古代思维注重整体性,以致中国古代不仅史学发达,溯本清源,以史为鉴,而且影响中国古代文论注重整体性,採取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到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这种研究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沿袭承传,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原始要终,语出《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3](89)主要是指从事物发生、发展的源流始终来掌握其规律。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意味着对文学现象的把握要从源到流、从根本到枝节全盘掌握,整体把握。《文心雕龙》采用史、论、评相结合的方式,历史源流的梳理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鉴赏评论相结合,在博观深识的基础上,力求全面地把握具体文学现象的整体,并从整体中去把握个别,进而从具象到抽象,从中总结出规律。《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二十篇采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即从头到尾论述该文体的产生及流变,解释此文体的名称,彰显其含义,标举代表性作家作品以确定该文体的体式,敷陈文理说明该文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明诗》篇,首先引用大舜“诗言志,歌永言”之语说明诗歌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持人情性”。然后说明诗歌的产生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接着便从葛天氏之歌辞梳理到刘宋朝近世之诗,简直就是一部诗歌流变的分体文学史。之后,进行总结:“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认为铺陈而观,列代而论,诗歌抒发情志的变化规律便能察知;而举例剖析诗章的同异,便可明白诗体的基本特征及写作要领。然后刘勰总结了四言诗与五言诗的体制特征,并举出代表性作家为典范:“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但又指出:“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4](61-67)我们看到,《文心雕龙》将史、论、评相结合,既包括对诗体的产生、变化的整体把握,说理的周详,也包括对诗歌特征的形象直观的直觉感悟,是具象与抽象、体验与概括、(审美)感受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杨明照先生曾指出:“在博览精研基础上的史、论、评相结合的方法,是古代文论家的优良传统,这种从下而上的,由鉴赏经验的概括总结而构成的诗学体系,与西方从上而下的,由先验的演绎推论而构成的诗学体系,恰好截然相反,而又各有千秋。”[5]钟嵘的《诗品》既有诗人诗作的品评类比,又有溯流别:追溯五言诗的源头与流派、传承(虽然其划分失于简单片面),也体现了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叶燮《原诗》从诗《三百篇》始,评析了古代诗歌三千余年间的源流、本末,总结了其正、变、因、创的规律。刘熙载《艺概》分别梳理了诗、文、词、赋、书等文学艺术的源流,总结其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样也体现了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第四,研究成果的表述方式不同。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是分门别类“解剖”对象,剥离表象,径取本质,所以其论述方式是运用抽象概念进行演绎归纳、逻辑推理,以此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是对文学审美对象的产生、变化的整体把握,包括对形象特征、表象的直观的直觉感悟,也包括在体验、感悟基础上进行审美概括,从中生发出理论观点,是具象与抽象、体验与概括、(审美)感受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因而其表述方式采用类比推理进行归纳,是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不仅大量诗话词话、诗文评、小说戏曲评点等随笔点评式理论批评采用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就连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理论著作的论述方式也是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
综上所述,中西文论在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研究方法、论述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不同的学术范式。
中西文论研究范式的不同,归根究底,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所造成。因为采纳什么范式、如何运用范式,是由思维走向、思维方式决定的。什么是思维方式?思维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过程,包括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它既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本文采取思维和意识相等的涵义)思维方式指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过程中意识的走向、路径,观察和反映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观察和反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决定着该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生产的特色,正是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成和传承着中西不同的文化,决定和传承着中西文学理论不同的体系、形态、研究方法与表述方式。思维方式犹如各民族文化的“基因”[6],正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范式。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特征和其系统的特质,才能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范式和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是:对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7]它的主要特点在于不是剥离事物表象而以先验的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而是以对事物原貌的整体观照和事物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来把握事物,注重延续和对立统一,十分关注现象和具体事物,重视实践、实用、经验的积累,将感性与理性、经验与逻辑、概念与现实相统一,并以象喻方式说明事物的特征和规律,以象尽意、以象明道,力图周详而缜密。如果说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直觉感悟、体味品评和以象喻方式类比类推的研究途径,具象与抽象统一、概括与体验统一的理论范畴,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便是由这一基因确定和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范式。
中国古代这种整体性思维影响古代文学理论力图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把握,即“以物观物”,趋向“全”。因此,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以体验感悟的方式把握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思维不脱离具体现象去作抽象的推理论证,这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直觉感悟、体味品评和以象喻方式评论分析的研究途径。注重以感受和意会的方式把握对象,导致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和诗文评、小说戏曲评点以随笔和点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受和审美体验,在类比中品评作品的高低,生发出理论观点,往往联系文本具体描写,点到即止,言简意赅,甚至以诗论诗,诉诸读者的直觉领悟。或者以意象、诗语描绘评论,如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又例如小说评点,这是刘辰翁、李卓吾、金圣叹、张竹坡等人前赴后继创造的一种合社会批判、史实评论、审美鉴赏为一体的小说批评方式。它包括小说文本或文集之前的凡例、读法,文本中的眉批、夹批、夹注、回评等,既有对作品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叙述方法的总体评论,又有紧密扣合文本具体描写的批语、评论,“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8],文字往往短小精悍,点到即止,诉诸读者的领悟感受,但理论观点也就在其中生发出来,精粹而透辟。
整体思维驻足于现象层面便产生了对于感觉和经验的依赖,并充分发展了直觉、类比和类推的方式。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很早就出现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比兴方法,铺陈排比、重叠复沓的咏叹方式。如《诗经》“比”以此物比彼物,抒情达意,充分体现了类比;而“兴”则以类推、联想取胜。古代文学理论对“赋比兴”手法的肯定和界定即是充分肯定了类比、类推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类比类推不仅运用于创作,也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方式,不仅诗话词话等随笔式的批评中大量运用,就是《文心雕龙》这种具有完整系统和较为严密的推理的理论著作中类比类推也比比皆是。刘勰从作家作品的比较中说明各种文体的流变和体制、特征,体现了类比类推的特色。文体论“论文叙笔”与创作论“割[剖]情析采”所采用的审美描述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其逻辑推理不是西方那种概念判断的三段式演绎推理,而是事物形象的类的分析比较与归纳的推衍,是类比推理,在类比中品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从具体的审美鉴赏经验中升华、总结、概括文学的特征与规律。如《辨骚》中,刘勰对《楚辞》一系列作品的评述正是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的结合:“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以并能矣。”由此而得出对《楚辞》的评价:“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4](47)对楚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结论也是从对汉代及其后作品文风变化的审美描述来推出,并进而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重要原则。其类比推理不是抽象概念的推导演绎,而是由文学现象内在联系的递进完成。其它如《时序》中对历代文学“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描述,《物色》中关于文学“缘情写景”变迁的描述等等,都是审美描述与类比推理的结合,是感受与认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从而言之有物,形象生动而又雄辩有力。
整体性思维注重对事物原貌的整体观照,农耕生产的“摸着石头过河”,注重经验性与实用性,排斥脱离实践的抽象思辨,导致思维保持物象类比和采用象喻方式说明问题。《易传》和先秦诸子均采用了这种方式。《易传》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相似。《易传》此句,孔颖达疏为:“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於天也。”《易传》说明圣人之设立卦象是用卦象摹拟天地万物,体现自然变化与人事休咎的奥妙。卦象虽然不能等同于它所摹拟(实为象征)的物象,但是它不同于抽象的概念,而是企图完整地表现对象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象思维”,它不是将物象分解,剥离表象抽取概念,而是“以物观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见《十三经注疏》本。)以具象类比的方式体现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的直观整体把握。卦象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体现了抽象与具象的统一,而与单纯的抽象概念不同。《易传》中的各种文辞正是将各个卦象与自然物象联系比附,来解释说明自然与人事的变化、规律。先秦哲人普遍认识到言不尽意,即以概念来表述的语言不可能整体把握对象世界,因而采取“以象尽意”的方式,追求言外之意,对事物的本质联系与规律的把握始终不脱离象。先秦时代普遍盛行的以象尽意、以象明道的言说方式和追求言外之意的话语传统充分体现了整体思维并进一步强化了整体思维。有学者指出,《周易》以“象喻”(卦象)为主,《老子》以“物喻”见长,《庄子》则以“事喻”居多。不仅如此,《论语》、《孟子》等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如孔子用自然物象(岁寒之松柏)喻人格形象(君子)来说明儒家之道。象喻方式其实就是一种诗性隐喻,可以说,以象喻方式喻道、论道,是思与诗的统一。整体性思维的不舍象、以象尽意,影响到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的建构,便是不完全剥离具体表象,力求达到具象与抽象的统一、概括与体验的统一。《文心雕龙》曾以人体喻文学作品:“以情志为神明,以事义为骨髓,以辞藻为肌肤,以宫商为声气。”[9](650)在对人的形体与精神风貌的体验和魏晋人物品评的基础上,将对于人的精神风貌与形体品评的风、骨转义概括为作品的情志与事义(思想情感与事实之意义的表达),这就好比是人的精神风貌与挺直的骨髓。当人们将风骨这对范畴用于评论作品时,自然会将作品与人体联系,从而对作品的情志与事义——风骨,有更生动具体的体验感受。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是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这也是整体把握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致。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意味着对文学现象的把握要从源到流、从根本到技节全盘掌握,整体把握。这充分体现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与钟嵘《诗品》溯源流的表述方式。钟嵘《诗品》追溯了五言诗发展的源流,梳理了诗人之间的渊源关系。虽然其流派划分忽视了作家作品思想艺术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失之于简单片面,但是他以《诗经》、《楚辞》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却是极有见地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文心雕龙》将每种文体历史源流的梳理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鉴赏评论相结合,力求全面地把握具体文学现象的整体,并从整体中去把握个别,进而从具象到抽象,从中总结出规律。我们看到,《文心雕龙》的史、论、评相结合,既包括对诗体的产生、变化的整体把握,也包括对诗歌特征的形象直观的直觉感悟,是具象与抽象、体验与概括、(审美)感受与(理性)认识的统一。
中西文论研究范式是否具有通约性?能否借鉴与融合?中西文论的学术范式、理论体系属于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物,无疑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不可能从整体上将二者组合、拼接在一起。但在局部、具体问题上是可以参考、借鉴,乃至融合的。例如原始要终与执本驭末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研究文学史、文体史的正确方法,实际上从古至今中西的文学史研究都遵循这一方法并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又遵循文学创作既“通”又“变”,即在继承基础上革新,又在革新中寻求发展的观点,在“通”与“变”的研究路径中把握某类文学创作或某个作家的创作。文学史研究属于文学理论(广义的),这说明中西文论研究范式的某些方面是具有通约性的。又如性格、典型、意象等理论范畴,其意涵中西文论大体相通。某些理论命题例如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观念是一致的,以致《文心雕龙·时序》的著名论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今天也常常被运用。此外,当代文论中也已经有融进古代文论范畴、命题的例证,后者如前述《文心雕龙·时序》的著名论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如意象、意境、典型等理论范畴都已融入当代文论中的艺术形象部分(不少文学概论教材《艺术形象》一章中均列形象、意象、意境、典型诸节,笔者主编的《文艺学基本原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即如此)。因此,我们应当仔细辨析中西文论研究范式的异与同,也许,当我们把中西文论及其研究范式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搞清楚了,当代文论学术范式的建构也就随之清楚了。
辨析中西文论研究范式的异与同,当然要采用比较方法。上个世纪80年代,老一辈学者就大力提倡古代文论研究采用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这三个结合其实也就是三个比较,即中西比较、古今比较、文史哲比较的方法,比较对照、辨明同异。老一辈学者身体力行已作了多方比较,例如王元化先生运用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10]王文生先生曾运用艾布拉姆斯的艺术批评诸坐标的角度和方法,从总体上比较中西文论各自的特点;杨明照先生以《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论著述的史、论、评结合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与西方文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比较,等等,证明比较的方法,比较对照、辨明同异是切实可行的好方法,我们应当继续采用。应当既从总体上比较中西文论学术范式各自的特色,又从具体运行中比较中西文论学术范式在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研究方法、论述方式等方面的异同,通过仔细比对,找到可以遵循、参照、借鉴、融合之处。
但是,实际上当下中西文论研究处于不对称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当代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的著述像潮水一样涌进国门,30多年几乎将西方一个世纪的文学理论巡览绍介殆尽,并持续涌现各种西方文论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古代文论研究无论从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处于“少”的状态,古代文论典籍的整理、诠释、研究任重而道远。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古代文论典籍的整理、诠释、研究,尤其是梳理古代文论理论范畴、范畴群生成、衍化的历史,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确定性与包容性,范畴的网络结构(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这是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进行中西文论学术范式比较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梳理范畴的过程也就是了解和体验古代文论研究途径、古代文论学术范式的过程。文学理论学术范式的建构不应当以先验的概念、构想来设定,应当在研究的实践中生发出来。当代文学理论学术范式的建构应当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通过仔细地比较对照、辨明异同,辨析中西文论范式的通约性与特殊性,找到可以遵循、参照、借鉴、融合之处,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学术范式的可循路径。而加强作为比较的前提和基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范式的研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抓紧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