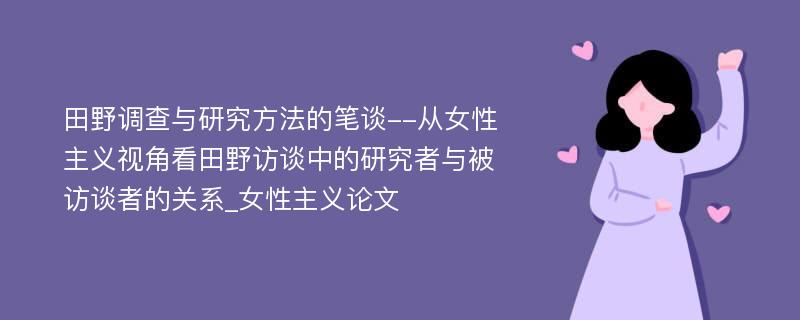
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笔谈——实地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的关系:女性主义视角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研究者论文,调查研究论文,视角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实地访谈本质上是男权中心的,将被访者看做是‘物’,访谈者隐藏在背后,不露面”[1]。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两种经典社会研究模式倡导的都是不真实的“纯净研究”,其中没有任何伦理困境,没有感情涉入。而事实上,研究者常常在访谈中面临研究原则与经验的冲突。
她们探索建立新的社会研究方法论,“要想了解对方,我们必须把她们看做人,她们与我们一起创造对于个人生活的阐释”[2](P668)。访谈者和被访者之间保持一个开放的、相互信任的、经常是更长时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更深入地进入被访者的生活。[3]在这种更为人性化的访谈关系中,访谈者不再努力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可以自然流露自己的情感、对事物进行评价。
按照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看法,双方的友好关系不只停留在资料收集阶段,被访者还应全面参与研究过程,如资料分析,以至文本的撰写,这样,在最终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听到多种声音。本文将主要对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的关系做一个探讨。
一、对Oakley研究的回顾
在英国社会学家Oakley发表于1981年的文章中,明确表达了女性主义访谈应重新确立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将其向“姐妹关系”推进。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关系”成为定性研究方法领域的热门话题。[1]
Oakley的主张基于她于上世纪70年代做的一项有关“女性向母亲身份的转换”的课题,该研究对处于怀孕生育阶段的一个女性样本群体做了多次追踪式访谈。Oakley谈到,做研究之前,她学习了一系列有关如何进行访谈的原则和技巧,但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她感到按这些规则去做十分困难。正是这些困难使她重新审视传统的方法论。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访谈对象在访谈过程中问了她一大堆问题;二是在多阶段的访谈中,双方的接触较多,涉及到非常私人的事务,如怀孕、生孩子、做母亲,以及一些敏感话题,如夫妻关系、性生活等,使得研究者个人的投入无可避免。
访谈对象提出的问题76%为有关医院设施、婴儿看护等的信息咨询,15%关于访谈人的生育态度和经历,如“你是否生过孩子”;6%是对访谈本身的好奇和疑问,如“你是要写本书吗”;4%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希望获得建议,如“你觉得产后多久可以有性生活”。在Oakley面前是一些初次面对生育的非常需要帮助的女性,她们在这样一个生命中关键时期拿出时间来配合作者的访谈,有的甚至允许她进入产房观看很私人化的生产过程,而她们大多数人并不会看到研究成果的发表,谈不到从中获益。这些令Oakley非常感动。因而,她感到自己有义务尽可能地回答她们的疑问,即使涉及到个人生活。比如,有的临产妇女会问她:“你生孩子时痛不痛?”她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尽力安慰她们,“为了孩子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Oakley努力与被访者建立起亲密、平等的关系,通过行动传递给被访者这样一种感觉——我不只想从你们这里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当访谈与被访者的家务活冲突时,Oakley会帮助她们做家务或照看孩子。她的这些做法,使得被访者越来越把她当作朋友而不只是一个资料收集者。
Oakley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研究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没有人中途退出,多数被访者表现出很强的主动性,经常打电话告诉她与研究相关的事件。甚至有的妇女在生完孩子后的第一个念头是告诉Oakley自己的体会。有将近3/4的被访者认为几次访谈对自己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改变了某些态度或行为、稳定情绪等。可见,面对生育这一人生的重大转变,Oakley的访谈提供了其家人、朋友所无法提供的精神安慰和信息支持。这一研究结束四年之后,作者与其中1/3的被访者保持着私人联系,有的成了好朋友,继续分享对于生活的感受。
在总结其经验时,Oakley感到,当一个女性研究者对女性进行访谈时,传统的访谈原则在情理上行不通,多数情况下,双方建立平等的关系,访谈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时,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多次访谈对融洽关系的要求很高,如果拒绝回答被访者的问题或者没有任何个人性反馈,被访者得不到参与感和满足感,将很难建立融洽的气氛,往往会拒绝以后的访谈。
二、女性主义方法论对“研究者与被访者关系”的探讨
Oakley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他女性主义研究者纷纷撰文,从各自的研究实践出发,或支持或提出异议,对“研究者与被访者关系”的探讨不断深入,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角度做一个了解。
(一)朋友关系还是友好关系
Oakley认为,女人对女人的访谈应在感情上尽量亲近被访者。Finch(1984)也谈到,妇女习惯于私人化的家庭领域,她们愿意和一个善解人意的听众聊天。
针对这种将研究关系“转向友谊”的主张,一些学者做出修正。如Cotterill认为,一些被访者愿意和研究者交谈,恰恰因为其作为陌生人的身份不会对被访者施加社会控制,对其生活影响较小,与“友好的陌生人”谈话时感到比较自在。在Cotterill的研究中,有的被访者与她在年龄、生活经历上有很多共性,按理说,应该比较容易发展出“友谊”,当她试图与之发展更近的朋友关系时,被访者却对“橄榄枝”视而不见,这令她感到困惑。Cotterill解释,这恐怕源于被访者如何定义这种关系,有的人愿意把研究者看作朋友,有的人更喜欢一种有距离的关系。
因此,Cotterill建议区分“友谊”和“友好关系”。友谊基于彼此的信任和个人信息分享,访谈则是人为地创造出这样一种谈话氛围。一旦研究者得到了他感兴趣的资料,双方的关系往往戛然而止。“亲密的朋友不会带着一个录音机来拜访你,认真地倾听,与你相谈甚欢,然后就消失了。”虽然,不少研究者在研究结束后,与被访者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友好关系”可发展为“友谊”。但更常见的是,研究者是一个“友好的陌生人”,在收集完资料后就消失了。因此,研究者对与被访者的关系应有一个合适的期望。[4](PP593-606)
(二)研究者的自我暴露
一些女性研究者发现,适当进行“自我暴露”是推动访谈的一个好方式。比如,在一个对强奸的研究中,Ann Bristow和Jody Esper告诉被访者,她们中的一位曾遭受强奸,这一坦诚的态度分担了强奸受害人的恐惧,这位妇女情绪得到放松,访谈进行得很顺利。自我揭露使得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研究者不只是在挖掘对方的生活信息,而是与对方在作对等的交流。
自我暴露应选择合适的时机。在访谈刚开始时,双方处于对访谈人—被访者的角色自我定位阶段,过早的自我暴露会使被访者缺乏准备,感到突兀,并且有可能根据研究者的说话内容揣测其用意和需要,努力表现成研究者想要的那样,使访谈效果受到影响。因而,研究者应该学会掌握互动的节奏,判断被访者何时需要研究者的自我暴露。
关于“研究者应该暴露什么”以至“是不是应该自我暴露”始终都存在争议。但是,多数学者赞同,合适的自我暴露会从被访者那里获得更多的反馈,对于研究计划的调整和进行,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访谈过程中的权利和控制
传统观点认为,当女性对女性进行访谈时,研究者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一般高于被访者,因而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对访谈有一种控制感。Oakley主张将这一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向“姐妹关系”靠拢,会使二者之间更加平等。她认为,作为女人的共享经验是建立亲密、无等级关系的最好办法。共同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特定的生活经历(如生育)拉近了她们之间的距离,使谈话易于进行。女性个人和集体的受压迫经历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足以跨越地位、阶层和年龄这些结构性障碍。
Cotterill则着重指出研究者在访谈中的弱势地位,并且认为不可能通过Oakley寄希望的“姐妹关系”去克服双方的不平等。在她从事的一项研究中,很多被访者年长她15岁以上,拥有社会地位,对高学历并不陌生,使她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甚至是被审视的地位。另外,她们大多数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年白人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没有人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对于那些男性主导、女性屈从的观念并不认同。双方在对于女性境遇的理解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很难在彼此之间发展出一致的身份认同。
基于此,Cotterill认为任何两个访谈都不可能完全一样,访谈双方的关系非常个人化,很难预言合作所能达到的程度。双方的权利平衡不是固定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访者对此项访谈的理解。地位、阶层和年龄这些因素对访谈关系的影响至关重要。[4](PP593-606)
三、对于“研究者与被访者关系”的现实理解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研究对被访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她们提供更广泛的合作:愿意被观察或访谈(有时是多次的),分享个人思想和经历,阅读评价访谈记录和研究报告的草稿等。但是,这些对被访者的期望实际上很难完全实现,缺少时间和兴趣、不同的教育背景、工作和家庭负担、对研究项目的不同期望,以及冲突的价值观都可能降低研究者所希望达成的合作关系的程度。毕竟双方与研究项目的关系不同,研究者确立研究项目,选择研究主题和研究地点,阐释研究资料,最关键的是,最终通过发表研究成果从中获益,当然对项目更关注,受访者对项目主要基于本人的兴趣,一般不受任何约束。因此,对于和被访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应该发展出一种现实的期望。
另外,必须承认,研究者和被访者的关系,像所有人类关系一样,受到权力、阶层、种族等因素的影响,双方一旦在情感上走近,很容易在访谈中产生不平等、误解、侵犯隐私等问题。
因此,Thomas Newkirk建议研究者在处理双方关系时应接受以下事实:
1.我们不会欣赏或喜欢所有被访者;
2.不必追求与所有被访者心意相通,尤其是那些比我们更有权势和地位的人;
3.与被访者选择性地发展友情;
4.只试图影响一些被访者的生活,而且方式也并不总是我们所希望的;
5.邀请被访者参与项目、分享经历时,有时会引起对方的难堪、困惑,甚至情感痛苦。
被访者的无拘束交流只是所有研究者的一个理想境界,如果我们能像Newkirk建议地这样现实地看待问题,就不会为不尽如人意的访谈关系而耿耿于怀了。
四、一点感触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关于研究者与被访者的关系的论述,唤起了我对于过往访谈经历的回忆,很多当时的困惑得到了解释,甚至是共鸣,有知音之感。下面仅就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用心与被访者交流
这是给我启发最大的一点,受传统方法论的影响,在访谈中,我们习惯于将对方视作资料来源,即使一些套近乎的举动,用意也很明显,那就是获得更好的配合,以便顺利完成调查任务。而Oakley能发自内心地与受访女性建立平等亲密的感情联系,源于她对于研究本身的认识。她主张构建“为妇女的社会学”,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通过对妇女的访谈记录她们的生活,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研究者的角色从“为研究者搜集资料”转到“为被研究者搜集资料”。这是研究立场和目的的一个根本转变。
只有真正将“为被研究者提供发出声音的机会”作为自己的研究使命,放弃“研究者本位”,访谈时才可能做到从被访者出发,用心与她们交流。
(二)女性的社会性别是否超越一切
在Oakley看来,女性有相近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和共同的生活经历(如怀孕生子),故而可将研究关系向姐妹关系转化,从而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异。我承认作为女性的共同点,但是更加赞同,仅仅“性别”很难超越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等因素。我们可以努力放低身段,尽量向被访者的身份靠拢,但实际上,实现完全的身份认同非常困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双方只有拥有共享的文化模式,才能达到相互理解。这就是Catherine Riessman所说的“性别并不足够”(Gender is Not Enough)。[5](PP172-207)
在我国,女性之间的文化差异更为明显,建国后长期的城乡二元分隔,不仅造成了经济差异,也形成深刻的文化差异,城乡女性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相去甚远。城市女性从小接受的几乎是无性别差异培养,以本人为例,作为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女性,我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没有感受过性别歧视(甚至差异都很少),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十分顺利。而在农村,一方面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的政治宣传,一方面由于其经济特征和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很多地区,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女性地位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溺婴现象屡屡发生,女童在受教育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实地访谈中,我也感到,如果没有长期深入的接触,很难与农村贫困环境中的妇女实现身份认同。在这个时候,作为同性别的我们在沟通和理解上的方便性远不及处于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异性。
(三)访谈者的脆弱性
访谈中,双方的权利关系非常微妙,常常发生转换,研究者的脆弱性有时不亚于受访者。
访谈以至整个研究对研究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被访者则无关痛痒,如果没有行政命令,放弃回答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损失。这时,往往会出现研究者有求于被访者的情况,即使一方是大学教授,另一方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通常的社会地位在这时会发生逆转。有时约好的访谈,登门拜访时,受访者不在家,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研究者也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唯恐失去这个被访者。这种被动的反应恰恰说明了研究者的弱势地位。
访谈中,访谈者由于肩负着建立信任、营造气氛的任务,心理上并不轻松。想想研究效果主要依赖于被访者的参与度,更增加了焦虑感。但是,不管研究者心里多么没底,也要尽量显得镇静,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紧张,留下缺乏经验、能力不足的印象。因此,访谈者的“强”有时是角色的需要。
在特定情景下,被访者的脆弱也会将研究者推入到脆弱的状态。前不久,我在中原某地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访谈,一位带着儿子前来的妇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她谈到感染艾滋病后遭受的种种歧视,家庭的窘况,又谈起大儿子当初因为交不起50元学费,被迫退学,忍不住哭了起来,小儿子在旁边,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这时候,我几乎忘记访谈者的身份,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除访谈费用外,又塞给他们50元钱。访谈结束后,我几乎不能忍受看他们孤零零的背影渐渐远去。这种难受的情绪久久萦绕,我一直保留着她的电话号码,常常想起他们善良而无助的眼神。
作为研究者,会接触很多社会层面,目睹社会不公平现象,而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间接地、长效地影响社会,不能直接、立时改变研究对象的状况,由此引出的心理冲突或许也是一种脆弱性。在艾滋病疫区,我接触了很多感染者,一次次感受生命的无奈,而我又能够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呢?一位七旬老妇,目睹四个子女相继离世,孙儿孙女现在都靠她养活,站在她家的院子里,看这些孩子们跑来跑去,听她絮絮叨叨地诉说家境如何困难,我感到了莫大的悲哀。
(四)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论的推广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套方法论不只适用于女性研究,而应该推广到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和被访者都不再被看作数据产生的工具,而是彼此熟知,进入对方的生活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场景。从我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解,这完全是可能的。尽管女性相比男性,存在感性、生活化等特征,适于与人“交心”,但男性并不是没有这种需要,按照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其感情表达的方面遭到压抑。当然,应该探索与男性受访者之间增进交流的有效方式,而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无疑会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