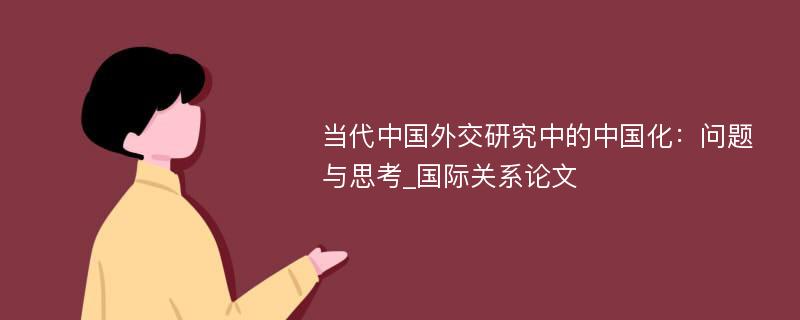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2-0001-15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从国际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了聚光灯下,中国的政治与外交日益成为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日渐从“玄学”成为“显学”。
然而,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热烈展开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讨论时,似乎仍没有把关注点投向一个基础的核心的领域,即对当代中国外交本身的研究。这个有意或无意的集体忽视,是令人遗憾的。很显然,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述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的思考。第一部分说明问题的由来;第二部分集中探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存在的学术困境;第三部分试图对如何实现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提出一些非系统的点与块的思考。这些思考来自作者多年来的教学体会,也是出于作者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学科建设的学术关怀。抛砖引玉,欢迎争鸣。
一、问题由来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成因有三:
(一)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起步晚,长期积弱,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强势的学术阵营
首先,由于冷战时期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国外交长期被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神秘的领域,因此,在建国后最初的30年间,试图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① 其次,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形成明确的外交档案解密制度,加上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外交的回忆录的出版,这些因素无疑都成为对当代中国外交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客观限制。
当然,不可否认,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国内学术界的前辈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②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中,随着各项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的改善,如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③ 外交回忆录、④ 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⑤ 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⑥ 等的系统出版,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⑦
不过,由于(下文将要分析的)种种原因,中国国内这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还没有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际学界,中国内地学者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迄今仍然非常薄弱。⑧
(二)相对于国内研究的薄弱状况,国外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不仅抢占了先机,而且经年积累,占据了强势的学术高地
如美国学界,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就对中国的政治和外交研究投入了关注。在一些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设有旨在对中国政治和外交进行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心。迄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研究队伍,⑨ 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日渐宽泛,⑩ 美国还通过不断大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11) 以及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期刊(12) 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牢牢占据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国际学术制高点。
欧洲(13) 和日本(14) 早在20世纪50年代也分别开始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关注和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出版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15) 此外,在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16)
毋庸置疑,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学术研究成就,各具特色,在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同样非常明显,如自我中心、浓厚的冷战思维,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现象的不求甚解、隔靴搔痒的解读,(17) 等等。
(三)问题生成
上述(一)(二)因素交汇,引发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严重不对称状况。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这种不对称状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我们看到,喧宾夺主之势还在日益高涨,以至于在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出现了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等方面,都统统向“洋”看齐的现象。
这种现象,从学理层面讲,已经危及当代中国外交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为,“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18) 更遑论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讲,也向国内学术界的对中国外交理论和政策的贡献能力提出了挑战,因为,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内学术界比以往更有责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理念、战略、原则、政策、实践等进行全面和透彻的研究,并用自己的思维和话语,对当代中国外交做出符合或接近事实的学理解读。
由于类似现象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学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有学者呼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19) 而本文的主张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不应继续任由其漂流在海外,为此,国内学界需要做出努力是,正视和解决问题,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主导权,都尽早回归中国。
二、问题表现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国内学界表现出的问题,具体来说,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研究起点
存在的问题是,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模糊、学科建设思路不清晰。
如果说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曾经颠覆了许多理论论断,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经典论断,即使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依然不容置疑。由此,从学理上看,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从1952年到1980年在中国内地的高校中没有设立政治学专业,因此“根据196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而在三所高校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系”,(20) 从一开始就没有中国政治学或者外交学的学科基础可以依附,(21) 这就使得,在此后出现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其学科定位的逻辑起点更加模糊不清。(22)
目前,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指导,政治学下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按照这种分类,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似乎可以被认为是一门三级学科,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二级学科的子方向发展。但问题是,单靠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这三门二级学科,是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外交研究的。不仅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科学性至今仍存有争议,还因为,教学实践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国际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实践出发,而不是从中国政治与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出发,来分析和审视当代中国外交,这种本末倒置的教学和研究思路的后果之一就是,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学生由于未能得到系统和严格的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等专业课程的训练,往往对西方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远甚于对中国外交体制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23) 甚至误以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过就是等同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24)
分析表明,在国际学术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一般被视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延伸或者衍生。国外大学里的中国外交研究专业通常是设立在政治学系,而大多数真正有造诣、有功力的中国外交研究者或外交官,其学术背景也往往是中国政治或者是中国历史。同样,在中国国内学术界,那些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的学者,也往往具有较为深厚的政治学、历史学或哲学的学术涵养或专业背景。
如果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初不是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生根,而是从国际政治研究中发芽,因而其学科设置的逻辑起点有些先天不足,那么,从1980年政治学专业重新设立至今,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应该说这为改变中国外交研究与中国政治研究的严重脱节的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学理基础。然而,令人堪忧的问题是,其一,近年来,高校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外交学学科不是在日益交融,相反,各立门户正成为趋势;其二,在更多的完全没有政治学专业的高校里,国际政治系仍在不断增建之中。(25)
(二)研究方法
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对西方流行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和教条主义运用。
无疑,在研究国际政治或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也必须要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完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思辨的过程。而由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治学方法有所不同,使得我们非常愿意了解和学习西方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并尝试运用各种新的先进的研究方法。然而,一旦陷入对某种方法论的盲目崇拜或机械地照搬某种新的研究方法,可能就难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比如,曾经在我们大力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时,唯心主义方法论被彻底打入冷宫,其结果之一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界无人触及对国家领导人的外交心理或外交行为的研究。而新的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界似乎正日益陷入另一个极端教条主义的泥沼,即在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言必称现实主义、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建构主义,(26) 以致在检索近年来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时,已经很难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字眼,相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时尚”,而建构主义则更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迅速占据中国大学、研究所、杂志社的话语阵地”。(27)
尽管,当一部分学者在向“建构主义革命”高歌喝彩时候,也确有另一部分学者开始大力呼吁要在方法论问题上“破洋立中”,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走过了引进和学习阶段,应该改变迄今由外来引进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进行方法论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不过,方法论究竟是拿来主义好、还是破旧立新好?其实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因为方法论不是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可以完整解释一切问题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也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式,先进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过时。(28) 实践表明,随着人类对自身和对世界认识的加深,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处于被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中。而最终决定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趋向的,是思想家或理论家的客观处境和主观立场,而非空穴来风,至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创新,则通常由命题本身的性质所决定。(29)
概言之,学习和借鉴各种先进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学风,但需注意的是,当我们尝试运用一种方法论来考察中国外交,或运用一种具体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外交具体问题的时候,对于这种方法论的本质或这种研究方法的原理,须兼有学术宽容和学术批判的慧眼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因教条主义式的崇拜而误导学术研究的覆辙。(30)
(三)研究资料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文献利用方面,国外学者在引经据典时,注重使用中文的一手材料,而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却往往以外文的资料作为权威的索引。于是乎,一些“进口的”或“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资料,常常大量地出现在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的注释中。
毋庸讳言,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缺席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外交回忆录出版不足,使得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中文原始资料严重稀缺,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但是,就是在同样的研究资源稀缺的情形下,美国学者Doak Barnett却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访谈、艰苦的田野调查、细致的文献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尽管书中的一些陈述和判断存在不实或偏颇之处,但该书还是被视为填补了国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的空白,长期被奉为该领域的权威扛鼎之作。
由此可见,在研究资料的问题上,进行主观反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量与中国外交密切关联的基础性原始文献,如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宪法及其修正案,党章及其修正案,历届党代会决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外交的部分,各种与外交相关的白皮书,(31)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阐述外交的文选,在不同场合关于中国外交的讲话集,中外条约文集,等等,都已经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在研究中国外交时,研读分析原始资料,迄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至于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访谈、田野调查工作和查阅原始档案的坐冷板凳的工作,虽是获得一手材料的最佳途径,但限于经费和研究习惯,国内学界有待努力的空间仍然非常大。
(四)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的意义在于,它关乎国家的外交问题意识和外交思维方式。
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议题设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们往往在自己的外交问题意识主导下,通过在不同时期提出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议题,主导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甚至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演进方向。(32)
相比之下,中国在近60年的外交实践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在各种外交场合也日益自信,但是,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迄今中国仍很少主动地为国际政治或外交关系的发展提出或设置议题,这使得中国外交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或者说,中国总是在被动地回应各种非内生的、由外部预设或强加的外交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社会提出的各种肯定中国、或批判中国、或涉及中国的议题更是层出不穷。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且倾向于对中国不友好的“激进议题”。比如,在冷战结束后,针对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相继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上,炮制和渲染“中国崩溃”、“中国威胁”、“中国责任”、“中国国际贡献”、“中国非洲新殖民”、“中国制造”等等夺人眼球的议题,试图通过这种强大的议题攻势达到“妖魔化”中国的目的。这类议题无疑对中国的理论和现实的回应能力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第二,与中国相关、但与中国外交关注重点有序位差别的“温和议题”。由西方学界或政界创制的国际议题,往往首先反映了西方各国自身的现实困境和突破困境的问题意识。虽然大部分议题往往都会以一个冠冕堂皇的概念出现,而且一些议题应该说也不悖于中国的国家利益,(33) 但由于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并非所有那些被西方发达国家在当下置于首位的议题,就一定是目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要优先去重视的议题,因此,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这些“温和议题”的挑战,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用高超的外交政治智慧和灵活而恰当的外交举措予以回应。
第三,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中,无论是理论议题还是政策议题,其实质都是具有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的。但由于在理论议题和政策议题之间有时很难明确划出界线,而且这二者很可能相互转化,因此,一些议题往往具有“暧昧”的特点。对此类“暧昧议题”,必须要准确辨别和剖析议题倡导者的真实背景和意图,(34) 分析议题导向的后台力量,把握议题发展的趋势,避免掉入陷阱。近年来,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北京共识”这个典型的“暧昧议题”的陷阱,(35) 但是,未来继续出现这类针对中国的“议题陷阱”,恐怕仍在所难免。
(五)话语体系
与中国外交研究相关的话语体系,也可分为理论话语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对此,国内学界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其一,二者混淆不清;其二,薄“中”厚“洋”。具体表现是:
第一,往往把西方提出的政策话语当成理论话语,如人权外交等。第二,对中国自己的政策话语缺乏透彻理解,甚或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生搬硬套地诠释或检讨中国的政策话语。把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公众外交”张冠李戴(36) 即为典型案例。第三,对西方理论话语盲目崇拜,缺乏批判精神。大量的论文都想当然地以西方理论中的概念和逻辑为标准,来衡量、诠释和批判中国外交,却很少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37) 第四,对中国提出的理论话语缺乏足够的自信。尤其是当中国的外交话语不符合西方的政策期望,或者在西方的理论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概念时,没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坚持己见。比如“和谐世界”一词刚出现时,因为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术语或概念,所以,国内曾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能否被国际社会认同产生疑虑。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话语的弱势状态,还有一个必须正视的外部原因,即美国主导的西方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中“话语霸权”。长期以来,美欧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在学术用语中的话语霸权垄断,主导了由外而内的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解读,不仅造成了一些话语误读,甚至出现了不少话语歪曲。(38)
(六)研究队伍
严格地说,“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除了良好的外语能力和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以外,就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而言,还需要有广博扎实的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其他相关国家的国别史)、哲学(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宗教学、国际法学、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知识结构。因为,无论是从宏观、中观,还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当代中国外交,都需要了解古今中国,了解马列,了解当代西方,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
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中国内地起步较晚,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日渐成为“显学”,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自然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的专家。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文史哲理论功底,能够继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辈们严谨治学的学风,自律自觉地将灵感、火花与脚踏实地的钻研结合起来,潜心从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七)学术成果(39)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可以发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的权威期刊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而由于外交研究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微妙性和“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期刊上的发表,因而,迄今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当代中国外交论文的中国学者,仍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军团”为主。
至于在国内学界,一方面,围绕着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是否“应该”以外文出版为最高级和是否“应该”以外语教学为最高级这一学术标准定位的问题,迄今仍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创建中国权威的外文学术期刊,以及如何提高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质量,扩大现有外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使更多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也是极为有益但仍待努力的工作。
此外,鉴于目前国内唯一以《中国外交》冠名的期刊,只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资料汇编,因此,是否有必要创设一种《中国外交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或许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如何回到中国
费正清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序言中,讲到一句研究中国问题的心得,他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40) 这句话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已成为过去的传统中国政治和外交史的解读,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解读正在发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实,正因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积弱太深,反而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当然,当我们在思考如何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回到中国时,首要的不是什么填补空白,或者去与国际学界叫板,而是要脚踏实地地从一些最基础的问题着手。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哲学、外交思想、外交体制、外交运作(实践)等各个领域都有很多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值得去潜心研究。以下就提出一些点和块的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历史与现状的关联
袁明教授曾中肯地指出:“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绝不是一种书斋中的概念的自我循环。那些著作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其根本在于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从大的方面看,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面上是一部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其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其实就是一部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的起点,或者说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各种外交理论、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其实都是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原……,只是,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的美感。”(41)
之所以大段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透彻地道出了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必须有正确的历史史观。
大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史放在整体中国外交史中来考察。因为,无论新中国的成立、建设,还是新中国政治和外交的萌芽、成长,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近代历史(1840-1949)和建国前的中共党史(1921-1949)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绝不等同于对当下一些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的研究,其跨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的外交史,包括中共在建党之后到建国之前的28年间的对外关系史,并且在探析当代中国外交理念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源,或分析一些历史遗留的外交问题如边界问题时,还完全有可能将视角向前继续延展到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甚至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中。
小的历史观,是把当代中国外交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基于一个独特的历史起点,近60年来,共和国的外交经历也非同寻常。当代中国的外交事业白手起家,外交资源从无到有,从少量到丰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以说,当代中国外交走过的每一步历程,都是波澜壮阔的当代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缩影。
概言之,只有从整体上把握好历史与现状的关联,才能够透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历程,理性把握当代中国外交的现状。
(二)外交与内政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体现在众多层面上。这里简单地谈谈二者在战略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关联。
首先,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联。一般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服务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在冷战格局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外交和内政的关联,在前30年表现为一种“外交影响内政”的非常形态。(42) 直到冷战趋缓,中国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国家发展战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后30年,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才回到了“内政决定外交”正常形态。虽然,“中国到底有没有外交战略”,迄今仍是一个经常被国际学界提及的问题,但是,在厘清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之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上就寓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比如中国倡议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和积极倡导“六方会谈”,实际上就与中国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两项外交举措实质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两大发展战略,或者说,是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最高内政在外交领域的延续。(43) 由此可见,只有正确理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之间的关联,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外交战略,并有力驳斥所谓“中国扩张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话语逻辑。
对当代中国外交体制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关联性的研究,也依然是一个相当薄弱领域。当代中国外交体制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的外交体制必须从研究当代中国宪法的演变、政治体制的演变、人大与党政军关系的演变这些角度着手。换言之,随着当代中国宪法与政治体制的跌宕起伏的演进,当代中国外交的运作体制也经历了从建国前的组织准备,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创、破坏、重建、制度创新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特征。比如眼下正在酝酿的大部制改革就意味着原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内部设置的负责本部门一些对外业务的涉外司之间需要进行大规模整合,相应的,其与外交部的协调关系也面临着重大整合。这也是内政外交在体制上联动的一个生动案例。(44)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外交与内政的关联,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另类。既然国内学界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外交体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那么在学理上,清楚梳理、准确描述建国近60年来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关联,无疑也是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最应该认真完成的课题之一。
(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无论是在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考察外交决策、运作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历来是对一国外交体制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在外交外事领域中,央地关系的形态及其关联,往往被作为考察一国政治体制民主化程度的一个视角。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分工协作,有着非常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历。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地方参与国家外交、外事活动的空间和能力空前拓展和加强,无论是沿海城市、(45) 沿边省市、(46) 内地省份还是港澳特区,(47) 都在积极以不同方式或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或承担国家的外交和外事任务。实践表明,在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在外交外事领域的协作,为丰富“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样本。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从法理层面、制度层面、运作层面对在外交外事的决策、运作中的央地关系做出梳理、分析、归纳,提炼出一套关于在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制度下的“央地关系”的独特话语解释体系,以此构建中国的“次国家行为体”外交角色的理论。
(四)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联
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对象总体上包括外交哲学、外交思想、(48) 外交体制、(49) 外交实践(50) 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可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面(51) 展开。本文认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大致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旨在探寻外交的规律,而中观层面的研究一般更倾向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故属于政策研究范畴。
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研究主要指对当代中国外交所涉及的相关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在知识体系化基础上,与其他一级学科中的相关理论和基础知识进行跨学科整合,(52) 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中国外交学科体系。基础研究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政策研究,则包括政策建言、政策反思、政策批判,等等。当然,无论是建言、反思还是批判,实证研究和实证评估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53) 而不是一个简单地从问题到建议的逻辑推断。(54)
虽然从理论上说,其实很难在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但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可以清晰界定的。(55) 在中国外交迅速发展的今天,全面的基础研究和扎实的政策研究都不可偏废,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为中国外交理论的健康生长提供优质土壤。因此,目前的政策研究门庭若市,基础研究门可罗雀的现象也是亟待改观的。
(五)与时俱进,巩固中国的话语体系
应该说,新中国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56) 并形成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外交话语体系,比如,“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安全观”、“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等等。然而,目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却面临着来自内外双重挑战,当下的任务是:
第一,既要敢于创新外交话语,同时也要敢于调整外交话语。(57) 近30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有被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也有主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58) 这表明中国外交政治智慧更加成熟,对外交话语意义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
第二,从“自言自语”的话语体系转向“对话沟通”的话语体系。从“宣言”式话语到“对话”式话语,标志着中国外交思维方式正发生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尤其是对尚处于“话语弱势”的中国来说,今后在提出中国的外交概念、政策、原则、理念时,不但要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且要在话语中包含有广义的关怀,让对方能够明白、理解和接受。(59)
第三,建立或巩固话语体系,绝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化。(60) 西方的外交话语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验,中国的外交话语也必须来自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无论是对传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的表述话语中,自然都难免带有各自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留下的印痕。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话语,就不仅将使我们失去对西方外交话语的局限性及其实质进行理性批判的能力,还容易使中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话语思维的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在建立话语体系时,“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61)
最后,从狭义的外交语言角度看,汉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定外交地位,所以,努力巩固和提升汉语在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国际会议、国际交流中,若以中国外交为主题,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会议或进行的交流活动,要逐步提出工作语言的双语使用。(62) 这一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有关中国外交相关词汇的翻译,也要掌握中译英的主动权。(63) 至于一些具有特定中国政治文化内涵的词汇,即使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翻译,现在也有必要纠正一些不贴切的译法。(64)
(六)研读当代中国外交的原始文献和经典文献
读经典文献,包括读中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三者不可偏废。这其中,读中国的经典是核心,包括古代、近代和当代的经典外交文献。每一类经典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筛选。读原始文献,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就是要研读宪法、党章、历届党代会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档案,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项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提出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读经典文献和原始文献,旨在探寻特定外交话语所由产生的真实语境,这是正确解读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理念真实含义的学术正途。忽视原始文献或对经典断章取义,往往导致对中国外交的误解甚至歪曲。例如对“和谐世界”目前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学理解读,(65) 究竟哪一种解读更符合这一外交话语的确切含义,恐怕还得找到这个话语的原始出处。
四、结语
什么是“本土化”、“中国化”?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振兴中华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不断求索的梦想,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外交的使命是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国民利益,服务世界和平。实践表明,当代中国近60年的外交努力,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而生动的研究样本。既然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说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主导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呢?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本土化”或称“中国化”问题,本文思考的基本结论是: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只有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首先投向当代中国外交的现实样本,才能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才能为最终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奠定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最终改变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理”未必屈而“词”穷的被动局面。(66)
收稿日期:2008年1月
注释:
① 冷战时期,全球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下,各国外交都被神秘化,在那样的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也笼罩着神秘的气氛。1978年以前,国家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实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例如,现在中国发射卫星、发射神州6号,等等,都是提前预告的,但是在1973年6月,中国成功爆炸氢弹,有关消息,是在2天之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而当时在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只能根据(西北地区)所有飞机航班取消的现象,来判断有大事在发生。再比如,现在开全国人大、政协、党代会等也都是提前预告的。这样,其他国家一般也不会在三会会议期间提出重要来访的要求。但在30年前的1973年8月24日至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高度保密的,这个消息也是在会议闭幕2天后才见诸于8月30日的《人民日报》。外界都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在忙着开会,结果给外交工作造成很多不便。比如,在这次秘密的党代会期间,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因要回国述职并讨论基辛格10月访华的事情,希望在回国前拜见周恩来和乔冠华。他通过副外长提出请求,但结果却石沉大海,以至于他怀疑,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所改变。后来他虽然明白了其中原因,但仍很难理解中国政治的这种高度的神秘性。事例参见徐珏:“70年代的中国外交体制和风格——戴维·布鲁斯的驻华印象”,载肖佳灵、唐贤兴主编:《大国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比如,外交学院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教材,此后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中国内地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教材。这本以编年史为体例的教材,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
③ 1998年开始,外交部档案馆开始了解密开放档案工作,并在1999年成立了外交档案鉴定开放领导小组。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明确公布了《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随后,首批开放了外交部1949-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9997卷中的3000多卷共1万多份文件,占全部档案的30%左右。第二批外交部1956-1960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于2006年5月10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本批开放的档案共25651件,366551页。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的外交工作透明化正在与国际通行惯例靠拢,也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有了实质进步。
④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首次披露了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时曾出现意见分歧的一些情况,当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1983年伍修权出版了外交回忆录。此后,外交回忆录出版沉寂了近10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在建国50年前后,出版了一批外交部副部长级以上官员的回忆录,如钱其琛、耿飚、冀朝铸、韩叙、熊向晖、黄华等。虽然,对于迄今已出版的约50种的各类外交回忆录的学术价值,学界仍有争论,但毕竟,它们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留给学术研究的一笔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⑤ 如《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⑥ 如外交部主编:《中国外交》,1983-2006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主编:《世界知识年鉴》,1982-2006年,各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编:《国际形势年鉴》,1983-2006年,各卷,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⑦ 如关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研究有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当代中国外交体制研究有张历历:《外交决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研究有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有关冷战史与中国外交领域,资中筠、牛军、沈志华和朱明权等学者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⑧ 迄今只有王缉思、吴心伯等为数不多的中国内地学者在与中国外交相关的英文权威期刊或有影响力的英文专著中,发表了相关论文。
⑨ 根据David Shambaugh在2006年的统计,目前美国已经大致形成了注重研究中国外交和注重研究中国安全这样两个团队,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美国高校和智囊机构及基金会两个领域。其中在高校从事中国外交研究的著名学者,从东部向西部有:Alastair I.Johnston(Harvard); Robert Ross(Boston College); Taylor Fravel (MIT); Samuel Kim (Columbia); Allen Carlson (Cornell); Avery Goldstein (Pennsylvania); Thomas Christensen (Princeton); Andrew Scobell (U.S.Army War College); Wang Hongying (Syracuse); Hat Yufan (Colgate); David Lampton (Johns Hopkins); Robert Sutter (Georgetown); Nancy Bernkopf Tucker (Georgetown); Margaret Pearson (Maryland); Shu Guang Zhang (Maryland); Warren Cohen (Maryland-Baltimore County); David Shambaugh (George Washington); Harry Harding (George Washington); Michael Yahuda (George Washington); Phillip Saunder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Yong Deng (U.S.Naval Academy); Li Hongshan (Kent State); Quansheng Zhao (American); Liu Guoli (Charleston); Wang Fei-ling (Georgia Tech); Wang Jianwei (Wisconsin-Steven's Point); Ming Wan (George Mason); Chen Jian (Cornell); Qiang Zhai (Auburn); Yu Bin (Wittenberg); Thomas Moore (Cincinnati); June Dreyer (Miamin); Kenneth Liberthal (Michigan); Ed Friedman (Wisconsin); Suisheng Zhao (Denver); Peter Hayes Gries (Colorado); Li Xiaobing (Central Oklahoma); Allen Whiting (Arizona); Susan Shirk (California-San Diego); Lowell Dittmer (California-Berkley); and Mel Gurtov (Portland State).在智囊机构也有一些专家从事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其中包括在华盛顿地区的Michael Swain and Minxin Pei (Carnegie Endowment); Alan Romberg (Henry L.Center); Richard Bush,Jing Huang,and Jeffrey Bad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Nicholas Lard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ates Gill,Bonnie Glaser,Kurt Campell,and Derek Mitchell (CSIS); Banning Garrett (Atlantic Council); Ted Galen Carpenter (Cato Institute); Roy Kamphause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ohn Tkacik and Peter Brookes (Heritage Foundation); Dan Bulmenth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David M.Lampton (Nixon Center); Evan Medeiros (Rand); and David Finkelstein (CAN corporation)和华盛顿地区以外的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New York),Jing-dong Yuan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nd Danny Roy (Center for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Studies in Honolulu).
⑩ 在20世纪50、60年代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中的传统、历史、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因素;70年代着重研究战略三角和党内斗争因素与中国外交;80年代,关注制度、观念和行为因素的变化;90年代以降,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进入大调整和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关注点如中国崛起、中共外交政策史、中国与冷战史、外交决策、中国的国际事务的观念尤其是对美国观念、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作用、中国的双边和地区关系,等等。进入21世纪,中国外交更加成为研究焦点,在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于2006年合编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新时期对中国外交与安全研究的20个新视点。
(11) 限于篇幅,此处无法一一列举,部分可参见David Shambaugh,“A 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Appendix,pp.603-617; Robert G.Sutter,“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and Perils,La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5,Appendix,pp.281-287.
(12) 有影响力的期刊包括Foreign Affairs,Foreign Policy,The National Interest,an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等。
(13) 欧洲在20世纪50到60年代,主要是少数的传统汉学家和新闻记者关注中国外交的进程;70年代以后,随着中欧建交国家的增多,一些政治家和基金会也开始研究中国外交;8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一些著名大学和智囊机构相继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到90年代,在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从欧盟委员会到私人跨国公司、大学研究人员和教授、智囊机构等各类组织组成的从地区到国别的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网络。
(14) 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一直具有高度的传承性,从高校到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研究梯队。其中已经出版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著作的著名学者有毛里和子、天儿慧、冈部达味、国分良成、小岛朋之、田中明彦等,新一代学者有青山瑠妙等。
(15) 如China Quarterly等。
(16) 详见Robert G.Sutter,“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 and Perils,Appendix,pp.281-287.
(17) 仅举一例说明。笔者2000年在东京大学旁听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政治与外交”,一次,教授曾给学生播放一张1999年中国建国50年国庆阅兵式上“女子民兵方块队”行进的幻灯片,教授向学生提了一个设问句:知道什么是“女子民兵”吗?女子民兵平日就是商店里的普通女营业员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普通农妇。课后,有学生来问笔者,是否中国全民皆兵?至于在学术论文中,类似“尼克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如同古代朝贡使者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之类的判断,可以说不胜枚举。
(18) 笔者在两年前曾就“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相兰欣教授交换过看法。相兰欣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9) 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年版。
(20)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1) 对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理论基础,更无自身特色。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年版。
(22) 1964年建立国际政治系时,三校分工的侧重点分别是:北京大学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人民大学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和世界经济。当时,三校国际政治系都没有研究中国外交的任务,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仅限于外交学院。外交学院曾于1964年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4)”的课程,但当时只是出了内部版的讲义。之后,直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则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陆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两门课程。
(23) 笔者对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多次课堂摸底测试的结果表明,学生们大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国务卿的名字,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却鲜有能够完全答对的。
(24)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讨论课上,凡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思想、体制等议题,发言者寥寥,而有关当代中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实践的专题,发言者踊跃。
(25)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国内已有近70个高校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系。
(26) 仅从中国国内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论文来看,近年来已遍及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且在政策建议里明确涉及对日思维、伙伴关系、和平崛起等战略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建构主义”,应“将建构主义为切入点重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52页。
(27) 有学者统计,单就论文发表一项,近几年国内的建构主义相关论文,已接近美国近10年同项作品数量的总和。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48页。
(28) 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18世纪的理性主义、19世纪的历史主义、20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但经典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在21世纪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见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辑,编前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9) 一个问题往往或为价值性命题或为实证性命题,当一个问题兼具价值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的特征时,用什么研究方法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理论指向还是政策指向。
(3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备受国内部分学者推崇的“建构主义”在其所由产生的西方学界内部其实已经遭到了严厉批判,如肯尼思·沃尔兹就提出,建构主义根本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它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8页。
(31) 截至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发行出版各类白皮书24种,其中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包括国防白皮书、人权白皮书、宗教白皮书等等。
(32) 如“邪恶轴心”议题,最终导向了“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失败国家”议题,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而所谓“民主和平论”议题,则不仅为冷战思维的合理化延续,而且为一些国家试图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军事同盟”等提供了理论口实。
(33) 比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减少温室排放”,等等。
(34) 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倡导者可能是政府、学者、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
(35) 林立民认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担心中国与美国争夺软实力,仍有“中国威胁论”在内(《瞭望》2007年第42期);郑永年认为,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来看,拒绝“北京共识”,有先见之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7月24日)。
(36)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 diplomacy)。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对海外各国公众的外交(如驻中国外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有责任向驻在国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的国情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各省市政府主导建立对等的友好姐妹省、友好城市等;2003年国务院设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沟通交流,主持海外文化年等各类人民外交活动,等等)和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交流(如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等)。“人民外交”虽然不是一项中国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外事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早已有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学术术语,最早是美国学者在1965年提出。其时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实践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通过VOA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双重特性,其职能之一就是由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外交”方式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草根发动影响,进行“和平演变”。
可见,中国的“人民外交”与西方的“公共外交”,虽然在外交对象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内容、形式、手段、性质上是有实质区别的。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对国家外交的关注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于2003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设置了“公共关系处”,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国内民众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国外交中首次出现了“公众外交”一词。但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公众外交”,其对象是本国公民,而不是针对外国公众,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在中国外交体制中,针对外国公众的“人民外交”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而针对本国公民的“公众外交”由外交部新闻司负责;而在美国,针对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而针对国内公民的外交解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与国务院无关。
然而,遗憾的是,在2003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关系处”之后,国内立即就有学者想当然地从字面上把中国的“公众外交”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一词挂起钩来,并开始运用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机械地诠释中国的“公众外交”,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公众外交”不仅对象有问题,运作逻辑也有问题,中国完全不懂公共外交,应该以美国的“公共外交”为蓝本,参照改进,等等。
孰不知,正是一些学者对中国外交部增设“公共关系处”的一知半解,混淆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和美国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正确的理解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人民外交”相对应,而中国的“公众外交”若放在美国,则属于公共行政而非外交范畴。
令人堪忧的是,这一张冠李戴引起的混淆,至今仍未澄清。很多学生对“公共外交”概念至今仍很糊涂,以至于试图写研究中国“公众外交”的文章,却要先引用一段美国的“公共外交”的理论。甚至,国内有些官员也放弃了使用“人民外交”概念,开始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对海外他国公众的外交。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适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38)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其原意是“要低调,不当头”(keep a low profile),但在西方的媒体和政策报告中,这一成语往往被译成了“隐藏真实意图”(hide your real intentions under your wings)。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1世纪初,“和平崛起”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正确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peaceful-rise,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国际会议或西方的媒体、学术杂志上,往往省略了前面的peaceful,只剩下了rise,这在字面上就已经扭曲了“和平崛起”这个外交政策话语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
(39) 这个问题虽然突出,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成果标准化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故此处不多赘述。
(40)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41) 袁明,总序,见[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2) 如中国因“抗美援朝”而不得不中止了解放台湾的计划;因“反帝反修,备战备荒”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则使中国从1963-1980年的4个五年计划,都具有浓厚的战备计划经济的特征。
(43)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关联,可以从时间序列角度得到清晰解读。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能源进口国,安全开发和运送西部能源成为当务之急,而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石油,需要投入巨资铺设管道。为确保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的安全,1996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要旨的“上海五国”,2000年中央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西部大开发”计划,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打击三股势力依然是核心宗旨。同样,从时间的序列上,完全可以找到对“六方会谈”与东北振兴战略之间关联性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44)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14个部委。而在目前国务院的28个部委中大都设有涉外司(局)。在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原有的涉外司必然进行功能性合并,因此,外交部与之协调的机构也必然面临相应调整。
(45) 如以上海市外办为例,截至2007年,上海共有62个总领馆(占全国领馆120多家的一半);名誉领馆5家;境外媒体88家,150多人;友好城市70个(自1973年横滨开始);全年举办国际会议200多场次;常驻外宾,可查的在11万到20万;外企4万多家。
(46) 如中国云南腾冲与缅甸有悠久的民间往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对外交往之一,但二战后基本停滞。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腾冲县政府以侨搭桥,在1992年与缅甸7个部的部长在甘稗地签署了翻修腾密国际公路的协议,1993年5月建成通车。2003年重新修路谈判开始后,缅甸的总理、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表示积极支持。2004年腾冲县政府再次与缅甸密支那政府达成协议,投资5亿8千万重修这条路,2007年4月,腾密公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个不大的边境县以民间方式与另一个国家沟通,主导一条国际公路的修建,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腾冲县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人民军、独立军三个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路修建中也得到缅甸各方政府的通力合作。腾密国际公路的成功合作,可谓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一个民间对外交往的奇迹。详见孙敏:“腾密公路——前往密支那的道路”,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8月,总第562期,第117-131页。
(47) 如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
(48) 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政策等。
(49) 包括决策体制、运作体制、辅助体制等。
(50) 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
(51) 其中宏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外交,把外交理解为内政的延续。据此,战争也被认为是外交的范畴。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即外交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中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阐述外交,认为外交是除战争以外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原则、政策、手段等。其核心概念是秩序和利益,即外交是一种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微观层面的外交,主要是从外交学层面阐述外交,强调外交是专业人员从事的专门工作,包括谈判、斡旋、外交官、外交机构、外交规范等。其核心概念是技巧,即外交是展现国家政治智慧的一门艺术,是职业外交官纵横捭阖的创造出来的一幅图画。
(52) 如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53) 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研究的范例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实现向联合国进军的目标,日本人事厅组织日本高校学者在1983年提出了一份《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该建议厚达200多页,其中详细研究了国际组织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合日本争取的各类职位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政策建议。此后,日本成功地相继推出了绪方贞子、明石康、植木安宏等一批优秀的国际组织高级官员。
(54)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论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省,如认为中国应该抛弃韬光养晦,不必固守不结盟概念,少提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但是,这些建言多为三言两语式的观点和推论,而无实质的政策批判的逻辑和实证。比如,众所周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语言始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而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相继瓦解,西方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垮台。在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情势时,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16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的初衷是告诫外交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冷静和低调,不做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如果学者提出对这一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就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论证。
(55) 高校的学者通常具有基础研究的优势,而研究所和智库需要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故无论是学者在高校讲坛上剖析反省批判政策,还是研究员在政策建议中使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都需要格外慎重。
(56) 如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的话语体系转换等。
(57) 笔者赞同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话语的理性回归。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和平发展”更符合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还有众多的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国际社会看,以日本为参照。战后日本在1968年GDP已位于世界第三,但正因为成功地韬光养晦,才真正实现了今天的富国强兵。即使如此,日本到目前也只提出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提作一个“崛起的国家”。这其中,就体现了一种外交话语的使用技巧。虽然,“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回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个外交话语,但一个国家是否崛起,以什么方式崛起,是以事实来表明和检验的。因此,在西方转而妖魔化“崛起”一词的含义时,中国明智地逐步将“和平崛起”这样一个极易被误解、被歪曲的词汇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淡化出去,回归到“和平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在选择外交话语时,也已日趋成熟和稳健。
(58) 如被动地提出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但在主动淡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又主动提出了“新安全观”、“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战略”、“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话语。
(59) 既往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原则话语的成功提出,迄今,这一外交原则话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60) 一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而把中国外交的问题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解释,就等于完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61) “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参见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
(62) 西方的第1代到第2代“汉学家”一般都曾在中国内地习得中文,能阅读古汉语;第3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多数在港台地区学习中文,但还是能阅读《毛泽东选集》等汉语原版;而第4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没有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虽能用汉语交谈,但精通中国国学者已为数不多。由此可见,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程度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各国“中国问题专家”正确解读中国外交的障碍之一。
(63) 例如赵启正指出,“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和运气的象征,与西方dragon有很大的不同,外形就非常不同,dragon在西方是有负面的隐意的,因此,中国的“龙”应该翻译成loong。同样,京剧译成Peking Opera从译名上就白白丢失了中国特征,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其他的资深辞书家,都认为应该译成Jingju更为合理。参见赵启正:“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
(64) 比如朝贡体系,一般翻译成tributary system,但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Chaogong system。因为,中国传统外交中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而是具有“薄来厚往”的特定含义。
(65) 一种解读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明中国外交从理论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是要用儒家的和谐文化造福13亿中国人,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此外,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还可以为“韬光养晦”画上句号。另一种解读反驳前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其核心价值,与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包括荣辱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也不同,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得到历史的借鉴,但绝不能在核心价值体系上丢掉自己的根本,不能搞历史的错位。回归儒家文化之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否定。
(66) 参见相兰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年第12期,第3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