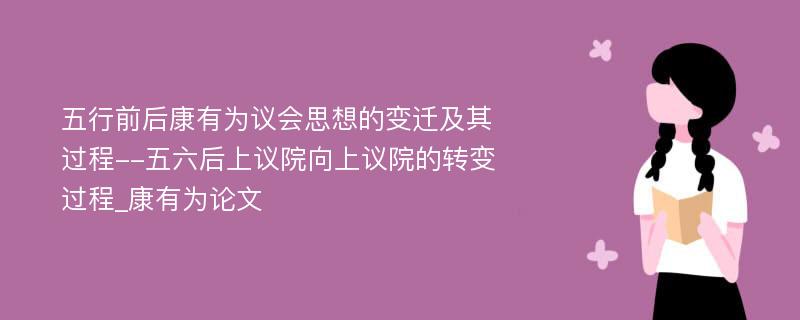
戊戌前后康有为议会思想的转变及其过程——以《第五书》和《第六书》之后从上下院到上议院的转变过程为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议院论文,下院论文,过程论文,议会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7)-04-0037-14
一、序言
在1895-1898年期间的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议会体系的有关问题提出以改革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维新派政治主张和要求。然而,上述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随着他个人身份的变化与光绪帝对维新变法支持与否以及当时客观政治环境的变化,康氏议会思想的形式和内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有时甚至变化显著。尤其是1898年前后,从《上清帝第五书》(以下简称《第五书》)之前的上下两院制到《上清帝第六书》(以下简称《第六书》)之后的上议院(“制度局”)一院制的重心转移正好反映出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和倾向。换言之,在《第五书》以前,上下两院制的议会思想,尤其是下议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与此不同,在《第六书》及其后奏议中,康有为不再建议《公车上书》和《第三书》中所论及的立即开民选下院(“十万户而举一人”①),也不再请求《上清帝第四书》(以下简称《第四书》)中建议的民选“征士”进入上院(“取于公推”②),并不再要求《第五书》中建议的“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和“定宪法公私之分”③,而代之以具有上院性质的制度局。较之《第五书》以前,其显然旨在进一步加强君权,而对君权的限制与挑战根本无从谈起。
康氏议会思想为何有上述转变?即康有为议会思想的重点究竟何时从上下院两院制转向上院一院制?其转变过程又是如何?其转变是否意味康氏完全放弃开设议会的理想,还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策略的让步和妥协?以上诸问题不解决,对于戊戌前后康氏议会思想转变的讨论将很难进一步深入。笔者对上述诸问题将做出较为圆满的回答,这是本文研究之所在。
以往,就1898年前后康有为从上下两院制到上议院(“制度局”)一院制的转变原因及其过程,曾引起史学界的众多关注。这缘于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政治路线转变、百日维新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保国会的活动,都同康氏议会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围绕上述问题,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康氏议会思想转变的原因、时机和过程以及康氏被召见之后有关“开国会”时间表等问题仍留有讨论余地④。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力图对康氏变法思想从上下议院转向上议院的主要原因、过程及其意义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辨析。
二、加强君权和让步民选下院
《第五书》和《第六书》都是在1897年末“胶州湾”事件后民族矛盾凸现的客观背景之下写成。两书相隔虽然仅五十余天,但在所主张的议会形式等方面却各自截然不同。当时的客观背景确实对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具有一定影响,而真正促使康有为不再请求立即开民选下院、民选上院的重要原因应该与康有为“被荐召对”和总署“询问”等事件有直接关连⑤,具有上院性质的“制度局”的雏形⑥大概就是在“被荐召对”和总署“询问”时期提出的。
至于康有为政治倾向转变的具体时期,我们可以从王照与犬养毅的笔谈中找到一些线索。王照是戊戌维新的当事人,在百日维新期间与康氏关系密切,所述当为可信。王照曾言:“及丁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变于下者,即立会之谓也。照以为意主开风气,即是同志。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⑦如前所述,康有为早先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与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制同时进行的政治策略。但在王照的记述里,却仅反映出康有为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思想,而没有明确提及康有为在奏折中曾建议的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据此,王照与犬养毅的笔谈尚不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对康有为两条路线的把握更为准确。梁氏认为:“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⑧暂且撇开康氏的民选下院路线不谈,在此只谈一谈康氏表现在奏折中的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转变的过程,即梁启超所言之“上书求变法于上”。
在“被荐召对”之前的奏折中,康有为坚持其开上下两院的主张,其中开下议院的建议占主导地位,即通过取得群众团体支持来推动君主立宪。但在“被荐召对”之后,康有为一改原来“变于下”的态度,转而提出“上书求变法于上”,主张以具有上院性质的制度局来代替下议院,即开制度局以推行讨论制度与制定宪法。“被荐召对”⑨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当时给事中高燮曾向皇帝推荐康有为,并建议皇帝赐其“特予召对”。这一时间大致与康有为将《第五书》递交给工部的时间相同,也与王照所称的“丁酉冬”相吻合。但是在王照的记述中没有涉及“特予召对”后改为总署“传询”等细节。而梁启超却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谈及此事:“皇上不得已,(戊戌)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⑩张荫桓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他说:“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恭邸建议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略)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众曰:诺。此年前冬(1897年)间事也。”(11)这是1897年12月12日的事情。此后光绪帝命“总署酌核办理”(12)。若此,康有为可否破例被光绪帝召见主要视康有为被总署传询时的表现而定。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二日(1898年1月23日)(13)接到总署大臣传询的通知。次日,康有为参加了总署大臣传询,力陈开制度局和制定宪法等的合理性。翁同龢、张荫桓对此事都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张氏说:“余与荣相(即荣禄)续出,晤长素(即康有为)高论。”(14)翁氏的记载比张氏更具体一些,他说:“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15)两人记载详略之所以不同,主要因为张荫桓当天有“西堂料理问答”的公务(16),提前离开总署,“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17)与此不同,张、荣两人离开后,翁同龢、李鸿章和廖寿恒等三人继续询问,“昏乃散”(18)。从康有为的回忆和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康有为议会思想的重心这时候已开始转向上议院(“制度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材料的共同点都在强调“变法”,只是翁同龢所称的“以变法为主”的“变法”实际上等同于《康有为年谱》中的“变法律”(19)。即这一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既不是康氏在《第五书》以前一贯主张的“民词”、“谋及庶人”、“辟门”、“许天下言事”以及“求天下上书”等下院的受理请愿权,也不是下院对“筹款”或赋税的财政权,而是与《第五书》所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上议院的立法职权密切相关的“变法”、“变法律”等宪法问题。与此同时,康有为重提《第五书》“变法三策”中的“上策”所论及的《日本变政考》一书,再三强调应仿效日本变法,说:“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20)。这表明康氏已将其关注重心转移至制定宪法的上院机构,而对以公民的请愿权和选举权为主的民选下院制度的实施做出让步。不过,康有为在总署传询时,并没有涉及具体制定宪法主管单位和成员及其议事程序等重大问题。这种具体提议主要表现于康氏《第六书》及其后有关制度局的奏折中。
总署传询这一天的话题并非完全照事先安排进行。初意,总署询问只应围绕“弭兵会”和“召见”等话题展开。然而从《翁同龢日记》和《康有为年谱》来看,这一天的谈话内容显然离题很远,从原来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外交话题转向“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或“以变法为主”等内政话题。《第六书》的王大臣《据呈代奏折》对传询走题的原因做了解释,认为:“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21)由此可见,传询之前,总理衙门内部对于传询康有为的内容存有异议。这大概与奕訢、翁同龢两人就政治倾向方面截然不同有关。就在总署传询的八天前,光绪帝曾询问过“变法”。翁同龢事后在其日记中写道:“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翁同龢)谓从内政根本起。”(22)由此不难判断,传询话题的转向实由翁同龢导演。不过,康有为虽然藉传询得到展示其维新变法蓝图的机会,但其被光绪帝召见的愿望却未能立即实现,这使他感到沮丧。
几天后,在翁同龢的周旋下,康有为得到了“令条陈所见并进呈”(23)的绝好机会。这件事对康有为个人来说无疑是个极大鼓舞,尽管尚未得到召见的任何承诺。总署大臣传询之后,康有为曾对自己的前途有所预测:“或加五品卿衔入军机,或设参议(行)走。”(24)时人张元济、叶德辉等人在其书信中对此事有所记载。叶氏说“朝传一电报曰: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2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康有为所称的“参议”可以与《第六书》中所提及的制度局“参议”成员相呼应,即“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26)既然已经得到上奏的特权并获悉光绪帝有“急欲变法”(27)的情形,康有为便不再请求立即开民选下院,也不再考虑民选“征士”进入上院等激进主张。正是因为康有为内心发生了上述变化,所以在正月初八日(1月29日)应召进呈的《第六书》中,他不再提及民选下院和民选征土进入上院等问题,并导入日本制度局概念。换句话说,康有为此刻提出的诸上院职权和制定宪法程序都不再触及对君权的否定抑或挑战,而只停留在与军机处等行政机构相分离的准权力范围内。这些可以构成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反对立即开民选议会,而代之以成立上院化的制度局及其称谓不一的诸上院机构的直接原因,也可以说光绪帝和翁同龢对其变法主张的认可是其政治主张转变的重要原因。
三、受理请愿权归属的转变
在翁同龢的周旋下,康有为虽然得到了可以上奏的特权,但这并不等于得到了召见的承诺,而被光绪帝召见是其最终目的。此后康氏主要围绕“召见”一事展开活动。
在《第六书》中,康有为首次使用“变法之纲领”,提出了三项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其中第二项开设制度局的建议与康氏制定宪法的立宪思想密切相关。(28)在此只略谈第三条政治纲领,即“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29)。以往,研究者们对此条纲领多不够关注。实际上《第六书》的第三条纲领是自《公车上书》以来康氏所贯穿始终的唯一政治纲领。从《公车上书》到《第五书》,康有为所称的“民词”、“谋及庶人”、“辟门”、“许天下言事”和“求言广听”以及“求天下上书”等上书权始终都与民选下院的职权连在一起。然而到了《第六书》,康有为突然改变原来的制度安排,把以往属于民选下院的受理请愿权(“上书权”)并入制度局的职权当中。即《第二书》中的“民词”、“谋及庶人”和“国人之皆曰”都属于与“辟门”相关的负责受理公民请愿的下院职权范围(30),而在《第四书》中康氏把它们以上书的形式固定化(31)。不过与《第二书》不同的是,《第四书》把上书的程序分为下院(“开门集议”)的“三占从二”的议决权与上院(“辟馆顾问”)的“条陈可采,召对称旨”这两部分。据此,无论《第二书》还是《第四书》、《第五书》,公民向下院提出的上书总是与民选下院的职权连在一起。
然而在《第六书》,康有为却对此进行大幅度修改。如果将《第四书》的第一项、第三项纲领和《第六书》中的第三项纲领做一比较,便能察觉《第四书》与《第六书》在制度安排上的不同。
《第四书》:一曰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嘉,或令召对,霁颜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三曰辟馆顾问……一取于上书。其条陈可采,召对称旨者,与荐举人并称待诏,亦令轮值(32)。
《第六书》: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33)
由此可见,康有为所谓“辟门明目”指的是民选下院。正如他所说:“《传》言文王与国人交,《洪范》云谋及庶人,虞廷之明目达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会大众,凡此皆民选议院之开端也。”(34)既然“辟门”是民选下院,那么“许天下言事”的上书就必须通过民选下院的“三占从二”进行议决。然而《第六书》却取消了民选下院的议决权,代之以由制度局“议之”。《第六书》的后半部实际上重复了《第四书》上议院(“辟馆顾问”)的“取于上书”;《第六书》的“参议”也等同于《第四书》上议院“轮值”的“顾问之员”(35)。原来上下院所管辖的或下院所管辖的“上书”等受理公民请愿权的归属在《第六书》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六书》中的“天下人上书”已经不再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也不再是下院的受理请愿权,而上院化制度局的“参议”成员也无需像《第五书》以前那样要顾虑公民的眼色和诉求。因为上议院的“参议”成员的命运已不再取决于公民的选举权,而要取决于君主的“称旨”和“擢用”。由此,《第六书》表明康有为已经开始对此前公民的选举权和请愿权以及下院的相关职权等硬性政治问题做出妥协,最终以君主敕选的“制度局”取而代之。
上述变化固然是康有为对其议会原则所做的消极性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妥协。但我们不能据此忽视他将“许天下人上书”的上书权并入制度局职权这一“妥协”背后所具有的积极因素。按照康有为对于制度局的构想,它的职权取代了清朝都察院和各级行政代奏机构的职权,凡“天下人上书,皆与传达”,由“制度局议之”。这种上行文书制度的重大改革无论是对开明的光绪帝还是对维新派来说都有利。就光绪帝而言,以往在许多情况下,地方督抚和中央都察院以及中央堂官出于个人考虑,将没有上奏权的地方、中央行政长官的上书以及士民上书隐瞒不报,或大事化小,使得光绪帝无法阅览一切奏折,这显然不利于康有为与光绪帝间的沟通,并影响到改革的推进。然而在康有为新设计的制度局职权下,光绪帝的君权可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即对一切上书奏报,皇帝皆能“乾纲独揽”(36)。所以,制度局的设立不仅能满足维新派“许天下人上书”的心愿,亦对光绪帝非常有利。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代奏制度下,士民和司员等因上书困难,几乎无从获得直接与君主沟通的机会,更谈不上“称旨召见”。到了这一时期,这些陈旧的代奏制度不仅已成为司员、士民向最高统治者表达民意的障碍,而且也成为康有为等维新派接近光绪帝的重要阻力。因此维新派人士必须改变以往代奏机构的上行文书制度。在康有为的重大修改之下,新的文书制度破除了代奏机构的束缚和限制,一旦为光绪帝采纳,就会打开司员、士民直接与光绪帝沟通的渠道,即意味他们可获得以往只有四品官以上官员才能具有的上书机会。尤其对争取光绪帝召见感到可望不可及的康有为来说,《第六书》中的“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擢入制度局参议”的制度安排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尽管它的积极意义不能与《第五书》以前标榜的公民请愿权和下院的相关职权相匹敌。上述建议反映出康有为的身份变化以及愿望影响其政治主张。
四、以公民选举权作为妥协和让步的对象
“民智未开”是保国会解散之后促使康有为不再请求立即开民选议院的重要理由,也是康有为在思想认识上有别于其他维新派的特点所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先进人士对公民权利(民权)概念鲜有讨论。他们虽然论及“下议院议员则皆由民间公举”、“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37)以及“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但他们并没有正面阐述公民的选举权与传统君主的任免权之间所存在的张力。这一问题(公民选举权与君主的黜陟权、议会职权之间的张力)直到1896年以后维新派才开始有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并未把公民的选举权看做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念,同时,公民选举制度也并非他们所极力追求的政治制度。在他们眼中这种制度的具体内容可以随公民总体素质(即“民智”)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他们几乎把公民选举权看做妥协、让步的对象,虽然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这是戊戌维新派的一大特点。戊戌维新派以“民智未开”为理由反对立即开议院实际上反映了这种心态。当然,不能就此说明戊戌维新派不如早期维新派高明,毕竟早期维新派对公民选举权与君权之间的张力关系从来没有进行过正面思考,他们只是孤立、分散地探讨民选方式与议会对行政命令的监督权等方面之间的关系。
最早认识到公民选举权与议院之间存在权力紧张关系的,可以追溯到严复和梁启超。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中提出了“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38)的政治主张。但是他所主张的“设议院于京师”并非从公民选举权的立场出发。在1898年初谈到君权与公民选举权(“民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严复以“民智未开”为理由反对立即开“议院”。他说:“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39)梁启超亦因受严复的影响而以民智未开为理由反对立即开议院,即:“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40)严、梁两人虽然没有直接探讨选举权,但是从他们所说的“议院”中不难推出,公民选举权受制于“民智”的程度,而与议院有关的公民政治权利只有选举权。
饶有兴趣的是,他们一方面根据自己所吸收的西方议会制度理论于1896年以前提出开议院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却依据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教化思想来反对立即实行议院之制。这种教化思想成为支撑他们“开民智”的强大理论根据。实际上,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和建立议会制度之初,西方人士对公民素质的认识并非像戊戌维新派那样具有随意性,他们所说的“启蒙”也不把公民看做通过别人或政府引导才能开启理性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能够自我排除偏见与愚昧的理性主体(41)。与此相反,维新派并不把公民看做自觉理性的主体,而是始终视其为由士人阶层和君主教化与引导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的根本弱点。这种对公民素质认识的随意性标准最终导致他们的认识呈现出如下两种趋势:一是强化君权。当他们认为“民智”尚未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程度时,其思想就有可能向强化君权的方向发展。这从1896梁启超在《古议院考》里的有关论述中就可看到,即:“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42);二是致力于先开民智。通过“学会”等具有传统意义的教化方式,来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为将来实行君主立宪打基础。这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维新派大量创办或看重各种“学会”等。
与其他维新派不同,康有为对公民选举权和民选下院等敏感问题的处理有其独到之处。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觐见光绪帝之前,康有为一直没有将公民选举权、民选议院与“民智未开”连在一起思考(43),这是他有别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一大特点。如前所述,他的政治取向往往取决于光绪帝对其上书的态度和对其仕途的影响程度。因此,光绪帝对康有为上书的认可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终转变为依靠君权实现自上而下变法的决定性因素。对康有为的开明君主路线在前面已有论述,此处只就康有为的民选议院路线进行必要的探讨。
关于民选议院路线,康有为在后来的文章和给友人的书信中道破了他在《第六书》之后在保国会活动中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在1902年春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一文中,他说:“昔戊戌之时,吾开保皇会(应该改为保国会)于京师,合京朝士夫及各省举人为之,首言民权,以上无变政之心,则当由下变之,由下迫之。”(44)1901年在给友人书信中,康氏同样披露了在《第四书》不能上达之后他所采取的民选议院路线,他说:“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圣人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45)在上述文字中,虽然没有涉及康有为的几次上奏活动,但其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康氏在他的学生以及其他维新派同志之间所倡导的民选议院路线。也就是说,康氏走向民选议院路线的原因并不如严复、梁启超等所主张的“开议院得民权”。光绪帝有无“变政之心”,或光绪帝是否“英明”才是他选择政治路线时所考虑的要点。对光绪帝能否赞同“变政”的判断令他面临两个政治选择:假如他确认《第六书》的第三项政治纲领(“许天下人上书”)得到光绪帝的认同并能“召见称旨”(46),其政治选择可能就是走向开明君主路线,依靠君权自上而下地进行维新事业。这类“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47)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第六书》及其后有关制度局的一连串上书和其代宋伯鲁等维新派官僚草拟的奏议中;反之,假如他感到光绪帝不理睬他的上书或无望得到光绪帝的召见,他则可能选择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走向民选议院路线。此类“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48)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在康氏的保国会等一系列活动中。
诚然,上述判断尺度只能说是康氏自己的一厢情愿,对康氏来说,光绪帝能否“召见称旨”更多是未知数。从他在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一文中所说的“当由下变之,由下迫之”的“下迫之”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康有为并非是被动地等待光绪帝的“召见”和“变政”,而是把公民选举权(“民权”)和民选下院(“开议院”)作为迫使光绪帝“变政”的重要举措和筹码。因此,康有为的民选议院路线的政治活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的真诚维护,倒不如说是出于迫使光绪帝推行开明君主路线的一种实用主义策略。这表明康有为在光绪帝正式宣布百日维新和召见之前并未把公民选举权与民选下院看做固定的政治理念和确定的政治制度而加以贯彻。由此可见,在对待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等问题的态度上,康有为虽然与严复、梁启超等人在反对民选下院的理由上有所不同,但就他们把公民选举权与民选下院都看做随时妥协、让步的对象这一点而言,三者的思路可以说殊途同归,这是维新派在贯彻其政治理念的运作思路上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那么,康有为究竟于何时在民选下院路线问题上公开让步的呢?也就是说,民选下院路线至何时不再为康氏所利用的呢?虽然康氏在《第六书》之后的各奏折中没有提及与民选下院有关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康氏与维新派人士打交道时他已经让步民选下院路线。继《第六书》之后,康氏又接连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和十卷《日本变政考》等一系列关于走自上而下变法维新的开明路线的奏折,而恰在同时,他却正式发起保国会,仍然坚持以公民选举权(“民权”)和“开议院”为核心的民选下院路线,尽管其目的是在敦促光绪帝选择自上而下的开明变政之路。
就在高燮曾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之后不久,保国会正式成立。保国会起源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1898年1月5日)创立的粤学会(49),旋后四川、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贵等省纷纷成立学会(50),这些都为保国会的创立打下基础。保国会正式于康氏递呈《日本变政考》十卷本(51)后之第七天(1898年4月17日)召开成立大会。根据黄彰健的考证,保国会先后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闰三月初一日(4月21日)和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召开过三次大会(52)。其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有为在其演说词中阐述了有关民选议院和民权的观点,即:“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53)显然,保国会的政治立场及其观点与康有为《第六书》及其后与制度局有关的一系列奏折中的相关内容截然不同,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的康有为采取了以“上书求变法于上”的开明君主路线为主、以“开会振士气于下”的激进民选下院路线为辅的政治策略。康氏保国会演说中所称的“君不甚贵,民不甚贱”的观点虽带有传统民本思想的色彩,但是这一传统的民本原则在与西方的民选“议院”结合之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与议院有关的公民(“民不甚贱”的“民”)不再是传统君主重民、民本的仁政对象和统治对象,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宪政时代的公民,下院议员的命运不再是取决于君主而必须取决于公民选举。其激进程度和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由此可见一斑。
保国会活动大致于戊戌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至四月十三日(5月31日)刊发康有为保国会演说词之后告一段落。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百日维新正式拉开帷幕,在徐致靖的“保荐”之下(54),康有为于戊戌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这不仅令康有为最终如愿以偿,且对他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拥有一个良好的仕途前景提供了上好机会,依靠光绪帝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这样一来,“开议院”和公民选举权(“民权”)对他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多少利用价值,而且他也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对巩固君权来说有一定刺激的保国会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康有为于五月二十八日(7月16日)公开发表了《答人论议院书》一文,向其他维新派人士公开表明他已经在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问题上做出妥协,认为“夫议院之议,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于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55)对文中所说的“议院”,康有为虽然没有直接注明是下院还是上院,但是根据他以前的思想,无疑指的是民选下院。
总之,康有为在被召见之后,以所谓“取乱之道”、“旧党盈塞”、“议院亦徒存虚名而已”、“民智未开”以及“中国不可行”等为理由反对立即开国会的言论,只是为他在民选下院路线问题上所做的妥协涂上了浓重的合理化色彩。在此情形下,严复和梁启超的“民智未开”论更成为支撑康氏政治路线转变的理论后盾,而“守旧盈朝”和“那拉揽政,圣人无权”则成为他说服谭嗣同和林旭让步“开议院”激进主张的主要理由。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无论与光绪帝打交道还是与维新派人士打交道,康有为原来两种趋向的政治路线就被以上院化的“制度局”或“懋勤殿”为标志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
五、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
细心的读者可能观察到,笔者对于康有为议会思想转变(即反对立即开国会)的解释,从未使用过“放弃”或“否定”,而代之以“让步”和“妥协”。这是因为,在《第六书》中从上下院到上议院的重心转移之后,甚至四月二十八日(1898年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之后,康有为一直没有否定或放弃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只是把开设民选下院和国会的时间置于设立上议院和钦定宪法的时间之后,将其视为未来的发展目标。
在《答人论议院书》一文中,康有为公开宣布要在民选下院路线上做出让步的同时,也展望在不久的将来,经过自上而下的维新事业的开展,中国社会可能最终会得以改变。即:“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二年可成。”(56)在此康有为所称的“日本三十年而强”和“全变”的涵义不十分清楚,究竟“二年”以内发生怎样的“成效”呢?我们可从《日本变政考》中寻找答案: “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57)康氏此处所言之“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指的是1890年明治政府正式开设的帝国议会。从“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的“尚非其时”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并没有否定或放弃在中国召开像日本帝国议会那样的“国会”的想法。言外之意,在时机成熟或者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将来一定会“开国会”,“开国会”依然是其未来的理想。(5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康氏反对立即开国会的做法简单视为康氏对其开国会目标的最终放弃或否定。
如何准备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之下“开国会”呢?康有为的回答很明确:“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59)其中“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这一句值得注意。按照康氏划分的“变法”标准,其“变选举”的议院选举方式属于“变政”的范畴;同时根据他设想的“变法”的逻辑顺序,“变政”内容及其推行的步骤也被规定于“宪法”之中,即:“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60)。这一逻辑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个“变法”步骤:首先把“改定国宪”放在推行“变法”的首要地位(61);其次将开设民选议院(“变政”)暂时搁置于“改定宪法”之后的次要地位,而且能否开设“改官制,变选举”的民选议院要取决于“定典章宪法”;然后依法逐步开设民选议院(“推行天下”)等“变政”事业。
那么又如何“先法律为改定”呢?康氏对此的回答也很有把握。他在《日本变政考·跋文》中指出“立制度局以议宪法”(62),在康氏年谱中也认为“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63)。可见,“改定国宪”或“定典章宪法”的主体是上院化的“制度局”,由它负责议定“宪法”,其宪法性质自然是由君主定夺之下的钦定宪法。从康有为的上述观点中不难看出,康有为把称谓不同的上议院机构看作是“开国会”的过渡性机构(64),通过上议院的具体操作(“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最后过渡到开国会(“改官制,变选举”)(65),从而完成推行“变法”这一维新大业之终极目标。
耐人寻味的是,将上述“变法”步骤与被史学界视为“伪造”(66)的《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事折》中所设定的开“懋勤殿”的步骤相比较,就会发现,该折于“变法”步骤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动,也没有与《第六书》之后康有为一贯的立宪思想相背离,反而经康有为稍加润色后,更能令我们了解戊戌时期康有为所采取的变法步骤及其真实意图。在谈到设立类似上院的懋勤殿之用意时,康有为指出:“乞定开国会期,先开懋勤殿……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国会之期,明诏布告天下。然宪法国会条例至繁,尚待选集,取资各国,今未开国会之先,请采用国会之意。”(67)显然,与上院化的“制度局”一样,康氏将“开懋勤殿”也看作“开国会”的过渡性步骤,即“今未开国会之先,请采用国会之意”。且康氏把“开国会”的时间置于设立上议院(“先开懋勤殿”)和制定钦定宪法(“定立宪为国体”)之后,将开设上院化的“懋勤殿”作为“开国会”的出发点。
先定宪法而后开国会的这种思路在康有为20世纪初所发表的《官制议第七篇·开议院》中仍然保持着逻辑上的统一性。即:“今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骤立议院,而各省乡县必当先举议员以自治,俟风气稍开,民智日明,而后开议院焉”(68)。康有为指出,在未开议院(后开议院)之前,由大臣推荐和皇帝敕选以及“平民公举”方式选出的“参与”和“议政员”等上议院成员对军机处等行政机构送到上议院的“草案”进行讨论议决。即:“草案既定,是为初稿。议员又公举讨论官、磨勘官,或大臣荐之,并请旨简派,必选熟于中外,曾游历外国,或任实官办事多年者交之,讨论官辨其得失而增损之,磨勘官专究其谬误而攻难之。”(69)据此,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前后没有多大的改变,依然遵循着这样一种步骤:先开设上议院机构,其“议政员”或“讨论官”等上院成员负责制定宪法,等时机成熟后“开议院”。
那么究竟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够“开议院”或“开国会”呢?当时康有为并没有提出过具体时间表。然而从康有为所拟定的变法时间表中可以窥见一二。康有为于戊戌时期在不同文章中基本上确定了“变法”的时间表(70),其中五月初一(1898年6月19日)递呈的《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中描述得最为详细。即:
皇上既统筹全局,臣谓下手之始,宜先变法,将内政、外交一切法度,尽行斟酌改定,使本末、精粗、小大、内外,皆令规模毕定,图样写就(康氏三个月以内预定的变法计划,引者注),然后分先后缓急之序,次第举行。选天下通达之才,与之分任,然后有效也(康氏三年以内预定的维新计划,引者注)。故必变定法度,而后徐图举事也。
今言变法,规模如何,未加讨论,图样若何,未见谱写……日本变法之始,盖能定规模、画图样,而后举行,故能骤致富强,故非特开制度局于内廷,妙选通才入值,皇上亲临,日夕讨论,审定全规,重立典法,何事可存,何法宜改,草定章程,维新更始,此所谓先写图样,而后鸠工庇材也(康氏三个月以内预定的变法计划,引者注)。若其粗迹,若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矿、铁路、邮政、海军、民兵及各省民政诸局,臣前者既言之;变科举开学会,议西书,广游历,以开民智,臣面对已略之,皆制度局中条理之一端而已(康氏一年以内预定的变法计划,引者注)。臣愚以为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也……三月而规模成,一年而条理具,三年而效略见,十年而化大成。(71)
引文中的“引者注”是笔者在将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与相关内容作过核对的基础上,推断出的康氏所拟定长达十年的变法计划。其中“三月而规模成”与上述引文中“规模毕定,图样写就”或“先写图样”中“规模”或“图样”之间相互对应,而“一年而条理具”中“条理”与“制度局中条理之一端”中“条理”之间亦相互对应。“规模”和“条理”两者都要在一年以内由上院化的制度局完成。假如变法一帆风顺,三年以内就当有“成效”。在《答人论议院书》中康氏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72)在康氏其他文章中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如“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73)康氏所谓“三年之内,治具毕张”这一句的涵义就是倘若通过上院化的制度局议定的具体措施(“治具”或“规模”、“条理”)逐步推行的话,那么三年或二年以内将产生相应效果。与此同时,康氏所谓“十年而化大成”或“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的具体内涵虽然尚不十分明确,但是康氏预定的“变法”时间表显示出他对中国赶上西方充满信心。
在上述引文中康氏对“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的涵义并未深入探讨,而是依然停留在开设上院化的制度局及其操作过程这一浅层次面上,不过从与该变法时间表有关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康氏此处“十年”所包含的内在含义。康氏说:“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强。”(74)此外,他在《日本变政考》还谈到:“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75)。照上述理解,假如将当年日本开国会的时间表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参照,那么康有为就应该主张中国至少在二十余年后才能开设议院。(76)然而康氏并没有生搬日本“变法”的时间表,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他说:“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吾民与地十倍之,可不及十年而成之。”(77)在此,康有为虽然没有将“十年”与“开议院”的具体设想连在一起讨论,而此处的“日本变法二十年”却可与上述的“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相呼应。由此,康氏在不同文章中所称的“治化大成”或“化大成”在具体涵义应上与“日本变法二十年而大成”中“大成”相同。假如这种推断没有错误的话,康有为一再提及“十年以内,治化大成”或“十年而化大成”的具体变法事项即与“开议院”密切相关,言外之意,康氏将日本从维新开始到开议院所经历的二十年时间表缩短为“十年”。即康有为大致预定了在中国开议院的时间表,于十年内“开议院”,完成“治化大成”的终极目标。而就十年内是否能够成功开设国会,上院化的制度局的职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十年”内果能开设议院,就像1890年日本明治政府废除元老院(上院机构)而代之以贵族院(上院)和众议院(下院)以设立两院制帝国议会一样,制度局和懋勤殿等这些称谓不同的上议院机构亦将被上下两院的“议院”或“国会”所取代,以最终达到康氏“后开议院”的终极目标。有趣的是,康有为预定开国会时间表的这些思路,与1906-1908年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步骤,即以九年为期预备召开国会的时间表(78)的思路有相似处。这可能因为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和清末的预备立宪多仿照明治日本。若此,康有为论及立宪时间表的思路,无疑为清末预备立宪提供了参考。
虽然康有为没有否定在不久的将来开议院的可能性,我们却又不能忽视康氏反对立即开民选下院思想中所存在的保守性因素。他从没有对广大民众进行过适当动员,其变法思想也就无从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于是其所推行的变法维新计划不免有国家行政官僚主义之嫌。不过,在传统王朝专制统治下,要开设议会,先依靠“雷厉风行”的君主集权作用在所难免,尤其在新旧势力旗鼓相当的情况之下,过渡性的上议院机构可能对议院开设的筹备提供方便。据此,在康有为的力劝之下(79),较激进的谭嗣同和林旭等维新派都接受了康有为设计的上议院路线,希望通过上议院的操作而顺利过渡到“开议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雷厉风行”的开明君主还是过渡性的上议院,都没有超出依靠君权的行政作用这个范畴。换言之,虽然康氏对于未来“开国会”仍然寄予厚望,而当前所关切者却是开设类似上议院的机构,只不过其开设上议院的主张不免要付出公民的选举权(“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和请愿权(“民词”)被削弱、剥夺的代价,即对于公民选举权和请愿权的实现与维护将起延误、阻碍的消级作用。这是现实实践与未来理想之间的二律背反。
在近代政治史上类似上述的二律背反现象并不只是出现在康有为等维新派身上,相信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种现象并不陌生。事隔十年之后,类似现象再次出现于革命派的民主实践中,即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制定临时约法期间,这种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现象重复出现了。诚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虽然与革命派的民主立宪在手段抑或终极目标方面截然不同,但在对待民主选举程序问题上,革命派的实际操作与康有为的实用主义策略却并无不同。
众所周知,武昌革命成功之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有关规定,应由类似于上议院的“参议院”选出临时总统,且由参议院制定和议决“临时约法”(80),为此后最终建立民主立宪奠定基础。然而从民主程序来看,革命派的实际操作并不符合民主选举的条件。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各省都督本身并不由公民选举产生,于是他们自然不具备公民的代表性。由这样不具备公民代表资格的各省都督指派而产生的参议院自然不能代表公民的民意。参议院只是倾向革命的各省都督的代表组织,参议院选出的临时总统也自然不是直接或间接的民选总统,而只不过是各省都督所拥戴之人,这种实际操作缺乏民主选举的程序。
若此,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派的“参议院”实际上与戊戌时期康有为所设计的上院化的“制度局”或“懋勤殿”很类似。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君主的敕选与各省都督的指派这一产生方式上的差异,但都是与间接或直接的民主选举程序背道而驰,其制定的宪法也自然不完全代表民意。从这一点来讲,革命派与康有为的实际操作是殊途同归的,这是中国近代政治领袖所共有的一大特点。即当他们尚未掌握政权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比掌握政权时更激进一些;当政治权力已落入手中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比尚未靠近政治权力和舆论宣传时却要保守一些。造成这样的原因,与其说是他们出于一种对民主理念和民主程序的真诚维护,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策略。在实用主义的策略之下,他们将民主选举的程序都看作让步和妥协的对象,其长远的后果是延误了民选方式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是未来理想与当前实际操作之间的二律背反,也是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之间的二律背反。
六、小结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议会体系的有关问题提出以改革政治制度为核心的维新派政治主张和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在进呈《第六书》之前,康氏的改革路线仍然坚持上下两院制的议会体系,尤其强调“约十万户而举一人”的公民选举权,下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第六书》之后和百日维新宣布之前期间,康有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上院化制度局)与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保国会的活动)同时并行的政治策略。最后,在百日维新的开始和康氏被召见并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他在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的激进路线问题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上院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但康氏的这一妥协和让步并不等于他否定或放弃将来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只是他把类似于上议院机构的制度局看作是十年内开下院或“开国会”的过渡性机构。
[收稿日期]2007-3-28
注释:
①康有为:《公车上书》,收入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二集,第100页。至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收入1986年第1期《历史档案》第51页。
②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收入《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79-180页。
③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收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98)第207页。
④房德邻:《维新派政治纲领的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90-94页。朱爱华、汪荣祖也持与房氏类似的观点。见朱爱华:《戊戌维新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贵州民族学报》(1997年第3期),第30页。见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卷上(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2),第185、257、263、368页。本文基本倾向于上述“出于策略考虑的实用主义”的观点。不过宋德华、王晓秋提出不同观点。见宋德华:《戊戌维新派政治纲领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第128页。见王晓秋:《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收入自李文海、孔祥吉编:《戊戌变法》(巴蜀书社,1986),第308-309页。见余明侠:《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99-100页;又见《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第188-189页。然而,宋、王、余氏的观点只看到召见之后康有为留下的相关记载,而对从《第五书》到被召见期间的康有为议会思想的动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⑤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入西洋弭兵会片》(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12.12)),转引于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台北),1998),第12页。
⑥关于康有为所建议的“制度局”的性质和渊源问题,请参见拙稿《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议会思想——以制度局的渊源与上院设立的蓝图为中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28辑,2005年)。
⑦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收入《戊戌变法》丛刊(四),第331页。
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94),第74页。
⑨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入西洋弭兵会片》(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12.12)),转引于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2页。又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第3068页。翁氏说:“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
⑩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页。
(11)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收入《戊戌变法》丛刊(一),第492页。
(12)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68页。
(1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0页。
(14)(16)张荫桓:《张樵野戊戌日记》,收入王贵忱、王大文标点:《张樵野戊戌日记》,《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三期),第85页。
(15)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86页。
(17)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丛刊(一),第492页。
(18)(19)(20)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0页。
(21)《据呈代奏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4页。
(22)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81页。
(2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0页。关于康有为得到上奏机会的情形,在康有为给其弟的书信中有相关记载,即:“上急欲变法,恭邸亦有□□吾《日本变政记》及吾条陈,上乃宣促速上,吾顷拟抄此书及条陈同上,□□□启圣,亦千载一时之机也”(参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775页)。
(24)康有为:《康有为致康广仁信·抄五日京中来函》,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775页。关于康有为对自己身份变化的期待和传闻,学界已有所涉及。例如,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7页。又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172-173页。但是学界以往只注意康有为与“五品衔”的联系,却忽略了康有为所说的“参议”与第六书中的制度局“参议”间的关系。
(25)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收入苏舆:《翼教丛书》卷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刊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165页。
(26)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黄吴本汇录》,第268页。
(27)康有为:《康有为致康广仁信·抄五日京中来函》,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775页。
(28)关于康有为所提出的三条政治纲领及其涵义,请参见拙稿《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议会思想——以制度局的渊源与上院设立的蓝图为中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28辑,2005);又见拙稿《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韩国史学史学报》(第12号,2005)。
(29)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黄吴本汇录》,第268页。
(30)康有为:《公车上书》,收入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00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所称的“辟门”在康氏其他著作和文献中始终与西方议会系统的“议院”和“民选议院”相对应。在1897年末撰写的《孔子改制考》中,康氏将“辟门”直接了当地与“议院”比附在一起,即:“辟四门以开议院(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348页)”。戊戌时期康有为发表于《国闻报》上的《答人论议院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指出:“夫议院之议,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原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898年8月15日),收入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附录,第61页)”。由此,在《第二书》中康有为所称的“辟闻”与西方的议院密切相关。此“辟闻”在康氏的议会体系中亦与“民选议院”联在一起。
(31)(32)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79页。
(33)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黄吴本汇录》,第269页。
(34)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六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137页。显而易见,康有为所称的“辟门”的具体选出方式实际上等同于西方的“民选议院”,即下院。
(35)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79-180页。
(36)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58页。
(37)郑观应箸,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议院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6页。
(38)严复:《附: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诗文上》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第30-31页。
(39)严复:《中俄交谊论》,《国闻报》,转载于王栻主编:《严复集·诗文下》第二册,第475页。
(40)梁启超:《古议院考》,《梁启超全集》,第62页。
(41)参见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25页。
(42)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
(43)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六案语、卷七案语、卷十一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131、196、306页。宋德华认为,“康梁从公车上书以来一直就认为欲兴民权,必先开民智”(参见宋德华:《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及其它》,《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第91页;《岭南维新思想述论》(中华书局,2002),第362-364)。对于上述宋氏的观点,本文不敢苟同。我们应将康有为与梁启超对于“民智”的观点区别开来。宋氏列举康有为有关“民智”的言论主要引用于《日本变政考·案语》、《康南海自编年谱》以及《答人论议院书》。但是宋氏引用的依据都是被召见之后康有为留下来的文献,因此我们由这些依据无法说明召见之前康有为的“民智”言论。
(44)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收载《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收入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稿汇刊》第16册(宏业书局(台北),1976),第93页。
(45)康有为:《与越曰生书》,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600页。
(46)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黄吴本汇录》,第268页。
(47)(48)(5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4页。
(49)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38页。
(51)康有为所编译的《日本变政考》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两度向清政府进呈,有十卷和十三卷的两个版本。第一次进呈该书的十卷本于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递总理衙门,二十三日(4月13日)进呈御览(请参考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59页)。关于第二次进呈的情况,康有为自己没有说明此书何时进呈。为此,史学界没有统一定见。黄彰健认为,康氏进呈此书时间应为“五月下旬”至“六月下旬”(见于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台北),1970),第208、245页)。但陈华新认为,自“五月初三日(6月21日)”到“六月底(八月中旬)”(见于陈华新:《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收载《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71页。此外,孔祥吉认为,“第二次进呈开始于五月上旬,大约到六月中旬进呈完毕(见于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81页。本文基本采用孔祥吉的说法。
(52)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82-83页。
(53)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收入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4,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又收入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238页。
(54)康有为:《康南海先生戊戌家书》,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774-775页。
(55)(56)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原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1898.7.16),收入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61页;第62页。
(5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六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131页。
(58)房德邻也看到康有为先定宪法而后开国会的变法步骤,房氏认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变法次第和法制章程,先开制度局于宫中,议决新政,草定宪法,依法逐步推行新政,最后设议院,完成变法大业”(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0页)。
(59)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七;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186-187页。
(60)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九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235页。
(61)用康氏年谱的话来说:“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参见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5页。
(62)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跋文》进呈本;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335页。
(6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45页。
(64)关于制度局具有过渡性的讨论,见王栻:《戊戌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346页;李时岳的《戊戌变法历史评价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3年第6期),收入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第178页;又见王晓秋:《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收入自李文海、孔祥吉编:《戊戌变法》,第308、310页:又见林克光着:《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264-265、268页。
(65)正如他对日本明治维新过程所把握:“宪法大成,民气大和,人士知学,上下情通,而后议院立”。参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十二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335页。
(66)对于康有为《戊戌奏稿》的作伪问题的代表研究,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8-9、57、222、594、597页;陈凤名:《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收入于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7)康有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先选才议政许民上书事折》,收入《戊戌变法》丛刊(二),第240-241页。
(68)康有为:《开议院》,收入《康南海官制议》第七篇,收入《康著汇刊》第14册,第99页。
(69)康有为:《官制议第七·开议院》,收入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第558页。
(70)至于康有为所拟定的变法时间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戊戌正月初八日(1月29日)进呈的《第六书》中,即“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至于十年,治功大着(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黄吴本汇录》,第271页)”。其后进呈的奏折中也提及与此类似的变法时间表,例如“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见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58页)。
(71)康有为:《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20-121页。
(72)康有为:《答人论议院书》,原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1898.8.15),收入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附录,第62页。
(73)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58页。
(74)康有为:《请改直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今小民六岁皆入学折》,收入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58页。
(75)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进呈本卷六案语;又收入《康著汇刊》第10册,第131页。
(76)李时岳早已看到康有为拟定“从开制度到制定宪法到开设议院”的维新步骤。(见李时岳:《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收入李时岳:《近代史新论》,第169-170页。)然而李氏对康有为的“变法”十年计划和缩短时间表没能引起注意。
(7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586页。
(78)关于清末预备立宪的论述,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第69-152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第57-96页。另,萧公权也看到康有为的立宪思想和清末预备立宪的关联性,见[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第178页。
(79)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59页。在康有为的说服之下,谭嗣同和林旭等大部分维新人士都接受了康有为的实用主义方寒。
(8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增订版),第544-547页。
标签:康有为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光绪帝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选举权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