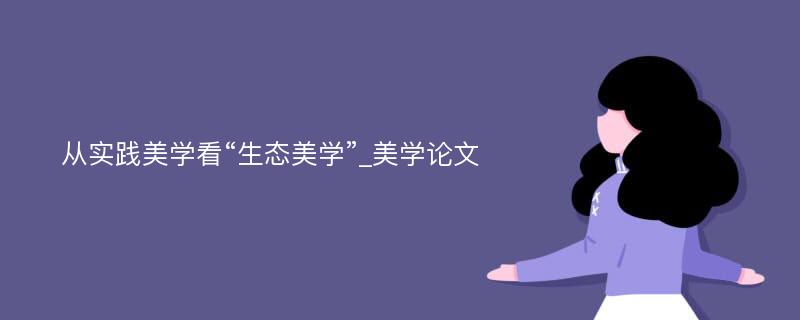
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生态美学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从美学角度来说,对生态问题的考察至少有这样几类基本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否存在“生态美”这一美的形态?如果存在,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和自然美、社会美的关系怎么处理?其二,从学科形态来说,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其三,提出生态美的意义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是否存在“生态美”?
严格说来,生态美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它是否成立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无论是生态也好、自然也好、社会也好,它们之所以对人来说成其为“美”,是因为在它们之中有某种形式结构,如韵律、节奏、比例、均衡、对称等,这些才是使事物成其为“美”的因素。无论是自然美、社会美或技术美,其“美”之所以成立,究其根本原因,都是跟这些形式结构有关的,是这些形式因素在起作用。而这些形式因素之所以对人来说成为美的,是因为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和体验到,这些形式因素跟人的心理结构有某种对应或应和。当然,这种对应或应和的产生同样是因为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体。
从哲学层面讲,如果承认自然美、社会美、技术美这样一些概念的合理性,那么,生态美概念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正如自然美、社会美和技术美这些概念是从美的对象的角度提出的一样,生态美概念也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提出来的。从它的定位上说,它应该是介于自然美和社会美之间:既有自然美的因素,也有社会美的因素。就其本质而言,如果说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是在“真”的形式结构中积淀了人的本质力量,其形式是“真”,其实质是“善”;社会美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呈现,其形式是“善”,其内容是“真”,是以“善”的形式显现“真”的内涵,那么,生态美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即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人对自然的回归和依赖,是在自然和社会呈现人的“善”目的的基础上对自然之“真”的回归和强调。从形式上说,它接近于自然美;从实质上说,它是人的目的的“善”合于自然之“真”,以含融了人的“善”的自然之“真”为其本质。人的自然化是从人与自然的联结角度来说的;自然的本真化是从自然本身的存在来说的。无论是人的自然化还是自然的本真化,都离不开人的角度;自然的本真化正是为了人有“自然”可“依”、可“化”,也就是说,自然的本真化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因为说到底,美终究是一种人类的价值、一种为人的价值。
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都是以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是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的。
自然美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形式美的产生是一个关键。它是自然从狭义人化进入广义人化的见证,也是人类的审美意识从其它意识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独立意识的证明。人类在长期、大量、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自然之中的各种感性形式——节奏、韵律、比例、大小、对称、光滑等等,使这些形式成为人所掌握的形式力量,从而产生美。
形式美来源于主体的操作实践活动,它一旦产生便有了独立的规则和力量,成为人类艺术探索和表现的主要对象。
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创造新的美的形式,人类所能欣赏的形式美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最初认为是丑陋的一些形式经过历史沉淀可能演变成美的经典。就表现形式而言,生态美跟自然美十分接近。它和自然美一为自然的人化,一为人的自然化,恰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从哲学涵义上说,生态美与自然美恰好是一对对应的范畴,是对自然美和社会美在更高基础上的超越。
“人的自然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在“自然的人化”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说,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自从人诞生以后,自然就经历着一个不断的“人化”的过程,那么,从人与自然的更为本源的关系上说,则人类产生于自然,是自然界上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因而在自然人化的同时,人也在经历着不断“自然化”、不断返本归元,从人与自然的广泛的情感联系中寻找更深层次的精神家园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更不可能只是一味地对自然进行索取和改造,即单向的人化自然。作为自然之子,人对自然还有另外一面的关系,一种更为原初、更为本原性的关系,那就是人对自然从精神上和生存上的皈依和依赖。人类之所以能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之所以能认识和改造自然,从根本上也同样是因为作为自然之子,人类的大脑结构具有认识、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人是自然之子为前提的。因此,人对自然的任何改造、利用和“人化”,都建立在人是自然之子的前提之上。由于有这种前提,人对自然的征服、利用和改造就必须有一个“度”,必须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之下进行。超出这个“度”,人类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人对自然从精神上和生存层面上的这种依赖、回归,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建立在人既能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时又依赖于自然的基础上的亲近、和谐、共生、共在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另一面,即人的自然化。而人的自然化的审美表现就是生态美。所以,生态美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人具备了较高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产生的历史概念。
生态美的实质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
“自然的本真化”问题同样是在自然的人化的前提之下产生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自然的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种“人化”到目前为止只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是人单向度地向自然的索取。而由于人类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这种开发和索取已经超出了自然本身的承受能力,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类的存在已经大大地威胁到了地球上其它动物和植物的生存。从人类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来说,这种状况对人类也是有害的。从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来说,当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从根本上改变,人已经从完全被自然所支配、所控制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变成一种主体性的存在物的时候,人所欣赏的就已经不再仅仅是那些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不再仅仅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人类产品,而应还有那些原始的、未打上人类烙印的自然。无论人类怎么发展,无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人的主体性发展到多高,人是自然之子这一点永远也无法改变。因此,人类必须保留一些原生态的、纯粹的、未经人类现代文明染指的自然,这就是“自然的本真化”。这是人类生存的“根”。没有这个根,人类将面临毁灭性的生存灾难。反过来说,只有保留住这个根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成为可能,人才能实现审美化生存的理想。
因此,从形式与内容的联结说,生态美介于自然美和社会美之间,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形态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才产生的审美形态。但从形式上说,生态美更偏重于自然美,它的形式主要是“真”,是人类的“善”的目的合乎自然本身的规律性。从具体感性形态来说,生态美更注重和强调人对自然的回归和依赖。因而,无论是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还是城市建设,生态美都以“自然”作为最高的审美目标。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来说,那些未经开发、尚未踏上人类足迹的原生态的自然形态,如原始的森林、大瀑布、河流、群山、沙漠,等等,更能体现生态美的理想;而在城市建设中,无论是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还是社区的设计,也同样都应该最大限度地贴进“自然”。
必须指出的是,生态美和自然美的区分只是从理论上进行的,在实际表现形态上二者并没有太大分别。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区分是绝对必要的。自然美的本质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没有这个人化,自然是无所谓美与丑的。而生态美则强调的是在自然人化的基础上人重新回到自然,依赖自然,亲近自然。它是比自然美更晚的审美形态,是一个现代美学的范畴,因此它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
二、人的自然化的实质:情本体的确立
人的自然化是指本已人化、社会化的人重新回到自然之中。迄今为止,人类一直处在社会化的进程中,先后经历了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但改造了自然,而且本身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也一再发生改变。这个改变的方向总的来说是越来越远离自然,无论是人的生活环境还是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是朝着更加社会化、人化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充分证明了人类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主体性,证明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甚至改造人自身的能力。
但与此同时,人类也越来越陷入自己制造的权力-语言-知识之中,陷入工具本体对心理的异化之中,使人的生活越来越不自然,现代社会中人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空前增多。与此相应,一些根源于心理问题的社会问题亦随之增多。因此,挣脱权力-语言-知识的工具本体,建立情感本体,让人重新回到自然,重新发现自然——这个自然不仅是外在的大自然,而且包括内在的自然,即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根源于人的自然存在的部分——就成为对工具本体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的纠正。当社会化、人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对自然本身的回归与依赖,挣脱理性的约束与制约,回到生命的本然与天真状态,建立情感本体,就成为当今时代和未来社会的重要主题。
人的自然化亦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外在方面大体上包含三个层次:
其一,人与自然界的共生、共在。可以借用庄子所描绘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自然对人来说,既是生存资源的提供者,也是精神和灵魂的安顿者,更是生命的寄托者和皈依。
其二,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人不但与自然界共在共生,而且对自然抱着一种同情、欣赏、亲近的态度,走进自然,投身于自然。
其三,人通过学习与实践达到与自然节律的同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境界。
从内在方面说,人的自然化即是建立情感本体,以纠正和补充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工具本体的过度膨胀带来的异化。具体途径首先是对形式感的培养,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艺术。艺术是对人的形式感的直接启发和培养;形式感的培养有助于科学之真的发现、发明和创见。这是“以美启真”。“以美储善”则是通过情感本体的建立,把道德建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通过区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启发人们的宗教情感和道德情感,以社会性道德建立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秩序和道德准则。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说,“情”的具体内涵在我看来主要应该是对自然的欣赏和敬畏之情。对自然的欣赏,就是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不是首先把自然作为改造、征服的对象,而是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去发现、了解和欣赏自然的多层次、多方面、多种形式的美,并主动投身于自然,把自己融入自然之中,以一颗自然之心去体验、感受自然的奇妙、神秘和美。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对自然的关系中,人还需对自然保持敬畏之情。
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在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基调。对自然的敬畏感源于原始社会中自然力量的巨大与神秘对人造成的威压与恐惧感;而农业社会里“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使人对自然的这种敬畏之情一直保持、延续了下来。一方面,自然是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的一切都必须从自然之中获得,因此,人对自然怀着尊敬、感激之情;另一方面,自然对人来说总是具有某种神秘性质,自然的力量、自然运行的规律、生命的诞生与成长,都使人对它有一种畏惧与崇拜之情。正是由于有对自然的欣赏与敬畏,在农业社会的上千年历史中,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才有效地维持了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保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只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主体性思想的确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都大为增强,自然对人才失去了神秘感,人才也失去了对自然应有的尊敬与感激,变为只是把自然当作获得生存的资源库,以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贪婪地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开发。这种做法在短时间内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生产力得到高速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快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掠夺式开发后,整个地球已显得不堪重负,自然已开始向人类报复。过去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人的贪欲的膨胀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摧毁了自然在上百万年、上千万年甚至上亿年才形成的生态系统,耗尽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的资源。因此,反思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恢复对自然的尊敬与敬畏,从哲学上和美学上来说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从人本身来说,如前所述,失去自然之情感的人类也正在被异化。因此,当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的自然化,无论对于自然来说还是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不仅仅是原始的宗教性的泛神论思想结果;对于现代人说来,它更包含着道德上的情感和意义。只有把自然当作一个伟大的对象,一个值得尊敬、崇拜和赞赏的对象,人才可能对之产生敬畏之情。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以灿烂星空的庄严肃穆、伟大辽阔来比喻人的道德力量的伟大庄严,可见,宇宙自然本身对于人来说的确有一种庄严与伟大。反过来说,只有具有一颗伟大宽容的心灵、道德上高尚的人,才能够去发现和体验宇宙自然的这种庄严与伟大。
因此,人的自然化也是自然和自然之美的重新发现,是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回归与亲近,是在自然人化基础上重新发现和建立的天人和谐与天人合一。从美的形态来说,人的自然化所呈现出来的感性形式便是生态美。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是以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没有自然的人化,就谈不上人的自然化,更不会出现自然的本真化问题。人类在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如何在对人来说威力强大的自然面前谋取生存资源。因而,对人来说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条件。只是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和进步,人对于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换言之,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掌握已达到了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支配自然、改变自然的存在状态的程度,而这种改变是不可逆转的:自然一旦被人改变,就无法再恢复到它的原始样子,它的生态平衡将被打乱,生物链将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任何行动稍有不慎,就足以造成无论对自然还是对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本真化已经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人来说,自然的人化作为美的必要条件的阶段已被超越。在这个全球化、现代化、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得足以毁灭自然的世界上,自然美不再是人化的自然,而是本真化的自然,是原生态的、未经人类染指和改变的自然。而这样的自然景观已经越来越少了,因而,自然的本真化不但是一个美学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三、“生态美学”何以成其为“学”?
生态美学虽然这几年相对来说比较热闹,但是,它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命题都还是空缺的。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它区别于其它美学学说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它的独特研究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得到有效的阐述。
生态美学要想作为一种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核心命题的学说而得到确立,还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困难。
困难之一:生态美学如何确定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顾名思义,生态美学应该是研究生态之美的学说。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自然界的生态现象。可是,生态现象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生态美学是研究生态之美的学说,那么,生态之“美”又是什么?依据什么原理去界定某种生态是美的,某种生态不美?或者说,是否符合生态规律的就都是美的?如果作出这样的判断,依据的是什么理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并非任何生态都是“美”的。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生态美就是和谐,就是自然界所有生命的和谐共存;而和谐又被理解为和平,似乎生态美就是生物之间和平相处、友好相待,特别是人与动植物之间和平相处、友好相待。但实际上,从生态原则来说,自然界里的生物遵循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弱肉强食的法则。所谓生态的和谐绝不意味着和平,而是所有的生物相对来说处于比较衡定的数量,相互之间形成了彼此依赖又彼此制约的生物环链。这个依赖是指处于生态系统环链中的上一级的生物以它下一级的生物为其生存的食物来源;而制约则是指由于生物之间相互以之为食物来源,因而无论哪一种生物都不可过多或过少,任何生物的过多或过少都将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打破这种平衡。这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过程是很残酷的,弱者被淘汰,强者才能生存。因此,所谓生态平衡就是生态美的观念只是未经思索的想当然而已。从生态学的角度界定美,把生态美界定为生物之间弱肉强食所产生的生态平衡系统,是违反生态美学论者的本意的。因为这样一来,必然导致的结论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无限掠夺是合法的——人类比其它生物能力强,当然可以掠夺其它生物生存的资源以为己用。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困难之二:生态美学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任何一种作为“学”的美学学说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践美学作为哲学美学,其研究方法是从对美和美感问题的哲学分析开始,而这种哲学分析是建立在实践论基础之上的。由此,实践美学就具有了向具体学科进行辐射的能力。事实上,前述对于生态美的内涵的把握正是从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生态美的这种分析立足于现代人类的生存语境,把美不但看作是自然的人化过程,而且特别强调在人类实践能力大为提高的现代社会,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在美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意义。然而,生态美学由于其基本哲学立足点的缺失,其研究方法既无哲学上的高屋建瓴气势,也无经验主义美学的实证分析的精细。事实上,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到目前为止,关于生态美学研究究竟怎样进行的问题,还没有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困难之三: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和命题是什么。如何从生态美学原理出发界定生态美、自然美、社会美、形式美这样一些美学概念?如何处理生态与生态美的关系?实际上,前面两个困难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困难上。生态美学之所以未能成为其“学”,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它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核心思想。生态中心主义主要跟伦理问题有关,它所面临的困难和悖论是一种伦理的困难和悖论。就生态中心主义来说,它本身还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原则,不但在理论上有反人类的嫌疑,而且在实践操作层面面临更大的困难。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生态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限的资源已经被殖民者掠夺大半,而现在人们要生存,有时候就不得不面临对生态的破坏。可是,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将不再有为自己生存谋求合法的自然资源的权利。退一步说,即便生态中心主义原则能够确定下来,即便能够解决它跟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之间的矛盾,可是这样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跟美有何关系?美就是不加人为干预的生态平衡吗?如果是这样,岂非说任何人类的痕迹都是丑了?换言之,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美就不再是一种与人类有关的价值,不再是人所要追求的理想了。那么,这种所谓“生态美学”跟人有何关系?
四、“生态美学”的意义
尽管生态美学何以成为“学”还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但是,生态美学的提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生态美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控制自然的现代社会,美不再仅仅限于自然的人化。相反,在人和自然都已经充分实现“人化”的条件下,人类的自然之根的保护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个“自然之根”既包括作为人类所生存于其间的环境的大自然,也包括人类本身的自然之性。
众所周知,理性的高度发达一方面给人类带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类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异化。因此,对自然的回归,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恢复,正是为了在异化的世界里寻回失落的人性,为了使人重新回到它所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之根。从美学上说,在自然的人化已经充分实现和展开的条件下,美不再仅仅是面向历史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自然的本真化,成为面向未来的美的主要形态。在这种前提下,不但生态美这种新形态的美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的理想形态、一种人类所追求的境界,而且,就是自然美本身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意义上的变化。
首先,虽然从历史过程上看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但从现实来说,自然美已经超越了自然人化的阶段,而走向自然的纯粹化、本真化,或者说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说,在当今天社会都市化、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的前提下,自然美的内涵已由从前的“人化”上升为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本真化、纯粹化。自然之所以美、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以其完全不同于现代都市人类生存环境的纯粹的“自然”形态、一种直截了当的形式呈现了人类生存的生命之根。当然,同时也还在于它给人提供了人在都市里无法得到东西——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未经污染的泉水,等等,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人类本身无法给予自己的,只能由自然来提供。
其次,自然本真化还意味着它对商业化的拒绝。在当今天社会商业化、都市化成为人的生存的主要形态的条件下,原生态的、未经工业和商业染指的自然景观已经成为一种稀有珍贵的资源,那些未为都市社会和现代媒体所发现的自然景观和富有传统色彩的文化,一旦被媒体发现,一旦被从商业目的出发进行所谓开发利用,它们便很快被侵蚀、改变甚至破坏,其原住民也很快失去原有的纯朴和在自然条件下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状态,其文化也很快从原住民的生命存在形态变成一种商业化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商品。因此,自然的纯化、本真化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生态美学”的提出,提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研究不仅仅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研究,生态问题中也不仅仅包含着伦理学问题,而且要从美学上去研究,把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的审美理想。这一点在对原始自然景观和具有原始文化形态的人文景观的开发中显得特别紧迫。
第三,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讲,提出生态美学的意义还在于,提醒人们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即关注人生存的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日常生活产品的设计、居住环境的设计是否符合人性化要求,是否符合人的自然化的审美理想。也就是说,生态美问题不仅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系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生存环境的关系。“人的自然化”不仅仅是指人对自然山水的游历与亲近,而且还指人从自己的整个生存向自然回归,以及人的心理文化结构中情本体的确立。这在被工具理性异化所困扰的现代社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学上讲,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设计应该有一种生态美的意识,一种建造都市里的村庄的意识。它的理想应该是使人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都市里,却能时刻感受自然、亲近自然,既能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充分的释放,又能符合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和生活舒适的要求。具体说来,城市空间、园林布局、建筑设计等必须首先在外观上保护人的视觉,剔除那些视觉暴力对人造成的伤害。如有些建筑外墙采用玻璃墙面,这就是一种视觉暴力,它在造成光污染的同时,也对人的视觉神经造成压迫,从而对健康造成损害。从美学上说,这种建筑就违背了生态美的原则,因为它不是使人向自然回归,不是使人自然化,而是利用各种人工材料使人与自然隔绝,使人更远离自然。再比如,在居民社区建设中,不仅应该提供完整的水、电、气等基本生活设施,而且应该充分提供一种生态之美。绿化建设应该是小区设计和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这种绿化不应仅仅限于产生视觉和嗅觉上的作用——绿色的树木和草坪在视觉上的怡人与嗅觉上的芬芳,而且还应该切实地发挥它的实用功能和作用,让人们能够休憩、散步、锻炼,这应该是城市建设的一个方向。
总之,“生态美学”的提出把生态美从一般的美的形态的地位上强化起来、提升出来,使得人们开始从美学角度关注生态问题,为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