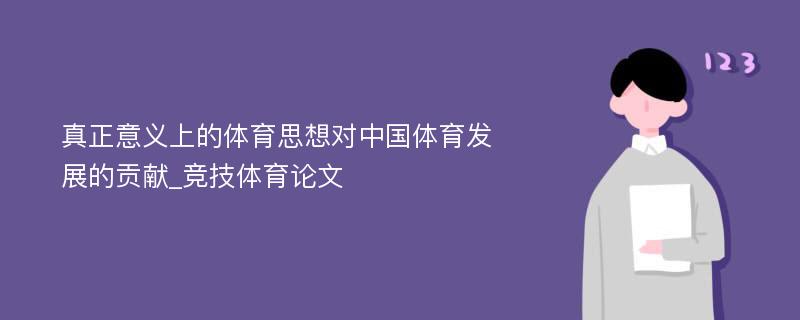
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体育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4)04-0007-05
什么是体育?这是体育工作者不得不首先回答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体育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还是一个至今一直未能解决的学术难题。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体育概念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综合型”概念定义法和“分析型”概念定义法。我国一般把“体育”这个名词看成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身体教育和运动竞技,虽然有一些学者一直主张分开,并坚持认为体育是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不是运动竞技(sports),但这种学术观点一直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所以持分开观点的国内学者不得不用“真义体育”(PE)这一语词来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区别于各种“转义体育”和“假义体育”。用“综合型”思维方法对体育概念下定义,也是导致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Sport大体育观”风靡全国至今不衰的主要根源。而在国外,PE和Sport或Sports一直是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语词概念,尽管国外也有人主张“用sport作为体育的总概念”,但这种观点也一直未能获得国外多数人士的认同。
1 “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
长期以来,“真义体育观”与“大体育观”这两种学术观点在我国体育理论界一直针锋相对,无法调和。从表面上看,我国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争论只是围绕着几个术语进行的,但从思维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1]。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2]曾指出:“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他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其最明显的差异根源,我认为就在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处处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诺斯罗普教授[3]在《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互补的重点》一文中也曾明确指出,概念的主要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用直觉得到的,一种是用假设得到的。他说:“用直觉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表示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它的全部意义是某种直接领悟的东西给予的。‘蓝’,作为感觉到的颜色,就是一个用直觉得到的概念。……用假设得到的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出现在某个演绎理论中,它的全部意义是由这个演绎理论的各个假设所指定的。‘蓝’,在电磁理论中波长数目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用假设得到的概念。”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4]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也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西方哲学讲究逻辑分析,中国哲学则长于直觉思维,而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诸位学者的上述精辟见解抓住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因此其结果,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分析型”方法(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以直觉思维为主的“综合型”方法(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换句话说,从假设的概念出发的哲学家偏爱有区别的,从直觉的价值出发的哲学家则偏爱无区别的。用冯友兰先生[5]的话说:“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我国体育界目前对体育概念所持有的两种相互对峙的学术观点——“真义体育观”和“大体育观”,实际上就是运用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对体育概念完全不同的认识结果。为了更好地从哲学思维层次全面阐释这两种体育观,本文仅就“真义体育观”做如下阐述。
2 “真义体育观”的主要学术观点
自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何为体育之真义”,到1952年6月10日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我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以来,我国体育界人士自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末至今,一直围绕着“什么是体育”这一重大体育理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论。其中以林笑峰先生为代表的“真义体育观”因其采用严格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一些关键性概念做出了清晰的解释而格外引人瞩目。林先生[5]首先借用“文化”的定义(“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把“身体文化(physical culture)”表述为“身体教育(PE)和身体娱乐PR(physical recreation)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并进而指出身体文化“包括在体育(PE)过程中人体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人民体质增强的程度;包括在身体娱乐(PR)过程中身体技艺提高的程度;包括体育科学和竞技科学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从林先生对这几个关键语词之间关系的清晰描述可以看出,身体文化(PC)、体育(PE)以及身体娱乐(PR)和竞技(Sport),在概念上是有明显区别的。身体文化与上位的“文化”相比,其“种差”在于“身体”二字上。确切地说,身体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的差异性表现在“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上。由动的身体产生了动的文化。并由此“动”字动出了各式各样的身体文化。因此,“身体活动”是阐明身体文化内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为了将体育的动从体力劳动的动、艺术舞蹈的动、马戏杂技的动,尤其是运动竞技(sport)的动中区分出来,持有这种学术观点的人士进一步强调引入“合目的性”这一思想的必要性。因为只有有了这种“合目的性”的身体活动,体育才能从它的属概念(教育)中显示出它与德育、智育的差异性,而且也将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身体文化的“家族类似”的缠绕中标示了出来[6]。对体育(PE)而言,身体活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合目的性(强身健体)的身体活动,才能作为体育手段。
有了对这些关键性语词概念的科学理性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持“真义体育观”的学者始终坚持认为“体育(PE)的真义是健身教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不是运动竞技(sport-athletics)、休闲(leisure)、娱乐(recreation),体育(PE)不是体娱(PR)[7]”,以及“作为教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与作为身体娱乐文化活动组成部分的竞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8]”等旗帜鲜明的学术观点。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一步指出“竞技和体育不占一个层次,竞技教育跟健身教育或体质教育(体育)占同一层次[9]”。这为人们创建《健身学》、《健身教育学》、《竞技学》和《竞技教育学》奠定了理性认识基础。“真义体育观”犹如阵阵春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使渊源于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大体育观”第一次受到了强烈冲击,使体育界人士“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并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历来被我们所忽视的重于分析、偏爱区别的逻辑思维,其强大的魅力和力量之所在。正是这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和主张,才促成了行政管理部门在1995年颁布实施了影响深远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求在持续多年对PE和Sport概念的争论中达成一个新的平衡。
由于“真义体育观”这些非常清晰的学术观点是在排除人的情感与偏爱因素情况下,运用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推理得出的精密的科学论证,所以虽然它或许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考虑到我国的上层文化传统经常追求的不是科学性,而是道德伦理——美学境界,因此这些学术观点的确令积淀了“天人合一”、儒道互补、中庸思想的中国人,当然包括整个体育界人士,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不舒服、不习惯,让人觉得这种运用“工具理性”推导出的“真义体育观”铁定无情、冷酷如冰,因此说从认知层次上看,“真义体育观”无疑是科学的、理性的、先进的,是令人“可信”的,但这种观点却让习惯于用直觉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大多数国人感到“不可爱”。
3 “真义体育观”产生的哲学文化背景
一个民族的新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对着或者经过了一场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没有这种深刻的大背景,整个民族的新觉醒是很难到来的;第二,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丧失信心,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那么艰难,只要奋起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并且看到了新的出路。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他的结局,正是从以上这两个方面同时给了中国人空前未有的强刺激。这场战争把中国旧秩序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往中国是被西方大国所打败,而这次却是被他们看作是东方小国的日本所打败,而且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么苛刻,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天津《直报》(1895年5月1~11日)上发表了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自19世纪末的甲午(1895年)戊戌(1898年)期间开始,西方哲学与文化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因为,尽管以前西方的坚船利炮轰破了中国的大门,但从表层到深层,儒学地位和传统以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并未受到影响。中日战争的失败才是真正的转折点。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似乎说明仅仅“船坚炮利”、引进现代西方的工艺科技等等“西用”,并不能拯救中国。因而这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重心已开始从外层的改变(如学习西方文化的“船坚炮利”等器用特征),中层的改变(即制度的改变,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变法维新”),转向内层的改变(如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的思想理论)。文化的改变到了这一层,实际上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反击。因此,在对待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态度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派思想、三种倾向,即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或“西体西用”派,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西体中用”派。这三派思想可说是开20世纪各派思想的先河[10]。
中国近现代化问题反映在哲学方面,即“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又集中表现为如何看待西方哲学这个根本问题。
冯友兰先生[3]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的哲学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但第一个吸引中国人注意的不是别的,而是逻辑。”而最早将中西哲学的比较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的,则是严复。严复是在近代中国最早讲逻辑学的人[11]。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天演论》、《法意》、《原富》的4部书,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严复眼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实导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逻辑思维方法。
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的巨大刺激下着手翻译《天演论》的。不但在严复的所有译著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的所有译作中,《天演论》是影响最大的。严复的《天演论》之所以能引起巨大影响,主要是该书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根据中国当时首次面临帝国主义各国大规模入侵,要求“瓜分中国”的危亡现实,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而作。所以鲁迅称赞严复是“感觉敏锐的人”,认为严复“做”的《天演论》确乎已不同于赫胥黎的原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了(《热风》)。严复强调“天演”是任何事物也不能避免的普遍客观规律,明确指出,生物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严复要人们重视的是:只有自强、自力、自立、自主,不断进化,才能生存、发展,否则就要被淘汰而归于灭亡。而这才是严复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思想的真正动机和核心。这是《天演论》的独创性之所在,也是此书及其思想长久风行、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11]。
在中国近代的“尚力思潮”史中,严复的确起着一种开启先河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可以说,严复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伟大的体育思想家。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体育始终占据着第一位的重要位置,也不仅因为在他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随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括梁启超、谭嗣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杨昌济、郭沫若、毛泽东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群体“尚力思潮”之崛起,而更为重要的是,严复在倡导“尚力”的同时,充分意识到逻辑在学术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学习西方的“汽机兵械之伦”及学习西方的“天算格致”都不是学习西方的“命脉”,西方的“命脉”是“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2]他认为西方长处的根本在于科学(学术)与民主(政治),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把逻辑学看作“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并把逻辑等西学作为“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16],强调“正名”,即明确概念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严复这样高度重视认识论和逻辑学,自觉介绍经验论和归纳法,就眼光和水平说,在一百多年前确是凤毛麟角,极为难得。这一点就使他超过了前前后后许多人。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无疑对后人如毛泽东教育和体育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对毛泽东对体育的科学理性认识(从《体育之研究》,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着巨大影响。年仅19岁的毛泽东在自学期间就在湖南图书馆认真阅读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天演论》等名著,到解放后他多次指示广大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些都是逻辑问题。”以及严厉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可以看出毛主席一生都非常注重对逻辑的学习。这一点国内体育学者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所以,毛主席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数十年经验时,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并列,共同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并非偶然。
继严复之后,梁启超、胡适等人也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科学与科学方法。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的梁启超[13]称“论理学(即逻辑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胡适[14]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他尤其强调“假设”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将这种重视“假设”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十字真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后,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金岳霖、汤用彤、殷海光、张岱年,以及被李泽厚誉为现代新儒家的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和牟宗三,也对逻辑学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做过精辟论述。如具有广博的中西哲学修养并对其做出比较研究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3]就曾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并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他把逻辑分析方法比喻为像神仙一样能点石成金的“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并指出“中国人要的就是手指头”。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就曾提出这样的设想:“我们期望不久以后,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由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并认为,理想的适合中国现代社会需要的哲学应兼有二者之长[3]。
之所以逻辑思维方法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概因我们的祖先不好逻辑,这已成共识。有鉴于中国人历来轻视逻辑,以及体育界学人在探讨体育概念时常常不重视逻辑,因此,笔者提出了体育(PE)思维和竞技(sport)思维问题[1],并对毛泽东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所提出的“何为体育之真义”[15]、中国体育sports化问题[16]和“健康第一”与“增强体质”指导思想[17]作了深入分析。
4 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的永久性贡献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真义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永久性贡献。其主要表现在:从思维方式的层次上,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体育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体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是依据目前正风靡全国的具有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特点痕迹的“大体育观”所能构建起来的,而是依据如何更好地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的体质服务,以及怎样增强人民体质这一体育的根本任务去构建的。要构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必须依靠逻辑思维,必须重视并加强这一我们历来非常轻视的科学理性认识工具。逻辑是我们构建体育科学理论体系所必需的立论工具;从语词概念的层次上,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要构建一套完整的体育科学理论体系,首先就应走进体育语言,重视并加强体育概念的规范化研究工作。并旗帜鲜明地指出,体育不是运动、竞技、娱乐、休闲、比赛、游戏、奖牌,体育的真义是健身的教育,是增强体质的教育,这对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把体育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落实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根本任务上来,具有长期正确的指导作用;从实践层次上,为我们科学地指导全民健身活动树立起了三大理性支柱:即健身运动处方、最佳运动负荷价值阈和巡回锻炼法,从而使人们把健身运动的重点放在增强与健康密切相关的体质成分(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和力量耐力、柔韧性和适宜的身体成分)上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值得重视的是,在国内诸多学人对体育Sports化问题不屑一顾时,国外近年来体育科学研究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更加注重与健康有关的运动(health-related exercise,HRE)和“理性”或“概念”体育("Conceptual"PE)的研究。
美国学者Dale等人[18]就中学生暴露在“理性”或“概念”体育(CPE)和以Sports为基础的传统体育(TPE)课程情况下,对男女生形成久坐不动行为方式的影响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发现,形成久坐不动行为习惯的比例,上CPE课或者称为“个人健身课(personal fitness course)”的男女学生,要大大低于上TPE课的男女学生。这暗示,CPE课在促进青少年养成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的行为习惯方面,要大大优于TPE课。该文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目前美国至少有7个州以及国防部所隶属的学校都必须实施这种CPE课程,并认为,理想的CPE课程应包括两部分,即教授健康和健身概念的室内课,和着重于个人健身计划、自我监测、自我管理技能和非竞争环境的室外活动课。笔者认为目前美国正大力研究的这种CPE课,也就是目前国内持真义体育观点的学者一直坚持并大力倡导的体育健身课。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著名体育学者Charles B·Corbin教授[19]撰文指出,目前美国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主要以Sports为主,并列举了美国目前成年人主要采用的10种身体活动方式(走、园艺、伸展性练习、阻力训练慢跑、有氧舞蹈、自行车、爬楼梯、游泳和网球),发现只有列在第10位的网球是成年人采用的Sports活动,并指出,在成年人参与的各种Sports活动中,列在前几位的也主要是一些个人Sports活动(如网球、保龄球等),而参加集体性Sports项目活动(如篮球、排球、足球、橄榄球、棒垒球等)的成年人很少,强调指出在选择列入体育课程的各种活动内容之前,确定我们所要实现的体育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另一位美国体育学者Robert P·Pangrazi[20]撰文进一步指出:“当体育课程局限于集体性Sports内容时,这种课程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是过时的和毫无价值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Sports活动的人数会急剧减少。”并引用了1996年USDHHS的调查研究数据指出:“30岁以上的成年人不到5%从事这种集体性Sports活动。”强调“一种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应教授促进学生健康的终身身体活动,培养学生对身体活动积极的行为方式,是体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上述学者在体育权威刊物(均为SCI期刊[21])上发表的这些鲜明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我国持“真义体育观”的体育工作者目前对体育的认识水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而这些体育学者们对体育的上述科学理性认识,实导源于被誉为西方“命脉”的逻辑思维方法。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真义体育观”并没有受到我国体育界人士的足够重视,“Sport大体育观”至今仍在体育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固然有诸多原因,而最主要原因,与国人接受现代启蒙时没有彻底吸纳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有直接关系。而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逻辑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逻辑和逻辑思维方式正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征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只有区分开思维与存在、知识与道德、理想与现实等,才是中国文明完成自身启蒙、进入现代形态的一个根本标志[22]”,那么中国体育界学人只有在正确认识诸如体质概念中的身心关系、Sports与5P(PC、PE、PR、PA、PF)各自含义及其关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之后,才有资格来谈论中国体育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因为历史与现实已告诉我们:没有逻辑,我们的学术不会强大;没有逻辑,不会造就指导世界学术的大理论家,不会出现领导科学革命的大科学家。因此,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更应倍加珍惜我国诸多志士仁人对体育所持有的科学理性认识,从而在新世纪率领我国亿万人民走真正科学健身之路。把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的体质服务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真义体育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发展,而且它与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一样,必将成为检验体育工作和体育工作者是否真正为人民群众健身服务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准。在此,我想引用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23]在《青春》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并与各位同行共勉:
“人类之成—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