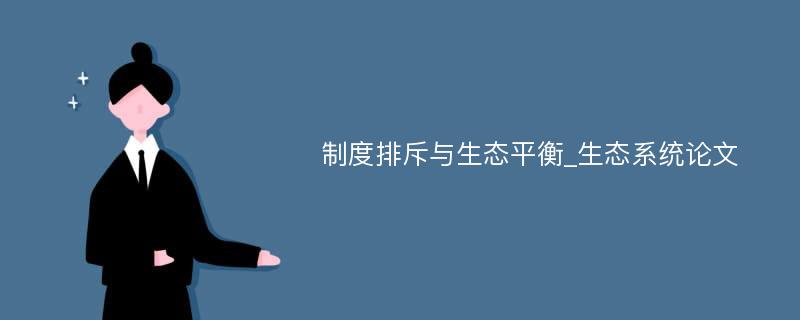
系统排异性与生态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平衡论文,异性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从系统论观点看,抗击“非典”是系统排异过程。系统排异性理论是近年来系统论研究的新成果[1],它为生态平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新方法。
系统的排异性是指一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性质和稳定而排斥进入本系统的外系统要素的特性。任何一个系统都是由其组成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正是系统诸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决定了系统的特殊组织形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系统结构。任何一个进入本系统的外系统要素都会或多或少地破坏该系统的有机联系和该系统组织结构的稳定。由于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有机联系,所以,系统的特殊组织结构将对进入本系统的外系统要素自动产生排斥作用,以维护本系统的性质和稳定。
系统排异性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生物种群系统对另一个生物种群的个体、生活习性、组织方式等构成要素是相排斥的,一般地说,一个猩猩家族是不会接纳一头狮子或一只兔子的,也不能想像这个猩猩家族会接受狮子或兔子的生活习性或组织方式。甚至于一个猩猩家庭对于另一个猩猩家族的成员也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每一生物种群都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相联系,从而形成特殊的依存关系,而建立在这种特殊依存关系之上的排异性则更为强烈。如生长在热带海边的椰子树在寒带山区的松林里就难以存活。从生物个体系统来看,排异性也是明显存在的。如人的器官移植,移入的器官都必然引起机体的排异反应。
系统并不是对所有外系统要素都不加区分地绝对地排斥。对于一个开放系统来说,它必须经常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正常状态,这就要求系统必须有选择地对待外来要素。一般地说,系统只是极力排斥那些有可能改变本系统的性质、危及本系统安全的外来要素,而对那些有益于本系统的外来要素则是尽力消除或抑制自身的排异性,积极吸取和引进这些有益的要素,使之为本系统的繁荣和发展服务。外来要素进入新系统后面临着系统排异性的巨大压力,如果能够迅速地加以调整和改造,使自己符合新系统性质的要求,它就可以逐渐成长为该系统有机联系的一部分。
系统的排异性与系统的有序性和目的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系统的有序性越强,排异性也就愈大。任何系统都具有一定的有序性,构成系统的要素都是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组合的。系统的有序性越高,系统的内在结构就越严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就越密切,因此,排异性也就越强。其次,系统的目的性的自觉程度越强,排异性也就愈大。目的性是一切生物系统的最根本的特征。生物界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的系统,它们的目的性是不同的。在较低层次,如植物、动物等,它们的目的是自发的,仅在于生存和繁衍,即只具有“自在目的”。而较高层次的系统,如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人类社会,它的目的不仅在于生存和繁衍,而更重要的是发展,是实现理想社会目标,它的目的是“自为目的”。在这种目的性的自觉程度较高的系统中,围绕着既定目的就形成了特定组织形式的系统结构和特定方向的系统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进入该系统的、有碍于该系统实现其目的的外来要素,都必然会受到该系统的强烈排斥。而动物、植物这类只具有“自在目的”的系统的排异性将逐次降低。
系统排异性的存在也是有条件的。首先,它在只有少量外来要素进入本系统时能够发挥作用,而当大量外来要素涌入,“淹没”了本系统时,排异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其次,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的外系统的“强势要素”进入本系统,可能导致本系统组织结构的严重破坏,而产生于系统组织结构中的排异性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也可说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系统的排异性是通过系统的破坏或毁灭表现出来的。
系统排异性对于生态平衡的稳定发挥着重大作用。生态平衡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其二是指环境系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建立的动态平衡联系[2]。生态平衡要求生物物种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要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而系统排异性正是保持这种稳定的重要机制。一个生物种群对外种群要素的排斥,是由这一种群内在的有机联系和维持种群性质和稳定的要求所决定的。这种排异机制使得有可能改变种群性质、危害种群安全的外种群要素难以进入或难以生存。而对那些有益于种群繁荣和发展的外种群要素,则是尽力抑制自身的排异性,加以吸取和接纳,并积极创造条件,使之成为本种群的组成部分。在系统排异性的作用下,各个生物种群不断排斥有害的外来要素,吸取有益的外来要素,使得本种群与其他种群之间,本种群与环境之间在相互作用中建立起一种动态平衡联系,维持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之后,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导致对自然界的“掠夺”的不断升级,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严重威胁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排斥或“报复”也在不断升级。要消除自然对人类社会的排斥,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生态化”的社会模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大自然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形成的,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使各生物种群之间处于相对稳定的、和谐的状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不产生危害生态平衡的“废弃物”。生物种群之间存在着“食物链”的相互关系,在“食物链”中,上一个环节构成了下一个环节的食物或生存条件。各生物种群之间的这种交流也是有选择的,在系统排异性的作用下,排斥有害的东西,吸取有益的东西,维持着种群的性质与稳定。当然,这一种群所排斥的有害的东西并不是自然界消化不了的“废弃物”,它有可能成为对其他生物种群有益的东西,从而被接纳和吸取。正是由于“自然链条”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使得自然界的各生物种群能够和谐地、持续地发展,并保持着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应当像自然界一样,建立起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类似“自然链条”的有机联系。同时,还要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向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的同时,维持自己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以求得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各要素之间并未形成环环相扣的、类似“自然链条”的关系,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并没有成为社会系统其他环节的“原料”,而是作为“废弃物”被粗暴地抛入自然界。大量的“废弃物”如废气、废水、废渣等等严重侵蚀着生态系统,当超出一定的限度时,就将导致自然界系统结构组织的严重破坏,其排异机制也就不存在了,从而导致生态失衡。实际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生态平衡不仅包括自然界内部各生物系统之间的平衡,同时,也应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交流基础上的动态平衡,这是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和理想目标。要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平衡的关系,必须使社会“生态化”,建立“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等等,消除“废弃物”,使之“资源化”,成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建立起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生态平衡”,才能消除自然界对社会的排斥或“报复”。
在开放系统之间的交流中,也会出现“强势要素”入侵现象。这些“强势要素”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能够迅速地抑制系统的排异性,进而破坏系统、侵占系统。在生物界,如果一个强势的生物种入侵另一排异性较弱的生物系统,则会造成该系统的破坏,引起局部生态失衡。在自然状态下,生物种群的存在都与环境紧密联系,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各生物种群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依存关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一般地说,各生物种群都有自己相对确定的地域,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强势要素”的入侵是很少见的。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入侵”现象则不断增多。澳大利亚早期移民带入的兔子以极快的速度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抑制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排斥。由于当地的生态系统缺少兔子的天敌,使得兔子大量繁殖,曾引起了当地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生物入侵”的情况。“生物入侵”现象在我国也很严重,“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森林、农业区、水域、湿地、城市居民区等,几乎到处都可见到外来物种入侵的现象。如水葫芦、牛蛙、豚草、紫茎泽兰、飞机草、薇甘菊、空心莲子草、大米草等等,都是目前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外来入侵物种”[3]。来自南美亚马逊河流域的“食人鲳”一旦适应了我国南方水域的自然环境,克服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排异性,形成新的种群,将会对入侵水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破坏。现在我国大约有120多种入侵动植物,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74亿元人民币。国内不同地域的物种的引入,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长江、珠江鱼种引入塔里木河,使土著种新疆大头鱼和塔里木裂腹鱼数量减少,处于濒危”[4]。可见,一些生物种群的“强势要素”可以轻而易举地冲破另一些生物种群的排异机制,迅速地适应这些系统,破坏其系统结构和系统稳定,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
随着基因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可以运用基因技术对生物基因进行重组,由此产生了大量转基因动、植物。目前,仅转基因植物已达35科120种左右[5]。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和林木等。这些转基因生物对于自然界生态系统来讲是“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它有可能给环境带来生态风险,甚至可能影响人类的健康。这些转基因动植物根据人类的需要改变了性状,具有了一些新性状,如抗病、抗虫、抗逆、抗除草剂、品质改良、发育调控等等。因此,对自然界生态系统来讲,转基因动植物是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强势要素”,大大超越了自然界生态系统排异机制的作用。在自然界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自然链条上增加了转基因生物这个新环节,无疑会给生态平衡造成较大的风险。现在这种生态风险已初露端倪,转基因生物与野生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可造成“基因污染”,从而有可能导致一些野生物种或稀有物种的灭绝。如墨西哥传统玉米受到外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的转基因污染事件[6]。“这事件对自然基因库造成了基因污染的后果。转基因逃逸如不断发生,会导致当地遗传多样性的丧失,造成遗传冲刷”[7]。此外,转基因生物的生态风险还包括“对环境中的非目标生物的影响”以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等等问题。由于转基因生物有可能影响到人类生存环境和食品安全,因此,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拒绝购买转基因食品的运动。这说明当转基因生物进入社会系统后,有可能威胁该系统的安全,因而引起了系统的排斥。
1996年英国罗林斯研究所首次成功“克隆”出了一只没有父本只有母本的绵羊“多莉”,标志着基因科技的重大突破。这种通过“细胞核转移”无性繁殖技术把生命科学研究带入到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使得“人造生命”成为可能。目前,多种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的“克隆”都已获得成功。从技术上讲,“克隆”人已没有大问题。但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很多,如自然链条对克隆生命的排斥程度如何?克隆生命有无生态风险?克隆人能不能融入社会等等。特别是克隆人已经引起了人类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已经遭到社会的强烈排斥。世界各国通过立法等各种形式禁止人的克隆。社会之所以排斥克隆人,主要是因为克隆人对社会系统的稳定以及社会伦理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如克隆人的身份难以纳入现有的伦理体系;人类繁殖后代如不需要两性的共同参与,将对现有家庭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成为恐怖分子的工具;大量基因结构完全相同的克隆人,可能诱发新型疾病的广泛传播;克隆人可能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产生心理缺陷,形成新的社会问题,等等。根据系统排异性原理,由于克隆人对社会系统造成了严重威胁,社会系统必然要强烈排斥克隆人,以维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由上述可见,系统排异性理论从一个新角度解释了生态平衡和生态失衡的现象,提示我们如果人类实践活动和科技创新只重视技术和效率,而无视自然界生态平衡和社会系统的安全及其精神生活的内在要求,就必然导致自然界和社会的强烈排斥。系统排异性理论是系统论研究的新尝试,为我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当然,它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
收稿日期:2003-05-21
标签:生态系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