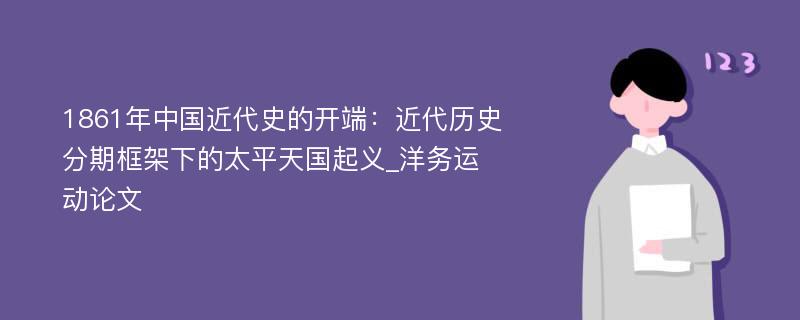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近代史分期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近代史论文,开端论文,框架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11—0070—06
一、1840年开端说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变局,影响极深远。史学界一般是将这次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放置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的。在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也曾被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被划分在起始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终止于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的近代史第一时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参考变量。太平天国起义被置于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假定的大时代背景下,并因此被认为不同于传统农民战争,甚至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近代史分期的讨论因分期标准问题产生分歧。胡绳同志认为“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划分时期的标志”。这样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正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所以环绕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备已不同于以往在封建时代的历次农民战争”,而且“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趋向于用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他们在不损害封建势力的范围内,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的外壳”。① 胡绳同志所说的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外壳的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是指“洋务派”。孙守仁同志是“外因论”的代表。他注意到“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他们使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他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② 黄一良同志坚决反对孙守仁的外因论,他认为既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历史”③,在肯定胡绳阶级斗争标准的同时,强调其“内因论”命题。金冲及同志则对阶级斗争内因论标准和外因论标准做了折中。他确定了两个着眼点,即两个标准:一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二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在性质上的变化”。④ 前者因为存在一个所谓“半殖民地化”问题而肯定无法回避“外因论”。而真正对太平天国起义何以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中国近代史第一时期做出解释的,则是范文澜同志。他从起义的领导者拜上帝会和起义后来在长江地区得到发展两方面论证太平天国起义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动大背景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他认为拜上帝教的来源耶稣教“包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道理,这些道理对中国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有相合之处。同时太平天国有反封建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资政新篇)”,并且“从后果看,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曾起到推动作用”。关于后者,他认为“广东有英国势力,太平军不能向广东发展,只能向湖南进军”,同时“长江一带受外国影响比北方大些”。为了强调内外因素的合力即反封建反侵略的结合,他认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两支主要革命力量,“李秀成在江浙一带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外国侵略,陈玉成在南京上游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封建压迫,分散的革命力量对抗结合了的反革命力量,失败是不可免的”。⑤ 戴逸同志的解释则进一步明确太平天国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他先从阶级关系的配备上,认定“城市平民大批卷入农民战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又强调“外国侵略势力已经通过鸦片战争而打入中国,因此处在革命形势第一阶段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群众已经在自己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外国干涉军的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他以“这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战争,客观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作为结论。⑥
这次讨论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降低,涉足者寥寥。其中李良玉教授对这次讨论,针对当前学术环境和近代史研究的任务,做了有益的梳理。他研究的意义在于打破长期以来把近代史分割为近代、现代两大块的习惯,而“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历史流程”,同时他认为“近代史分期的调整,不仅是叙事体系的更换,还包含历史观念更新的内容”。李教授尤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做了历史回顾和理论辨析。他没有涉及太平天国起义在近代史的意义问题,在他重新划分的近代史第一阶段中,太平天国起义结束的1864年不再被作为这一阶段的终止年份,而是被确定为1861年,从而对阶级斗争标准做出了突破。李博士认为“1861年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⑦ 但他忽视太平天国起义的意义,从而没有深化他对1861年标志性意义的认识,并依然墨守1840年开端说的格局。
笔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讨论,把太平天国置于鸦片战争后所谓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存在诸多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同时李良玉教授对太平天国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本忽视也有纠正的必要。
二、对1840年开端说的质疑
传统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江宁条约》的签订,领土开始不完整,传统自然经济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解体,因而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这个约定俗成的定论,其实不过是一个假设,它假定中国社会因为外部世界的冲击而自然发生变化,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将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任何变化,即便是因为外力压迫而被迫运动,也应该存在一个组织内部的内在驱动力,至少也应该存在这样一种驱动力的酵母。换言之,即使英国等西方侵略势力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也仅仅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提供了可能。具体是否发生变化,变化的趋势和进度如何,则都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即满清朝廷和绅士精英集团的认识能力和变革意识。英国割占香港岛的确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是否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则不可能像土地的割占这样直观。西方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里只能冀望于借助通商口岸向中国内地缓慢渗透。而这是否也能够同时引起中国政治主导力量的有意识的变革,则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因素,更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变革,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仍旧顽强地维持着。即使有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上海,且全部为外资。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没有兴办本民族自己的实业,特别是中国统治集团和绅士精英阶层,除了少数民间知识分子如魏源,对时局做出一些冷静分析外,统治集团根本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萌发出变革意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仍然因循旧例。茅海建教授在其《天朝的崩溃》中感叹“天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他是对鸦片战争的所有当事人进行了思想与行为的综合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茅教授发现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道光皇帝“并没有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在他执政时期,甚至最容易起动的“器物”变革也没有认真落实,由此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更无从谈及。茅教授总结到:“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胁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道光皇帝的消极态度自然深深影响了他的臣子。茅教授分析的办理过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事务的清朝大员中,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等对自己的战争经历几乎没有任何感悟,耆英、黄恩彤走上了“柔夷”的极端,刘韵珂虽然玩弄权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阴制”英使德庇时,但不过是蹈袭“抚夷”的老谱,而最为后世尊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尽管“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从神光寺事件,可看出他并没有吸取战争教训⑧。这说明中国的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并没有被战争的失败“打疼”。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虽然对洋人的“利器”有所忌惮,但是依然留恋固有的思维定势和行政程式。整个社会,至少是能够带动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变革的主导政治力量,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震动,以别于传统思维定势和行政规则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并有意识启动社会变革的进程,甚至仍然相信“夷”是可以通过“抚”或“阴柔”御于国门之外的。这导致处理外事的清朝官员根本无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自己的外交策略。如两广总督叶名琛,本是处理内政的高手,先审时度势,扼杀了太平天国旁支凌十八部,又处乱不惊,将围攻广州的红巾军一一击破。但在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外交时,他的知识结构由于并没有经过更新,结果对西方列强的外交举措处处判断失误,“没有看清西方列强的修约活动是其侵华的重要步骤”,仍然沿袭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老路,因此他便不可能判断出大规模侵略战争前的山雨欲来之势。⑨ 从广州等地的反入城事件来看,受官府纵容的绅士领导的民众斗争,仍然恪守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这种观念虽然仍然是“后来近代民族主义产生链条中的一环,是中华民族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觉醒的先声”,但也说明当时中国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绅士阶层并没有为将来的思想变革做好准备。通过反入城事件,中国人对鸦片战争失败所做出的反思或反应,表现为“只是一种低级水准的斗争”,⑩ 并未突破战前的认识框架和经验范围。中国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力量既然没有形成需要变革的共识,没有形成推动社会和民族吸收鸦片战争后新经济因素的意识,那中国社会是否由鸦片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命题,便值得质疑。对鸦片战争的思想反思,基本停留在民间著述的范围内,而且这些思想家的言论根本得不到主政者的重视,其政治作为更在体制内得不到舒展。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本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实践办法,但在当时根本得不到主政者的重视。于是魏源等人的怀才不遇,便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而由于启蒙思想家们的探索并没有物化为执政者的政治意图,这更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
既然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根据不足,那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阶段,且因为受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而承担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的论断也便显得牵强。上世纪50年代的讨论,因为论者们事先把太平天国划分在他们认为的近代史第一阶段,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太平天国起义找外因论的根据,即所谓反侵略的任务。当然太平天国起义也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尝试或第一次革命高潮,天然成为阶级斗争标准内因论的根据。他们在解释太平天国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时,甚至出现了一些违背基本史实的臆断。如范文澜同志认为拜上帝教的来源耶稣教包含着资本主义的道理,“对中国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有相合之处”。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猜想。即便拜上帝的教义来源于耶稣教,也早经过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改造,并且政治化,特别是在起义的策源地广西客家山区,甚至与最原始的降僮巫术结合,成为后来政教合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全无关涉。他还以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起义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倾向的例证。其实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其主要政治目的仍然是出于维护洪秀全绝对君主权威的政治斗争需要。(11) 其文本尽管确实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但充其量停留在预案阶段。特别是《资政新篇》制订后,并未有效指导太平天国后期的农村政治工作。相反,是农民将领李秀成,在充分总结前期地方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建设的新思维,成为太平天国政治的亮点。在进一步的解释中,范文澜同志夸大长江流域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程度,为太平天国起义寻找资本主义因素。其实长江流域当时仅上海一隅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波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长江流域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况且太平天国选择进军长江流域,也根本不是因为长江流域受外国影响比北方大些,而是因为经过两年多的流动作战,太平天国需要找到一个政治中心,以此为基地推进他们针对清朝的王朝战争。况且太平天国也长期未把上海方向作为主攻方向,也没有理会来自上海小刀会的响应。范文澜同志甚至为太平军的两位后期主将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规定了反封建和反侵略的任务,为他的理论安排证据。这些也完全不符合史实。这种倾向在戴逸同志的观点中也有表现。他认为阶级配备上“大批城市平民卷入农民战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因此这样的农民战争将“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关于所谓城市平民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另一场关于太平天国性质问题的讨论中,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质疑。
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实践,因为他们并无意推行激进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具体施政仍然遵循着“照旧”原则,又由于太平军普遍崇尚旧有的征贡手段,并未有意识改变行政工作作风,以及乡官们利用太平军贵族缺乏地方行政经验之机大肆中饱私囊,结果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基本没有实现平等与公正的原则,其最高施政水平也仅仅通过颁发田凭,在法律上重新确认原业主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影响便仍然停留在他们的对立面清朝的水平,并且清朝农村问题的两个焦点——因人地矛盾而导致的土地问题,与因地方行政腐败而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太平天国均未有效解决。因此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村政治实践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即便他们有一条儒家化的政治轨迹,也无从改变他们施政总体水平的低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尽管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因其实践意义的苍白,而注定不能作为太平天国起义包含资本主义因素的证据。
三、中国近代史开端1861年说
然而,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的考察,却并不能因他们农村政治的不成功而就此停止,更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价值。笔者认为,既然鸦片战争不足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太平天国起义本身也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本主义因素,作为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的证据,那太平天国起义在近代史上的意义就需要重新认识。笔者认为,是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61年更是因为具有一系列标志性历史事件,而有理由作为近代史开端的年份。
首先,只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形成的《北京条约》体系,和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冲击,才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真正侵入中国内地,也使清朝统治集团开始真正有意识地改变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政治旧习,开始寻求解决中西冲突和摆脱内忧外患的新出路。
洋务运动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上至满洲主政贵族和督抚大员、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影响整个政治精英和绅士阶层的,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运动。虽然这场经过外战屈辱和内乱震荡带来的思考是苦涩的,甚至是不情愿的,但是不论怎样,他们开始平等地对待以前视作夷狄的西方侵略者,甚至开始有意识地适应条约制度,尝试在中西合作的背景下,共同重建经过英法联军之役和太平天国起义冲击的社会秩序。这一思想变革的可贵,在于这些行为人,是在痛苦地与自己的儒学背景和思维定势反复摩擦与互动后,才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的。“同治中兴”正是这一努力的产物。虽然即使在中西合作的蜜月期里仍然存在着讨价还价和明争暗斗,但是新的“夷务”毕竟代替了传统的“剿”夷和“抚”夷。总理衙门的设立和外国公使进京,都说明“满大人”的心态不再过激与高傲。尽管顽固派的力量依然强大,特别是在慈禧太后的权术驾驭下,洋务派不可能在朝堂彻底战胜顽固派,但是洋务运动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可贵的是,洋务派以主要为官办的方式建立起大量的实业。洋务实业或许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因为它可以不依赖市场的调节。但是这些实业一旦与民间资本结合,便不仅诱发了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如股份公司,也势将为民间资本的形成提供可能和开拓道路。因此洋务运动就不仅是一场精英阶层的思想和政治观念的变革,也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在洋务运动的条件下,才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如果说鸦片战争并未引起精英阶层整体的思想变革,而且民间启蒙思想也与主流政治脱节,因而使鸦片战争不具备作为近代史分期的里程碑意义的话,那在洋务运动时代,由于形成了一个上至洋务官僚,下至民间实业家和洋务知识分子的洋务社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这样就充分说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共同作用形成的变局条件下,二者的合力通过洋务运动,真正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拥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这其实是深入理解近代史分期问题,特别是近代史开端问题的关键。单纯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不能实质性地促使中国统治集团对自身文化背景和统治行为方式做深刻反思,并进而产生思想领域的变革。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没有对这次战争的经验做出总结,他的继承者咸丰皇帝是一位更盲目排外的皇帝,正是他的偏执引发了英法联军之役。而咸丰皇帝之后的执政者慈禧太后则是一位嗜权如命的宫廷女子,当然也不可能在自觉总结战争经验的前提下,寻找解决应付外部威胁新办法的见识。皇帝的意向自然会影响到辅政朝堂的政治气氛。这样的统治集团仍然有可能延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无所作为。于是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冲击和对统治集团传统行政习惯的考验,便显得意义非凡。太平天国起义者自身的农村政治实践,或许并没有他们对敌人统治秩序的冲击意义更重大。起义者对历史的贡献是通过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合力,作用于清朝的洋务运动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义者的鲜血换来了他们要推翻的统治集团的实质性的,虽然仍然是部分的觉醒,使那些双手沾满他们鲜血的刽子手们,成为新一代的洋务精英。这些刽子手们日后开创的业绩,或许是起义者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更不用说,正是太平天国起义才促使上海租界当局和清朝官府默契合作,完成条约制度下中国最典型的中西合作社会的构建,也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才迫使苏州大地主、清朝进士冯桂芬成为上海的买办,这在传统社会也是难以想像的。同时,也正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才使得清朝统治集团真正认识到当日变局之亘古未有。“咸同时期的大量事实已证明,满族贵族已经腐败无能,只是由于能被迫放弃主导地位,让出很大部分政权,换取以湘军集团为代表的汉族地主的支持,才得以度过难关。”(12)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等全国范围的大叛乱,他们最终被迫承认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形成的湘淮势力,在部分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太平天国为中国洋务运动这样一场全民性的思想运动和生产关系变革,打出了一个新格局,这使太平天国理应成为一座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最后,1861年这一年因为以下三个标志性事件而有理由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起始年份。这一年,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失守;这一年,曾国藩在安庆的废墟上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一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意义。是年9月,天京上游的屏障安庆失守,导致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上游要地尽失,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天国政权在战略上已经陷于必亡境地。虽然表面上太平天国还保持着他们从1860年5月开始的扩张势头,1861年11月攻克通商五口之一的宁波,12月攻克浙江省会杭州。但是由于战略上更具决定意义的上游的失去,太平天国很快在湘淮军的东西夹击下崩溃。尽管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标志,但是他们失败的命运在1861年安庆失守时就已经注定。
1861年1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1月在安庆的太平天国废墟上,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大营内军械所。这两个事件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总理衙门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但是它毕竟表明清政府开始放弃固有的夷夏观念,以近代邦交的全新视角处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虽然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精英集团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个非正式机构而彻底改变固有的华夷之辨,即便最开明的满洲贵族奕忻也还不能忍受西礼觐见,其他洋务派官员们也大多在此事上恪守传统礼教。(13) 但是总理衙门的建立是一个良好的兆头,是中西合作的同治中兴的前提。在这一背景下,清朝开明的当权派,从中央官署到地方督抚,与外国驻华外交官中的温和派人士,都希望通过在条约制度下的合作,获得各自最大利益的实现。中国洋务派希望通过办洋务增强中国抵御西方威胁的能力,而西方驻华代表也希望更多通过和平外交手段为他们的政府和企业界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总之,总理衙门的设立为中西和平共处提供了外交平台。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理衙门的建立无疑具有全局影响。而曾国藩设立的军械所,虽然还不能算做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企业,但仍然可以看作洋务运动开端的象征之一。因为这不仅是对西方“利器”的真正实践,而且是洋务运动一系列实业的先声。因此安庆军械所的设立与总理衙门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综上所述,1861年无论对于太平天国还是对于清朝,都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太平天国,1861年预示着它作为洋务运动催化剂作用的历史任务行将完成,而对于清朝,它要承担的近代化任务在1861年才刚刚起步。
总之,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近代史分期问题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催化剂,体现着自己的历史价值的。太平天国政权本身的农村政治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任何资本主义因素,但起义者的战斗为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打出一个可以施展的新格局。相比之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整体性的政治观念的更新和新经济因素的引进,而1861年因为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太平天国安庆失守、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更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注释:
①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57年版,第7—8页。
② 孙守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商榷》,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2—23页。
③ 黄一良:《评孙守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37页。
④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6—47页。
⑤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0—72页。
⑥ 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30—131页。
⑦ 李良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⑧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第560—577页。
⑨ 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⑩ 茅海建:《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3—116页。
(11) 王明前:《洪仁玕新政失败原因新探—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
(12) 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13) 茅海建:《公使驻京本末》,《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237—245页。
标签:洋务运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第一次鸦片战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政新篇论文; 茅海建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