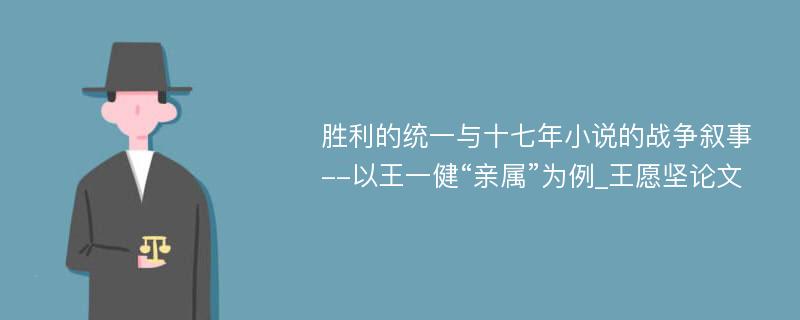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例证论文,亲人论文,战争论文,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1-0112-03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普遍采用的一种结构模式,其突出特征表现为 以革命的必然胜利作为主要的叙事话语,并以此来结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但战 争的基本形式是杀戮,即使最终取胜也定付出相应的代价:房倒屋塌、土地荒芜、家破 人亡,中国的民主革命战争也不例外。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十七年小说究竟是怎样营 造大团圆结局的?在此,王愿坚的《亲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典型的解读文本。
王愿坚作为革命战争小说的代表作家,常常从生活的细微处着眼,极力表现革命战士 在极端困境中所闪耀出的精神光芒——对革命集体的无限忠心及其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 。《党费》、《七根火柴》、《亲人》莫不如此,只是《亲人》一直未受到重视。
作为短篇小说,《亲人》的情节并不复杂:解放初期,衰老病弱的曾老汉苦苦寻找因 参加革命而26年未有音信的儿子,他给与儿子同名同姓的曾将军写信,想证明一下是否 是自己的儿子。其实他的儿子早已在红军过草地时牺牲。曾将军了解真相后,出于阶级 友爱冒充老人的儿子给他回信并按时寄钱寄物,但并未从情感上真正认同这个“父亲” 。曾老汉因思子心切,从遥远的江西赶到北京来和“儿子”团聚,现实状态中的不忍心 、历史情景中的阶级爱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曾老汉为了革命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一个儿 子和一双眼睛),使将军彻底完成了自我情感的转换,血缘亲情在“伪装”下得以延续 ,革命战争向老人流露出脉脉温情,小说在大团圆中结束。
《亲人》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解放后,没有直接描写民主革命的战火硝烟,但写出了硝 烟散尽后遗留在战场上的受伤的人:战乱使子失怙、父丧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 认为这是对战争的更深切更细微的叙述。从这个切入口,我们看到,作者似乎马上就要 拓展出对灾难的深层心理感知,显示出对战争的非政治言说,这归功于作者对生活的切 实体察。但作者对此浑然不觉,他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胜利大团圆走去,他以超 血缘的阶级爱为解决现实难题、消除战争灾难的法宝,理直气壮地让失父的将军为抚慰 孤苦的陌生老人而冒充其子,并以极大的耐心细致地描绘出了将军的情感变化历程。可 见,“胜利大团圆”并非真的没有灾难、死亡,也并非作者真的没有看到这些苦难现象 ,而是作者有意以阶级集团的最终胜利化解、替代个人的悲哀。
事实上,《亲人》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替代:一是题材内容层面的替代,即曾将军替代 曾老汉的儿子;一是主题意蕴层面的替代,即阶级爱替代血缘情。小说凭借这种替代最 终完成的是歌颂阶级爱的主题,化解的是战后人们的个人悲哀。而所有这一切都依存于 第一层面替代的可信性,即怎样使曾将军能够冒充曾老汉的儿子并愿意接受陌生的曾老 汉为自己的父亲,换言之,作者一定要写出曾将军情感过渡转变的细微处和现实可能性 。这决定着曾老汉的寻找结果,也决定着小说主题表达的成功程度,更影响着读者阅读 感受。如果描述失真,所有的主题承载将全部塌陷。庆幸的是,王愿坚的描写是可信的 ,他不仅细致地描写了曾将军能够冒充的可能性,而且使这种冒充最后转变为真正的“ 替代”。
曾将军能够冒充曾老汉的儿子,最直接的原因是曾老汉自己不明真相,他不知道儿子 早已牺牲,也不信儿子会死,所以才给同名同姓的曾将军写信。曾将军的回信使他决定 到北京亲眼看看儿子,但即使面对面,他也无法判断儿子的真假,因为他的眼睛不好, 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视力,再加上26年的时间跨度,儿子的具体相貌已茫然莫辨,仅有的 几个不相符合的特征也都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如年龄问题,曾将军含糊过去,没有 说出自己的真实年龄;如左手拿筷子的问题,曾将军解释为左手在战争中受伤而改为右 手拿筷子;“嘴角的瘊子”问题,曾将军的妻子回答:“嫌刮胡子不方便,早就弄掉了 !”曾老汉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你是大旺子?……”“你是我儿子?……”。在得 到肯定的答复后,曾老汉自己也认定了这一事实,自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不明真相的曾老汉因眼睛不好、思子心切能够认曾将军为儿子,但明白真相的曾将军 怎么能够愿意接受陌生的曾老汉为自己的父亲?小说没有滞留于表层的冒充,而是细致 地描绘出曾将军“亲人”认同感的产生历程:曾将军最初看到“吾儿见字”的信时,哈 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但当他读完信后,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等到明白真相回信时,他无论如何都不忍心如实地告知老人,又想到“我这条命是战友 给的呀!”于是决定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每月寄钱寄物但并未从情感上真正认同这 个“父亲”。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曾老汉的儿子,自己的父亲早已被国民党杀害 。但当他面对从遥远的江西赶到北京来和“儿子”团聚的老人时,发现他几乎失去了所 有的视力,将军更无法将“我不是你的儿子”说出口。而在得知老汉是为了反抗白军而 失去视力时,曾将军才将过往的战争年代和眼下曾老汉的现实联系起来,“仿佛直到现 在,将军才更清楚地体会到为了革命胜利人民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对于这些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一切的人,你怎么爱他们也不会过分的!’他觉得自己的心和老人靠得更近 了。他深切地抓住了老人的手:‘爹,那些年你可受了苦啦!’”至此曾将军对老人的 认识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而是已渗透到自己的感情之中,曾将军在打消老汉的 种种顾虑的同时最终完成了自我情感的转换认同。这样,作者就把阶级爱与血缘情胶合 在一起,使它们浑然一体,阶级爱以亲切的情感为基础,并以大家都能接受、理解的方 式代替了血缘情,达到了胜利大团圆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曾老汉的思子之情及衰老病痛,引起的不是曾将军对战争的清醒认识 ,而是恻隐之心和奉献的冲动,曾将军的情感变化引导着读者去赞扬阶级爱的美好,并 从心底生发出对革命将士的崇敬之情。曾老汉的人生伤痛不仅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且 被转换、化解为阶级爱的有力佐证。换言之,战争灾难在作者王愿坚心底引发的不是对 战争的反思,而是对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集体主义的礼赞。其实,阶级友爱既是革命者的 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的崇高无私品格,其实质上也正显示出战争的残酷性,在战争中 个体生命在伟大的整体事业面前微不足道,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事实证明,强大的 集体一致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是一条比任何类型的友谊更结实的纽带,“暴力的实施把人 作为整体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条巨大锁链上的一环,都是暴力这一呼啸而起 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1](P30)。以战争年代的阶级爱为坚定信念的王愿坚,并没有看 到这种阶级友爱的真实根源。他在小说中多次叙述到曾将军不忍心让曾老汉绝望,其实 这既是曾将军的不忍心,更是作者的不忍心,而这种不忍心正是战争残酷性给人的心理 感受,作家因不忍心面对战争的残酷性而满足于社会层面的胜利大团圆,使战争的灾难 性后果从作者的叙述中淡化以至消失了。
《亲人》的这种以“替代”来营造大团圆结局的做法并非个别,而是十七年小说中的 一种普遍存在。几乎所有的革命战争小说,都极力描写革命信仰、阶级友爱是血缘情所 无法比拟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敌人把杨晓冬带到他妈妈的牢房,妄想以母子之 情动摇其意志,杨妈妈识破敌人的诡计,勇敢地跳楼自杀;《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一 家,也面临着两种尖锐对立的选择:出卖革命同志活下去,或者掩护革命同志用生命来 冒险。小陈一家选择了后者;《苦菜花》中,仁义嫂子被严刑拷打后,又眼睁睁地看着 敌人杀死自己的幼女嫚子,但她始终没有告诉敌人兵工场的位置;《红岩》中,江姐在去川北的路上看到丈夫的头被割下挂在城墙上示众,她强忍着悲哀与眼泪去执行任务……在这种种悲壮而催人泪下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阶级爱对血缘情的战胜与超越,体会到的是革命信仰的魅力和阶级大家庭的温暖团结。其中杨妈妈跳楼自杀的悲 惨、无辜儿童嫚子的被残杀、小陈的家破人亡,既不是用来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也不是用来展示个体生命的珍贵短暂,而是用来表达革命胜利的取之不易,用来歌颂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及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于失去亲人的个人伤痛则被阶级的最后胜利所冲淡、化解以至悄然消失。死去的人物将在意识形态的符号意义上获得不死的承诺,并因此而在“烈火中永生”。
可见,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伤亡从未作为纯粹生命现象的自然状态被叙述,而是充分 地显示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这是因为作家不是站在人类或个体的立场上看战争,而 是站在具体的政治集团的视点来描述战争,作家的这种自我身份意识,使叙述人完全以 国家、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与价位来判断与评价战争及其伤亡,作为个体的人面对死亡的 感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则处于空缺状态,这是叙述人的主体定位所带来的遮蔽。“叙述 人的主体定位是一个‘前语言’问题,它决定作者的写作行为将以何种角度向人、向生 活、向经验切入,决定作者对叙述方式的选择(语式、语态等),也决定文本的组织结构 方式,并最终制约意识形态的传达。”[2](P15)国家、政府代言人的身份使十七年的小 说作者自觉从阶级、集团的利益来判断与评价战争及其伤亡,以集团的最后胜利化解个 体的过程悲苦,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满足于社会层面的胜利大团圆,而根本忽略探索 战争对于个人生活、命运的影响。更何况当时更多的作品只是在战争背景下铺衍一些胜 利大团圆的英雄故事,根本没有达到《亲人》所具有的形象化,也没有写出人物情感变 化的内在理路,从而失去了可信性。这种高扬阶级爱、抑制血缘情的价值取向,在后来 的“样板戏”中发展为毫无血缘关系的革命家庭,造成人物的阶级性对人性的彻底排斥 。
小说对战争的这种叙述,除了作家的自我身份定位的原因外,也反映了特定的社会文 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 是讲述话语的年代。”[3]《亲人》创作的年代,中国是个一体化的社会,包括一体化 的文化机制、单向度的社会语境和单纯明朗的社会心理,作家处于社会意识的中心,创 作中言说得更多的是权威意识形态,作家及其创作都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生的豪迈乐观 ,常自觉不自觉地营造胜利大团圆的结局。
总之,胜利大团圆之所以成为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在于当时的社会 文化语境使作家只能站在集团、阶级的立场来观察社会和感悟人生,以民族、国家代言 人的身份言说革命战争,并因此而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体利益,以阶级胜利化解个人哀伤 ,以结局胜利抵消过程苦难,从而使小说只看到社会层面的战争结局而忽略了个体心理 的人生伤痛,根本放弃了走进战争这种极端境遇下人的心灵深处的努力,满足于表面的 胜利大团圆也在情理之中。
收稿日期:2004-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