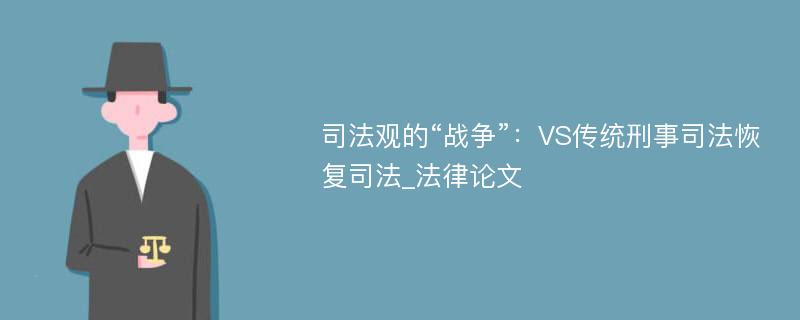
司法观的“交战”:传统刑事司法VS.恢复性司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恢复性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之提出:何谓司法?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传统司法在理论上的无尽困惑,特别是实践效果的巨大失败,西方刑法学界开始探寻一种全新的刑事冲突应对模式。此时,普遍存在于各国社会的传统解纷方式——“和解”,逐步进入了主流学者的研究视域,并在社会的急迫需求中,获得了迅速复兴的强大动力。以“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为核心,在实践与理论上逐渐发展出一套崭新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①
通常认为,美国学者Barnett最早提出了“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②在其1977年发表的大作《赔偿:刑事司法中的一种新范式》一文中,首先阐述了“犯罪人——被害人和解”试验中产生的一些重要原则,包括最为核心的“恢复性指向”。其后,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学术立场出发,相继提出了一些类似性的概念,如关系性司法(Relational Justice)、补偿性司法(Redress Justice)、社区司法(Community Justice)、平衡司法(Balanced Justice)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概念并非处于紧张与对立的关系之中,而是分别强调着恢复性司法的某一侧面,可以统一收归于这一整体形象之中。
由于恢复性司法的实践模式众多,理论内涵又异常丰富,因而很难达成一种理解上的共识。此时,一种明智而务实的思路,就是提取恢复性司法中的“公约性”因素,来帮助我们认知与判断。Jennifer J.Llewllyn和Robert Howse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在《恢复性司法:一个概念性框架》一文中,两位作者以其宏阔而精微的观察,提炼出恢复性司法的11个构成要素。它们是:(1)所有与冲突有利害关系的各方纳入程序;(2)认可和寻求对损害的处理;(3)参与程序的自愿性;(4)程序以陈述真相为前提;(5)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之间的直接会面;(6)保障被害人、犯罪人的权利;(7)程序辅助者的参与,以保障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8)以犯罪人、被害人重新融入社区为目标;(9)达成协议;(10)不以惩罚为内容;(11)以程序结果是否达到了恢复性效果为评估参照。③我个人认为,这11个要素具有宽阔的涵盖力与敏锐的洞穿力,完整而精炼地抽象出恢复性司法的硬核,可谓迄今为止对这一范畴最为精彩的概括。
然而,当这样一种司法模式,遭遇到强而有力的传统司法观时,就会使人感觉到明显的紧张与断裂。以往,占据人们理解中心的,乃是某种国家主义的、诉讼主义的刑事司法观:从狭义上讲,它仅仅是指刑事案件的审判;从广义上讲,它包括了从侦察到起诉再到审判、行刑的全过程。但无论做何种理解,刑事司法都被认为是专门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处理犯罪案件的诉讼活动。而“恢复性司法”,则是一种以社区中介组织为主导,并采用和解——此种灵活的非正式程序——来处理犯罪的一种活动。于是,一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从性质上讲,“和解”属不属于“司法”的范畴?以和解为核心形成的恢复性司法,虽顶着“司法”的大名,但究竟算不算是“司法”?
至少在两个关键点上,“恢复性司法”与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无法兼容:其一,主导机构。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唯一主导机构,整个司法程序乃是在正式国家机关的支配下运行。而“恢复性司法”则以民间组织为中立机构,在其筹备、协调和组织下进行;④其二,解纷方式。传统刑事司法以诉讼为唯一解纷方式,司法程序便等同于诉讼程序。而“恢复性司法”则以和解为基本解纷方法,其程序意识和具体规则与诉讼可谓相去甚远。一旦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无法调和,恢复性司法便难以融入传统的刑事司法范畴。
然而,如果我们不把正统司法观念看得不可置喙,如果我们不把正统司法观视为是唯一正确的司法观,“恢复性司法”就可能并非那么离经叛道。相反,它甚至会为我们开辟出关于刑事司法的另类理解。那就是,在更为开阔的法社会学意义上,刑事司法应该被视为某种“刑事解纷的解决过程”。这是一种脱离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脱离了诉讼中心主义限制的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在这里,不仅国家主义的司法仍有其重要地位,而且社区司法、社区——国家合作型的司法亦有其生存的空间;不仅诉讼方式仍构成刑事纠纷的基本解决思路,而且非诉讼的方式也构成不可忽视的、有作用力的程序选择。无论是依靠何种力量,无论由谁来主导程序的进程,无论借助哪种解纷形式,只要它通过某种法的运用,或是“通过某种规则的治理”,来解决刑事纠纷,就未尝不能算是“司法”。⑤这样一种理解,有效地抨击了人们的正统法学常识。它意味着人们深信不疑的国家、诉讼型司法作为司法唯一形态的原理的破灭,意味着一种更为开放的、多元主义的司法进路。
二、司法观的“交战”:八组关系的互动显现
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种主要的司法模式:报应型司法与矫正型司法。⑥这两类司法形态不仅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主宰着人们关于司法的理解。今天主流的刑事司法模式,乃是一种以报应为基底,同时有效糅合了矫正性因素的司法类型。
“恢复性司法”之于司法的理解,则与今日主流的刑事司法相去甚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独特的司法理念,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与我们当前主流的刑事司法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观察。这种比较,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恢复性司法观与主流司法观之间有何继承关系,又有何发展与突破,并进而展示,为什么恢复性司法在很多方面要优于现有的司法模式。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不仅将对现有模式的缺陷获得更为清醒地认知,而且,对于恢复性司法的未来命运,也可能有更为真切的体察。
从方法论上讲,这样一种比较的前提,乃是将当下的主流司法模式,与以刑事和解为中心的恢复性司法模式,视为两种“理想类型”。无论是报应——矫正性司法,还是恢复性司法,都总是有形态各异的实践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既有比较典型的样态,但更多的,可能是边缘的、非典型的样态。而作为这里的比较基准,则是一种经过思维加工的、最为典型的模式样态。此种Weber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实质上乃是一种“逻辑的理念类型”。⑦它作为某种思维抽象的结果,并非以纯粹的形式在现实中出现。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和可能,才将之作为思维上的存在。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从八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
(一)犯罪人中心主义司法与被害人中心主义司法
可以看到,传统刑事司法是围绕着犯罪人而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制度实践的理论基础,可以回溯到传统的刑事古典学派及刑事实证学派。在古典学派那里,关注的中心是犯罪行为,刑罚则是对犯罪行为道义上的非难。而到了实证学派,关注的中心从犯罪行为转移到了犯罪人,刑罚是基于犯罪人的危险性格而施加的某种社会防卫,或是对犯罪人危险性格的矫正。可以看到,无论是犯罪行为还是犯罪人,既往的刑事法理论总是将视点集中在犯罪的一面。正是在此种理论的辐射性影响之下,犯罪人被置于传统刑事司法的中心,而被害人则在刑事司法中被边缘化。这集中体现为:(1)在程序进程中,犯罪人具有支配性的影响,而被害人则不能对程序进程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对犯罪人赋予上诉权、再审申请权等权利,可以使犯罪人在一定范围内扭转程序的格局。而被害人则不仅不享有提出诉讼的权利,就连上诉权也被剥夺。被害人只能作为一个有作证义务、应随时配合的证人,参与到诉讼之中。(2)司法处遇完全针对犯罪人,被害人则被彻底忽视。在传统刑事司法中,犯罪人的处遇被置于中心地位。无论是报应性措施,还是矫正性措施,都是针对犯罪人来实施。只有犯罪人才需要以刑罚加以报应,只有犯罪人才需要以刑罚、保安处分加以矫治。对被害人物质精神损失的赔偿,对被害人回归社会的需求,则无须考虑。(3)司法以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为中心,而被害人的人权则被彻底遗忘。面对中世纪司法机关的野蛮擅断,当代的刑事司法异常强调客观主义的立场,其核心目标是以此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由此,司法权的行使被施以一系列的限制,如法定原则、比例原则等,犯罪嫌疑人则被赋予一系列的权利,如辩护权、沉默权、申诉权等,试图竭力保持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对抗平衡。的确,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犯罪人作为弱势一方,必须被倾注“同情之泪”。但是,在对犯罪人予以温情脉脉的关注的同时,被害人却招致了无情的遗弃。不仅被害人的情感体验,被司法体制视而不见,而且被害人的利益诉求,也只能淹没在对所谓国家利益的追逐之中。甚至,连对被害人最为基本的主体性尊重,也成为某种奢求。一个不愿意出庭的被害人,可能违反其意愿而被带到法庭。在极端情况下,法院对一个不愿陈述、又没有可说服法院之理由的被害人,还可以施加强制处分措施,如强制监禁。对被告人或罪犯的需要和权利不能满足,动辄就被上升到人权问题;而对被害人需要和权利的遗忘,则被视为正常。⑧
在今日的刑事法理论看来,犯罪与被害,就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犯罪事件绝非犯罪人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一种“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过程”。被害人不仅可能在犯罪的发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催化、导引或是诱发作用,⑨而且在整个犯罪事件的进程中,始终与犯罪人处于博弈和抗争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其切身利益遭受了现实损害。因而,被害人必须被视为犯罪事件的不可或缺的一方主体,在司法中得到主体性的尊重。
在这种全新理念的支撑下,恢复性司法将被害人置于司法程序的中心。在这里:(1)被害人在程序中取得支配性的权利,开始主导程序的基本进程。被害人是否同意与犯罪人展开和解,将直接决定案件的走向:是继续在国家追诉的道路上前行,还是另辟蹊径,纳入另一种纠纷解决程序;被害人是否接受犯罪人的责任履行,并与犯罪人达成和解,将直接影响案件的最终结局:是停止追诉从而对行为予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减免刑罚,还是维持刑事追诉并予以常规化的处罚。(2)对被害人的物质赔偿和精神慰藉,成为刑事司法处遇的重要关怀。刑事司法的处遇,不能只是围绕着犯罪人展开。固然,犯罪人的恶行需要一定的惩罚,犯罪人要重返社会也需要相应的矫治,但是,被害人作为司法过程的主体,其利益与需求同样值得认真对待。特别是,在犯罪发生之后,被害人不仅在物质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在精神上也遭受了极度的创伤。他们不仅要背负严重的心理阴霾,而且平日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安全感、控制感和自主感也被彻底摧毁。他们迫切需要帮助,需要重新融入健康的社会生活。因此,并非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犯罪人才需要“复归社会”。事实上,被害人同样需要“复归社会”。惟其如此,刑事司法的处遇措施,必须要考虑被害人,考虑被害人的现实需求。(3)被害人在司法中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对自己的利益有更为充分的表达。恢复性程序从最初的筹备,到协商的开展,再到协议的最后达成与履行,都必须依赖被害人的充分参与。可以说,没有被害人的参与,程序根本无法启动,更无法推进和展开。伴随着被害人对程序越来越深的介入,其情感的表达、需要的满足、利益的伸张都变得更为直接,也更为充分:在和解的准备中,被害人可以表达对主持人的期待,对犯罪人态度的期待,对会面时间、地点和氛围的期待;在会面中,被害人可以向犯罪人及社区公众袒露心扉,将被害的痛苦、被害对自己正常生活的影响,真切地传达给听众。被害人可以直接了解犯罪背后的真实原因,亲身聆听犯罪人的忏悔,并畅快地对犯罪行为予以谴责;在协商的最后,被害人可以直接表明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立场与态度,对犯罪人责任内容与形式的基本意见。可以说,在恢复性程序中,被害人获得了比以往任何司法体制更多的参与机会,更充足的利益表达。
总之,在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中,被害人必须作为自治性的主体被纳入,而不能再沦为某种刑事司法的客体;被害人必须在程序中具有支配性的权利,主导程序的基本进程,而不能再成为某种“有作证义务”、应随时配合的证人;被害人必须在程序中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对自己的利益有更为充分的表达,而不再是刑事司法的看客;被害人必须取得实质的物质赔偿和精神慰藉,这必须成为他们不可撼动的基本权利,而不再是“为了震慑犯罪的需要”或是“施舍与同情”。
当然,也必须看到,恢复性司法并非认为,只有被害人才是唯一关注的对象。毋宁说,恢复性司法也同样关注犯罪人的责任承担和重返社会,关注社区安宁的恢复和社区和谐的重建。只是说,针对以往刑事司法眼中只有犯罪人而彻底遗忘被害人的状况,恢复性司法更为强调对被害人的关注。
(二)国家专权式司法与国家——社区合作式司法
以往,犯罪被视为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挑战,因而,在刑事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对犯罪的回应权力自然被国家所独占。国家成为整个解纷过程中绝对的垄断者,不许民间力量插足。犯罪被认为与社区毫无关系,司法中根本没有社区的位置。这是一种由国家专门控制、由国家“独资”投入的专权式司法。附着在这一司法体制背后的,乃是某种国家全能主义的司法观:所有犯罪都被认为是侵犯了国家的利益,而应当由公共力量体系来处理。公共权力的触角可以无限延伸,无所不及而又无坚不摧。国家具有无限的能量,完全有能力建立统一的刑事司法体系,并举全国之力处理所有的刑事犯罪。公共司法体系是社会正义的唯一代表,而社区力量的任何介入都必须严加拒绝。因为,民间力量的每一次涉入,都可能会在实质上削弱公共权力机构的意义与威力,甚至使人们无视它的存在。由此,国家必须垄断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才能获得自尊与自足。
然而,我们要问,既然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被认为是最没有效率的,那么,在犯罪控制中,是否也是如此?国家垄断型的司法控制模式能够高效处理犯罪吗?
事实上,此种司法模式在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首先,国家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在将所有刑事解纷予以“公共化”的同时,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却逐渐暴露。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刑事案件的受案率呈现出扶摇直上的态势。这使得本已十分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加难以为继。1972年至1977年,美国监狱的收容能力增长了约23000张床位,但同期的监狱人口则增长了81000人。由于司法资源的严重不足,到了1984年,州一级监狱所关押的人数已超过了关押能力的10%左右,而联邦一级监狱更是达到24%之多。⑩其次,国家司法的效果低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为监禁与矫正制度的失败。近30年来,西方国家进行了无数次的实证研究,试图在监禁刑与犯罪预防、犯罪人矫正方面建立起积极联系,然而,却始终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监禁刑对于犯罪预防与矫正的正面作用。相反,倒是有许多数据表明,犯罪人在接受刑罚之后,其再犯可能反而比不受惩罚更高。(11)再次,国家司法的固有缺陷。国家司法通常只能在犯罪产生之后发动,而不能在犯罪的萌芽阶段介入,属于某种被动的、事后型的司法。司法机关对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犯罪隐患往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偏偏习惯在犯罪发生之后露出狰狞面目。这导致国家司法对犯罪事件的预控能力不足;国家司法虽然拥有法律上的权威,但是,在促进犯罪人道义上的觉醒方面,在促使行为规范内化为道德直觉的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正如普雷尼斯所言,我们要求政府改变犯罪人的道德观念,是提出了它根本不适合承担的期望。(12)因为,虽然刑事司法系统拥有法律权威,但道德权威则存在于社区之中。
恢复性司法的出现,则使控制司法的基本力量发生了重新分配。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所有的刑事解纷,不但力有未逮,而且在相当情况下会产生失灵。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社区在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此种反思的起点,就是重新理解犯罪事件。如果把犯罪视为个人对统治秩序的挑战,就将直接掠过社区这一中间环节。如此一来,犯罪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与社区毫无干系。然而,犯罪总是在一定的社区中发生,其不但会对社区其他成员的安全感带来重大挑战,而且会使健全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社区交往蒙上阴影。更为重要的是,社区构成了个人与国家的中介,任何对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等公共层面的影响,都必须透过这一中介才能传递。不可能想象,对社区毫无危害,却会直接对公共秩序和国家利益带来损害。因此,犯罪必须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社区冲突,其次才可能视为个人与国家的争斗。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社区不仅是犯罪事件的被害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犯罪事件的制造者。因此,社区也必须对犯罪肩负责任。正是这一犯罪观的转变,导致了社区在整个刑事冲突解决过程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社区再不是某种旁观者的角色,而是与纠纷的处理有切身利害关系,因而必须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加入进来。
当社区成为司法的一种力量之后,社区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将更为积极与全面。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其一,在当下的解纷处理中,作为某种中立的角色出现。很多和解项目都是在社区中介组织的主持下完成。其二,从长远的纠纷化解来看,社区的作用更为全面。例如发展社区安全项目,重建社区行为规范,加强社区道德建设,帮助弱势群体,健全社区教育等。其三,值得特别强调的,社区对于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服务。因为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人,而且“被害人恢复”过去被长期忽视,所以社区特别注重对被害人提供有益服务,以帮助其重返社会。这些服务项目包括:(1)支持者在庭前会见被害人,如果必要还可以陪同被害人参见程序;(2)为被害人开通“危机热线”,通过电话与被害人沟通并提供咨询;(3)为被害人提供避难所和“安全之家”;(4)警察、牧师为被害人提供咨询意见;(5)被害人干预项目(Victim Intervention Program),在接到第一次报警电话后迅速介入;(6)修复项目,补偿被害人的部分损失;(7)对被害人予以“交通援助”;(8)为盗抢被害人提供“换锁和维修服务”;(9)支持团体介入;(10)来自学校、社区、机构或者政府的被害人调查人员充当被害人的联络人;(11)开展对被害问题的训练和教育项目。(13)此外,社区也非常重视对犯罪人的监督和服务。在监督方面,主要是建立起对犯罪人承担责任的跟踪机制,确保和解协议的执行。在服务方面,主要是加强犯罪人的技能培训,为犯罪人提供工作机会,帮助其与其他社区成员加强联系等等。
当然,社区功能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司法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只是,国家的角色必须相应进行调整。一个总的倾向是,国家开始逐渐从一些司法领域中撤退,从某些案型的处理中解放出来。但是,国家仍然在以下层面起着关键性作用:(1)对恢复性司法的授权与推动。恢复性司法作为在正式制度边缘生长起来的一种实践,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得到国家的正式授权与承认,从而取得合法化的地位。从世界范围内看,国家对于恢复性司法的开展,始终起着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国家在正式司法的领地内开辟出一块空间,交给和解来进行实验,时机成熟便将和解正式纳入立法。没有国家的授权和支持,恢复性司法不可能在正式制度上得到承认。(2)对恢复性过程的监督。和解中,双方当事人的资源、能力、社会关系并非完全对等,因而,极有可能出现一方压制、强迫另一方的可能。特别是,当这种强迫以一种表面自愿的形式呈现出来时,就更加具有迷惑性与危险性。国家的任务就是,必须保证程序的透明、公开与平等,保证被害人、加害人能在程序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同时保证当事人自由、真实的意志表达。(3)对恢复性协议的确认与保障。和解协议虽然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达成,但是,协议最终必须由国家司法机关审查确认。因为,协议必须在合法、自愿的框架内形成,不能违背国家强行法的规定,不能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最终审查原则”。(14)(4)对恢复性程序的最后救济。和解如果失败,就意味着先前所有的解纷努力都归于无形。然而,纠纷还是必须最终化解,责任也必须有人承担。因此,在和解失败后,案件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回到国家正式诉讼程序来予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15)(5)无法恢复的案件中,直接由国家司法解决。尽管恢复性司法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还是会在某些领域出现适用上的失灵。这正是程序多元化安排的最初动因。在没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在自己是被害人的案件中,在抽象被害人的案件中,恢复性的和解都可能发生适用上的难题。(16)此时,只能由国家司法直接出面解决。
可以看到,从“国家专权型”司法到“国家——社区合作型”司法的转变,意味着国家与社区的司法角色必须重新塑造。无论是国家还是社区,单靠任何一方孤立的行动,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犯罪问题。只有国家与社区通力合作,既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又相互配合与支援,才能遏制犯罪的增长。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强化社区在司法过程中的参与,增进社区预防、控制犯罪的能力,可能正是当务之急。经验表明,社区的介入应当是犯罪预防和控制的最有力手段。如果说,人们都保持这样的态度,“我知道隔壁邻居在违反法律,但我还是做自己的事吧。因为这些事情是职业警察处理的。”那么,犯罪的控制与处理就不可能成功。低犯罪率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人们只关心自己事务的社会,而绝对是一个相当依赖社区参与犯罪控制的社会。某种意义上,法庭不堪重负的案件压力,也可部分地归咎于社区缺乏对那些源于社区的犯罪的处理能力。因而,犯罪的高效控制只能寄望于与社区的合作,重建社区的犯罪预防体系,并拓展社区在犯罪控制方面的资源。这就意味着,国家应当从犯罪控制的前台撤离,“国家应当从那些冲突各方自己能够更好地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领域中撤退出来,国家司法应当是对那些无法恢复的情形的最后诉求和法律保障的最后留存。”而反向观察,这正是一种将冲突重新交还到个人与社区手中的过程,也就是某种“冲突的再个人化”(Reprivatization of Conflicts)过程。
(三)对抗式司法与协商式司法
犯罪乃是某种人际冲突的显现,司法则是对于此种冲突的解决。一般说来,对冲突的处理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容忍;二是对抗;三是协商。传统司法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抗”。在传统诉讼制度的“三角结构”中,原、被告双方被自然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相互展开抗辩。与此种对抗性结构相适应,司法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之配套:首先,强调被告人的辩护权,以此积极对抗控诉。这一制度的基本设想乃是,被告人在程序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必须赋予被告人以一定的诉讼权利与手段,实现诉讼武器之对等。同时,真相乃越辩越明,因此,只有在双方当事人的互相抗争中,事件的多维意义才能凸显,案件真相才能最终呈现。其次,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以此消极对抗控诉。如果说,辩护权乃是一种与追诉积极对抗之手段,那么,沉默权就是一种消极抵抗之手段。据此权利,被告人可以免去自证无罪之义务,不与控诉方进行任何积极配合。这是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鼓励某种“无声的对抗”。再次,注重证据规则的运用,在技术上推动双方当事人展开对抗。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都是以证据事实为基础来展开程序的运作。而在证据的运用中,不但讲究当事人的证据提出,而且更为重视证据的说服。此时,当事人围绕证据的形式、程序、证明力等问题,必须展开相互的质询、辩驳等质证工作。这无疑也是在技术层面鼓励当事人的相互竞技。最后,从其他程序设置上,也注意当事人的相互对抗。如在侦察机关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时起,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控诉人申请鉴定之时,被告人可以申请反向鉴定等等。总之,在传统司法中,双方当事人的对抗,不但构成程序推进的动力,而且构成逼近事实真相的手段。进一步地,它也被认为是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一种显现。
然而,此种对抗式的司法却可能导致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对抗导致时间及金钱等资源的大量消耗。当事人的对抗,往往导致程序的复杂化与繁琐化,不仅诉讼久拖不决,而且人、财、物产生巨额耗损。其次,对抗导致双方当事人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一上法庭,双方当事人就剑拔弩张、势如水火。被告人拼命隐瞒、推卸事实,这对于被害人而言,不啻是在伤口上浇盐,但又不得不面对此种“二次伤害”。诉讼完结之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只会进一步恶化,而根本无法维系和经营。以对抗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不但难以弥补裂痕,而且只会使裂痕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再次,对抗也难以使真相得以呈现。在对抗中,被告人只会利用现存制度的优势,或者以沉默的方式竭力隐瞒真相,或者打着抗辩的旗号尽力歪曲真实。在对抗中,我们将难以看到真诚的坦白,诚挚的忏悔和请求宽恕。任何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都可能成为奢侈。
恢复性司法的理解则迥然不同。在它看来,司法并非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对话,谋求各方都乐于接受的结果。在维持法制底线的框架内,这种纠纷的解决过程试图让双方都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相互之间减少不必要的对抗,增加更多的对话和合作,试图使不同的利益需要尽可能地找到结合点。
隐含在这一思路背后的,乃是某种更深的谋划。通过司法的协商化,恢复性司法试图进一步实现以下价值:(1)促进司法效率之追求。对抗式司法的展开,必须有正当程序的保障。然而,正当程序的严格设置,却可能导致司法效率的低下。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刑事案件的增长扶摇直上,对正当程序的追求面临着被“积案”摧毁的危险。惟其如此,设置多元化的解纷程序,并在此基础上保证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就成为一种有效的应对思路。而协商化的程序设计,相比对抗化的制度安排而言,明显具有效率上的优势。协商程序灵活,没有繁琐的侦察、起诉、抗辩、证明过程,而且可以更多地利用非工作时间。协商对于缓解正式司法的压力,提升司法体制的整体效率,有显著的促进意义。(2)更好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大量数据表明,犯罪经常是在熟人之间发生。以最为严重的杀人罪为例,美国47%的谋杀罪发生在熟人之间。(17)这意味着,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交往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某种持续的、长期的交往过程。协商的方式相比对抗的方式而言,显然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关系的维持和长久经营。退一步讲,即使犯罪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和解的方式也更有利于双方矛盾的和缓解决,有利于裂痕的愈合与恢复,而不是加深此种裂痕。(3)容纳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并寻找其最佳结合点。争斗式的诉讼,其最终结果就是你死我活。此种胜负之争,只能形成某种“零和博弈”的局面,一方获得的利益,就是对方失去的利益。然而,协商式的司法却试图通过理性的对话,寻求某种“所有利益主体都相对满意的结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的利益诉求。此种对话的目标,绝非你死我活,而是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努力达致一种各方需求都相对满足的“共赢”局面,一种“非零和的博弈”。
应当看到,刑事法律本身就是协商的产物,就是意志交合的结果。刑事法作为某种合意程序的产品,必须具有保障合意的品质。更为重要的,刑事法的应用,应该还能促进合意的产生,促成意志的整合,而不是单纯提倡争斗与竞技。正如萨默斯指出的:“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18)尽管上述议论是从整个程序法的角度出发,但其对于刑事司法而言无疑具有适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迫切需要刑事司法的观念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从对抗走向对话,由争斗走向协商,由单一价值走向多元诉求,由胜负之争走向双赢格局。
(四)代理式司法与参与式司法
传统刑事司法中乃是某种“代理式司法”。在这套体制中,国家公诉人代替了被害人承担控诉职能,而律师则代替了犯罪人承担辩护职能。即使在被害人参与的情况下,也通常会有诉讼代理人的帮助。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案件的实际当事人尽管参与程序但却难以控制程序。相反,程序的实际运作是由代理人来支配和掌控。将犯罪视为对国家的侵害,构成了公诉机关替代被害人的部分原因。在此之外,代理人广泛介入刑事司法,甚至实际控制刑事司法,还可归因于刑事规则的专业性。艰深的实体法知识,决定了案件应如何起诉,也决定了案件应如何辩护,当事人因为缺乏相应的知识背景往往不知所措;而程序规则的专业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复杂的程序设计,繁琐的证明规则,精微的诉讼技巧与经验,这些都与大众的常识如此之隔离,以至于普通民众难以理解。在上述知识壁垒难以清除的前提下,案件的当事人只能将自己的利益交到职业代理人的手中。
然而,在这一利益移交的背后,却隐藏着极为严重的危机。那就是,职业代理人对司法过程越来越深的把持,以及实际当事人的不断边缘化。“法律科层具有一种可以理解的人类倾向,即总是试图增大自己的权力并扩大自己的权利。科层时常不是作为一个忠实的仆人去行事,而是力求成为自己所管辖的那部分的主人。”(19)实际上,现代司法的逻辑早已预设了这样的“话语——权力”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在刑事司法不断专业化、技术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职业法律科层基于对知识的垄断,必然寻求权力的扩张。(20)从历史经验上看,法律职业在其萌生的初期,便开始表现出对自身特权的野心,表现出学科知识话语的扩张和对“他者”知识的排斥。(21)而根据福柯的洞见,这种知识话语的扩张和侵蚀,必然带来一种权力的膨胀和压迫,只不过在法律精英们的高妙掩饰下,此种知识——权力的压迫更容易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刑事司法的代理化,导致了精英话语对大众话语的霸权压迫,导致了代理人的中心化与当事人的边缘化。这对于恢复性司法而言,乃是不可接受的“易客为主”。在它看来,将犯罪的处理从犯罪发生的社区背景中硬生生地抽离,将犯罪的决定权授予与案件毫无利害关系的专业人员,将真正受犯罪影响的人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这是传统刑事司法的巨大失败。刑事纠纷的解决必须吸纳犯罪人、被害人及社区的直接参与,让他们成为司法过程的支配性主体,而不再沦为看客。当事人必须在事件处理中拥有更为直接的发言权,对于自己的命运自己来把握。他们不但有权决定是否以和解的方式处理纠纷,而且有权决定和解的具体程序及其细节,决定最后的责任形式与责任程度。所有与犯罪有关的人,都被鼓励参与到犯罪事件的处理当中来,他们完全有智慧也有能力直接管理自己的事物。越是不让当事人和社区参与,他们处理冲突的能力就越是得不到提高。只有在不断的参与中,公众处理冲突的能力才会稳步发展,社区控制犯罪的能力才会不断增强。
当然,恢复性司法所提倡的广泛参与,是与解纷过程的专业性下降相关联的。首先,实体法知识的意义大大降低。犯罪无非是违反社区规范和行动规范的行为,而这些公共规范可谓人所共知。责任的确定更无所谓专业。对每一个犯罪都可能有个别化的处理,因为每一个当事人都可能有不同诉求。展开友好协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双方当事人满意的责任约定,就是正当的、有效力的责任确定;其次,程序规则和经验技巧也不再神秘。和解作为古老的知识传统,乃植根于我们的血脉。我们对这种理念、程序或是规矩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不再需要那些太过“专业”的辅助。甚至,程序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协商、需要而随时变化、量身定制,程式化与标准化不再是主要追求;再次,犯罪事实不再需要以繁琐的证据规则来探明,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坦诚相待,事实会得到更为全面、真实地呈现。事件解决的基础,不再是专业规则意义上的“证据事实”,而是交流对话意义上的“协商事实”。
解纷过程的专业性下降,以及当事人和社区的广泛参与,进一步意味着职业代理人的角色必须重新调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世界范围内恢复性司法的模式多种多样,因此,职业人士的角色也并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是,在刑事司法中区分出不同领域,在传统诉讼领域中,专业人员仍然保留传统的权力,在恢复性司法领域中,则由普通公民来控制;第二种情况是,在恢复性司法领域中,仍然让司法人员扮演传统的角色;第三种情况是,让职业人员彻底转变担当全新的角色。也就是,让传统司法专业人员变成恢复性司法中的专业人士,成为调解者、问题解决者和社区参与的促进者。(22)可以看出,第二种做法实际上并不涉及角色的变化,专业人士在和解中完全承担着原先的功能,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第三种做法是希望专业人士能够彻底脱胎换骨。这种想法虽然能够节约一定的司法人力资源,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长期的角色扮演中,专业人士已经将自己的代理人角色模式化,他可能完全转变过来吗?他能够安然接受现在的配角身份,而彻底忘却过去的风光?即使强行要求此种转变,又怎么能防止他们不产生角色的错乱和混淆?更为要紧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沉重的肉身”,都必然受到利益的驱动。专业人士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职业利益,而本能地拒绝这样的角色转变。(23)某种意义上,诉讼(公诉)制度乃是检察官的安身立命之本,而律师也只有在诉讼体制下,才有一展拳脚的天地。
因此,在我看来,第一种做法可能更为妥当。那就是,针对不同案型,区分出传统诉讼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的不同场域。在此基础上,在传统司法的保留领域,仍然让专业人士发挥他们的特长与优势,而在恢复性司法领域,则让当事人成为程序的主导与中心。当然,恢复性司法也不是要断然抛弃传统司法的所有价值。例如,对犯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就仍然是必要的。此时,专业人士的咨询与辅助,就成为传统司法价值在恢复性程序中延续的有力保证。但是,请不要忘记,司法人员的此种介入必须是有度的。正如克里斯蒂恰当的提醒:“司法专业人员在恢复性司法中的角色,只应是一个司法资源的提供人和咨询人,而不是司法的主导人和中心。”(24)
(五)问题式司法与关系式司法
传统刑事司法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司法。简单地说,这一问题的指向,就是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法律规格,以及在满足这一规格之后应如何量刑。其中的重点,又是前一问题。
正如Zehr教授正确指出的,正式司法习惯且擅长于在事件发生之后,发出这样的设问:“谁触犯了刑法?触犯了什么规范?应处以何种惩罚?”(25)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正式司法总是首先“客观”、“充分”地调查案件事实,然后搬出那一套严格规整的犯罪构成理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所谓工整的三段论演绎,以犯罪构成为大前提,以事实与犯罪构成的完美对接为小前提,然后径直得出结论。当然,上述大前提并非是给定的,而是法官凭借自己的法意识,从法条的汪洋大海中捕捉得来。一旦这一“找法”的过程出错,换言之,找出的犯罪构成与当下案件事实无法对接,那么就必须重新开始“找法”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可见,所谓三段论的推演,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直至最后找到合适的规范,能够与当下的案件事实形成对接,或者实在无法形成对接时,只能作出无罪的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关注的,并非是案件所有的事实特征,而是与特定法律判断规格——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只需这样的事实能够确定,案件在法律上的定性就可完成。
可见,传统刑事司法的法律适用过程,关注的是案件在法律、技术层面的解决。一个案件的实体形成过程,其核心便是“该当犯罪构成的事实”的发现与证明过程。(26)在此过程中,特定犯罪构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观念参照,在其指引下,法官完成了对原始案件事实的筛选和过滤。法官并不关心犯罪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也不关注案件在生活意义上的全部真相,他只关注影响案件之刑法性质的犯罪构成事实。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一方面,犯罪构成是极为僵硬的,它早就在案件发生之前规定于刑法之中,且始终固定不变。因而,根据此种犯罪构成而圈定的事实,也是极为僵硬的,它并不能正确反映当下犯罪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另一方面,犯罪构成又是极为片面的,它只是对犯罪事件中某些以立法者的观点看来是重要的因素加以规范,而忽略了事件背后更为广阔的行动背景、社会关联与复杂成因。更为可怕的是,在将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相互对照时,案件事实很容易产生被“格式化”的倾向。也即,一旦客观事实无法顺当地服帖于犯罪构成的概念和框架,法官们便倾向于固守那些被认为确信无疑的概念和框架,并尽量将事实按照这些概念和框架的要求予以裁剪,以使其符合这一固定的包装。(27)他们的策略和立场,与其说是以刑法解释生活,倒不如说是以生活解释刑法。在这一世界中,纷繁芜杂的生活事实从前台撤退了,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素材,注释着那些刑事法律中的“经典”命题和框架。于是,一个案件的真实意义被掩盖起来,被它的规范与技术意义所取代。
恢复性司法则试图还原犯罪事件的真实意义。在它看来,犯罪的真相,并非是僵硬的、片面的、格式化的构成事实所能取代。对于犯罪事件的处理,也绝不能满足于某种法律、技术层面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犯罪事件的发生往往有着极为复杂、深刻的背景。而且,相当多的犯罪还涉及当事人心底深处的隐私。而传统刑事司法所调查了解的犯罪事实,通常都只是犯罪的外观,或是犯罪事件的最后引发,而不是犯罪事件内在的真相。因而,从规范、技术的层面来处理犯罪事件,就只是一种相当表面化的问题处理,而并非对事件内在的、整体化的解决。另一方面,很多犯罪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长期矛盾冲突的结果,是一系列人际事件的最后爆发。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锤子买卖,而是某种长久的、持续的互动。因此,刑事纠纷的处理就绝不止于当下个案的解决,不止于事件的一次性解决,而是涉及更为长期的关系梳理和持久经营。
在恢复性司法的世界中,关系是一个核心范畴。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很多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极为相近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社会关系:毛利人称之为“whakapapa”、印第安人称之为“hozho”、非洲的班图人称之为“ubuntu”。(28)而无论是在毛利文化、印第安文化还是班图文化中,刑事和解都构成化解刑事冲突的重要传统。因此,将恢复性司法视之为“关系式司法”,实在是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这种关系化的视野中,犯罪被视为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某种侵犯,而犯罪事件的处理则是对当事人关系以及社区关系的恢复。犯罪乃是人际关系恶化的产物,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冲突,就必须从人际关系上入手。刑事冲突的化解,实质上就是一种重建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区之间关系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会面和真诚交流,清除误会、化解怨恨、聚集共识,从而重建当事人之关系,使他们能够在社区中健康地交往下去;另一方面,更要恢复当事人与社区之关系。不仅要帮助被害人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重新振作,重建人际交往中的安全感、控制感,重新融入社区生活,而且要帮助犯罪人发展工作技巧,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顺利复归社会。因此,犯罪的处理不能被简化为机械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执行判决的流程,而是一种发现矛盾——解决冲突——愈合关系的过程。
不难看到,此种对犯罪事件及解纷过程的理解,乃是立基于对社会的下述假设之上:人们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交往之中。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社会关系的牵绊,我们注定要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无论是犯罪人还是被害人,无论是冲突发生之前还是冲突发生以后。因此,当这张大网出现裂痕或是缺口之后,我们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力加以弥补和修复。这种关系化的观察方式,一方面使犯罪事件与其前期的矛盾形成、事件的后续发展等联系起来,从而能够更为全面、动态地把握犯罪事件。它避免了将犯罪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孤立化地进行犯罪应对;另一方面,这种观察更试图抛开法律要件与规范事实的束缚,深入到犯罪事件的内部,从犯罪发生的深层背景、复杂成因、社会影响等方面来观察事件的意义,从而内在地、实质性地解决刑事冲突。它关注的,并不是纠纷在法律技术层面的解决,而是纠纷在社会交往层面的解决。不是冲突的一次性、暂时解决,而是冲突的长久的、彻底的解决。
(六)隔离式司法与会面式司法
传统刑事司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隔离。即通过强制措施、刑罚等羁押性手段,将犯罪嫌疑人、罪犯关押在看守所、监狱等场所。这种隔离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将犯罪嫌疑人与家属、朋友相隔离。犯罪嫌疑人一旦涉诉,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就有可能被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亲属朋友等都不能随意与之见面。其二,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相隔离。上述的隔离措施,不但将犯罪嫌疑人与亲属、朋友隔离开来,而且将其与被害人隔离开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处理,可能是为了防止犯罪人再次接近被害人,从而防止被害人“二次被害”。其三,将犯罪人与社区相隔离。犯罪人一旦进入监狱服刑,就意味着彻底与社会相隔离。监狱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最为封闭的场域,据称,只有在此种封闭的环境中,犯罪人的犯罪能力才能被抑制和剥夺,犯罪人才能被矫治并完成人格的重塑。
应当看到,此种隔离的确有其积极意义。它使犯罪人/犯罪嫌疑人处于某种司法控制的状态,从而无法毁灭罪证、串供勾结、畏罪潜逃或进行其他妨害诉讼的行为。而且,它也将犯罪人与被害人隔离开来。此种隔离,有效隔断了犯罪人对被害人可能的报复与不满,从而具有重要的过滤与保护机能。然而,不容回避的是,此种隔离的副作用也极为明显。首先,与亲属朋友的隔离,使犯罪人无法获得来自家庭成员、朋友的道德教育与情感支持,而这些对于犯罪人的彻底醒悟和积极悔罪,可谓意义重大。(29)因为,一个做了错事的人,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当他听到自己最信任的人的真心劝告,当他看到自己的亲人因自己的行为而痛心疾首,他往往能真正感受到道德的力量,认清自己的错误,并激发出向善的勇气与决心。其次,与被害人的隔离,可能进一步加深双方的隔阂与猜忌。与犯罪人的隔离,容易使被害人对犯罪人产生“妖魔化”的印象。一旦将犯罪人想象为穷凶极恶之人,只会使被害人进一步加深对犯罪人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安。与被害人的隔离,则使犯罪人无法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影响,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从而无法真正促进犯罪人的觉醒。
在恢复性司法的理解中,打破隔离、直接会面将具有突破性的价值。和解始终把会面作为犯罪处理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加以对待。此种会面,对于犯罪事件妥善处理的意义在于:首先,将使事件真相更好地得以呈现。犯罪事件发生以后,无论是犯罪人还是被害人抑或社区公众,都会形成自己对犯罪事件的理解。犯罪原因何在,事件发展中谁是谁非,事件的后果与意义究竟如何,围绕这些问题都会形成各自的认识,形成各种“主观真相”。然而,这些对事件的主观理解与认知,并非必然正确和妥当,它完全可能基于不同的观察立场、情感体验和利益诉求,而偏离于事件的真实。因此,要使主观真相尽量接近于客观真相,就必须在不同主体间、特别是当事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通过此种直面的叙说过程,一种关于事件的“主体间性”的共识,就可能形成。这正是Herman Bianchi所指的“关系性真相”(Relational Truth)。关于此种真相,他解释道,“真相总是一种社会性观念,是一种互动结构的一部分。”的确,真相既不是完全主观性的,也不是完全客观性的,相反,“真相总是人们对现实性的解释。真相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一些有待激活的资料。”(30)其次,打破模式化的人物想象。对犯罪人的恐惧,有时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定式化的认识之上。犯罪人通常被想象为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不仅狡猾奸诈,而且暴力残忍,毫无人性。然而,此种对犯罪人的“妖魔化”想象,经常背离了实际情况。犯罪人其实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其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与普通人都无太大差别。他们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基于特定的动因引诱,而实施了错误行为。正确的思维是定义事件本身,而非定义行动者。再次,自然引导出情感的表达。会面不仅是希望带来真相,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带来情感的宣泄、释放及交融。会面不仅是简单地将各方带到一起见面而已,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会面本身不会有任何收获。会面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叙说和陈述,它还意味着相互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或愤怒或痛心,或谴责或悔恨,参与各方不但获得了叙述自己的情感与体验的空间,而且在相互尊重地予以倾听的基础上,获得了进入对方情感世界的机会。尽管情绪的表达被排除在我们当前的司法程序之外,但是在恢复性程序中,情感的宣泄非但是允许的,甚至还是不可替代的。正是通过发自内心的情感释放,心灵与心灵之间才得以通畅和澄明,才得以相互体谅与接纳。(31)
当然,会面也蕴涵着风险。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有勇气会面,也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希望会面。对于犯罪人而言,与被害人见面意味着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错误,接受面对面的情感宣泄与道德教育,以及将自己置于公众的议论和谴责之中。这需要犯罪人有巨大的勇气,及彻底的悔悟。并非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只要获得减免正式处罚的优待,任何犯罪人都会选择和解与会面。事实上,还是有一些犯罪人宁愿在正式司法中接受处罚,也不想再次面对那悲怨的眼神和愤怒的斥责。(32)另一方面,被害人也可能并不希望见面。被害人可能认为与犯罪人的会面具有危险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担心来自犯罪人及其支持者的报复,以及由此而来的人身安全问题;而且还因为,在会面中过去的痛苦经历不得不再次回忆,伤疤会被重新挑破。而这些,可能恰恰是情绪易伤的被害人所不堪忍受的。所以,会面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都自愿同意,并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七)标准式司法与个性式司法
传统刑事司法极为重视程序的安定性与普适性,从而构成一种标准化的司法样态。在这种司法模式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一,程序始终是一种一般性的陈述,其适用之对象也被想象为具有统一的特质。传统司法程序仅被区分公诉与自诉两种类型,两种程序之间有相当程度之重合。而在公诉案件的范围内,尽管有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之分,但无非都是以一审程序为基础加以简单变化而成。因此,可以说,传统程序设计是一种高度单一化的设计。之所以如此,最为重要的是因为,程序适用的对象被抽象化和一般化,案件被想象为具有极为统一的特点,因而可一体对待。在这一抽象的过程中,案件的个性特征被彻底抹去,成为毫无生气的“没有轮廓的脸庞”。其二,以程序的普遍性为前提,传统司法试图进一步实现某种程序的安定性。因为,只有当程序具有一种普遍性时,它才能从容面对数量繁多、形态各异的刑事案件,它才有可能保持一定的弹性与张力,妥善地化解各种问题,而不至于朝令夕改。因此,从侦察、起诉到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传统程序都相当强调程序的稳定特征,一板一眼不可随意变更。其三,以安定性为基础,进一步实现程序的可预测性。在韦伯看来,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可预测性,这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正常运作的一个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韦伯将确定性、可预期性等法的形式要素提高到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要求将法律的这些形式要素贯穿到立法与司法的始终。这样,立法的“精确性会使法律结果的正确预测最大化”;(33)而就司法而言,“司法形式主义使法律制度可以像技术性的理性机器那样运行,因而,它能保证个人或团体在相对广泛的自由制度里活动,并使之可预料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34)
不难发现,传统司法所追求的,乃是某种程序规则的统治。质而言之,是一种形式理性的统治。这样一种司法理想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如下的信念:标准化的程序具有极大的确定性、客观性与可预测性,因而能极好地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然而,问题是,程序的标准化乃是以程序对象的一体化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在适用程序的刑事冲突具有一致性时,程序的标准化方有正当性可言。如果纠纷性质存在巨大差别,但却无视此种差别,强行适用标准化的程序予以处理,那就会在所谓“普遍化”、“形式化”的追求中,丧失对“个性化”、“实质化”的关注。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导致了利益较量与冲突的多元化趋势。这就迫切要求在法律程序上,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程序选择,以实现更具适用性和针对性的纠纷处理。在刑事冲突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要求。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恢复性司法才试图在某种标准化的解纷程序之外,开辟更为灵活、更为弹性的制度安排。在它看来,刑事纠纷本身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形态各异、性质不一。比如,发生在熟人之间,特别是家庭成员内部的纠纷,就应当按照不同于一般案件的程序处理;对于历史遗留案件,如南非种族屠杀事件的处理,(35)就显然与普通刑事纠纷有不同要求;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案件,如藏区的故意伤害案、怒族的重婚案,就与普通汉族地区不可同样对待。(36)因此,绝不能对刑事冲突做某种简单的同一化看待,更不能对程序安排做僵硬的一体化设计。进一步地,即使是针对同一纠纷类型,有时事件背景、冲突细节甚至是当事人期待都各不相同,因而也必须为个性化的处理留有余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恢复性程序在时间、地点、形式甚至结果上,都没有特别固定的、普遍化的规则,完全可以由当事人自主协商决定。不过,恢复性程序的灵活性,也不应被理解为毫无一般规则可言。必须承认,当事人的自愿参与、犯罪人的坦白认罪、程序过程中的平等对待、相互守秘等规则,仍然构成恢复性程序的底线正义。
从价值上讲,个性化的司法是试图在抽象正义和形式理性的宰制下,为具体正义与实质理性创造一种自由空间。根据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的区分进路,正义可被划分为“抽象正义”与“具体正义”。其中,抽象正义(一般正义)可解释为一种行动原则,根据该原则,凡属于同一主要范畴的人或事应予一样对待。而具体正义(个别正义)则与之相对,只承认所谓的特殊价值。(37)在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司法试图实现的,不是某种“大写的正义”,而是活生生的个案的正义。在此种理念看来,比普遍秩序、一般正义或普适价值等宏大叙事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实践——从一个个具体的个案中,去触摸司法的精髓和脉搏。通过灵活的、弹性化的制度安排,使每一个刑事冲突的解决都能各得其所,由此化零为整,积沙成塔,经由“具体正义”去实现司法程序的“抽象正义”。
另一方面,形式理性尽管构成了法治的主要特征,构成现代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尺,但是,对形式理性的尊崇也不能超过限度。事实上,在现代法律的发展中,已经包含了强烈的削弱形式主义的趋势。这种对形式理性的削弱和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实质理性的加强和重新得势。现代刑事司法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刑事证据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证据的自由评价”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代替了原来的僵化的证据规则。通过对证据的自由心证,许多原来被视为形式法律思想的领域正在逐步消退。刑事实体法中这样的例子也在所多有。先前的刑罚理论中,刑罚被机械地限定为对犯罪的形式报复。然而,今天的刑罚理论已经明确将“预防犯罪”的目标摄入,在刑罚的设置和量定中更多地关注实质性的功利效果。“刑罚目的”在当下的刑法理论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正是通过这一理论,非形式性的要素被不断引入法律实践。所有这些,包括恢复性司法的强劲勃兴,都表明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即今天的刑事司法逐渐对极端的形式理性展开反思,反对至少是过分的形式理性,同时强调形式理性和形式理性法律应该不断“实质化”(Materialization)。(38)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科特利尔才率直地指出:“韦伯的法律统治与戴雪所称的法治,最多只能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变化则很难用法律统治或法治这样的思想来概括。”(39)科氏的结论也许过于极端,我倒更愿意把此种变化看做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断循环运动的一个环节,看做是传统形式主义司法的一次当代危机,以及,对之不大不小的一个修正。(40)
(八)消极平衡式司法与积极平衡式司法
传统司法是以报应为基底的司法。此种司法模式的基本关注在于:社会的平等性。因为犯罪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伤害,所以也必须以刑罚的形式给予犯罪人一定的痛苦。其目标是,通过对犯罪人施加该当的惩罚,实现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平等。然而,这一司法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方向和手段却大错特错。基于追求平衡的良好目的而出发,但却走上了“恶恶相当”、“以毒攻毒”的邪路。必须清醒地看到,“两次错误不可能成为一个正确”,“负负不能得正”。正义不能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实现,暴力只能培养出新的暴力,而不能使损害得以恢复。“惩罚所造就的是一种持续的不安感,因为在惩罚性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冲突像是疼痛的伤处一样仍然历历在目。”(41)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司法没有为“以恶制恶”的平衡,确立正当化的操作标准。换言之,“恶害”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怎样才算是恶与恶的平衡,这一点远非传统司法想象得那么清晰。而如果不能确立这样一种标准,司法就完全可能在平衡恶害的口实下,进行刻意的报复或是伤害。因此,必须为限制惩罚的严厉性划上一条稳定、公平的基线。然而,遗憾的是,传统司法至今尚未提供这样的基线。回溯惩罚主义的生命历程,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一条从等害惩罚到等价惩罚再到等序惩罚的演进轨迹。(42)今天的刑罚仅仅只是在轻重序列上与犯罪保持一致。用最为直白的语言表达,就是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犯罪与刑罚在轻重等级上维持一种“序”的对应。不是吗?如果现行刑罚体系仍然禀持着“恶恶相等”的观念,那么,盗窃他人钱财的行为为什么不单处罚金刑,而要剥夺人身自由?对于强奸犯为什么不处以宫刑,或是反过来强奸“他”一次?(43)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又为什么不施以肢体刑?还有,与危害国家安全之恶相等的刑罚是什么?与破坏环境犯罪之恶相当的刑罚又是什么?可以看到,犯罪从表现形式到损害形态都是无限的,而刑罚由于只能以个体为对象,便注定了它在剥夺权益的种类、方式上的有限性。企图在有限的刑罚种类和无限的犯罪形态之间追求“物物交换”,实现损害形态和性状上的完全对等,无疑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即使如黑格尔般,试图抛弃对犯罪与刑罚间损害形态上对等的追求,转而寻求两者间内在价值上的等同,也并非可行。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在犯罪的“罪恶量”与刑罚的“痛苦量”之间,难以发现可通约的精确标准,从而无法实现价值上的转换与对等。正是由于传统司法无法提供关于“恶恶相抵”的稳定、清晰之标准,使得所谓的“以恶制恶”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进而影响其正当性。反过来,退一步讲,即使“以恶制恶”的理念被合法化,其操作标准也决不能仅仅因为理念的合法化而被自然地“去问题化”。
传统司法的逻辑是,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遭受了损失,因此,就再以报应的名义给犯罪人造成同样的损失,由此形成损失与损失的平衡。然而,这样的平衡对于被害人而言毫无实益。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侵害根本得不到弥补,所遭遇的精神创伤也得不到抚慰。对于犯罪人而言,惩罚只是无谓的、刻意的伤害,非但难以激起犯罪人改恶从善的决心,反而可能造成对社会的仇恨与敌视。对于社会而言,在一种伤害产生之后再制造一种伤害,根本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只会使社会资源双倍消耗,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加速离散。因此,传统司法所追求的,绝不是一种积极的、有任何改善意义的平衡。
反面观之,恢复性司法也非常注重犯罪发生后社会关系的重新平衡。但是,它所提倡的绝非某种“负负平衡”,而是一种恶害被清除、弥补之后,对各方当事人都有正面意义的积极平衡。这种平衡的产生,必须经由一条恢复性的路径才能达致:通过犯罪人的真诚道歉、物质赔偿,使被害人的精神和物质伤害得以弥补,重新恢复健康的社会角色;通过对犯罪人的责任承担、能力培养和道德重建,使犯罪人从过往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以积极的社会角色重新回归社区生活;通过犯罪人的社区服务,及其在社区中的矫正措施,重新确证社区道德、调和人际交往、强化社区安全,使社区生活回复到安宁与和谐的状态之中。
进一步地,此种平衡的重建,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恢复到犯罪之前的状态。因为,犯罪之前的社会环境,并非一定健康、和谐。罪错行为不仅是造成社会不平衡的原因,而且有时也是先前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同时,在犯罪之前,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也可能早已冲突不断,犯罪的产生只是持久人际纠纷的一种最后引发。因此,犯罪之前的状态绝非完美,简单地恢复到犯罪之前的状态,也并非恢复性司法的最终追求。如果在犯罪的处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及社区成员能够正确对待,仔细探究犯罪的原因,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致力于清除犯罪发生的渊薮,那么社区关系就可能比以往更为紧密,生活状态也可能更为和平与安宁。惟其如此,犯罪的发生不仅蕴涵着危险,而且更饱含着机遇。以当下纠纷解决为契机,进一步改善个案背后的人际关系,全面提高犯罪人的各项能力,发展社区的犯罪预防与应对机制,就能够在促进、改善和提升的意义上,带来一种更为积极的平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恢复”一词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回到既往,而是蕴涵着更高的精神意向:那就是以个案处理为契机,努力实现某种提升、改进与超越。
三、结语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从八个方面仔细地梳理了传统司法模式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关系。这样的尝试,不仅被先期的恢复性司法学者所热衷,而且在近来的犯罪学、少年司法学领域也风靡一时。但是,也不是没有学者反对此种比较研究。Kathleen Daly就明确认为,将报应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做对立化的比较,是一种错误。(44)Zehr在其晚期的研究中,也对早年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反思。(45)
在我看来,比较的思考进路本身无可指摘。实际上,任何认知都只有在比较性的思维中才能获得。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以传统司法为参照背景而存在。只有在两者的比较中,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司法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意识到和解性司法在发生学上的背景、动力及其基本指向,也才能进一步对司法改革的可能前景有所体察。比较并不是为了突出两种模式之间过于夸张的对立与紧张,而是在“理想类型”方法的指导下,分析性地展示两种司法的不同气质与特征,从而更为清晰地把握两种司法的整体轮廓。
当然,上述的对比分析主要立足于两种模式的差异,立足于和解性司法对传统司法的扬弃与突破。这样的观察,不应该被误认为两种司法之间毫无可沟通之处。事实上,和解性司法也吸纳和整合了“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中的某些重要因子。比如,和解关注犯罪人个人责任的承担,关注犯罪人道义责任的实现,这与报应主义一脉相承;(46)和解注重帮助犯罪人认清错误、重整规范意识,注重对犯罪人职业技巧的培养、交往能力的提高,从而以积极的姿态重返社会,这与矫正思想气息相通;和解容许犯罪人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中承担责任、教育培训,这与矫正主义的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思想环环相扣;和解不仅重视对过往行为的责任承担,此点与报应主义相似,而且重视对未来犯罪的预防,此点与矫正主义相通。因而,将和解性司法片面地视为“前瞻性司法”,而将传统司法视为“回顾性司法”,就可能存在失误。(47)
总之,和解并非与传统的司法类型毫不相干,它与传统司法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然而,和解又绝不能被视为“报应性”因子与“矫正性”因子的简单整合,在上述八个重要方面,和解都突破和超越于传统司法,因而必须作为某种全新的司法图景来认真对待。
注释:
①“恢复性司法”的最早出现,乃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出现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犯罪人——被害人和解程序”,而“恢复性司法”一词就是用来描述这一程序。可以说,“恢复性司法”乃是以“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为其发生学上的源头。另一方面,在“恢复性司法”的成长与壮大中,尽管孕育出形形色色、纷繁芜杂的运作模式,但是,它始终以“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为其核心模式。根据Tony Marshall的总结,恢复性司法的运作形态主要有“犯罪人——被害人和解模式”、“群体会议模式”、“量刑圈模式”、“邻里司法中心模式”等等。但是,这些模式几乎都是以“犯罪人——被害人和解”为基础,只是在参与主体的范围、调解机构的选任、适用案件的类型等方面有细小差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和解模式乃是恢复性司法最为核心、最为典型的运作形态。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恢复性司法”始终以“刑事和解”作为其理念、价值的形成中心。易言之,它始终是以“刑事和解”为对象和参照,来提炼、抽象和型塑关于犯罪、责任及司法的理解。而其他模式的发展,尽管也丰富了恢复性司法的文化适用性和操作空间,但是,它们从未在实质上损益、动摇或改变那最为实质的理念内核。惟其如此,“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在基本的理念框架、体系和核心观点上,才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本文也基本上是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这两个概念。更为详细的分析,可参见Tony Marshall,Restorative Justice on Overview,A Restorative justice Reader,William Publishing,2003.
②Barnett,R.,Restitution:A New Paradigm of Criminal Justice,Ethics,Vol.87:4,pp.279-301.
③Jennifer.Llewllyn & Robert Howse.,Restorative Justice:A Conceptual Framework,http://www.lcc.gc.ca/en/themes/sr/rj/howse/index.html.
④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看,恢复性司法主要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力量,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是以正式官方机构为中介力量。
⑤这里,我坚持的乃是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进路。它隐含着对西方法学普适性的深刻挑战与质疑。申言之,那种围绕着西方话语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司法观”,其普适性并不总是真实的,其相对性倒是确信无疑的。关于法律多元主义的立场与主要观点,可参见Sally Engle Merry,"Legal Pluralism",Law and Society Review,1998,22/5,p.869.
⑥Kathleen Daly,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ribu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see Heather Strang & John Braithwaite,Restorative Justice:Philosophy to Practice,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0,p.34.
⑦关于此点,可参见胡玉鸿:“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兼论法学中‘类型’的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又可见(德)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页379及以次。
⑧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1。
⑨参见储槐植、许章润:《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页124及以次。
⑩(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吴宗宪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38。
(11)Gena M.Gerard,Community-Based Restorative Justice:A Capacity-Building Tool for Confronting Crime,http://www.Tcfreenet.org.
(12)Pranis and Kay,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in Community Sentencing,Minnesot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1995,p.23.
(13)Restorative Justice for Victims,Communities and Offenders,Produced by center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 Mediation,School of Social work,University of Minnesota,386,McNeal Hall,1996,p.19.
(14)关于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37届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项目的基本原则》决议的第15条中有明确规定。也可参见李忠诚:“关于恢复性司法方案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律师》2002年第9期。
(15)关于司法最终救济原则,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37届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项目的基本原则》决议的第16、17条中有明确规定。也可参见李忠诚,同上注。
(16)刑法理论通常认为,像同性恋行为、通奸行为等,都属于“无被害人的犯罪”,而吸食毒品等行为则是“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当然,关于这些问题学界也仍然存在一些争论。相关分析可参见彭勃:“‘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17)Gerald R.Williams,Negotiation as a Healing Process,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1996.
(18)参见陈瑞华:“通过法律实现程序正义:萨默斯‘程序价值’理论评析”,《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一卷第一辑,页190。
(19)M.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G.Roth and C.wittich,Bedmister Press,1968,p.1418.
(20)See M.Weber,Supra note(20),p.1418.
(21)R.Unger,Law in Modern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6,p.71.
(22)Olson,S & Dzur,A.,The Practice of Restorative Justice:Reconstructing Professional Roles in Restorative Programs,Utah Law Review,2003,p.57.
(23)Anthony Mason,Restorative Justice:Courts and Civil Society,see Heather Strang & John Braithwaite,Restorative Justice:Philosophy to Practice,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0,p.2.
(24)Christie,N.,Conflicts as Property,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1976,pp.1-14.
(25)(美)霍华德·泽尔:“恢复性司法”,载狄小华、李志刚主编:《刑事司法前沿问题——恢复性司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页25及以次。
(26)某种意义上讲,上述过程也可被看成是法律适用的过程。实际上,事实形成过程与法律适用过程从来都不可能被分割开来。更为详尽的分析,可参见拙作:“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一种基于方法论的扩张性思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27)参见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28)泽尔,见前注(25),页25及以次。
(29)Braithwaite在参加了很多恢复性程序之后发现,无论是外表上多么冷酷的犯罪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亲在程序中失声痛哭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懊悔。可参见John Braithwaite,Restorative Justice and a Better Futu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Dalhousie University,17 October,1996.
(30)See Jennifer.Llewllyn & Robert Howse.,Supra note③.
(31)和解的核心步骤就是:表达真诚悔悟和初步谅解。而这正是某种情感的自然表达,也正是试图通过会面所自然引出的效果。这个步骤是否实现,对于双方关系纽带之恢复,对于最后之协议能否达成,都有关键性意义。See Kathleen Daly,Supra note⑥,p.34.
(32)人们总是认为,和解对于犯罪人而言非常轻松,并且让他们从正式司法的惩罚中轻易溜走。然而,和解过程实际上也包含着强烈的谴责、痛苦与负担。而且,是在一种具有强烈道德氛围的环境中进行此种仪式,其对犯罪人的剥夺感、压迫感可能更强。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人并非一定愿意选择和解。
(33)(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226。
(34)同上注,页227。
(35)关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更为详细的介绍可参见(南非)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6)藏族地区的故意伤人甚至故意杀人案件,通常都是赔命价的方式来处理。怒族则基于民族传统、地理状况及人口结构等因素,一直流行一妻多夫制度。如果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就可能区别于汉族地区。更为详尽的分析,可参见拙著:《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统——刑法视域中“习惯法”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442。
(38)Cunter Teubner,"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Law and society Review,1983,Vol.2,pp.239-285.
(39)参见(英)罗杰·科特利尔:《法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页178及以次。
(40)事实上,德国法治国的发展也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这一趋势。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形式的法治国理论成为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法治国理论。希特勒执掌的第三帝国更是将法治国推向了形式主义、实证主义的极端,由此引发了不但是德国而且是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法治国,不仅仅依赖“法”为工具,而且必须进一步对此“工具”的目的(“法”的目的),以及国家实施整套法治主义的目的加以探讨。此时,作为国家统治依据的法律,固然依旧保有其主要是作为工具的角色,但是其正当性的诉求亦开始面临挑战。由此,以“形式意义的法治国”为基础,再加以实质性的价值审查,即构成了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必须澄清的是,实质意义的法治国绝非形式意义法治国的简单对立,而毋宁是在形式意义法治国的基础上导入实质性价值判断而已。更为详尽的分析,可参见陈新民:“德国十九世纪‘法治国’概念的起源”,载《政大法学评论》第55期。
(41)See Jennifer.Llewllyn & Robert Howse.,Supra note③.
(42)这是借鉴了邱兴隆教授关于报应主义演进的分段方法。可参见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10及以次。
(43)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这也并非不可能。
(44)See Kathleen Daly,Supra note⑥,p.34.
(45)泽尔,见前注(25),页25及以次。
(46)刑事和解关注道义上的责任,关注犯罪人个人承担责任。这点与报应主义相通。但是,和解认为社区也是责任者之一,社区对犯罪的发生负有责任,这与报应主义又有明显区别。具体可参见:Kathleen Daly,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ributiv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see Heather Strang & John Braithwaite,Restorative Justice:Philosophy to Practice,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0,p.35.
(47)事实上,无论是传统司法还是和解性司法,都有回顾与前瞻的两个面向。传统司法的报应向度,着眼于过去的恶行,而矫正向度则立足于未来可能的恶行。和解性司法中同样包含了对过往犯罪的责任承担,和对将来行为的矫正与改善。然而,还是有很多的文献将传统司法视为“回顾性司法”,将和解性司法视为“前瞻性司法”,这是值得仔细商榷的。可参见:Braithwaite,J.,Restorative Justice:Assessing Optimistic and Pessimistic Accounts,Crime and Justice,Vol.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