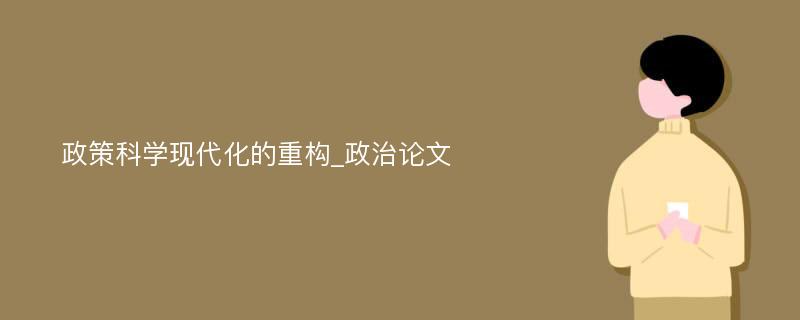
政策科学的现代性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政策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策科学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即将那些被现代主义政策科学所遮蔽和祛除的,但又属政策生活实践之构成性规定的成分,重新纳入政策观念体系之中。
一、政治的回归
现代主义政策科学将政策理性等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带有明显的技术统治论色彩,忽视或有意屏蔽了政策中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群体性参与行为,包括利益的冲突、冲突的化解、分层的暴露和对抗的爆发。“精确地说来,政治生命的特征就是一个在歧见纷呈、主张抗衡和利益冲突的语境中不断地创立统一体——一种公共性——的问题。离开了相互抗衡的主张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领域就没有了主题;就无需去做什么政治决策”①。
事实上,许多政策分析家都很清楚,任何政策都是政治的。可是囿于其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往往被认为是有违科学理性的“愚蠢的政治”,未被认真分析。正如费希尔所言,“实证主义的政策分析具有在概念上歪曲政治过程的性质和公共政策的功能的倾向”。究其原因,就在于它力求从“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角度,把对技术合理性的强调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现代主义“政策科学家并不承认他们的方法的社会和环境的局限性,而常常会因为他们自己分析上的失败而责怪政治体制本身。倘若一个系统无法与技术要求取得一致,就会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结构不合理、有待改革”②。
与现代主义的政策分析不同的是,政治化的政策分析不会“把个人喜好作为‘假定的事实’……而是考虑人们究竟是从哪里得出他们对世界的印象,这些印象又如何决定他们的喜好”。实证主义的政策分析方法根本不谈人们怎样为了某种政治利益的憧憬或社会性质而申辩、抗争、协商;政治化的政策分析则认为,争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有创造性的、很有价值的特征”,它强调一种讨论或辩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把政治的和政治中的分析理解为深谙世俗的论证”③。这就是说,政策思想意味着一系列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观点。每一个政策问题的背后都隐含着对同一个抽象目标的诸多互相矛盾的解释(尽管往往同样可信)之间的竞争。
于是,观点和意见成为政策分析的核心。它们使得激发人们去行动和团结众人努力为集体目标而奋斗的共同意愿成为可能。政策制定成为一个永恒斗争的过程,即指导人们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信念上的斗争、政治范畴的定义上的斗争、分类标准上的斗争。这种政策分析的基础是承认分析概念本身建立在政治诉求上,而不是作为普遍真理的、被赋予特权的偶像④。
政策科学中政治的回归意味着利益与观念的多元性重构,意味着政治辩论及其民主程序的必需,意味着对真理式的政策霸权的解构。理性主义政策霸权之所以会因政治的引入而解构,是因为任何“政治判断产生的规范(都)是暂时的”——这“并非因为规范是相对的或者脆弱的——事实上也许是强有力的,可激发决定性的行动——而是因为规范来自公众意志,而公众意志本身是暂时的、经常变化的,且要经由不断延续的民主讨论、辩论、判断和行动的过程而产生,并正因为这个过程而合法化。该过程是政治文化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逐渐形成的公众目标的体现和反映”⑤。
二、政策主体观念的重建
现代主义的政策分析对技术专家和政治商业精英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是对的,因为这些政策主体确实严重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实际进程,他们也确实是政策空间的“大数”。然而,由于其反政治化的倾向和理性个人主义的基本假设,从而忽视了民主政体中的政策主体的“实然”和“应然”概念当中一些重要的成分,即主体间性或曰关系型主体的概念。同时,这种静态的观察也遮蔽了政策主体的多样性、灵活性、具体性和易变性。
现代主义的公共政策制定通常被假定为“直接决策者”的意志表达,他们似乎责无旁贷地、排他性地履行着科学决策的功能。然而,公共政策的政治现实却往往对此进行质疑。因为,如前所述,政治意味着多种利益与价值的冲突性表达和行动。直接决策者不仅受制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干预,而且还得接受民主政治和各种政治群体的制约。将公共决策视为一种政治生活,意味着对各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总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其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特定的群体活动创造出“我们”的同一性,构建出(临时性的)政策霸权。恰恰在这里,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现代政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变成了政策理解的一个障碍。我们应当抛弃那种把个人视为一个单子,一个先于社会、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无牵挂的、拥有独自的内生的理性偏好的个体观念,而将其定位为这样一个位格:它由各种“主体地位”的总和构成,在多样性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得到刻画,是多种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多种群体形式的身份认同过程的参与者⑥。为此,我们应当发展另一种政策主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政策主体是一种去中心的、去整体的行动者,这种主体是在多种多样的主体地位的交叉点上被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地位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必然的联系,而他们之间的连接是争夺政策霸权的实践的结果。因此,没有任何政策联盟、任何一种同一性是永恒不变的;当不同的主体地位被连接在一起时,总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歧义性⑦。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种观察政治化的政策过程的全新视角。当代公共政策的许多失败,就源自权力当局对政策主体(包括独断的决策者自身)的关系性和灵活性的忽视和无知。
有学者提出用“政策网络”概念来替代科层制的政策机制。这是一个不错的概念。将公共决策及其执行机制视为一种网络,意味着公共权力进入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卡蓝默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方面:“渐入清晰、进入对话、导入方案”,并试图以此构建有效的公共政策机制⑧。
公共政策利益与主体的多元性对程序上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民主的要求。民主政策的工作者不能指望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令所有社会成员永远同意的政策规划和安排,而是把权力和排斥摆出来,使它们可以被观察到,使其进入论辩和对话的空间中。按照法国的格莱特(Gret)研究小组的观点,主体间伙伴关系意味着“关系的均衡与平等,共同分享的政治观点,技能知识的互补,相互了解与信赖”⑨。关系型政策主体概念的提出,直接意味着主体间平等对话和政策话语的重建。
三、政策话语的重建
现代主义政策科学往往把政策分析视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这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过程,意即由决策者对自然对象、政策人口与社会的状态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把握,最终提出“科学的”政策方案。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我们不否认科学理性在政策分析中的作用,并在一定范围(即客观世界)内承认主客体认知的合理性,但是,因为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所以,我们反对将这种主—客体的单向认知活动扩展到政策的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而主张一种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对话模式。
政治性和际主体性在政策分析中的介入,使政策认识活动变成一种政策主体间的对话过程。这种对话要想顺利达成,按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必须同时满足四种有效性要求:(1)可领会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领会的表达,以便言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2)真实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3)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4)正确性: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达成某种默契⑩。这确实是一套值得我们向往和努力实现的政策对话规范。然而,置身于政治化的政策活动空间,除了“可领会性”以外,其他三条都是奢望,可遇不可求,因为政治本身就包含着策略。
我们主张的多元性民主政策观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是:(1)给各种政策主体平等的话语地位和发言权;(2)给予各政策主体真实表达自己的价值的机会;(3)对基本的政治价值——自由与平等——的共识,这是达成政策共识的基础。在此抽象认同的基础上,允许运用自由和平等原则,形成特定政策空间的不同理解和诉求。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构成了政策对话主体的“交往资质”或“交往能力”。
公共权力主体的责任在于,必须既能使自己与他者进行平等对话,又要保证其他行动者之间进行真诚和公平的对话;提供适当的公共领域空间和机制,并承担培育政策主体的交往能力的责任。阿马蒂亚·森认为,公共政策的作用不仅在于实施那些从社会价值标准和认同中产生的优先主次,而且在于推广和保障更充分的公共讨论。政府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公共政策帮助和促进公共讨论的范围和质量,诸如新闻自由和传播媒体的独立(包括废除审查制度)、扩展基本教育(包括妇女教育)、增强经济独立(特别是通过就业,包括妇女就业),以及有助于个人成为参与性公民的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革。事实证明,扩大识字和学校教育,保障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扩展社会弱势者的就业、挣取收入的能力与经济地位等,是提升政策主体的对话资质、促进政策对话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切实措施(11)。在这些条件逐渐成熟之前,转变政策分析人员的角色和功能,使他们能支持公民政策参与、代表社会良知、发现或扩大缺席者和弱势者的声音。
四、政策分析功能的重建
参与性政策分析的基本目标是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互相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12)。根据这种观点,政策分析人员需要把分析员、公民和决策者的角色集于一身。参与性的政策分析将使专家的实践满足公民政治授权的要求。
在这种参与性政策规划中,政策分析家扮演的角色是理论知识和不断竞争的规范论点之间的阐释性调停员。政策分析家们努力为政策执行者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性框架之间的对抗进行调停。詹宁斯曾号召采取解释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称为政策分析的“委员会”模式。该模式以客观性的“后实证主义”概念为基础,把政策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重新塑造为多种声音的谈话,由商谈伦理的阶段性标准来裁决。依据这种方法,政策专家与公民的角色将不会明显地截然不同,分析家最好被看成是一个“有专长的公民”(13)。
于是,政策分析专家将被重新定义为公共知识和权利的“提供者”。他们不仅提供数据,还将努力地把过程分析与技术分析的经验主义要求结合起来。为此,他们必须成为民意专家——熟知人们是如何学习、如何表达和如何作决定的;应当创造制度和知识条件来帮助人们用自己的生活语言(或日常语言)来提出问题,并且对技术分析进行检验,从而决定对他们来说哪些问题更重要(14)。
具体来讲,政策分析功能的更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民主成分的加入,这意味着由“统治”到“共识”的转变;二是伦理学成分的加入,即要实现由“求真”到“求善”的转变。在我们看来,政策分析的“求真”——对假想的最优政策方案的追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政策分析从根本上讲,应是一种社会实验;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充当的是一种学习机制和调节机制。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应当是对社会福利的促进,是“求善”。
但是,“求真”与“求善”二者并不矛盾,恰当的“求真”是“求善”的工具和过程;而且,对于不同的政策领域,二者构成的比例也应有所不同,譬如,一些高科技政策的制定,“求真”的成分就应更大些。如果像现代主义政策分析经常做的那样,将“求真”作为根本目标,或者虽然以解决问题、促进福祉开头,但在政策分析的过程中却忘记了这一目标,那么,“求真”的努力就值得我们警惕,因为,这往往会走向技术专制(technocracy)和权力话语的独断。
五、知识基础与分析框架的重建
现代主义的知识概念是一般的、普遍的,拒绝“意见”和“个识”,因而,其对象人群的概念是抽象的,只具有统计学的数量意义。其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的普遍价值的获得,靠的是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性概念。为此,认识主体和对象都被强制地拉到了一种同一性(统一性)的认识中;这种“同一性”统治着“差异性”。为了破解技术“知识”的“统治”,首先,有必要在政策分析的知识体系中引入“政治知识”,用“政治判断”去冲破“技术诊断”的樊篱。
政治知识,在巴伯看来,是公众和共识的产物。政治知识与抽象标准无关,它是应用的、实际的,可以理解为一种惯例,即行动的理论。政治知识是创造的、有选择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派生或发现的,因而总是与不断变化的历史形势和不断进化的社会意识相关联。“政治知识的条件性是真正自治的人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具体体现”(15)。政策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到实践性的知识,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科学的或其他的;在于找到共享的意见,而不是不变的原则。我们在进行政策分析与规划的同时,其实也是在重塑自己的知识——这种重塑是通过政治对话、民主协商和观念辩驳进行的。因此,我们应该用交往的、政治的实践理性取代或补充独断的、专家的科学理性。在这样做时,我们还应当批判地汲取西蒙和林德布洛姆等人的“有限理性”概念,用以克服现代理性的狂妄。
为了防止政策活动被纳入纯粹的技术活动,恢复其蕴涵政治与伦理实践活动的一面,除了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以外,还应当引入某种更具行动意义的思想。就此而言,实用主义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思想资源:(1)实用主义是一种看待现实与人类经验的态度。我们可以把实用主义的态度描述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不断试验的预设。这一预设乃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通过行动可以最好地理解现实。这一预设意味着必须把人类所“认识”的一切看作是暂时的,是必须作为假设或无限的东西悬搁的,直到下一次行动来对其进行检验。(2)理性主义选择模式的本质,就是正确或最佳选择的概念,其前提是假定存在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一真理先于实践,并应该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相比之下,实用主义的模式把知与行合并为一个过程。如果对一切都进行实验,并抱着求同存异、存疑改善的态度,那么,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是可能的。作为当下行动基础的同一性,是暂时的而非原则的,不是有关得出一个独立于我们的集体对话的权威结论的基础的问题。因为,“现实”是多元决定的和动态的。(3)“精英理性政府通过权力的运用(不论是政治的还是行政的)来使工具性的行动发挥作用;而实用主义主张通过合作性的行为发挥作用”(16)。实用主义的政府行政追求作为大众意志的表达,而不是否定后者的工具。
最后,为了将公共政策科学的重建工作落到实处,还需一种可行的政策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应该更为综合,既能包含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合理性,又能超越实证主义的线性逻辑。综合性的政策分析框架,应当将事实调查与价值批判、对政策目标的规范性分析与经典的经验主义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性的政策分析要完成两个层次的四重任务:一是“就政策论政策”,包含“经验论证”和“情景分析”两重任务。经验论证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实证性和参与性的经验分析,确定政策问题的性质、程度、范围,拟制问题解决要达到的指标体系,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情景分析就是要评价和考量既选政策方案和既定努力目标能否真正地解决政策问题,其针对性、适恰性、充分性能如何。譬如,在对地方经济发展政策研究中,GDP增长指标的确定就属于经验论证;而对GDP增长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考量则属于情景分析范畴。二是超越政策本身进入公共政策的社会系统,需要完成“系统论证”和“终极反思”两项任务。即关注政策目标对社会系统的贡献,关注政策秩序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譬如,系统论证要考虑经济的快速增长政策可能会给生态保护和能源的可持续开发造成的影响;而终极反思的对象是经济发展模式背后的理念(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否符合社会组织的基本理念(如平等和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本身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纯粹的物质丰裕还是人的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公共政策是对一项公共行动的政治上的辩论与决议。我们希望通过“政治的回归”、对政策主体和利益的多元性的重视、政策话语机制和知识基础的重建,能超越现代政策科学实证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理性主义倾向,建立一种转型的或解放的政策科学。其目的在于帮助政策分析者重构其分析理念与框架,帮助政治行动家们更好地理解公共政策的政治与实践内涵。这种政策科学力求既从理性方面又从感性方面把政策过程澄清并加以理论化。与此同时,“必须重申,经验主义研究对于这种探索十分重要。但是,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能够通向更大的、更广阔的规范性辩论,而不是仅仅在其经验主义的预测力方面”(17)。这种政策科学的基本目标不是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的预测和社会控制,而是要协助并且提供对创造性的政策设计、政治矛盾和民主可能性的推论性的探索。
注释:
①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②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③Deborach Stone,Policy Paradox and Political Reason,Glenview,IL:Scott Foresman/Little Brown,1988,p.4.
④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第227~228页。
⑤Benjamin R.Barber,Strong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70.
⑥墨菲:《政治的回归》,第111页。
⑦这种政策主体思想源于墨菲的政治主体概念,参见墨菲《政治的回归》,第14、111、115页。
⑧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170页。
⑨转引自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第159页。
⑩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12)Patsy Healey," Planning Through Debate:The Communicative Turn in Planning Theory" ,In Frank Fischer and John Forester ( eds.) ,The Argumentative Turn in Policy Analysis and Planning,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238.
(13)转引自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第232页。
(14)Frank Fischer,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Newbury Park,CA:Sage,1990.
(15)Barber,R.Benjamin,Strong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170.
(16)M.C.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17)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