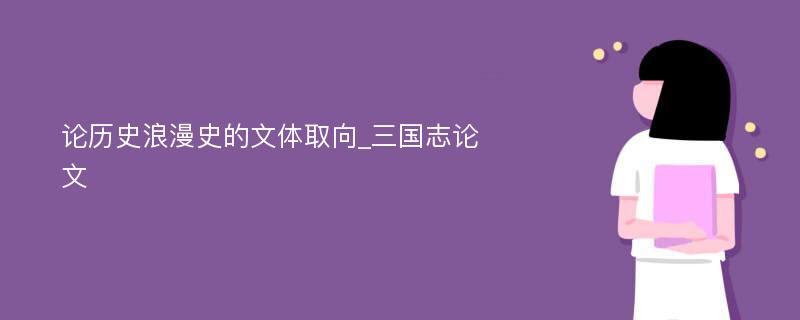
论历史演义的文体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演义论文,文体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演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文体?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无事生非之嫌。我想,很多研究者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历史演义”是一种以历史事实为题材的通俗文学体裁,其文体性质当然是文学性的;历史演义=历史演义小说=历史小说。在这种小说本体意识的引导下,学界对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的创作与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如下的模式与程序进行:
首先,把一切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设定为小说,把一切有关历史演义的理论设定为历史小说(或历史演义小说)理论(不少研究论文或专题就直接以“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理论”为题)。
其次,对这些被设定为小说性质的历史演义创作和历史演义理论进行评析,指出它们在处理“虚”“实”关系时的特点,然后把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创作和历史演义理论大体分成三类:①严格忠实于历史,但艺术性贫乏;②基本上忠实于历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虚构;③随意驰骋想象,严重违背历史。
最后,对第②类进行充分的肯定,对第①类和第③类提出批评,认为第①类没有意识到历史演义的小说性质,历史演义毕竟不同于历史书;而第③类则没有意识到历史演义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创作,它还要受历史规律所制约。
譬如杨子坚先生的《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在论及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的时候,首先为历史演义下了定义:“我们把《三国演义》以及明中叶以后陆续出现的,以一朝一代兴亡为线索,依据正史,采撷野史、杂记、民间传说,敷演成章回体的历史小说叫历史演义。”(杨子坚著《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第10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先把历史演义定义为小说范畴,然后在此一范畴下去探讨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的虚实关系和艺术成就。这一研究模式普遍出现在古典小说研究界。
这个研究模式与程序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呢?由于明清时期的评论家的“历史演义观”是在具体评价某一部历史演义的时候表达的,其本意并不是要全面阐述历史演义的性质、虚实关系等,所以其评述往往是点到即止。当我们全面探讨一位较多方面谈及历史演义的评论家的观点的时候,上述模式与程序便面临着操作上的危机。譬如赵明政先生的《明清演义小说理论概说》(《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一文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论述:把一切历史演义视为历史演义小说和把一切历史演义理论看成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然后把修髯子、于华玉、梁绍壬、褚人获等人的主张归入“要求演义小说、情节以至细节,必须按史实‘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全面把它作正史看”的一类。最后批评道:“这一派文人的主张,看似抬高、推崇演义小说,实则抹煞了小说的文学性,混淆了史书与小说的根本区别。”其实,修髯子等人并不都把历史演义当“历史演义小说”看。赵先生把陈继儒归入“在总结《三国演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抓住演义小说的根本特点,提出了比较确切的界说”的一类。指出:“他们反对演义小说‘字字句句与史尽合’,认为虽要依傍正史,但不应拘泥于史实,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可以点缀附会,也可以添设敷衍情节,这就是‘踵事增华’。”指出“陈继儒认为演义小说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杂采野史传说敷衍辅衍,二是以通俗谕人。”似乎陈继儒在提倡演义作品的小说特性、文学特性、想象特性。然而,很多研究者却把陈继儒归入严格纪实的一类。如果我们不是把历史演义预先设定为小说性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大多数研究者的判断。
在明清时期的有关历史演义的论述中,有不少评述者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但他们的评论却以纯粹历史学的实录为准绳。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譬如,方正耀先生在其《中国小说批评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说到:“当然,明代的理论在不断变化,明显表现在不少批评家虽对演义小说,描写时政的小说仍以实录标准衡量,而对其它小说则不再苛刻要求实录了。”(上书第122页)“以毛宗岗、蔡元放为代表的批评家, 强调实录主要是针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而言,尽管他们的论述涉及了其它的小说,但并非强调一切小说都得实录。”(上书第151 页)我们恐怕没有理由怀疑明代胡应麟的艺术感悟力,他的《少室山房笔丛》所闪耀出来的艺术睿智一直令后世读者为之折服。但是,他却使用史学实录的标准去评价《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不符史实的情节进行指责。冯梦龙更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通俗文学家,在文学的虚实关系问题上发表过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他曾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警世通言·叙》)然而,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对《列国志》中不符合史实的虚构部分,包括野史、民间传说等进行删除。赵明政先生说:“明末冯梦龙以《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为依据加以改编的《新列国志》,把一些富有艺术想象的生动故事一扫而空,虽然在情节的编排和文辞的修饰方面胜过原著,但毕竟缺乏艺术吸引力。”(赵明政《明清演义小说理论概说》,《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 期)这些“矛盾”现象应该怎么解释呢?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具有深厚艺术素养、文学创作经验的评论者一进入历史演义领域就对艺术性麻木不仁?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评论者如此蛮横地剥夺历史演义作者的艺术虚构的权利?究竟是这些评论者的艺术修炼还未到家、还不全面呢,还是他们对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另有看法?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评论者虽然认为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是小说,但它既然以历史为题材,以演绎历史为任务,那么,它必须严格忠实于历史,演义家的工作只是排比、剪接、组合历史事实,清代的蔡元放就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情况是,评论者虽然身为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看成是小说的、文学的,而是看成是历史学的,他们把历史演义当成正史的普及通俗版,这样,他们对于历史演义采用历史学的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而,对于后一种情况,简单地站在文学立场上的指责也就显得不恰当了。
二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体观念的不同,同一个文本的文体性质可能会被作出不同的理解与定位。对于先秦人(或东晋的郭璞)来说,《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其文体性质是地理学的,后世的研究者尽可以用神话学观念去研究它,但是,如果要探讨《山海经》作者的“神话学观念”,那么,它的作者恐怕会觉得这样的概念简直匪夷所思。对于清代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来说,尽管他没有把哲学书、史书、辞赋、诗歌、小说、戏剧等视为同一种文体,然而他以“同一付手眼”评点《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表明他的文体意识近乎零。在他的眼中只有一种大文体,那就是“文章”,他把一切文体的文本都当作一种文章来读,他以传统文章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去评判、赏析一切文本。这样文章学眼光是明清时代文学理论界的一大特点。清代评点家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见解精到,成就很高,影响深远,但是,他在谈到《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问题时,却认为《三国演义》之所以高出于其他小说,就因为它严格忠实于历史。把史学实录强调到不符小说本身的实际的地步,这样一位评论者能够体悟到《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吗?实际上,这样的“矛盾”在毛宗岗身上并不矛盾,与其说,他是在运用小说学的理论去评点《三国演义》,不如说,他是在运用文章学的观念去评点这部小说。所以,一方面他能够揭示出《三国演义》诸多叙事之妙,一方面又在历史演义中确立史学实录的最高价值。
历史与文学,从强调撰写者的主体性这一点上看,它们具有同一的一面。文学是作家的心灵写照,这在今天已经成了共识;而史书的撰写也必须寄寓撰写者的主观评判,这就是传统历史学中的“皮里春秋”的原则。既然都是要表现或寄寓撰写者的主体性,那么,即使是文章(历史文本或文学文本)的材料排比,也必然要依据、围绕着撰写者的主体性而展开。因此,不仅不能把文学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纯客观的镜子般的反映,而且不能把历史书当成是对历史的纯客观的记录。正由于历史学与文学有诸多同一性,尤其当文学取材于历史的时候,历史学与历史文学便面临着相似的命题,并形成相似的范畴。譬如“历史事实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关系,虚与实的关系,等等。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明清演义普遍存在着“讲史之病”:“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言辞,又颇惮于叙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清演义的这种“讲史之病”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因为第一流的小说家对历史演义这种文体不屑一顾,而蹩脚的作家却对这种文体情有独钟呢?抑或是明清历史演义的编撰者另有追求?我看两者都有。《三国演义》出现之后,的确还未见有演义作品在文学性方面可与之比肩并驾;同时,并不是每一个《三国演义》的效仿者都以《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为追求目标,有的效仿者追求的是史学的真实性。这就关系到另一个问题:明清历史演义家是如何看待历史演义这种文体的?这也关系到如何看待“讲史之病”的问题。从文学的角度看,明清演义的确普遍存在“讲史之病”,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讲史之病”只是历史普及工作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小毛病而已。
即使如此,历史学与文学(包括历史文学)仍然表现出各自的鲜明的个性。史家、演义家与历史文学都面临着一个基本命题:虚与实的关系。然而,历史文学的虚实与历史学的虚实却是貌合神离的。对于史家来说,强调虚,有其不得已的无可奈何;对于历史文学家来说,强调虚便是回归(相对于中国史官文化中心而言)文学本性。我们不能一看到有人谈虚,就说他在表达他的文学观。从学科性质上看,一属于科学,一属于艺术。科学强调实事求是,艺术强调失事求是。——这已经是文艺理论界的老生之常谈了。我们不能因为历史学与文学有诸多方面的同一性而消除它们各自的本性,不能因为历史文本具有“文学趣味”而把它划入文学范畴;同样,我们不能因为一部文学文本具有“史诗”性质而把它划入历史学范畴。我们可以在文学文本(当然不止文学文本,而且应该是一切文本)中寻找材料以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但文学文本并不因此而改变文学性质而变成社会学著作;同样,我们可以在一部历史学文本的“文学趣味”上获得审美上的愉悦或创作上的启示,但是,历史学文本并不因此而变成文学作品。
曹础基教授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常常将《左传》、《国策》、《史记》,乃至《国语》、《汉书》等列为文学作品来讲。”(曹础基《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点》,《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 期)有人甚至“否认了《左传》的根本性质是历史。把《左传》作为纯文学,和小说创作等量齐观。”(转引自上文)又有人说:“《史记》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从主要篇幅——传记部分来看,它不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富有文彩的历史),而是历史文学。它可说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清史演义》一类作品的先驱。……传记中的文学作品竟逾三分之二。”(《再论〈史记〉不是史》,见《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转引自上文)
把古代历史文本划入文学范围,这似乎还可以从今天这一类学者的个人兴趣上去解释。然而,这种文类的当代转换在古典文论研究上却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厚诬古人”。古代历史文本的研究者、评论者是在历史学范畴上发表他们的见解的,而经过今天的文类转换之后,某些历史文本变成了文学文本,这些古代历史文本的研究者、评论者所发表的见解就被当成他们的“文学思想”。最终,我们不得不抱撼:这些研究者、评论者为何如此缺乏艺术细胞!
作为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的《史记》无疑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史记》的文学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如果因为《史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就把它归入“传记文学”,如果因为司马迁具有高超的文学手段而把他的撰史理论当成“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那将会陷入张冠李戴的局面。郭沫若先生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家实在是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就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那里面有好些文章,如《项羽本纪》、《刺客列传》、《货殖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等等,到今天还是富有生命的。”(《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我们今天以“历史小说”眼光或“史诗”眼光读《史记》,这当然“也可以”,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认为司马迁是以“历史小说”眼光或“史诗”眼光去撰写《史记》的。在陈兰村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下简称“陈著”)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记文学”概念的最为宽泛的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对“传记文学”的解释是:“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什么样的情形可称之为“文学性较强”?是指在纪实题材中加入大量的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呢,还是指高超的剪裁、取舍、组合技巧呢?倘若是前者,那么司马迁恐怕会把当今学者加在《史记》头上的“传记文学”头衔视为对《史记》的批评:倘若是后者,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切史书都具有文学性,我们更可以进而指出,一切性质的文本(不管是史学的、哲学的、经济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具有文学性,这样“文学”的概念就可以成为揽括人类一切撰写行为的概念。这样过于宽泛的概念由于其大而无当反而失去了概念的本性。然而,陈著却欣赏这种“模糊”、“宽泛”的概念,因为“使‘传记文学’的概念宽泛一点,可以包容‘文学性较强的’各种传记作品。”(第2页)在这个宽泛的概念之下, 陈著探讨了司马迁传记文学思想。司马迁并没有阐述他的“传记文学思想”的专文,于是,一种循环论证的模式出现了:先把《史记》定性为传记文学,于是司马迁的撰写行为就是一种传记文学创作,司马迁对他撰写的《史记》的总结、论说,就成了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于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部分序赞、《报任安书》等总结、论及其撰史经验的文字便成了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的表述。
我们赞赏司马迁《史记》的文学魅力,我们注意到《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也注意到《史记》中丰富的文学因素。然而,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因此而把《史记》看成是传记文学。《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书都蕴含着程度不同的文学性,但并不因此而改变这些史书的历史学性质。承认《左传》、《史记》等的历史学性质,并不妨碍传记文学家从中汲取文学创作的养份。
应该承认,文学和史学有其相通的一面,然而,文学和史学毕竟又有各自的个性。譬如对于“虚”“实”关系问题,文学与史学的价值取向显然是不同的。对于史学来说,虚构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是史家应该尽量避免的,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做了一些虚构。然而,这样的虚构却不值得大肆张扬。但是,对于文学家来说,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却是检验文学家的艺术素质和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把《史记》假定为传记文学、把司马迁的有关论述当成“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对司马迁抱着这样的遗憾:司马迁在其“传记文学理论”中没有对艺术虚构、艺术想象作出足够的论述。而实际上,这样的遗憾与司马迁及其《史记》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东晋时有“良史”之称的史学家干宝写过一部搜神志怪的书,叫《搜神记》,今天的学者把它看成是“志怪小说”,然而干宝却并不认为他在创作小说。他说:“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搜神记序》)他认为他在做史学意义上的实录工作。我们如果把干宝这段话当成干宝的“志怪小说观”或“小说虚实观”,那么干宝一定会认为我们在痴人说梦。我们不能采用这样的批评程序:我们认为《搜神记》是志怪小说,干宝说,他的《搜神记》是实录,说明他的“志怪小说观”忽略了小说的文学性质,小说毕竟是小说。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干宝把《搜神记》视为一项史学实录工作,认为神怪是与历史事件一样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他“博采异同,遂混虚实”(《晋书·干宝传》)。这个“虚实”当然是史学意义上的。
历史演义作为一种文体,在明清时期,既有人把它当成文学文本,也有人把它当成历史文本。一个评论者对其评论对象的文体性质的理解,规定着其评论话语的基本性质的特征。
如何处理历史描述与当代意识的关系,这是我们理解、诠释历史现象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在诠释历史现象时,首先应该设身处地、从历史现象的历史氛围去描述,然后才是以当代意识去评判它。倘若忽略历史描述的阶段或以当代意识去代替历史描述,那么,其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往往会似是而非。譬如,关于明清以来的“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理论究竟是如何的?迄今为止的学术界倾向于用今天的“历史小说”的概念去理解、诠释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有人甚至把明清历史演义统称为“历史演义小说”。然而,在明清文人那里,“演义”究竟是一种历史文体,还是文学文体?倘若不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准确把握明清文人的历史演义理论。
所以我们对明清时期历史演义理论的整体性考察似乎可以遵循以下程序:首先考察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作家和评论家对“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的理解,看看他们究竟是从文学范畴还是从历史范畴去理解“历史演义”的;再分别考察作为历史学范畴和作为文学范畴的历史演义理论是如何规定各自的虚实的基本关系的;最后才是对各种历史演义理论的价值评价。
三
我们先看看明清时期的人是如何给“演义”下定义的。
何谓“演义”?明清文人给它下的定义一直并未达到概念上的明晰与一致。
袁宏道说:“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明代甄伟说:“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通俗演义也即使正史通俗,演正史之义。
在明代的天许斋那里,“小说”与“演义”甚至是可以互换的:“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在天许斋看来,《三国志演义》是小说,而冯梦龙的“三言”则是“演义”。在这里,“小说”与“演义”其实是二而一的。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鄙可嗤也。”(《庄岳委谈》下)在我们今天看来,《水浒传》属英雄传奇,《三国志演义》属历史演义。但在胡应麟眼中,《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一样都被归入“演义”。天目山樵把《红楼梦》、《金瓶梅》也称为“演义”(见天目山樵《儒林外史新评》)。
刘廷玑说:“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刘廷玑《在园杂志》)这个“添设敷演”的幅度究竟可以有多大而不致破坏“本有其事”的大原则?刘廷玑指出《三国演义》中“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同上)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大致说法而已。
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说:“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出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歧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如《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唤田家妇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
我们可以从文体论的角度,把明清时期的有关历史演义的论述分成三类:
(一)把“历史演义”视为正史的通俗版,正史的普及读物。把“历史演义”定位在正史与野史之间。
不错,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历史演义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我们今天关于“演义”体的理解是由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的。今天,《三国演义》只出现在文学史上,而不是出现在元、明历史书上。《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使今天的学者有理由把它归入文学史中。况且,历史小说在20世纪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体,于是,把“演义”理解成文学体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然而,明清文人并不都把历史演义当成文学创作。在某些明清文人那里,“演义”是一种历史文体,是正史的通俗版。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即是说,它是史书《三国志》的通俗演义。
提倡采自野史轶闻并不等于提倡虚构的文学想象。而是基于野史可补正史之阙的观念。
从这种观点,我们来看看小说批评史上那些一直被认为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理论究竟是如何看待“演义”体的性质的。
明代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一直被认为是小说批评史上第一篇讨论历史演义的文章。实际上,在这篇序文中,蒋大器自始至终并未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也许有人会说,蒋大器从史的角度谈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有意提高《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地位。然而,直至终篇,蒋大器并未从史的论述过渡到文学的论述上。所以,他的史学角度并不是官样文章。这篇序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史书的实录与春秋笔法的关系,这是一些史学界的老生常谈的说法。第二段指出正史“理微义奥”,所以“众人”知难而退。而野史则过于鄙俗,与正史相比,走向了另一极端。而“演义”体刚好处于正史与野史之间。他指出,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历史材料“留心损益”。不少论者认为“损益”指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其实,这里的损益是指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对“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也即花一番心思在史料的选择增删上。这使《三国志通俗演义》不致堕落到野史的鄙俗上。同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这又使《三国志通俗演义》不致如正史那样理微义奥。
显然,蒋大器把演义体定位在正史与野史之间。属于史的范畴,也即把演义体视为正史的通俗版。在这种理解下,他当然不会讨论演义体的“艺术虚构”问题。
这篇序的第三部分谈蒋大器读陈寿的《三国志》之后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并要求“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即在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也应思考这些历史问题。
明成化间林瀚在为《隋唐演义》作序时同样把“演义”体定位在正史与“稗官野乘”之间,“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
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同样指出演义体是正史的通俗版,所以他着重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俗近语,隐括成编”,“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虽然他说:“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这里的“稗官小说”指的应该是野史,而不是指文学范畴的小说,所以这篇“引”并不涉及演义体能否虚构的问题。
陈继儒更是严格地看待历史演义的正史通俗版性质,他说:“往自前后汉魏吴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世则有演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陈继儒《唐书演义序》)所以他为“时采谲狂,于正史或不尽合”的熊大木所创作的《唐书演义》作序,“亦怂恿光禄之志”,这种低调处理的态度自可见出他对熊著未能严格忠实于史实感到遗憾。
正由于陈继儒是在史学范畴上定位历史演义的,所以他可以把余邵鱼的《列国传》视为“此世宙间一大帐薄也。”(陈继儒《叙列国传》)他说:“《列传》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核而详,语俚而显,诸如朝会盟誓之期,征讨战攻之数,山川道里之险夷,人物名号之真诞,灿若胪列,即野修无系朝常,巷议难参国是,而循名稽实,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譬诸有家者按其成薄,则先世之产业厘然,是《列传》亦世宙间之大帐薄也。如是虽与经史并传可也。”(同上)
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有云:“……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迄于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沉。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继群史之遐纵者,舍兹传其谁归?”
对于这类演义观,如果责备它们缺乏艺术感觉,那是不公平的。
(二)把“历史演义”当成野史。
高儒看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据正史,采小说”的特点,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学性的一面(见《百川书志》)。实际上他是把《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成一部野史。所谓“据正史,采小说”,显然把“演义体”定位在正史与小说之间,在对正史进行通俗化的过程中,小说也被采入,这就是野史。
杨尔曾则充分肯定《东西晋通俗演义》的作者对于通俗历史小说的倡导之功:
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三国》、《水浒》始也。(《东西两晋演义序》)
(三)把“历史演义”当成小说。
这里又可分两种:一种认为既是小说,则遵循小说想象的规律;另一种人则认为,虽是小说,但毕竟属于历史的演义,所以应严格忠于史实。
与把历史演义当成正史的通俗版的文体观不同,明代熊大木把历史演义的文体性质看成是小说。有人提着《精忠录》找他,“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也即请熊大木为他创作历史演义。于是他创作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并采用了一些与正史不同的小说故事。在这部演义的序文中,他为这种引小说入演义的做法辩护,认为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可以两存之以备参考。这实质上是肯定了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他在该序文中所提及的“用广发挥”就不仅仅是指对史料进行取舍组合,这一提法极易引申为在史料的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切入艺术的本性。
熊大木创作《唐书演义》,有人因为这部演义“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而认为这部演义不足以行世。对此,李大年从文学的观点予以辩解:“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且词语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岂以其全谬而忽之耶?”(李大年《唐书演义序》)
谢肇淛已把《三国演义》当小说,但认为《三国演义》太实,艺术想象不足。他指出:“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关,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五杂俎》)也即以文学的艺术想象特性为标准去评判。
明代酉阳野史编《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有人提出批评:“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议乎?”酉阳野史反驳说:“世不见传奇戏剧乎?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始终有就尔。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虽不能比翼奇书,亦有感追踪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云。”(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酉阳野史显然已经把通俗列传(历史演义)定位在小说上,并从小说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去肯定历史演义的价值。
明代可观道人把通俗演义定位为小说:“小说多琐事,故其节短。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他把《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夏志传》、《有商志传》、《列国志传》、《西汉演义传》、《东汉演义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等视为小说。然而,可观道人又认为,历史演义应该严格忠实于历史。对于《有夏志传》等通俗演义,可观道人认为它们出自村学究之杜撰,故令识者欲呕。而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则是“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同上)实际上,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曾在符合史实的原则下对余邵鱼的《列国志》进行大修改,将原书叙事与史无征、详略失宜、身世姓名谬误的一一改正,有些部分还作了删节和补充,比旧作更符合史实。删除了原书中采撷的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某些艺术虚构的情节。纠正了原书中铺叙之疏漏,人物之颠倒、制度之失考等。
清代的蔡元放取《新列国志》而略作文字加工,写成《东周列国志》,并加上大量评语,成为近两百年来同类题材的最流行的本子。他在总结其创作经验时说:“《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都是假话,如《封神》、《水浒》、《西游》等书,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东周列国志读法》)这样的历史小说连“补截联络之巧”都用不上,所以反不如虚构作品好看。
当我们在探讨明清时期评论家的“历史演义观”的时候,首先应了解其时的评论家是在历史学范畴还是在文学范畴上谈论“历史演义”。至于在实际上或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作为历史学范畴的历史演义与作为文学范畴的历史演义有什么不同,则是另一回事。历史演义的虚实关系与该作品的艺术水准之间并不构成比例关系。
标签:三国志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三国论文; 小说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水浒传论文; 搜神记论文; 读书论文; 司马迁论文; 国语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野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