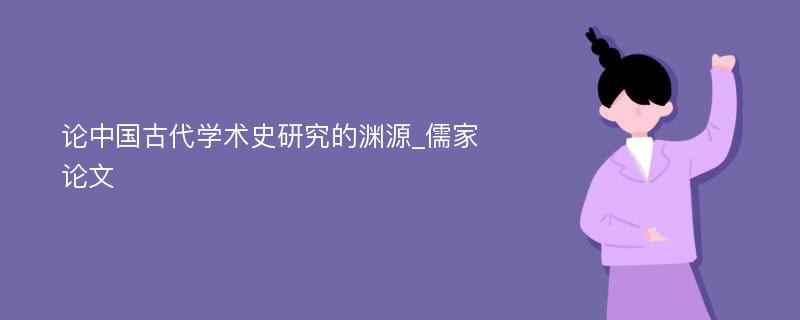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之源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之源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6-0001-08
一、学术史研究与古代学术文化的起源
学术在中国古代又称“道术”,乃圣贤治天下大经和大法所托寓,故可谓学术研究的实质相当于探索治天下的要旨大义。于此可见学术史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古人治学,系在模拟治天下或国家,孔子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孟子谓墨者夷之欲以薄丧之道“易天下”(《孟子·滕文公上》),皆可为证。也就是说,学术史研究关乎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及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这可以儒学史的研究说明之。若不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儒学史,不理解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便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以此可见学术史研究之重要。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目的是以“求道”、“明道”为本;亦或提出,学术史的研究理念以“道”为体,以“史”为用。那么,何谓“道”,便成为中国学术史必须解决的问题。道是宇宙世界的本原,古人将“道”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人们“求道”、“明道”,是为了认识世界和究明社会,并从中引伸出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秉持的信念及行为方法。由于“人为天地心”,故中国古代的道术探索以个人道德修为及家国社会治化为中心,可将其归入政治伦理的意义范畴。《潜夫论·赞学》曾如此论述探索学问的宗旨:“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故而追求学问的宗旨在于修成德义人格。在古人看来,政治不过是人格的延伸,故德义人格修养是最为根本的学问功夫。儒家认为,自天子下至于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由于人是宇宙天地的中心,修身进德乃为人立事之根本,中国古代学术史“求道”、“明道”的探索即围绕此核心主题展开的。总之,历代学者探索道术的活动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框架。
从大的方面讲,学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主要与人们探索世界未知、解读自身以及揭示社会运作及其发展法则诸方面的实践需要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需要,即政教治化管理之需要,培育人才之教育需要,社会精神文化自身的发展需要。
首先,《庄子·天下》篇在追溯道术起源时提出“神明”概念作为道术的形上本性,圣王乃有得于神明本原的得道者,他们又具体表现为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个形上人格。此形上的道术本原转为形下的世事器数之理时,则具体表现为君子、百官、庶民的形下人格特征。由此形上的神圣道术本原转为形下的世事器数之理,乃由圣而俗的变换,再表现为“其明而在数度者”,即进入具体的现实学问,出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邹鲁缙绅“六经”及散处天下中国的百家之学。道家思维哲理的根本是抽象之道,故庄子在追溯学术起源时,演绎了由形上而形下再推原出现实的学术理念,论述显得神秘而迂曲。但若透过其关于道术产生之抽象神秘的论述形式,则可发现,庄子欲说明的乃是学术的产生适应了政教管理的现实需要。
荀子未像庄子如此专门论述过学术的起源问题,但通过对其相关思想的分析,可知其认为学术知识乃经圣人、君子的创造积累功夫而形成。荀子认为,圣人、君子乃国家社会的根本,乃道法治化之原。《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致士》曰:“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圣人、君子既为道法治化之本,故其人格高尚可贵;其人格之形成,乃努力于礼义的创造积累功夫所致。《儒效》曰:“涂(途)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王制》曰:“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此不惮其详地引述荀子之言,就是为了着重说明圣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及礼义法度皆乃经创造性实践的积累功夫而成,皆非“生而知之者”。荀子又特意指出圣人优异于众人者,在于其富有人的主体创造自觉,即《性恶》所谓:“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按:“伪”指人的主体创造自觉。荀子又指出,道乃由圣人掌控,“六经”则是用来表述道的。道与“六经”出于圣人创制,也用以表现圣人道德功业的知识文化成果,其崇高自不待言。但若以圣人、君子与“六经”文本相比,其人格要比“六经”文本价值高出许多。以富于生命感染的君子人格作为效法榜样,要比仅仅学习经书文本效果好的多。这反映出荀子对主体本原创造性的充分肯定,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关键所在。荀子所看重的是道德经世功业,而非经书文本,反映出他对儒家重经世实践精神的认同与坚持。综之,荀子虽未像庄子那样专门论述过学术文化的起源,但通过分析其关于圣人、君子与道法礼义关系的认识,可以发现其重经世实践而轻经书文本的信念,由此可从中推导出荀子必主张学术知识出于实践创造积累的结论,尤其是他所谓“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对于我们理解此问题更有直接的启发。这样,借助荀子的论述可使人认识到,圣人、君子出于政教治化之需要,创造积累起礼义道法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学术文化知识,儒家“六经”即是。不唯如此,“六经”实乃上古学术文化知识成熟性的标志和集大成总结,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进一步谈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关于“六经”的性质,《汉书·儒林传》有很好的概括:“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将其政教治化意义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
其次,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培养人才的教育需要关系密切。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以周为代表,周代教育的发展从以实用知识技艺为主向以文本知识为主演进,故学术文化在周代有了极大发展。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贵族教育,较早见诸记载者为《尚书·舜典》“教胄子”制度。中国古代堪称圣贤模范政治,首重统治者道德人格的垂范影响,尤强调政教治化主体的道德修养。《尚书·皋陶谟》提出为政以德的问题,有谓“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即为政以德方可达于理想的政治状态。为此,居治位之高下要以德之大小来区分,如“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即三德者可为卿大夫,六德者可为诸侯,九德皆具者为天子。关于修德之目,可举《尚书·尧典》所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大体相当于《礼记·大学》所谓修齐治平的功夫。与此相关,家国治化之教育重在德教。《礼记·文王世子》:“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指明德教乃正官、治国、成君之本。贵族教育很注重以礼乐方式修德,如《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乐相比较,乐更重要,因为祭祀需要音乐娱乐交通神明,以营造“神人以和”的氛围和效果。同时,乐是培养内在道德世界和完美精神人格的手段,故成为贵族教育的主导内容。《文王世子》曰:“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按:“干戈”、“羽籥”俱指乐舞,一为武舞,一为文舞。《礼记·内则》言“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舞大夏”。说明乐舞为贵族教育的主导内容。《礼记·王制》有“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制,主诗书礼乐四术的教官即小胥、大胥、小乐正及大乐正等乐官,仅此足见乐教在贵族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综而言之,周代继承了三代以来的贵族教育制度,其突出特征是乐教、乐舞内容占较大比重,这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及其文化的一个特征,即注重实用知识技艺在教育上留下的影响。此外,周代社会被称为礼乐文明,一因周代国家提倡以礼乐教化天下,二因周代贵族注重以礼乐修身进德。这种礼乐教育是导致乐教、乐舞地位突出的根本原因。学术文化的发展促使知识表述向文本集中,礼乐文化成果被孔子在经书文本中汲取继承下来,成为学术文化获得发展的一个表现。
乐教、乐舞在古代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当时的交流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早期语言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产生了诗歌这种有着节奏和韵律的简明生动的表达方式,人们为摆脱语言交流上的局限,不得不借助于肢体的动作,于是形成了诗歌与舞蹈的结合。诗歌与舞蹈往往还须借助于音乐节奏的协同配合,于是形成诗歌、舞蹈与音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以致于无论是祭祀与神灵交流,还是在一般较庄重的场合,多采取诗歌、舞蹈与音乐相伴的形式,以示隆重热烈,由此而决定了乐舞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在各种交流表达方式中,还有诗歌与音乐结合,舞蹈与音乐结合等方式,这同样决定了乐教、乐舞在贵族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孔子删订“六经”,使诗与乐各自独立,各为一经,但据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及“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的记载,诗与乐舞结合的形式仍旧保存着,及至后代依然。但由于诗歌与舞蹈及音乐各自都经过相当程度的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艺形式,与早期交流中为增强表达效果而不得不相互配合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们在经书中并列为各自独立的文本样式,是即《诗》、《乐》二经。孔子删订“六经”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周代负责六艺教育的原为师氏、保氏,以德行、道艺为主,六艺本属道艺范畴。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乃贵族必须掌握的实用知识技艺,与“祀与戎”所谓国之大事相关;书数则是应用广泛的日常实用知识。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贵族的没落,新的士阶层与新式文官的出现,六艺体系逐渐被新的文本化知识体系所取代。特别是春秋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达,其突出表现即孔子删定“六经”。“六经”使学术文化趋于文本化、专业化,知识表述向文本集中,已不再局限于实用知识技艺层面。孔子以“六经”教士,文本知识普及,学术文化寻求到更适宜深入发展的专业化、知识化形式,孔子以“六经”文本取代了旧式的“六艺”教育。《孟子·滕文公上》述三代学校制度时有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此借助教育倡明人伦道德,以使广大庶民向风影从,反映了三代以来所设计的由上而下推行教化管理的意识,礼乐教育方式无疑是最为适宜的。此面向庶民百姓的明伦教育随后沿袭下来,如汉代《论语》、《孝经》在县乡基层的普及即是。但仍须借助经书文本的形式推行,这是春秋以来学术文化向下层平民教育的深入发展。
再者,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主要与以下两点相关,其一为文明起源与学术文化起源的方法途径,其二是作为民族文化最高精神思维原则的形成。历来讲中国古代精神文明起源,几乎首先提及伏羲画八卦之说。《易·系辞下》有一节关于上古文明起源历程的著名记述,其由庖牺氏数起,历叙神农氏、黄帝及尧、舜,并历举各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概况。庖牺氏既为首出,取得文明成就亦颇大,其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段记述内涵丰富深邃,极为重要。它指出庖牺氏乃上古首出的文明酋长,对后世最具开启意义的文明成就可归结为“始作八卦”,谓其开创观象制器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并下启神农、尧、舜观象制器等发明,从而具体表明八卦作为原初的精神文明成果,对古代思维方法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系辞下》关于上古文明经历的叙述,极受后世推重。刘歆《世经》基本据此,三皇五帝史统之形成,此记载是重要根据之一。更重要的是,以此记载为框架,衍生出上古文字起源的叙说。《说文序》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此段文字显然取自上引《系辞下》,但内容文字经许慎重予编组。《史记·太史公自序》据“六经”述上古文明史,亦首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即从三皇五帝史统讲,伏羲乃上古文明发端期,继起的神农、黄帝则继承了此文明发皇的辉光。如果八卦可归结为初起的原始文字,那么,伏羲画八卦对仓颉造书契本有开启意义,而且由文字发明更可证明伏羲八卦在文明初启时代原创性影响的持续。儒家谓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亦即以尧舜为上古文明的开启时期,故有学者主张中华文化胚胎于夏商,化成于两周,自应为研究古代文化起源者所关注。但古代关于伏羲、周文王、孔子代表的易学文明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不容轻视。尤其是将三圣相传之脉集于易学这一关乎古代精神文明起源的早期经典上,其中必具深意,应予关注。至少这是借伏羲、周文王、孔子三位文化英雄的权威,提高《易》在中国文化上的尊崇地位,从而强化《易》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经典性本原意义。
《汉书·艺文志》谓诸子百家之学皆曰出于王官,则学术文化的起源应与官守职掌有关。与古代文明发端于伏羲时代相应,《汉书·百官表》亦追溯官制始于伏羲时代,《荀子·正论》、《礼记·明堂位》及《尚书·周官》等亦论及唐虞夏商官制,至《周官》载三百六十职而三代官制大成。从现存资料看,一般认为《尚书》所载尧舜命官之事乃关于官制出现的较早而可信的记载,此前多为传说,只是不可谓无稽。因为即使正式设官制度仅能推原至虞夏前后,但此前若干世代积累的相关管理经验是不容抹煞的,它们会以不同方式渗透融入后来的官制中发挥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追溯官制于伏羲时代才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伏羲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源头,这是古代多数学者的共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论上古起源甚早的五行之官时,述及其时的官守原则:“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上古官职父子世守,各有专门之业而不敢失,这是为使守官者精勤职业所定的制度,有利于知识技术的积累传承。《荀子·荣辱》:“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侍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这里同样谈到世守专门之业。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之数,此乃官人百吏居官守职的治法细目,是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百家之学所从出的官守内容的具体概括,包括治事所需的各方面知识技术、法规文书等。《管子·君臣》在论及官民行事关系时云:“有符节、印玺、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按:“符节、印玺”乃居官凭信,“典法、策籍”则除行政法令文书外,亦应包括与专门官守相关的知识技术、方法规程等,此同为百家之学所从出的渊源。《汉书·艺文志》论百家之学的渊源,俱归于王官某守之说,乃探索古代学术文化起源时极有参考价值的观点。百家之学出于王官之守的文化背景,乃是知识技术集中掌握于国家的“学在官府”、“工商食官”的早期社会状况所决定,此导致章学诚所谓官守学业合一的状态。《周官》篇首说到周王建国应该做的几件事,其中之一乃“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可见,“设官分职”在国家治化管理上极为重要,故在探索学术文化起源的层面尤具特殊意义。由官守职掌探索中国古代学术的起源,深合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实情。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重实践的致用精神为指导,此精神主导贯穿于古代文化的全部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在创造和发展物质文明的活动中,同时塑造和展现了自己的社会精神文明,形成重实践致用精神主导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此由官守职掌诠释学术文化的起源,乃是从物质活动实践入手,探索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而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乃是作为社会精神文明演进的文化承载基础。
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足以代表民族最高的精神思维原则或基本的精神思维原理,它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引导并决定着社会历史文化的性质及运作方向。在中国古代,可举“易道”或曰“易理”的概念说明之。如前文所述,经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孔子作《易传》的过程,易道或曰易理体系最终形成,它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中华民族古代最高的思维原则,在精神思维领域留下多方面的、深入的影响。古今多以《易》、《老》并称,二者均在古代精神思维领域留下了深刻影响,但二者的思想互有不同。相比之下,《易》的影响更大一些。如果说老子崇尚虚无,《易》则“言有不言无”[1](P239),《易》是关于世界存在变化的理性思考。关于易道或曰易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旨:其一,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皆以道为枢机根本,谓之存在的道本论。《说卦传》谓《易》兼天地人三才之道而两之,故六画成卦,六位成章;模拟三才之道是易卦体系的基本思想原理。其二,天地万物存在的具体形态是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谓之存在的辩证统一论。其三,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一个生生不已、变动不居的往复循环过程,谓之存在的生生变易论。此三者乃中国古代哲学认识宇宙和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基本精神及思维原理,即所谓易道或曰易理。此精神思维原理最终可归为一点,即人应法天而动。郭店楚简《语丛一》曰:“《易》所以会天地人道也”。《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言:“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易道或曰易理的大义要旨在于合会天道人道,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亦即法天行事,假天立道,以天成人,此乃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点。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对其效用有较详的阐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于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此乃极言圣人秉“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道大法,在政教治化上所能获得的理想效果。易道或曰易理作为中华民族古代的最高精神思维原则的意义,在于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所具有的主导影响,引领和决定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独特发展路径,塑造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体系和并世无双的品格形态。
由于学术文化本身的特殊意义,易于导致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此外,也与士在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角色和地位密切相关。至少从周代开始就极为重视学校教育,且形成“以诗书礼乐造士”的文化教育传统。春秋时,管仲治齐,进一步巩固了士农工商的四民制度,有所谓“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并使士作为“讲学道艺者”居四民之首(《国语·齐语》)。后来,孔子以六艺教士,孟子倡言“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要士以道义自守,这些都突出了士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春秋战国之际,新的士阶层兴起,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士大夫阶层也成为学术文化的天然担当者与传承者。它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从学术文化层面上讲,士大夫乃古代王朝存在的社会根基,故国决不可一日无士。而士与学术文化的联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关系。学术文化的发达,是因为士阶层兴旺,由此促使学术文化发达,并进而促使国家的兴旺发达。因而,历史上的兴盛时期通常又表现为学术文化的繁荣发达,新王朝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开始注重发展学术文化。但秦代为例外,即秦人为完成武力统一大业,采用极端方法使万民抟力于农战,故有焚书坑儒、打击学术文化的残酷暴行。周代留给后世的最大文化遗产,就是倡导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此传统经秦人铲削几无遗余。当新的统一帝国重新建立,必须恢复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鼓励学术文化,培植士大夫阶层。这些以汉武尊儒为标志,并开创了崇儒尊学、考试取士的制度。当然,科考文化只是士人登入仕途的捷径,国家还必须塑造可以保证其长久存在的学术文化体系,而其担当者与传承者仍然为士。总之,重视学术文化乃是维护王朝必须采取的举措,重视学术史的研究亦成为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实,学术史研究相当于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对士大夫及王朝进行思想统治模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曾提出士为中国文化仆隶之说,以寓士竭诚尽虑为中国文化效力用命之意。可以说,士既为中国文化而生,亦为中国文化而用,终为中国文化而死,死生以之。中国文化自造就士为其仆隶始,就有了为其传承繁盛而效力用命的社会知识群体[2](P1—2)。实际上,士一直以维护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为其历史使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士大夫以学术文化为职志建立自己的学统与道统。学统与道统之重要,在于它既与政统鼎立并峙,同时又作为政统得以建立的社会文化根据及相应的约束制衡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愈益彰显出士的历史使命之重要。可以说,学术史研究关乎对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概括总结,还相当于对士的社会文化使命审视性回顾总结,最终可归结为对社会与国家机制从文化角度的解读及维护,其重要性由此可知。这样,对学术史的研究也成为士大夫学者的一种学术自觉。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这种现象,即在政治文化缺乏旺盛生机之时,学术文化却相对繁荣。如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都发生在政治实力相对侵削之时,生活于此时的士大夫努力以学术文化的生气补益政治的萎靡,试图以文化生机催发社会活力。为此,这时所表现出的士文化意识的自觉,尤应予以肯定。综而言之,正由于士大夫对学术文化的自觉担当,才使学术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孔子修定“六经”对学术史研究的开启意义
讲儒学起源必溯及周公,如《荀子·儒效》称周公、孔子俱为“大儒”,实则孔子乃承周公之道,故《淮南子·要略》云:孔子“述周公之训”,《扬子法言·学行》曰:“孔子,习周公者也。”以此之故,杨倞《荀子序》谓:“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即周公创之于前,孔子述之于后。周公在《尚书·周诰》之中反复言以夏商为鉴,后孔子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即承周公而来,此“文”有重视文献之意,孔门四教即有“文”。孔子承于周公者主要是文献有征的精神,《论语·八佾》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是言夏商之礼必须文献足征方可。墨子则受儒者之业,熟于诗书经典。《墨子·非命中》谓“言有三法”,“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此“征以先王之书”,即受自孔子征诸文献之义。《礼记·中庸》有谓“无征不信”,“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以《中庸》原文与墨子“言有三法”相比,二者语义行文略相似,因为二者俱受孔子“足征”说影响。儒家注重文献有征,是因为其中包括后世应遵行的先圣王之言。如荀子认为学问之大在于圣王遗言,所谓“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然先王遗言以“六经”为代表,故谓:“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即“六经”所载乃先圣王之遗言余教,故为文本知识的终极汇粹,天地之理毕备。“六经”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汇粹,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载先王之道可用于垂教后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即孔子述“六经”,是后世推行王道正法,据以教化天下的表仪统纪,故孔子一生的最大贡献乃在于删述“六经”遗教后世,“六经”也成为评价孔子学术地位的重要依据。关于修“六经”,汉代记载中有下列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追修经术,以达王道”;《盐铁论·相刺》云“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论衡·问孔》云“还定经书”;《白虎通义》卷九《五经》云“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所谓“追修”、“追定”,“追”有二义:一谓追迹先王;二与“退”、“还”义近,指孔子周游列国而无所得,乃决意归鲁,为追补前失,乃以修“六经”正之。孔子本意在于直接参与政治,实现其改变现实的目的。但现实的失败,遂使其寄望于将来,决意归鲁,专以修“六经”垂教后世为务,此即所谓“退修”、“还定”,故孔子归鲁修“六经”代表了他一生的志意成功所在。但从“追修”、“追定”、“退修”、“还定”诸说透露出的信息,都是孔子在“六经”文献上的“修”、“定”整理功夫。所以,如上述汉代记载中的这些说法,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就是“修定”,其中包括孔子所作文献上的编次、整理及论定功夫。孔子讲前代历史注重文献有征,这是导致孔子修“六经”的潜在原因。但为垂教后世的需要,孔子必以己意作出整理修定。从表面看,这相当于文献学的性质,但实际上修定“六经”又相当于对古代学术思想文化的研究总结,但其总结结合了文献学方法,将学术史研究与文献整理结合起来。汉代刘向父子校雠整理群书即由承此传统而来,故他们在学术史研究上亦有相当高的地位。
司马迁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论述值得关注。首先,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继承《春秋》修史之意,并揭明孔子修“六经”“以史传道”之意,表明自己继《春秋》作史,亦为倡明王道,因而也用“六经”作为构造上古三代史的史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六经”的各自大旨:“《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从中揭示了“六经”的各自特点,以及在内容次序构造了上古历史,如《自序》言继孔子修史应“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此言以“六经”为史料,且把它与百家传记在史料的意义上等同起来,即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孔子修“六经”是为了“以史传道”,那么,他修定“六经”,相当于从史学角度对经书材料的考订整理,编次诠释,孔子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开启者。为此,他修定“六经”的方法和过程值得研究探讨,以证明孔子是如何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开启者的。
司马迁熟谙“六经”,对孔子修定“六经”亦多所记述,因而可据其所述,考证孔子修定“六经”的方法过程。《史记·儒林列传》载,“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按:“论次”,即论定序次,乃修《诗》、《书》的方法;“修起”,指修旧起废,乃修《礼》、《乐》的方法;“自卫返鲁”,乃孔子周游列国返鲁之年,为修定“六经”之时。《史记·孔子世家》叙述稍详:“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按:“序《书传》”,“序”非指作《书序》,主要应指序次篇目,即“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起《尧典》、终《秦誓》之篇目次序;《书传》应指孔子曾为《书》作训解,下“《书传》自孔氏”可证,今传《尚书大传》中多有孔子说《书》之言。“《礼记》自孔氏”,按:“礼记”乃对礼的说解。儒家对“经”的说解,一般称“传”、“说”、“记”。其中,“记”似对礼、乐的专门说解,如《礼记》、《乐记》。对礼的说解,应起自孔子,后为七十子所承。《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有《记》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继言《诗》乃由删削而成即所谓“去其重”。《十二诸侯年表序》述《春秋》之作亦有言“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取可施于礼义”,应为删《诗》标准。“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乃言《诗》之内容起讫,此与所谓正风、正雅有关;下言“至幽厉之缺”则为变风、变雅之起。所谓《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始,亦与《诗》之篇目次序有关[3](P139)。《诗》用于祭祀、宴飨,与礼乐相关;其作为乐歌,与乐关系尤密,故有此“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继言孔子定《易》,诸《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皆乃孔子所作《易传》,与上言之《书传》、《礼记》同为说解之类。总结以上对《孔子世家》记载的分析,孔子修定“六经”至少做了以下工作,即去除复重、删选内容、序次篇目及撰作说解等方面的整理。
传出孔安国的《尚书序》,述及孔子修“六经”时有一较全面的说法,“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颖达的疏解,对认识孔子修“六经”方法颇有参考意义。他提出,“修而不改曰定,就而减削曰删,准依其事曰约,因而佐成曰赞,显而明之曰述”。又曰:“芟夷者,据全代、全篇似草随次皆芟,使平夷……翦截者,就代、就篇辞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为翦截也。举其宏纲即上芟夷烦乱也,撮其机要即上翦截浮辞也。且宏纲云举,是据篇、代大者言之,机要云撮,为就篇、代之内而撮出之耳。”[4](P114)孔安国用“定”、“删”乃至“芟夷”、“翦截”诸概念说孔子修定“六经”之法,其法是否如孔颖达所言那样详悉细密,已难考实确知,不过代表了古人对孔子修定“六经”方法细密繁复的一种看法,认为孔子是认真并花费相当功夫的。《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春秋》“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三代世表》也说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按:“录”者传录、抄录或校录之谓,皆乃文献整理所用到的方法功夫。《国语·鲁语下》记孔子先人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此应为篇目校录,由此可以联想到孔子修定“六经”时涉及的诸种整理方法。汉代刘向父子校理群书时,用到校雠讹误,去除复重,编定篇目及定著缮写诸事,为此并撰有“叙录”、“书录”、“目录”等,推定其端绪皆应发自孔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孔子修定“六经”时谓“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按:此即《儒林列传》之“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主要涉及内容文字上的修定,“作《春秋》”则迥异于此。首先,“作《春秋》”当然也涉及对所据原作内容文字上的修定,《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为《春秋》之教可以概括之。此外,更主要应是意义寄托。《春秋》异于诸经修定而独称“作”,就因为它寓有孔子自家的思想创意。如《春秋》最大的意义被归结为“拨乱世反之正”,以此为根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申说孔子作《春秋》之义,大要有三:其一,以王道为是非标准,借《春秋》批判当世,所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二,申明君臣父子大伦,以为天下立本,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其三,褒扬三代德治,为后世作则,所谓“《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又借壶遂之口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此乃本董仲舒所谓《春秋》乃孔子素王事业所在而倡明之[4]。司马迁所论表明,《春秋》乃孔子政治理想最集中且最有代表性的表达,是故称之为“作”,从而使《春秋》之作有异于其余诸经之修定。孔子作《春秋》需要相关文献史料的借鉴参证,即所谓“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为此,孔子大费周折,如观书周室及求史记等事皆足证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谓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劝孔子因于“周之征藏史”老聃;《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故孔子问礼于老子时,有可能看到周室藏书。相关记载如《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5](P1705),是将如周观书与修《春秋》联系起来。有记载将观书周室说成求史记,即孔子受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5](P2195)。孔子修《春秋》确参考过史记,《史记·陈杞世家》、《晋世家》俱谓“孔子读史记”,《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俱谓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孔子为求史记必须至周,《史记·周本纪》有谓周幽王时,“周太史伯阳读史记”,《六国年表》则谓“史记独藏周室”,因此为求史记,孔子必须至周,那么,如周观书与求史记当是一事,俱应与孔子作《春秋》相关。综合上述记载,孔子作《春秋》,曾为求得相关的参考史籍,必费一番周折功夫。《春秋》的表现形式也颇费孔子思量。前曾言孔子作《春秋》是为批判当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因而在思想表达方式上,孔子煞费周章,终不得不采用隐微曲折的方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故导致“其辞微而指博”(《史记·儒林列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史记·匈奴列传》),《荀子·劝学》则径谓之“《春秋》之微”。总之,孔子作《春秋》在表达方式上较其他诸经多费心思功夫,这与孔子在《春秋》中寄托的精微深邃之义有关。
孔子作《春秋》之说,发于孟子而大倡于司马迁,但却与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的主张有异。这是为何?按: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是因自不欲以圣人自居。古代有“作者曰圣”的观念,如《考工记》论及百工制器之事时,有谓“圣人之作”、“圣人之所作”,“作”成为圣人的专利性标志,作者犹发明创作之义。如《墨子·非儒下》言“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在《荀子·解蔽》及《吕氏春秋》之《君守》、《勿躬》等中皆有此类“某作某物”的记载,《世本·作》是此类记载的集中表述,即谓有创物利民之作者皆可谓之圣人,由此形成“作者曰圣,述者曰明”(《文心雕龙·征圣》)的观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道孔子“作《春秋》”,对自己的《史记》则不敢称“作”,仅以“述”自居。故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实表现了不以“作”自居圣人的谦谦之德;另一方面,孔子“述而不作”也与他在谈到三代文化间的因革损益关系时,重“因”而不重“革”的一贯态度相符。至作《春秋》则不然,《春秋》乃孔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寄托,亦为其垂教后世的根蒂所在。如孟子比孔子作《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司马迁则比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二人对《春秋》推重有如此之高,那么用“作《春秋》”的称道使之独出诸经修定之上,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
通过以上考释,可知“作《春秋》”之说乃出于后来者对孔子的推重,主要以孟子、司马迁二人为代表。按照其说,孔子对“六经”的修定,以作《春秋》为标志性成果。因为它远远超越一般章句文字、篇目内容方面的基础性编次整理,而上升到更高的思想义理层次的寄托追求,而这是学术史研究中的关目枢纽,孟子、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所突出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如若正确评价孔子修定“六经”的意义,务必集中关注孔子作《春秋》一事,从而才会深入揭示孔子在道术研究层面的贡献,也就是真正全面理解和分析孔子在中国古代早期学术史研究上的开启性意义。最后,还应指出的是,孔子修定“六经”,结合文献整理方法开创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端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继承此传统,将学术史研究在形式上与校雠目录学结合了起来。
[收稿日期]2013-07-23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伏羲八卦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道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