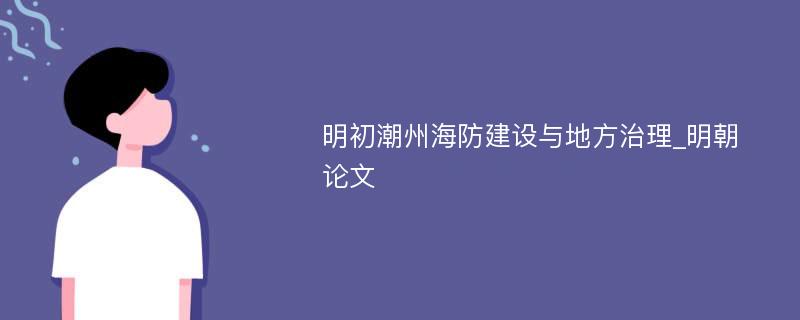
明代前期潮州的海防建置与地方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州论文,海防论文,明代论文,建置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26-08
明代的海防与海禁,是两个相为表里的研究课题,前辈时贤已有众多的成果。在研究明朝海防、海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的时候,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它置于国际关系与海外贸易的视野之中,认为明王朝加强海防力量、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一是为了防御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二是为了对付流入海中的朱氏宿敌残部,三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影响①。由于这些研究大多视野广阔,海防又被定义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在沿海布置的防务,防御倭寇入侵被强调为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海防既为保卫国家安全而设,国家安全所面对的潜在威胁,即可能来自内外两面。而海禁实施的直接对象,更是濒海之民。因此,过分强调海防、海禁政策与防倭的联系,不免掩盖更为复杂的历史面相。本文希望通过对潮州文献的深入解读,对明王朝的海防政策如何在地方实施的过程作更加仔细的研究,来纠正宏观研究可能造成的偏颇。
一、畲疍与南宋潮州的兵防
明代的潮州,在莅任的官师们眼中,是一个“难治之区”,充斥着海盗和山贼的祸乱。明代前期的海防建设,和明代中期众多新县的置立,都与这山海之间的动乱很有关系。而从潮州的历史看,这些海盗和山贼又与宋元时期活动于潮州的畲疍民又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宋元之交,潮州的畲疍民才引起国家政权和官师们的注意,并进入文献记载中。对潮州畲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文天祥的《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中说:
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②
刘克庄《漳州谕畲记》对这个畲人社群有具体的观察和描述:他们采用跟定居农业不同的“刀耕火耘”的生产方式,在山林中烧荒垦种,一两年后,土地肥力下降,他们又会转移到另外的地点垦殖。由于以游耕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不断迁徙,居所无定,自古以来,这个社群从不受国家政权的管辖,不纳赋税,不服徭役③。
对疍民,宋元时期本地文献中没有直接的描写。照刘克庄的说法,蛮(苗)、徭、黎、疍、畲,似乎是不同的地方对杂处溪峒的化外之民的称呼。活动于漳潮一带的这类社群,当时被称为“畲”。漳潮山海之间,一直是他们生存的场所。如果要把这类族群细加区分,可以把山居而主要从事迁移式农业的群体,称做畲人,把水居而以捕鱼或者航运为生的群体,称做疍民。从国家的角度看,畲人和疍民在文化上有着很相同的一些特点,诸如漂流不定,去住无常,难以驾驭等等,因此,也不妨把他们混称为“畲”。举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宋元之交,对潮州政局影响甚大的陈五虎陈懿兄弟,及其率领人数总多的畲兵,被文献指认为“海盗”,他们拥有多艘海船④,根据地又地处海畔⑤,说他们是疍民,从文化面貌看,实际上也应该非常合适。
总之,在宋代,潮州的山区海畔,生活着数目不小的畲疍民。他们利用本地尚算得上丰富的自然资源生存,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不受国家权力的统制。
同样,从宋代开始,潮汕平原的开发进程加速,定居农业成潮州地区的主流文化形态。在这里定居的农民成为国家赖以征取赋役的良民,平原地区逐步变成国家可控制的中心地。
南宋政权在潮州实际可控制的地域并没有我们所想象那么大。旧志说:“军国养兵以卫民”。又说:“军之衣食既出于民,民之防卫必赖于军”⑥。从当时兵防情况,也许足以分析出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控制程度。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营寨”记载,南宋潮州驻军兵制,分禁兵、厢兵、铺兵、土兵四种。禁兵总名“澄海”,分成4营,共有1600人。厢兵有“清化”、“牢城”、“作院”、“城面”4指挥,分3营,共有384人。禁兵和厢兵都驻扎在潮州城。铺兵分散在驿递道路的各个站点,统共153人。土兵有“潮梅”、“同巡”2巡检司,各100人,驻扎在州城内;又有“小江场巡检寨”,在州城东方50里外,大约在今天韩江北溪口的东陇狮山附近,驻军100名;“赤砂巡检寨”,在潮阳县东南10里外,驻军也是100名;“鼓楼冈巡检寨”在揭阳县旁,驻军120人。
另外,绍兴二年(1132)黎盛之乱平定以后,粤东山区叛乱蜂起,朝廷调用大兵镇压。平乱之后,留统制韩京一支军队驻守循州,在相邻各州都分派精兵守卫,名号为“摧锋军”。潮州的摧锋军营在州城北郭,驻军因为听从国家统一调用,常驻人数变化不定。
乾道三年(1168),有海盗作乱,知州傅自修派人招抚,并请示朝廷,创立水军寨以安置降卒,共有军额200名,驻揭阳城西边的宁福寺旁。嘉定十五年(1222)水军寨外移到桑浦山前海口的鮀浦场。
淳祐二年至四年(1242~1244),再有“黄冈寨”的设置。本来,闽粤赣三省边区动乱,冲击潮州北境,饶源、湖潦等处居民被害,知州奏请朝廷在该处建寨屯兵防卫。结果,却按朝廷的旨意,审度形势,把寨子移建在黄冈河口紧靠着驿道的地方。这个寨子有100个兵员的名额,新招50名,其余50名派鮀浦寨水兵轮流驻扎。
南宋时期,国家政权把潮州兵防的力量,安置在州城和潮阳、揭阳两个县城和驿道上。“小江场巡检寨”和“赤砂巡检寨”的设立,是为了这两个地方盐场的防卫。那时候,盐业生产对地方经济和税收影响力很大。“水军寨”外移鮀浦场,“黄冈寨”的设置,用意恐怕也在盐场的防卫。城市和道路系统连结着三江平原和海边盐场,这就是南宋潮州政权所能够控制的中心地。
山地、海域和盐场之外漫长的岸线——特别是水深潮大,不利于产盐而方便船舶往来、停泊的港口,成为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域。畲疍们十分自在地在这个边缘地域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宋元之交,这股几乎与国家政权互不相干的社会力量,也被搅进该改朝换代的政治漩涡里面。文献记载向我们展示,这一时期有数目相当多的畲疍人在潮州活动,并且左右着易代之际本地的政局⑦。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表现出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得不使有国者侧目。
二、明初潮州的海防建置
明王朝一建立,国家政权显然注意到对边缘地域控制的重要性。在传檄平定广东之后,马上广置卫所,驻兵防守。在潮州,有潮州卫和海门、蓬州、程乡、大城、靖海等守御千户所的建置⑧。卫所兵员的来源,除元朝降明军队外,还通过垛集民兵补充。明陈天资《东里志》上,就有官府把南澳岛居民徙入潮阳海门所充军的记载⑨。同时,潮州各县,又有巡检司的设置⑩。在明初,巡检司的主要职能是地方警戒,即所谓“主缉捕盗贼,盘诘奸伪”,都设置在关津要害处,有巡检官率领土兵守卫(11)。
除了卫所与巡检司之外,还有一个水寨,控扼着韩江北溪(秋溪)和樟林港的通道(12)。这个水寨可能就在北河口的南宋时期小江场巡检寨旧址兴建(13)。
明初潮州的防卫布置,很明显地偏重于海防。洪武间,除潮州卫设在府城,沿海设置的海门、蓬州、大城、靖海4千户所,腹地只有程乡千户所。在内地设置的巡检司,有三河、吉安、北寨和湖口4处,而沿海则有枫洋、辟望、门辟、招宁、鮀浦、黄冈、神泉等7个巡检司。其中黄冈和鮀浦两司,就建在南宋黄冈寨和水军寨的旧地。
沿海兵防,又很明显地布置在本地几道大河流的入海口和主要港湾。
洪武初年(1368),韩江北溪入海口,重建了水寨城。洪武二年(1369),韩江东溪入海口,设辟望巡检司;榕江口外西侧,设门辟巡检司。洪武三年(1370),韩江西溪入海口和黄冈河入海口,有鮀浦巡检司和黄冈巡检司重建。洪武四年(1371),在韩江西溪,枫洋巡检司从韩江平原顶部与丘陵地带连接的归仁都,迁移到平原中部已经开发的南桂都。练江入海口,原有潮阳县城控扼。洪武二十七(1394)年,龙江河河口,又设置了神泉巡检司。
在韩江西溪口,牛田洋内海通外海要扼之处夏岭村,洪武二年(1369),建了蓬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牛田洋内海通外海的另一通道濠江海峡中段,又设招宁巡检司。这两个据点的建立,目的是控制波涛浩淼的牛田洋水域。
洪武二十四年(1391),海门守御千户所在潮阳县城建立。洪武二十七年(1394),海门守御千户所从县城徙置海门。如果联系大城守御千户所和靖海千户所的新建,这显然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海门湾和柘林湾这两个潮州沿海最主要的港湾。
总之,明初潮州兵防的设置,已经不再以三江平原中心地为重心,而转向漫长的海岸线特别是主要河流的入海口和大港湾,也就是宋元时期畲疍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生活的边缘地域。
三、潮州地方志关于明代兵防兵事的记载
就现在可以读到的载籍而言,潮州地方志对明代地方兵事的记载,开始于万历十三年(1585)潮州知府郭子章撰写的《潮中杂纪》。该书卷十“国朝平寇考”的记载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第一条记载,就是倭寇的扰掠潮州:
洪武二年,倭寇惠潮诸州。时天下初定,海内乂安。倭夷窃发,滨海骚动,乃命行人杨载使日本,以玺书谕其国王。书曰: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被倭来寇山东,不过亦乘胡元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震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一十年。自去岁以来,剪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14)
这本书接下来关于沿海寇乱的记载,已经是永乐十九年(1421)的事情了:“永乐十九年春正月,倭寇靖海,副总兵李珪擒之”(15)。在这两个事件之间,明陈天资撰《东里志》还记录了另一事件:“明洪武三十一年,倭夷寇东里”。而《东里志》的下一条记载,则是宣德初年(1426)事:“明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倭夷犯上里,耆民陈彝率众击走之”(16)。
清代以后潮州各种志书的记载,基本上都承袭着上述内容。也就是说,嘉靖以后的本地方志几乎一致认为,明初潮州沿海兵防设置的加强,是为了对付外来者(即倭夷)的入侵。
然而,这一判断与史实有很大的距离。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初期日本对中国的侵扰,主要地域在山东到浙江沿海,自胶州、即墨、诸城、莱阳,到淮安、海盐、苏州、松江、明州、台州、温州各地(17)。上引《潮中杂纪》卷十关于洪武二年(1369)杨载出使日本的那一条记载,显然与潮州并无关系,只要稍用心细读,就可以明了。当然,其时潮州濒海也受到侵扰,《东里志》所记洪武三十一年(1398)事就是一例。不过,侵扰情况似乎并不严重。
那么,为什么自郭子章《潮中杂纪》开始,本地方志会把明初的海防建置与日本人的入寇联系起来?比《潮中杂纪》更早的本地方志,如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和嘉靖二十四年(1545)郭春震《潮州府志》,也有关于倭寇和备倭的记载,但是,这些方志里的“倭”,并不专指日本人(18)。事实上,嘉靖二年(1523)日本争贡之乱发生后,市舶司制度被废除(19)。原来自浙江市舶司入贡的日本人,乃“之南澳互市”(20)。因为此前明王朝已经弃守南澳,把居民迁入内地,南澳反成为民间贸易的便利场所(21)。一开始,主客双方在买卖过程还相安无事,后来主人欺客,有点霸市的味道,如地方志所讲,潮州市集“居积最多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黠民以此昂其值于诸番,因而为患”(22),潮州倭祸渐萌。到了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浙江海上私商贸易被严厉禁逐,以南澳为中心的潮州沿海,变成祸乱的中心,当时社会上甚至有“北卤(虏)南潮”的说法(23)。海防建置成为潮州官师们施政思想和行为的重心。正是在这种祸乱的背景下,《潮中杂纪》把明初的海防建置与日本人的入寇联系起来。这一点,“国朝平寇考上”前面的小序,说得非常明白:
潮自周秦以来,其寇乱载之往牒,独国朝未备。且嘉隆之际其乱尤仇,而勘定得人,递发递灭。今往牒载者不录。独录本朝,以为倡乱者诫,讨乱者镜焉。(24)
这种引倭乱为镜诫的理念,支持着当时有关海防问题的众多写作,《潮中杂纪》并不是孤例。从写作时间推断,甚至可以说,《潮中杂纪》把洪武二年(1369)杨载出使日本的记载与潮州倭乱牵涉到一起,其实是照搬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25)。
这些地方志书为什么没有提及明初潮州沿海畲疍民对刚建立的政权可能造成的危险?理由其实比较简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大部分沿海畲疍已经为官府所控制,成为编民(26)。
总之,不能否认,明初沿海兵防的设置,有对付倭夷入侵的考虑的一方面,但是,在潮州,海防建设的目的只是为了抗击外患吗?地方志上关于蓬州守御千户所的那一则很短的文字,记录着洪武年间这个千户所的内迁。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变化,也许它能够说明初国家政权加强潮州海防建设,是为了地方的控制。
四、蓬州守御千户所内迁与夏岭之乱
天顺四年(1460),潮州纳入明王朝版图已近百年,夏岭24村发生了叛乱。这是明代前期发生的,对潮州社会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在地方志书和本地文人文集中,留下不少记载。黄佐《(嘉靖)广东通志》的记事最为详细曲折,也最有故事性:
天顺三年,海寇黄于一、林乌铁、魏崇辉胁逼夏岭等24村作乱,经潮州知府周宣前后两次的抚剿兼施,终于平定。第一次进剿,周宣先用惩戒手段,“亲督兵,据险扎营凡七所,与贼相距四十余日,擒杀渠魁”。继以儒生进入乡村粘贴告示,并“自诣贼营抚谕”,使用规训手段。而24村民基本上也只听周宣的劝诫,动乱暂时平息。接着,周宣改调离任,24村之乱又起。当道只好再调回周宣。第二次进剿,周宣反而先用规训手段,“出榜约日招降”,使村民知有“上尊下卑”之道,接着却突然间用兵剿灭24村动乱(27)。
不过,根据另一些文献,夏岭动乱的剿灭,已经同周宣无关。李惠《平寇记》载:
是年秋,奉命征夏岭。九月既望,出师海上。时张公通奋其勇,陈公濂发其略,大参慈溪刘公炜督其粮,宪佥余姚毛公吉、都阃三湘胡公瑛统兵应之,潮阳大尹眉山陈侯暨陈侯爵统民快助之。……山攻水战,势如摧朽。破其巢穴,火其庐居,斩首数千颗。余贼奔溃,官军追碣石等澳,杀获及溺水者不计其数。(28)
当时人李龄在成化初(1465)所写的一篇文章,对夏岭之乱,有另一个角度的描述:
揭邑有沿海而村者,曰夏岭,以渔为业,出入风波岛屿之间,素不受有司约束。人健性悍,邻境恒罹其害。寻有豪猾者互争田土,诉于官,连年不决。有司动遣巡司率隶兵而拘执之,则侵扰其众,豪夺其有。民弗堪,乃相率乘舟道海 而逃。因之以岁凶,加之以水灾,遂大集无赖,攻城剽邑,肆为杀戮。海、揭二邑,受害犹甚。(29)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指示造反者的身份,二是说明动乱发生的原因。就第一点而言,李龄指出造反者濒海居住,“以渔为业”,没有提到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动乱的诱因,却由土地的争夺引起。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元时期的畲疍。如果再从黄佐文中“魁渠服色僭拟侯王”的描写看来,造反者的经济状况,已经超越从事渔业生产的收入水平。到明代中期以后,富有的商人、地主中间普遍流行的在服饰方面的僭越,已经表现在这伙造反者的领袖身上。可以推断,夏岭24村之民,在渔农之外,还进行着海上贸易与营运。这是宋元濒海畲疍重要谋生手段,但在明代却是非法的。就第二点而言,其时明王朝奄有潮州已近百年,而造反者仍然“素不受有司约束”,终于不堪官司的骚扰,揭竿而起。可见明朝的海防建置,对潮州濒海区域的控制非常无力,而夏岭之民却拥有强大的武装,且在受抚前后也没有多少改变。黄佐就说周宣在平息夏岭第一次动乱之后,“潜起从良民黄伯良等”,出其不意,大破山贼罗刘宁(30)。一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引用潮州通判范维恭的牒文,还说:“近因漳州海贼越境劫掠人财,本官召募本土鮀江都大家井惯战海夫余严八等五百名,俱以拣阅记籍在官,欲以四月初旬上班”(31)。大家井即为当年参与动乱的24村之一。只是在70年后,原来威胁着明政权的这股势力,变成了官府赖以保卫潮州海防的力量。
李惠《平寇记》里还有两段话值得讨论:
夏岭外薄洋海,黄寨内通徭獞。往往恃顽弗率,既历宋元,余风未殄,……顽民魏崇辉、许万七等仍蹈覆辙,天顺四年以来,窃据夏岭、西陇、赤窖、乌合、浮陇、华坞、大家井等村,大肆蜂螫蛇豕之毒。……
胁从者二千余,悉遵诏命抚入腹里良善乡村居住,欲其同归于善而已。贼巢自夏岭至西陇、赤窖俱革,不与居住。揭阳边患自此无虞矣。(32)
第一段话指明夏岭24村所在。夏岭、西陇、赤窖、乌合、浮陇、华坞、大家井等村的地理位置,都在韩江西溪出海口,当时揭阳县属蓬州、鳄浦、鮀江三都最濒海之处。夏岭的位置,又居诸村的最前端,所谓“外薄洋海”。乘潮而上,可抵黄寨所在的蓝田都,直入深山丛莽,所谓“内通徭獞”。把蓬州千户所建置在夏岭,显然就可以控扼韩、榕两江出海口。这大概是洪武二年(1369)官府的设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位于海岸最边缘的夏岭,处在众多濒海村落的包围中,如果这些村落尚未归顺朝廷,又拥有自己的武装,那么设置在这里的千户所本身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这就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蓬州千户所要从夏岭内迁鮀江西埕的原因。
第二段话交代了朝廷对夏岭等村落的处置。在这次动乱平息后,诏命把24村居民全部迁走。这种“徙民虚地”的做法,洪武年间在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比较广泛曾经推行过(33)。明初,闽粤边界的南澳岛民曾被徙潮阳海门所充军户(34)。夏岭24村民被“抚入腹里良善乡村居住,欲其同归于善”,也就是国家终于控制了这些居住在濒海地域、一直“恃顽弗率”的乱民。
如果洪武年间的“徙民”是为了防倭,那么,天顺间潮州濒海的“徙民”又是为了什么呢?李惠说,夏岭之民,“既历宋元,余风未殄”。又说动乱平息“揭阳边患自此无虞矣”。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在李惠的观念里,夏岭之民,还是宋元时期的畲疍;而濒海地域,依然是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疆。
总之,夏岭之乱这一事件正好提示我们,蓬州守御千户所的内迁,是由于濒临牛田洋水域的三江口沿海,有着十分强悍的官府难以控制驾驭的社会势力。从明初潮州沿海的情势看,这股势力,正是宋元以来一直活跃在此地的畲疍民。
明初实施的海防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因此,御倭和对付方、张余党,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确为最重要理由。但是,如果从潮州乃至广东全省看,倭寇和方、张余党对地方社会的威胁也许并不那么严重。此时明王朝在潮州海防建置,更加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地方社会势力。
五、余论
夏岭之乱后,潮州濒海获得近50年的安定。嘉靖末年,江南沿海倭祸复炽。在朝廷重兵围剿之下,余党南流至漳潮一带。这时,政府又一次加强潮州海防力量。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琏之乱平定。割海阳、揭阳、饶平三县沿海七都,新置澄海县,县治就设在原辟望巡检司所在地。夏岭24村这时也都归并澄海。澄海置县的理由,也是地方动乱。刘子兴说:
澄海潮郡裔邑,旧即海阳之辟望逻司。先是岛彝入寇,剽掠横骛无虚日。其山海恣睢逋荡之徒,承倭倡乱,啸聚朋凶,营垒连结于兹地,盖寇贼渊薮也。(35)
澄海首任知县周行在《澄海县建置图序》中也说:
澄海,潮之新建邑也。邑治辟望,旧隶海阳下外莆都,为辟望巡检司。……迩岁残于倭,继而遭海寇之虔刘者无宁日,民率死、徙。斯地昔称乐土者,遂一望丘墟矣。幸赖圣明,不遐遗海隅苍生,……允建全设邑治于前地,且蒙御赐邑名“澄海”,盖欲海宇澄清意也。(36)
可见,澄海由巡检司而置县,还是为了海疆的安定。上引两段文字,也强调倭寇的入侵。但当时所谓“倭寇”的构成,仍然以地方势力为主体。嘉靖二十四年(1545)潮州知府郭春震就说:
近年,倭鲜至,而闽粤人与其温绍人亡命者,率窜入海,遂肆猖獗,为滨海诸郡患。(37)
作为潮州本地士大夫,刘子兴在文章里反复提及“岛夷入寇”,本地盗匪只是“承倭倡乱”,只不过是利用了“倭祸”的公共记忆,来争抗地方官“北虏南潮”的指责罢了。实际上,此时海防建设的加强,目的仍然在地方控制,而非完全为了抵御外患。
注释:
①就作者所经眼的文献而言,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北京:《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郑克晟:《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郑州:《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汤开建:《明代潮州海防考述》,《潮学研究》第7辑,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文山全集》卷11,四部丛刊本,第1页。
③刘克庄:《漳州谕畲记》,《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四部丛刊本,第7页。
④参见《元史》卷10《世祖纪七》“至正十六年二月庚寅”,卷12《世祖纪九》“至正二十年十一月癸丑”记载。
⑤王岱:《(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陈懿”条,古瀛志乘丛编本,广东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第161页。
⑥《永乐大典》,卷5343,《营寨》。
⑦参阅黄挺、陈占山:《潮汕史》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7~247页。
⑧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2,《建置志》,古瀛志乘丛编本,第28、34、35、37、39、40页。郭志未载靖海所建置时间,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一》引吴颖:《(顺治)潮州府志》系年于洪武二十七年。
⑨陈天资:《东里志》卷1,《疆域志》“澳屿·长沙尾”条,古瀛志乘丛编本,第21页。该志卷4又载明嘉靖十七年饶平知县罗胤凯《豁虚粮》文:“窃照本县信宁都地名隆、南、青、深四澳,僻在海岛。……洪武二十四年,该广东按察司佥事耿奏为海岛事,将四澳人民,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
⑩《(嘉靖)潮州府志》第30、33、35、38、39页所载洪武年间潮州各县设置的巡检司有11处,另外,第36页所载程乡县巡检司3处,未记设置时间。
(11)张廷玉:《明史》,卷75,《职官志四》“巡检司”。
(12)(15)(22)(37)《(嘉靖)潮州府志》,第20、69、32、20页。
(13)明初小江水寨城的位置,在《永乐大典》卷5343的“潮州府图”和“海阳县图”上都很突出地标示出来。
(14)(24)郭子章:《潮中杂纪》,古瀛志乘丛编本,广东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第68页。
(16)《东里志》,古瀛志乘丛编本,第49页。
(17)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8页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
(18)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海寇》引《增减夫船新议》一文,转录潮州通判范维恭牒,提及倭寇和备倭,但文中倭寇与海贼并无分别。且此书卷35《外夷》所列举,皆东南亚诸国,未提及日本。《(嘉靖)潮州府志》也如此,卷1《地理志》提及倭寇和备倭,具体所指也是“暹罗诸倭及海寇”。
(19)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1~169页。
(20)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一》,明嘉靖二年“倭之南澳互市”条,广东汕头:潮州修志馆,1948年,第25页。
(21)马楚坚:《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于明代海防线上转变为走私寇攘跳板之发展》,收入杜经国:《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广东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137页。
(23)郭子章《诸有司教四条》说:“潮阳昔常韩二公过化之乡,称文献区。嘉靖中赤子弄兵,四郊多垒。今议者论国大势,辄曰北卤南潮。夫埒潮于卤,此亦地方之厚辱也。”见《潮中杂纪》,古瀛志乘丛编本,第35页。该本虽名影印,实有修补,此段文字中“国”字原残,修补为“固”字,误。
(25)参见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2,《王官使倭事略》;卷3,《广东倭变纪》。
(26)关于明代广东疍民编户,可参阅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的论述,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页。虽然此文并未讲到潮州,但从当时人把“广之番禺、南海、东莞、新会,及潮之三阳濒海数邑”(见《广东通志初稿》卷23《田赋》)相提并论的情况看,潮州濒海疍民,也经历过同样的编户过程。下文将提及的夏岭二十四村抚民的安顿,就是编户的例证。而《(嘉靖)潮州府志》、《(隆庆)潮阳县志》上也有河泊所和疍民户口、税课的记录。
(27)(30)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誊印本,第1727页。周宣,其他志书或作周瑄。天顺三年,其他志书多作四年。比较详细记录这一事件的,还有李惠的《平寇记》,该文记述重点与黄佐略异。李惠,海阳人,景泰进士,仕松江知府。
(28)李惠:《平寇记》,《(雍正)揭阳县志》卷7。古瀛志乘丛编本,广东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第319页。“是年”,按上下文,为天顺六年;本地志书多将此役系年于天顺七年。
(29)李龄:《赠郡守陈侯荣擢序》,收入冯奉初:《潮州耆旧集》卷1,香港潮州商会印行,1980年。李文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东里志》,卷2,《境事志》,记事大同。
(31)《(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增减夫船新议》,誊印本,第576页。
(32)《(雍正)揭阳县志》,卷七,第319页。
(33)参考郑克晟:《明代初年的福建沿海及海防》,郑州:《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
(34)明初南澳民内徙时间,文献资料所载略异。陈天资《东里志》所引明嘉靖十七年饶平知县罗胤凯《豁虚粮》,载在洪武二十四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杜臻《闽粤巡视纪略》,载在洪武二十六年;齐翀《(乾隆)南澳县志》、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一》,载在洪武二十年。
(35)刘子兴:《儒学海壳蚶蛎场租碑记》,《(康熙)澄海县志》卷9,第76页。“逻”字当是“巡”字之误。
(36)《(康熙)澄海县志》,卷2,《建置》,第40页。
标签:明朝论文; 潮州论文; 明朝服饰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嘉靖帝论文; 历史论文; 永乐大典论文; 倭寇论文; 澄海论文; 专门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