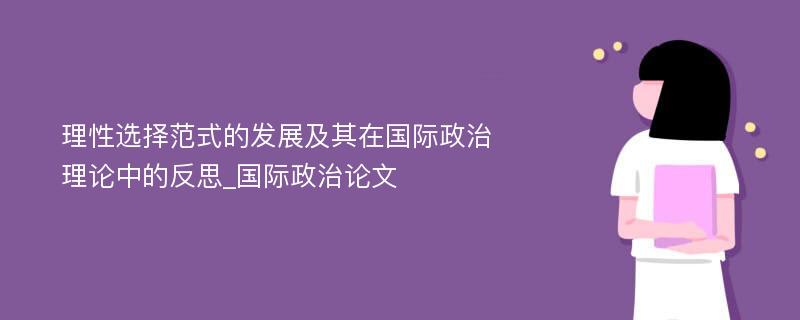
理性选择范式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反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治理论论文,理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克莱斯勒所说,当今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学派都建立在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之上”。(注:Stephen Krasner,“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 (Steve Smith,e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9.)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各流派间展开对话的学理基础无疑都是理性选择范式,因而统称为理性主义理论。理性选择范式也为反思主义的代表——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论争的可通约性提供了学术平台。所以,对理性选择范式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学术发展的探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首先考察了理性选择范式的学术发展历程,然后梳理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理性选择范式的运用,认为各学术流派之间的争论无疑是理性选择范式自身发展的进程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反映。
一、理性选择范式的学术嬗变
理性选择范式(rational choice paradigm)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假设的核心是经济人模式,即认为社会中的基本行为体是理性的,行为体的行为是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行为体具有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体现出行为体所认知的自身利益,其目标是连续的、稳定的;在既定约束之下,行为体致力于使其预期的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所做的理论抽象,这种抽象方法的实质在于有意识地突出研究对象的主要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原型加以合理的推演和外延,进而形成模型化的研究客体,然后通过对客体模型的研究,去间接地探讨其原型的规律。理性选择范式的演变是一个思想撞击的过程,它从哲学领域中得到了启蒙,在经济学领域中得以成型、发展与完善,随后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推广开来。
1.理性选择范式的哲学渊源
从认识论的层面上讲,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一直是与经验主义相对而言的。理性主义的观念发端于柏拉图,中间经过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哲学家的发展,其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理性主义的主旨是,人的感官并不能使人们完全具有理解所观察到的事物背后的机械作用的能力,因此只有借助于人类头脑中特有的逻辑推理能力,人们才能推演出现象与其背后的机械作用之间的关系。(注:Steve Smith,ed.,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1.)我们所讨论的理性选择范式中的理性则直接源于托马斯·霍布斯的思想。霍布斯在他的名著《利维坦》中指出,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是自私和利己本性的表现,人性和道德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为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利己本性是人类行为最强大的驱动力。因此,如果没有拥有权力的国家机器的控制,受原始利己动机驱使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势必会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幸好,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能够运用其理性权衡利弊,从而服从国家权力所施加的各种限制,因而就避免了无政府的状态。霍布斯对人的利己本性问题的探讨随即在伦理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论。休谟赞同霍布斯对人的本性的分析,但同时又强调善与美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试图建立关于人性的综合学说。他在《人性论》中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具有充分的远见卓识,都具有促使他奉行公平和公正的强有力的爱好,抗拒眼前的快乐和利益的诱惑,那么,政府或政治社团这类东西就永远不会存在,人类就会生活在永久和平之中。洛克在《政府论》中继承了霍布斯关于人性自利的观点,但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使人能够权衡利弊得失,为达到最大的幸福提供正确的途径。在洛克看来,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非起源于人类自身的弱点,而是因为资源的稀缺,为了消除因资源稀缺引起的争端,国家权力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则提倡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在其著作《蜜蜂寓言》里,他把自利行为看作是社会文明和经济进步的源泉,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完全是由人的本性所激发的各种行为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结果,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富足,也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得以实现。(注: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0页;第175—180页;第190—194页;第207页。)
2.理性选择范式在经济学中的成型与完善
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理性选择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模式。经济人模式的思想产生应当归功于亚当·斯密。斯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超越了人性的利己和利他之间伦理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转而论证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问题,从而把这一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创造性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or Economic Man)的思想。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而清晰地纳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对理性人的自利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富足的经济机制进行了证明。他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是政治经济学中个人的基本心理动机,也是人类生命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对于个人的自利行为与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的关系,斯密提出了与霍布斯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存在着一只无形之手,它会在“正义法律”的基础上,化解理性行为体之间、行为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能够同时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注:参阅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册)[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斯密的思想经过边沁、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继承和发展,逐步抽象为经济人模式,成为解释各种形态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逻辑基石。
经济人模式的演变始终伴随着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促使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对经济人模式的发展影响深远。第一次比较有影响的争论是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self-interest)”与“利他(altruism)”问题的交锋。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模式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抽象的片面性。他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把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非常狭隘的,社会经济状况远比其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和丰富,自利决不是人的惟一动机。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到人的行为的复杂性,用历史、文化、法律等的综合观点去探讨问题,才能找到合适的经济学原理。对于这类责难,门格尔等反驳说,古典经济学派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理性人除了追求自身利益以外还有其他动机,但是为了理解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就必须像物理学家对真空的抽象和化学家对元素的抽象一样,分析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即人的基本行为,并把与行为最相关的动机抽象出来进行研究。(注: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0页;第175—180页;第190—194页;第207页。)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模式是在古典经济人模式的基础上对人的经济行为逻辑的第二次抽象,以杰文斯(Jevons)、瓦尔拉斯(Wairas)、门格尔(Menger)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对经济人模式作了近似苛刻的限定,将经济人假设严格公式化、模式化,以致于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西蒙(Herbert A Simon)为首的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模式进行尖锐地批评,并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并因此项理论创新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指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人模式转化为一整套完全理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行为体被抽象为全知全能的形象。但事实上人的理性行为是有限的,它要受到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客观限制,还要受不完全信息和行动后果不确定性的限制,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根本无法求得最优策略。而且,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坚持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是以“满意的收益”作为其追求的标准。赖本斯坦因(Harvey Leibenstein)也认为,只有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人们才会采取极大化行为,而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决策,同时也依赖于惯例规范等方面。因而个人的行为努力并不是一个常量,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注: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0页;第175—180页;第190—194页;第207页。)正是在这种挑战与回应之中,信奉经济人模式的经济学家们不断反思与修正,使经济人模式日臻完善。
3.理性选择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
理性选择范式在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但并不处于主导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起,微观经济学开始大举“入侵”其它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主要武器就是以经济人模式为核心的理性选择范式。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各种批判意见纷纷组织起来,从多个层面对理性选择范式展开挑战。为了回应批评者的挑战,经济学家一方面放弃了经济人模式中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的假设限定,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批评者的部分观点,引入了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以及制度等新概念,并且对原先的经济人模式给予广义的解释,最终导致经济人的第三次抽象——广义经济人模式的产生,增强了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以布坎南(Buchanan)为首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析,贝克尔(Becker)等经济学家对“偏好问题(The question of Preference)”的关注,诺斯(North)等经济学家对制度变迁与产权的研究,把理性个体的成本收益核算引入了非经济行为,把理性选择范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非经济领域之中。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永远不会结束,理性选择范式的嬗变是一个充满挑战与论争的过程,随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向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不断渗透,这些论争必然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际政治学者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来研究国际问题了,但这种范式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流研究方法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60年代末,行为主义日渐式微,国际政治学者试图建构一种能从阐明的前提中推导出明确无疑的论断模式,而理性选择范式则由于其分析框架较为严谨简约且有相当的洞察力,逐渐取代了行为主义的地位。(注:詹姆斯·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与此同时,理性选择范式自身的争论以及相关话题也随之成为国际政治各流派争论的焦点;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理论的各个流派还主动吸纳经济学的最新思潮,从理性选择范式的嬗变中寻求理论发展的动力。
二、理性选择范式在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应用及其论争
现实主义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马基雅弗里、霍布斯等人的学说。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展开论战。随着30、40年代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破产,现实主义开始占上风。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现实主义更是如日中天。也正是由于现实主义在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地位,所以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挑战。
现实主义大师卡尔(E·H·Carr)、摩根索(Morgenthau)、赫兹(John Herz)、基辛格(Kissinger)等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无不深受哲学家对人类本性探讨的启发,试图揭示出国家的政治建构中所凸显出的永恒人类本性。受霍布斯学说的影响,现实主义者都把国家视为无政府状态下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宽泛地讲,整个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逻辑基础就建立在理性假设之上,即使是摩根索这样的强调保持政治领域独立性的现实主义大师,也有意从微观经济学中借用了效用最大化的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注:Barry Buzan,“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in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Steve Smith,e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7.)在他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摩根索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提供关于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他认为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政治行为的出发点是用权力界定的利益,利益是指导、判断政治行为惟一的永恒标准。通过政治现实中的谨慎之德才可以建立理性的外交政策,从而能够使国家面临的危险降到最低,使利益增至最大。(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第3—4页;第3页。)
与现实主义研究相伴而行的战略研究也是最早运用理性选择范式的领域。战略分析家们从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的假设出发,运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对国家之间的核威慑问题、裁军与军备控制、危机决策与讨价还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为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名著《冲突的战略》、《武器及其影响》、《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拉帕波特(Anatol Rapoport)的著作《战斗、竞争与辩论》、《博弈论——一种解决冲突的理论》以及后来斯沃兹曼(Arid Schwmtsman)的著作《“小鸡”博弈:美国40年的核政策》等都是运用理性选择范式的成功典范。
现实主义中理性选择范式的应用相当有说服力,但是现实主义从霍布斯的哲学出发,将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与冲突问题界定在人类本性善恶的道德层面,从1930—50年代,对于人类本性的利己与利他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冲突与合作问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理想主义认为,源于普遍正确的抽象原则的理性和道德的政治秩序可以实现。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和无限可塑的,社会秩序不符合理性标准的原因在于缺乏理解和知识。现实主义则认为,尽管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不完善的,但它却是人性中固有的力量的结果。(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第3—4页;第3页。)世界本质上是利益对抗和利益冲突的,道德原则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实主义被其批评者视为一种试图使国际体系的等级结构与冲突关系合法化的理论。
1950—7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发展,各理论流派对现实主义展开了新一轮攻击,论争的焦点直指现实主义中理性选择的核心假设。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等功能主义者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出发,强调人们可以把对国家的忠诚转移到国际合作的事业上来,从而取代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哈斯(Ernst Haas)的新功能主义同样着眼于各集团对于自身利益的价值维护,但同时又强调一体化进程中的外溢(spillover)效应。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国际政治》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概念,直接挑战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以马丁·怀特(Martin Wright)和汉迪·布尔(Hedley Bull)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也提出了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概念,对人的自利本性导致社会冲突的存在具有必然性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尽管所有的批评使传统现实主义面临着发展创新的压力,但理性选择范式的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争议,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理性选择范式基础上的论争
沃尔兹(Waltz)、吉尔平(Gilpin)以及格瑞克(Grieco)等人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信条,同时摆脱了霍布斯式的人性层面上的争论,抛开国家单纯以权力为目的假设;不仅如此,新现实主义还运用了科学的概念,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修正。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通过系统层次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并因此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在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框架时,沃尔兹借鉴了微观经济学的方法论,把国家设定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如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公司一样;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好比是市场结构。这样,沃尔兹将整个权力政治建立在经济人模式之上,并以此为基点把国家之间的行为模型化。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理论。他从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国际体系中霸权和国际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国际冲突的频率与霸权国家的相对国力之间存在着逆相关的关系。克莱斯勒(Krasner)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机制》中指出,大多数学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采用修正式的结构现实主义方法,即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时从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来考察国际机制存在的原因,以及国际机制与权力、利益、价值观等基本因素的关系,强调国际机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仍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注: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21.)
合作理论是新自由主义中最重要的流派,主要用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具体地讲,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等理性行为体的自利本性往往会导致囚徒困境,无法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结局,从而也无法有效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合作理论的研究主要针对上述问题。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探讨了国际政治经济中存在着共同利益时国际合作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市场的失灵,而国际间的制度安排却能够通过提供信息,建立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有许多共通之处:双方都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最主要的行为体是主权国家,其它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相对来讲是次要的;国家是具有计算和权衡能力的单一理性行为体;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各国共同接受的政治权威,因此,国家采取自助的政策,自行决定其对外政策,尽管其选择受到国际体系的约束和限制。尽管双方的理论基础相通,但两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整个1990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论战的主要内容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合作问题。
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出发,双方都同意国际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就其可能的程度产生了分歧。格瑞克认为从现实主义出发,国际合作既难建立,更难维持,并且有赖于国家的权力;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可以消除交易成本等问题,有效地促进国际合作。(注: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mtemporary debat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5.)可以看出,论争的双方从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中汲取营养。所谓合作问题,在公共选择中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一般认为,由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理性的结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存在着外部性问题、信息费用和交易成本等因素,个体的自利行为往往会产生囚徒困境,导致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无法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这就是奥尔森(Olson)所说,个体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自利行为是行为体的本性,无视国家自利本性的国际社会结构只会扩大分歧、冲突和分裂。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目标就在于,在承认理性行为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如何能使国际行为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变得有序化,以使其个体效用函数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另外,论争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一个隐含条件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格瑞克认为新自由主义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从生存动机出发而采取的行动的重要性,而他认为这恰恰是无政府的必然结果,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绝对不能漠视相对收益。李普森(Lipson)则认为尽管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新现实主义夸大了它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国际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从而过分追求相对收益。(注:Ibid,pp.5—6.)客观上讲,新现实主义的担心并非多余,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市场领域中的行为体追求绝对收益,众多公司建立的同时伴随着无数企业的破产倒闭,但国家如果忽视了相对收益,将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不仅是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争的核心问题来看,双方对于理性选择范式的运用,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利与利他问题的道德层面,开始侧重于借鉴现代经济学中关注的公共选择、产权以及制度等前沿理论对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关注研究。
四、理性选择范式在建构主义中的应用及其争论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理论经过各流派之间艰苦卓绝的论争之后,呈现出向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90年代以来,理性主义阵营的新制度主义与反思主义阵营的建构主义开始相互融合,朝主流的理论方向逐渐迈进。(注:Ole Wa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Steve Smith,e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9.)
建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理性主义的理性选择范式,同时又把理性选择的研究起点作为自己质疑的对象,试图超越理性选择范式。但是我们经过分析就会发现,理性主义和建构方主义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关注不同问题,甚至可以说,建构主义尤其是弱式的建构主义可以包容在理性主义之中。所以连温特(Wendt)本人也承认,认为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性选择范式之上的共通的学理基础,才使得建构主义与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也正是建构主义实现沟通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理论的成功之所在。
首先,从认识论上讲,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并没有冲突,建构主义假设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不能被还原成各个部分;国家是真实的行为体,我们可以把意愿、信念、意图等人的性质合情合理地赋予国家;国家具有内在的动机即国家利益使国家模式具有“生命”;国家无疑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与国家的身份有关;尽管国家利益有其客观因素,但对这种客观利益的认识同时又建构了驱动行为的主观利益。(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53页,第145—150页。)建构主义的理论假设与理性主义的理性选择范式不无相同之处。
其次,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在本体论上的分歧也并不严重。建构主义认为,双方虽然都认可意愿是国家采取某种行动的原因这一假设,但对于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究竟是内生于国家体系的还是外生于国家体系存在争论。理性主义侧重于环境中的激励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所以假定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互动之前就已经具有的既定因素;而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的意愿是由观念建构而成的,利益本身就是认知和观念,行为体的互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因此身份和利益总是处于某种进程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53页,第145—150页。)建构主义对于理性选择范式的这种批评是有失公允的,理性选择并不排斥互动的观念,只不过行为体之间在行动抉择上的相互依赖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因素。通常理性的行为体被假设为具有贝叶斯理性(Bayesian rationality),就是说能够利用条件概率的“贝叶斯公式”或称“贝叶斯法则”,根据互动过程中获得的新信息更新自己的“事前”主观概率判断。换言之,理性的行为体能够根据自身处境与自身利益做出判断,经过主观的调整和改进,通过有意识地积累实证经验和资料来调整自己的判断和策略。(注:谢予识:《纳什均衡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体偏好的建构问题也一度成为经济学争论的焦点。建构主义认为,偏好就是行为体对于如何实现自我身份需求所持有的观念,而国家的身份本身是由内在和外在的体系建构而成的,身份根源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认识这两者之间的一致,因此偏好就是不断建构而成的。在理性选择范式中,经济人模式假设个人具有“偏好秩序(orders of preference)”,能够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物品,按一定秩序做出安排,偏好具有完备性、传递性和决定性等特点,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保证所期望的目的得以实现。既然偏好是指个人对于客观事物按照其偏爱的程度进行的评价,那么它应该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之所以将“偏好既定”作为逻辑起点,是为了避免在模式应用的过程中产生“无休止的倒推问题”。从这一点出发,贝克尔认为根本无需假定个人偏好和需求结构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可以认为是“时间价值的改变”。换言之,行为体的偏好没有发生变化,而仅仅是满足这种偏好的方式产生了变化。(注: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0页;第175—180页;第190—194页;第207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范式为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提供了学理基础与学术平台。正是在这种学术平台之上,两大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争论才具有了一定的可通约性。
从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理性选择这种分析范式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思路,尽管它本身的引入也带来了歧义与纷争,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建构之际,国际政治理论从粗糙的形态步入了成熟的阶段。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使得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与可靠的预言都不会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以理性选择范式为分析基础的国际政治理论不仅不是完美无缺的,并且基于理性选择范式自身的争论而引起的理论分歧依然会延续下去。但是对于理论的判断,借用摩根索的话来说,关键的因素是“要看它是否赋予了如果没有它将仍然是毫无联系和无法理解的纷繁现象以条理和意义。”(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第3—4页;第3页。)我们不能确定国际政治理论中理性选择范式是否完全揭示了国家行为体的本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至少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解释框架。国际政治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诚如克莱斯勒所言,“尽管不是防治邪恶的万应良药,但至少给致力于回报社会的学者们带来了希望。”(注:Stephen Krasner,“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n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 (Steve Smith,e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