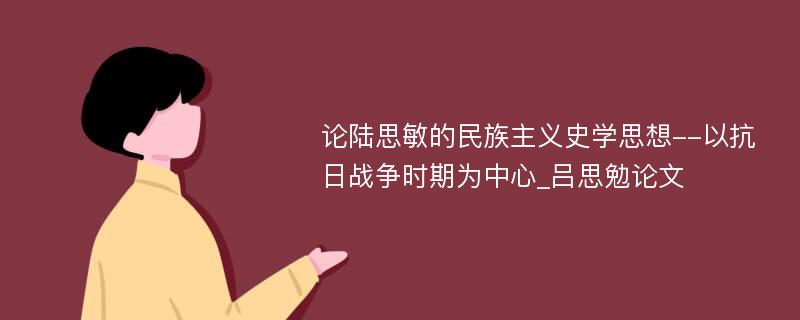
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以抗战时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6—0088—06
吕思勉(1884—195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家。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博览群书,著作等身,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吕思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不断修正和补充原有的观点,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本文以抗战时期吕思勉的史学著述为中心,略论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一、史学所以经世济时
吕思勉认为,“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者也”;“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① 历史知识的价值即在于它能有助于人们借以了解现在和推测将来:“史学之所求,不外乎①搜求既往的事实,②加以解释,③用以说明现社会,④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② 他之所以致力于撰著中国通史,就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③
读史所以经世济时,这是吕思勉的史学价值观的核心所在。但他对历史知识的借鉴价值的重视和利用是建立在历史知识真实性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吕思勉治史虽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但他更强调坚持史学的科学性,反对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任意剪裁,反对“强史就我”。吕思勉认为,“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因而他断然声明:“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④ 在他看来,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或把本民族看得过高,把他民族看得太低,“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导致民族主义的滥用。这种“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唯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⑤
在吕思勉看来,学术研究讲求致用固然不错,但绝不可急功近利。吕思勉明确指出:“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谬矣。”至于那种“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为矫诬”的做法,简直就是“愚民而惑世”⑥,更不足道了。他还说,“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然要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⑦ 吕思勉认为,“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因此,对于所谓宋明学者潜心于理学乃“不切实际,空谈误国”之论,吕思勉并不以为然,相反,他对宋明理学的学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予以很高的评价。因为“学术之为利为害,正自难言。”辽、金、元、清的入侵,有其深远复杂的原因,即使当时学者“尽弃其幽深玄远之学不谈”,短期内也于事无补。“理学讲尊王攘夷,严义利之辨,重君子小人之别,遂使中国之民族主义,植下深厚的根基,异族的压迫愈甚,我族之反抗亦愈力”,虽历尽艰难,“而卒能达其目的”,“又安能不归功于理学的栽培呢?”⑧ 但他强调,民族主义“须有智识以行之”,因为“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⑨。
可见,吕思勉是一位热情而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冷峻和严谨在民族生存受到极大威胁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他把这种治学思想贯彻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史学实践中。他把“二十四史”通读了二三遍,其中前四史竟然通读了四遍之多,并作了大量札记。再有,吕思勉在史书编纂中非常注重通俗性,他的许多著作都是用现代白话文写的,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是他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又一表现。
二、文化乃国家民族盛衰兴替之本
吕思勉强调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得以立足的根本:“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文化其本也,政事、兵力、抑末矣。”⑩ 他主张恢复古代的“兵民合一”之制,“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 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军事的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11) 吕思勉并不否认武力的强弱在国家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依然认为, 武力只是一时一地的因素,比较而言他更相信文化的力量。“一族一国,犹一人也,过刚者必折,不戢者自焚”,“历来民族国家之竞争,胜者之风气,固多尚武,然其所以胜者,实别有在,初非由其好杀;败者之风气,固多柔靡,其使之柔靡者,亦自有其由,初非徒矫其柔靡之迹而遂克有济;更不应因此遂怀偏激之见,并其所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者,而亦唾弃之也。”在他看来,中国“所以不亡者,亦自有故,而非必恃兵”,因此,未来中国最好的国策应是实行寓兵于农的民兵之制,从而做到“有兵之利而无其害”(12)。这里的“别有在”、“自有故”,当是指一民族之文化,他曾说:“凡民族之文化,发展至一定程度者,虽因①社会关系内部之矛盾,随文明之进步而深刻。②旧时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一时为外力所侵入,然其光复旧物之力,终潜伏而不至消亡。”(13)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究竟是提倡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吕思勉则相当理性。他确信人类社会终究是要向大同之境迈进的:“人类是只有相亲相爱,相扶相助,而没有互相争斗残杀的,人类有余的势力,要求消耗,都将用之于对自然的抗争。然而未至其时,则欲求自存,亦必须有相当的强力。”在世界未进于大同之前,民族国家,“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在世界上依然存在民族竞争的情况下,一国的“文事武备”二者缺一不可。比较而言,文化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武力的超越,亦要靠文化维持”(14)。他说:“天下最可怕的是,是文化的侵略。别种侵略,无论如何厉害,你自己总还记得是自己;一旦事势转移,就可以回复过来了。独有文化侵略,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自己忘掉自己,这不就是灭亡吗?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文化的侵略,岂不就是民族的危机吗?”(15) 有鉴于此,吕思勉相信,只要中国文化不失坠,中国就永远不会亡国,即使一时为异族所征服,也有恢复的一天!正因为认识到文化的力量,所以,置身于沦陷的上海,他一直以讲授国史、传播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对“中国不亡”有信心。
在吕思勉看来,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一个民族的盛衰。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何谓“文化”?一般而言,文化是共同体内部传承历史传统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等要素,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和近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吕思勉也看到中国政治不如人,军事不如人,经济更不如人。怎么办?难道中国就应该俯首听命、任人宰割吗?对此,近代中国爱国学者们给予了断然否定的回答。
这一时期的陈安仁就特别强调“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评断一国民族之盛衰,常可以文化之盛衰而推测之;评断一国文化之兴废,常可以民族之兴废而证验之。”(16) 他还说:“土地”、“人民”、“主权”固然构成“国家的要素”,但一国倘若“文化不能独立”,是不足以当“国家之名实”的。试看今日“弱小国家被侵略之后,土地已失,主权并丧,人民亦为牛马,而帝国主义者,尤且汲汲皇皇,以消灭弱小国家民族之文化”,原因即在于文化的停顿灭亡,才真正是“国家与民族衰落沦没之朕兆”(17)。
同样,在钱穆看来,文化的保存与发扬较之于民族、国家的存亡更为重要,因为凡“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皆为“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无不是其背后文化的代表;文化演进须“凭依”民族、国家而“发扬光大”。“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获得长存者。”环顾这个世界,中国民族命运之悠久,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古今”;而“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民族国家的前途,必须“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18)
可以这样说,文化民族主义者坚信:中国文化有其很强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并坚信,只要国人自立自强,光大优秀的民族文化,韬光养晦,就一定能战胜强敌,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看来,将吕思勉归入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之列是有根据的。
三、“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
吕思勉虽然对史学的民族主义趋向怀有一定的警惕,但他在史学著述中,始终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资源极为关注,抗战期间尤其如此。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吕思勉在在流露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诸如他说: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也“多少带了些中原文化以俱去”,这是“中国文化拓展的路径”(19)。中国民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向外扩展,是因为“我民族之文化,本甚优越,而又能时时吸收他民族之文化而融化之,以自辅益”(20) 的缘故。
然而吕思勉并不同于一班固守传统的国粹主义者,他毫不讳言中国文化的缺失:“中国文化之弊,在于文胜而失之弱”,特别是“自宋以后,陈义弥高,去事情弥远”(21),因此,中国应吸收外来文化之长来弥补固有文化之短。这和抗战时期的雷海宗、林同济等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文轻武的柔性主义特征的判断不谋而合(22)。他指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西方所长,在于科学方法,即克服天然之力;中国所长,在于合理生活,即人与人相处之道。”中国文化的优点包括:“①在政治上,较为自由平等;②在经济上,分配较为均平;③在道德伦理上,尚中庸而不趋极端,重实在而不务空想”,这些特点都“足以裨益世界”。中国不仅应该而且有能力吸收西方文化特别是“物质上之文化”为我所用;因此,“融合中西,另创一种新文化”(23),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
吕思勉认为,“民族主义必以民族为至上,民族的利害,不是但就物质方面计较的,其尤重的是荣誉。与其屈辱而生,毋宁光荣而死,在个人固当有此气概,民族亦然”,因为“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吕思勉剖析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不够发达的原因,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达只是八百年来的事情”,宋代因异族的入侵和压迫,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发达。他认为,指责宋儒“论是非不论利害,谈义理不审时势”,未免太“激于意气”了。在他看来,“宋代的恢复论,就民族主义言之,实放了万丈的光焰”。思想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此等议论,一时看似无甚效力,然潜伏人心,其力之大,实乃不可思议。明末遗老所以百折不回,事虽不成,然仍深藏着一个革命的种子于民间,至近代革命时犹收其效力,还不能不说是此种议论的影响。”(24)
如果把吕思勉与同时代的民族主义史家柳诒徵做一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二者的视角有着明显差异。同样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怀有深情厚爱,柳诒徵认为,要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不能单单讲国势已经衰落的宋朝,而应大讲强盛的汉朝、唐朝,从而探求当时中国致强之由,以为今人提供借鉴。他认为,“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否则惟有坐以待亡,不必再自命为优异之民族也。”(25) 而吕思勉对宋代文化评价评价甚高,特别是所谓“恢复论”,是因为这时候中国国土大片沦陷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国人中不乏丧失抗敌信心者。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志士仁人面对强敌,坚持抵抗,力求恢复中原,那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屈意志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正是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阶段时,最值得中国军民发扬光大的品格。
吕思勉还借宋朝遗民诗人、画家郑所南(思肖)的事迹曲折地表达了国土沦陷的痛苦心情。郑所南在宋朝亡国后,所画的兰都不带半点泥土,见者感到不解,便问其中缘故。郑所南非常愤慨地回答说:“土为番人夺取,汝不知耶?”郑所南“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乘天寺井中得之。其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26) 但清朝的一些文人却诬称《心史》为伪造,吕思勉不禁痛斥这种人为“全无心肝”,语气中饱含着强烈的愤怒情绪。
在吕思勉看来,中国近百年来民族主义的发展的情形“更值得追溯和检讨”。他指出,“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利害虽有矛盾,然当外力来临之际,由于文化的相异,总还能团结一致以御侮;但其团结紧密的程度,以及其赴机的迟速,就要看其有无矛盾,以及矛盾的深浅,以分优劣了。这是民族相争,或胜或败的大原因。”对于文明民族常为野蛮民族所征服的现象,他的解释是:“文明愈进步之国,则其社会的矛盾愈深,这就是文明民族所以常为野蛮民族所败的理由。”(27) 这个判断是其博览群书后思索的结果,确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四、“不信我为奴隶,今生便了”
“战争是社会的变态”,“旷观历代,都是当需要用兵时,则产生出一支真正的军队来;事过境迁,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种军队,亦即凋谢,而只剩些有名无实的军队”,“但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更无论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28)“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逸。一骄奢淫逸,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压迫,既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29)
既然世界的将来要向大同之途迈进,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个别的文化呢?吕思勉认为,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30) 语云:“败军之气, 累世而不复”,在吕思勉看来,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决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31)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民族精神的强调,几乎是吕氏在抗战时期著述的灵魂。吕氏认为,宋代的灭亡,可以说是中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竞争之故。两国国力的强弱,不取决于其人力物力本身的多少,而是取决于调动资源的能力。南宋“虽其一部份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由此看来,失败也是一种财富,因为遭受异族的压迫而激发其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孽时期。南宋时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32)
如果引申开来,遭遇外敌入侵无疑是一场国难,但只要善加利用,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不是吗?正是由于抗日战争,中国的社会动员才得以如此的深度和广度,所谓“地无分南北,男无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在纾解国难的过程中得以彻底的洗礼,从而升华到一个新高度。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转折点,中国人民距离“站起来了”的那一天也为时不远了!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吕思勉极力强调坚定信心的重要性。针对一些人的和平幻想,他明确指出:“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我们现在的处境固然非常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他非常乐观地说:“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他对悲观主义者说:“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难道我为奴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隶,今生便了。”(33) 字里行间洋溢者中国人民必将战胜强敌、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自信和乐观,这种乐观根植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切体认,根植于对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读来令人振奋。
众所周知,汪精卫叛国集团之所以走上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归路,其思想根源正是他那中国“战则必亡”的“软骨病”。他们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民气涣散,不是国力日隆民气赳赳的日本的对手,因而主张委屈以求生,和平以自存。归根结底,这种奴隶思想和行为是民族文化自谴论泛滥的必然结果。钱穆说的好:“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无文化民族的国民对其民族爱之甚浅,“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34)
吕思勉对民族前途的乐观,不仅在其史著中鲜明地表达了出来,更在其个人生活中身体力行。1941年上海“孤岛”为日本侵略者占据,像他这样的文化名人当然为日伪学校所求之不得。尽管他一家老小都靠他教书和稿费过活,但他还是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开。在和学生分别时他题“一片冰心”四字互勉坚守节操。回常州老家后,他先在游击区传薪授徒,后隐居家中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当时常州一些地方有日本兵岗哨,行人经过要脱帽,吕思勉不堪其辱,发誓非光复不戴帽(35),此举既是民族风骨的表现,又是对中国必胜的乐观自信的流露。
有学者指出,吕思勉为人淡泊宁定而治学平心静气,读吕思勉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这和他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36) 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要而言之,吕思勉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必胜根植于他长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精深研究。对历史学者来说,对民族国家怀有一份“温情和敬意”并不难,难的是在崇敬中保持着清醒,唯有清醒,方能真正发现我民族文化的光彩之处并发扬光大之。由此看来,吕思勉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一位理性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收稿日期:2005—12—29
注释:
① 吕思勉:《本国史答问》,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
②③④ 《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69页。
⑤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22页。
⑥⑦⑧⑩(12) 《吕思勉遗文集》(上),第282、402、402—403、454、35—47页。
⑨(13) 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6、248页。
(11) 《吕著中国通史》,第384页。
(14) 《吕思勉遗文集》(下),第150—151页。
(15)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183页。
(16)(17) 陈安仁:《中国文化演进史观》“自序”,文通书局,1942年。
(1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
(19) 见《吕著中国通史》第二十四章《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20) 《吕思勉遗文集》(下),第498页。
(21)(24)(27) 《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54、183—189、191页。
(22) 田亮:《战国策派再认识》,《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3) 《吕思勉遗文集》(下),第499页。
(25) 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
(26) 《吕著中国通史》,第450页。
(28)(29)(30)(31)(32)(33) 《吕著中国通史》,第156、143、5、436、5、496—497页。
(34)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35) 吕翼仁:《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4页。
(36) 王家范:《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标签:吕思勉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吕著中国通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秦汉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