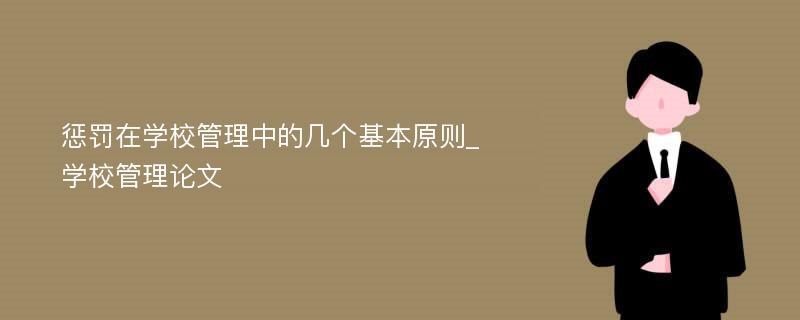
学校管理中使用惩戒的几个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基本原则论文,学校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理论界,围绕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要不要惩戒以及如何惩戒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即使在争论最为白热化的时期,惩戒的使用也从来都不曾从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消失或中断过。所以,问题的关键已不是惩戒这种手段可不可以被使用,而是惩戒在教育中究竟应该如何被使用。基于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以及学校管理的现实背景,我们认为,惩戒的使用至少应符合以下原则。
第一、合法性原则
近年来,诸如罚跪、打耳光、在脸上刻字等有关教师体罚的报道屡见报端,因体罚事件而引起的学生、家长与学校、教师间的法律诉讼案件亦时有所闻。于是乎,“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渐成办学的圭臬,校长、教师人人谈惩色变,对学生的违规行为则“视而不见”。然而,面对学生日益增长的违规违纪行为,面对学校、教师的漠然和回避,又有了“惩戒不可弃”,“放弃惩戒就是放弃教师的责任和良心”的大声疾呼。由此看来,惩戒的合法性和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单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的问题,而且也日益成为一个在实践中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具体来讲,学校管理中惩戒的合法性原则:
首先,要求学校管理中的惩戒主体要合法。只有合法的主体才能行使相应的惩戒权。在教育实践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惩戒主体,都能行使一定的惩戒权的,只有特定的惩戒主体才可以执行特定的惩戒权力。惩戒权作为一种带强制性的权力,既要有“权力来源的法定性”,又要有“权力行使的合法性”[1]。《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都明确规定,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惩戒的合法权力主体就是学校和教师。作为国家教育执行机构的学校和作为国家教育意志代言人的教师,代表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对学生实施教育,并以其特有的地位和权威,促使学生按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健康成长,当学生的行为与社会和国家的意志相矛盾、相抵触时,教师必须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进行控制和制止,避免类似行为的再发生,促进合规范行为的产生和巩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所以,任何非惩戒主体做出的惩戒行为,或超出了惩戒主体的行使权限,或把惩戒权转让给他人都是非法、不能允许的。
其次,要求行使惩戒权的具体依据要合法。合理行使惩戒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就是“有法可依”。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已从宏观上为教师正确行使惩戒权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学校来说,惩戒权的行使还必须结合学校、班级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订出实施惩戒的具体依据。学校的校规校纪是学校使用惩戒的具体依据,因此,校规校纪是否合法也直接影响到惩戒使用的合法与否。在学校,小到班级的条条框框,大到学校的规章制度,其制订首先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不能超出国家法律的要求和权限。因此,要明确制定出与违纪违规行为相对应的惩戒措施,使惩戒权的执行透明化、制度化。
第三,要求惩戒的对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惩戒针对的只能是学生特定的问题行为、不良行为或违规行为本身,而不是学生本人,不是学生的身心,不能损害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名誉权等,要基于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学生个体差异等的尊重。所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分别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必须“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任何出于私愤或个人情绪并给学生造成人身或精神损害的都是有违惩戒法权规定的。
第四,要求惩戒措施要合法。惩戒主体必须在法律赋予的权限内行使惩戒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以及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并对体罚以及其他滥用惩戒权的行为作了明确的处理规定。这就是说,学校管理中任何教育策略、惩戒措施的出台和实施,都必须限定在相关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当然,惩戒的合法化,应是既要保护教师教育的权益,使其教育权包括惩戒权合法有度地行使,又要保护学生接受教育的权益,使学生受到的惩戒有法律的保护。就目前看,我国相关的法律条文对教师惩戒权的行使的限制是非常明确的,但对惩戒权的合法化似乎讳莫如深。我们认为,把现代教师的惩戒权纳入法治的轨道,使教师的惩戒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既是落实“依法治教”的要求,也是避免传统教师惩戒种种弊端的根本途径。
第二、合规律性原则
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同其他教育手段一样,其作用不是绝对的。正确合理使用惩戒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必须符合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现代心理学对惩戒或惩罚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惩戒类别类型和方式是否有不同的要求;儿童认为什么样的惩戒是公正的、合理的;儿童认为什么类型的惩戒更有效。关于第一个问题,认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学生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呈阶段性发展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独特性,道德、认知和行为的发展都是如此。任何教育或干预手段,只有充分尊重这种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在学校教育中,不同教育阶段所适用的惩戒手段也存在差异性。如义务教育阶段,一般不能采取停学、勒令退学或开除等形式,而在非义务阶段,对此的限制就比较小。关于第二、三个问题,研究证明,不同年龄儿童有不同的惩戒观和公正观,相应地,对外部惩戒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在使用惩戒手段时,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这些反应。儿童惩罚观、公正观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抵罪的惩罚”到“回报的惩罚”的过程。“抵罪的惩罚”是指儿童往往认为应该用强制的手段使违规者服从成人的命令或规定,用痛苦的办法使违规者知道他的过失,如儿童说谎就罚站、罚他抄书等;“回报的惩罚”则不是给违规者的行为本身造成直接的痛苦,而是只要让他感到由于他的错误所造成的痛苦就行了。如违反大家的约定则受到孤立,不肯帮助别人则得不到大家的帮助等。7岁以前的儿童认为规则是外在的、是成人制定的,服从是公正的,违反规则的行为意味着犯错者破坏了服从的规则,对这种行为,抵罪的惩罚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在这个阶段,儿童“责任观念的形成是成人施加约束的结果”[2],所以施以适当的惩戒是能收到很好效果的。而对7岁以后的儿童来说,规则不再是外部强加之物,而是为了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制定的。违犯规则之所以要受罚,是因为他违背了平等和互惠的原则。采取回报惩罚的办法就可以使违规儿童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外,心理学就惩戒与儿童行为改变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适度的惩戒可以减少重犯错误的可能性以至终止不好的行为;惩戒有助于学生学习别人好的行为;惩戒可以阻止学生模仿坏的行为。同时研究也表明:(1)在使用惩戒减少一个不良行为时,同时强化另一个适当的行为,会收到很好的效果。比如,对迟到、旷课的学生,除了给当事人以批评外,还可以对那些按时到校、长期不旷课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提供足球入场券、提供免费电影等。(2)即时的惩戒要优于延迟的惩戒,也就是说,惩戒一定要在不良行为发生后立即给予,延迟的惩罚可能是无效的。比如,教师在学生进行了不良行为之后没有马上处理,而是隔了一段时间或者等待某个重要人物如孩子父母的出现,这样就会使孩子学会在没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表现恰当的行为。(3)在一个集体中,惩戒执行标准的一致性有助于使学生明确规则的要求,当教师把规则及行为要求告诉学生后,就应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前后一致,标准统一,否则学生就会对规则以及教师的期望感到迷惑,并在行为中表现出来。(4)避免强化不良行为。处于青春期好动的学生,有时出现的违纪行为或者问题行为不一定就是思想品质的问题,他们只是一时想引起别人的关注。比如,有的学生故意捣乱课堂,可能他就是喜欢老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批评他,这样可以提高他在同学们心中的地位。此时,教师就应避免对他的公开惩罚,可以采用“软”批评的方式。因为时间长了,这样的学生在正面场合下不能获得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就会转向通过经常实施不正当行为来获得大家的关注。因此,教师“必须保证学生由于不良行为而得到的注意要少于由于适当行为得到的关注。”[3]
总之,现代心理学有关惩戒或惩罚问题的研究对学校教育中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惩戒提供了诸多启发。正如有学者指出,任何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除非考虑这些心理学的理论,否则就不可能是合理的”。[4]
第三、合目的性原则
马卡连柯说过,“正确地和有目的地应用惩罚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教师利用惩罚的制度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笨拙的、不合理的、机械地运用惩罚会使我们一切工作受到损失。”[5]
以往人们对惩戒的目的理解为使学生改正错误行为,做合乎规范的行为。学校在制定校规校纪时则往往把惩戒定位在维护正常的教学管理秩序。而现实惩戒权的行使则容易简单地“以惩代教,以惩了事”,而忽视了这样的惩戒是否能达到“戒”的效果。事实上,惩戒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使学生“改过”,更重要的是使其“迁善”,应有助于、有利于学生良好品行的养成和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首先,惩戒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向善,而不单纯是避恶,惩戒要有利于学生积极德行的养成。信仰、理想对一个人来说,就像黑夜中的明灯一样,指引着其前进的方向。教师除了教给学生一定的必备知识外,对学生人生的引领至关重要。教师的责任不单是用惩戒的手段制止违规行为,还要为学生提供积极的行为导向。德行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为恶(wù)恶,而且要向善。教师在实施惩戒时不能只向学生传达什么是错误的、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也许会降低学生采取错误行为的愿望,而它本身并不能告诉学生怎样做才是适当的。除了使学生明白为何不能进行该行为之外,还要使他们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是适当的,要为学生提供积极引导,使学生自愿能动地实施好的行为。
其次,惩戒要有利于学生探究精神的激发和创造性智慧的培养。在英国,有一则因惩戒而成就一名科学家的故事,以至传为美谈。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麦克公德小时候为弄清狗的内脏杀了校长家一条名贵的狗,校长得知情况后并没有斥责或批评麦克劳德,而是罚麦克劳德画一副人的骨骼图和血液循环图。而正是这一次不寻常的受罚经历激发了麦克劳德对生物的浓厚兴趣和创造欲望。所以,我们在因学生学习或行为的一次失误或失当而惩罚学生时,始终不要忘记惩罚永远都是教育和管理的手段而非目的。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的目的似乎只是使学生通过各种类型的考试、记住那些死的知识、追求更多的标准答案、成为唯上唯书的听话者,违背这些目的就要受罚。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无视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和创造性的养育,压制与扼杀学生个性,压抑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对学生奇思怪想的漠视甚至讥讽,对一次失误所进行的罚抄作业,对抗拒划一要求和标准答案行为的严惩等等都是这种目的观在实践中的表现。我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在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慧、创造性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惩戒使学生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要为他们创造更多更积极的发展机会,要为学生的探究乃至异想天开提供更宽松和宽容的环境。创造性智慧、创造性才能只有在充满机会和个性得以彰显的教育和教学环境中,只有通过学校的创新性实践和创造性活动,也只有通过教师对学生创造性的尊重、爱护和激发才能培养出来。
再次,正确使用惩戒还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和对学生身体摧残的变相体罚。体罚虽然在许多国家已被取缔,但屡见报端的体罚乃至摧残学生身体的现象说明了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没有正确认识惩戒的目的。体罚不仅给学生的身体造成伤害,而且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荷。因此,在学校管理中要坚决摈弃任何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的惩罚形式,使学生拥有健康、阳光的学习心境和健康文明的成长环境。
第四、合伦理性原则
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存在一种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而且也存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惩戒的使用也要符合教育的伦理要求。合伦理性原则是对教育者惩戒行为的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
第一是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性。尊重学生是指教师的惩戒对象是人而不是物,要把学生“当人看”,当作活生生的、具有独特存在价值的个体来看待。人格和尊严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东西,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人的一种普遍需要。尊重学生最起码和最基本的就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友好平等地对待学生,不粗暴压制学生,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侮辱学生人格的言行。一个人如果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增强前进的信心和动力,相反,如果人格受到侮辱,就容易产生自我否定的消极情绪,甚至步入歧途。尊重学生还集中地表现为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学生的个性是每一个学生个体存在价值的集中体现。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就要冲破封闭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使我们的教育成为一种促使学生开放性成长的教育,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开放的、自由呼吸社会新鲜空气的学校;尊重个性就要打破划一的目标、划一的内容和划一的方法,尊重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需求:尊重个性还要拒斥机械主义的程式化的训练,以人化的、成人的方式教育、管理学生。
第二是要信任学生。信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尊重,它不仅是一种教育的要求,也是对教师的一种道德要求,任何惩戒手段的使用都必须以对学生的信任为前提。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惩戒才有可能发挥出应有的教育力量。教师把学生当成什么样的人来对待,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学生的诚信品质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猜测甚至敌意的环境中养成的。不尊重事实、不听解释,不问原由的一味惩罚,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更是对教师神圣职责的亵渎。
第三要懂得关爱学生。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的活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内尔·诺丁斯教授从关怀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关心者不必然都是教师,但是教师则必然应成为关心者。”[6] (carer)。有些教师借口关怀学生而对学生严厉管教,然而,关怀绝不是单方面的、强权的、自以为是的。善的、符合道德的关怀不完全取决于关怀者一方,还取决于对被关怀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惩戒的使用绝大多数是由于惩戒者善性的目的,但是惩戒到底起到多大作用及效果如何,还要看教师是否做到了真正从关爱学生出发。
总之,惩戒作为学校教育与学生管理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只有在合法、合伦理的前提下,尊重儿童知行发展的规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学校教育和管理的目的——促进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