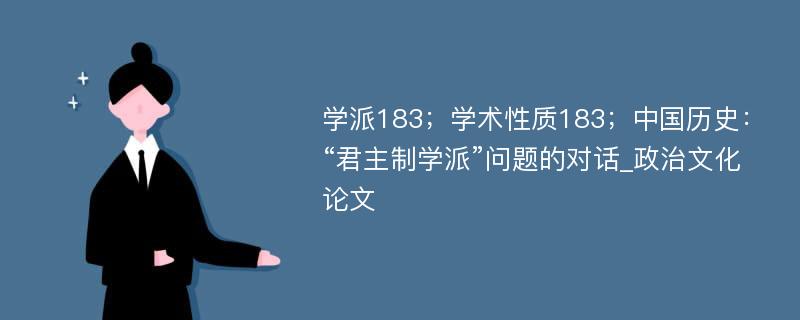
學派#183;學術個性#183;中國史觀——關於“王權主義學派”問題的對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學術個性论文,中國史觀论文,王權主義學派论文,關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學派”對於中國學術的意義 劉澤華:李教授,《文史哲》第四期竟然打破常規,在首篇刊出了你長達四萬字的文章,讓我非常吃驚。究竟其意義何在呢?我個人揣測,李教授和《文史哲》的諸位決策者都意在學術界提倡“學派”。但我的問題是:爲什麽現在要提倡“學派”呢?1949年以後,中國史學界除了官方認定的一個學派外,其他的基本上談不上什麽學派了;即便有一些“學派”苗頭的,也沒有什麽好的結果。於是,包括我在內,大多數人都成了“緊跟派”。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聖人發言了,就緊跟聖人;聖人不講話了,就緊跟賢人;總而言之,當時是唯權力是瞻,誰的權力大,誰就是真理。就當時情況而言,也並非完全出於被迫,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認同的;即使有心存異議者,多半選擇沉默或進行自我批判——歷史學界重量級的學者幾乎都有自我批判的文章。最爲傷痛的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郭沬若(1892—1978)竟然要焚毀自己的全部著作以求存身。“文革”結束以後,大的環境出現了變化,學術界又開始思考問題,對不認同的觀點提出質疑,並且出現了多元化的勢頭,但也不時會出現一些要“統一”思想的聲音。從政治家的初衷來說,在政治組織內部對其成員的思想行爲作出規定,予以約束,從而形成統一意志,是有其正當理由的。但是,由於中國語境下的政治與學術邊界模糊,政策執行者容易混爲一談,使得學術研究深受影響。以歷史學爲例,哪些人物、事件應該肯定,哪些人物、事件應該否定,不否定是否就都是肯定,不否定是否就不能分析;如果允許分析,到哪一步是允許的,到哪一步是禁止的,由誰來判定,等等,這些都涉及一個歷史認識的大問題。另外,現在還有一種“交學費”的觀點很盛,認爲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進行探索,都是爲後來的改革開放所交的必要學費和應付出的代價。這類認識固無不可,問題是不准與之相左的看法公之於世。這就讓人感到害怕了!難道學者都得沿着這個思路去思考、去認識?所以,我想請問李教授,你現在提出“學派”問題,用意何在? 李振宏:我之所以要提出“學派”問題,並提出一個以您爲首的“王權主義學派”,並不是出於對您個人的感情。劉先生的大名我雖早已耳聞,非常敬仰,並且在20世紀80年代就受到過您的影響,但過去我們之間並沒有交往,而且我也不習慣於爲某個人做事。我之所以提出“學派”問題,而且要張揚一個“王權主義學派”,出發點在於推進當代的學術發展。 在我看來,任何學術都是要在充滿活力的學派林立的局面中獲得其生命力的。如果沒有不同學術理念、不同歷史觀的認知、不同學術風格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的對立和爭鳴,學術生命就會窒息。對此,古人深諳其道。《漢書·藝文志》開篇就講:“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所以,孔子(前551—前479)死後,《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一個學術的創始人死了以後,他的思想是一定要分化的。這個分化的最終結局,就會形成不同的學派。其本始是一派,派中又分派,這是必然的現象。正是學派的對立和爭鳴,推進了學術的發展。馬克思(K.H.Marx,1818—1883)逝世後,繼承馬克思的人,或者有志於學習、研究馬克思的人要不要分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爲,不同人所理解的馬克思都衹是他自己理解的馬克思。於是,在理解研究馬克思的過程中自然就會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學派。這些學派的對立與爭鳴,就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這是學術發展的正道。如果不是這樣,衹有一種聲音,那學術怎麽發展?而學術的對立和爭鳴,是要靠形成一批相對穩定、集中的學術共同體來實現的。這個學術共同體就是學派嘛!衹有穩定的學術共同體,纔能把某種學說、某種理論、某種學術思想推向一定的理論高度,創造具有相對完整並付諸實踐的、能夠經得起檢驗的一種理論體系。單個人是沒有力量來完成這些的。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有相對一致的問題指向、選題指向,有大體相同的學術理念,有相同的歷史觀認知,有相同的方法論,它在這個領域的開掘會達到相當的深度。這是學術共同體的作用。有這樣不同的學術共同體存在的對立和爭鳴,自然就推進了學術、繁榮了學術。所以我想,衹有學派林立的學術時代,纔可能是學術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 1949年以來,中國衹有一個學派,即馬克思主義學派。顯而易見的是,衹有一個學派,也就等於沒有學派了。中國史學界在過去幾十年裏,從50年代到80年代,開了“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結果怎麽樣?後來都敗落了吧,現在人們很少知道或提起“五朵金花”了。起初還以爲是“文化大革命”把它們的研究進程打斷了,所以,“文革”以後,歷史學家們又重操舊業,重開了“五朵金花”,結果沒開多久就枯萎、敗落了。爲什麽呢?因爲它根本上還是一種聲音。比如,關於“古史分期”好像有八家學說,其實都屬於五種形態史觀之內。按照我的說法,可以稱之爲“同株異葉”。一根樹幹,生長出不同的枝葉,衹要樹根、樹幹出了問題,那所依附的各種枝葉也就都枯萎了,哪一派也活不下去。古史分期就是這樣的結果——當五種形態史觀受到挑戰後,以此爲理論的各家學說也就統統被置於尷尬的境地。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就是想在中國學術界發出一些不同的聲音,張揚一下學術的個性,並最終實現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與繁榮。這是我的初衷。 劉澤華:接下來我想問的是,“學派”如何界定?比如說,一種思潮算不算學派?近年來的“國學”熱,新儒家與尊儒之風很盛,以及新道家等等,算不算是一個大學派?還有,許多認識領域的開發,也有相應的理論。比如,社會史、文化史等,算不算學派?所謂“學派”,你主要是看價值體系,還是認識領域和認識體系(解釋體系),抑或三者的交織? 李振宏:按我的理解,“學派”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如果要下定義,就不一定能說得很精確。大體說來,就是在同一個學科中由於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學術理念、價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學術派別。一個學派,就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共同體,即一個由共同的價值觀體系、共同的方法論思想(即解釋體系)和堅守共同認識領域的人形成的學術共同體。一個學派是否成立,主要看幾個要素:(1)有共同堅守而又區別於他人的價值觀體系和系統的方法論思想。在歷史學範圍內說,就是有共同的歷史觀和方法論。(2)有共同的治學理念和學術宗旨,亦即學術目的性問題。(3)有共同的概念體系或話語系統。(4)有明確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如果是在這幾個方面都有所體現的學術共同體,就可以稱之爲學派。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現代“新儒家”是可以稱之爲一個“學派”的。他們的確有一致性的價值觀認同,有共同的學術理念和學術宗旨,有他們的概念體系,也有比較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而那些所謂“國學”熱以及強盛的尊儒之風,就算不上什麽學派了,僅僅是一種思潮而已。它們甚至都劃不到學術的範疇內,衹是一種思想或觀念的浮躁和喧囂。而文化史、社會史則衹是一種觀察歷史的角度或方法,是從特有的視角觀察歷史所形成的不同學術路徑。文化史或社會史儘管有着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體系,有很多從業人員,但其從業者並不一定在歷史觀、價值觀、治學宗旨、學術理念上與其他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相區別,如果籠統地稱之爲“文化史學派”、“社會史學派”也無大謬,但嚴格地說,是不具備學派的基本要素的。在歷史學的範圍內說,判斷學派問題,最重要的是歷史觀、價值體系、解釋體系、治學宗旨這樣幾個要素。這裏申明一下,人們常說的“文化史觀”,無疑是一個學派。 劉澤華:談到學派問題,我認爲首先要關注歷史的“真”。但是,“真”在哪裏?比如,在討論近代史從何時開始這個問題上,有宋朝說,有明末說,有鴉片戰爭說。這算不算學派?又如,近代以來,有現代化爲主流說,有“挨打”爲主流說,還有既“挨打”又輸入現代文明說。這些算不算正常的學派?再如,經常會有一些有權勢的人憑藉權力而形成學術壟斷,這算不算一個正常的學派?中國傳統史學中是很強調“正統”的,而越是“正統”,假的東西越多,是否“正統”也算是一派? 李振宏:歷史研究是以求真爲前提的,衹有弄清了歷史之“真”,纔可能從真實的歷史中提取出可靠的歷史借鑒。但是,問題的詭異之處就在於,什麽是歷史之“真”?歷史之“真”在哪裏?不要說帶有解釋性的歷史認識,就是純粹客觀的歷史現象,我們都難以捕獲。歸根到底,客觀的或解釋的歷史,都需要通過史學家的頭腦來發現,來表達;而一旦經過了頭腦,不同的頭腦解釋或揭示出來的東西,就一定不會是同一個面貌。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我記得,您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次關於歷史認識論的講座中,就曾談到過歷史事實的問題。您說,每個歷史學家都說自己是憑事實說話,但事實在哪裏?同一個歷史事實,拿在不同的人手裏,就是不一樣的事實。當然,這不是您的原話,但大意如此。我是從別人的錄音磁帶裏聽到了您的演講,很受啓發。歷史研究就是這樣,我們面對的是消失了的對象,對它的解讀不能不打上無法清除的主觀性印記。給歷史以解釋,在解釋中傾注我們全部的主觀能力,這是歷史學家特有的職責和權利。於是,在近代史的開端問題上,就出現了您所說的宋朝說、明末說、鴉片戰爭說等等;但這些不同的說法,並不一定是由於歷史觀的不同、價值觀的不同的結果,也不一定是方法論的問題,其實就是對材料的解讀問題,對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市民社會”等等概念的理解問題,它是由個人的思想觀念、學術修養、認識能力等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這些就是一般的學術觀點的不同,不一定都要上升到學派的高度去認識。 關於近代歷史進程的認識或解讀,過去傳統的說法就是“革命史觀”,改革開放之後出現了“現代化史觀”,最近有些人在批“歷史虛無主義”的同時,把“現代化史觀”上升到需要大加撻伐的“歷史虛無主義”的高度,這些是不能稱之爲學派的。“革命史觀”是政治爲學術規定的解讀路徑,不屬於學術的範疇,而政治與學術之屬性不同則是不需要論辯的。“現代化史觀”作爲一種學術觀點,就目前情況看,表達這些看法的人似乎還沒有形成一種學派,沒有成爲一個穩定的學術共同體,不一定要從學派的角度去認識。 在近代史研究中,堅持“革命史觀”的大體可以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自身並非政治家,卻用政治家規定的思維路徑去“裁剪”歷史。這些人由於缺乏思維的獨立性,對“學術”爲何物並不理解,當然是談不上學派的。另一種是,如果有着自己的獨立思考,在自己真誠的學術研究中抽象出了一個“革命史觀”,有着自己獨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那是可以稱之爲學派的。 一個學派的基本要件,或者說正當性與合理性的主要支點,在於它是獨立思考、思想自由的產物,而不在於它的觀點和理論本身。如果是在這樣的情景中形成的學術群體,無論它與政治家的宣傳多麽相似,它也是應該受到保護和鼓勵的。因爲,它是學術研究中的正常現象,是認識的常規產物。我贊成恩格斯(F.V.Engels,1820—1895)的觀點:“真正科學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謬誤和真理這種教條式的道德的說法。”①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中,不要輕易判斷什麽是真理與謬誤,從自由思想場域中產生的任何觀念、觀點,都要肯定其正當性。其實,說穿了,正統不正統,不在於觀點本身,而在於你是不是以獨立思考、自由思想爲前提,在於你是不是真正具有學術的本性。 劉澤華:如果“學派”叢生,每個學派都有自己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對於同一個問題各有自己的答案或解釋,歷史的“真”是否會被“異化”,還是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學派林立是否會引起人們對“歷史學”的懷疑——歷史是否會成爲任人梳妝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是否就會變成民間藝人——“說書人”口中之物,衹是給人以樂趣而已? 李振宏:您提的是一個歷史認識論的問題。對於歷史的不同解釋,其實正是學術的魅力之所在,正是學術的生命力的表現。 事實上,每個歷史學家都是從一個特有的角度去認識歷史,都衹是提出對歷史的一個獨特的認識,因此,每個人的認識,都衹是看到了歷史的一個方面,再聰穎、再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洞察歷史的全部真相。我們都來認識歷史,你看到了歷史的這個方面,我看到了歷史的那個方面,他看到了歷史的另一個方面,不同的歷史認識彙集起來,對歷史的認識就更加豐富和全面。因爲,真實的歷史就埋在各種各樣不同的歷史解釋之中。所以,學派叢生所造成的不是歷史的異化,而是歷史學的繁榮,是歷史之“真”的充分揭示。衹不過,在中國,這是人們還不太適應的學術場景。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太習慣於“一”——統一和同一。由於文化傳統中的專制主義土壤過於深厚,人們不能接受對於同一種事物的不同解釋,好像不同的解釋就一定衹有一種是確定正確的,而其他則是錯誤或荒謬的。其實,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衹有確定的一種解釋,對於消失了的歷史現象的解讀更是如此,這也正是學術研究要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原因。而衹有學派林立,纔可能造成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派林立,百花齊放,在一定時期內的確會給人以炫目之感,會使長期在學術一統的氛圍中生活慣了的人們感到某種不適,但是,這種局面卻正是科學春天的象徵。在這個問題上,我深深感到,中國史學界需要進行歷史認識論的補課。有了認識論方面的常識,人們就不會爲歷史解釋的紛然雜陳而感到不適了,就不會把豐富多彩的歷史認識戲稱爲對小姑娘的梳妝和打扮了。 劉澤華: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究竟是提倡學術個性,還是應強調特定的歷史規定性?如果學術個性與特定的規定性發生矛盾,是求同存異、展開爭鳴、擺事實(打材料仗)呢,還是服從特定的規定性呢? 李振宏:當然是要提倡學術個性了。任何認識,在其原初意義上都是個體性認識,學術個性是學術發展的前提。從學術的本質出發,不僅不應該強調特定的規定性,而且對於認識來說,就根本不應該有“規定性”這樣一個提法。認識應該是自由的、生動的、變動不居的、因人而異的。有了規定就取消了自由,就沒有了認識。所謂“規定”,是對認識的規範、控制和牢籠。思想被規範了,還是思想嗎?認識被規範了,還是認識嗎?被規範的思想是教條,被規範的認識是模板。如果一種學術研究,不是從事實本身出發,而是從明確的既定的政治目的出發,研究的全過程、最後得出的結論始終被一種東西規定着,甚至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的結果就已經明確了,這還叫研究嗎?這還是學術嗎?規定性是學術研究的對立面,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和真正的學者應該鄙視和摒棄的東西,這是常識。 當然,我理解,您提出的這個特定的規定性,指的是歷史認識中的政治因素、意識形態因素,改革開放前學術界對歷史的認識就是被這些東西規定的,但這是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造成的不正常現象,不是認識的常規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要極力擺脫的正是這種東西,儘管至今這種規定性還不時地在困擾一些學者。作爲中國學者的個體,要想完全擺脫規定性的控制是困難的,但可以呼籲認識的自由,呼籲有與之爭鳴的權利;從我內心來講,是不認同任何人有控制我學術個性的天然權力的。 劉澤華:在歷史認識上有很多關乎國家、民族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否“國家”意志或某種利益集團的利害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可否有“學派”的不同認識? 李振宏:這是個現實性很強的問題。在歷史認識中,的確有許多關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站在國家或民族的立場上,一定有着特定的利益表達,於是也就有與之相應的觀點表述,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歷史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會與這些問題的國家認識相一致,這也是極爲正常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就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根據特定的國情來處理。 首先,從學術的角度說,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學派”的不同認識,或者是個人的不同認識,當然是可以的。這個“可以”是天經地義的,與其他一般問題的認識一樣,沒有人有剝奪不同認識的權力。但是,具體到中國的特殊國情,這些涉及國家、民族利益問題的不同認識,應該採取合適的渠道去表達,不一定要與一般的歷史認識那樣去訴之於公開的學術媒體。因爲,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學術的控制過於嚴苛,學者也必須表達與國家意志、國家意識形態完全一致的看法,這樣一來,學者公開發佈的研究成果,外界、國外往往視之爲政府立場的表達;因此,如果一些學者從學術自由的立場出發,在此類問題上公開發佈與國家意志不同的看法,那麽,這些本來是表達學術個性的看法就可能被誤讀、曲解爲國家立場。所以,對於這類與國家意志不同的認識,是需要慎重考慮它的發佈渠道的。 其次,隨着國家政治環境的改善,學術自由的空間也在大幅度拓寬;當學者們可以完全自由表達個性化認識的時候,學者的認識與國家意志可以明確區分的時候,公開發佈與國家意志相左的看法或認識就正常化了。理想的學術狀態是,對於同一個問題,即使是涉及國家或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國家意志與個性化認識都可以自由表達、互不干涉、共同生存,學者們的不同認識表達不會引起什麽歧義或麻煩。 二、“王權主義”作爲一個“學派”的依據 劉澤華:我現在提另外一個問題:你根據什麽把我們這一群人撮成一個學派?我先自詡一下,我這個人一直是提倡學術個性的,我本人也想追求一點學術個性。正因爲如此,我寫的東西多多少少還是產生了一些影響的,有的甚至越出了國界。例如,我在1987年出版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這本書,在中韓建交之前就已經被翻譯成韓文了;後來,韓國人又把我、葛荃、張分田分別擔任主編、副主編的三卷本的一百二十多萬字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翻譯成了韓文。在日本,也有人介紹我的觀點。在英語世界,比利時魯汉大學有一個影響很大的刊物《當代中國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季刊),有四十多年歷史了,最近推出了我的一個專輯:我想,他們也認爲我有點學術個性吧! 但是,由於我認定儒學主導部分是帝王之具,於是遭到尊崇儒學者的批評;現在尊儒之風浪潮洶湧,我是有點兒討嫌。在我印象中,最早批評我的是張岱年(1909—2004)先生。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通過方克立先生向我轉達:“劉澤華,怎麽老是講王權主義啊?你講王權主義,中國的傳統文化往哪兒放?”我回應說:“這是兩回事啊!中國的王權主義是個事實問題,傳統文化該接受什麽、該怎麽評價是另外一個問題。”後來,批評我的人多了起來,叫“劉澤華學派”。其實,最初叫“劉澤華學派”的是把我批判得一塌糊塗的人,說我這個人狗屁不通。有一些人批評我是全盤否定傳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謝地坤在一篇文章中把我作爲全盤否定論的代表②,美國華裔教授陳啟雲先生也持這種觀點,類似的批評很多。當然,也有不同評論,方克立先生就接過“劉澤華學派”這個稱呼而給予充分的支持;瑞士漢學家畢來德(J.F.Billeter)在分析當代中國思想的時候,說中國當代有四大思潮,其中有一個是“反思派”,代表人物就是劉澤華。還有不少的學人大體認同我的觀點。其實,我與你李教授衹見過一兩次面,很少交流,那麽,你是根據什麽提出一個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王權主義學派”呢? 李振宏:這個問題很簡單。我以爲,你們這個“王權主義”研究群體符合作爲一個學派的要件:第一,這個學術群體有一個代表人物。這自然就是您劉先生了。第二,不僅有一個穩定的學術群體,而且還有一些標誌性的骨幹核心人物,如張分田、葛荃、張榮明、林存光等。第三,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您的三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集》;另外四位核心人物也都有代表性著作。第四,有着共同的重大的歷史認知,在歷史觀和方法論問題上有着明顯的一致性。比如,您下面這段話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在傳統中,政治的幽靈無處不在,而且舉足輕重,決定一切。從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以其獨特的方式與政治緊密地糾葛在一起。政治問題成爲全部社會問題的核心,甚至一切社會問題最終都被歸結爲政治問題……政治思想也就成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心。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正是這種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化傾向,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因此,要準確而深刻地剖析傳統,就必須以政治爲楔入點。③ 第五,有着共同的選題指向。您帶出來的一群博士,所有的選題都是指向了政治思想史,而且所有研究政治思想著作的核心都是解剖王權、專制這個問題。這一點是非常鮮明的。甚至那個叫劉暢的博士,寫了身體史這方面的東西——心君同構,也是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這個群體,有着共同的選題指向、共同的問題意識、共同的學術理念、共同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我在投給《文史哲》那篇文章的初稿中,還詳細檢索了你們幾個主要人物使用的學術術語,因原文太長,這部分在發表時刪掉了。單是您用過的術語,我就總結出了五六十個概念;張分田、張榮明等人的術語,我也總結了一些。這些學術術語有着相當大的共同性。使用的概念術語的共同性,也就是你們分析工具的共同性,你們的話語體系是由你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決定的。劉先生,這麽多的共同性還不足以說明這是一個學派嗎? 劉澤華:對此,我在這裏不免感到有點兒不安。“不安”什麽呢?就是我把學生都拉到我這一條道路上了,是不是帶有“學霸”色彩?我也多次想過,自認爲在我與學生之間,我從來沒有要求學生遵守什麽。比如,選題我一概不管,必須是博士生自己選。在我看來,如果自己都不能選題目,還做什麽論文?一旦有了選題方向,我會與他們反復討論。爲什麽我不贊成講“劉澤華學派”,因爲劉澤華是一個土老頭,學識很少,把這麽多學生都放在“劉澤華學派”中,一是忽視了每個人的個性,二是也不尊重各自的獨創性。跟隨我學習的博士們的論文幾乎都出版了,你稍微翻翻就會看到每個人的獨創性,有很多遠遠超越了我,我爲他們的獨到創見感到驕傲。所以,我不接受“劉澤華學派”這幾個字。 李振宏:呵呵,“王權主義學派”還是可以接受的。 劉澤華:我覺得,要說我的學術有特點,還是能夠接受的;但能否構成一個“學派”,可能還有疑問。我在論著中所說的王權主義首先是“事實”問題,而“價值”也不是簡單的一邊倒;有些人說我是“全盤否定論”、是“虛無主義”,其實他們沒有理會我提出的“陰陽組合論”,我是在矛盾的陳述中評說“價值”的。有人說“陰陽組合論”不是“一分爲二”,而是“一分爲一”,我估計他就沒有仔細讀我的文章,大概看到“王權主義”就反感。“反感”也正常,也是一種學派吧! 三、中國史觀意義上的“王權主義” 劉澤華:剛纔李教授提到了我有一套中國史觀,我有點坐不住了。“中國史觀”這幾個字,我看得非常重。我這個人雖然有點個性,但畢竟一身土氣,坐井觀天,不大可能創造一個獨立的中國史觀。所以,你現在提到我有一個中國史觀,我請問,你是怎麽找出這個中國史觀的? 李振宏:我把您的觀點上升到歷史觀的高度,您是有點恐懼,這正是中國王權主義的特點。王權主義搞得一切都變成政治問題了,好像我們一般人就不能有個歷史觀,誰要有個歷史觀就大逆不道了。所以,我在《文史哲》那篇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 很久以來,用“學派”來稱呼一個學術群體,在中國學術界已經很不習慣了,中國學人似乎已經不習慣於張揚獨立學術個性,一旦某個人自己提出了獨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不管是別人看他,還是他自我思忖,都會油然而生一種大逆不道的感覺。他會像犯了罪似的不敢坦然面對學界的狐疑。④ 坦率地說,我們爲什麽就不能提出一個歷史觀呢?這裏,我之所以認爲劉先生的“王權主義”是個歷史觀,是因爲您這個王權主義關照的是中國歷史的整體。1998年,您在《天津社會科學》發表的那篇文章對王權主義講得很清楚: 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着社會經濟分配,社會經濟關係的主體是權力分配的產物;在社會結構諸多因素中,王權體系同時又是一種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在諸種社會權力中,王權是最高的權力,在日常的社會運轉中,王權起着樞紐作用,社會政治動盪的結局最終還是恢復到王權秩序中,王權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則是社會理性、道德、正義和公正的體現等等。⑤ 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歸結爲王權,王權關照到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而且最後您總結說,王權主義“大致說來分三個層次,一是以王權爲中心的權力系統,二是以這種權力系統爲骨架形成的社會結構,三是與上述狀況相應的觀念體系”。您看,政治結構、社會結構、觀念體系,社會的幾個主要層面都突出了一個王權;您的王權主義關照了整個中國社會,解決的是一個歷史的整體認知,您說它不是個中國史觀又是什麽呢?至於說,這種中國史觀能否與哲學上講的唯物史觀等量齊觀,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二者也的確是有區別的。就它們之間的關係而言,有如下三點區別:第一,唯物史觀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學說,而您的史觀衹是中國史觀,衹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本質抽象和整體把握,兩者相比,處在不同的層次上。第二,王權主義歷史觀應該是繼承了唯物史觀的某些東西,沒有完全背離或脫離唯物史觀。比如,唯物史觀認爲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而您也是承認歷史的客觀性的。又如,唯物史觀認爲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儘管您對這個東西沒有完全認同,因爲您講過兩者是“雞生蛋和蛋生雞”的關係,但您也不是完全脫離社會存在來講思想的發展,並且特別注重政治思想與社會的互動。第三,王權主義確實在某些方面對唯物史觀有所突破,如果沒有這個突破,我不會認爲您是一個學派。比如,對於“侯外廬學派”,我就不大承認。因爲,侯外廬(1903—1987)先生衹是貫徹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來研究中國思想史,並沒有很突出的個人特色。您的突破就在於您不再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樣一些觀點來解釋中國歷史,而是強調中國歷史發展中政治權力的決定性力量和支配意義。總之,我感覺,“王權主義歷史觀”不是對唯物史觀的抛棄,而是在承襲唯物史觀的某些方法論並將之運用於中國歷史的考察中形成了與唯物史觀相區別的一個中國史觀。我這樣來認識,不知您能接受嗎? 劉澤華:你這是“哪兒有瘡疤就往哪兒揭”啊!捫心自問,我自己都不敢講。實際上,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出格了。我的確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樣的基本觀點上有所變更。 李振宏:終於承認了,終於承認了吧。 劉澤華:我是個小“修正主義分子”。我很早以前寫文章提出要給“修正主義”正名,因爲不搞“修正”就不能發展;但我這個人做學問時缺少一點理論上的勇氣,衹能打打擦邊球。因爲,寫出文章還得能發表纔行,所以有時候我也爲“影射”做辯護,說“影射”是中國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傳統,不能正面講,衹能拐彎抹角地講。這類事情多得很。我曾多次建議我的學生們研究一下中國的“影射文化”,可惜指導了這麽多博士生,卻沒有一個人接受我這個建議。 中國學術要進步就必須要爭鳴,而爭鳴是不能設有前提的。我曾在1986年寫過一篇文章《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⑥,又寫過《史家面前無定論》⑦。如果有前提,有定論,那還算什麽“爭鳴”?何況,我們身處的世界紛繁複雜,就算國內“統一”了,還有一個與國外學術界爭鳴的問題:要求國外學者以你限定的思想爲指導來討論學術問題,這是不大可能的。 作爲一門科學,歷史學本來是開放的,從哪種角度進行研究都可以,關鍵是看哪種論述更接近於歷史事實。但是,現實中的一些現象仍然對正常的歷史學研究形成制約:一是有些部門對重大的歷史問題研究設置“框框”,研究成果不能見諸正式出版物。二是壟斷了檔案資料,一些本應解密的檔案衹公佈“一角”,造成“史出一孔”。當然,這種現象的完全消失,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但作爲史學研究者來說,即使外在條件“萬事俱備”了,如果自身缺乏基本功的話,也難以有成。這除了“德”、“才”、“學”之外,還要有“膽”,即學術膽識。魏晉時期的嵇康(223—263)就寫過一篇文章叫《明膽論》,一個學者如果學術膽子小的話,是很難有創見的。 四、如何發展“王權主義歷史觀” 劉澤華:我再給李教授提個問題。你在文章中講,這個“王權主義歷史觀”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那麽,請問,它有哪些開拓空間?怎麽開拓?會不會越開拓越麻煩? 李振宏: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對這些問題想過一些。“王權主義歷史觀”已經被您三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及您這個學術群體大量有分量的學術著作所證實。當然,還有您與汪茂和、王蘭仲合著的《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一書,對王權支配社會有相當精闢的論證。但總的來說,它還是偏重於政治思想史,對整個中國歷史研究缺少力度。那麽,這個歷史觀是否站得住腳,能否成爲解讀整體中國歷史的一個方法論,就需要回到具體的中國歷史研究的實踐當中來。目前,“王權主義歷史觀”已經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範圍內產生了影響。在2010年5月《文史哲》編輯部舉辦的“從秦到清社會形態問題討論會”上,與會專家對秦到清末的社會形態基本上形成共識,認爲“自秦商鞅變法之後,國家權力就成爲中國古代的決定性因素,不是社會塑造國家權力,而是國家權力塑造了整個社會”。這不就是王權主義嗎?不過,真正拿您的王權主義作指導來研究歷史的人還很少,至今還沒有一部以“王權主義歷史觀”爲指導編寫的《中國古代史》。我們能不能把中國古代社會就命名爲“王權主義社會”?這個詞是我想的。秦統一以後的社會過去叫“封建主義社會”,現在就叫“王權主義社會”,秦以前的稱之爲“前王權主義社會”,如何?就我所知,剛剛去世的南開大學校友、山東大學的張金光(1936—2013)教授最近十多年的研究,就是在證明着“王權主義歷史觀”的正確性。我不知道張教授是否讀過您的王權主義的書,是否受過您的影響?如果沒有,那就是他在自己獨立的研究中發現了王權主義。 劉澤華:他的論說很有發現意義,但時間應該在我之後。 李振宏:所以,這個學派纔以您的研究來命名。2013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張金光《戰國秦社會經濟形態新探》一書。他認爲,秦以後的中國社會就是官紳經濟體制模式,是國家權力支配的這樣一個社會模式。這本書由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出版,當時他找了兩個推薦人:一個是北京大學的閻步克,一個是我。我爲他寫了推薦信,但那時我還沒有把他的書與您的王權主義聯繫起來。我是這樣寫的: 作者的理論概括,把該書命名爲“官紳經濟體制模式”,爲人們理解該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官紳經濟體制模式說的提出不僅可以確立一個新的中國古代社會歷史體系,而且將更新傳統的社會歷史觀和國家觀。它就是一個新的歷史觀,是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一把鑰匙,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意義。 現在,我研究了您的王權主義以後纔知道,他的研究是依附於您的王權主義的,實際上他突出的也是這麽一個東西。2010年,他在《文史哲》發表的文章討論秦至清的社會形態問題時,使用的概念就有“國家權力中心論”。⑧《文史哲》主編王學典在給張教授寫的祭文中這樣評論道: 張老師也做出了一些宏觀歷史判斷:周秦以降三千年,不是民間社會決定國家,而是國家權力塑造整個社會,國家權力是中國歷史的決定性因素,官民二元對立是中國古代社會階級結構的基本格局。 張先生幾十萬字的書,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實際上都是在證實着“王權主義歷史觀”。所以,您是有知音的。我認爲,“王權主義歷史觀”在實踐的領域中還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我相信,將來會有很多人受這種歷史觀的影響去看待與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 從理論的層面看,如果用“王權主義歷史觀”解讀中國歷史的時候,會有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需要面對。比如說,“王權支配社會”,怎麽支配?深宮之中,皇帝就兩隻手,他能滲透到社會中去嗎?他衹有豢養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和支配。那麽,在中國古代,這樣一個官僚體系與皇權是什麽關係?由此我們要回答,官僚階級能不能成立?中國存在不存在官僚階級?如果根據過去馬克思、列寧(В.И.Ульянов,1870—1924)關於階級的定義、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四個方面去判斷,顯然不行。但是,老百姓的土話說得很清楚:“官官相護。”爲什麽會官官相護?因爲有共同的利益。那麽,他們能不能成爲一個階級?還有,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不管“官僚階級”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官民矛盾、官民對立應該說越來越普遍地被人們認識到,這種矛盾甚至超越了過去所謂地主與農民的矛盾。王權主義需要回答中國古代社會是否存在官僚階級,其基本矛盾究竟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還是官與民的矛盾這些重大的理論問題。 從我對您個人的評價來說,恕晚輩不恭,您是史學家、思想家,但不是哲學家、理論家。如果“經驗主義”不是貶義詞的話,您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您的理論來自對經驗的總結和抽象,您最大的優長之處是對歷史的直接洞察,您直覺到了歷史的本質,而不是從哲學的理性分析抽象出了歷史的本質。我爲什麽能體會出這一點呢,因爲我的思維也有這一特點。我也不懂哲學,也不敢做理論研究,也是個經驗主義者。您現在的王權主義理論缺乏純粹的理性分析和內在的邏輯結構,這是需要再去建構和完善的。王權主義歷史觀從實踐和理論上都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可以說前程無限。 劉澤華:你說我不是哲學家,很對;你說我是思想家,我也不敢接受;我接受“經驗主義者”的稱呼。因爲,我寫文章基本上是以史料爲依據的,從史料裏面往外抽象,而沒有按照一個事先設定的理論框架,用演繹法去演繹歷史。我這個理論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一步步的,從研究這個問題得出個結論到研究那個問題再得出個結論。就這樣,從20世紀70年代末一直滾到80年代中期,我纔提出一個“王權主義”理論。1983年,中國歷史學界第一次召開地主階級問題討論會,由《歷史研究》雜誌社、南開大學、雲南大學各出一人組成三人領導小組來主持會議,鄙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人是《歷史研究》雜誌社的龐樸和雲南大學的謝本書。我提交會議的文章是《論地主階級的產生和再生道路問題》。我提出,權力決定了地主階級的主要成員,他們是權力分配造成的。我這個說法一拋出,便遭到與會幾位理論大家的批評,他們說我是杜林(K.E.Dühring,1833—1921)“暴力論”的翻版,早被恩格斯批得體無完膚。我成了杜林的走卒,這讓人怪害怕的。我說,你們最好先反駁我的材料,如果材料都錯了,那我自然就垮臺了。1986年,我又在《歷史研究》第6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從春秋戰國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決定作用》,探討所謂的第一代地主都有哪些人,是怎麽產生的。我當時理解的就是,中國古代社會主要不是地租地產化,“地租地產化”是胡如雷(1926—1998)先生提出來的:我認爲地主階級的主要部分(在社會上起控制作用的部分)主要是通過“權力地產化”形成的。 這裏我再自詡一下,是我最早發現“授田制”這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制度的。1973年,我就在鉛印的《中國古代史稿》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封建國家通過“授田”把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耕耘,農民要負擔沉重的賦稅和徭役、兵役。這些農民都被詳細地登記在戶籍裏,並派有專門官吏管理,沒有任何行動自由,如逃亡被捉住要施以嚴重的刑罰。這些編戶民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農奴。 “授田”是一種社會體系,關涉到賦稅、傜役、兵役、戶籍、行政管理、人身控制。鉛印教材使用之後,我一直留意戰國授田制問題,不斷地積纍相關資料。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了秦簡;1976年,《文物》雜誌第7期公佈了《雲夢秦簡釋文二》,其中《田律》有“人傾芻、槁,以其受(授)田之數”的記錄。看到秦簡中“受(授)田”二字,我十分興奮,這給我此前提出的“授田”提供了鐵證。隨後,我就着手撰寫《論戰國時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發表在1978年的《南開學報》第2期。所以,我認爲,“授田制”這個大的制度是鄙人最早發現的,現在涉及學術史的文章都承認我是最早揭櫫授田制的。授田制的意義在於,它奠定了國家對農民控制的模式。胡適(1891—1962)說:“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⑨我發現了一個大制度呢!我當時寫這篇文章完全靠的是經驗,即資料的積纍。 我的這個“王權支配社會”理論正是在經驗的基礎上作了些概括和總結,但反過來又作爲一種觀念指導我去再認識歷史,但做得有限,年齡不饒人,今後更難了。我說的“經驗”,也包括古今人的對話。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死死盯住“歷史”的人,我有現實關懷感。你們看,這些年的土地變動說明,政治支配遠大於經濟意義。這些年私人資本有明顯的發展,經濟學界不少人提出“官僚資本”、“權貴資本”“權力資本”等等,都是從權力爲切入點分析問題。從更廣泛的角度說,他們與我的思路是否有相通之處呢?我認爲應該說是有的。中國歷史上的貪污、特權一直讓人心煩,有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這不是道德品質所能解釋的。究其原因,我認爲最根本的是“權力支配社會”帶來的必然現象。 至於“官僚政治”“學人政治”這些概念,我是不用的。講“官僚政治”,比較好的是王亞南(1901—1969),著有《中國官僚制度研究》一書。在這本書中,他講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與民的矛盾;剛纔你提到的問題,在王亞南的書中已經提到。“學人政治”最早是由錢穆(1895—1990)提出的,近來又有人提出“士人政治”。是的,王權離不開官僚、學人、士人,但我不用“官僚政治”“學人政治”等概念,因爲他們不是獨立於王權與王權並列的權力系統,而是附屬於王權體系的,更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在王權社會中,大致說來是“王—貴族—官僚—農民”這樣一個序列組成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結構中,有人提到的王權與農民聯合起來鬥爭官僚,或農民與官僚聯合起來反王權,對此我不否認,但這些沒有說到底。把一姓的王反掉了,接下來是什麽?難道不是另一姓的王再支配社會?當然,不是一講王權支配社會,好像其他問題都沒有了,社會上還有很多其他問題;權力也不是在任何意義上統統支配經濟。一個理論的概括衹能是最高的概括,而歷史的豐富多彩性不是任何一個理論都能概括進去的。我認爲,衹要抓住其中的主要之點,而這一點具有較多的解釋面,就可以了。“王權主義”衹是解讀中國歷史的一個角度,並不排斥其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解讀方法。我想,這正是我在治學中的經驗主義的態度與方法。 注释: ①[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第433頁。 ②謝地坤:“文化保守主義抑或文化批判主義——對當前‘國學熱’的哲學思考”,《哲學動態》10(2010)。 ③劉澤華:“前言”,《中國傳統政治思維》(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④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文史哲》4(2013)。 ⑤劉澤華:“王權主義:中國文化的歷史定位”,《天津社會科學》3(1998)。 ⑥劉澤華:“除對象,爭鳴不應有前提”,《書林》8(1986)。 ⑦劉澤華:“史家面前無定論”,《書林》2(1989)。 ⑧張金光:“關於中國古代(周至清)社會形態問題的新思維”,《文史哲》5(2010)。 ⑨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一集,第2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