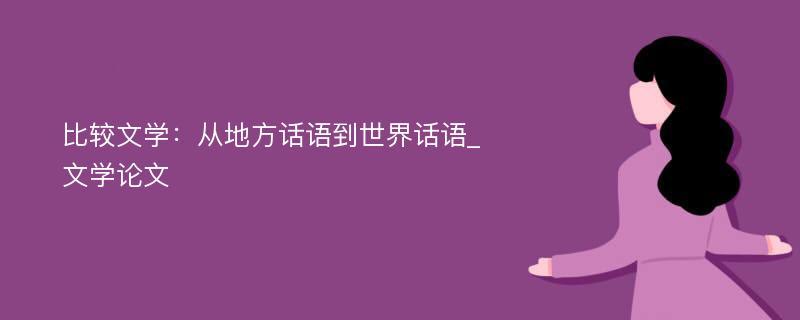
比较文学:从本土话语到世界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比较文学论文,本土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随着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人文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和震动,我们的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界,乃至整个文化学术界,有关“失语症”的焦虑日渐滋长,并由此引发了关于话语问题的热烈争论。人们好象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在西装领带和牛仔服取代了中山装、可口可乐易拉罐取代茶壶茶碗、肯德鸡和麦当劳夺走饺子馆生意的同时,我们的学术话语和日常语言也早已被西方“强奸”了,我们本土祖先的语言传统正在消解和被人遗忘,我们所说所读所写,几乎全是上一世纪闻所未闻的外来东西。
不要提让许多人望而生畏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一套时髦,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又同我们的李白杜甫有何干系?我们是怎样将这些进口的“强势话语”之标签,未加思索地硬贴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现象上的?经过这种反思之后,所谓失语症的危机意识,已经可以和上个世纪末的那场“自强保种”的民族文化危机相提并论了。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究竟如何看待这种话语之争呢?
笔者曾提出,面临冷战后全球文化对话的新局面,比较文学研究有可能发挥建构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先锋作用[1]。文学人类学或比较诗学这类命题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寻找一种足以指称和概括各民族文学经验的世界性话语。有没有可能和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元话语,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难题。从文化对话的现实看,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从没有这种元话语到开始创造这种元话语的历史转变过程之中,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认可它,超越种族、国家、地域、政治等各种界限的世界性话语正开始萌生,人类再造巴比伦塔的伟大工程业已揭开了序幕。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看,各民族文化对世界性话语的贡献是极不平衡、也不平均的。因此,反抗西方霸权话语宰制的呼声此起彼伏。在新近流行于欧美大学中的英文著作《后殖民研究读本》里,派瑞(Benita Parry)的《当今的殖民话语理论的问题》和穆德鲁鲁(Mudrooroo)的《白人的形式,本土的内容》两文,便分别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体现了这种思考。后者作为澳洲原住民的代表,将原住民的本土文学称为“第四世界”的弱势话语,要求在英文写作的白人的形式之外,保留本土语言的文学表达形式[2]。与此相应,台湾学界近来也提出台湾原住民文学应在台湾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在充分注意这类呼声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多元文化的时代自然要求众声喧哗的局面,但是交流与沟通是以相互对话和理解为前提的。在话语权上各自为政毕竟有碍于对话与理解的时代趋势。弱势话语与强势话语、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的冲突只能按照语言行为的自然大法——约定俗成的原则去由历史来解决,因为任何从个人本位或国族、地方本位的立场上所提出人为话语权要求都只有适应了人类沟通交流的需要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否则就难免沦为一厢情愿式的自恋行为。
当然,这里也存在文化对话过程中局部的“入超”或“出超”的忧虑。关于西方话语在文化交流中大大“出超”的诘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考虑答案。
首先,西方话语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在其历史发生发展过程中自然吸收许多非西方的话语成分,并经过调适而容纳于自身。关于“零”的概念来自阿拉伯文化,而晚近在宗教学、人类学方面使用频率极高的“图腾”,“马那”等均直接取自非西方的原始文化,哲学方面的“道”、“阴阳”、“瑜珈”、“禅”(zen)等皆为东方概念之音译,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也正是有了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西方话语才会在文化对话中较那些相对封闭,隔绝于世的本土话语更具有优势和竞争力。
其次,西方话语是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而抽象化程度高、理论思辩性强作为西方语言文化的突出特征也必然充分体现在其理论话语中。文学人类学所取法的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产生于西方,而且恰恰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而兴起,但它并未蜕变为殖民主义的御用工具,反而率先倡导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相对观,这说明理论话语本身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可以是中性化的,可以为不同的文化所共享共用。在话语权问题上,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自身的矛盾困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他们一方面激烈要求消解西方中心的认知暴力,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寄宿”于西方主流话语之中。如斯皮瓦克(G.C.Spivak)所说:“后殖民知识分子非但不能拒绝他们所批判的西方话语,反而需要亲密地寄居其中。”[3]正象我们不能为了抵制西方话语霸权,就必须放弃公历纪年以及月与星期(礼拜)的历制,回到六十甲子的进位制;放弃每周七天的礼拜制,回到祖先的旬(十天)制一样,在输入学科、理论成果方面也不能因噎废食,退回封闭保守的“本土话语”窠臼中去。我们能够只用司空图、严羽的方式去讨论诗或严守金圣叹、李卓吾的本土方式去批评小说吗?
其三,本土话语的本土性其实也是相对的,同西方话语一样不是僵固不变的和绝对纯粹的。以时间而言,似乎越古老,受外来影响越少,则本土性也就越强。那么,文明以来的话语不如史前时代那样纯粹,而山顶洞人的时代又不如北京猿人的时代。我们现在当作本土话语的一些基本词汇,如世界、众生、真谛、因缘、慈悲、六根、一刹那等,其实都是汉代以来佛经汉译所带来的印度词汇。一部《佛学大辞典》收词三万多条,大部分是古汉语所受容的印度赠品。倘若真要以本土话语为封闭不变的正宗嫡传,那么我们现在恐怕已经无法讲话了。撇开时间的因素,从空间的界限看,本土话语对于当今中国人而言,也还有细究的必要:儒家的不同于道家的;鲁国士大夫的不同于楚国狂人的;官方雅言不同于十五国风;汉民族的不同于《格萨尔王传》或《福乐智慧》的。除了虚怀若谷,兼收并蓄以外,任何一种自我本位的取舍都会重蹈狭隘和排外的复辙。
其四,确认吸收西方理论话语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土话语或对外来的东西毫不防范地任其自然生灭。从人类学的立场看,文化对话交流的“涵化”结果总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其间要经历选择、剔除、对接、转移、再阐释等一系列复杂的运作过程。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精神促使我们注意如何以批判分析的态度接受西方话语,并强化“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的自觉意识。人类学所说的“再阐释”指文化变迁过程中,“把旧的意义附属到新的因素上,或用新的价值改变旧有形式的文化意义”[4]。近有学者经过权衡,提出了“中国诠释学”的四种可能的选择方式,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
1.可以对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及其对诠释和理解的问题之贡献引以为鉴,从而系统地处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诠释问题。
2.也可以强调中国诠释系统之“中国性”,而这种“中国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但这种策略似乎对拓展比较话语无甚俾益,使中国话语沦为不能与外来文化沟通的神秘他者。
3.也可以将中西传统并置。但如此并置可能会让支配性的一方扭曲了“他者的话语”。
4.“相互的陌生化”(mutual defamilization),亦即经常对我们的构建方法提出质疑。把所谓“中国诠释学”看作一种质疑既存的支配性话语范畴的工具:“让中国通过现代的话语(话语这种概念本就是现代的)来在某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进入现在,从而质疑西方话语实践中所容许知识生产及播散的过程”[5]。
朱耀伟所主张的办法是第四种。为什么呢?他从福柯那里了解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觉得“要重建文化,我们得要有自己的话语。我们自己的话语却得借用西方的声音,因为合法性是话语的条件,也是由主导话语所支配的条件。所以要为自己发音,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借用西方话语。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话语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发音,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话语,拓立出自己的话语空间”。笔者以为,既然“自己的话语空间”还要从借来的西方话语中去“拓立”,这不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吗?或许只有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宽容对话而不是故意抗衡的心态,才能在话语问题上摆脱非此即彼的矛盾困境吧。
综合以上分析,本土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关系呈现为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透过本土话语去获得人类学家所说的“地方特有的学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此种“地方特有的学识”放置到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评价,这就意味着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的调适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经过这种对译、沟通、再阐释的往复过程,世界话语的胚胎才能在多元对话的边缘空间中诞生。警惕西方霸权话语在对话中的宰制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坚守本土话语的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
注释:
[1] 拙作:《文化对话与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 派瑞:《当今的殖民话语理论的问题》,阿什考夫特等编《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罗特累齐公司1995年,第36—44页。穆德鲁鲁:《白人的形式,本土的内容》,同上书,第228—231页。
[3] 斯皮瓦克:《美国人的构成、英语教学与文化研究的未来》,《新文学史》第21卷4期,1990年秋季号,第794页。
[4] 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文化动力》(Cultrual Dynamics)纽约,诺福公司1964年,第190页。
[5] 朱耀伟《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台北骆驼出版社,1994年。“话语”一词该书中译为“论述”,引者据大陆习惯改称“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