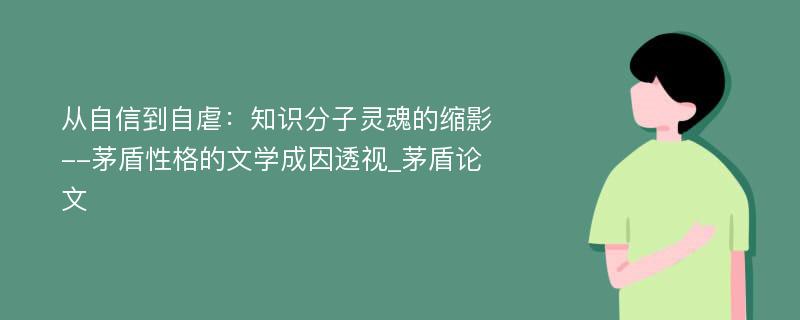
从自信到自虐:知识分子的灵魂缩影——茅盾性格的文献发生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缩影论文,知识分子论文,透视论文,信到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路》自序中说:“幼年秉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至今未敢怠忽。”① 周扬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对茅盾的看法:“我和他长期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我常常感觉到,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不但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够,对茅盾的认识也是不够的。尽管天天在一起,有一段……毗邻而居,但是我也不能很深地认识他。……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完全认识了他。”② 这两个材料似乎都在说明茅盾的个性是“谨言慎行”的,但从文学批评及其相关材料来看,茅盾并非一直如此,他有一个从张扬到含蓄再到封闭的个性发展过程,其人格也由单纯渐趋矛盾。
1920年,茅盾因勤奋好学而被任命为《小说月报》主编,他提出的条件既有不顾馆方利益的“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也有自视甚高的“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初出茅庐的茅盾似乎还没有很多的社会经验,即便是在变成铅字的文学批评文字当中,也时常露出他的峥嵘。他在《答钱鹅湖君》中“劝钱君赶快去请医生治治神经错乱病罢”,③ 在《“半斤”VS“八两”》中“要把郭君送给我的几句天才式的谩骂——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及其他——一一璧还。”④ 他甚至还发表了一篇今天看来尽现其自负与浅薄的《杂谈》,文中对吴宓、洪深等人担任“中国影片制造股份公司”悬赏征求“影戏脚本”活动的特聘评判员表示莫名其妙;他说:“我最不懂的,吴洪两位在西洋所受的文学的训练,难道也包括影戏术么?我只听得前年美国影戏公司请西班牙大小说家伊本纳兹做一篇小说以便他们排为影戏——注意,伊本纳兹此次是失败的;却不曾听见什么影戏公司请某某文学家做‘脚本’的评判员!我竟不知文学家的批评眼光还可以应用到‘影戏术’的批评上去!我竟不知文学的批评和‘影戏术’的批评是有共通点的!哼!”⑤
这真可以说是一篇奇文,尽现一个个性张扬的青年无知时的无畏。他与鸳鸯蝴蝶派及创造社的论争虽有文艺观念冲突的根本原因,但少年气盛,不计后果肯定也是掺杂其中的重要因素,结果他因《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点了《礼拜六》杂志的名而丢了《小说月报》主编的职位,这可以说是他在进入社会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挫折,但这次打击并没有使他收起自己的锋芒,他仍会寻找机会平衡自己。1925年,茅盾参与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大罢工活动,虽然在大的方面说是党的部署,但就茅盾本人来讲,却未必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潜因。罢工胜利让茅盾感觉到了党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但绝没有想到这种力量也能使他受到重创。《蚀》三部曲本是为了将自己从幻灭之中拯救出来,但那种消极的情绪却与革命者的鼓吹完全悖反,结果他受到了群体的围攻。如果茅盾此时真正做到了谨言慎行,恐怕他既不会写《幻灭》、《动摇》、《追求》,更不会写那篇引起更激烈反应的《从牯岭到东京》,那些给人以口实的心迹表露,试图以申辩与诤言的方式求取理解的做法,带来的却是适得其反的结果。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自《从牯岭到东京》以后,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舒展的精神自传式文体从此不见了,即如《〈时代的记录〉后记》虽还有个人的精神印迹,但所凸显的不是个人的情绪而是具有情绪特征的对时代的理性认识。
茅盾也许就是在与“革命文学”阵营的冲突中懂得了应该谨言慎行的道理。他不参加那些飞行集会之类的活动,却只是“自由”行动,而不发表声明;他要发表反对文学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见却要和党的权威人物商量或得到党的文件许可。他的这种姿态应该与他的脱党及不被党重新接纳不无关系,也许就是被党抛弃的命运及被集体围攻的经历给他的心灵留下了久久难以复原的伤痕。
但是茅盾并没有就此完全改变自己,《怎样编制“文艺年鉴”》一文又隐隐现出了茅盾昔日的影子,他对《中国文艺年鉴》的编辑者杜衡和施蛰存说:
第一,“文艺年鉴”是“编年史”的性质,不应该选录作品,即不得已而选录作品,就应该实居于“附录”的地位,不能比本身大,甚至于大过数倍。
第二,“文艺年鉴”的本身应该是文艺各部门的详细论述,凡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理论文字,翻译等等,都要独立一章,详细论述;像该《年鉴》的《鸟瞰》之类的论文只能算是各专章前的一个“绪言”。又关于旧文学的整理,旧的新发见等等,该《年鉴》中并无一字提及,可是这也应该在“年鉴”中占独立一章的。
第三,作家著作索引及书籍编目,才算是“附录”,然而这“附录”必须详备,尤必须每书有一则简明正确的“提要”!
第四,一年内出版的文艺性期刊,不论大小及出版久暂,都应该编目著录,并且每种加一“提要”,说明该刊物的旨趣及重要内容。
第五,国内的文艺团体,不论大小,不论新旧,都应该详细调查,照实记载。⑥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茅盾没有署名。即使是有话要讲,即使不懂常识的杜衡与施蛰存是左翼阵营攻击的对象,但对文艺年鉴问题有充分自信的茅盾还是把自己的面孔遮了起来,不给对方面对面反驳的机会。翻读茅盾的批评文章,且不说1920年代与创造社郭沫若的冲突,单就革命文学论争以后来讲,他指名予以批评的实在不多。指名言蒋光慈的缺点,应该是服从集体的表现,因为在对“革命浪漫蒂克主义”的清算中,蒋光慈不仅是批判的对象,还被开除出党;点名指责周扬,却是茅盾想兼顾“两个口号”,可周扬却不理会他的苦心,终于在激怒了鲁迅的情况下也激怒了茅盾,惹得他大讲周扬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及“反装大门”的错误。茅盾是在双方情绪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才因编辑做手脚一事光火起来,这该是其个性展露的一个例外,而更经常的,他总是保持一个低调的状态,不仅在参与论争时总有一种勉为其难的味道,而且即使参与,他也避开锋芒,写两篇文章露一下脸了事。茅盾遮起的半张脸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慎行”的具体表现。至于“谨言”,本与“慎行”密切联系,但在1946年却有典型表现。
茅盾在题为《也是漫谈而已》的文章中就文艺问题谈了一些个人看法,但在头尾处却竭力说明文章是设计好的擂台,“我们相约去打这擂台”,以使开场锣鼓之后不冷场。⑦ 茅盾在这篇文章中就民主革命文学的分期、思想斗争、统一战线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尤以他对“左联”评价问题引人注意:“雪峰说:‘左联自行解散,于是开始清算着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好像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乃在那时方始清算,而且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好像是依附了‘左联’这机构乃始有根可托,这恐怕也未必然。事实上,‘左联’未解散前,便已经屡次和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作斗争,‘左联’解散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并未绝迹——这一切雪峰都亲身经验过,因而我相信这里的‘于是开始清算’不过是措辞上的失检。但恐读者不明过去历史而有误会,所以带便提一笔。⑧”
其实倒未必是“带便提一笔”,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他虽然最初骑墙,却终于也进入一“派”,茅盾恐怕“有误会”而细加辨明,隐隐有摆脱干系的味道。作为左联的实力派作家及有威望的文学领导者,曾与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作过斗争,那么他当不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中的一员,而左联解散后,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并未绝迹,可见也非领导者不力,此一番解释既为自己开脱也为当初的左联领导开脱,显得周到而有心机。富有社会经验又历经政治磨练的茅盾正是在字句的推敲中才清晰地显现出了他谨言慎行的个性特征,两次要求重新入党均未获准,他想留在延安,却被派往重庆,而后又在政局的巨变中被派往远离组织的香港,这一切都分明给他一种要不断接受考验的不被信任感,以及因这不信任而产生的被抛弃感,他只能努力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保持一致,更加勤奋地工作,谨小慎微地保护自己。
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1942年,因战事爆发,茅盾离香港至桂林,短暂停留之后又去了重庆,受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欢迎,茅盾也与之建立了一种很客气的关系,结果便在“我们自己的朋友中”,“有了微词”。当叶以群将这些闲言碎语告诉茅盾时,茅盾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为了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让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⑨ 那些微词一定又让茅盾想起了当年那些“朋友”从政治立场对他进行的批判,他的回答也似乎又有了申辩的味道,但终于没有落到纸上。很快,他便写出了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清明前后》,焉知这政治题材的选定仅是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而无个人自我保护的隐衷?已被国民党认定有亲共倾向的茅盾其实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向共产党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绝不想因人事的关系而重蹈被称为“不长进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覆辙。
茅盾便是在这种政治的微妙处境中渐渐变得“老练”、“成熟”,他的个性变得谦逊、诚恳、谨小慎微。1946年,在他已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四处演讲时,其开场白总不忘说几句自谦之言:“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各位先生面前讲话,觉得十分荣幸”。“刚才主席对我的夸奖,我实愧不敢当。我今天讲的题目大了一点,恐怕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胜任的,也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就我所有的感想,拿来讲一讲,讲得对不对,还请各位批评指教”。⑩“今天有机会在各位面前讲话,是非常荣幸的。我干文学工作虽已多年,可是修养很浅,对于今日预备讲的题目不敢说有很好的意见贡献给各位,但只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和感想,拿出来给大家参考罢了!”(11)
这看似礼貌性的开场白,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个表现,这种收敛的处事风格与其演讲内容的个人见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顿显其谦谦君子之风。进入政界之前的茅盾尽管从个性表现上有一个从张扬到收敛的转变,但总体看来并不失正常的人格,但在进入政界以后,其人格却产生了病变。
1950年起,作为作家的茅盾终于让位给作为政府高级官员的沈雁冰,此时他已无法像当年那样白天搞政治,晚上搞文学了,他的白天和晚上都交给了政治,甚至思想的须臾离开都会使他陷于被动。开始他还对自己远离了文学充满了愧疚,在各种讲话中常见他表述内心的不安。有时他说:“我自己呢,过去也干这一行,可是最近整整一年不但没有‘创’什么‘作’,就连各位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也读得不多”;(12) 有时又说:“说来实在很惭愧,各位提到的作品,大多数我都没读过,空空洞洞要来发议论是很困难的”。(13) 然而1952年因给白刃《战斗到明天》作序而不得已的检讨,(14) 却已让他意识到了政治的凶险,所以他感觉应该做出一种姿态“检查自己的失败的经验”,于是又有了《〈茅盾选集〉自序》,全面检讨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给自己订了一个生活计划:“漂浮在上层的生活必须赶快争取结束,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回到我的老本行。”(15)
想“回到老本行”的愿望既有他对文学的眷恋,也与他意识到政治的险恶有关。茅盾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能够感觉到政治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能量。政治因素的参与,会使文学上的论争充满激烈斗争的火药味,但其后果不过是在口舌之快中含沙射影,他会给人的心理带来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而若政治权力参与进来,则不但从此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会累及自身性命。频频的政治运动,使茅盾不知如何既能维护人民政府的威望,又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曾两次向周总理递交辞呈,却未获准,便尽力适应形势,参与各种运动。1954年,他终于发表了有关《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意见,但其中的意味却可作多种理解。他引用郭沫若的话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解剖:
刚才郭主席的发言里有一段话,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反复体味,痛切反省。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箧一样,上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行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
这段话,在郭主席,是自己谦虚的话;但在我们,却不能不说是真实的写照。拿我自己来说,我在青年时代,由于崇拜庄子,就企慕魏晋,由于企慕魏晋,就爱好骈文,“五四”前一二年,我也一度为安那其主义所吸引,——这大概和我早些时的崇拜庄子有点关系罢?“五四”时,我受了《新青年》的影响,自然也受了胡适的文学思想的影响。直到距今二十年前,虽然在政治上我已经认清了胡适的反动的本质,但对于学术思想上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的本质,我还是茫然无知的。因此在一九三五年我应开明书店邀约,编一本所谓《红楼梦》话本的时候,我在前面写了所谓的“导言”,就完全抄引了胡适的谬论。我不讳言,那时候,我做了胡适思想的俘虏;我尤其不敢大言不惭地说,今天,我的思想中就完全没有胡适思想的残余了!不敢说就没资产阶级思想了。……我觉得,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学得好,就好像是在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旅馆商标的大脑皮质上又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标语;表面上看看,有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经不起考验;一朝考验,标语后面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商标就会冒出头来;如果是从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隙缝里钻了出来,那就叫做露了马脚,那倒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最危险的,是顶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标语而冒出来;那就叫做挂羊头卖狗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足以欺世盗名!我想,我们一定要有勇气来反躬自省,从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好好学习,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来肃清我们大脑皮质上那些有毒素的旅馆商标,而不是在这些旅馆商标上加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我们必须改掉那种自欺欺人的作风。我们要反躬自省,老实学习,这才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敲起警钟的婆心苦口!(16)
这段文字有一种意义上的复调,前半段似乎是自我解剖,后半段却在抨击某一类人,虽然茅盾在后面的文字中以作协主席的身份替“《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可是却又强调郭沫若的这样一段话,似乎颇有开脱《文艺报》的意味:
在广泛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一问题上,郭主席指出,要“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并提出了十六字:“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在“加强扶植新生力量”这一问题上,他指出,“在培养之中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不要使爱护发生偏差,我们要善于爱护”。他又着重地指出:“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有的朋友在发言中透露了这样的意见:只要对于青年批评那就是压制新生力量……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问题作了片面的了解。青年当中还有些坏的成分,这虽然是旧社会的遗毒使然,但我们不能置之不管。假使说既要扶植新生力量,那就连不良的青年或青年的不良倾向也不能矫正了,那应当说是相当大的错误”。郭主席的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切铭记。奉为行动的指南。(17)
茅盾引郭沫若这么多话来借题发挥,看来他的确心有同感。也许在他的内心当中对这种小题大做式的“运动”颇不以为然,但他又需有一种姿态,于是他的话便充满了内在的冲突,在结构上也形成了明显的反讽。表面上看,是批胡适,支持新生力量,骨子里却反对挂羊头卖狗肉,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欺世盗名之徒和青年中的不良倾向,隐隐可以感觉到里面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茅盾自有其精明之处,他本来是想表达自己的意见,可却借用郭沫若的话去表达,自己则因此遮起了半张脸,这是一种明显的自我保护,以至自我保护成了他在1949年之后最主要的个性特征。
1955年,茅盾向周恩来总理请创作假,这当然有他圆自己创作之梦的企图,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他要以创作逃避政治的隐衷。在已无望创作的情况下,他又会以生病逃避他不能理解的批判运动。1957年8月28日,他致信邵荃麟说:“最近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参加,原因是‘脑子病’。”“病情是:用脑(开会、读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胀疼;于是至少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他们好像不相信”,“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实在不能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18)
这是一封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的信,其中有茅盾的智慧和狡猾。不是不写,而是生病了不能写;病好了自然就可以写。茅盾那些每每滞后的政治表态文章或许都有这类“智慧”的托词藏在后面吧,所以我们时而会看到他义愤填膺的批胡风、批修正主义的人情味,时而又见其精警地批那些“应时”、“应景”的文章,(19) 批评把鲁迅作品“神秘化”“深奥化”的作法……(20)
政治让茅盾感受到了一种恐惧,所以他时时小心,事事在意,绝不让人抓住什么把柄。1958年在长春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他以《文艺和劳动相结合》为题发表了讲话,在谈到文学技巧问题时,他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茅盾认为古希腊诗人荷马善用新鲜比喻,他曾经用“苍蝇一样的勇敢”来形容士兵的勇敢,从而以“苍蝇见了糖或血就群集飞来,赶走了又回来,坚韧得很”的品性表现了战斗轮番进行,而战士绝不气馁的战斗精神。这个新鲜的比喻“使人看了就会发生活泼泼的联想”。讲过之后,茅盾却“郑重声明”:“我不是说,今天我们还要用苍蝇来形容勇敢的战士,今天这样形容就很不妥当了。”如此郑重是因为过去有过误会:“五六年前,我到某处讲演,也引过这个例子,后来就收到不少的信,说我把苍蝇比战士是诬蔑了我们的战士。这真是张冠李戴,十分冤枉。我明明是说古代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此形容士兵的句子,证明技巧来自生活,并不是用苍蝇来形容我们的战士。也许是听错了吧?我的话,土音很多,常常要被听错。所以我在这里特地多说几句。”(21)
一个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却要为一个比喻而多费口舌,可见当时社会中那种政治的火药味有多么浓烈。也正是这样的政治环境促使茅盾从自谦走向了谦卑。1955年,在《关于文学创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中他还能够说:“上次已经跟同志们谈了谈关于人物性格刻画的问题,现在同志们又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我再谈一下,我个人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榨不出油来了。今天只能根据同志们所提的问题,讲一讲自己的经验,供大家参考。”(22) 到了1962年,他的口气却是:“听到周扬同志内容丰富的发言,我感到有很多启发,才有胆量讲几句。”关于题材问题“周扬同志讲得很好,我没有新的意见”。(23)
但是,即使他以如此谦卑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茅盾最终也没能逃过“中间人物”论的错误,不久之后,他便因毛泽东指责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而被免去了文化部长的职务,他那枝书写了四十多年的笔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韦韬曾问他为何不对最新指示发表意见,茅盾说:“我是不写这种文章的。一个人的信仰,要看他一生的言行,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我不喜欢赶浪头,何况我对‘最新指示’有的还理解不了”。(24) 一向跟随时代潮流的茅盾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他那些滞后的表态也许可以从这句话里得到一定的解释。待他离开了政治岗位,便已不必被裹在不理解的浪里跑了。他以沉默表达自己的不理解,又以沉默进行自我保护。甚至在他的日记里,也难以找到他对时局的看法,这种彻底的自我封闭,将茅盾的“世故”以及人格的扭曲变形清晰地折射出来。
韦韬曾这样评述茅盾的日记:“爸爸的日记是流水账式的生活日记,很少在日记里发议论。‘文革’前还不明显,有时还能读到他对文艺问题的感想。‘文革’开始后,爸爸的日记里就几乎嗅不到政治气息,所有社会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打倒’刘少奇,‘二月逆流’,‘砸烂公检法’,‘一月夺权’风暴,等等,在日记上没有一字的记载,似乎爸爸是个与世隔绝的局外人。……也许这就是爸爸对‘文革’的态度:我怀疑,我不理解,我需要观察,所以我沉默”。(25)
不向外人展示内心的想法,这可能是逃避现实风暴的有效手段,这种极端的自我保护措施将自己置于一个纯粹的生存状态上,由此他的生命也再无光芒。随手翻开他的日记,其记载不外是日常的饮食起居,那种客观的记述,甚至连形容词都吝于使用,请看他在1966年6月12日记下的日记:
(晴,多云,三、四级北转南风,三十一度,十七度)今晨四时醒来,加服水药一小杯,六时行又醒,即起身,做清洁工作如例。上午阅报、《参资》。中午亦未小睡。下午阅书。今日为星期,桑、小曼及两孩均来吃晚饭,七时半归去。晚阅电视至九时,服药如例,但是十二时后仍未入睡(因阅书),乃加服S.一枚,约半小时后入睡。(26)
这样的日记无任何心迹表露,既无阅报的感想,也无阅书的内容,把一个以自我封闭方式进行自我保护的茅盾呈现无遗。日记里藏起的心理内容在他的书信里有所表露,但现有的资料却无1964—1969年间的内容。我们无法确证在资料空白的几年间茅盾有过怎样的情绪起伏,但1970年我们在书信里见到的茅盾却已不再“矛盾”而是非常“世故”。也许是现实政治的迅疾变化练就了他一双洞若观火的眼睛,也许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已使他下意识地产生自动的警觉,那些可笑又烦琐的劝说,活现了一个“在共和国旗帜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老知识分子可怜的面影”。(27)
韦韬发现,茅盾“写信很讲究策略。除了称‘病’之外,对于不了解的人或比较生疏的朋友,他常抄几句报纸上的话;对于比较熟的朋友就不抄报纸,但也不谈政治;只对少数亲戚,有时在信中发发牢骚,但这牢骚也不涉及大的政治问题”。(28)
于是我们最先看到了1970年1月26日致杨建平的信:
杨建平同志: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你的来信转了几处,昨日方到我手中。你我素不相识,承你写信,不耻下问,我很感谢。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些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极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
收信人的身份无从查考,但显然为茅盾所不熟悉的人。这封留着鲜明时代特色的信以谦虚到对自我进行完全否定的姿态表达了老作家的拒绝之意,但却显示出一个很革命的个人形象。已退出政治舞台的茅盾对于陌生人似乎还想保留自己与时代同步的“革命者”形象,可今天读到这封信却觉颇像上演着一出历史的滑稽剧,一个追随时代但又对时代有自己理解的文学家、批评家如何竟至于将自己变成了鹦鹉学舌的老人!笔耕一生的茅盾尽管在政治与文学、个人与集体、权力意志与个人理解的选择中备受煎熬,徘徊矛盾,但总还守住了一个边界,没让自己彻底丢失,可这封信映出的茅盾却自甘浅薄,在戏弄历史时代的同时也在污损自己。这是一种弥漫的悲哀,映射出政治与权力如何戕害生命戕害灵魂,一个人正常的人格就在这种戕害中扭曲病变,以至失了高远的境界,只把眼光逗留在卑琐的个人世界里。
他对单演义说:“为大作《鲁迅在西安》题字或署鉴,请恕不能遵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指责事项之一,盖突出个人,乃当时所严厉批判,亦今日所严防回潮之一事也”。(29) 他对沈楚说:“单公向你索取我的信札拍照,我仍以为只能把有关学术的给他……我以为单公主观,他把我的信拍照是他所谓‘喜欢’我的手迹,但流传出去,又变成我在设法自我表现,个人突出了。爱我适以祸我。也曾对他说过,无奈他终于不理解,那也没法,只可少和他接触了。”(30) 他对胡锡培说:“现在趁早凉写这封信,是再次阻止你托人买广柑寄来。因为虽是你的诚意,但传说开来,以为我那么享受,从四川弄广柑来,这不是您的一片好意反而于我不利么?”(31)
也许上述材料只是茅盾个性的一个侧面,而非他的全息影像,但是即使这一个侧面也足以见出他自我压抑、小心翼翼的精神状态。翻读茅盾全集中的“中国文论”部分,1949年前的文章除国民党明令禁止的主题外(如向西方大众介绍左联)极少有未发表者,而1949年后未及时发表的手稿却比比皆是,以至在搞数据统计之时,不知该按写作年份还是按发表年份归类(如《夜读偶记》的后记写作于1959年,发表于1982年)。这些未能及时发表的文稿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的是茅盾在跟随政治形势时的窘迫,墨迹未干,形势已变,若想不给自己带来凶险,便只能不让它面世。但不管怎样,他那时的小心翼翼或自我保护还有一种从大事上着眼的气魄,而后来竟至于斤斤于各种各样的小事,其人格的卑琐已在其表达中赫然显现,以至于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他直到临终前才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希望身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愿,除了他的信仰,是否也有自我保护的意思藏在里面?非党的身份保护他在十年文革中免遭肉体的伤害,为了保全生命,他只将信仰留在心底而躲在“统战”的保护伞下,直到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对他有所伤害了,他才让信仰以具体的形式附于他的身体。
当一个新的时期进入历史的时候,茅盾已经老了。他将自己称作“退伍的老兵”,(32) 虽然他仍能以一种睿智看出郭沫若是“我国文坛上的彗星”(33) 而非恒星,虽然他在晚年以回忆录的方式为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然而他终未能冲破已形成惯性的思维方式,直到1979年6月,他仍坚持说:“十七年中,文艺上的大小事情都是在毛主席指示下进行的……如果把十七年说成已经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那就会把人们的眼光指向毛主席,这是全国人民不许可的。所以我以为这样的议论不可扩散。”(34)
从人格特征角度来说,茅盾从自负到自信再到自谦、自卑以至自虐,有那么一条自我压抑的清晰线索,而构成他思想、感情及行为的人格模式也便因此可以“矛盾”名之。在兴趣与需要、志向与信念、价值观与人生观之间,他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主选择,又因为他在政治上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以至于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从性格上讲,“他既不能像毛泽东式的典型政治文人那样富于极度的冒险精神,用历史的眼光去对待政治上的每一次大变动;又不可能像郭沫若那样既能功利而潇洒地进入政治领地,又能戏谑而无忌地挥手告别政治。因此,他的一生只能在忧郁的精神炼狱中苦苦熬煎”。(35) 直到晚年,还在给友人的信中自责道:“白吃人民粮食,忽焉遂至八十,中夜内疚,抚膺自悲。……唯有抓紧学习,改造世界观,以冀风烛余年,少犯错误。”(36)
茅盾的自责与自悲,其实是戴着面具的“自我”在惩罚自己。他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却终于未能实现自我价值,不但丢失了自己的志向,甚至丢失了自己,这样的命运如何不是抱负终成泡影,一生仅为稻粱谋?忆起如此“不足取”的一生,又如何能不“百感交集”,又“百无聊赖”?那种心有不甘的叹息,充满了悲凉,也充满了无奈。茅盾的一生,便是一代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命运与人格的缩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与权力如何在折磨他灵魂的时刻,铸造出了奴性与自卑,又使他们从自卑走向自虐,灵魂的悲剧在夹起尾巴做人的表演中显得惊心动魄又鲜血淋漓。
注释:
①茅盾:《我走过的路·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1页。
②周扬:《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茅盾研究丛刊》1983年第1辑,第5页。
③《答钱鹅湖君》,《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4月1日第33期。
④《“半斤”VS“八两”》,《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9月1日第48期。
⑤《杂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7月11日第43期。
⑥《怎样编制“文艺年鉴”》,《文学》1933年10月1日第1卷第4号。
⑦参见《也是漫谈而已》,《文联》1946年2月25日第1卷第4期。
⑧《也是漫谈而已》,《文联》1946年2月25日第1卷第4期。
⑨茅盾:《我走过的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493页。
⑩《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3月24日在广州三个文艺团体欢迎会上的讲演》,《文艺生活》1946年4月10日第4期。
(11)《文艺修养——四月十九日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讲》,《文学修养》,广州国华书局1946年6月版。
(12)《文艺创作问题——1月6日在文化部对北京市文艺干部的讲演》,《人民文学》,1950年3月第1卷第5期。
(13)《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1950年3月在<人民文学>社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群众日报》1950年3月24日。
(14)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未经茅盾本人的同意就刊登了《关于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的检讨》。
(15)《〈茅盾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2年4月版。
(16)《良好的开端——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结束语》,《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17)《良好的开端——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结束语》,《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18)1957年8月28日致邵荃麟信。《茅盾全集》第36卷第411页。
(19)参见《在全国省、市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未发表过,《茅盾全集》第24卷,第390—394页。茅盾在文中说,他读到一篇小品“名为《作品发表的秘诀》,指出有些业余写作者善于揣摩迎合,专写‘应时文章’和‘应景文章’。但愿这不是普遍现象!可是也不能太乐观。那篇小品文,自然有点夸张,然而摹仿的风气不能不说是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在《葡葡熟了》以后就出现过不少什么什么‘熟了’”。
(20)参见《如何更好地向鲁迅学习?》,《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号。茅盾在文中指出有些人是以“钻牛角尖”的方式来阅读鲁迅的,“忽略了整篇主要意义而专门注意个别章句背后隐藏的‘象征’,这样做最好的结果,也将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最坏的结果便是把鲁迅作品当做‘推背图’了。”
(21)《文艺和劳动相结合——在长春市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长春》月刊1958年第8期,《文艺报》1958年第18期转载。
(22)《关于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解答》,《电影创作通讯》1955年3月10日16号。
(23)《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未发表过。
(24)茅盾:《我走过的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663—664页。
(25)茅盾:《我走过的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665页。
(26)《茅盾全集》第40卷第130页。
(27)黄侯兴:《茅盾——“人生派”的大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28)茅盾:《我走过的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744页。
(29)1974年4月7日致单演义,《茅盾全集》第37卷,第240页。
(30)1974年8月2日致沈楚,《茅盾全集》第37卷,第281页。
(31)1975年7月22日致沈楚,《茅盾全集》第38卷,第9页。
(32)《老兵的希望》,《人民文学》1977年11月12日第11期。
(33)《化悲痛为力量》,《人民文学》1978年7月20日第7期。
(34)1979年6月11日致林默涵,《茅盾全集》第38卷,第355页。
(35)丁帆:《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重回五四起跑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36)1976年7月6日致王亚平,《茅盾全集》第38卷,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