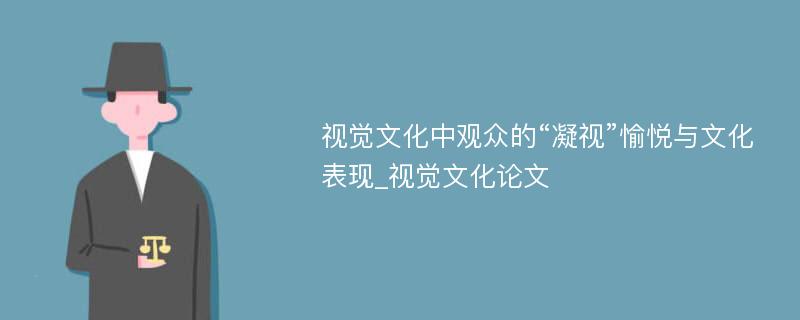
视觉文化中受众的“凝视”快感与文化表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表征论文,受众论文,快感论文,视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2X(2008)01-0103-07
“受众”(audience)是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话语范畴。按照英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奎尔(Danis Mc Quail)的说法,①受众的概念起源于戏剧、竞技和街头杂耍的观念群,起源于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所有不同形态的参与“演出”的观念。在麦奎尔看来,受众其实是一种大众的集合,通过个人对愉悦、崇拜、学习、消遣、恐惧、怜悯或信仰的某种获益性期待自愿作出选择性行为,在一种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它受到统治者可能的或实际的控制,因而是一种集合行为的制度化形式。印刷技术问世之后,受众概念首次重大的历史补遗是“读者大众”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个人阅读行为产生了对特定作者和风格类型(包括报纸)的崇尚和趋附。当社会在印刷时代开始经历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时,读者大众还促进了利益、教育、宗教和政治共识等方面的总体分化,帮助奠定了正在形成的公众概念。电影的发明和影院放映方式的出现“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起分享相同的、经媒介传播的情感和体验,批量生产的拷贝传播,取代了个性化的、活生生的现场表演和互动。到20世纪初中期,广播电视的发明,使受众身份第一次与技术手段的拥有联系在一起,跨越有形疆域的无形传播,大大扩展了传播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时空转换性更强,共时分享的受众也更多。
一、能动受众的意义建构
美国当代媒介文化批评家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认为,受众的构成方式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同人员形成不同的分层,这些分层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大众在一个高度复杂而精密的社会机构网络间穿梭时产生了“游牧式主体”(nomadic subjectivities)和集体性的对抗主体(collective oppositional),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构型(formation)。②在菲斯克看来,围绕各种差异轴,如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等,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基质,社会结构得以成形,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权力向度。如果没有权力差异,就没有社会差异。比起阶级之间的对抗,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对立才是整个矛盾的主线,而文化区域正是围绕着这一矛盾分化的。大众文化更是环绕着这一矛盾,即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抗而加以组织的。“游牧式的主体性”便通过它与权力集团的对抗和抵制而得以识别。
菲斯克对游牧式主体”拒绝充当“商品化受众”而带来的颠覆性文本阅读非常推崇。按照菲斯克的说法,“游牧式主体”能够产生从主流到反对的一系列意义,说明受众产生意义的活动以及在这一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决定。受众在其与电视文本就意义进行协调的社会构型中可以发挥积极能动的作用。受众并不是一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处于产业巨头控制之下的“文化白痴”(cultural dopes),而是能够掌控文本,鉴别选择文本并从中获得快感的意义的生产者。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受众并不是以被动的方式介入文本的。他们把广播用作日常活动的辅助。例如,在开车或做家务时收听广播节目;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也同时从事各种活动,如弹奏乐器、做家务,等等。解读电视文本是对现存主体位置与文本提出的位置进行协调的过程,而在这种协调中,力量的均衡取决于受众。不是受众的主体性服从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文本中发现的意义朝着读者的主体位置偏移。电视文本要想流行,就必须受到许多不同社会群体解读和欣赏,这样它的意义就能以多种不同方式进行变化。这样一来,电视文本的符号性和公开性都要由受众在对节目进行解读时加以变化或颠覆。也就是说,解读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受众之间的对话中生产意义。在考虑文本意义的时候应该必须根据文本在特定环境中与各种话语的碰撞,根据这种碰撞将如何重新构建文本的意义,以及如何重新构建它所遇到的各种话语。于是,《豪门恩怨》(Dallas)被大众解读为对资本主义或父权制的一种批判(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读者在每一次观看时都能发现大众的意义和快感)。然而,在理论上极其可能、而在实际上也很有可能的是,有些观众是从宰制者的立场对《豪门恩怨》进行解读的,并在将自身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性别中心、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受众利用流行文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来生产符合自己立场的意义,以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首选解读。在菲斯克看来,仅仅是抵抗性阅读还远远不够,只有把这种阅读提升为一种“快感”,受众才能摆脱文化工业的控制,成为大众文化文本的生产者,意义与快乐的制造者。菲斯克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把大众视为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么,解读的多重性和随之而来的亚文化身份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这又涉及娱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两者是两个分离的文化领域。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它们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电视的抵制性解读(resistive reading)和快乐并不会直接转化成对立的政治行动或社会行动。相对自治的文化领域之间并不是以简单的因果关系相互关联的。没有直接的政治后果并不意味着没有广义上的政治功效。抵制性解读实践确定了受支配者在其表现过程中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快乐,向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控制人们的权力提出了直接的挑战。”③
不难看出,菲斯克是宣扬受众在意义生产中“自主权”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肯定受众权力的思潮。当时的后现代主义和以受众为中心的媒体批评家都主张,受众不仅能够掌控文本意义的生产,同时也能从文本当中获得快感。菲斯克反对把受众视为在文本面前毫无抵抗力的“受害者”和“文化白痴”。相反,他提出了“生产者文本”的重要理论,淡化文本的作用,弘扬受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强调受众能够抵抗媒体生产者潜在的商业化意图。
二、女性受众的审美之维
性别差异无疑会造成媒介使用的差异,而某些形态的媒介使用则是由女性受众所引发的,特别是某些杂志(如时尚杂志)和某些形态的小说(如言情小说)等。性别化的受众经验是某种媒介内容、一般日常事务以及“父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复杂结构下的产物。简妮丝·纳德薇(Janice Radway,1984)对痴迷于言情小说(the romance)的女性受众所做的研究是一项被广泛引用的典型案例。④纳德薇以女性受众所提供的解释来说明言情小说之所以令人无法抗拒的原因。纳德薇发现,言情小说为女性受众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女性受众通过阅读言情小说来为自己建立一种私有“空间”与时间,以暂时逃避丈夫和家庭责任的滋扰。此外,言情小说为女性受众提供了理想的爱情版本,尽管它以梦幻的形式来表达,但也足以给她们带来情感上的悦乐和安慰。尽管女性主义批判言情小说有一种欺骗和反动的倾向,但纳德薇的研究却表明,女性受众可以在言情小说中找到自己的替代物和偶像,至少能够给予她们一些温馨的支持和认同。
广播和肥皂剧是另一种吸引大量女性受众的媒介类型。对肥皂剧女性观众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肥皂剧因为对女性受众有着特殊的意义而广受欢迎,不仅成为她们的谈资,而且也被用来反映她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洪美恩(Ien Ang,1985)曾对迷恋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女性观众进行研究,⑤结果显示,观众一面欣赏虚构无聊的电视剧,一面批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她们可以很随意地采取或消遣或嘲讽的态度来观看电视节目。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受众对所提及的某一内容或媒介的表面看法来框定受众,那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受众的存在和愉悦的产生与他们对特定节目内容的选择以及可能引发的对审美、道德、政治背景的批评是彼此不相关联的。
两性受众之间的关系和特定的性别角色对人们使用诸如电视这类家庭媒体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这方面,莫雷(David Morley,1986)的研究堪称经典。⑥在关于家庭收视情况的民族志研究中,他强调指出,甚至在家庭这样一个微观受众环境下,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默契和行为模式存在。最典型的是,晚间收视的控制权,一般掌握在家庭中的男人手中。女性通常较少有计划地或不间断地观看电视。她们往往在看电视的同时,兼做其他事情。由于社会原因,她们会克制自己的兴趣,服从其他家庭成员的收视偏好;她们会在看电视时聊天;会因为独自看电视而感到愧疚。女性可能倾向于将电视看做是调节家庭紧张气氛、缓和争端的一种手段,是鼓励人们在观看中实现不同程度的个人自由或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通常情况下,女性观看更多的是游戏节目、综艺节目、电视剧等;而男性则更多地观看动作片、暴力片、新闻节目和体育节目等。
在《电视文化》一书中,菲斯克用两章的篇幅通过对电视形成的性别化叙事形式和电视文本叙事策略的运用,重点分析了以“肥皂剧”为代表的“女性受众审美”(feminine aesthetic)。在菲斯克看来,肥皂剧文本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她们的去中心女性主体性(decentered subjectivity)是女性受众审美的特点所在。三者组成的并不是对抗性的女权主义文化,而是在男权之下肯定女性特点价值与快乐的女性文化。在争取一个能够产生并传播女性意义领域的过程中,肥皂剧“持续地将男性置于受质疑的地位,使女性的价值观念合法化,那些依靠女性价值而生存的女性因此而有了自尊。简而言之,肥皂剧提供了对抗主流父权价值的女性文化的手段。尽管肥皂剧可能不会以直接、激进的方式对男权统治发起挑战,但它至少可以不断地削弱男权对女性的控制力量;就最好的意义而言,它不仅向无男性控制区发起直接的挑战,而且还提供了发起挑战所必需的女性自尊。”
很显然,菲斯克的这种女性受众审美观带有浓重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色彩。通过对阳性和阴性之间形而上的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二元划分来消除媒体性别差异中的文化结构,分析电视文本中男、女性别差异的符码系统。菲斯克更倾向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拉康(Lacan)关于主体建构方式的镜像理论去解读男性电视叙事文本(以动作片为主)中女性主体的缺省(the absence of woman)。在菲斯克眼里,女性是男权社会中被贬低的群体,她们易受伤害、多愁善感、情感、承诺、体贴、细心。女性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诺,物质上也每每处于需要的地位。“男性”特点是强有力的,受到褒奖;而“女性”特点则比较软弱,受到贬低。男性和女性身份的定义在社会文化形态中被灌注成为男性至上的概念。看的对象,就“凝视”的关系而言,男性显然是主动的,而女性则是被动的。“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与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之凝视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其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凝视、被人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⑦
三、“凝视”快感与欲望表征
一般说来,人类的“观看方式”(forms of spectatorship)大致可以分为“凝视”(the gaze)、“瞥见”(the glance)、“观察”(observation)、“监视”(surveillance)、“视觉上的快感”(visual pleasure)等几种类型。英国学者伯纳德·沙拉特(Bernard Sharratt)划分了当代视觉文化中的四种观看模式:透视(glimpse)、凝视(gaze)、浏览(scan)和瞥视(glance)。按照沙拉特的说法,透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片面的观点,或许是观众潜在的强有力的表征,或许是观众渴望的东西。凝视是一种延长了的观看形式。⑧凝视由三个“政体”(regimes)组成,第一个政体是表征,这与霍尔的论述大体相似,即:可以通过某事物的关键的或有代表性的形式来再现该事物,以传达向所有人开放的真实感。第二是复制,复制是某物可以被完全再造,可以给出完整的图像。但是当有人给我们看复制品时,我们会有一种这是人造形式的意识,这种人造形式的清晰意识让受众时时保留一种疏离感。例如,我们在看电影时就经常会暗示自己,这是人编出来的,不是真实的。凝视的第三种政体是观看,它描述的是一个观看者观看、凝视一个真实而不是复制的风景的可能方式。
许多理论家在探讨“凝视”问题时都指出,人们通常把“男性化凝视”加以“自然化”,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看行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男性化的凝视又常常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男性对女性存在着性欲望,而该女性又是以其母亲为原型来塑造的。因为,母亲是男性所凝视的第一个女性。据此,美国传播学者E·安·卡普兰(Kaplan,E.Ann)归纳出“男性化凝视”的以下的三种类型:⑨
第一,片中的人物会带着性欲望来“凝视”女性;
第二,摄影机会对准片中的女性,有时甚至会像片中的人物那样主观地“凝视”女性;
第三,电影院中的观众通过摄影机的镜头来“凝视”片中的人物。
西方人体绘画里充斥着男/观看/主动与女/被看/展示的关系。绘画里的女性总是在奉献自己的女色和身体,等着男性的“凝视”,在男画家笔下的女性裸体其实相当程度上投射了男性对于女性的喜好与理想。同样,在好莱坞相当多的电影中,女性形象一直是男性视觉快感的重要来源。那些成功的英雄人物身边总有一个得力并且热情相助的红颜知己,这些红颜知己使男性观众产生了一种向往,并在将自己设身为英雄时也会有拥有红颜知己的快感和成就感。
在心理分析理论家看来,分析“凝视”行为就是要考察作为主体的受众所具有的结构、功能和行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类内心世界当中相互冲突的势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性,这种互动与“视觉驱动力”之间此消彼长。当我们凝视某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观看”或“被看”当中获得快感,也就是说主动或被动地获得快感。我们在这种相互对立的位置之间来回“游移”,在阳刚和阴柔的特质之间来回“游移”。观众的“凝视”向外作用于电影当中的影像,向内则作用于思维的运作。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实际上就是在“凝视”和反思其内心当中隐藏的冲动和“另外一个自我”。
法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Lacan,1993)指出,理解“凝视”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理解“镜像自我”的概念。无论是照镜子还是看电影,人们都会在观看影像的过程中产生兴奋和快感。但其间却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间隔,也就是说,镜子或银幕上出现的是自我的影像,不是真正的自我。⑩而在电影中,这一间隔(即观众希望把银幕上的影像当作“真实”来理解)给观众造成了一个相互对立的心理定位:观众在凝视影像时,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是“真实的”,但同时又知道它们并非“真实存在”。观众能够主动介入到影像的体验当中,但却无法控制银幕上影像的流动,因而又是被动的。观众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影像的意义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构建,却无力操控银幕上的世界。
拉康认为,“凝视”是一种双重体验:我们一方面在观看银幕上所展现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又把这个银幕世界移植到我们的头脑中,将其转化为我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部分认知。换而言之,我们一方面是根据对自身的认识来理解影像,另一方面又根据影像来形成认识自身的方式。拉康的理论阐明了相互指涉的双向循环过程,即:我们对影像的凝视是主动的,并且根据自身的身份/认同来构建影像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又根据对影像的理解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的评估。电影批评家们常把拉康的理论运用到电影研究当中。在他们看来,观看电影和理解其意义也是一个“缝合”的过程:人们在通过思维把不同的镜头联结为一体,从中构建出某种意义。
克里斯蒂安·麦茨(Mets.C.)强调观众对观看的认同和对叙事的认同。他指出,由于观众将“眼睛的观看”和“摄影机的观看”合为一体,因而倾向于接受摄影机所构建出的意义。(11)观众对摄影机的认同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对叙事的认同。影片中的人物就是认同的切入点。观众通过“交感类比”的心理过程,把自身的体验投射到这些人物身上,进入到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故事中去。就此角度而言,观众理解电影文本的意义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控制文本。事实上,摄影机处于“客观第三者”的位置。当然,依据麦茨的理论,摄影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它似乎是在引导观众的思维及其对电影文本的理解。这就意味着,观众必须意识到他们不一定对文本拥有完全的“控制力”。在麦茨看来,当观众通过观影行为构建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认同、偷窥和恋物。“偷窥”是在电影院观看电影的整个语境中的一部分。无论是电影角色还是身处黑暗中的其他观众都无法看到你,因此,你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从而可以“偷看”银幕上的人和事。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偷窥者。“恋物”的过程可以用“性恋物癖”来进行类比,后者使女性身体的某些器官带有色情含意,并且转移了人们对那些无法看见事物的关注(比如,弗洛伊德理论中提到的“阴茎缺失”)。电影当中的影像和画面承载了观众的想象,代表了那些缺省的事物。“电影的能指本身就是想象出来的。因此,只有电影才能将观众带入到一个缺席和在场的游戏中去。”
穆尔维(Mulvey,1989)在麦茨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偷窥癖”的概念,旨在让人们更加关注观看所带来的快感。(12)穆尔维指出,电影中的女性人物一方面是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影片情节框架内被动的客体。男性观众的凝视与片中男主角的欲望是一致的,同时与男主角对电影叙事的驱动作用也是一致的。相比之下,女性观众的凝视与电影中作为欲望对象而存在的女性人物是一致的,因而是一种被动角色的被动凝视。这也是一种“物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把女性转变为欲望对象的过程。这样一来,女性就不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自身欲望以及能够说“不”的人。因此,女性的快感就成了男性的快感。女性观众要想获得快感就必须接受男性的视角。穆尔维指出,为在窥视过程中,男性一方面在女性“阴茎缺失”的优越感中确定自己的主动地位,以视觉将女性限制在框架中,贬低其作为被动的客体,另一方面由于“阴茎缺失”的女性不时提醒男性阳物被阉割的威胁,造成男性的焦虑,强化了男性的窥视行为,并促使其结合虐待狂的心理来惩罚女性。而男性为了逃避女性“阴茎缺失”事实,便给予女性高跟鞋、皮带、利剑、机关枪等以替代女性的“阴茎缺失”,此即“拜物现象”,并因此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凝视女子”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色情图片里总充满了拜物主义与各种阳具象征(比如照片中常使女性拿着手枪、空瓶等),例如,世界影星波姬小丝的写真宣传画就是蟒蛇缠绕裸体。女性流行体制也产生了满足这种“可被偷窥”的“性感符码”,如高跟鞋、黑色网纹丝袜、若隐若现的透明丝衫等。男性凭借着视觉的权力优势,在色情/性别的论述中将女性客体化、非人格化。
按照穆尔维的说法,偷窥是一种男性的快乐,说明窥视者拥有对被窥视者的权力。这种偷窥的快乐来自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观看,所以,在好莱坞叙事的典型进程中,都是由男性的行动来推进情节,其间穿插一些男主人公注视或占有女性身体的镜头。男主角成为体现男性观众和摄影机的男性“目光”对拍摄前事件的见证。注视和占有女性所产生的视觉快感,是前一段故事中男性行动获得成功后的回报。这就产生了一个男性解读主体,尽管电影的观众可能有男有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也可以成为男性化的主体,因而也能体验男性的快乐。她们和男人一样,都能用男性化的眼光来注视女性的身体。在我们生活中,广告经常使用女性形象特别是女性身体作为展示载体,例如,在化妆品、洗发水、汽车、健身等广告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极力表现女性身体的魅力,使之变成迷恋的对象。这些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激起的是女性观众男子式的欲望,并为她建立一个男性化的解读立场,让她可以用男性的眼光来理解自己的身体。对女性形体的迷恋来源于照相机或摄影机镜头过度渲染“崇拜”女性形体,这是解除女性带来的阉割恐惧和恋母情结罪恶感的一种方式。偷窥欲望得到满足所产生的快感与男权社会的要求十分协调。菲斯克认为,穆尔维基本上在男权、快感和两性自然差异这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无法打破的关系。她似乎把男权建立在人性基础上,认为男权力量与人类性欲的实质难以区分,并以此来解释电影带来的快乐。(13)
在菲斯克看来,穆尔维也许承认可能会产生一种激进的快感,但她对激进快感产生的原因并没有作出分析,这就使穆尔维这位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摧毁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快感,而用一种新的快感来取代,以形成一种没有权力优势的新的观看方式。菲斯克承认,穆尔维的快感理论应用于一般的视觉形象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在电视广告,尤其是化妆品广告中(期刊和各种招贴画广告也不例外),女性形象或女性身体越来越成为男性的观看对象以及产生偷窥权力和快感的来源。美丽、性感、优雅这些女性身体的基本印象显然都是基于男性窥视经验基础之上的。
菲斯克以美国歌星麦当娜的MTV造型为例,对“看”与“被看”之间的“凝视”快感、“窥视”欲望的文化表征以及权力关系等予以分析解读。
在麦当娜的音乐电视Into the Groove(《随着节奏摇摆》)中,麦当娜将自己设计成一种怪异的形象:十字架、花边内裤、男人的吊裤带、透明的粉红色上衣合成而成的形象。麦当娜不仅是这个剪辑过程的产物,同时也是该过程的制造者。她把十字架从原有的宗教所指话语中剥离出来,作为自己的权力能指:她还展示了自己控制色情“语言”的能力(肉体,纤薄的内衣,黑皮革等)——以非色情的方式利用色情语言,为自己的快乐和身份服务,而不是以此取悦男人的“窥视”。麦当娜音乐电视中大特写镜头是切分并崇拜女性身体的摄影代码,它使女性身体的任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男性窥视欲望的去人格对象。麦当娜音乐电视的一个特色就是,突出并控制自己肚脐的色情意味;唇部和眼睛的大特写镜头也在其控制之下,她从一个角度看着摄像机,同时要求摄像机也从这个角度去拍摄她本人。这样一来,麦当娜就把自己变成了观赏对象,不给观看者以任何偷窥权力。她不让自己置于偷窥者的“凝视”之下,而是控制着这种“观看”的条件。她意识到自己外表的色情含义以及观看者的在场,并且能够控制自己的色情外表和观看者的窥视欲望:她不是依赖男性的“观看”才拥有意义的对象。相反,她是她自己的观赏对象。在这样的观赏中,偷窥者并不存在,正常的观看权力关系已被颠倒,正如狂欢一样,看与被看都以平等的身份共同参与观看以及意义生产的过程。“观赏的狂欢性否定了阶级和性别的从属性,也否定了使用话语的社会权力。”(14)很显然,作为“被看”的麦当娜,其身份认同和意义生产都在这种观看的狂欢性娱乐中得以彰显。
1986年,麦当娜的MTV作品《敞开心扉》(Open Your Heart)展示了对男性“凝视”的类似解构。(15)片中表现的是,麦当娜在窥视秀(peep show)中火辣表演脱衣舞,庸俗的男人则向她明抛媚眼,但她似乎对此显得无动于衷。不妨把该部音乐电视读解成:是男性将女人身体对象化加以窥淫癖的一种展示。依照这种读解,麦当娜其实是拒绝在节目中让自己成为男性欲望的窥淫对象的。对于那些想如此观赏麦当娜的男性观者而言,由于他们被置于庸俗的、窥淫的主体位置而显得不安和尴尬。因此,尽管此节目大肆展示作为窥淫对象的麦当娜的身体,但影片其实最终未能成为一种拜物性的观看,因为它把窥淫癖与女性身体的对象化看作是一种社会化的身份认同过程。麦当娜的脱衣舞表演并不是在引诱男性窥淫者对她“凝视”,而是对他们进行一种欲望控制。对麦当娜来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颠覆弗洛伊德窥淫癖理论中的权力关系。对此,苏珊·伯杜则提出反驳。认为,该音乐电视恰恰强化了女性被男性欲望对象化的窥淫场面,而观者也不会真的被这一节目弄得茫然失色,尽管节目的形式上包含着一种“含混性”,叙述的语境也是文不对题。事实上,难以确定的正是,不同的观者究竟如何对待麦当娜的这种音乐电视。当节目中的画面有可能强化那种将女性身体被男性欲望对象化窥淫之时,叙述的语境以及歌词与画面的并置等却可能以现代主义的方式来打断这种窥淫。如同《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音乐电视一样,《敞开心扉》也会有自相矛盾的效应,既能吸引那些愿意看到解构与颠覆的文化批评者和女性主义者,同时也能吸引那些喜欢看女性身体的男性,以及那些从自己被男性欲望对象化了的女性的身份认同中获得快感的女性。麦当娜的魅力就在于其多义的文本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受众和复杂多义的解读。
注释:
①McQuail D.,Audience Analysis,Saga Publication,1997,p2.
②Fiske,John.Television Culture,Routledge,1989,p309.
③Fiske,John.Television Culture,Routledge,1989,p326.
④Radway,J.,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and Popular Literatur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⑤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London:Methuen,1985年版)是媒介文化学者洪美恩1985年用荷兰语写成的,是她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该文被广泛引用,公认是电视观众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洪美恩的研究对象是八十年代风靡欧洲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当时在荷兰撰写硕士论文的她在一家妇女杂志上登了一则启事,说她喜欢看《豪门恩怨》,但总是得到一些古怪的反应。希望读者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她: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不喜欢?结果,洪美恩得到42封回信,反应从喜欢到不喜欢直到讨厌,各不相同。
⑥参阅 David 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1992.
⑦劳拉·穆尔维(Mulvey),《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转引自张红军,《电影与新方法》,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⑧转引自陈龙、陈一,《视觉文化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2页。
⑨E·安·卡普兰,《女性与电影——摄影机前后的女性》,曾伟祯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6-37页。
⑩Lacan,J.,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in A.Easthop (ed.),Contemporary Film Theory,,Harlow:Longman,1993.
(11)Mets,C.,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The Imaginary Signifier,London:Macmillan,1982.
(12)Mulvey,L.,Afterthoughts on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spired by King Vidor;s Duel in the Sun,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Bloomin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28.
(13)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Routledge,1989,p225.
(14)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Routledge,1989,pp.225-253.
(15)Susan Bordo,Materil Girl:The Effacements of Postmodern Culture,in Cathy Schwichtenberg (ed.),The Madonna Connection,Boulder:Westview,1992,pp.265-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