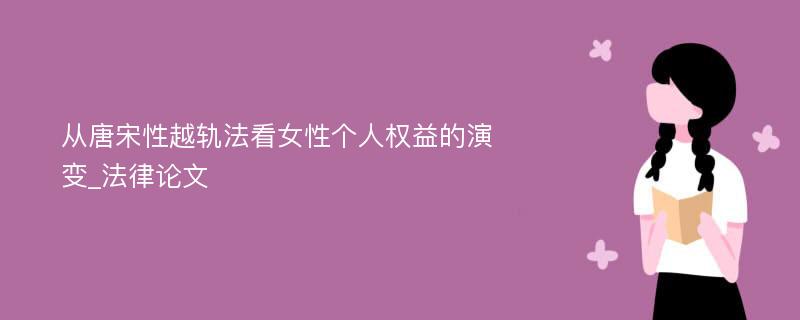
从唐宋性越轨法律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人身论文,权益论文,女性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有关唐宋女性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但有些领域尚待发掘,例如同女性自身密切相关的性问题,不但涉及私人生活、贞洁观念,而且同当时社会的性别制度、秩序理念以及两性权利密切相关。在由男女两性共同构建的性秩序格局中,考察女性的人身权益如何,一个直接的视角是法律文本和司法实践。本文试从法律与性的角度透视女性生活,通过对唐代与宋代性越轨法律的比照,并结合宋代司法实践,探讨从唐到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
一、概念的界定与法律文本的选择
从古至今,性不仅是私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关系到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所以任何时代都把对男女性行为的规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必须遵行的道德约束。就法律而言,尽管不同时代对于性行为的规制有所不同,但通常意义上,都是针对该社会性行为的越轨而制定的。“越轨”一词,在现代社会学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①,然古已有之。“轨”,本义为“车辙也”②,在中国古代,它兼有伦理规范与法制规范的双重含义。例如,《管子》云:“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③《汉书》称:“楚孝恶疾,东平失轨”,颜师古注:“轨,法则也”④。《申鉴》云:“越轨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⑤《佩文韵府》亦云:“轨,法也。车迹也。”⑥ 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越轨是指背离法则或伦理规范的行为。本文所谓“性越轨”,专指刑事法律意义上背离社会规范的性行为,亦即非法律许可之性行为。性越轨行为属于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的法律有其不同的界定与规制。唐宋法律有关性越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犯奸罪”的条文中。
“奸”,《说文解字》释为:“犯淫也”,段注进一步明确:“此字谓犯奸淫之罪。”⑦“犯奸罪”是针对男女性越轨而设的罪名,主要包括“强奸”、“和奸”以及“乱伦”等。“强奸”是指男性使用暴力,强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越轨行为;“和奸”谓“彼此和同者”⑧,是指在女性同意前提下发生的性越轨行为;“乱伦”指亲属间违背伦常的性越轨行为。在现存唐宋法律文本中,对性越轨的规范,集中体现在《唐律疏议》、《宋刑统》以及《庆元条法事类》对犯奸罪的判罚条文中。
唐代法典有律、令、格、式四种,“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⑨。至今传世者仅《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余皆亡佚。《唐六典》是唐玄宗时编订的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法规,《唐律疏议》则是唐代“正刑定罪”的刑事法典,也是终唐之世最主要的法律依据。《新唐书·刑法志》云:“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⑩《旧唐书·刑法》亦称唐代“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11)。
宋初依唐律修订《刑统》,虽然学界不赞成《宋刑统》为唐律之翻版说(12),但其内容基本上沿袭唐律之旧,不少条文与宋代社会现实相脱节(13)。《宋刑统》颁行后,很快便不能适应宋代社会的发展要求(14),因而不断有朝臣建议重修宋律。如仁宗时夏竦即认为,《刑统》律文“未契皇朝好生之化,有辜陛下恤刑之德,诚宜具刑宪之书,求献议之士,诏择能臣,督其详订”(15)。夏竦的建议虽然未被仁宗采纳,却反映了《宋刑统》已不适应宋代社会需要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从宋初开始,统治者便不得不运用大量敕令来补充律之未备,变通律之僵化。
敕是皇帝在特定时间对特定人或事临时发布的诏令,通常谓之“散敕”,并不具备普遍的法律效力,《唐律疏议》卷三○《断狱》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16) 要使散敕上升为一般的法律形式,还须经过编修程序,即对积年的各种散敕删其重复,去其抵牾,存其可为常法者,汇编后加以颁行。宋初编敕,皆取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准律分十二门”(17),至仁宗朝,编敕始有“丽于法者”(18),即开始附有刑名。编敕体例的这一变化,冲破了以往编敕不附刑名的旧制,形成律外有律的局面,为后来的以敕代律作了准备。至神宗,则明确规定:“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19) 从此,“敕”正式取代了“律”的地位,使“律存乎敕之外”(20)。如朱熹所说:“律是刑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敕令。”(21) 所以,与刑统相比,宋朝历代敕、令、格、式更直接地反映了宋代社会的实际生活。
宋代几乎每一朝都有新编敕问世,“到南宋孝宗朝时,于编敕之外又编撰条法事类”(22),乃取“敕、令、格、式及申明五书”(23) 分门修撰。现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修成于宁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八月,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七月诏颁于天下。《庆元条法事类》产生时,宋代社会已历时二百四十余年,又正值南宋社会中期,此时宋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已经成熟,尽管该条法不能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全部,但就存世法律文本而言,其内容“包括早自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晚至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七十二年间所颁布的政令,甚至在卷七三中尚引到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七月六日尚书省的札子”(24),是现存最能反映宋代尤其是南宋社会生活的一部法律文本,“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宋代法制史的重要文献”。(25) 因此,本文对唐宋社会性越轨法律的考察,即以《唐律疏议》与《庆元条法事类》作为主要分析文本,兼及《宋刑统》,从法律条文的变化并结合司法实践来探寻从唐到宋性越轨法律演变的轨迹,考察其中反映的女性人身权益之演变。
二、从法律对同一阶层之内性越轨规范的差异看唐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文化的一部分。(26)“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27),法律的立场,实则与该社会的价值取向、秩序理念以及文明程度直接相关。同样,法律条文的增删,并不仅仅是为应付突发事件而作的暂时考虑,或简单的文字调整,它所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不同时代秩序理念的变革。
(一)关于“和奸”与“强奸”
和奸是在女性同意前提下发生的非婚性行为,其性质为男女两性共同违背社会道德伦理、家庭秩序,男女属于共犯。强奸性质则不同,是男性使用暴力,强行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是被动的受害者,因此强奸惩处法的保护对象明确为女性。所以,对强奸罪的重视与否,同该时代女性的人身权益以及社会对女性人身权益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对强奸罪的重视程度能够体现社会对女性人身权益的维护。
唐宋法律对强奸罪与和奸罪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摘录相关条文,列表对照如表1。
表1 唐宋有关“和奸”、“强奸”的法律条文简表
朝代 条文内容 出处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强者各加一等。折伤者,各加斗折伤罪
一等。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
【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妻、妾罪等。
律》
【疏】议曰:“折伤者”,谓折齿或折指以上,“各加斗折伤一等”,谓良人从凡斗
唐 上加。
十曰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疏】议曰:“及与和者”,谓妇人共男子和奸者,并入“内乱”。若被强奸,后遂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
和可者,亦是。
(与唐律内容相同。此略)
《宋刑统》卷二六《杂律·
北 准周广顺三年二月三日敕节文,应有夫妇人被强奸者,男子决杀,妇人不坐罪。
诸色犯奸》
宋 其犯和奸及诸色犯奸,并准律处分。
(与唐律内容相同。此略)
《宋刑统》卷一《名例律》
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亦同,流三千里,配远恶州。未成,配五百里。折伤
南 者,绞。先强后和,男从强法,妇女减和一等。既因盗而强奸者,绞。会恩既未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
宋 成,配千里。
《杂门·诸色犯奸》
表1可见,唐律对和奸罪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强奸罪,《唐律疏议》于犯奸罪的首条便规定了对和奸的惩罚,而且对有夫之妇的惩罚重于他人,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妻、妾罪等。”对有夫妇女惩罚的加重,说明唐代社会对已婚妇女的人身约束比对未婚女子严厉,因为已婚妇女犯奸被看作是对丈夫权益的侵犯,同时其性行为关系到家族子嗣血统的纯洁。反之,唐律对强奸罪的惩罚很轻,只不过在和奸的基础上“各加一等”而已,而且仅以寥寥数字附在和奸罪之后。即使男性在强奸女性的过程中,因暴力而造成女性“折伤者”,也只不过再“加斗折伤罪一等”而已,而且律疏明确界定,所谓“折伤者,谓折齿或折指以上”(28),言下之意,“折齿或折指”以下的其他伤害则不算伤害。这种忽视强奸、重视和奸、对已婚妇女的惩罚重于男子的现象,看似违反常理,实则体现了唐代性别制度的秩序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女性仅以男性附庸的形式出现,其人身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宋刑统》承袭唐律,没有对上述法律作出修订,但是,在唐律基础上增加了后周广顺敕文,加重了对于强奸“有夫妇人”男子的判罚力度。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了显著的变化。《庆元条法事类》对强奸罪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和奸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法律条文的设置顺序与判罚力度上。《庆元条法事类》对强奸的判罚置于“诸色犯奸”诸条之首,而且判罚力度远远重于唐律。规定,诸强奸者,“流三千里,配远恶州”,即使强奸未遂者,也要“配五百里”。若男性因暴力而造成女性身体受伤,则要处以绞刑。其二,对“先强后和”加以明确区分。《庆元条法事类》强调“先强后和,男从强法,妇女减和一等”(29)。“先强后和”的情况唐律并非没有注意。《唐律疏议》曾在规定“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入“内乱”时提到“先强后和”的情况,但并没有因此而加重对男性的惩罚或减轻对女性的惩罚,而是一律以和奸罪判罚。律疏强调,“妇人与男子和奸者,并入‘内乱’。若被强奸,后遂和可者,亦是”(30)。显然,唐律对于伤害女性的犯奸者判罚力度不够,而对于女性则显得苛刻。其三,唐律对有夫之妇和奸的惩罚重于他人,而《庆元条法事类》取消了对已婚妇女和奸加重处罚的条文,同时规定“诸妻犯奸从夫捕”(31),这是唐律所没有的内容。正如宋人自己所言:“捕必从夫,法有深意”(32),妻子犯奸,若丈夫不告诉,那么法律便不追究妻子的责任。这种规定,一方面反映出法律对于夫权的维护,在妻子犯奸的案例中,告发与否的主动权取决于丈夫;但另一方面,该法律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以及夫妻关系的和谐,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社会他人对夫妻之间情感的干预,也不至于听信他人对妻子的诬告。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可从当时的司法实践得到佐证。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因奸射射》一案中,黄渐与妻阿朱“乔寓永福,依于陶氏之家”,主人陶岑与寺僧妙成交讼,“遂及其妻,因谓有奸”。该案初判时,判决黄渐、陶岑与妙成各杖六十,阿朱则射充军妻。范西堂重新审理此案,依据“诸妻犯奸从夫捕”以及“离与不离听从夫意”两条法律,判定原判无效,并对原判执行吏人张荫、刘松“各从杖一百”,改判阿朱“付元夫交领”,但因牵涉奸事,“不许再过永福”,寺僧妙成“押下灵川交管”(33)。倘若宋代法律没有上述“捕必从夫”的条文,那么,阿朱就不可能得到较为宽松的判决并与丈夫团聚。
上述变化,并非仅是刑罚轻重或有无的问题,而是反映出与唐代相比,宋代社会加大了对于男性非法性行为的约束力度,同时也相对提高了对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力度。
此外,《庆元条法事类》明确规定了诱奸10岁以下女童,罪等于强奸,“诸强奸者,女十岁以下虽和亦同”(34)。而在唐律中没有这类罪名,这并非唐代立法者的疏漏(35),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社会对未成年女性人身权益的漠视。自宋代首惩奸污幼女的罪行以来,后世诸朝均相沿此例,在犯奸罪中加入强奸幼女“虽和同强”的法律,只是年龄限定稍有不同。如元代规定为十岁以下(36),而明清则为十二岁以下(37)。
(二)关于“犯奸未遂”
唐律中没有犯奸未遂的条文,反映出唐代对奸罪的认定以是否成奸为准,对未遂者不予惩罚。《宋刑统》与唐律相似。而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则明确规定了对犯奸未遂者的惩罚。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
诸奸未成者,减已成罪一等。诱谑者,杖八十。妇女非和同者,止坐男子。
诸奸同居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虽未成,男子勒出别居。
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
南宋不仅在法律条文中增加了犯奸未遂的罪名,而且贯彻在司法实践中。《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一案中,“胡千三戏谑子妇,虽未成奸,然举措悖理甚矣,阿吴固难再归其家”,因而蔡久轩判决阿吴“再行改嫁……胡千三未经勘正,难以加罪。如再有词,仰本县送狱勘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为为舅而举措谬乱者之戒”(38)。尽管司法官员对此类案件的判罚并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犯奸未遂”罪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女性的人身权益。
(三)关于“奸生子女”的归属
《唐律疏议》中没有涉及因奸所生子女的归属问题,宋代立法者则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宋刑统》卷二六《杂律·诸色犯奸》:“准户令,诸良人相奸,所生男女随父。”《庆元条法事类》在《刑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女性有权抚养自己的非婚生子女,卷八○《杂门·诸色犯奸》:“诸因奸生子女,随父。其母愿自抚养者,听。妻被离出所生子小,而愿自将带抚养者同。”《庆元条法事类》规定,非婚生子女“随父”,这使得男性不能逃脱抚养子女的责任;在这一法律前提下,如果女性愿意,则允许女性抚养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这一规定保障了女性作为母亲的权益,反映出南宋性越轨法律中女性权益有所扩大。体现了南宋社会对于女性人身权益的重视。
(四)关于“乱伦”
“乱伦”是指亲属之间违背伦常的性越轨行为。比照唐宋有关“乱伦”的法律条文,亦可看出唐宋社会性别制度的差异。
表2可见,在重视礼法与伦常的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对于亲属之间违礼乱伦的犯奸行为一律科以重罪;而且妾的地位明显低于家庭内部其他成员,在唐宋性越轨法律中对于奸妾的惩罚明显轻于对其他家庭成员。但唐宋之间也存在差异,表现为唐律重在维护尊卑、伦常秩序,宋代法律则更为重视家庭关系的敦睦和谐,妻子在这一法律体系中获得了较多的权利。《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妇人犯奸,非义绝,并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奸,未成,离与不离听从夫意”(39),这是唐律所没有的内容。妻子犯奸,只要不在“义绝”(40) 之列,离婚与否由丈夫决定;另外,妻子与亲属相奸未成者,离与不离亦由丈夫决定。这种规定,一方面反映出法律对于夫权的维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法律注重维护家庭的稳定妻子的权利在受限制的同时也得到一定保护。此外,“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的法律条文,扩大了妻子的离婚自主权,表现出对女性意愿的尊重。
表2 唐宋有关“乱伦”的法律条文简表
朝代
条文内容
出处
十曰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疏】议曰:“及与和者”,谓妇人共男子和奸者:并入“内乱”。若被强奸,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
后遂和可者,亦是。
唐 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
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余条奸妾,准此。
诸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从祖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
流二千里;强者,绞。
诸奸父祖妾、谓曾经有父祖子者。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
者,绞。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
北 (同上。略)
《宋刑统》二六《杂律·诸色
宋 犯奸》
诸奸同宗缌麻以上亲者入内乱。
诸奸父祖女使徒三年,非所幸者,杖一百。曾经有子以妾论。罪至死者奏
裁。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
南 诸奸本宗异居缌麻以上亲,听依同籍捕格法。诸奸同居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
《杂门·诸色犯奸》
宋 上亲之妻者,虽未成,男子勒出别居。
诸妇人犯奸,非义绝,并与夫之缌麻以上亲奸,未成,离与不离听从夫义。
被夫同居亲强奸,虽未成,而妻愿离者,亦听。
《庆元条法事类》的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性的人身权益,体现了从唐代到南宋性越轨法律朝着有利于法律完备、公正方向的变革。
三、从法律对不同阶层之间性越轨规范的变化看唐宋下层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视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所以“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惨疚。其友朋亦视其为当然,而不非议”(41)。宋代社会不同,较为重视对士大夫性行为的规范(42),下层女子的法律地位也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面貌。
(一)关于下层女性等级地位的法律界定
本文所指下层女性,限于唐宋性越轨法律中涉及的唐代官私奴婢、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宋代奴婢和女使。由于唐宋时娼妓制度合法化,狎妓不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性越轨,因而处在社会下层的各类娼妓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对于下层女性身份地位的法律界定,是不同阶层之间性越轨法律规范的前提和基础。在这方面,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司法案例,都可以看到宋代社会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平民的四肢”(43) 的特色。
唐律严格界定“良贱”的等级,奴婢属于贱民(44),他们“身系于主”(45),“同于资财”(46),“律比畜产”(47)。《唐律疏议·户婚》称:“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48) 买卖奴婢不仅合法,而且与买卖牛马同列,规定:“买奴婢、牛马驼骡驴等,依令并市券。”(49) 唐代“官私奴婢地位最低,唐律根本不承认他们有独立的人格”(50),更遑论其人身权益。
宋代法律对于奴婢身份地位的界定与唐代有较大差异。(51) 宋代奴婢在较多方面视同良人,早在窦仪等人编修《宋刑统》时既已提出:“奴婢诸条,虽不同良人,应冲支证,亦同良人例。”(52) 自宋初以来,朝廷屡下诏书明令不许买卖奴婢,如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诏:“应广南诸郡民家有收买到男女为奴婢,转将佣雇,以输其利者,今后并令放免,敢不如旨者,决杖配流。”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咸平元年(公元998年)诏:“川陕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53) 对于掠卖奴婢,“宋朝法律一直是禁止”(54) 的。在宋代,“略人之法,最为严重”,“略人为奴婢者,绞”(55)。《庆元条法事类》还规定“诸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称女使者,乳母同。”(56) 可见,宋代下层女性的社会地位比唐代有较大提高。与此相应,宋代法律对于不同阶层之间性越轨的规制也与唐律有所不同,从中可见对下层女性的人身权益较为重视。
(二)关于“以下犯上”的法律规制
不同阶层之间性越轨法律的规范包括“以下犯上”与“以上犯下”两种。
表3可见,在维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唐宋社会中,对于“以下犯上”的性越轨行为,惩罚均很严厉。所不同者在于,唐律中的部曲、杂户、官户,在宋初编修《宋刑统》时依然沿用;而在《庆元条法事类》中,“以下犯上”则改变为“人力”、“佃客”以及“旧人力”奸主的类型,这种称谓的变化体现了从唐到宋人身依附关系的转变。唐代的“官户”、“杂户”属于贱民中的“官贱”,“部曲”属于“私贱”,其与主人的关系属于终身隶属关系;“佃客”一词没有在《唐律疏议》中出现。宋代的“人力”、“佃客”是租佃契约制之下的雇佣劳动者,与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为松散,从制度上说仅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期满,依附即自然结束。“旧人力”的称谓突出反映了这一点。而且,从惩罚力度来看,法律对于“旧人力”奸主的判罚轻于对“人力”和“佃客”,原因就在于“旧人力”已经脱离了同主人的隶属关系。
表3 唐宋有关“以下犯上”的法律条文简表
朝代
条文内容 出处
部曲、杂户、官户而奸良人者,并加良人相奸罪一等。
唐 诸奴奸良人者,徒两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
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
主之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
北 (与唐律内容相同。此略)
宋 准户令……杂户、官户、部曲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听为良。其部曲及奴奸
《宋刑统》卷二六《杂律·诸
主缌麻以上亲之妻者,若奴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合没官。 色犯奸》
诸人力奸主,品官之家,绞。未成,配千里。强者,斩。未成,配广南。民
南 庶之家,加凡人三等,配五百里。未成,配临州。强者,绞。未成,配三千
宋 里。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
诸旧人力奸主者,品官之家,加凡奸贰等。民庶之家,加一等。即佃客奸
《杂门·诸色犯奸》
主,各加贰等。
以上妇女……各以凡论。
(三)关于“以上犯下”的法律规制
表4 唐宋有关“以上犯下”的法律条文简表
朝代 条文内容
出处
【疏】议曰:……良人奸官私婢者,杖九十。
唐
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
【疏】议曰:“奸他人部曲妻”,明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
北
《宋刑统》二六《杂律·诸色
宋
(与唐律内容相同。此略)
犯奸》
旧主与女使奸者,各以凡论。
南
诸受人欲雇者,若雇人欲贩者,相犯及奸,并同凡人。奸欲雇、欲贩妇女 《庆元条法事类》卷八○
宋
者,止坐男子。
《杂门·诸色犯奸》
唐律中,主人强奸自己的家贱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唐律甚至暗示主人强奸家贱是合法的,律疏明确规定:“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不坐。”由于奴婢贱人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侵犯他人奴婢仅仅被视同为对他人财产的侵犯,因而唐律同时规定:“奸官私奴婢者,杖九十”,“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57)。
《宋刑统》对唐律的上述规定没有变动,但在《庆元条法事类》中,对于“以上犯下”的性越轨法律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若干条文。如,旧主与原女使犯奸者,“各以凡论”,从法律上保证了同主人解除契约关系的下层女子,免受原主人的侵犯;对奸欲雇女性的判罚,法律同于“凡人”;而且,“奸欲雇、欲贩妇女者,止坐男子”,这些都反映出宋代性越轨法律对于下层女子的人身权益较为重视,它与宋代下层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是相一致的。
余论
通过以上对唐宋有关性越轨的主要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比照与分析,可以看到宋代女性人身权益比唐代有一定程度的伸张。进而一步,法律应然与社会实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宋代性越轨法律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实施的,是否真正有利于维护女性的人身权益?本文的最后,笔者拟简要检讨这一问题。
其一,《庆元条法事类》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唐代而言宋代女性人身权益有所伸张的法律条文,然而,司法实践的情况却很复杂。一方面,儒家的恤刑宽仁精神,使得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性越轨的案件时,一般都会从轻量刑。同时,敦亲睦族,大兴教化,厚风俗,美人伦,成为宋代士大夫审理司法案件时的基本职责。真德秀甚至将道德教化上升到“为政之本”的高度,提出“为政之本,风化是先”(58)。这种风气,也使得宋代司法官员在处理“暧昧”案件时,往往以道德说教为主,而以刑罚惩戒为辅。加上宋代社会对士大夫的优待,司法官员在处理士人犯奸的案例时,往往会偏袒士人。这些都使得女性的人身权益在社会实然中很难得到合理的维护。另一方面,尽管在宋代司法审判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法意与人情相背离的情况,但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及作出判决的过程中,仍然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人情只能参酌而不能左右法律。因此,法律条文本身是否有利于维护女性人身权益,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宋代女性人身权益比唐代而言有一定程度的伸张。
其二,诚如前辈学者所论,中国古代法制以儒家思想与家族主义为宗旨,家族既是伦常主义的中心,又是个人生活的归属,重视家族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共同特色。(59) 家族内部成员或具有血缘关系,或存在尊卑名分,因而家族内部的性越轨,属于违礼乱伦之行为,凡亲属相奸,罪行必然重于常人,这一点在唐宋法律中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尊尊、亲亲、长长,名份、等级等思想贯彻在法律中,如唐律规定“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两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余条奸妾,准此”(60)。家庭内部同性成员之间因身份高低不同而惩处轻重有差,使得法律在维护女性权益方面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庆元条法事类》同样为尊者、长者讳,明文规定:“诸同籍若本宗异居缌麻以上尊长与人和奸,不许告、捕。”(61) 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尊长可以肆意妄为,卑幼却不得告发。这对于维护女性,尤其是家庭中儿媳等辈份较低女性的人身权益极为不利。《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执法者在处理公公侵犯儿媳的案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牺牲儿媳利益,袒护尊长权威,儿子一旦上告,还要受到惩罚。(62) 这不能不说是等级制度与家族主义统摄下的法律与性别制度的不合理,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无法从整体上逃脱劣势的处境,她们的人身权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维护。
注释:
①现代社会学因流派纷杂,对“越轨”的界定不完相同,但简单地说,则包括违反法律、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的所有行为。参见〔美〕杰克.D.道格拉斯(J·D·Douglas)等著、张宁等译《越轨社会学概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4页。
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二七《十四篇上·车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页。
③《管子》卷一○《君臣上第三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④《汉书》卷一○○下《叙传第七十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63页。
⑤《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59页。
⑥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卷三四上《上声·四纸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47页。
⑦《说文解字注》卷二四《十二篇下·女部》,第625页。
⑧《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6页。
⑨《大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日本广池学园事业部1973年影印本,第139页。
⑩《新唐书》卷五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07页。
(11)《旧唐书》卷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41页。
(12)参见徐道邻《宋朝的刑书》,《宋史研究集》第8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6年版,第313—346页;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论著从《宋刑统》与《唐律疏议》内容与体例等方面的差异,说明《宋刑统》并非唐律的翻版。
(13)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宋初《重详订刑统》基本上照抄唐律,正如一些宋人所指出,其中不少条文已与宋代社会现状相脱节。”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文史》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7页)。
(14)郭东旭先生指出:“《宋刑统》只是北宋中前期的现行法,并非终宋的常法。”参见氏著《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5)张溥辑《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一○《法令》,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张溥刻节录本。
(16)《唐律疏议》卷三○《断狱》,第562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三,真宗咸平元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校点本。
(18)《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63页。
(19)《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第4963页。
(2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六七《刑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3页。
(21)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1—3082页。
(22)戴建国:《点校说明》,谢深甫等纂修,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3)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淳熙事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1页。
(24)王德毅:《关于〈庆元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5页。
(25)《关于〈庆元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第4页。
(26)格雷·多西(G.Dorsey)提出“法文化”的观点,认为法律是组织和维护人类合作诸事例中安排秩序的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参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8—271页。
(2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8)以上引文见《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第493页。
(29)以上引文见《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1页。
(30)《唐律疏议》卷一《名例》,第16页。
(31)《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2页。
(3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因奸射射》,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页。
(33)以上引文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因奸射射》,第448—449页。
(34)《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1页。
(35)钱大群《唐律研究》一书认为,唐律无强奸幼女之条文,这是“唐代立法者的疏漏和不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36)《元史》卷一○四《刑法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54页。
(37)申时行、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一七四《刑部十六·罪名二》,明万历间司礼监刻本;唐绍祖等纂《大清律例》卷三三《刑律·犯奸》,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3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第343页。
(39)《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3页。
(40)所谓“义绝”,指“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参见《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第267页。
(4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54页。
(42)例如,士大夫的“暧昧”事件频频遭到台谏官的弹劾,“内则言事官,外则按察官,多发人闺门暧昧,年岁深远,累经赦宥之事”(《长编》卷一六三,仁宗庆历八年二月甲寅条)。地方官若放荡淫狎,也会遭到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不少这类案例,参是书卷二《知县淫秽贪酷且与对移》等。
(43)〔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44)唐代贱民分为官贱与私贱两类,官贱有奴婢、官户、杂户、工乐户、太常音声人五种,私贱有奴婢及部曲两种。参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46页。
(45)《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第334页。
(46)《唐律疏议》卷四《名例》,第88页。
(47)《唐律疏议》卷一七《贼盗》,第132页。
(48)《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第270页。
(49)《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第501页。
(50)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页。
(51)《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杨际平:《唐宋时期奴婢制度的变化》(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及戴建国《“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文都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研究。
(52)《宋刑统》卷六《名例律·杂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53)以上引文见《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第120—121页。
(54)《宋朝的奴婢、人力、女使和金朝奴隶制》,第201页。
(55)《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56)《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4页。
(57)《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第493页。
(5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第1页。
(59)参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2—74页。
(60)《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第493页。
(61)《庆元条法事类》卷八○《杂门·诸色犯奸》,第612页。
(62)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妻背夫悖舅断罪听离》、《妇以恶名加其舅以图免罪》、《子妄以奸事诬父》、《既有暧昧之讼合勒听离》等,第379、378—388、388、388—3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