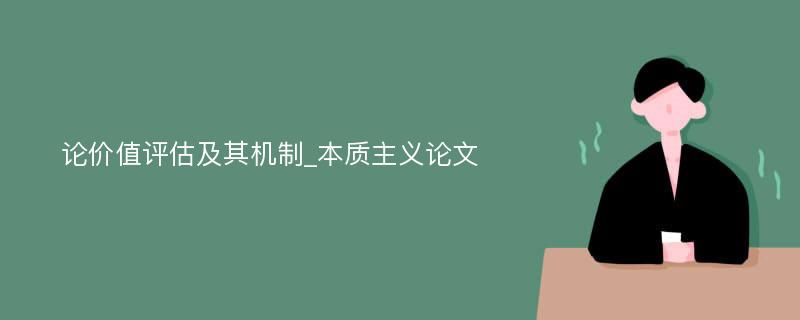
略论价值评价及其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评价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B018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价值及其评价问题作为经济转型的先导和理论表现,逐步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得到不同学科多视角的深入考察。本文主要以对评价本质的哲学分析为切入口,通过对主体需要的考辨,从而揭示出评价的内在机制。
一、评价及其本质
人类认识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随着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客观事物进入人对象性活动的领域,成为人改造和认识的对象,从而产生了对象对主体、客观世界对人的意义问题,亦即价值问题。
价值既然指涉的是客体对主体、客观世界对人的意义,所以就其本质而言,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关系范畴。这种特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如果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对于主体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并有利于主体的存在、发展和完善,那么,对主体而言,该客体就体现出对主体的价值。相反,如果客体的特有属性和功能不仅不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而且妨碍了主体实现某种需要,该客体对于主体就有消极的否定的意义,即无价值。但是,问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这种需要与满足、意义与无意义、价值与无价值之间的关系,又是通过什么以及如何来确定的呢?这必然会涉及评价问题。
所谓评价,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客体是否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所做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它以价值为对象,以确定事物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为目的,是主体在对客体的属性、本质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做出的评判。可见,评价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一种认识活动,或者说认识活动内在地包含着评价。
认识过程内在地包含着评价,这首先表现在作为认识成果的“定义”之中。列宁曾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一一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也就是说,作为事物的完满定义,既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又要包括事物同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因为从动态的角度看,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事物的认识所获得的并不是光溜溜的关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而是同时涉及到人的需要的。所以,作为把“全部实践”都包括在内的“完满定义”,必须既包括认知又包括评价。
认识内在地包含着评价还表现在评价在认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或者说评价本身具有认识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评价的目的得到说明。评价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确定为我之物的功能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既对对象的属性、功能、本质和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有所认识,又对人本身的需要即对人的本质力量有所认识;同时,还必须在这两种认识的基础上,对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做出评判,而评判本身又包含着一定的观点,观点作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本身是具有认识功能的。所以,就评价作为确定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反映,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功能。
当然,从广义的角度我们承认认识包括着评价,承认评价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反映,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可以把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区分开来加以分别考察,也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认识过程中认知和评价的区别。实际上,评价与认知虽然都是作为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的反映,但二者仍然有着原则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我们尽管可以从诸多方面予以说明,但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认知与评价所反映的主客体关系的不同。
众所周知,认知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物,在认知过程中,对象总是在主体之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这样,主体才有可能客观地反映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由此便决定着在认知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外在关系。与认知过程中主客体的外在关系不同,评价在于把握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所以评价的对象是为我之物,评价就是要把握“物”与“我”处于一定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物的功能、属性,亦即把握一定关系中的为我之物对于主体需要而言的何种功能。这样一来,在评价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或者说评价过程中的主体需要及其状况与客体属性及其所呈现的功能之间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一方面,从客体的属性、功能来看,对象的属性、功能是客观的,不以主体的需要为转移,它既可以是主体需要的,也可以是主体不需要的。但是由于评价所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外在关系,所以客体属性、功能的客观性又离不开主体的需要。离开了主体的需要及其人与物的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客体的属性和功能。另一方面,从主体需要来看,主体需要本身是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它不仅不以客体的属性、功能为转移,甚至相反——主体的需要、状况的改变,有时会影响到客体功能的显现。但是主体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所指涉的对象又是不同的,主体需要指涉的是主体本身,主体需要的满足指涉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就主体需要而言,具有对于客体属性功能的独立性;就主体需要的满足而言,又离不开客体的属性和功能,离开了客体的属性和功能,主体需要的满足根本无从谈起。可见,评价作为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其本质在于客体的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内在统一。
二、主体的需要及其特点
当我们把评价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把评价的本质规定为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的内在统一的时候,无疑意味着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不同于认知关系,它不是主体向客体的趋近,而是客体向主体的趋近。与此相适应,评价则是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内在尺度,对客体向主体趋近过程所发生的价值关系做出的评判。这样一来,要真正揭示评价的本质和内在机制,还必须对主体需要及其特点做进一步考察。
从远古的时候起,需要就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而被人类所意识到。但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作为人的需要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并以欲望、动机、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等主观形态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理论体系中,需要总是被看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来源于个体意识或“神”的旨意的精神力量。
实际上,从最原初意义上,需要不仅不是一种精神力量,而且也不是人类所特有的。早在物质运动的生物阶段,就已经产生了需要。当然,处在这种阶段和水平上的需要,主要与生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相联系,是狭隘的、有限的,并以自然的需求与自然的满足为特征。换言之,这种阶段和水平上的需要只是萌芽形态的。
随着物质运动形式向高一级的发展,亦即随着从动物适应环境的本能活动向以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的发展,需要也逐步得到提升,成为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无限发展着的活动。这种活动与动物本能的需要和自然满足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状态不能满足人的全部需要,“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9页)。由此,“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3页)。正因为人的需要是与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实践活动密切关联的,是在劳动生产中被不断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的需要就超越了动物需要的狭隘性、有限性而成为无限发展着的活动。
当我们从劳动活动的角度把人的需要看成是无限发展着的活动的时候,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实践活动的需要是人最根本的需要或者第一需要。正是这种第一需要,从而使人超越了自己的自然需要的界限,不仅创造出了无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在这种满足中又发展出了新的需要和满足新的需要的方式。同时,也正由于人的需要是同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从而说明了人的需要同人的本质的内在一致性。这样,人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创造、丰富自己需要的过程,也就是人的本质被不断充实、丰富的过程,二者在实践基础上达到了动态的一致。
三、评价的机制
以对评价的本质和主体需要的考察为基础,我们进而可以对评价的机制做一些分析。承上所述,评价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主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并且这种解决是以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但是,由于评价活动不同于认识活动,评价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是内在的,评价活动也主要是客体向主体的不断趋近过程。所以,评价活动的发生,主要表现为主体客观需要被不断地提升为主体价值意识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以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活动来考察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否认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而是特别注重人的现实活动在意识中的“反射”和“回声”。从这样一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出发,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主体的需要尽管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客观历史过程,但这一客观历史过程总有其在意识上的“反射”和“回声”,并且只有当这一客观历史过程能够在意识上有所“反射”和有一定“回声”的时候和地方,它才能够作为意识到了的存在即主体的需要发生作用,而需要在意识上产生“反射”和“回声”过程,也正是客观需要被逐步提升为价值意识的过程。
客观需要被提升为价值意识的第一种形式是欲望。欲望是价值意识的最初形态,它直观地、自发地、具体地表现着需要。但这并不是说欲望一经形成,就是凝固不变的。欲望如果稍加发展,并注入主体的目的性,就会被提升为愿望和动机。与欲望相比较,愿望有更明确的目的性,而动机则使欲望延伸到人的行为领域。当欲望经过进一步的沉淀,并逐步成为比较主动、自由的心理状态时,就会形成一定的兴趣。兴趣仍然以人的需要为基础,或者说需要使兴趣成为必要。
在客观需要被提升为价值意识的过程中,意志是比较高级的形式。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体现,具有自愿选择的自主性和自愿选择之后在行动中不畏困难一贯坚持的专一性。正因为意志具有这种双重品格,从而使它能够将欲望、动机、兴趣等价值意识综合、协调起来以实现既定的目的,所以在价值评价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意志的核心和实质是目的,而目的又是人的价值关系和需要的现实形式,所以意志的自主和专一又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主体需要的反映并受主体需要的制约。
在客观需要被提升为价值意识的过程中,理想是最高级的形式。对于理想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规定,就最一般的哲学层面而言,理想无非是现实的可能性与人的需要相结合而观念化的形态。由于理想既涉及现实的可能性,又涉及人的需要,同时又将现实的可能性与人的需要相结合并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决定了它成为规范和指导人们进行价值评价的主要观念。
主体的客观需要被不断地提升为各种价值意识是评价活动的重要前提,但还不是评价活动本身,因为评价的目的主要在于确定为我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所以评价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利益,而利益又可归结为幸福、快乐。就此而言,评价实际上就是解决利害和苦乐的问题。对于利害和苦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就哲学史的角度看,无非是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两种理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以墨家和儒家为代表,墨子将利规定为“所得而喜也”,把害规定为“所得而恶也”;孟子相反,对利害做了非功利主义的理解,他强调“可欲之为善”,并用类比的方法论证了人对善和美德的追求是令人喜悦的。尽管儒墨在利害的看法上有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之分,但能否满足人的需要、能否给人带来利总是共同的一致的标准。我们且不论这种满足、利是何种意义上的,只要能够给人带来利,使人觉得它是可爱的、可喜的,人们就给以肯定的评价;相反,如与人的需要相矛盾,得到它使人感到厌恶、可憎,人们则给以否定的评价。
与利害相联系的是苦乐问题。人作为一种生物,天性中总有求乐避苦的一面。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正统派儒家从极端非功利主义出发,否定人求乐避苦的自然属性,最终导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但事实上,人求乐避苦的自然属性是无法抹杀的。人为地、主观地无视人的自然属性,过分强调人的道德属性,强调人的行为及其评价的非功利性,必然会造成或者勉强或者虚伪的人格,并最终导致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所以,在解决利害苦乐问题时应有科学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就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劳动活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出发,把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利益作为评价利害、苦乐的基准,这是评价的宏观机制。
利与害、苦与乐不仅是相反的,有性质上的差别,而且还有数量上的差别。所以,还必须对利害、苦乐进行比较、权衡和选择。对利害、苦乐进行比较、权衡和选择是评价的微观机制,包含着两个环节:其一,主体对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利害、苦乐进行分析、比较以决定取舍;其二,以对苦乐、利害的分析、比较为基础,并以在需要中提升出来的价值意识作为权衡的标准进行选择,以指导行动。任何评价性活动,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离不开这两个环节。
当然,作为评价的微观机制,人们在对利害、苦乐进行比较、权衡、选择的过程中,还会遇到手段与目的、精神与功利的矛盾。因为“利”作为最广义的好,凡对人有利就理论上来说,应该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利作为人欲求的目标,要实现它,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而手段和目的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同时,由于人的需要的多层次性,决定着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是多层次的,其中精神价值与功利价值是两个最基本的层次,而这两个层次在现实的价值运动中也不总是一致的。所以,如何处理好手段与目的、精神与功利的关系,也是价值评价的内在机制之一。
标签:本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