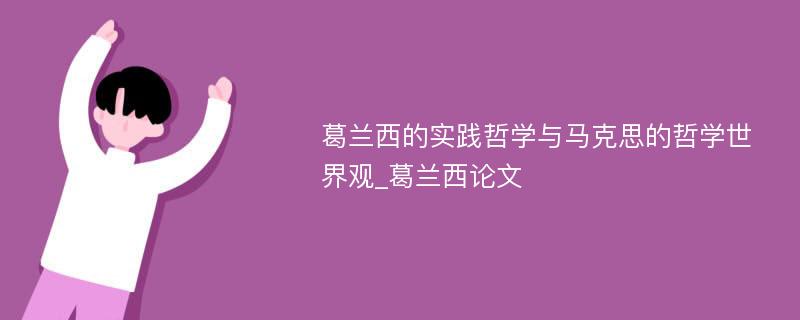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世界观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试图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确立一种以依存于人的外部自然为实践内部对立同一一方的实践一元论。它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在于:前者只讲实践而不讲唯物主义,否认外部自然界独立存在于实践之外;后者则不仅强调实践,而且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坚持称自己的观点为唯物主义的。据此,作者指出,抹煞葛兰西实践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原则界限,把二者等同起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重申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引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概念的广泛重视和深入研究,这无疑是葛兰西实践哲学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中期,身陷法西斯主义囚牢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他所写《狱中札记》中,曾经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准绳,来评论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状况,并对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趋向”进行了猛烈的评击。葛兰西写道:“在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条提纲中批判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彼此片面的立场正在重复着,现在还和那时一样,虽然处在历史的一个较为发达的时刻,在实践哲学发展的更高的水平上进行综合还是必要的”;与普列汉诺夫自我标榜的正统趋向相反,他“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去了”,而且“普列汉诺夫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实证主义方法的典型,并证明了他的思辨和编史的能力的贫瘠”〔1〕。与此同时,葛兰西系统地展开了在他看来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哲学路线的实践哲学的论述。
应当强调指出,在20世纪20-30年代,就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去把握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质,以此为标尺去评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状况,去揭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趋向的缺陷,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事情过了六七十年之后,在我国学术界深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时候,当有些同志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提出来,说它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说葛兰西坚持的实践第一原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说葛兰西从实践意义上理解物质的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时候,深入剖析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实质,弄清楚它同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关系,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一项不可推诿的重要任务。
一、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企图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尽管在《狱中札记》的许多地方,葛兰西是把他从拉布利奥那里借用来的“实践哲学”这个名词当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的,但他毕竟赋予它以他自己的涵义,其中之一便是企图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在《狱中札记》的“辩证法”篇中,他说:“只有当着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完整而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而实践哲学则在其超越作为过去社会的表现的传统的唯心主义和传统的唯物主义,而又保持其重要要素的范围内做到这点。如果只把实践哲学看作臣服于另一种哲学,那就不可能领会新的辩证法,然而,〔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它(指辩证法)来实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2〕。
葛兰西从实践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来论证其“超越”性:“实践哲学是以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喀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的这种历史观。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峰”〔3〕。在这个过程中,当社会经历变革, 新兴阶级从全民中崛起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人民文化的繁荣,就会出现唯物主义的昌盛,而衰老的阶级则抓住唯灵论不放。“处在法国革命和复辟的中途上的黑格尔,给予思想生活的两个要素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以辩证的形式,但是,他的综合是‘一个以头站地的人’”〔4〕。 黑格尔死后,他的门徒破坏了这个统一,有一些人回到了唯物主义的体系;他们接受了过程和历史性观点,却排除任何主体活动的思想,原因和过程被确定为外在的;另一些人则回到唯灵论的体系:他们意识到了人的活动的基本本质,却按意识或精神来定义活动,他们强调变化和主体性,却把主体理解为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一切经验,以便重建辩证统一的综合,‘用脚站地的人’”〔5〕。但是,在马克思以后, 实践哲学又遭到了黑格尔的学说所经历过的遭遇,人们同样企图把它扯碎为几个部分:正统派企图把实践哲学和传统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回到了康德主义;一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则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要素。所以,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正面临着文化-哲学的综合的任务。
那么,葛兰西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到底是怎么看的?实践哲学又是怎样超越和综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
对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问题,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并没有提出一个全面的定义和界说,但从一些有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这些论述大致分为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唯物主义与宗教的关系。
在批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一书时,葛兰西谈到“在常识中居支配地位的,是‘实在论的’、唯物主义的要素,原始感觉的直接产物,这决不同宗教的要素相冲突,远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这里,这些要素是‘迷信的’和非批判的”〔6〕; “民间宗教是非常地唯物主义的”〔7〕。但是,在札记《术语和内容的问题》中, 当葛兰西回顾“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时却说,“在19世纪头50年中,对于‘唯物主义’此词,不应仅在其有限的专门的哲学意义上去理解,而且具有在随着现代文化的崛起和胜利发展而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辩论中,论战地获得的较为扩展的意义。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被赋予了任何一种从思想领域中把先验排除出去的哲学学说,所以,它不仅被赋予了泛神论和内在论,而且被赋予了政治现实主义所鼓舞的任何实际态度”;“唯物主义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灵论即宗教唯灵论的对立面”,“在常识的术语中,唯物主义包括一切倾向于把生活的目的放在这个地球上而不是放在天国里的一切东西”〔8〕。 忽而说唯物主义的要素决不同宗教的要素相冲突,甚至认为民间宗教是非常地唯物主义的,忽而又说唯物主义是宗教唯灵论的对立面,指把生活的目的放在这个地球上而不是天国里的一切东西。葛兰西关于唯物主义的这两种论述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关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的关系
正因为葛兰西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就出现了忽而把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列入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忽而又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划出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外的现象:根据唯物主义是宗教唯灵论的对立面的定义,葛兰西说“人们能够把整个黑格尔主义、一般地说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感觉主义和法国启蒙哲学统统包括在唯物主义的标题之下”;而在同时,葛兰西又赞扬新康德主义者朗格把费尔巴哈排除在外的唯物主义定义,说他(指朗格)“对唯物主义有一个十分精确、明晰和有限的概念”〔9〕。
第三,关于机械唯物主义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关系。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致力于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可是,他又不时地把机械、庸俗唯物主义和哲学唯物主义等同起来,特别是当他正确地批评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为一种被认为可以按照自然科学方法来构造的、称作社会学的历史和政治理论,和另一种本来意义上的哲学时,竟脱口而出地说“哲学的〔唯物主义〕别名是形而上学的或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10〕。这里姑且不论布哈林的哲学世界观如何,哲学唯物主义却决不等同于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它是哲学上一切形色的唯物主义的总称,其中也包括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第四,关于马克思同唯物主义的关系
正因为葛兰西把哲学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因而他就千方百计地否认马克思同唯物主义有任何关系。他说,作为实践哲学创始人的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称作是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时,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未使用‘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11〕。
应当着重指出,葛兰西关于马克思同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这一段论述,在三个基本点上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是关于马克思是否把自己的观点称作唯物主义的问题。事实是,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过“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两者结合的真理”〔12〕的论述,但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究竟是费尔巴哈的思想,还是他本人的思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然而, 无论如何, 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就在反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明确指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是“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13〕,而且在以后始终坚持称自己的观点为唯物主义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14〕;在1868年12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又强调“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15〕。面对马克思的这些明确论述和重申,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从来不曾把自己的概念称作是唯物主义的”呢?十分明显,葛兰西的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
二是说马克思在写到法国唯物主义时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这也是和事实不符的。事实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读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例如,在那里,马克思明确指出,“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16〕。怎么能够把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肯定评价,纳入葛兰西所谓“马克思总是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地批判法国唯物主义”的框框呢?
三是葛兰西把“合理辩证法”同“唯物辩证法”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的说法, 同样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 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紧接着,马克思又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1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是明确地说明了他是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角度来标出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的吗?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从未使用过“唯物辩证法”这个公式呢?
至于把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对立,表述为“神秘辩证法”和“合理辩证法”之间的对立,原是渊源于马克思关于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8〕的论述,恩格斯据此而谈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之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19〕。但是,在这里,所谓“神秘辩证法”同“合理辩证法”的对立,也是从属于“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其它的意义上,更不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说的。为什么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秘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他〔指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的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20〕。为什么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理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之后,也就一举而剥除了它的神秘形式、神秘外壳,恢复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关系。所以,把唯物辩证法和合理辩证法对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
那么,葛兰西对唯心主义又是怎样看呢?
葛兰西对唯心主义也没有作过明确、系统的规定,但从他一些有关的论述中,同样可以看出他对唯心主义的基本态度。
早在1917年底,葛兰西在其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文章《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中,就宣称:布尔什维克在这一革命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种永恒的,代表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却被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外壳所玷污了的思想”〔21〕。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成是由于继续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唯心主义思想,毋庸进一步分析,就可看出这是对唯心主义的歪曲的赞誉。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虽然没有再重复这种说法,但是对实践哲学的产生,是由唯心主义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所完成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例如,在“思辨哲学”篇中, 葛兰西写道:“《神圣家族》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一段十分好和十分清楚地描写了实践哲学的产生:它是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所完成的并和人道主义相溶合的‘唯物主义’。同样真实的是,随着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完善,只有哲学实在论还留下来”〔22〕。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首先是指的黑格尔主义。正因为葛兰西把实践哲学的发生看成是由于思辩哲学本身的工作所完成的,所以,他就十分自然地把实践哲学的发生看成是由于思辨哲学本身的工作所完成的,所以,他就十分自然地把实践哲学同黑格尔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加图”〔23〕;“在某种意义上,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24〕;“无疑地,(相对地讲)黑格尔主义是我们作者〔指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动机”〔25〕。
有人说,葛兰西是在反对任何一种片面化倾向的意义上谈论实践哲学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的,然而,上引论述却清楚地说明了葛兰西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看法本身就是非常之有倾向性的,因而他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综合”和“超越”,就不能不说是极其倾斜的。
这种倾斜首先表现在葛兰西把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说成是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又把实践哲学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说成是继承黑格尔的这种超越而来的。例如,在《“正统”的概念》篇中,葛兰西在论证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动机时,就说过“特别因为它企图在一种新的综合中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概念,这种新的综合无疑地具有十分异常的重要性,而且它代表了哲学探究中的一个世界-历史要素”〔26〕。显然,如果事情真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对黑格尔亦步亦趋的话,那就只能陷入唯心主义,而根本谈不上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超越。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葛兰西把这种超越性说成:不是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而是用内在性和超验性的对立去看待问题。内在性,原是传统思辨哲学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中心概念之一。“内在”这一术语,按其思想意义来说,源于亚里士多德;其字面意义最初开始应用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内在”的现代含义是康德提出来的,内在与超验不同,表示某物存在于自身之中,在唯心主义看来,哲学的内在历史就是把哲学看作是一种主要由自身规律决定的过程,而排斥经济、阶级斗争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哲学思想演变的影响。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把内在性接过来当作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看来似乎只有实践哲学才是唯一首尾一贯的‘内在论’概念”〔27〕。葛兰西一再谈到“实践哲学设想内在性的特殊方式”〔28〕,这就是借助于法国的政治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把德国的古典哲学提出的思辨形式的内在性概念转变为“历史主义形式的内在性概念”〔29〕。这样,实践哲学就“从这三种活生生的思潮的综合,而达到清除了先验性和神学的一切痕迹的新的内在性概念”〔30〕;“实践哲学继续了内在性的哲学,但清除它的一切形而上学的装置,并把它带到具体的历史领域中去”〔31〕。说来说去,实践哲学设想内在性的特殊方式、它的新的内在性概念,都表现在把内在性“带入具体的历史领域”,使之成为“历史主义形式”的内在性概念。所以,葛兰西的内在性概念最终就是把自然界作为外在的超验因素排除在外的绝对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和顶点。从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出现代唯心主义和实践哲学。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有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历史主义和绝对人道主义”〔32〕。显然,用这样的内在性与超验性的对立代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去观察问题,既没有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者,更不能超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
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确立实践一元论以及它同马克思思想的原则界限
在《狱中札记》的“认识的客观性”篇中,葛兰西在谈到“唯心主义的‘精神’的一元论”、“实证主义的‘物质’的一元论”之后,紧接着就指出研究实践哲学的一元论的问题。他写道:“在〔实践哲学〕这个场合下,‘一元论’此词的意思是什么?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那就是某种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解地联结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对立的同一性,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33〕。显然,所谓实践哲学的一元论,就是指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的同一性,亦即人的活动中以某种组织起来的物质为一方,以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对立的同一性。
在《札记》“‘创造性’哲学”篇中,葛兰西还写道:“为了避免唯我论,同时又避免包含在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整理的活动的机械论概念,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意志’(归根到底它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当作哲学的基础”〔34〕。显然,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主张把意志即实践当作哲学的基础,这正是在确立实践一元论。
在《札记》“‘正统’的概念”篇中,葛兰西总括了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认为“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思想,绝对的世俗化和此岸性,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人们正是必须沿着这条路线追踪新世界观的这条线索”〔35〕。大体说来,葛兰西所说的这种追踪主要集中在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上:
首先是对外部自然界的看法和态度。葛兰西把自然本身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札记》“物质”篇中,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自然所提供的机会,并不是对于预先存在的力量--对物质的预先存在的性质--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同社会兴趣、同生产力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紧密相联的创造?”〔36〕他承认,它作为一种抽象的自然力,甚至存在于它之被归结为一种生产力之前,但他却认为在那时它处于“历史的‘虚无’”状态〔37〕。这就说明,葛兰西是把自然包摄在人类历史之下的,他也是据此而把自然归结为被人所支配和利用的对象的。例如,在《札记》“进步与生成”篇中,葛兰西一再谈到“要加以统治的自然”、“人支配自然”〔38〕,认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的合理统治。在实际上,葛兰西也正是据此而批评卢卡奇那种否认自然界有辩证法存在的观点,是预先假定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二元论”,“落入到为宗教和古希腊-基督教哲学所特有的、也为在实际上(除了在口头上之外)并没有把人和自然成功地统一起来和关联起来的唯心主义所特有的自然观中去”〔39〕的。也正因为这样,葛兰西的这种人类中心论,被马丁·杰称作“族类的帝国主义”〔40〕。
其次是把客观事物溶解在人的实践中,因而再三再四地强调要从人同自然的关系上去认识客观实在和物质。在他看来,哲学之所以是“创造性的”,就在于它指出了“并不存在独立的、自在和自为的现实,而只存在处于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关系之中的现实”〔41〕。因而,“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利益”〔42〕。他认为,常识是在现实、世界由上帝在人之前和独立于人之外创造出来的范围内肯定现实的东西的客观性的。这样,它就代表了一种神话学世界观的表现。葛兰西觉得,既然是人创造了一切价值,其中也包括科学的价值,那么,没有了人的活动,客观性会是什么呢?只能说是一片混沌,也就是虚无。
接着,葛兰西就从正面、反面和各个侧面来展开他的这个论点:在《札记》“康德的本体”篇中,他说,看来,“现实的外部客观性”问题是就它同“自在之物”以及康德的“本体”概念相联系而言的。看来难以排除这样的假定:“‘自在之物’是从‘现实的外部客观性’和从所谓希腊-基督教实在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中导衍出来的,从整个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产生了新康德主义和新批判学派这个事实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导衍”〔43〕。在“所谓外部世界的现实”篇中,他说,“广大公众甚至不认为能够提出诸如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人们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会引起一阵压制不住的大笑的爆发。公众‘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地实在的,但是问题就产生了:那个‘相信’的根源是什么。‘客观地’此词的决定性价值是什么?在事实上,这个信仰具有宗教的根源,即使那个分享这个信仰的人对宗教并没有兴趣”〔44〕。那是因为一切宗教总是教诲人说,世界、自然、宇宙都是上帝在创造人之前所创造的,所以人来到已被一劳永逸地编好目和规定好的现成的世界上,这个信仰就变成了“常识”的不可变动的教义,即使宗教感情已变得缓和和减轻或取消了,它还像以前一样顽固地存在着,结果是,求助于常识经验以便对主观主义一笑置之,这是一种暗中回到宗教情绪去的“反革命”的计谋。葛兰西说,“看起来似乎可能存在着一个在历史之外和人类之外的客观性,但是,谁是判断这种客观性的法官呢?谁能使自己采取这种‘宇宙本身’的观点,而且这样一种观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的确可以说,在这里,我们所涉及的是上帝这个观念的残余,正是一个神秘形式的未知的上帝的概念的残余”〔45〕。
葛兰西认为,既然恩格斯在论证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时,是求助于历史、求助于人以证明客观实在的,那么,由此可以结论说:“客观的总是指‘人类地客观的’,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地主观的’相符合,这就是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人客观地认知,这是在对于被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单个的文化体系中的整个人类来说知识是实在的范围内来说的”〔46〕。葛兰西还批评“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客观的’观念显然打算指一种甚至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性。但当人们说即使人并不存在,某种实在也会存在时,人们或者是在用隐喻说话,或者落入到一种神秘主义去了。我们只是在同人的关系中去认识实在,而既然人是历史地生成,认识和实在也是一种生成,那么,客观性也是如此,等等”〔47〕。
葛兰西特地把东西南北这样的方向问题挑出来作为实例去论证他的观点。他说,“为了准确地理解外部世界的现实问题所可能意味的东西,值得把‘东’和‘西’的观念当作例子提出来,即使分析说明它们无非是一种约定的,即‘历史的-文化的’构造,它们也没有不再是‘客观地实在的’”。他援引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说,要是地球上没有人的存在,我们就不能想象伦敦或爱丁堡的存在,但我们能够想象空间中两点的存在,一点北,一点南,现在的伦敦和爱丁堡就在那里。葛兰西据此引申发挥说,人们根本不能想象只是在人存在时才存在的任何事实或关系,“要是没有人,北-南或东-西意味着什么?它们是现实的关系,然而要是没有人,没有文明的发展,它们就不会存在。显然,东和西是任意的和约定的,即历史的构造,因为在现实历史之外,地球上的每一点都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48〕。他认为,在东西南北这些地理名词上面,是附加有历史内容的,因此,“东和西这些说法就指出了不同的文化复合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样,当意大利人谈到摩洛哥时,往往称之为一个‘东方’国家,指它的穆斯林和阿拉伯文明。这些参考系是真实的;它们符合于现实事实,它们允许人们在陆上和海上旅行,达到人们决定达到的地方,‘预见’未来”,反之,“要是不理解这种关系,人们就不能理解实践哲学,它的在同唯心主义和同机械唯物主义相比较中的位置”〔49〕。
那么,对于物质又该怎样看呢?
在“物质”篇中,葛兰西说,“显然,对于实践哲学来说,对于‘物质’,既不应当从它在自然科学中获得的意义上来理解(物理,化学,力学等--要从其历史发展中来注意和研究的意义),也不应当从人们在各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中发现的任何意义上来理解,应当考虑到一起构成物质本身的各种物理(化学、机械的等等)特性(除非人们求助于康德的本体概念),但只是在它们变成一种生产的‘经济要素’的范围内。所以,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组织起来,而自然科学则应当相应地被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一种人类关系”〔50〕。
从上引葛兰西的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所确立的,是一种使外部自然界依存于人,依存于人的实践,使之成为实践内部对立的同一性中的一方的实践一元论。这种实践一元论虽然高扬了人的实践,但由于其不仅不坚持、而且竭力抨击唯物主义,还否认外部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之外,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只讲实践而不讲唯物主义的哲学。这种实践一元论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新唯物主义”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其原则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在马克思那里,不仅高扬实践,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要“从主体方面”,“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且认为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51〕;不仅指出人们的感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而且强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2〕。
和葛兰西所说的相反,马克思不仅再三强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且确认外部自然界优先地位的思想,始终作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基石之一,出现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之中。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53〕;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5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是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强调“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而反对“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56〕。
所以,抹煞葛兰西实践哲学同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原则界限,把两者等同起来,说实践哲学表现出了葛兰西对马克思的深刻理解,说葛兰西坚持的实践第一原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说葛兰西从实践意义上理解物质的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思想等等说法,是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
三、国外学术界对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分析评价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他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右倾社会主义,在被捕入狱后,又强忍着囚禁生活对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强忍着病痛,完成了近3000页的《狱中札记》,为现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所有这一切使葛兰西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后人的广泛尊敬,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都是如此。那么,对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外国学术界又是怎样分析评价的呢?
已故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是葛兰西的同乡、同学、同志和战友,他推崇葛兰西是其“同龄老师”。他在1927-1964年间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致力于弘扬葛兰西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把葛兰西哲学思想上的误差也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陶里亚蒂分析了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明确指出此文既包含了“要求解放的呐喊”,又“包含着错误和我们无法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提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写道,在该文中,“‘《资本论》’指的便是卡尔·马克思的巨著,‘革命’指的是1917年10月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十分明显,标题本身便是错误的,文中的某些判断也不对”:该文说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说他们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在马克思那里却被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外壳所玷污。陶里亚蒂认为,“这个论点也是我们今天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马克思身上受到污染,而是在那些进行苦苦宣传的论文和小册子中受到了污染,变成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57〕。
原苏联科学院集体编著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书一面肯定了葛兰西所说绝对历史主义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在这一概念中暴露出了历史主义的实质本身所产生的片面性的因素:⑴对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注意得不够,因而对自然科学问题和认识问题注意得不够;⑵在某些场合,对社会经济结构注意得不够”,并强调“哲学和历史的某种等同,也就是现实和意识的某种等同(葛兰西称为‘绝对历史主义’)会导致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58〕。
日本共产党领袖和理论家石破哲三在60年代中期就发表长篇文章剖析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认为葛兰西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就是由于他把以物质、自然为一方,以精神、意识为另一方,理解成统一在人的实践之中的两种因素的缘故。这种“实践哲学”事实上把自然、物质还原为实践中同人的活动合为一体的、从而归根到底要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一个从属性因素了。所以,尽管葛兰西试图按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阐发实践,结果却只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向改写了《提纲》。葛兰西实践哲学中所说的物质、自然,是人类社会中被组织起来的自然,作为“物质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的物质,而先于、外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存在,却从一开始就被葛兰西当作实践哲学对象之外的东西加以舍弃了。石破哲三认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实践的理解,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葛兰西却把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除去,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推广到对自然的认识中去。这样,实践哲学在其最初的出发点中,就抛弃了独立于人的活动的、先于人的活动的自然的存在,成为放弃唯物主义而接近唯心主义的独特形式,而葛兰西把客观的说成是普遍地主观的观点,则接近于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立场。石破哲三由此引出结论说,虽然葛兰西的哲学是从要在哲学上论证人的革命实践的意义,并抵制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潮流,以此来复兴作为“全面独特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正当要求出发的,但“在实际上,它却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道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这种设想,归根到底也只是造成了放弃唯物主义和对唯心主义让步的结果” 〔59〕。
英国学者约翰·霍夫曼在《葛兰西的挑战》一书中,批评葛兰西把庸俗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使他去拥护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和绝对历史主义和绝对人道主义,使外部世界依存于人的认识。而这种绝对历史主义导致存在和思维的一种思辨的神秘的同一性,理论和实践的同样神秘的同一性,导致一种抽象的实践,它显然是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支撑完全不符合的〔60〕。
都柏林的科学哲学家海伦娜·希曼指出,葛兰西的哲学方向是决定性地片面的,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和哲学史上唯心主义传统相连续的特征,而故意忽视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和唯物主义传统相连续的特征。如果说,布哈林由于忽略辩证法、历史而偏爱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话,那就可以从相反方面指责葛兰西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唯物主义重点,而偏爱历史活动的辩证法〔61〕。
意大利学者丁伯纳罗致力于探索葛兰西实践哲学向唯心主义倾斜的原因。他把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看作是“对于唯物主义的稀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列宁主义者在哲学上宣布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哲学领域中的主要敌人并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实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歪曲,同时又误认为“唯心主义的文艺复兴”可以作为医治第二国际的渐进主义和议会主义的补药而发挥作用。为什么在20世纪,葛兰西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会用反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去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丁伯纳罗认为,要是仅仅用克服第二国际的无为主义和庸俗进化论去解释其原因,那显然是不充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葛兰西那里,缺乏唯物主义。葛兰西本来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从克鲁齐对它所作的工具性的使用中赎救出来,结果却把突出性给了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被新唯心主义挑选出来和孤立起来的特征。而当葛兰西一旦接受了唯心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和宗教同样是“先验”和“形而上学”的诡辩,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所打算反对的、在唯心主义内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一方, 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62〕。
我们研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其目的首先是为了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高度,去总结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而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无疑地是这一链索中的重要一环。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第二国际的、还有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突出的实践概念,得到了重申和强调,这一切无疑地都是葛兰西实践哲学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个环节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又被偏离到和机械唯物主义相反的方向--唯实践主义去了,这无疑地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缺陷所在。为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经验教训,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明确指出葛兰西实践哲学所包含的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无疑地是非常必要的。反之,要是随意抹煞或夸大其中的一个方面,则显然无益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注释:
〔1〕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71年伦敦版,第402、387页。
〔2〕《狱中札记(选)》,第435页。
〔3〕同上引,第395页。
〔4〕同上引,第396页。
〔5〕《狱中札记(选)》,第396页。
〔6〕同上引,第420页。
〔7〕同上引,第396页。
〔8〕同上引,第454页。
〔9〕《狱中札记(选)》,第454、456页。
〔10〕同上引,第434页。
〔11〕同上引,第456-45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版,第57、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21〕1917年12月24日〔意〕《前进!》,转引自《葛兰西(1910-1920)政治著作选集》,1977年伦敦版。
〔22〕《狱中札记(选)》,第370-371页。
〔23〕同上引,第400页。
〔24〕同上引,第404页。
〔25〕同上引,第465页。
〔26〕《狱中札记(选)》,第465页。
〔27〕同上引,第371页。
〔28〕同上引,第412页。
〔29〕同上引,第400页。
〔30〕同上引,第402页。
〔31〕同上引,第450页。
〔32〕《狱中札记(选)》,第417页。
〔33〕同上引,第372页。
〔34〕同上引,第345页。
〔35〕同上引,第465页。
〔36〕《狱中札记(选)》,第466页。
〔37〕同上引,第467页。
〔38〕同上引,第358、360页。
〔39〕同上引,第448页。
〔40〕马丁·杰:《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1984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版,第170页。
〔41〕《狱中札记(选)》,第346页。
〔42〕同上引,第368页。
〔43〕同上引,第368页。
〔44〕〔45〕〔46〕〔47〕〔48〕《狱中札记(选)》,第441、445、445、446、447页。
〔49〕《狱中札记(选)》,第447-448页。
〔50〕同上引,第465-466页。
〔51〕〔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版,第54、77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57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
〔57〕《陶里亚蒂论葛兰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193页。
〔58〕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90、492页。
〔59〕石破哲三:《现代修正主义和葛兰西的理论》,〔日〕《文化评论》杂志1964年5月号。
〔60〕霍夫曼:《葛兰西的挑战》1984年牛津版,第105-112页。
〔61〕希曼:《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哲学》,1985年伦敦版,第299-300页。
〔62〕参见丁伯纳罗《论唯物主义》, 1975 年伦敦版, 第29 -30、56、124、235-238页。
标签:葛兰西论文; 一元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文; 世界观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狱中札记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