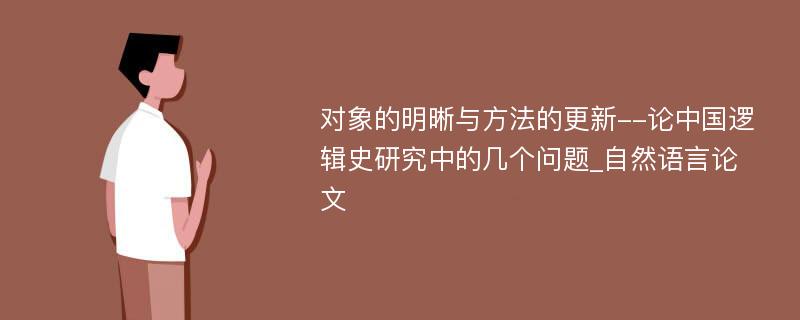
对象的明确和方法的更新——论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史研究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产生了一系列争论。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传统)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古汉语的语义学;内涵逻辑;自然语言逻辑;等等。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现代逻辑;传统逻辑;自然语言逻辑;语义学;等等。这些争论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模糊认识,这对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疑又是十分不利的。本文仅就几个基本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对象问题
当我们说研究中国逻辑史并围绕研究的对象展开讨论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这是关于逻辑的历史,而不是其他什么史,比如哲学史、认识论史、心理学史、语言学史,等等。基于这一点,可以说上述不同意见是对逻辑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也不是诸如关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归纳逻辑的分歧。在这一前提下,无论是说中国古代逻辑是形式逻辑,还是说它是自然语言逻辑,或内涵逻辑,或非形式逻辑,等等,都可以说是围绕逻辑的对象进行讨论。下面我们就围绕这几种观点进行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直接依赖于自然语言,没有使用变项,没有提出形式推理规则,因此它是自然语言逻辑(参见[1],第22页)。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第二,自然语言逻辑的特征是不是就是直接依赖于自然语言,不使用变项,不提出形式推理规则?
我们先来考察第一个问题。自然语言逻辑在我国目前似乎是研究的一个热点。许多人都说这是周礼全先生倡导的研究方向。那么让我们首先看看周礼全先生的观点。周先生认为,“正统逻辑,包括传统逻辑和正统数理逻辑,只研究命题和命题之间的真假”,“自然语言逻辑不仅要研究正统逻辑所研究的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而且还要研究各种包含了言语行为和命题的语句,如陈述句,命令句和疑问句等之间的真假关系”。([9],第29、30页)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周先生是从真假的角度来说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对象的。我们也知道,研究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是研究推理的另一种说法。因此,从研究对象这一角度说,自然语言逻辑与正统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研究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都是研究推理。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的范围还要更宽泛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说自然语言逻辑要研究正统逻辑所研究的那些东西。这句话的涵义很多,比如,研究正统逻辑所揭示的那些逻辑规律在自然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性质和意义,等等。但是基本的一点是承认正统逻辑研究的对象和成果,从而承认正统逻辑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因此可以说,自然语言逻辑是在正统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来并有待发展的。
在明确了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之后,我们再来考察第二个问题。“直接依赖于自然语言”这句话是比较含糊的。在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比较明确的表述是逻辑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参见[6],第22、25页;[2],第2页)。有人认为,以语言作为逻辑的直接对象,并非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要透过语言的表层结构去分析深层结构,透过语言形式分析逻辑形式,着眼点在逻辑(参见[1],第23-24页)。这种说法是极其含混的。如果说逻辑研究语言,那么逻辑研究的形式当然就是语言形式,怎么又会是逻辑形式呢?说逻辑研究语言,而着眼点在逻辑,那么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逻辑不是研究语言的,而是研究推理的。它从语言入手研究语言表达的推理形式,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丝毫不表明逻辑是研究语言的(参见[5]、[12])。周先生在论述自然语言逻辑时说:“逻辑结合语言,是要研究丰富的自然语言中的逻辑形式”([9],第35页)。由此也可以明确地看出,自然语言逻辑不是研究语言,而是结合语言,研究的仍然是推理。
“不使用变项”也不是可以成为自然语言逻辑的标准。一般来说,变项并不是逻辑研究的东西。中国古代语言中有“彼”、“此”这两个词,在今天看来,它们可以作变项。但是谁也不会承认,有了这两个词,就有了逻辑。在传统逻辑中,人们常常使用“凡人皆有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有死”,“所有天鹅都是动物,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所以有些动物是白的”这样的例子。这些句子表达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使用这样的例子是为了使人们不去或尽量不去考虑句子的内容,而考虑句子的形式,即“所有”、“有些”、“是”、“所以”这些逻辑常项。这就说明,一方面,逻辑研究的不是变项,另一方面,不使用变项也是可以进行逻辑研究的。既然如此,逻辑研究为什么要使用变项呢?从历史上看,亚里士多德使用一些字母作变项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出句子的形式结构,从而揭示其逻辑结构。例如,如果A属于每个B并且B属于每个C,那么A属于每个C。在这个三段论中,A、B、C是变项,用它们是为了揭示句子中“如果,那么”这样的结构以及“每个”、“属于”(是)这样的语言因素的逻辑性质,即我们所说的逻辑常项的性质,因为这些正是逻辑研究的东西。使用常识性的例子固然可以使人们尽量不去考虑句子的内容,但是使用变项则可以使人们根本不去考虑句子的内容,也就是说可以比使用例子更好地显示句子的逻辑结构。而在现代逻辑中,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都是用符号表示的。在一阶谓词逻辑中,一个形式语言一般有命题变元、个体变元、个体常元、谓词变元、命题联结词、等词、量词,等等。一阶谓词逻辑主要是研究命题联结词、等词和量词。这些都是逻辑常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有时也说现代逻辑也研究变项。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一般来说,一阶逻辑研究量词,而研究量词必须结合个体变元来进行。实际上,不用个体变项,从而不用量词来建立一阶逻辑系统也是可以的。例如,奎恩的谓词函子系统。它提供的有效推理形式和标准的谓词逻辑系统是一样的。因此,使用还是不使用带个体变项的逻辑语言只是一个记号的问题。原则上可以消除个体变项,但是使用它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公式的意指,所以在标准的系统中接受个体变项。由此说明,无论是传统逻辑,还是现代逻辑,主要都是研究逻辑常项,而不是研究逻辑变项。由于现代逻辑是用符号表示的,所以变项的使用看得不太明显。而从传统逻辑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使用变项只是一种方法,是比仅使用自然语言更好的方法。在这种意义上说,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要使用变项的。因此,不使用变项决不是自然语言逻辑的标准。
逻辑研究一定要提出推理规则。无论是传统逻辑或是现代逻辑还是自然语言逻辑,都不会例外。“没有提出形式推理规则”的说法强调的是“形式”,似乎是说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提出形式规则,而自然语言逻辑不提出形式规则。这里存在着对逻辑的认识问题。逻辑研究推理并且是研究推理形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逻辑研究的是具有必然性的推理,而这种必然性不是由推理的内容而是由推理的形式决定的。如上所述,自然语言逻辑也是研究推理,只是范围扩大了。它实际上是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研究正统逻辑揭示的逻辑形式在自然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研究自然语言中尚未被揭示和刻画的逻辑形式。因此它研究的也应该是具有必然性的推理,为此,它也必然要提出推理规则来。有人认为《墨经》是用举例的方式列举推理的具体模式,让人们通过特例悟出推理的规则(参见[3],第66页)。这种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逻辑规则难道是凭几个例子“悟”出来的吗?特别是,作为一门科学,逻辑就是让人们去从例子中“悟”出推理的规则吗?显然不是这样。作为一门科学,逻辑必须明确地提出推理规则。必须明确地告诉人们,以什么方式可以得到必然的推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因此是自然语言的逻辑指号学(参见[1],第23页)。这里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语形、语义和语用。
语形、语义和语用分别是英文“syntax”、“semantics”和“pragmatics”的中译名。“syntax”的直接翻译是“句法”(而且这也是我个人倾向于使用的翻译)。“syntax”和“semantics”是最先区别使用的一对概念。这是人们在现代逻辑中从语言学借用的两个概念。现代逻辑的显著特征是使用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使用形式语言就要首先给出一系列初始符号,然后给出形式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用这些符号就可以构造这种形式语言的语句。有了形式语言,才能进一步构造演算系统。形式语言中这些初始符号、形式规则等等就是“syntax”。因此这种“syntax”是一种句法。它告诉我们用那些符号根据什么步骤来建立合适的语句,因而可以说是关于建立合适语句的规则。
在形式语言中,初始符号没有意义,因此用初始符号构造的句子也没有意义。对于这样的没有意义的句子,充其量只能说它们是一些符号串。为了使它们有意义,必须对它们进行解释。比如,P→Q是什么意思?x(Fx→Gx)是什么意思?这种解释就是“semantics”。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不仅所谓的语形是形式化的,而且语义解释也是形式化的。现代的语义解释就是模型论。简单地说,从这种解释出发,一个表达式的真值就是其构成部分的真值的一个函数。由此可以对一个表达式和它的真值之间的关系做出精确的描述。比如,P→Q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又比如,x(Fx→Gx)在什么情况下是可满足的,等等。
语用则是在语形和语义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简单地说,它涉及句子的表达者。但是实际上,它是关于句子中的索引表达式(比如人称代词、指示词、时间表达,等等)的理论。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有关含索引表达式的句子的真假和推论的问题。比如,“我们必将做出牺牲。”这个句子离开了使用它的语境就无法确定它的真假。
从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在语形(句法)、语义和语用中,语形是根本的。语义和语用是第二位的。没有语形,语义和语用就无从谈起。而就语义本身来说,虽然它是对句子提出的解释,但是它的解释主要是围绕句子的真值进行的。就语用来说,虽然它涉及的范围比一般的语义要更为宽泛,但是它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句子的真假进行的。因此,如果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包括语形、语义和语用,那么就应该能够论证中国古代逻辑在句法方面进行了论述,也应该能够论证中国古代逻辑对句子的真值方面进行了论述,还应该能够论证中国古代逻辑对含索引词的句子、特别是对这样的句子的真假进行了论述。可是实际上,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论证。相反,许多关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解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语形就是字词的形式,语义就是字词的意义,语用就是语言的应用。显然这是望文生义。这种理解距现代意义上的语形(句法)、语义和语用实在是相距甚远。比如,有人认为,逻辑的语义必须以语言的语义为基础,脱离了语言的语义就无所谓逻辑的语义(参见[1],第23页)。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史就是古汉语的语义学史(参见[10],第48页)。这样一来,逻辑就不再是研究推理的科学,而成为研究字词意义的了。这样的观点最终就会导致取消逻辑,并且取消逻辑史。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恰恰是没有理解什么是语义,或者严格地说,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逻辑学家所说的语义。无论如何应该明白,逻辑学家所说的语义绝不是字词的意义。
也有人正确地理解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中国古代逻辑缺乏语形的研究,但是有语义和语用的研究(参看[4],第52-53页)。然而,如上所述,在逻辑研究中,语形研究是基础,语义研究是第二位的。语用则是在语形和语义研究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语形的研究,那么语义的研究以及语用的研究又如何进行和发展呢?换句话说,即使说中国古代逻辑缺乏语形的研究而有语义和语用的研究,那么这种语义和语用的研究的基础是什么呢?这样的研究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内涵逻辑。有人说,中国古代逻辑注重语词分析,因此主要是内涵逻辑(参见[1],第23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内涵逻辑?其二,注重语词的内涵分析是不是内涵逻辑?
一阶逻辑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它是外延的,其二它是二值的。因此它的一条基本规则是:一个句子的真值是由其构成部分的真值决定的。一阶逻辑可以处理许多问题,但是有些问题却处理不了。特别是这条规则对于一些形式的句子是不适用的,因为有些句子的真值不是由其构成部分的真值决定的。比如像“相信P”,“知道P”这样的句子。也就是说,这样的句子的真值不仅涉及其中的P的外延,而且涉及P的内涵。自塔斯基建立了逻辑语义学之后,现代逻辑对句子的真值提供了系统的语义说明。这种说明包括对句子的结构,即对个体、谓词等等的说明。但是这种说明仍然是外延的。后来人们对于对句子真值仅有外延的说明感到不满,还要求对句子的内涵做出说明。这种研究发展最终形成了内涵语义学。因此可以说,逻辑的发展首先形成了外延逻辑,在此基础上后来才形成了内涵逻辑。我们还可以从模态逻辑的发展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
一阶逻辑是古典逻辑。非古典逻辑的发展首先是模态逻辑。在命题逻辑中引入模态算子必然“□”或可能“◇”,从而建立了模态逻辑系统。但是在模态逻辑的研究中,一阶逻辑的上述规则失效了。因为□P和◇P不是真值函项,它们的真值不仅仅是由P的真值决定,而且还要取决于使P为真的那种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种性质不是处延的,而是内涵的,因此仅用真值函项方法不能处理,必须进行内涵方面的研究。模态逻辑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建立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理论,为模态命题的语义提供了解释。简单地说,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理论把模态命题的真值与可能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把必然性和可能性解释为一种关系结构。它的基础是古典逻辑的外延方法。
内涵和外延最初是传统逻辑用来分析概念的两个术语。所谓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现代逻辑沿用了内涵和外延这两个概念。内涵逻辑成为现代逻辑的一个分支。内涵逻辑把内涵看作一个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它主要考虑句子,并且为此考虑句子的构成部分。在内涵逻辑看来,个体词的内涵是从可能世界到个体词指称的对象的函项;谓词的内涵是从可能世界到谓词指称的个体类的函项;句子的内涵是从可能世界到句子的真值的函项。因此内涵逻辑的“内涵”与传统逻辑的“内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在传统逻辑中,内涵是对概念的分析,与句子没有关系,从而与真假没有关系,而在内涵逻辑中,内涵是对句子的分析,并且始终是与研究真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内涵逻辑绝不是语词分析。认为内涵逻辑是语词分析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什么是内涵逻辑,而是在传统逻辑的意义上对内涵逻辑的内涵做了错误的理解。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来论述逻辑史是没有什么用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内涵逻辑是在外延逻辑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内涵逻辑,那么首先就应该论证中国古代逻辑中有外延逻辑。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非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是以实际论证为研究对象的(参见[8])。
非形式逻辑是现代逻辑的一个提法。它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研究实际推理或实际论证。所谓实际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和实际论证(practicalargument)是指日常的推理或论证。这样的推理或论证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特征。比如,它们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是形式化的,它们不脱离推理的具体内容,与一般形式逻辑表述的规则也不完全一样,等等。这种推理和论证的研究,即所谓非形式逻辑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这样的推理研究是为了揭示其中有规律的形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进行推理和论证。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逻辑是这样的非形式逻辑,那么显然,它必须具备一种赖以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不论中国古代有没有形式逻辑,至少持非形式逻辑之说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因此,中国古代逻辑不可能是现在通常所说的非形式逻辑。
持非形式逻辑观点的人认为,中国古代逻辑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表现的形态不同于传统逻辑,是一种非形式逻辑(参见[8],第21页)。我认为,这种描述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缺乏深入的考虑。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是这样的非形式逻辑,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的对象是什么?它所依据的方法是什么?它是否形成了形式逻辑?或者说它是否发展成了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探讨了这样的逻辑,建立了四谓词理论。他从主词和谓词可以不可以互换、谓词表示不表示本质这样两条原则出发,区别出四种谓词,提供了一系列推理规则,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理论。这是最初的论辩的逻辑。后来亚里士多德又研究了命题以及命题之间的推理,建立了三段论系统,创建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亚里士多德最初的研究就是没有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因为在他以前还没有形式逻辑。但是他从对推理形式的研究出发,经过发展,最终建立起形式逻辑这门科学。今天我们讲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主要指他的三段论,道理也在这里。中国古代本来也没有逻辑。但是当古人以推理为对象进行研究以后,就有可能产生逻辑。如果我们说中国古代这样的研究是非形式逻辑或论辩的逻辑,那么就应该考虑,它依据的是什么?它是否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或至少提出了几条推理规则?它是否形成了一个逻辑理论?它是否发展成为形式逻辑?这样的考虑才是至关重要的。
与以上几种观点相对的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史是形式逻辑史(参见[10]、[11])。这种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它指出,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科学是指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形式逻辑。因此中国逻辑史只能是关于这样的逻辑的历史(参见〔10〕,第47页)。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在形式逻辑的前面加上“传统”二字,并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于推理形式的论述,但只是用自然语言表述的有关思维形式方面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建立严格的公理系统和形式系统,因此只能限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和范围(同上)。这样的论述的缺陷是明显的。比如有人就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有关推理,而传统逻辑没有关系推理,因此这种观点不对(参见[7],第61页)。这种批评显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产生实际上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在我国,高校逻辑教材讲的一般是传统逻辑。经过十几年来的改革,增加了许多现代逻辑的内容,比如,介绍了应用形式语言的一些方法,比较普遍地增加了真值表,等等。这样的改良的教材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一方面它讲真值表,从而告诉学生句子的真假与句子的内容无关;另一方面它又讲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从而要求学生必须考虑句子的内容,这就造成矛盾并势必带来混乱。但是最主要的是,这样的教材并不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掌握现代逻辑的精髓,即形式化和演算。同时这里还产生一个问题。虽然这种教材增加了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但是没有人说它是现代逻辑;尽管可以标新立异,称这种教材为普通逻辑,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它是传统逻辑。恰恰是依据这样的教材和理解才产生了上述观点,即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形式逻辑。在这种意义上说,上面提到的那种批评似乎就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委屈。因为在我们的教材里也是有关系推理的。
我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于对逻辑这门科学的性质的理解。逻辑是研究推理的。传统逻辑是如此,现代逻辑也是同样。使用不使用形式语言,建立不建立演算系统,只是方法的问题,而不是逻辑研究的对象的问题。形式语言的使用和演算的建立虽然使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得到鲜明的区别,但是并没有改变它们都研究推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没有改变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都是关于推理科学的性质。因此,如果说中国有逻辑史,那么就应该是关于推理的学说的历史,是形式逻辑史。无论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一些内容是传统逻辑没有的,还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可以包容在传统逻辑之中,中国逻辑史都是形式逻辑史,而不是传统逻辑史。而且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对于前面提到的几种观点也应该是适用的。
二、方法问题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我主张借用过去的两个口号,应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尤其是要“推陈出新”。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明确以后,应该说,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可以的。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以前没有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照样可以研究逻辑,并创立逻辑这门科学。有了传统逻辑以后,人们当然可以以传统逻辑为工具来进行研究,并且取得成果。《中国逻辑史》(五卷本)就是最好的说明。如今现代逻辑是比较成熟的科学,人们自然可以以它为工具。现代还有许多理论可以成为人们研究逻辑史的工具,比如语义等、符号学、自然语言逻辑,等等。此外还有数学方法、语言学方法、哲学方法等等,都可以为我们使用。在研究方法上,从理论上说,绝不能说哪一种方法能用,哪一种方法不能用;只能用哪一种方法,不能用哪一种方法。
但是这里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一,无论用哪一种方法研究逻辑史,我们都必须把这种方法学好。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不同的观点实际上都是依据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是对于这些理论和方法是不是做到真正掌握。如果应用自然语言逻辑的方法,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自然语言逻辑,并且把这种方法学好。如果应用内涵逻辑的方法,那么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内涵逻辑,并且掌握这种方法。绝不能仅仅使用一些新学科的一些新的名词术语,而对这些学科本身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懂。否则只会是断送了中国逻辑史的研究。
第二,虽然研究方法很多,但是哪一种方法更重要呢?我说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并不意谓我主张用所有方法或随便什么方法。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和逻辑有关,因此最主要的还是逻辑方法。而说到逻辑方法,现代逻辑方法无疑是最重要的。现代逻辑突破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解决了传统逻辑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为逻辑的研究和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一般来说,传统逻辑能够解决的问题,现代逻辑都能够解决;而许多现代逻辑能够解决的问题,传统逻辑却不能解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应该抛弃传统逻辑,提供现代逻辑。这也就是研究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掌握现代逻辑的人不会、也不应该剥夺不懂现代逻辑只懂传统逻辑的人研究逻辑史的可能性,因为懂现代逻辑并不是研究逻辑史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懂现代逻辑的人应该明白,传统逻辑是有明显局限性和弱点的,应该努力学习现代逻辑,否则在研究上终究是要落后的。好比人家有了汽车,我们仍旧坐着牛车慢慢地赶路一样。
自然语言逻辑、内涵逻辑等等都属于现代逻辑,只是不属于现代逻辑的经典部分。应用这些方法,较之一阶逻辑也可以说是推陈出新。实际上,对于现代逻辑,也有多学一些,掌握得更多一些的问题。逻辑工具掌握得越好,处理问题的本领就越强,研究才会更加深入。然而目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同志似乎越来越多,但是许多同志甚至并没有掌握现代逻辑的经典部分,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很难相信,这种状况会使中国逻辑史研究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学习和掌握现代逻辑乃是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明白,学习现代逻辑,不仅会使我们掌握现代逻辑方法,而且会开阔我们的逻辑眼界,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和把握逻辑这门科学的对象,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会它的性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才会更上一层楼。
标签:自然语言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形式逻辑论文; 逻辑学论文; 科学论文; 句子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