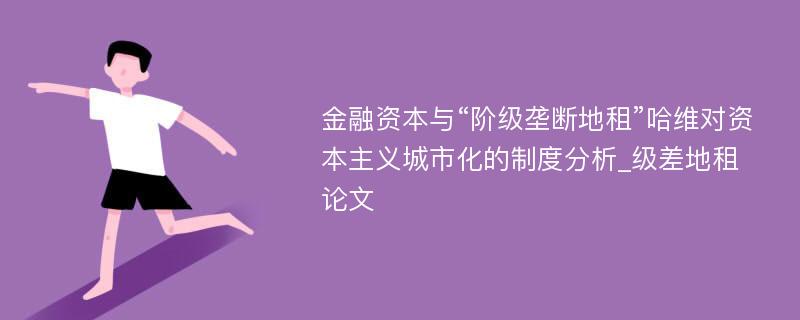
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金融资本论文,地租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后,厘定了自己的地租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①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地租的理论。虽然马克思也曾涉及城市地租,但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真正独立的城市地租理论。其次,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以当时英国农业部门特有的阶级关系为前提,即存在着由土地所有者、产业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组成的“三位一体”社会结构。第三,土地所有权被视为前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遗留与同化,与此相应,地租也往往被视为资本积累的消极障碍。第四,地租的形成要以产业资本循环为前提,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构成了地租的直接来源。第五,在《资本论》体系中,地租理论是生产价格理论在农业中的应用,与生产价格理论相比,地租理论仅仅是一个附属的理论,在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降,国外围绕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讨论逐渐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时出现了复兴的态势;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普遍出现的土地及住宅价格急剧上升的局面,客观上也需要从地租理论出发,求得一个解释。在此背景下,城市地租问题就成为大家普遍关注和争执的焦点。②自70年代初开始,地理学家出身的英国学者大卫·哈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开始构建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并用以解释当代资本运动规律的新特征。在哈维的理论中,“阶级—垄断地租”的概念占据着核心位置。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地租理论,依其要旨而言,就是关于“阶级—垄断地租”的理论。自70年代以来,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哈维几乎不间断地发展和完善着这一理论,在不同时期都留下了一些重要文本。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时间跨度较长,相关思想散布在各个时期的著作和论文之中,不少重要文献尚未出版中译本,客观上给研究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哈维的观点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哈维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本,还原其理论发轫和演变的过程,并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对哈维的贡献给予适当的评价。 一、“阶级—垄断地租”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恢复了对地租理论的兴趣。但是,与级差地租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理论在当时显得更受重视。据海依拉(A.Haila)的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级差地租理论在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已经得到相当完善的发展,几乎无须任何修正。另一方面,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当时面临的问题而言,级差地租似乎与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从其定义来看,级差地租是以市场生产价格的形成机制为前提而产生的。这意味着,级差地租本身并不会影响到产品的价格。海依拉指出,在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急于“为迅速上升的土地及住宅价格找到一个解释。级差地租并非产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因而被忽略了。在分析住宅的时候,典型的做法是将地租看做垄断地租。”③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于垄断地租或绝对地租问题的重视,意味着将财产权、阶级关系和权力等因素引入地租的形成过程。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致力于发展地租的制度理论,即力图通过相关制度分析,揭示出垄断地租或绝对地租由以产生的制度基础。在这一理论路线上,大卫·哈维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其70年代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哈维一方面着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批判了新古典地租理论。新古典理论片面地专注于相对空间和级差地租,认为地租是因土地转向更有效率的用途而产生的,即土地的利用决定了土地的价值。而哈维则主张,在存在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场合,是土地价值决定了土地的利用。根据他的观点,土地价值的变化,是在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参与下,由特定的权力关系决定的。而新古典理论则因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忽视制度因素在地租形成过程里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垄断地租或绝对地租范畴。④ 哈维构建其城市地租理论的出发点,是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⑤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否拥有土地,现在变成了在一般资产组合中选择何种资产的问题。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变化也相应地改变了土地所有权或地租与资本积累的关系。用哈维的话来说,就是“将土地解放出来,使之隶属于生息资本的流通,并将土地市场、土地利用以及空间的竞争纳入资本的一般流通过程。”⑥在哈维的理论中,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因完全纳入资本循环,而被“内生化”了。在此意义上,哈维还主张,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对于土地利用和资本积累的空间配置,可能起到马克思当年未曾设想过的正面作用。⑦ 要理解哈维的“阶级—垄断地租”概念,首先需要澄清“阶级”一词在哈维那里被赋予的含义。正如前文提到的,马克思在考察农业地租时,是以英国当时的特定阶级结构为前提的。当地租理论的研究对象转移到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地租时,其面对的是一个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形成的不同阶级结构。而且,地租的直接源泉也不再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包括利润和工资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收入。对雇佣工人而言,一方面,他们要在直接生产领域中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即在购买或租用住房时,还要遭受土地或房屋所有者的剥削。但问题是,在城市地租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中,受到影响的并不限于雇佣工人,其中有些群体甚至阶级根本就不会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基于这些考虑,在城市地租的场合,哈维没有援用传统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过程和分工出发来厘定的阶级概念,而是将阶级定义为在支付地租时,某一群体的个人发现彼此之间享有共同的利益,并与其他群体的利益相冲突的那些集团。 在哈维看来,这个定义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但与之并不矛盾。即便在马克思的分析里,伴随剩余价值的流通,也会在生产过程之外,因各种收入的支付而形成不同的阶级(如食利者阶级)。哈维还认为,他所界定的阶级,可以视为传统阶级概念之下的“次生阶级”(sub-class)。这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社会阶级如资本家阶级的内部,会发生某一集团向另一集团支付租金的情形,如“公司董事要屈从于开发商的阶级垄断权力并交纳绝对地租”,并因此而进入互相对立的关系。⑧ 哈维这里使用的阶级概念,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的影响。哈维试图把吉登斯的一些概念和马克思的积累理论联系在一起。依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积累为了克服其内在矛盾,必须不断地扩大和创造出内部市场,为此就要不断地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培育各种新的欲望和需要。这一趋势必然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带来消费方式的革命,都市化就是这一革命的具体体现。在这一消费革命中,用吉登斯的话来说,会形成各种“与众不同的消费阶级”(distinctive consumption classes),其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哈维接受了这个概念,强调这些“与众不同的消费阶级”的产生,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和都市化之中的。⑨ 在上述阶级概念的基础上,哈维进一步探讨了“阶级垄断”或“阶级垄断权力”的概念。“我们所谓的阶级垄断是指在结构性稀缺的形势下,一个生产者阶级(或消费者阶级)对一个消费者阶级(或生产者阶级)所拥有的权力。”(10)在哈维看来,阶级垄断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也出现过。马克思曾这样说,如果商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对占优势的一方而言,“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11)在哈维那里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某一个土地或房产的所有者,以高价出租或出售城市土地或住宅时,其他土地或房产所有者也能获益,这便在土地或房产所有者之间形成了共同的阶级垄断。 在哈维1973年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就运用了阶级垄断的概念。所谓阶级垄断是以“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的概念为前提的,而绝对空间是空间的物理属性和制度特性的统一。在欧几里得的物理三维空间中,土地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改良具有空间的唯一性,不可能有两个人或物同时占据完全相同的区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的这种绝对属性由于私人产权的存在而制度化,土地所有者拥有了支配相应空间的垄断权力,并可利用这种权力谋求其经济上的实现形式。(12) 在绝对空间的基础上,哈维进一步讨论阶级垄断的概念。他设想一个由观众在剧院选座的思想实验。此处的剧院是对拥有固定存量的住宅市场的隐喻。观众分为穷人和富人,他们一起为剧院里的座位展开竞争性投标。结果,穷人只能在富人之后,最晚进入住宅市场,并且只能选择那些挑剩下的、品质最差的住宅。哈维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住宅供应者将拥有某种类似垄断的地位,迫使那些最晚进入竞标过程的穷人让渡其消费者剩余,使之转化为房产经纪人、房东等人的超额利润或租金。“换言之,对于向低收入租户提供住宅而言,我们所涉及的是一种阶级垄断。”“一方是住宅的消费阶级,他们没有信用评级(即无法得到贷款——笔者注),除了随遇而安没有别的选择。另一方则出现了房东阶级,他们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可是,由于消费者没有别的选择,房东作为一个阶级就有了垄断的权力。个别房东之间会互相竞争,但作为阶级,他们展示出某种共同的行为模式。例如,倘若资本收益率下降到某个水平之下,他们将使住宅退出市场。”“富人由于拥有丰富的经济选择,与那些选择格外有限的穷人相比,更有能力规避这种垄断的后果。为此我们得到了基本的结论:富人可以支配空间,相反,穷人则落入了空间的陷阱。”(13) 在发表于1974年的两篇论文中,哈维反复使用这个包含低收入租户的次级市场(submarkets)模型,但在细节上做了修改,并将其作为理想类型。在这个模型中,只存在两个阶级,即房东阶级和低收入租户阶级。前者可假定为专业化的房东—经理阶级。至于低收入租户,则是那些无法凭借其收入、社会地位、信用等级而购置住房的人,他们也无法申请到公共住房,因而别无选择,只能在低收入者的租赁市场上寻找居所。他们被困在这个次级市场上,只能仰仗房东阶级来满足其基本需求。假定房东的资本主要体现为住宅,并可以参照其他次级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回报率调整投资的去向。如果在低收入租户的市场上,取得的预期回报率低于其他市场,房东就会放弃对房屋的维护,削减投资。由此便会造成住宅品质的下降,其中一些质量最差的住宅甚至会退出市场。住宅供给将会形成有利于房东的稀缺,其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即“阶级—垄断地租”就会上涨,直至与其他市场的投资回报率相等乃至更高的水平。低收入租赁者和房东之间的阶级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双方各自拥有的相对政治权力的大小,对“阶级—垄断地租”的高低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低收入租赁者有力量推动政府实施最低居住标准,或对租金实施立法控制,房东的“阶级—垄断”权力就会受到约束,最终在一个较低的投资回报率水平上与租户达成妥协。反之,如果低收入租赁者的政治力量较弱,租金便会提高。低收入租赁者面对租金上涨、可支配收入有限的窘况,只能进一步拆分居住的空间。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居住得更为拥挤,甚至使自己的住宅沦为贫民窟。 “阶级—垄断地租”并非仅存在于低收入租户的市场,而是可以在所有房地产市场上得到实现。哈维还曾特地谈到高收入者的案例。高收入群体在住宅市场上可有较为广泛的选择。但是,如果他们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极度敏感,希望能和门当户对的人比邻而居,那么这一需求就可能为投机者—开发商提供一个实现“阶级—垄断地租”的机会。哈维写道:“如果投机者—开发商凭借特定社区某种住宅的优点能说服高收入群体,并且完全主导了政治过程,那么优势就在投机开发商一边。如果消费者不为投机者—开发商的甜言蜜语所动,且牢牢地控制着影响土地规划调节和基础设施供应的政治过程,那么投机者—开发商的阶级垄断权力就将受到遏制。”(14) 地租是收入的一种转移支付。“阶级—垄断地租”遍及房地产市场,其最终的攫取者是谁呢?从现象来看,低收入租户会把租金支付给某个房东。但后者可能居住在高收入者生活的郊区。而在郊区的住宅次级市场上,投机者—开发商则是“阶级—垄断地租”的攫取者。低收入租户缴纳的租金,会通过房东,转移到投机者—开发商手中。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流向,投机者—开发商还会把租金交付给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偿还为完成开发而得到的贷款。这样,正如哈维强调的,就形成了“阶级—垄断地租”向上流转的等级结构,金融资本位居这个结构的顶端。(15) 一个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是,所谓“阶级—垄断地租”,究竟属于绝对地租还是垄断地租呢?在马克思那里,这两种地租的形成都来自农产品按垄断价格的出售。在绝对地租的场合,无论何种土地的产品,均可按照高于生产价格但等于价值的价格水平出售土地产品。作为绝对地租形成原因的土地所有权垄断,是一种集体垄断权力,阻碍了资本向农业部门的自由流动。与此不同,垄断地租则是由于个别区位的土地具有非常特殊的生产条件而产生的。“这种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16)这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只是经济生活中极个别或偶然的情形,垄断地租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畴。它所涉及的垄断权力,只属于那些具备特殊优越的生产条件的个别土地所有者。 因此,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形成虽然都涉及某种垄断,但在上述两种场合,垄断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就前者而言,垄断权力明显地带有普遍性,所有土地产品都服从劣等土地产品的价值这样一个统一的垄断价格。就后者而言,只是一种个别垄断价格。哈维在70年代最初提出“阶级—垄断地租”时,考虑到了这种区别,并将“阶级—垄断地租”在概念上界定为绝对地租。例如,他写道:“或许可以这样来明确垄断地租和绝对地租之间的区别,即把前者看作是在个别层次上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所有者正好拥有某种另一个人特别想要或需求的),而后者则是从某个部门的一般生产条件产生的地租(这是一种阶级垄断的现象,它影响着所有农业土地的所有者,所有低收入住宅的所有者,等等)。”(17)1974年,哈维及其合作者甚至直接在论文题目中使用了绝对地租的概念,以此展开对“阶级—垄断地租”的讨论。(18) 然而,这一观点在刚形成时,哈维就流露出踌躇不决的态度。在1974年发表的另一篇由哈维单独署名的文章中,他写道:“这种地租形式究竟应属于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还是垄断地租范畴是不明了的”,“我个人的意见是,‘阶级—垄断地租’最好还是被当作绝对地租的一种形式。但由于这是一个有争议、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在后文里还是援用‘阶级—垄断地租’这一中立的术语”。(19)但是,在约10年后的1985年,哈维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资本的都市化》,其中收录的该篇文章,刻意删除了这段犹豫不决的文字。(20)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此前的1982年,哈维出版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著作《资本的限度》。他在第十一章中提出,马克思把绝对地租视为自己对地租理论的主要贡献,这一看法是不恰当的。“绝对地租不是重要的范畴”,因为在农业中能实现多少绝对地租,取决于很多不确定的条件,其数额是极为有限的。毋宁说,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级差地租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1)在新近出版的《资本之谜》一书中,哈维再度重申,绝对地租的概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理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在讨论地租问题时可“不予考虑”。(22)这意味着,从1982年至今,他持续地否定了主张“阶级—垄断地租”属于绝对地租的观点。 哈维的这种犹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源于马克思在界定绝对地租时,所采用的方法及其在个别观点上的含糊之处。马克思从形成原因和形成条件两方面,界定绝对地租。就形成原因而论,绝对地租的产生源于土地私有权的资本主义垄断。哈维最初认为“阶级—垄断地租”是一种绝对地租,就缘于此。但是,马克思还从形成条件上界定了绝对地租,把它归因于“农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但这种情况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才存在,并非普适性的条件。马克思本人也明确地承认,一旦农业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水平,绝对地租就会消失。(23)届时,“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或者在租金的名义下,把他的租佃者的一部分利润甚至一部分工资刮走。一个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24)这里论及的因掠夺一部分利润甚至一部分工资而形成的地租,与哈维讨论的“阶级—垄断地租”有极大的相似性。其一,地租此时来自两种派生的收入(即利润和工资),而非直接来自剩余价值。其二,地租形成的原因在于土地所有者的“阶级—垄断”权力。不过,马克思并未明确这一点,他把获得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的土地产品价格,都笼统地称为“垄断价格”,(25)这引致了哈维的上述犹疑态度。《资本的限度》还提出,在马克思那里,绝对地租的产生又取决于农产品能否实现一个足够高的垄断价格。由于供求关系的不稳定,它的实现极不确定。马克思承认,在一般情况下,不管农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有多大,农产品中所能取得的绝对地租在数额上都是少量的。(26) 哈维的“阶级—垄断地租”与马克思笔下的垄断地租,在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哈维将马克思意义上的垄断地租称为“个别垄断地租”(individual monopoly rent),并与“阶级—垄断地租”概念对举。(27)在哈维看来,后者在某种制度环境下,伴随着“阶级—垄断”权力的形成,把前者的个别性和偶然性扩大为可复制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崭新独立范畴。 二、都市化、制度环境与“阶级—垄断地租”的形成 研究地理学出身的哈维,始终不满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后者的明显弊端,是未能将空间维度纳入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最近发表的题为《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一文中,哈维以尖锐的笔触写道:一直以来,“在将有关都市化过程和营建环境形成的认识,纳入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方面,都没有出现严肃的努力。其结果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因危机而如此欣喜若狂,却倾向于把最近这次崩溃看作只是他们所钟爱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版本的反映(不管这是利润率下降、消费不足,抑或其他什么版本)”。(28) 在哈维看来,当代资本积累从根本上是由都市化推动的。任何经济理论如果不具备这一视角,对经济危机和资本积累动态的解释就必将流于片面。为了理解哈维的上述观点,先让我们检视一番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 哈维提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大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急剧增长,剩余价值的吸收成为资本积累面临的核心问题。1929-1933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其后虽有短命的复苏,1937年的美国经济跌入了又一次经济危机。两次危机联翩而至,使传统经济周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面临长期萧条的局面。在第二次危机还没结束的1939年,欧战爆发,大量过剩资本和失业劳动力,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和军备经济吸收,终于帮助美国摆脱了长期萧条的困扰。可是,在二战结束后,过剩资本又是如何被吸纳的?哈维指出,战后美国的大规模都市化,成了化解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出路。(29) 除了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这一经济上的原因外,对都市化还有来自政治的考量和推动。哈维提到,在30年代大萧条时就有人提出,背负债务的自有住房所有者不会参加罢工。战后成千上万的军人从战场复员回到家乡,如果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和萧条,势必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动乱。有什么办法可以起到一石两鸟的作用,既重振经济,又缓和美国的社会矛盾?答案就是通过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和郊区化。1947年,美国通过《住宅法》,宣布所有美国人都有在体面的住宅里居住的权利。在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鼓励下,拥有私人住宅的所有权,成了“美国梦”的灵魂,一种盛行的文化价值。战后拥有家庭住宅所有权的人数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从20世纪40年代的40%,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的逾60%,在2004年甚至一度接近于70%,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峰值(2010年该比率又下降为66%)。(30) 哈维以大都市纽约的重建为例,指出战后美国的都市化摒弃了对城市化的传统看法,进而从整个大都市(metropolis)的角度,规划这一进程。“通过借贷的方式修建高速公路、完善基础设施,通过郊区化,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型建筑技术,重建整个大都市区,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城市,摩西(纽约都市化改造的设计师——笔者注)找到了利用过剩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赚取利润的方法。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向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扩张,这股郊区化的浪潮也蔓延到了美国其他地区。这不仅对战后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非常有利,而且对以美国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1) 都市化的作用并不限于兴建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城市消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不断创造出各种新的产品和新的需要,是克服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郊区化的发展使人们变得日益依赖汽车和高速公路;位于郊区的标准化住宅成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标准,还进一步刺激起对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乃至割草机的需求。所有这些变化都伴随着石油、钢铁、电子等新兴部门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第四次技术革命为基础的巨大浪潮。 要实现这一切转变,需要有各种制度层面的支持,不仅包括金融制度和行政结构的调整,而且还要保障劳动阶层有能力为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承担必要的成本。哈维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或调节学派一样,都提到了战后出现的“资本—劳动协议”所起的作用。即在核心经济部门就业的工人,有机会分享生产率进步带来的收益,从而保证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协同增长。自3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机构针对住房的消费信贷也得到了发展,加之政府为家庭买房提供的税收减免,以及为鼓励退伍士兵购置住房和接受高等教育而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为美国战后都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都市化必然会促进城市地租的发展。在其早期著作中,哈维比较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意义。他认为,在19世纪,以芝加哥为代表的新兴工商业城市所拥有的交通系统,以及城市本身的生产性,意味着级差地租可能是这一阶段地租的主要形态,土地的利用决定着地租的规模。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地租则在大都市中心(以及19世纪的伦敦那样的商业和行政中心)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地租此时将进入企业的成本,并决定土地的利用。(32)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垄断地租”的崛起是携手并进的。(33) 哈维对于都市化和资本积累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同以巴兰、斯威齐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的分析,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研究“阶级—垄断地租”的具体形成条件时,哈维所采纳的制度分析进路,又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或调节学派颇有可比之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哈维因其1974年的论文,开启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先河。 哈维反复强调,“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取决于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制度结构。在这个等级制结构的顶端,是国家和金融资本。(34)依照哈维的概括,国家和金融资本推行的制度和政策,旨在通过都市化实现三项基本目标。(35)第一,确保在建筑业、经济增长和新的家庭形成之间的稳定关系。第二,通过将建筑业和住宅部门作为凯恩斯主义的调节工具,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并大致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第三,通过住宅供应,调节社会福利的分配,以确保国内的和平和稳定。如果改换成更为政治经济学的语言,都市化的上述目标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在个别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层面,确保长期稳定的资本积累。第二,确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在推进都市化和郊区化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由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组成三级政府结构,每个层级都有其相应的独立官僚体系。在联邦层面,联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负责各种政府项目,并独立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官僚体系而运作。哈维指出,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作用,既包括直接干预,也包括间接干预,后者在美国是更为常见的形式。直接干预是指政府通过公共行为从事住宅生产。间接干预则是指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担保利润或消弭风险的方式,帮助金融机构、开发商和建筑商。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种制度手段对房地产市场的运作进行限制或约束。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都市的区域划分和土地利用进行有计划的控制。最后,政府还可凭借公共服务、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住宅的外部环境,影响住宅的价值。 哈维指出,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最主要的协调机制,是具有等级制特点并受国家监管的各种金融机构。它们包括各州的地方储蓄和贷款协会(State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Federal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以及抵押银行(mortgage bankers)、储蓄银行(savings banks)和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s)等。抵押银行、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利润为导向,其运作不限于房地产市场。储蓄和贷款协会具有非营利性,依规定只能在房地产市场上开展业务,其宗旨是在当地人民中间提倡节俭,并为他们购买家庭住宅提供融资。其中,地方的储蓄和贷款协会以社区为基础,规模较小,并由储户控制。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则受到专业化的管理。联邦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起,还先后设立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国有机构(80年代后私有化,但仍得到联邦政府支持)。它们通过从金融机构手中购买抵押贷款,为相关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进而达到熨平建筑业经济周期波动的目的。 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分层结构及其相关政策,对消费者在房地产市场的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并在此过程中塑造出各种次级市场,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对消费者而言,在适当条件下取得按揭的能力,不仅取决于个人的收入以及在购置住宅时的选择,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及政府的相关政策。例如,由于不同价位的住宅所需要的服务成本大体相同,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以利润为导向的金融机构)往往偏好为那些昂贵的住宅提供融资。不同金融机构对于购房首付、信贷可靠性等有各自不同的政策。政府机构(尤其是FHA)也会在这些方面进行干预,并对中低收入家庭产生很大影响。此外,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有明显的“邻里偏向”,即在融资上对不同社区的偏好或厌恶倾向。 哈维在1974年的两篇论文中,以巴尔的摩住宅市场为例,讨论上述问题,分析“阶级—垄断地租”产生的制度条件和机制。多年后,他就巴尔的摩的典型意义评论道:“在北美各城市中,权力结构如巴尔的摩这般简单者很少见”;“在许多方面,它是美国资本主义下城市塑造过程的代表,是当代都市主义的实验室样品”。(36)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巴尔的摩地区总共约有两百万居民,其中90万人居住在巴尔的摩市,60万人居住在环绕巴尔的摩市的郊区即巴尔的摩县。当时,全美都处于郊区化的巨大变革中,巴尔的摩也不例外。郊区化的发展使巴尔的摩市迅速衰落,人口和投资源源不断地从巴尔的摩市流向巴尔的摩县。在金融和政府机构的作用下,巴尔的摩的地理结构得以重塑,当地的住宅市场被分割为13个次级市场。哈维将它们归为八个类别,着重讨论了其中六类次级市场的情形。(37) 1.巴尔的摩内城。在内城的旧宅市场上,现金与私人贷款交易居于主导地位,鲜有制度或政府的参与。在这里存在着上文谈到的房东与低收入租赁者之间的矛盾。由于住房供应量在该市场上总有剩余,房东大量地削减对住宅的投资,设法取得了大约13%的收益率。低收入租赁者多为黑人,缺乏良好的组织,政治控制权十分薄弱,从而被困在这个次级市场。专业化的房东力图使其资本收益率反映机会成本,实现“阶级—垄断地租”。 2.巴尔的摩白人居住区。在这一市场中,自有住房者占多数,为住房交易提供融资的,主要是立足本区域的小规模储蓄与贷款协会。它们没有强烈的赢利目的,旨在为社区提供服务。由于几乎不存在“阶级—垄断地租”,即使居民收入较低,仍能以相当低的价格买到不错的住房。 3.西巴尔的摩黑人居住区。该区基本上是60年代营造的,居民多为黑人,收入多处于中低水平。他们未成立储蓄和贷款协会,也得不到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在60年代早期还受到FHA的歧视。当地居民若要成为住房所有者,唯一的办法就是诉诸“土地分期付款合约”(land-installment contract)。如先由投机商以7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栋住宅;然后加上买卖的佣金、各种融资费用、间接成本、翻新装修的费用等,再加上20%的税前销售利润率,大约以13000美元的价格出售。为了给这笔住宅交易融资,投机商凭借自身的信用,替住宅购买者从银行取得一笔估值为9000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然后又向银行另借入4000美元,最终为购房者安排了一笔价值13000美元的组合贷款。为了确保交易对银行而言是无风险的,投机商仍留有房产的所有权。买者占有这项房产的条件是,每个月的偿付不仅涵盖银行贷款的利息和管理费用,还包括一部分钱用于赎回房产的所有权,直至他偿还了开发商借来的4000美元,原先的组合贷款才转变为一个估值为9000美元的常规抵押贷款,从而取得房产的所有权。 上述整套手续都是合法的,并且是60年代早期中低收入黑人能够成为住宅所有者的唯一途径。与白人居住区同等收入的居民相比,购买类似的住宅,白人只需花费7000美元,而黑人要花费13000美元。两者的差额,被哈维称为“肤色税”(black tax),也就是投机商所攫取的“阶级—垄断地租”。投机商不仅利用各种既有的金融和政府的政策,还利用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除了金融机构和政府等正式制度,种族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也在“阶级—垄断地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迟至60年代末,黑人社区才醒悟过来,意识到投机商只有在政府和金融机构无所作为时,才能牟取暴利。于是,爆发了反抗“土地分期付款合约”的政治冲突。随着土地分期付款合约制度的没落,“阶级—垄断地租”的实现需要另觅新的途径。 4.巴尔的摩的高周转居住区。这里的居民原先以白人为主,但自20世纪60年代,黑人开始迁入,白人则逐渐迁至郊区,造成了这一次级市场较高的住房周转率。在该市场中提供融资的,主要是抵押贷款银行,并结合以FHA提供的担保。这些金融服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对60年代“土地分期付款合约”的替代,目的是帮助黑人和城市贫民转变为背负债务、具有社会稳定作用的住房所有者阶级。这些金融服务项目和行政指导结合在一起,终结了歧视黑人的做法,造就了一个主要由黑人组成的、低收入的次级市场。FHA提供的担保项目“221(d)(2)”是主要的融资工具,它允许向没有能力提供首付的中低收入居民提供担保。它使投机商不容易再榨取到“肤色税”,但又为其实现“阶级—垄断地租”创造了新的机会。伴随低收入黑人迁入这一区域,白人也开始迁离。投机商此时可按低于估值的价格,趁机购买白人居民的住房,即向迁离者收取“迁出税”。而且,如果FHA设定的住房质量标准偏低,或者FHA能为腐败所左右,投机商就可对住宅先做廉价装修,然后以较高的价格转卖给黑人或低收入者,即向其征收“迁入税”。在以上两个场合,投机商都取得了“阶级—垄断地租”。 5.巴尔的摩东北部和西南部的中等收入居住区。这些地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以中等收入居民为主。直到60年代,为该地区居民提供购房融资的,一直是联邦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一些规模较小、面向当地居民的储蓄和贷款机构。然而,这个次级市场的内侧边缘经常受到低收入者的入侵,市场上的融资风险也在增加。金融机构逐渐倾向于撤出该市场,并造就了一个住房融资的真空,投机商于是在FHA项目和抵押贷款银行的支持下,趁机而入。面对其他地区居民的入侵,属于中等收入集团的居民,一方面会开展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会到郊区寻觅新的住宅。 6.高收入者居住区。属于该市场的居民会在更大程度上,通过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融资,很少诉诸FHA的担保项目。这一群体通常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抵御投机商的侵扰。除非他们自身的偏好发生变化,或是金融结构的服务质量下降,否则,他们是不会迁离的。在这个次级市场上也可能形成“阶级—垄断地租”,如果高收入者偏好以住宅来维持其声望和社会地位,就有可能被投机者—开发商利用,实现其“阶级—垄断地租”。 哈维指出,从长期来看,次级市场的这种地理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市场力量的兴起和衰落,投机商、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的运作,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政策变化,人们偏好的改变,都会引发形形色色的冲突和斗争,推动城市地理结构持续转型。但在短期内,这种次级市场的地理结构是相对固定的;正是这种刚性使“阶级—垄断地租”在次级市场上得以实现。 哈维对城市住宅次级市场和“阶级—垄断地租”形成条件的制度分析,不仅涉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还包括“种族、民族、社会地位、声望、对生活方式的渴求、社区以及邻里团结”等,它们相互结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些特征都增强‘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潜在可能性。这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维持那种孤岛般的结构,造就了心态褊狭的共同体的绝对空间。”(38)在哈维看来,城市地理结构的变迁是都市化过程的产物,都市化既是吸收过剩资本、拉动资本积累的引擎,又是缓解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工具。围绕这两方面职能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相关制度形式,也有可能发生冲突。那些支撑都市化和郊区化的制度架构,虽然有利于资本积累,却可能最终妨碍其社会稳定功能的实现。 三、“阶级—垄断地租”和资本的次级循环 对都市化和房地产部门的依赖,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根本特征。在哈维看来,这种依赖不仅表现在将这些部门作为资本积累正常开展的开发场所,而且表现在将都市化作为转嫁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新空间,使之成为与资本的初级循环截然不同的次级循环。在哈维那里,资本积累从“初级循环”(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转入“次级循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的结构性条件,便是“阶级—垄断地租”在次级循环中的普遍形成。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最先提出,资本由初级循环转入次级循环,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转变,“全球剩余价值在工业中形成和实现的比例下降,在投机、建筑和房地产开发中形成和实现的比例,同时却在上升。”换言之,作为资本积累的基础,资本的次级循环(即资本在其各种虚拟形式中的循环),已经取代了资本的初级循环(相当于产业资本循环)。(39) 哈维在1974年和197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试图进一步发展列斐伏尔的思想。他在肯定列斐伏尔对初级循环和次级循环划分的基础上,对二者做了更明确的界定。资本的初级循环是指产业资本在生产性部门经历的循环;资本的次级循环则是资本在所谓营建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生产中经历的循环。(40)哈维把营建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生产的营建环境,指的是用来支撑生产过程,并嵌入土地的各种物质结构。另一类营建环境则服务于消费或劳动力的再生产,被称为消费的营建环境或消费基金(consumption fund)。消费基金的构成项目并不直接作为投入进入消费,但构成了消费的支持条件。从定义来看,在两类营建环境之间显然存在相当大范围的交集。一些可用作生产的营建环境的项目,也可用于消费基金;反之亦然。事实上,在哈维的论述中,营建环境囊括了一切嵌入土地,并用于支持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物质结构。此外,哈维还把资本对科学技术的投资,以及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投资,称作资本的第三级循环。 哈维在讨论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的关系时,提出了许多重大观点,并在很大程度上,预见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步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所发生的变化。笔者经过梳理,将哈维的这些散布于不同文献里的观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哈维假设,资本积累从初级循环转入次级循环,一方面要以初级循环出现过度积累为前提,另一方面要以次级循环普遍产生“阶级—垄断地租”为前提。 资本积累在初级循环中始终受到马克思所揭示的各种矛盾运动规律的主宰,或迟或早会屈从于利润率趋于下降、人口相对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威胁,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哈维认为,这种过度积累为资本转入次级循环提供了必要条件,大量过剩资本亟待在初级循环之外寻求增殖的可能性。然而,要使这些过剩资本转入次级循环,还需满足另一项条件,即在次级循环中普遍地生成“阶级—垄断地租”。过度积累作为“推力”,“阶级—垄断地租”的普遍形成作为“拉力”,共同解释了资本积累由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的转移。 哈维在研究巴尔的摩房地产市场时曾提出,“阶级—垄断地租”虽然初始于个别次级市场,但可通过一种“乘数效应”,扩散到其他次级市场,造成“阶级—垄断地租”在次级循环内的普遍化。这对于理解资本从初级循环转入次级循环非常关键。“巴尔的摩的材料提出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某一个次级市场上取得的‘阶级—垄断地租’和另一个市场上实现的‘阶级—垄断地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在这里检测到某种强烈的乘数效应。假定在内城存在着投机性繁荣,为此就会有新的次级市场从原先的社区产生,这些社区的老居民就会被迫去郊区寻找居住的机会。内城投机商取得的‘阶级—垄断地租’越多,在城郊边缘实现这一地租的机会也越多。这种乘数效应可能会被同一金融机构攫取,或被同一个企业家所攫取。若不存在造成这种乘数效应的有意共谋,[资本]对赢亏以及预期或可识别风险的算计,就会像‘看不见的手’一样起到调节作用,并达致相同的结果。”“如果‘阶级—垄断地租’实现的乘数效应是普遍的,我们就可部分地解释,为何投资有可能从资本的初级循环不断地转移到次级循环,就像列斐伏尔假设的那样。”(41) 第二,哈维指出,资本积累向次级循环的转移,须以金融机构和国家的支持为中介,并且与金融资本的历史性崛起联系在一起。 哈维认为,围绕营建环境的投资多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投资历时长,数额巨大,产品通常难以按常规方式来定价。其二,营建环境建成后,往往由集体来使用。其三,对营建环境的投资更容易产生沉没成本。单个资本很难担负起营建环境的生产,带来哈维所指出的矛盾现象。“单个资本家倾向于在初级循环中过度积累,而在次级循环中投资不足。”(42)单个资本要转入次级循环,就必须获得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支持。“使资本流入次级循环的一般条件是,存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以及一个愿意为营建环境的创造进行资助或保证其大规模长期规划的政府。”“要将资源从初级循环转入次级循环,无法离开货币供给和信用,后者在实际的生产和消费之前创造出‘虚拟资本’。这一点既适用于消费基金(从而派生出消费信贷、住房按揭、市政债务的重要性),也适用于固定资本。由于货币和信用的生产是一个相对自主的过程,我们必须把控制这个过程的金融机构和政府,视作在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的关系中,开展治理和起中介作用的集体神经中枢。金融机构和政府及其政策的性质和形式,可以在阻碍或促进资本从初级循环流入次级循环,或流入次级循环的某些特殊领域(比如交通、住宅、公共设施等)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43) 由于金融资本在都市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哈维进而认为,资本主义由此迈入了一个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崭新阶段。“金融资本通过政府、公司和金融机构来运作,有效地协调了所有社会活动,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在直接生产产品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演化成了一种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后者不仅寻求通过产品的生产来创造和占有价值,而且通过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欲望和需求,创造和占有价值。”(44)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谈及的“生产方式”是一个被哈维拓展了的概念。在哈维那里,生产已不限于直接生产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占有剩余价值,而是一种“作为整体的生产”,其中还包括新的消费方式的生产,以及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产。(45)因为新的消费方式、新的欲求和需求都是都市化催生出来的产物,这种生产实际上即是以都市化为内容的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概念,也把我们引向哈维观点的第三个面向。 第三,资本积累向次级循环的转移,是与都市化过程及其催生的新的消费方式、新的欲望和需求的生产相联系的,即与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变化相联系,这种变化为资本增殖创造了新的空间。从总体的循环看,这是资本主义为其资本过度积累进行时空修复的过程。 哈维强调,必须把都市化这一纷繁复杂的现象,抽象地还原为营建环境的形成和劳动力再生产这两个维度,以便将都市化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考察。在马克思那里仅指出,工人阶级作为众多单个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是从属于资本积累的。哈维则更进了一步,他把工人阶级的劳动力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扩充为整个都市化过程,并将工人阶级本身的再生产视为现代都市化的实质。工人阶级的消费对资本积累的隶属关系,如今具体化为金融资本对大众消费方式的操纵。“金融机构和政府管理着都市化过程,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并缓和社会的不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新的消费方式以及新的社会欲望和需求就必须被生产出来”,否则,“人民就要被迫或被哄骗着接受它们”。“通过对人民面对的各种选择进行构造和再构造,通过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决策环境,都市化过程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这个目的。”(46) 哈维论证了金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剥削形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对直接生产过程分析的基础上的(假定消费方式以及欲望和需求都保持不变)。然而剥削还可产生于新的消费方式的创造,以及把新的社会欲望和需求强加给人民——剥削可以将自己建立在收入循环的基础上,就像建立在资本循环的基础上一样。”(47)它概括了哈维地租理论的重要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垄断地租”的攫取是以各种收入形式为基础的,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收入,可以与利润等其他形式的收入一道,成为“阶级—垄断地租”剥削的源泉。哈维为此总结了资本进行剥削的两种途径:“以劳动为基础的剥削”(work-based exploitation);“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剥削”(community-based exploitation)。(48)后者作为以劳动力再生产为基础的剥削,在整个新自由主义阶段对金融资本的价值增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构成了资本金融化的实质。(49)金融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加深了劳动对金融资本的实质隶属。这部分地解释了金融资本何以替代产业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力量。“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狭义的生产(工业生产的组织)。而在晚近资本主义下,在其各个面向上进行的生产可以预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工业家仅仅熟稔于直接生产,因而对作为总体的生产几乎没有控制力。金融资本(通过产业、金融机构和政府而运作)作为霸权力量,便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崛起了。都市化也从工业家的生产性需要的表现,转化为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金融资本凌驾于作为总体的生产过程之上的控制权力的表现。”(50) 第四,哈维指出,资本由初级循环转入以都市化为代表的次级循环,虽然有利于克服初级循环中的过度积累,但其缓解作用有限,会导致次级循环本身乃至资本积累总体陷入危机。这种震荡即为资本“重构空间”的痛苦过程。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断地“用时间消灭空间”,以加速资本流通的周转速度。这需要大规模地营建都市的基础设施,其主要构成包括低价乃至免费供应的公共服务产品。以都市化为代表的次级循环所构建的营建环境,通过对都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吸收初级循环的过剩资本,再加上嵌入或附着于土地的住宅、写字楼、厂房、酒店旅馆、物流及文卫设施等,致使超大规模的固定资本集聚地沉没在静止的城市空间中,极其缺乏流动性。资本空间的扩张和固化,反过来又会成为资本流动和周转加速的障碍。一旦滞留在初级循环中的过剩资本引爆经济危机,导致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无产业支撑的都市营建环境,会瞬间由繁荣沦为“鬼城”,引致哈维所说的毁灭现有营建环境的“去地域化”。(51)营建环境的资本主要来自“阶级—垄断地租”,其采取的虚拟资本形式,以投机欺诈为特征,当资本在次级循环中过度积累时,往往会首先急剧地贬值。因此,债务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又会成为通过经济危机“去地域化”的征兆。 在讨论“阶级—垄断地租”的乘数效应时,哈维就提出,这一乘数效应的存在虽然是吸引资本转入次级循环的条件,但问题在于,这一乘数效应只能是短期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何以在较长时期内,来自次级循环的收益仍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如果所有资本都去追逐租金,而不从事生产,就不会有价值生产出来,而后者是地租所代表的转移支付能够形成的源泉。”(52) 在次级循环中进行的营建环境的生产,虽可用于贮藏财富,但多半并不直接生产价值。于是,就引出了哈维所谓的“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资本金融化所采取的虚拟形式,是“因应竞争性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产生的,但其本身又因各种矛盾的趋势而变得不稳定和困难重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出于必然性,将货币看作‘自在之物’,并因此倾向于不断破坏价值的生产,以追求财富的形式而非实体。货币的这种异化与虚幻的权力,以及各种被创造出来以促进金融资本运作的制度,与价值的生产毫无联系。这可以解释投资以牺牲生产性初级循环为代价,进入次级循环的转向。这种试图不生产价值却又要实现价值的持续趋势,事实上是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这一核心矛盾的具体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城市风景中看得清清楚楚。”(53) 在这一矛盾的驱使下,初级循环“导向过度积累的趋势并没有被取消。相反,这个趋势被转化为在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中导向过度积累的普遍趋势”。(54)哈维指出,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历次主要危机,如1929-1933年危机、1973-1974年危机,乃至最近出现的2008年危机,都是以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为先导的。(55)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危机的形成,都有着都市化虚假繁荣泡沫的根源。但遗憾的是,危机成因中的这个维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都被忽视了。哈维尖锐地提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缺失,它们“未曾有过严肃的尝试,在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中纳入对都市化和营建环境之形成的理解”。(56)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确实发人深省。 尚需指出,哈维关于资本次级循环的定义,其初衷着眼于营建环境的生产。但次级循环的界定应更为宽泛,可将一切虚拟资本的循环都纳入其中,成为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虚拟资本循环的叠加。资本在营建环境中的循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样,哈维针对“阶级—垄断地租”及其内含的一切矛盾的分析,将不仅适应于营建环境构成的房地产市场,而且适用于一切由虚拟资本构成的资本市场。 纽约新学院大学的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邓肯·弗里(D.Foley),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以类似的方式,谈到租的概念对于分析当代金融市场和金融收入的适用性。“从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金融收入都是全球剩余价值蓄水池中的一部分,本质上都类似于土地和资源的租金。”(57)在他看来,这些租金(实际上就是“阶级—垄断地租”)在金融、信息和服务业的再生产,涉及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占有在国内和国际间的不平衡运动,收入分配在国内和国际间的两极化,以及生态和环境因素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的制约等一系列当代社会的重大矛盾。这表明,哈维当年面对的问题今天正获得越来越多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弗里的文章并未提及包括哈维在内的其他学者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谱系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家(而非仅仅是地理学家)的哈维,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重视。 马克思指出,英国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但是,“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益,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58)马克思进而强调,“地产和资本”是“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姿态,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59) 哈维确认了当年马克思的预期,资本从其本性出发会抵制将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因为这样做也会危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威胁到私人资本本身。(60)他进一步提出,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土地转而成为一种金融资产,一种虚拟形式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找到了“驯服”土地私有权的途径,实现了土地对资本的“实质隶属”。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界限完全消失了,地租和利润之间的界限也是如此。(61)地租理论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理论,因为只要存在持久的超额利润,不论这一利润是否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事实上都可纳入地租理论的解释范围。在此意义上,地租理论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已然占据着传统理论难以想象的重要地位,用哈维的话来说,成为现代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核心内容。(62) 哈维关于“阶级—垄断地租”、都市化和金融化的理论,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些理论在分析进路上与当代几个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如垄断资本学派、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存在着相似性。这既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服从于某种共同的演化逻辑,也彰显出哈维的理论所内含的普遍意义。 在哈维的著作中,人们不难找到他对“消费不足论”的批判,(63)而“消费不足论”恰恰是以斯威齐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学派在解释危机成因时常用的观点。其实,“消费不足论”可划归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类别,即从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对立关系,理解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层成因。这正是哈维和垄断资本学派之间的相通之处。(64)差别只在于,双方对于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剩余的增长和吸收,是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他们揭示,自二战结束以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据的份额一直在提高,这一趋势反映出垄断资本为了克服剩余的增长,将广义金融部门的扩张作为吸收剩余的手段之一。(65)此后,斯威齐在与马格多夫合著的一系列论文中,又进一步利用上述分析架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指出金融化已成为吸收剩余的最主要手段。(66)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哈维借鉴了垄断资本学派的基本分析架构。与垄断资本学派不同的是,他将围绕营建环境的投资和都市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吸收剩余的最主要手段。(67)在其后续的著作中,哈维进一步提出了资本积累由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转移的假设,并以此作为分析金融化的框架。这个新的框架实际上是对垄断资本学派的发展,因为整个次级循环都可以看作剩余吸收的领域。他们都认为,金融化在长期内是难以为继的。生产性部门的停滞趋势或过度积累,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只是被转移,并没有被消灭,最终将带来整个体系的危机。 哈维思想与法国调节学派的亲缘关系更为明显。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中,哈维系统地采纳了调节学派的概念和思想。(68)尽管在危机理论中,哈维一直批判调节学派所坚持的“利润挤压论”,但他与调节学派(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提倡对资本积累进行制度分析,不妨将它们并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学派。(69)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和调节学派识别了资本积累与其制度环境的内在联系。它们强调,资本积累是受制度约束的;一个稳定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或调节方式的存在,是资本积累得以迅速和持续展开的必要条件;在长期内,积累的社会结构或调节方式界定了资本积累的基本模式。这一分析进路与哈维的制度分析大体一致。哈维认为,只有在国家和金融制度的支持下,作为资本积累具体型式的都市化才能得到发展,并达到维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缓和社会矛盾的目标。 哈维对相关制度类型的分析,与上述两个学派也有明显的可比性。调节学派的布瓦耶(Robert Boyer)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概括为:货币信用制度、雇佣劳动关系、竞争的类型、国家干预的方式、加入国际体制的方式。(70)类似地,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那里,相关的制度分析涉及资本—劳动、资本—资本、政府—市场、金融体制等多个维度。在哈维的分析中,金融制度和政府对于绝对空间或次级循环的塑造起着关键的作用,并把基于劳动力再生产而形成的次级剥削提升到重要范畴的高度,拓宽了资本—劳动关系的含义以及相关制度分析的范围。 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殊的制度分析相结合,展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中的“中间层次分析”。哈维关于城市土地利用和“阶级—垄断地租”的制度分析,也是如此。哈维曾自述其方法论的特点:“可以就此得出的结论是(倘若这个结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还不明显的话),地租只在因情况而异的意义上存在——它取决于一种生产方式以及和财产占有相关的某些制度”,“并不存在一个‘一般的’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论。只有特殊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在下述意义上发挥作用,即在一套特殊的假定下(这些假定涉及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性质、社会流行的各项制度),帮助阐明其存在的条件,或确立有关的选择。”(71) 哈维对都市化及其吸收剩余作用的分析,与调节学派注重有效需求的制度分析极为类似,并可互为补充。哈维强调,战后都市化是从需求方面解决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重要手段。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资本主义聚焦于消费、尤其是工人阶级消费的扩张。“对这类解决方法的寻求,经历了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和消费的转变。资本主义本身改变了动力,从‘供给面’转向‘需求面’的都市化。”由此形成了所谓“凯恩斯主义城市”,“通过对空间的全面重构,动员有效需求,以便使对汽车、石油、橡胶和建筑产业的需求,成为一种必要而非奢侈品”。(72)可见,哈维实际上为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概念,增添了一个空间重构的维度。 总之,在哈维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却未曾被当事人充分体认的契合关系。哈维的理论尽管有其特立独行的风格,但并非游离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潮流之外。将哈维的观点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派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到贡献,也便于我们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总体风貌。 ①《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8页。 ②A.Haila,"The Theory of Land Rent at the Crossroa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vol.8,1990,p.278. ③A.Haila,"The Theory of Land Rent at the Crossroads," p.279. ④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pp.187-188. ⑤马克思也曾说,租地农场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资本论》第3卷,第698页) ⑥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Oxford:Basil Blackwell,1985,p.97; 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London:Verso,1999,Ch.9,11. ⑦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Ch.11. ⑧参见D.Harvey and L.Chatterjee,"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Government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tipode,vol.6,no.1,1974,pp.34-35,36(note 18). ⑨参见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80,113-114. (10)D.Harvey and L.Chatterjee,"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Government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32. (11)《资本论》第3卷,第215—216页。引文中的黑体为笔者所加。 (12)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58,168. (13)参见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68-171. (14)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68-69. (15)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69. (16)《资本论》第3卷,第864页。 (17)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182. (18)D.Harvey and L.Chatterjee,"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Government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9)D.Harvey,"Class-Monopoly Rent,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Regional Study,vol.8,1974,pp.239-255. (20)参见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65.并可与注释14指出的页码相比较。 (21)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pp.349-353. (22)哈维:《资本之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23)“如果在一个国家,农业资本的构成与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相等”,“农产品的价值就会同它的费用价格相等。这时只可能支付级差地租。那些不提供级差地租、只能带来[真正的]农业地租(指绝对地租——笔者注)的地段,这时就根本不可能支付任何地租了”。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448页。 (25)《资本论》第3卷,第862页。 (26)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p.353. (27)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91,194. (28)D.Harvey,"The Urban Roots of Financial Crises:Reclaiming the City for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Socialist Register,vol.48,2012,p.7.笔者把英文里的“urbanization”译为“都市化”,而非“城市化”,是基于以下考虑,在哈维那里,“urbanization”是与另一术语“Metropolis”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他所谈论的城市化是从大都市的角度来规划的,因而并非一般意义的城市化。 (29)哈维:《资本之谜》,第165—167页;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270-273.哈维还指出,早在波拿巴执政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由奥斯曼主导的巴黎城市改建工程,就已成为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克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参见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8、128页。 (30)D.Harvey,"The Urban Roots of Financial Crises:Reclaiming the City for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pp.15-16. (31)哈维:《资本之谜》,第165页。 (32)哈维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一现象会派生出以下悖论。即一些在社会中最不具有生产性的活动,却坐落在区位最佳、边际生产率本应最高的地段。哈维对这个悖论是这样解释的:城市中心区位的地租并非来自土地的边际生产率;那些位居城市中心的企业或机构,恰好位于社会制度层级的顶端,可以汲取到足够的收益以支付垄断地租。参见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188. (33)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192. (34)D.Harvey and L.Chatterjee,"Absolute Rent and the Structuring of Space by Governmental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p.23-24; 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166; D.Harvey,"Class-Monopoly Rent,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哈维在分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由奥斯曼主导的巴黎改建过程时也曾强调,国家、金融资本和地主利益的结合,是支撑和推动这一工程开展的核心制度架构。参见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第113页。 (35)D.Harvey,"Class-Monopoly Rent,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36)哈维:《资本的空间》,王志弘、王玥民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9页。 (37)D.Harvey,"Class-Monopoly Rent,Finance Capital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38)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0. (39)转引自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62. (40)D.Harvey,"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2,nos.1-4,1978,p.104. (41)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81-82.从理论上看,这种乘数效应还可从哈维在他处阐发的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的概念中,获得进一步论证。哈维区分了空间的三种属性,即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正如前文提及的,绝对空间是形成阶级垄断的前提。相对空间则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基础,它会因交通条件的改变而变化。所谓关系空间,按照他的解释,是从相对空间中独立出来的一种属性,意指空间“在下述意义上被包含在对象之中,即一个对象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表现了与其他对象的关系时,这个对象才可以说是存在着。”在哈维看来,关系空间对于理解地租乃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具有关键的意义。他写道:“不同地段的土地可以获取收益,因为它们包含了与其他地段的关系”,“在地租这一形式中,关系空间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面向而出现了。”(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3-14)哈维认为,“空间是个关键词”,参见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15、120页。 (42)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7. (43)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7.黑体为笔者所加。 (44)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6. (45)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7. (46)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0. (47)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7. (48)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6. (49)对金融化这一面向的分析,可参见C.Lapavitsas,"Financialised Capitalism:Crisi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7,2009,pp.114-148. (50)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8. (51)哈维用不断深化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空间修复”(spatial fix)以及“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因素”(capita's mom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分析资本积累的潮起潮落在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参见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52)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64. (53)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88. (54)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12. (55)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19-20; D.Harvey,"The Urban Roots of Financial Crises:Reclaiming the City for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56)D.Harvey,"The Urban Roots of Financial Crises:Reclaiming the City for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57)D.Foley,"Rethinking 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5,no.3,2013,p.264.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5、643页以及813页注209。引文中的“租”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一版中均译为“地租”,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没有什么区别。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引文中的“资本”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1版中译为“金融资本”。 (60)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Ch.11. (61)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65,92-93.但有学者认为,土地作为纯粹的金融资产只能是一种趋势,因为存在各种反作用的影响,包括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企业行为的变化、政府和立法干预的影响、土地所有者的竞争等诸方面。参见A.Haila,"Land as a Financial Asset:The Theory of Urban Rent as a Mirror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tipode,vol.20,no.2,1988,pp.79-101. (62)D.Harvey,"The Urban Roots of Financial Crises:Reclaiming the City for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p.7;哈维:《资本之谜》,第177—178页。 (63)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pp.77-94. (64)他们都反对“利润挤压论”。后者把1973—1974年危机的成因归于分配领域的阶级斗争,忽视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这一在总体上支配资本积累的矛盾结构。参见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pp.52-54. (65)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35页。 (66)H.Magdoff and P.Sweezy,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7. (67)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92,270-273; 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191. (68)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90. (69)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70)Robert Boyer,"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in Giovanni Dosi et al.,eds.,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88. (71)D.Harvey,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pp.192,194. (72)D.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pp.202,207.标签:级差地租论文; 地租理论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价格垄断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大卫·哈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