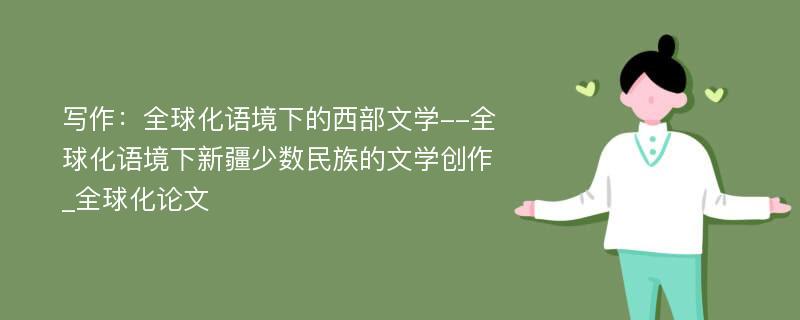
笔谈: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全球化语境中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笔谈论文,新疆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最初仅是经济领域的事,倡导者和规则制定者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已积聚了充分的条件和基础,从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必须加入这个进程,否则就会被21世纪的世界淘汰。可是,高悬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艺术,是不是会随着经济的变革而完全实现直接转化呢?文化历来标榜的是“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文化更是以多元化、“本土化”的追求来尽可能地保留本民族传统,并给予其他民族传统以一席之地的。因此,作为全球化的最大敌人的民族国家利益,它所表现的“本土化”思维方式,正是在文化问题上显现得最为突出和尖锐,这种力量,是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生于斯长于斯旦夕呼吸于斯的,它对个体有着先验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潜在制约(亦即“种族集体无意识”),是任何个体不能也不愿超脱的。文化的全球化在新疆体现为一种“语境”的热流。“语境”一词在这里的深刻性表现在它不是物境,不是实境,而只是“话语”之境,只是一个话语阶段。
首先,“文化全球化”的最主要的阻力,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本身包含以中国的伦理道德本位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包括赛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它同西方文化是很难趋同的。而新疆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伊斯兰文化作为这里主体民族的宗教信仰,它的影响早已不仅是宗教传统了,它甚至构成了维吾尔、哈萨克、回、乌兹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内容。假如说,新疆地区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始终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作为主流话语的儒家文化保持着既互相影响渗透又始终有一段距离的关系而不能真正地完全融合的话,那么它与西方文化的距离则是更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伊斯兰文化是反对“全球化”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和宗教传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那就是涉及到有关民族生活的内容,就无法离开伊斯兰教的传说、词语、意象的变异,它们已与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俗语、谚语、格言混合在一起了。例如诗人铁衣甫江的爱国主义诗篇、爱情诗篇均有这类引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宗教观念体现在意识及行为方式上,它决定了一个民族对人生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解和选择。维吾尔族青年女作家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小说《鸿雁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及情感关系的理解即具有明显的与内地作家不同的方式。
其次,“文化全球化”的第二个阻力,是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化对自身文化传统及主体性的维护。连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也指出“全球化正在危害各国的文化传统”(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这一认识出发,除美国之外的各民族国家甚至包括与美国一起高喊经济全球化的西欧,都在竭尽全力维护民族文化传统。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新疆各少数民族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变化,那么,新疆的作家是怎么对待这种力求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变化的呢?
伴随着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迅速扩展,他们都表达了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的强烈担忧。近年来,在新疆极有代表性的作家麦迈提明·吾守尔是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中一面重视凸现维吾尔族的幽默特性,一面却让读者在笑声中感到一种虚空的沉重:“女人们留着假胡子,男人们戴着假发,吃饭下馆子,睡觉住店,自己家的屋子出租挣钱,喝热茶要放冰块,冰激凌要搞热了吃……这些怪事真叫你吃惊。我们街上的赛来塔洪你可能认识吧?他如今卖裤头袜子可发了,去朝圣回来成了阿布都赛来提阿吉。这些日子以来他发火了,说:‘我们的传统跑到哪儿去了?’用大布缝了一件衬衣穿上,又用细土布做了一条领带系上,新买的小轿车里铺了一领席子开着到处跑……”小说《镶金牙的狗》本身是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撞,在这里,西方文化既破坏了本民族文化,严重扭曲着本民族原有的人际关系,却又是隐指作者批判甚至戏谑的对象。麦迈提明·吾守尔同时又以一种哲学家、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独有的才情与眼光,以对本民族生活、性格、文化的深刻的理解去追寻着民族精神的复归。在《被沙漠淹没的古城》中,他连续运用维吾尔民间叙事中的诸多母题,如“行吟诗人”、“三兄弟”、“小儿子与家族继承权”等等,将这些统一在一个故事中,表面看来似乎写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其实在深层结构中,有绿洲、水、纯善的道德、美的精神的、适于人生存的古城所代表的正是已失去的传统文化,而寻找古城,想要复原古城终生不可得,却又传遗言于子孙后代(继承“家产”)再去寻找的老人,则是固守传统的精神象征。淹没了古城的沙漠是与传统文化构成对立的赤裸裸的人欲、物欲。这篇小说所包含的是厚重的历史精神和广阔的民族生活世界。
即使是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仍然是固执地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在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中熟练地使用汉语,叙说的是锡伯族的辉煌与挫败、奋起与跌落。他是东北移驻新疆的锡伯族官兵的后裔,锡伯族西迁的历史像汹涌而来的忧郁而又悲壮的诗篇,追随着他的心灵和生命。他的《父亲之死》虽是短篇集,但却又是许多篇章组成的历史长卷,它写尽了西迁的血泪、生死、爱恨,充满了对命运的无奈又洋溢着抗拒命运的骄傲与不屈。这是一个古老民族伤痕累累的历史,然而这伤痕却又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其他民族文化的海洋之中傲然屹立的力量源泉。如果说麦迈提明着重体现的是民族化,那么傅查新昌着重体现的是“本土化”。他是生活在都市的作家,却以“客居”的态度去写锡伯族的乡土文化,无论是西迁系列,还是“阿古古系列”都是从不同侧面苦苦营造着锡伯族的精神故土。与西迁系列那种沉重却又充满自豪感的追寻相反,“阿古古系列”描绘的是现实状况的本质以及身处其中的锡伯族当代文化的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传统文化崩溃与消失前的恐慌与不安。一方面是在向其他民族的读者展示着锡伯人生存的过程,另一方面却是在灾难面前迷失方向的文化带给他的抑郁。
最后,“文化全球化”还面对着西方20多年来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影响。后现代文化思潮建立于西方的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的后工业化社会,而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本不具备这种思潮传播的社会条件,可是后现代的“除中心论”“反同一性、反总体论”,强调“差异”“多元化”“多样性”等等思想和理论却在这里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究其原因,它们恰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有关。新疆的文化始终是多元化的,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互相传播的重要文化中介,经此东渐的西方文化和西渐的中原文化莫不打上了西域文化的鲜明烙印。各种宗教都曾在这里传播,各个民族的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其他民族语言或以双语进行着文学创作,组成了各具特色又百川汇海的文学状貌,所以,它们之间是既“输入”又“输出”的。至今,它们与其他民族地域文学的关系仍是相互影响、交流又各自独立的。这,就是今日新疆文学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诚如詹明信所说:“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但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决定了它只输出文化,输入人才、能源、金钱,却绝不输入文化,它将自己的文化作为惟一主体,而将世界其他文化作为客体,以征服的态度来对待除它之外的文化,体现出文化侵略的浓烈的帝国主义气味,形成其他民族的逆反心理,反而加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再如詹明信所说,美国人的回答很干脆:“文化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化。”(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此,我们显然不准备追随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而是应该发展我们自己的中国式的审美文化。
这种中国式的审美文化,包括我们的主流文化,也包括民族化、本土化、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少数民族文化。它需要的不是“趋同”的“一体化”的全球化,因为,一旦人类的文明统一到一种单一模式了,它就丧失继续发展的动力,那将是文明的尽头。对此,傅查新昌的话最能代表新疆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需要:“就像你了解我一样,我很相信自己很了解你的存在。你的存在与不存在,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故事,所以我无法把你存放于我的生命深处……你不要伤害我,请你允许我存在,尽管我的灵魂与风暴贴得很近,请你允许我走向阳光地带,尽管你已把深深的伤害涂遍我的躯体内外,请你允许我的灵魂在风雨中闪光。”我们认为,如果真有“全球化”文化,那么,它所迎来的应该是地球人全面发展,人性高度和谐,个性充分展开,审美品位极大提升的时代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而在这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们还是致力于建立我们民族多元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