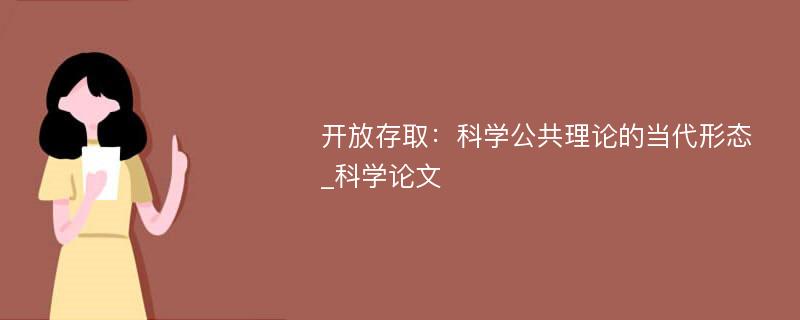
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主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4)01-0037-06
一、科学公有主义规范与传统的科学期刊出版制度
在科学公有主义建立之前,很多新的科学知识往往处于保密状态。知识的保密必然导致不断的重复发现,使得科学进步缓慢。然而,如果不使用保密的方法,则会损害科学发现者的利益。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出版之前,如何兼顾科学家之间知识交流的需要与科学知识发现者的利益,成为摆在当时的皇家学会组织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在此之前,曾多次出现争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公案。如何建立一个合适的科学信息交流系统,是当时科学共同体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了鼓励科学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当时的科学共同体最终确立了以发现优先权的归属作为科学实践“德行”的奖励方法[1]。这种奖励方法建立在发现者公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标明发现优先权的方式,将科学发现与科学家的名字相联系。这大大调动了研究者公布研究成果的积极性。这样就解决了保护科学发现者的利益与促进科学知识传播之间的矛盾。
默顿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科学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性的概念,是与科学发现应该交流这一规则联系在一起的。”[2]默顿详细考察了在奥尔登伯格主导下,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提出、科学公有主义规范的确立和同行评议制度的开始,他认为以上三者与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哲学汇刊》出版的常态化是同一过程。而这一整套规范,都是围绕着科学共同体的实践特征设立的。[3]默顿后来在《科学社会学》中文版序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对同行承认的优先权的奖励,能起到使系统进行迅速而公开的科学交流的作用。它为科学的‘公有化’提供了制度化的动机基础。这一过程被科学产权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强化了。”[4]
在奥尔登伯格时代,科学公有主义以及相关一整套制度的确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这套制度明确了“知识论”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的归属权问题,但忽略了科学知识的获取问题,即没有考虑科学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这套“权宜之计”与科学期刊的印刷、出版、发行,以及学会制度和公共图书馆系统一起,共同形成了传统的科学共同体内部信息交流机制。
时至今日,这一套制度已运行了300多年。然而,从第一天起,这套制度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学公有主义认为科学知识的产权归属于全人类,任何人都不能私自占有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特质中的共有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中把技术当作‘私人财产的概念’水火不容”[5]。然而,在这套制度下,获得最新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免费的,学术期刊必须通过购买获得。长期以来,学术期刊的价格相对于其生产成本往往是高昂的。学术期刊的收入曾长期是各个学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如:“英国物理学会和英国化学会的期刊出版收入可占学会总收入的70%以上,IEEE的出版收入是学会收入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为会议收入),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出版《科学》杂志。”[6]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各国增加对专业学会的资助,学会不再需要学术期刊出版作为经济来源,各个专业学会纷纷将旗下知名的期刊出售给出版集团,或者自发兼并组成更为庞大的学术期刊出版集群,进一步垄断了学术期刊出版市场。[7]
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信息传播主要建立在传统印刷技术、纸质媒体和图书馆借阅的基础上,在这种传统模式中,存在着科学的发现者(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包括图书馆系统)和学术期刊出版者这三方利益—伦理主体。科学信息的传播必然涉及信息的所有权问题,印刷出版的过程也必然涉及版权的归属问题。学术期刊出版者由于出版行为而拥有版权,从而拥有法定的承载科学知识媒介的独占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和使用。学术期刊出版者拥有的版权和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公有主义规范显然是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是学术期刊最初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时就埋下的定时炸弹。在纸质载体时代,由于期刊的复制有一定成本,开放获取也不具备技术条件,因而学术期刊的有偿出售有其现实基础,再加上各国对公共图书馆系统投入较大,使得这一矛盾并不那么明显。然而,当条件逐渐发生变化后,学术期刊出版商的逐利本性与科学公有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
二、当代“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
当代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的获利是惊人的。2009年SCI核心版收录期刊的平均年订阅价格达到1302美元[8]。在2002年—2011年间,国际学术出版界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的平均年盈利率为30%,其中2009年的盈利率高达35.74%。而在美国经济最为活跃的IT产业中,2009年微软的盈利率为27.7%,谷歌为27.6%,苹果公司仅为17.8%[9]。数据库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方便了科学知识传播,但国际大出版商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对学术期刊的垄断和不断高涨的使用费为科学知识传播设置的人为阻碍让科学界越来越难以忍受。面对这样的局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起来进行抗争,要求打破出版商垄断学术期刊、真正实现科学知识的公有,而且多国的政府机构也积极支持,从而使开放获取从一种理念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并逐渐成为科学共同体内部信息传播的一种新模式。
开放获取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开放仓储(Open Access Archives),即提供平台由作者自由发布论文,自主决定采用开放获取的方式供大家利用;另一类是开放获取期刊,即基本遵循传统的学术期刊的规范,论文经过编辑筛选和同行评议之后,在公开的平台上进行发表。开放获取平台主要采用作者付费分担运行成本、读者免费的方式,不以赢利为目的。
一般认为,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1991年建立预印本服务器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开放获取的尝试。由于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周期很长,严重影响科学交流,当时一些科学家将即将发表的成果通过预印本(preprint)的方式进行交流。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建立专门网站只不过是将纸质媒介的交流方式变成网络数据库的交流方式。2001年,该网站被转交康奈尔大学管理,并更名为arxiv.org。该网站目前是最重要的开放仓储网站之一,发表过一些重要的论文(如著名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发表在该网站,而没有投给任何期刊)。
2001年12月,德国马普学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集了关于开放获取的国际研讨会,并起草和发表了《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布达佩斯倡议》对开放获取的定义为:“开放获取文献是指在互联网上公开出版的,允许任何用户对其全文进行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或链接,允许网络蜘蛛对其编制索引,将其用作软件数据或用于其他任何合法目的,除网络自身的访问限制外不存在任何经济、法律或技术方面的障碍的全文文献。开放访问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术信息免费向公众开放,它打破了价格障碍;二是指学术信息的可获得性,它打破了使用权限障碍。”[10]
由于开放获取可以节约大量的公共科研经费,有效地促进科学信息的传播,各国政府和科学管理机构纷纷表示支持开放获取运动。200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HR2613号提案《公共获取科学法案》(Public Access to Science Act),该法案要求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论文不受版权保护[11]。2004年7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议,凡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论文,应当存于开放获取论文库中,在论文发表6个月后提供在线免费访问[12]。2005年底,美国参议院通过CURES法案,提出将开放获取政策从NIH拓展到卫生部下属的其他机构,要求作者在论文被期刊录用时即进行开放式存储,并明确提出不服从本方案的机构有可能将来被拒绝资助。[13]
欧洲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对开放获取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2003年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科学院和重要的科研机构在柏林联合签署了由马普学会发起的《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 and Humanities,简称《柏林宣言》)。该宣言旨在利用互联网整合全球人类的科学与文化财富,为各国的研究者与网络使用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提供一个免费的、更加开放的科研环境;呼吁向所有网络使用者免费开放更多的科学资源,以促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进行科学交流与出版[14]。此后,“开放获取柏林会议”每年定期召开,探讨更有效地推动《柏林宣言》的实施。2004年5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表明了中国科学界和科研资助机构支持开放获取的原则和立场。2010年10月,第八届“开放获取柏林会议”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举行,这是首次在欧洲之外的国家举行这一会议。会议期间,中科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正式发布上线。
近年来,面对高昂的期刊订阅费,一些实力雄厚的西方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感到难以承担,科学界与期刊出版商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以下列举几个典型的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西方众多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0年6月,为了抗议自然出版集团(NPG)计划将其旗下的67种期刊的在线订阅费上涨400%,加州大学声称要抵制NPG。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锐减,学校难以支付高昂的数据库使用费。加州大学图书馆在公开信中指出,在2004-2010年间,加州大学学者为NPG贡献了5300多篇文章(其中638篇发表在Nature上),而且加州大学的学者多年来义务为NPG承担了审核、编辑和顾问等工作,NPG却每年向加州大学收取巨额费用。信中表示,除非NPG维持现有价格,否则学校全体教职员将集体抵制NPG。[15]
2012年4月,因难以承受持续上涨的期刊订阅费,哈佛大学向全校教师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关于期刊价格的学院咨询委员会备忘录:主要期刊订阅难以维系》(Faculty Advisory Council Memorandum on Journal Pricing: Major Periodical Subscriptions Cannot Be Sustained)。备忘录指出,在某些大的出版集团的价格垄断行为下,学术期刊的价格持续上涨,使学校图书馆面临极大的困难,传统的期刊订购模式难以为继。该委员会向全校师生提出多点建议:1)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的开放获取网络数据库,所有读者可自由访问);2)投稿给开放获取期刊,鼓励“从获得声望和荣誉转向开放获取”(move prestige to open access);3)如果教职员担任期刊编辑,而该期刊不是开放获取期刊,或价格较高,请考虑辞职;4)努力推动相关学术专业社团支持更开放的学术交流模式。[16]
一些著名科学家近年来也猛烈抨击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巨头。2012年1月,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威廉·高尔斯(William TGowers)发表了一篇博文,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爱思唯尔集团。在此文的影响下,数学博士泰勒·内伦(Tyler Neylon)建立了一个网站(www.thecostofknowledge.com),至今已有一万多名科学家在该网站上签名(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声明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不担任编辑。网站呼吁科学界同仁向“开放获取”网络期刊投稿,促进科学信息以更为“开放”的方式进行传播。
经过多年的发展,开发获取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开放获取资源数量庞大,学科覆盖面也非常广泛。2013年是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网站搜索引擎www.doaj.org创办十周年,该引擎目前收录的开放获取期刊即将突破10000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开放仓储接近3000个[17],开放获取期刊超过23,000种[18],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自开放获取运动产生以来,在西方很快掀起了各个领域的研究热潮,许多学者从多学科、多角度、多进路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截止2013年6月,Springer官网收录了52万余篇对开放获取的研究文章,仅哲学分类下就有1.5万篇之多。西方STS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如:米歇尔·派克对开放获取所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进路[19];安娜·霍金斯对学院内部开放式获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0];斯蒂芬·哈德曼从生物医药领域科研资金投资人更倾向于开放获取的原因入手,分析了开放获取本身能够极大促进科学信息传播的特征[21];丹·斯蒂恩等人则认为开放获取有助于医疗研究的全球对话[22]。
在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出版界和传播学界等对开放获取运动进行了较多的讨论,但由于学科的局限,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对开放获取的技术特点和实现方式进行介绍和分析,并没有深入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探讨。与西方STS领域的研究热潮相比,国内STS领域的学者对这一问题涉及甚少①,令人遗憾。
三、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
科学共同体遵循科学公有主义规范,但在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下,本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却被少数出版巨头用来获取暴利。在学术期刊的产生过程中,主要工作都不由出版商承担:各种公益性资金资助了大部分科学研究,科学家撰写论文,并支付发表论文的版面费,同时还义务承担了期刊论文的评审、编辑等工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只有出版商获利。随着技术的发展,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发行进入了网络数据库时代,这为开放获取提供了技术基础。然而,出版商的付费订阅方式却没有改变,而且费用越来越昂贵。当代开放获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实质上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共同体要求创立一种新的科学传播模式。一些研究者认为开放获取运动是对传统科学公有主义的回归,但这种模式所倡导的科学公有主义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公有主义,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
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一系列倡导知识共享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起,自由软件运动、开放源代码运动(Open Source)、Linux运动、公共信息许可证运动(General Public License)等陆续兴起。这一系列运动强调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反对通过版权窃据知识。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尤其是Web2.0时代的来临,这股反对版权、倡导知识共享的浪潮从专业的软件领域蔓延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开放运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这些运动主要包括:开放获取(Open Access)、开放科学数据(Open Science Data)、开放科研记录(Open Notebook Science)、开放科研(Open Research)、开放教育(Open Education)、开放同行评议(Open Peer-review)和科学2.0(Science2.0),等等。这一系列运动的主旨是在科学公有主义和开放版权思想的引导下,利用互联网模式打破旧的封闭式科学(Closed Science)研究模式,反对利用知识产权独占科学知识,提倡知识对所有人公开,提倡知识协作生产,提倡可介入式的科学研究,其核心是倡导知识是一种公共财物,而非私有财产。
在这一系列运动中,开放获取运动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得到了科学家群体和各国政府及科研机构的广泛支持。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一,开放获取所遵循的理念,与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在科学共同体中已深入人心;其二,开放科研、开放教育等其他开放性运动受科学实践的情境性影响较大,对其他研究者的使用价值较小;其三,开放获取的对象主要是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一般不涉及技术产品和专利等,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上的麻烦,也避免了与既得利益者的更大冲突;其四,开放获取可以节约大量的科研经费,能得到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的积极支持。
开放获取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形塑了科学公有主义。默顿所总结的传统的科学公有主义只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公有主义,它与传统的期刊出版模式联系紧密,强调科学家不占有科学知识,但并不考虑研究者与公众如何获取知识。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普及的条件下,科学信息的传播通过学者与编辑的共同协作即可完成,出版商的参与并非必需。在开放获取的模式下,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同样属于全社会,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科学公有主义。
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必将改变当下科学的面貌。首先,开放获取的普遍采用,不仅可以降低传播成本,还可以加快出版速度,减少知识传播的障碍,大大促进科学交流;其次,开放获取将使普通公众都可以方便地获得最新的学术信息,这对促进全社会对科学研究的认知和理解将大有裨益;最后,开放获取模式将弱化发达国家的信息优势,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科学研究方面的差距带来很大的便利。
四、开放获取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虽然开放获取作为一种新的科学传播模式有着诸多优势,但当前依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由于大部分开放仓储平台和部分开放获取期刊缺乏完善的评审机制,论文往往过多过滥、良莠不齐②;其次,开放获取期刊一般需要作者缴费,而且费用不菲,如果没有相关经费的支持难以长期维持;第三,目前开放获取论文平台过多,却缺乏一个能够整合所有平台资源的搜索引擎,使用起来颇为不便;第四,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现在的学术期刊等级是在传统的模式之下通过长期的运作形成的,目前绝大部分高级别期刊并不是开放获取期刊,而大部分开放式获取期刊也没有较高的声誉。研究者往往会把好的研究成果投给较为权威的学术期刊(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开放获取期刊),以此来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这使得原有的期刊格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将基本维持现状。不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使开放获取期刊走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开放获取最初是一种科学共同体自发的行动,与原有的依托学会或研究机构的科学共同体组织体系相比,具有零散和随机的特征,难以通过交流组成以学科专业为单位的公共空间。因此,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从政府、研究机构和学会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支持,建立整合各种开放获取资源的搜索引擎,并保障平台的长期稳定运行。同时还应从经费、人员、政策导向等多方面入手,对开放获取期刊给予更大的支持,减轻作者付费的压力,促使和鼓励高级别期刊转为开放获取,并逐步提高现有开放获取期刊的声誉。
对于解决开放获取当前存在的问题,中国有着一些天然的优势。首先,与西方很多国家不同,中国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归属国有,至少在理论上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且绝大部分学术研究都得到各种公益性资金的支持,只要政策确定,实现模式转换在操作层面并不困难;其次,与西方很多国家相对分散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体制相比,我国的体制更便于统筹协调,更有能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建立一个包含各种开放获取资源的统一平台。因此,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对推进开放获取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笔者所查阅到的国内文献中,仅有一篇论文(丁大尉、李正风.科学信息的开放存取与知识的“公有性”信念.科学学研究,2012(10))对开放获取与科学公有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开放获取是对传统公有主义的回归。但该文对知识产权的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的误解,将科学知识与技术专利知识混在一起讨论也有待商榷。
②美国《科学》杂志2013年10月所刊登的一条新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哈佛大学一名生物学家编造了一篇据称有高中以上化学知识就能看出的造假论文,投给了304 家开放获取期刊“钓鱼”,居然有一半以上的期刊“上钩”。《科学》杂志对此配发评论文章,指出开放获取期刊质量堪忧,亟须探索新方法予以提高。(Bohanon J.Who's Afraid of Peer Review?[J].Science,2013,342(10):60-65.)对于这一事件凸显的相关问题,笔者将另撰文专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