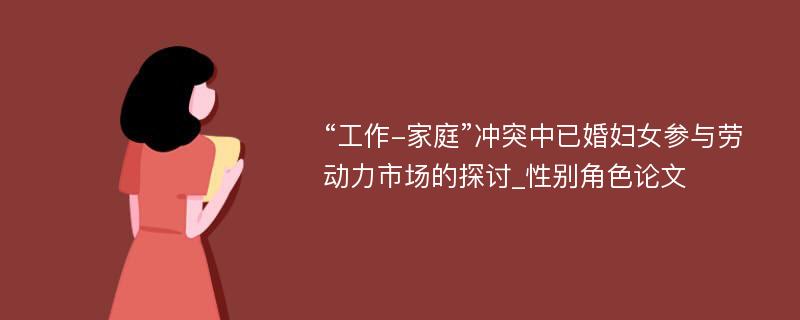
“工作——家庭”冲突中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冲突论文,家庭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791/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241-05
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对妇女、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性别分层的影响在已婚女性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婚女性的就业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各国学者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已婚女性就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深度,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持续下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作——家庭”冲突矛盾中,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已婚女性人数不断攀升,已经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状况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家庭以及性别平等都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探讨现代社会中性别角色观念转变及“工作——家庭”冲突加剧背景下已婚女性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最新动向,可为改善我国已婚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提供有益参考。
一、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
(一)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
性别角色大体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传统主义类型(Traditionalists)和平等主义类型(Egalitarian)[1](P346-367)。传统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主要观点是:家庭中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分工不同,女性成员应该留在家中照看孩子并承担家务劳动;男性成员在家庭中处于领导地位,是养家糊口的人,为家庭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这种观念在各国历史中都流传甚广,是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的价值观之一。哈基姆等人的研究指出,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中这种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还是相当普及的[2](P429)。平等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主要观点是:家庭中的男女两性是社会地位平等的成员,人们不应把女性的角色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男性也应该分担家务劳动。目前,平等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已逐渐被大多数年轻人所接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加强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现实、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变化趋势在各国的表现是有区别的,和美国、德国等国家相比,英国社会由于较强的传统主义思想,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相对缓慢[3](P76-88)。
(二)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因素
性别角色观念会受到来自历史、现实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都是宏观视角下的影响因素,也是以往性别社会分层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这些年来,国外视角逐渐转向微观的个体层面,探析影响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微观层面因素,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1)受教育水平。一个人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强有力的影响因素,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点。(2)性别因素。性别差异对性别角色观念影响显著,相对于女性群体而言,男性群体更倾向于赞同传统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3)年龄因素。研究发现,年龄较小的受访者相对于年长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赞同平等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进一步推论,平等主义类型的性别角色观念随着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的逐渐离世有加强趋势。[4](P76-88)
在当代中国,尽管提倡男女平等,改革开放和妇女运动也涤荡了旧时的风俗,但是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作为历史的积淀仍旧存在于现实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中。一直以男性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女性依然处于依附和从属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对今天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职业女性的影响依旧是广泛而深远的。人们认为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教育子女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女性的社会角色置于次要位置。同时,大多数职业女性对社会赋予自身的传统角色持认同态度,并将之内化,转而付诸行动。一些研究表明,在中国,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年轻的女性,平等主义性别角色的观念倾向性越大。她们提倡男女平等,对社会角色有着极大的渴望,劳动参与率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不仅要像男性一样扮演社会角色,承担工作上的压力,而且还要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由于时间、精力、生理等方面的限制,女性在扮演两种角色时,心理冲突与困惑就不可避免产生,工作与家庭冲突逐渐显现。
二、当代社会已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决策
(一)“工作——家庭”冲突
卡恩等人最早界定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含义,认为其是角色间冲突的一种类型,即分别来自工作角色的要求和家庭角色的要求产生了冲突,即由于工作任务或者工作需要而难以尽到对家庭的责任,或是由于家庭负担过重而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5]。格瑞豪斯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维度的概念,因工作角色的要求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work-to-family conflict WFC)和因家庭角色的需要而产生的“家庭→工作”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 FWC)。所有参与工作的社会成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工作——家庭”冲突,这其中在已婚女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严重。阿波科隆比和沃德的研究指出,在当代社会,相当多的职业女性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5](P41-42)。已婚妇女在冲破家庭的藩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均衡“工作——家庭”冲突的问题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来自于家庭方面、最易与工作形成冲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子女问题上。威尔弗德雷等人的研究指出,子女的存在是制约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屏障[6],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方面。家庭中养育子女的费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职业女性的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降低其效益工资(Effective Wage)。通常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中妇女的酬劳比男性的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均衡利弊后的选择倾向于让妇女减少一定的工作量,用来照料子女以降低儿童保育费用。
在中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作用,已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对于其影响日趋显现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来自于家庭,最易与工作形成冲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家务劳动。有研究表明,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城镇为3.75小时、农村为5.18小时,有56.1%的职业女性感觉家务劳动非常繁重。(2)子女抚养与教育。如今,独生子女居多的中国家庭对于子女抚养与教育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绝大多数母亲往往愿意花大量精力与时间投入其中。一方面,照顾幼儿容易使人疲劳与疲倦,另一方面,在孩子入学后,接送孩子以及奔波于各种教育培训班之间成为绝大多数母亲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象,在这种状态下,这些已婚女性投入工作的时间与精力是很有限的。(3)照顾年迈的父母。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增强,一对夫妻养护四个老人的现象也在与日俱增。在老人身体健康能够自理的情况下,职业妇女可以正常工作,但在老人生病住院需要护理或者长期不能自理时,职业妇女通常成为护理老人的主力军。因此,纵观中国已婚妇女整个职业生涯期,伴随着“工作——家庭”冲突,至少给已婚妇女产生四方面负面影响:影响职业女性业务水平的提高;影响身体与身心健康;减少娱乐时间;不得不放弃业余爱好。
(二)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新决策:“回归家庭”?
“工作——家庭”冲突在各国都普遍存在,每个已婚妇女都在权衡各方面的因素,谋求符合自身状况和社会环境的理性选择,力求以最适合的模式来对待婚育后的就业问题。近几年,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在已婚、有子女的女性群体中,逐渐产生一种从工作回归家庭的最新趋势。布伦纳、贝尔金、美国广告公司新闻等相继宣称,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从工作回归家庭,以便更好地照料子女。这和一直被论证了的日益增长的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相悖,引起了相关领域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认为,这类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只是暂时回归家庭,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此完全放弃工作、一直留守在家中承担家庭事务。她们在更加需要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选择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并等待时机成熟(如子女成长到学龄年龄等),在合适的时机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可以说,她们把这种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视为一种特殊的产假(Baby Sabbatical),其中的逻辑依据为“兼得之,但不同时得之”[7](P526-556)。
通常情况下,这种暂时回归家庭的趋势只在受教育水平高、经济状况相对富裕的年轻孕育妇女群体中才存在,而在受教育水平较低、无经济保障的女性群体中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低、无经济保障的妇女在子女抚育质量方面的预期比受教育水平较高、有经济保障的妇女的预期要低,她们养育子女的预期费用也相对偏低;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较低、无经济保障妇女的家庭经济状况不足以支付其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损失。而且,她们由于受教育水平低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就很难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安娜和斯特凡妮对德国和波兰妇女的调查就表明,家庭中有幼年儿童需要照料的妇女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往往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是迫于养育子女压力下的被动选择。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妇女逐渐希望重新就业。但是,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就业机会时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于是被动地继续维持失业状态[8](P331-345)。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只要达到了工作要求的标准,这些妇女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类似问题与现象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在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曾经是较高的。一方面,国家提倡男女平等,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就业领域,鼓励女性参加工作,宣传劳动光荣,独立自主。在城镇,“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单位提供的保育方面的福利,为已婚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劳动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提供了空间。由于减少了妇女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时间投入,使其能从生育子女的“重任”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水平,并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截止到1990年,妇女就业率就已经上升到73%,远远高于世界53%的平均水平。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加快与市场竞争加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开始走低。尤其是近10年,“回归家庭”逐渐成为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决策的新趋势。分析其中原因,除了经济结构调整下引发的被迫性失业(即下岗),更多的已婚女性正是面临“工作——家庭”矛盾而不得不选择阶段性就业或永久性自愿失业。
家庭效用最大化成为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主要决策依据之一。在自己劳动收入低、文化技能水平不高而配偶有稳定收入的女性群体中,考虑到家务劳动、照顾子女的各种成本与工作收入间的差异,其往往会自愿选择“回归家庭”。而收入和综合素质均较高的职业女性,一部分会选择继续阶段性就业,即在儿幼时,选择“回归家庭”,悉心照顾子女与家庭,待孩子成长后重新就业;而另一部分看重社会价值实现的女性,虽然会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但在“工作——家庭”冲突下,她们更多的是面临职业与家庭带来的双重压力,在牺牲闲暇时间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据2010年底新浪网的最新调查,有逾四成的已婚妇女想当全职太太,其中绝大多数人的理由是“工作家庭双重压力大,很累”。
三、“工作——家庭”制衡下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政策路径
国外一些实践证明,国家对已婚女性支持越大,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就越高。斯蒂尔和卢因·爱普斯坦对12个工业化国家中哺乳期妇女的就业状况的研究表明,在向职业妇女提供有效支持的国家中,哺乳期妇女持续就业率是最高的,相应的,在不能提供足够支持的国家中,哺乳期的妇女的失业率高[9](P17,31-60)。威尔弗德雷等人的跨国研究显示,各国间在支持已婚女性就业的制度性安排方面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子女问题对妇女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力的差异[8]。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制度层面来探求保障已婚妇女群体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对策。
(一)普及儿童保育服务,完善家务劳动社会化体系
在保障已婚女性就业的制度性安排中,儿童保育方面的公共服务应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已婚妇女的工作与国家对其子女的照料是直接相关的,只有子女得到安全妥善的照料,她们才能解除来自于家庭最大的后顾之忧、真正冲破家庭的壁垒、重新返回到劳动力市场中。
在中国,幼儿园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能针对三岁以内儿童的日托、全托机构,或者在工作单位附近设置的幼儿看护所等公共设施是稀缺的。这些儿童多半是由祖父母辈的老人在看护,倘若家里无老人,孩子的母亲退出工作就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即使是上了幼儿园或小学的孩子,出于安全的考虑,花费一定时间接送孩子成为目前家长每天的必修课。虽然现在家政服务非常流行,但是在专业化、规范性以及普及型方面还有所欠缺。倘若不能根据现实需求,提供专业的服务、能够被接受的市场价格,家政服务将永远停留在简单做家务的体力劳动范畴内,是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
(二)提供符合已婚妇女需求的就业机会
在劳动力市场中适当设置工作时间弹性较大的兼职工作、临时工等职位,也是提高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有效渠道。我们要把为已婚女性提供符合需求的兼职就业机会和兼职工作的女性化(Feminization)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已婚女性在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兼职就业的需求,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兼职工作都让女性群体来承担。兼职工作的女性化本质上是性别不平等在劳动力市场中加剧的表现,是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杜绝的。主张给已婚女性提供一定量的兼职就业机会,是为了让有兼职就业需要的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更符合其需求的职位,而不是走向极端、认为所有的兼职工作都应该由女性去承担。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我们不应该加以区别对待,并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中。
(三)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
劳动力市场中的全职、正规工作往往是一些管理性质的文职工作,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通常对受教育水平有较高的要求,其收入比兼职工作要高得多,但严格的职业标准让大多数已婚女性丧失了全职工作的机会。有就业要求的女性大多数只能从事诸如手工制作业、零售业、服务业之类行业的兼职工作,这往往也是其无奈之举。日本就业安全局的数据资料显示,1995年国内自愿申请兼职工作的人数为13 300人,而同年却有114 120人在承担兼职性质的工作岗位,可见,有相当比例的人从事兼职工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全职工作的严格要求让其望而却步,迫于生活的压力,只好选择兼职的职位。在中国,有相当多的阶段性就业的已婚女性,由于长期受到职业阻隔,在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临时性工作,而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因此重新“回归家庭”,成为永久的“被迫”失业者。受教育水平偏低、缺乏足够的职业培训与文化学习已经严重制约了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这不利于社会充分利用闲置的劳动力、不利于贫困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不利于已婚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解决问题的出路不应是降低全职工作的准入要求,而是提高已婚女性群体的整体素质,加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这里最关键的途径便是教育与培训。如何为已婚“失业”女性提供有效的教育,创造培训机会应是我国政府与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继续发挥人口政策的积极作用
如上所述,影响已婚女性群体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绝大多数妇女必须经历的生育期。妇女的每一次生育期都必须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中断职业生涯。生育子女多的妇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更长、次数更多,生育次数的多少也成为已婚妇女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直接影响因素。每个家庭的生育决策不仅在宏观层面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人口发展走向,而且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已婚女性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因此,每个家庭都应结合客观情况、制定适合自身的理性生育决策。理性的生育观在国家和个体维度都是十分重要的议题,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尤为重大。
就中国而言,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在扭转中国人口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丰功伟绩。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个体层面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在提高已婚妇女群体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诚然,这里我们并不是在盲目夸大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都应随着不同的社会现实而调整),而是强调在一定时期内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这也是制度安排层面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继续推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推动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有必要的。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决策者和学者都力图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在对照国际社会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适合本国的最佳应对措施。然而,要获得解决问题的有针对性的方案,最重要的还是要立足本土、结合本国具体的制度、文化背景做全方位的考量。
随着中国已婚女性“工作——家庭”观念的变迁,由此带来的冲突影响也在加剧:一方面是在职场面临与男性同等条件的工作状态与考评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家务以及子女照顾的主要承担者,长期心理疲惫与精力透支已经严重影响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和谐,是继续工作还是回归家庭,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这些已经成为众多已婚女性必须回答的问题。无论这些已婚女性是否真正退出劳动力市场,至少我们看到“工作——家庭”冲突对中国已婚妇女未来劳动力市场参与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关注与解决这个问题是国家、社会乃至每个家庭应有的责任。对于政府而言,应从政策引导和制定上缓解此类冲突下的不利影响;对于学界而言,要关注社会变迁下已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下就业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以及心理层面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而对于社会与家庭来说,更多的应是从心理层面向已婚职业女性提供理解与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