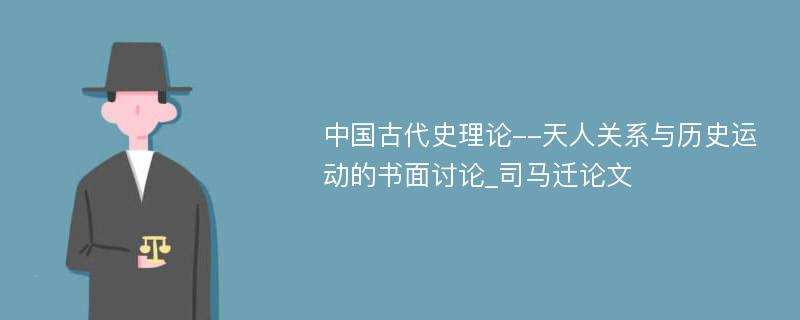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天人关系与历史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历史论文,天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 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人们对“天命”、“天道”和“人事”、“人道”有很多言论 ,也有一些困惑和辩难,其总的趋势是向着轻天命、重人事的方向发展。这反映了人们 的历史观的进步。
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一个史学家从历史撰述上把天人关系作为一个重大命题提出来, 并力图从历史事实中寻求答案,“破解”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问题,则始于西汉司马迁, 这就是他提出来的“究天人之际”的命题。按照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这涉及到论 天、论人、论势和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论天。殷和西周时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是那时人们 历史观念的核心,它在很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并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突出的反映。这种 观念在后世虽然还时隐时现地出现,但它已不能在历史观念上占据统治地位了。至晚从 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对“天”的含义已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这在史书中多有 反映。子产、单襄公等人所说的“天道”,尽管还没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 包含了自然天象的成分(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国语·周语下》)。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讲“天”,反映出人们对“天”的认识的矛盾性和过渡性。他一方面说“获罪于 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一方面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关于“天”,是持谨慎态度的。孔子是现 存最早的史书《春秋》的作者,他对“天”的这种态度,在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
春秋末年,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趋于丰富,《国语·越语下》记越国大夫范蠡的话 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 与地。……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这里所讲的,是治理国家要受到天时、人事和环境的影响。而统治者的高明就在“随 时以行”,即“守时”。反之,“天时不作”、“人事不起”则不可轻举妄动。从历史 观点来看,范蠡说的“天时”、“人事”、“随时”、“守时”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反 映出了关于天人关系中客观形势与主观判断的新认识。由此可见,当着人们对“天”不 断提出新的认识的时候,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 念发展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除有历史的根源,也还有现实的原因。当时,董 仲舒是善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汉书·董仲舒传》)的有影响的人物。他把天人 关系又拉回到古老而神秘的气氛中去了,并且赋予它以理论的形式。司马迁提出“究天 人之际”的问题,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原因,即汉武帝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和祈求 神仙活动。这种皇帝和方士的结合,使西汉社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历史氛 围中,司马迁大胆地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显示出了一位史学家的理论勇气。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上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 。第一,是对“天道”的怀疑和否定。第二,是着力阐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是揭示“时势”与人的历史活动的关系。当然,司马迁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 的窠臼和“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但这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体系中,只是 很次要的部分;这同他以大量的史事和论述阐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比较起来 ,那就更显得脆弱无力了。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 知几尖锐地批评史书中的天命思想,他认为,《汉书·五行志》和《宋书·五行志》在 这方面都存在许多谬说。他坚持“天道”“不复系乎人事”的论点,指出前代史书详载 灾异、祥瑞方面存在的“迂阔”和疑惑。
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家柳宗元在论天方面有特殊贡献,从而把中国史学上人们 对于“天”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天说》一文中指出:天地、元气、阴阳都 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只有通过人们自身去说 明,祈望和呼唤“天”来赏罚,给予人们以同情和爱护,那是再荒谬不过了。柳宗元在 《天对》中,对作为自然物的“天”自身生成和运动等问题,作了唯物的解释,从而比 较彻底地揭示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天”的神秘和敬畏的认识误区,为在新的高度上重 新探讨“天人之际”问题开辟了正确认识的道路。他对于史书《国语》所作的系统的批 评即《非<国语>》在历史观念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作为自然的天地“自己”运 动的观点。柳宗元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也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 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柳河东集 》卷四四)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作打算 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存在着相互排斥和相互吸引的现象,把这看做 是国家兴亡的征兆,是没有根据的。这样,柳宗元就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 命”的影响,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的影响。这是他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 发展上的重大贡献。
其后,史学家还有许多精辟论说。总之,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在关于“天”的 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尽管他们还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 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 向真理的王国。这正是中国史学在“天人关系”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突出表现。
(二)关于论人。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一部史 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 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 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 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 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 面,是记“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 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 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确立的标志。
——具体地描述出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写的是一部通史。从“十二本纪”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完全是由人事为发 展线索显示出来的。“十二本纪”的后论表明,司马迁是抛开了“天命”在写一部贯通 古今的人事的历史。这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是伟大的创举。
——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司马迁评价陈胜说:“陈胜虽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 他“脱挽辂一说”,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刘敬叔孙通列传》 后论)。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 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后论)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 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 。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绛侯周勃世家》后论)等等。可见他善于从历史转折 关头和重大事变中去发现起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
——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 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苏秦列传》后论)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 ,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 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陈丞相世家》后论)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 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孝景本纪》后论)六国合 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 的重要因素。
——注意到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几篇普通 人的列传的撰述宗旨时,着意称赞他们的德行。他在《游侠列传》、《滑稽列传》、《 货殖列传》中,都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可以认为,《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 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史学有重大 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历代正史在记述皇朝、皇位更迭时,有时也 会称说“天命”,但每一部正史,都毫无例外的是在写人的活动及其影响。至于制度史 ,是记述制度的沿革及其作用;编年史如《资治通鉴》,则是把“国家兴衰”、“生民 休戚”放在首位来表述;纪事本末体史书所突出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事”是其 关注的核心。凡此等等,都一再表明作为有意志的“天”的隐退,而是“人”和“事” 的凸现。
(三)关于论“势”与“理”。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 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另一条 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分开来,有时甚至是 交互进行的;而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的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 人意”与“时势”的困扰。举例来说,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 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是得 益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 守之。”(《文选》卷五二)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做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 一种明智的做法。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文选》卷五四) ,也是把所谓五等分封之制看做是“先王”之意。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 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 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他们的所谓“封建”,是指“封国士,建诸侯”即 分封制。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在对待分封制上是 “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全唐文》卷一四三)。柳宗元的《封建论》 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到 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涉及到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柳宗元 的《封建论》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这一范畴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并 用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他从“生人”之初为着“自奉自卫”这个发展趋势,阐明“ 封建”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他还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郡 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柳河东集》卷三)。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观念之明确涵义 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理 论上的启示。宋人曾巩、范祖禹等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曾巩撰《说势》一文 (《曾巩集》卷五一),其历史见解是折衷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文中所说“ 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的“势”,是指的一种综合的力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 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 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唐鉴》 卷二)范祖禹说的“时”,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评论历史 时也讲到“势”。他认为:“势因乎时,理因乎势,智者知此,非可一概以言成败也。 ”(《读通鉴论》卷一二愍帝之一)这就是说,一个有历史见识的人应当这样来看待历史 。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势”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的,这是古代史家之历史观念 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 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叙论三)。所谓“求顺于理” 的“理”,以及上面所说的“理因乎势”的“理”,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个历史 理论范畴。在王夫之看来,“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他认为“理本非一 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卷九《孟子 ·离娄上》)。“势”之必然之为“势”者,便是“理”;“理”与“势”是一致的。 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同“理”的关系来看,“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 ”的本质。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 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天人关系”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是:从“天命”决 定人事,到“天命”与人事各不相干,再到对“天命”的唾弃和对“人事”的推重;从 人屈从于“天”,到人的作用的被发现,再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要地位的被肯定;从 探讨“势”与“时”在历史运动中的意义,到揭示“势”与“时”中的“理”的存在等 ,可以说是在逐渐走向真理性认识的道路。
收稿日期:2004-04-30
标签:司马迁论文; 汉朝论文; 史记论文; 读书论文; 柳宗元论文; 读通鉴论论文; 封建论论文; 王夫之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