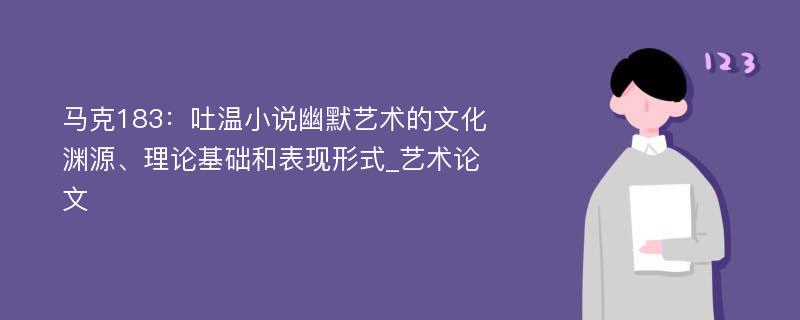
马克#183;吐温小说幽默艺术的文化根源、理论基础与表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论文,表现形式论文,根源论文,理论基础论文,幽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马克·吐温是19世纪后期美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纯粹的美国气质,标志着地道的美国本土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了马克·吐温小说独特的幽默艺术。第一,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不仅建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而且以当时美国的边疆生活作为根基,因此显得厚实、深沉、凝重与生动;第二,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是其幽默理论的具体实践,体现着幽默的内在品质,蕴含着丰富的闪光的真理;第三,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具有异彩纷呈的表现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有四种,而每一种又都是极具审美价值的。
关键词 马克·吐温 小说 本土文学 幽默艺术
马克·吐温是19世纪后期美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他之前,虽然美国的许多小说家和诗人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性地采用民族题材,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创作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国文学传统的浸润而缺乏纯粹的美国气质。惠特曼在《诗人与其计划》(1881)里援引过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指出声名鼎卓的美国诗人“过分忠实地承袭了英国的格调、气派和心情,那些修养不够深厚的英国知识分子简直要把他们看作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了”〔1〕。然而, 马克·吐温则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表明,地地道道的美国本土文学凭借独特的风格与魅力,走进了广阔而深邃的世界文学之林,不再是英国文学的附庸。正因如此,马克·吐温才被门肯称为“真正的美国文学之父”〔2〕, 被福克纳称为“我们大家的祖父”〔3〕, 被豪威尔斯称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4〕;也正因如此, 马丁斯·戴伊才说马克·吐温是“第一位摆脱了欧洲散文传统的、完全‘美国式’的散文大师”〔5〕, 帕林顿则对他作出这般评价:“现在总算有了一位地道的美国人——一位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自己的眼睛进行观察、自己的方言说话的土生土长的作家。一切欧洲的东西都丢开了,最后一点封建文化的残余也消失了,他既属于地方与西部,但也属于全美国。”〔6〕
幽默作为一种最具感染力的艺术风格,在欧洲文学尤其是西欧文学的长河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美国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有自己的幽默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幽默情调,还不足以让评论家或高层次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可是,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把幽默当成“苛求的艺术——精美的高级艺术”来追求,并且他的幽默艺术有卓尔不群的表现形式,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系统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我们就会禁不住为之击节称赏。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便是如此。
一
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不仅建构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而且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为根基,因此显得厚实、深沉、凝重与生动。早在印刷所当排字工人时,马克·吐温就大量地接触过美国西部幽默文学作品,并被其中的名篇佳作深深吸引。等到他开始创作生涯时,美国“乡土文学”和“幽默文学”更是处在极盛时期。其中,“乡土文学”作家往往运用方言,刻意描绘本地区人民的生活图景与劳动场面,他们的作品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同时也透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情调;而美国西部的“幽默文学”作家则着眼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将一种口头叙述故事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写出了许多带有消遣性的滑稽故事(tall tales)。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滑稽故事通常运用夸张手法,满篇都是方言、反语和俏皮话,一般旨在逗乐,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它们,因为正是这些滑稽故事,为后来崛起在美国文坛上的马克·吐温,提供了若干可资借鉴的艺术手法。
当然,给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带来最大影响的,乃是当时美国著名的西部幽默小说家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和阿特莫斯·沃德(Artemus Ward)。起初,马克·吐温所写的通讯报道和幽默小品,可以说承袭了哈特与沃德的艺术风格。只不过,作为一个有远见有追求的小说家,马克·吐温后来有意识地摒弃了哈特与沃德幽默故事的粗俗与平庸,把严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令人折服的审美观念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从而使他的小说不再只是简单的逗趣,不再只是为幽默而幽默。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吐温幽默艺术的深度与力度,并且蓦然发现,在马克·吐温崭新的幽默艺术和美国西部原始的幽默艺术之间,委实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吐温幽默艺术的诞生及其魅力,和他对美国边疆生活的深刻感受息息相关。美国西南部、边境矿区和太平洋沿岸是马克·吐温最熟悉最不能忘怀的三个地区。当时,美国的边疆生活相当艰苦,文化娱乐活动也异常贫乏。面对边疆生活的冷瑟与苍凉,满怀一腔热血的马克·吐温一度滋生了深深的悲观主义思想,继而勃发了一种忿怒与憎恨相互交织的情绪。正如长期沉默的人需要瞬间的爆发一样,长期悲观的人(笔者在此指的是艺术的创造者与接受者)需要用乐观情调来浸润他们的灵魂,于是马克·吐温在美国边疆广袤的土地上,锻造了他独放异彩的幽默艺术。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尼科尔曾经指出,马克·吐温深爱黑人歌曲,是因为在黑人歌曲中,幽默和悲哀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而幽默也能和忿怒憎恨的情绪并存,就象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讽刺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严肃而深沉的思考,使马克·吐温变得愤世嫉俗,使他的幽默艺术透出了姜厉而激烈的成分。有时,他确实善于以快乐的心情描写流血事件,甚至对于尸体的气味都要加以戏谑,令人感到忍俊不禁而又毛骨悚然。这种幽默艺术,又总是让我们想起约翰·尼科尔说过的另一段话:“美国式的幽默……是一个一向严肃的民族所具有的那种罕见的花穗,它的见识与其说深奥,不如说明晰;它主要依靠夸张和亦庄亦谐,由此产生的效果就象黑人歌曲用悲凉的调子唱出滑稽的歌词一样。”〔7〕显然, 马克·吐温是在边疆生活的失败与绝望中挥洒幽默的笔墨,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生活。正因如此,深谙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鲁迅先生才在《二心集·〈夏娃日记〉小引》中写道,马克·吐温“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
二
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幽默的主要外部特征当然是笑,而它的内在品质则是深刻隽永的哲理内涵和鲜明的是非美丑观。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就体现着幽默的内在品质,它是其幽默理论的具体实践,蕴含着丰富的闪光的真理。其中,最能反映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精神的幽默理论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马克·吐温看来,幽默作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发读者的笑声,让他们在开怀的大笑中得到松驰,在会心的微笑中得到愉悦,在无奈的苦笑中得到解脱。然而,马克·吐温也深深地意识到,要掌握与创造真正的幽默艺术却并非一件易事。他说:“幽默故事是一种很苛求的艺术——精美的高级艺术——只有艺术家才讲得出来。”〔8〕马克·吐温的这种幽默观念和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两段话相比,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其一是“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9〕其二是“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10〕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和马克·吐温对幽默艺术有着相同的感悟与希求,只是钱钟书先生说得更精细更明朗更生动更渊博罢了。他们的阐发表明:幽默作品决不能成为浅薄的游戏文字,不能单纯为了卖笑而存在;它是作家观照严酷现实和沉闷人生的包孕丰富的艺术载体,是作家表现是非、美丑与善恶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帮助读者在笑声中领略人生百味,增长才智,提高对人物或事物的评判能力。
其次,马克·吐温崇尚幽默文学的教谕作用。他认为,正直的作家应该具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意识,自觉地用幽默作品来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或人们身上的缺点,否则他们的作品就会缺乏力量,不能千古流传。马克·吐温曾经指出:“有人说一部小说只能是专为艺术而写出的作品,你切不可用小说来做宣传,切不可用它来教训人。这种说法,对小说来说,也许是对的,可是对幽默来说,那就不对了。幽默决不能明目张胆地说教,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宣传;但是如果要永垂不朽,那就二者都要做到才行……我就常常说教……如果幽默是主动出现、不请自来的,我就让它在我的布道词里占一个地位,不过我却不是为了幽默而写我的布道词。”〔11〕从马克·吐温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卡拉维拉县驰名的跳蛙及其他》(1867)到他中期和后期创作的大量小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杰出作家一直实践着自己的幽默艺术理论。
再次,马克·吐温主张,幽默故事应该有一种庞大的插曲式的结构形式,作家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向读者描述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幅。他说:“幽默故事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只要它喜欢,愿绕多么远就绕多么远,并不要到达什么特定的目的;……幽默故事一路讲,一路轻轻松松地冒泡。”〔12〕在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中,《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最典型地采用了这种庞大的插曲式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结构形式并非马克·吐温首创,欧洲所有的流浪汉小说都曾经采用过。正因为马克·吐温沿用这种庞大的插曲式的结构形式,通过第一人称的真实而生动的叙述,表现了主人公哈克的流浪行径,所以有的评论者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称为美国的流浪汉小说。
三
马克·吐温毕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幽默方家,他的作品处处都充满了幽默,而他的幽默艺术又有着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总是令人叹为观止。
1、运用怪诞荒谬的思维,将事物的正常情态转变为不正常情态, 然后浓墨重彩地大肆渲染,从而造成绝妙的幽默效果。在《修表记》中,马克·吐温为我们讲述了一件平凡的日常琐事:他买了一只漂亮的新表,这只表“十八个月中从没慢过,也没快过,更没停过”。然而有一天,深受主人喜爱的手表终于出了一点毛病,于是“我”便把它拿到外面去修理。没想到,修表的人都是外行,因此这只表越修越坏,到最后完全不能使用了——这件日常琐事本无幽默可言,但马克·吐温却运用怪诞荒谬的思维,将事物的正常情态转变为不正常情态,然后浓墨重彩地大肆渲染,从而造成了绝妙的幽默效果。下面,我们不妨看看马克·吐温在《修表记》中的几段文字:
我的表走得快了起来,而且一天快似一天。不出一个星期,它已病得发起高烧,脉搏的温度在背阴处也已跃到一百五十。到了两个月将尽,它早已将全城里的大小钟表统统抛到后面,比历书上的日子超出十三天还有余。它早已提前入冬,独自个儿去赏雪,尽管人间此刻还是晚秋,落叶乱飘。在它的带动下,我不得不赶凑房租,赶结帐目,赶办一切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有时,一连好几个小时,它那里边简直是在闹鬼,又是吵嚷,又是吼叫,又是呼哧,又是咳嗽,喷嚏不断,鼻息不停,搅得你意乱心烦,不知如何是好;在它这么折腾的时候,天下的确没有第二只表赶得上它。
(我的表)每次发动起来,简直象子弹出镗一般,坐力很大,震得胸口发疼。因此好几天来,我不能不戴上护胸,以保安全。最后,我只好再去找人修理。
从以上三个实例可以看到,马克·吐温运用拟人、夸张、想象与讽刺等艺术手法,似乎在向读者描述一种事实,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但读者又分明感到,这里描述的情景是离奇与不正常的,它取决于作家怪诞荒谬的思维,而这种怪诞荒谬的思维在造成作品的幽默效果方面,发挥着十分特殊的作用,难怪当时的一位评论家狄克逊·威特说道:“马克·吐温已经学会为了艺术而更加不顾事实。”〔13〕
2、着力表现人物语言与行动的矛盾冲突, 让浓烈的幽默意味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马克·吐温的这种幽默方式,是和他的讽刺意图密不可分的。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作家栩栩如生地勾画了哈克父亲的形象。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衣衫褴褛的酒鬼,“他从前老是喝醉了就和硝皮厂里的猪睡在一起”(第二章)。后来,当法官跟他讲了一通戒酒的大道理后,他居然痛哭流涕,决心重新做人,伸出手来对大伙儿说:“请看看这只手,诸位先生、诸位太太小姐;你们把它抓住吧;咱们来拉拉手。这只手呀,从前简直是个猪爪子;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它现在是个要改邪归正的人的手,这个人宁死也不再走老路了。诸位记住这些话——别忘了这是我说的。我这只手现在是干干净净的了;咱们拉拉手吧——别害怕。”当时,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感动了周围的人,于是“大伙儿一个又一个地通通都来跟他握手”,更令人惊奇的是,“法官太太还亲了亲他的手”。然而可笑的是,就在这个酒鬼作出保证的当天夜里,他又发了酒瘾,终于“拿他的新上衣换了一壶酒劲儿挺凶的威士忌”,醉得“从门廊顶上滚下去,把左胳臂摔坏了两处”。同是在这部小说中,马克·吐温还表现了“国王”与“公爵”——两个无耻的江湖骗子——在言行上的矛盾冲突,他们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地发表戒酒演说,但最后又用戒酒演说得来的钱买酒,喝得烂醉如泥(第三十一章)。在马克·吐温的小说中,象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马克·吐温善于运用独特的幽默方式,对人类的缺点或者败行劣迹,进行无情的嘲弄。他让人物自我暴露,使读者忍俊不禁。
3、采用夸张与漫画手法,突出幽默对象的本质特征, 追求幽默艺术的强烈性与深刻性。
可以说,巧妙地运用夸张与漫画手法,这一点充分显示了马克·吐温的幽默才具。在《苦行记》(Roughing It,又译《艰苦岁月》, 1872)的第15章,马克·吐温为讥讽一夫多妻制,杜撰出了一个男人娶了七十二个老婆的故事:“我把牲口卖了,造了架七英尺长九十六英尺宽的床。但我没法入睡,我发现那七十二个女人一齐打呼噜,那咆哮声震耳欲聋。还有性命危险呢!我是这么看的。她们一齐吸气,你可以看见房子墙壁真正给吸瘪进来了,然后一齐呼气,你会看见墙壁又给吹得胀了出去。她们一使劲,你会听见檩子嚓嚓作响,瓦片希里哗拉。”〔14〕通过这段描写,我们看到,马克·吐温大胆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对幽默对象的表象、数量等方面进行了极度的夸张,从而使得幽默效果更加强烈。除此之外,马克·吐温还经常用漫画手法,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幽默场景,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他的幽默艺术的深刻性。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第十八章,我们跟随着主人公哈克来到一座教堂,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景:“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两只猪,因为教堂的门并没有锁;猪在夏天贪图凉快,挺喜欢在那木条子钉的地板上睡觉。你要是留神的话,上教堂的人差不多都是万不得已才去的,猪可就不一样。”初看起来,这段夹叙夹议的话似乎有点漫不经心,但是,只要我们想起马克·吐温曾在作品中多次讽刺宗教以及人类的弱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漫画式幽默的思想内蕴。
4、打破传统幽默艺术的单一模式, 熔喜剧成分和悲剧因素于一炉,使幽默带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就美学范畴来说,幽默本属于喜剧,而传统的幽默艺术也主要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喜剧氛围,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以及美国西部幽默文学先驱们的作品,都具有这一特征。但是,马克·吐温却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幽默艺术的单一模式,促使他的幽默不同程度地悲剧化了。换言之,他的幽默往往是喜中含悲,悲中有喜,悲喜交织。《百万英镑》描述的本是一桩悲剧事件,但作品透出的幽默却含有丰富的喜剧因素;《竞选州长》本该是一出洋溢着欢乐情调的喜剧,但马克·吐温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幽默却满含着辛酸的泪水,飘荡着冷瑟的心绪;《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则更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时悲时喜、悲喜难辨的幽默,具有深刻的心灵洞察力与强烈的社会讽刺性。只要细细品味一下这些作品,我们就能发现,马克·吐温将一片强烈的爱憎感情溶贯在自己的幽默之中,从而使得他的幽默带有鲜明的抒情色彩。再者,他的幽默作品常常采用第一人称“我”,或者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或者作为某一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叙述者,向读者娓娓讲述那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给人以十分亲切又十分犀利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吐温可以说是一位既具有诗人气质又具有杂文家风采的小说巨匠。
谈到马克·吐温幽默艺术的喜剧成分,我们还有必要审视一下他惯用的一种手法,这就是借助人物的滑稽表演。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马克·吐温不仅喜欢看美国流行的滑稽歌剧,而且喜欢听民间流传的滑稽故事,他甚至认为“谁能讲笑话谁就能得到尊重”。正因如此,马克·吐温在创作小说时常常借助人物的滑稽表演来造成幽默效果。例如,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第二十三章中,马克·吐温描写了“公爵”与“国王”两个江湖骗子丑陋而滑稽的表演,他们为了诈取别人的钱财,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肆无忌惮而又寡廉鲜耻的勾当:这两个无赖搭起一座戏台,说什么要为大家表演“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好戏”。等到戏场里挤满了好奇的看客,“公爵”面对大家一阵神吹之后,突然把幕拉开,于是大家看到,“国王马上就光着身子,四肢着地,神气十足地爬出来了;他浑身都画了一圈一圈的条纹,五颜六色,象天上的彩虹一样”。面对这种情景,看客们“差点儿笑死了”,而“国王”依然在台上左跳右蹦,一直等到跳够了以后,才丑态百出地退到后台。至此,马克·吐温用挖苦的口吻写道:“这个老笨蛋做的那些怪相,可真能叫一条牛看了都要笑起来哪。”作为读者,我们正是透过作家对人物滑稽表演的描绘,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幽默,而在细细思忖之后,我们又体味出,这种幽默的喜剧成分恰恰是和一种悲剧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同时,它又让我们想起这样一句精当的论断:“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就变成滑稽。”〔15〕
当然,马克·吐温幽默艺术的表现手法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但笔者认为这四个方面却是最重要的,它们足以表明,马克·吐温善于把幽默当成诱发自己与读者理智的“酵母”,使自己与读者以清醒而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社会,去剖析人生百态。马克·吐温生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他的优秀作品所呈露的幽默以及由这种幽默牵引出来的理智,使他打破了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新派势力的迷梦,洞察到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和那个“镀金时代”的腐朽本质,也使他对丑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嘲弄与批判。正是他的幽默艺术,滋养了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等美国现代幽默作家的创作。由此可见,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成就是不朽的,其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收稿日期:1994年8月27日
注释:
〔1〕〔7〕转引自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上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43、146页。笔者对原有的译文进行了必要的校正,仅供读者参考。
〔2〕See 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Book Ⅱ,Washington,1971,P·55·.
〔3〕参见珍·斯坦的采访,《巴黎评论》( Paris Review),1956年春天第1期,第46页。
〔4〕See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ume Ⅱ, Mcamillan.1980,P.332.
〔5〕See Martins Day:A Hand book of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St.Lucia.Queensland.1975.P.162.
〔6〕See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s. Volume Ⅲ,Harcourt,1930,P.86.
〔8〕〔12〕[美]马克·吐温《怎样讲故事》, 见孙法理译《美国散文选》,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9〕〔10〕参见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9页。
〔11〕转引自《马克·吐温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页。
〔13〕转引自刘文哲、张明林译《苦行记》前言,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刘文哲、张明林译《苦行记》,版本同注释〔13〕。
〔15〕参见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