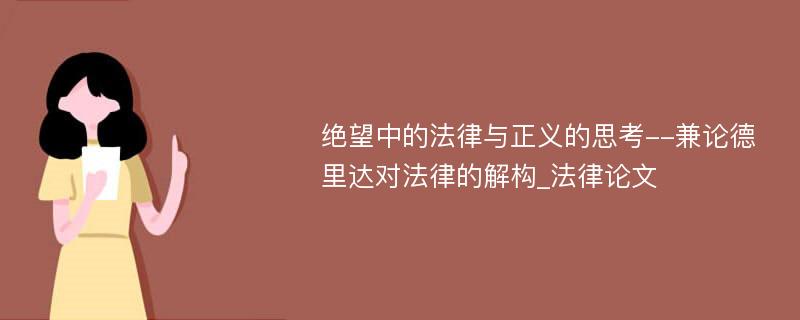
在绝境中思考法律与正义——论德里达关于法律的解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绝境论文,正义论文,思想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文学与法的关系作了多次探讨,这些探讨如此诡异奥妙,引起了不同领域的人们的浓厚兴趣。德里达本人肯定也因此受到鼓舞,他更加深入地进行到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领域。事实上,在这些领域边界的拓展中,德里达始终保存着他早年就在关心的主题、他的一贯思考的核心——那就是力量与暴力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深沉地隐蔽在语言学的内部,为其他更具符号学特征的术语所覆盖,而并不显山露水。只要看看他早期的那些论文。例如,最早对罗塞特的结构主义诗学进行解构的论文《力量与意谓》(Force and Signification),对列维纳斯读解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Violence and Metaphysics),以及《签名、事件和语境》(Signature,Event,Context)①等,都涉及到力量、暴力与法律等主题。显然,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谈论的主题经常围绕力量与暴力、力量与法律、暴力与权威以及由此所显现出的“绝境”主题展开。他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性,也更具有政治性,他试图重新思考力量、暴力与语言、法律以及理论的政治性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联系的内在关节点依然是通过语言修辞来表现的,但其修辞性激发出不再是符号学(或文字学)层面上的哲学玄思,而是理论的政治性和现实社会及其经验层面上的哲学反思。即使在这一时期,德里达对他的理论可能包含的政治意图也依然相当矛盾。正如南希·弗朗塞在《法国的德里达:政治化的解构或解构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德里达避免任何直接的沉迷于政治问题,并且在他的著作中抵制明晰的、直接的政治化。然而另一方面,他几乎是与此同时声称他的实践是政治的,而且哲学行为在总体上是一种政治实践。”②这种状况已经成为现代一种无可摆脱的真实性,政治成为任何实践的一种视野,任何行为都有必要铭刻在政治的主导性之内,预示着政治体制和由此产生政治的效果。但政治无处不在的“自明性”(self-evidence)也使它很难给政治以确切的意义。而这一点,或许也是德里达难以避免的,一方面,他既不愿意直接处理那些政治主题,始终要把他的处理保持在哲学层面上,并且依然是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来展开;另一方面,他又总是触及到当今社会现实的政治性,试图去解开那些隐含在当今政治困境中的深层问题,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的那篇影响卓著的论文《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The Force of Law:The“Mv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篇论文的读解,来看德里达对法律、宗教和政治主题的处理,由此再引向德里达后期更具广延性的“绝境”主题。
一、法律、正义与语言暴力
德里达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内容涉及法律、正义、暴力、权威及其神秘性等诸多方面,德里达要通过他的解构揭示出这些关系项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被收录在《宗教的行动》(Acts of Religion)③[1]一书中的《法律的力量》是最完全的版本,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正义的权力:从法律到正义》出自德里达在卡多佐学院的讲演。德里达1989年10月在美国卡多佐法学院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构与正义的可能性》的讲座;第二部分《本雅明的第一个名字》(First Name of Benjamin)最早是德里达1990年4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的报告,当时论文用的题目是:《纳粹与“最后的决断”:表现的有限性的探寻》,收进《宗教的行动》时做了略微修动。这两部分显然是德里达连续性的思考,从行文来看,前一部分开篇不久就声称要对本雅明的《暴力的批评》进行阐释,但在其具体论述展开中,并未过多深入阐述本雅明的这篇文章。直到第二部分才对本雅明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可能也是因为关于本雅明的话题贯穿始终,所以德里达把两次讲座的内容合成一篇,都列在《法律的力量》名下。正如德里达其他文章经常表现的那样,他谈的是本雅明,但说的是自己海阔天空式的想法。实际上,这两篇东西既可合在一起来看,也可分开来讨论。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宗教行动》中的《法律的力量》的第一部分《对正义的权力:从法律到正义》。德里达开篇半开玩笑一样谈起了语言问题,他“不得不说英语,不得不用一种语言来说……”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正义的感觉”。德里达在此对语言与正义的关系进行了调侃,而这一点,正是后现代法学赖以存在的前提④。正是因为对法律语言的解构,现代法学所赖以存在的统一的、普遍的、规定性的法律本质观也就难以成立,法律的主体观念随之被文本的游戏所瓦解,现代实证法学的本质观被一种多样性的、差异的、描述性的体系所替换。因此德里达强调说,语言和惯用法构成他讨论问题的关键。
德里达在卡多佐学院参与的研讨会的主题是:“解构与正义的可能性”。德里达关注的是法律与正义解构的可能性,这里的思路贯穿了德里达一贯的作风,那就是不断地在修辞之间寻求差异,寻求颠倒的连接方式,寻求补充替换的痕迹。在德里达看来,应该避免把问题本质主义化,一切都要在差异的系统中探讨,要注意到差异的强力与作为强力的差异。在最具强力特征的事物与最弱的事物之间,有时会有一种连接方式,如力量与形式、力量与意谓。形式、意谓都是阴性的,都是弱的东西,它们经常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但力量会转化为形式或意谓。德里达在最早写下的关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力量与意谓》里就谈论过这一点。很显然,解构的巧妙处也在于它要借助于差异之间的转化来展开解构的运作。对于权威的基础问题,德里达也同样强调,它既不是一个基础主义者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反基础主义者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礼节性的说法,德里达在卡多佐学院讲道:比起理论系和建筑系,法律系更是“解构的家”;比起文学、哲学、建筑学来说,法律更具有解构性[2]236。德里达此种说法像是面对卡多佐的法律学家们行一个脱帽礼。德里达此前在多篇文章中已经把法律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来展开解构,现在他直接面对法律,在法律的大本营——法学院,德里达设想建立一种“批评的法律研究”,由此可以呈现一种解构的风格;另一方面,可以连接或结合文学批评、哲学,这就是形成一种法律文学性的反思和批评的法律研究。话说到这一步,德里达像是要倡导一门解构主义法学并使之横空出世。
德里达的分析从康德所说的“法的可强制性”开始。法的可强制执行表明没有强力就没有法,这并不是作为法的补充或第二本质,而根本上就是法的本质。强力就作为本质性包含在作为法律的正义中。按照康德在《权利科学导言》中的观点,权利建立在每个人意识到的对法律承担的义务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都要适应普遍的法。康德当然是从人类的理性原则来谈人对法的服从,对于康德来说,这是道德的内在律令,是人的自觉⑤。德里达从中看到的是法的强制性,不管如何,人们要适应普遍的法这是事实,法就带有强制性。没有强制性就没有法,没有法的适应性和强制性就没有法。德里达追问道:如何去辨别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⑥?如何辨别强力的合法性和暴力的非正义性?到底什么是强力?什么是非暴力的强力?
当然,这里还牵涉到语言问题,德里达一直在几种语言的翻译问题上存在困惑。在本雅明的“暴力的分析”中,“暴力”一词的德语原文是“Gewalt”,意思是强力、威力、不可抗拒之力、暴力等,暴力只是其中之一。但本雅明的“Gewalt”译成法文和英文都是violence,原文的“Gewalt”所包含的暴力程度没有英文的“violence”强,德语中的“Gewalt”经常还指精神性方面。德里达对法律的强力以及暴力的读解是从本雅明那里引申出来的,所以,他在卡多佐学院所做的报告是用英语,这使他不断地要面对语言问题和惯用法的问题。在本雅明的意义上所谈论的德语的“法律的Gewalt(暴力)”,与英文理解的“violence(暴力)”并不能完全等同。同样,用汉语来讨论“法律的暴力”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但汉语的暴力概念是英语的violence的直译,应该是最接近的了。德里达这里谈到语言翻译问题,实际上暗含着“语言本身就是暴力”之意,这与他后面要谈论的法律总是写下的文字,法律条文总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有关,这本身就包含着“暴力”在里面。德里达的谈论看似东拉西扯,其实都暗含着机锋。
因此,德里达把“法的可强制性”看成是一项语言的行为。法律的正义性要从它说出的第一个词开始。德里达说道:“‘强制实施法’总是提醒我们,除了诉诸强力或从它的第一时刻或从它的第一个词语请求强力,正义就不是必要的法,或者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正义。正义在其开始就已经有逻各斯,说话或语言,但这不是必要的与其他的‘开始’相矛盾,这将是说,‘在那个开始已经有了强力’。对此我们必须去思考,因此,这是强力在语言自身中的实践,在它本质的最亲密中的实践,这就是它凭借的独特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强力从自身中解除自己。”[1]238正义总是寻求法律的支持,这就是在它开始实施的时刻就要有一种语言被说出,就有某种确定的条文或理念先在地起作用。正义寻求法律也就是寻求力量,要实行正义,要获得正义,都要有法律作为依据,都要有力量来实施。
在帕斯卡看来,正义就是有力量,就是说正义必须被追随,必须追随最强者。被结果跟随,被影响跟随,这就是期待“迫使”(enforced)。这里表达的公理是,正义就是最强者,最具有正义性的是最强者,正义必须被追随[1]238。在这里,德里达显然不是从正义所具有的历史、社会、政治、法律、宗教信仰以及道德伦理来评判正义,而只是从抽象的结构关系和形式来评判。正义因为其正义所以被人们追随,它代表着历史前进性,代表着最普遍的意志。但是反过来,因为它有力量,所以它能代表历史的前进性,它会得到民众最普遍的拥护。德里达去除掉正义的实质内涵,而是从力量的抽象关系意义上来看待它所具有的普遍效力,即自我在场的逻各斯。按照帕斯卡的观点,没有强力的正义就是没有权力,如果它不能实施“迫使”,它就不会有成就,正义也就不是正义。强力没有正义就是残暴,正义没有强力就会遭到否定,没有正义的强力就会被谴责。因此,有必要合并正义与强力。这就是正义的强力、强力的正义之意义所在。当然,这也是很难令人做出决定的事,到底在何种情势中正义要放置在强力里,在何种情势下强力要具有正义,只有依靠正义的要求来决定。说到底,还是正义本身包含着强力的要求。
二、法律的神秘基础与可解构性
德里达擅长旁征博引,他认为帕斯卡的这些观点是来自对蒙田的阅读,尽管帕斯卡没有提到蒙田的名字。德里达的解构,或者说他的理论的提炼和归纳,都来自对不同文本的阅读,恰恰是通过对那些经典文本的重读,把它们纳入到他的解构体系中,才使西方哲学史中的那些思想形成一种传统之链,而传统之链也是解构之链。从本雅明到康德,再到帕斯卡,再到蒙田,这个历史谱系被连接起来,对于德里达来说,他也有一种固定历史的形式,很显然,他只抽取这些思想家的某方面的论点,在他所理解的那个点和层面上来建构起历史图谋。有了蒙田作后盾,德里达的论说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蒙田辨析了来自正义的法律——法律的正义也就意味着:作为法律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法律之作为法律就不是公正的,而是因为它具有权威性。人们要信任它,仰仗它的权威。德里达由此触及到“神秘的基础”问题,这一神秘的基础就在于法律具有虚构性。蒙田说过,没有虚构就没有法律⑦,正义的真实就建立在法律的虚构性基础上,这就是“神秘的基础”的实质。虚构性隐含着巨大秘密,谁有权力虚构?为什么要虚构?为什么要这样虚构而不是那样虚构?当然,我们要理解法律的合法性虚构,而不是简单地去质疑法律的虚构性,指出其虚妄,那样并不能真正揭示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的神秘基础。什么是法律虚构的合法性?什么又是正义的真实?这种合法性不是源自外部,在蒙田看来,是因为法律自身在自然法和历史形成两方面都不完备,它有必要寻求虚构的补充。虚构既是权威性的补充,也是力量的补充,补充之后的法律(虚构之后的法律)就具有权威性和力量。
神秘的基础的实质就在于:法的基础就建立在自身根基上。德里达认为,不能把法或正义简单地解释为是从外部为社会力量或权力服务,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力量外在或先于它存在,不能简单地解释法律依赖这些力量存在,在动用法律或正义时这些力量从外部发挥着作用。德里达强调要从法的内在性去理解它的神秘基础。它们是它们自己的一种没有其他根基的暴力,根基就在它自身,法不能放置在任何其他位置,就是在它们自己的基础上的暴力。它们超出有基础或没有基础的对立。德里达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强调从自身去寻找,解构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其内部,其自身形成的内在性去思考。解构的思维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性的思维(也就是对内在绝境的思考)。要从内部找根源,找出那个错位或虚构的根源,这就是解构的要害之处。所有的外部都事先在内部的形成中存在,德里达在揭示逻各斯的本体论时,它是否也把内在起源性先验化了?这会使人想起他早几年对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的解读,胡塞尔一直在思考一种先验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思考的是存在,德里达则把这种先验的和本体论的存在转化到事物被可认知/不可认知的内部,那是事物自我起源和本质构成的基础,德里达现在要解构的就是这种被确认为基础的东西(它就是一种难题或绝境),当然,德里达换了一个说法,那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形成的根基。法律的暴力性就是在它自身,就在其内部——解构就是这样发生的。
德里达的意思是说,权威在其起源的意义上,除了它们自己外,不能被定义搁置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在它们建构的时刻,它们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一定要把它们理解为是超出创建和不被创建的对立,或者任何基础或反基础的对立。德里达不主张在简单的二元对立意义上去阐释权威创建的基础,因为这样的基础包括了太多的不可能的事物。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德里达做出论断说:法律本质上是可解构的(deconstructible)。德里达写道:“法律是可解构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什么坏消息。人们可以在所有的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机遇中发现这一点,但是,我要提出讨论的悖论在这里:这是法律的可解构的结构,或者,如果你喜欢,作为法律的正义也是可解构的,它也确保解构的可能性。如果外在或者超出法律这样一个事情存在,正义在它自身中就不是可解构的。只是解构自身如果存在。解构就是正义。这也许因为法律是可解构的(为此我将持续试图去辨析正义与法律的区别)。在某种超出惯例和自然对立的意义上,它能超出它被建构的对立——可解构性使得解构成为可能,或者,至少使得解构的实践得以进行,总是有根据地继续到法律的问题以及法律的正义性问题。”[1]243
德里达由此列出三个主张:其一,法律的解构使得解构变为可能。其二,正义的不可解构性总是使得解构可能,确实是使解构与正义不可分离。其三,结果是,解构发生在从法律的解构中分离正义的不可解构性的间隔,因而解构作为一种不可能的经验就是可能的。即使它不存在,如果它不在场,还未或从不发生,也依然有正义在那里……这可能是德里达关于法律与正义的解构性的最经典表述了。德里达的三项主张如同三道公理,这里面的概念和关系似乎是绕来绕去兜圈子。这里面包含着法律的可解构性与正义的不可解构性之间的关系,有两点需要加以解释:其一,为什么说法律的解构使得解构变得可能?按照常理,法律是最严密、最公正的文本,也是社会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但法律一旦用语言表达出来,它里面就包含着强力因素(关于何以包含强力,以何种方式包含强力,前面已经阐述过了,这里就不再说明)。这一强力本身带有暴力因素,那是它的语言具有暴力,形成中带有暴力因素,它的强制执行带有暴力特征。法律因为代表着正义,因而它具有规范训导惩罚社会的效力,社会依赖法制才得以正常运转。如果法律内在是解构的,那么,解构就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解构就可能存在任何地方,可能发生于任何地方,其他的解构不过更简单明显而已。其二,为什么说正义的不可解构性使得解构总是可能?正义不可解构,因为正义是一种不可能的经验,但解构作为一种不可能的经验却是可能的,解构就是要去经历不可能的经验。正义作为一种不可能的经验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正义,正义永远不会实现;但解构是对所有不可能性的读解,解构就是指出所有的不可能性,穿过所有的非正义的场域,经历正义的不可能。但解构无法指出正义的不可能性,解构不指出正义的不可能性,解构知道正义的不可能性,所以解构就是可能的。这是德里达为自己、为解构设置的一条底线,正义的底线——正义不可能性的底线,这就最大可能迫近正义。恰恰是正义的不可能性,正义不可能解构,使得解构得以进行,使得解构不是盲目的和目空一切的。因为解构知道正义的底线,知道正义的界限,知道正义不可能性,解构就是冲着正义去的。法律的解构是与正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律是借了正义之名,因为正义的可解构性,法律的解构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德里达这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不是互为基础的那种关系(那就外在了),法律与正义是在内部发生关系,其解构当然是互为牵连,可以互证的。
为什么会有解构与正义的可能性这样的命题?从解构的角度看,正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正义寻求普遍性,正义具有最大可能的普遍有效性;但解构主义反对普遍性,不可能存在普遍正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或者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人类社会被划分为民族国家、阶级性别,在人类社会就不会形成普遍正义。如果没有普遍性,正义就不是真正的正义,正义就不存在。然而,难道说人类社会没有正义的观念?没有正义的标准和尺度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把“正义”视为维护社会制度稳定的根本价值,它有赖于全社会的所有人能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维护共同的利益。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开宗明义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3]3在把正义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和根本的价值这点上,德里达与罗尔斯有相同之处⑧,不同的是,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可以理解和认识的,可以有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可以通过一套制度建设来抵达和保护正义。但到底什么是“正义”,即使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众说纷纭。对于罗尔斯来说,正义观念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公平(《正义论》的第一编“理论”,第一章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这就是社会成员可以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制度。罗尔斯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也是确立在普遍公平的基础上:“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3]61
罗尔斯不是在阐释历史,而是在给人类社会设计正义的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自有它具体的理论阐释和论证,这里不加赘述。我们只是简要指出这种设计无疑是普遍主义的,对于罗尔斯来说,普遍正义是可以得到社会成员共同认知的价值。但对于德里达来说,可以共同认识只能是一句空话,说得好听点只是一种想当然的理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尽管罗尔斯的公平观念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但何谓“合理”依然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而且这种满足手段要通过制度建构,这又必然要通过法制的建构来实施和完成。如此看来,正义不是不存在,而是它无法现身,无法以一种社会共同认知的普遍形式现身。
从解构的观点来看,这种普遍性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则如何要设计呢?如何有意义呢?人们都在以正义之名做着各种事,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些事的含义和结果是根本不同的,不会有一个人类共同体来确认一项行动或某个事件是正义的,但它们确实都可能是在正义的名下进行和完成的。德里达的朋友和学生南希对共同体说过这样的话:“‘共—在’在差异中而没有同一性,同一性的‘共在’在关系的腹地中区分着,它是自身区分的,因此也是为了他者和为了自身的。一个共通体(共同体)的同一性因此也无限区分着自身。”[4]当然,共同体内在的差异无疑是根本性的,个人、种族、地区、传统、语言等等的差异性,使之共通/共同变得有限。但人类社会结合成这样一些阶层、社团、民族、国家,这些共同体还是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层面上对某些利益和价值达成共识。如没有这样的共识,人类不可能结合成社会,也不可能朝向未来发展。不管是德里达还是南希,都是在终极和根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共通/共同体的不可通约性。
德里达显然也相信正义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性,但他几乎没有论证地断言,“正义是一种不可能性的经验”,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人们没有经历过正义,真正的正义是不可能的,正义只是一种愿望,一种呼唤,一种理念,一种理想性。它本质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不可能的经验,就没有正义。这句话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如果没有对正义的理想性期待,就不会有对正义的无限切近,正义就不会最终降临——这是在时间上说的;其二,如果没有经历这种不可能性的经验,也就是不断付诸实践的经验去经历正义不可能的过程,就不会最大可能地接近正义——这是在空间上说的。
正因为此,德里达明确地断言,法律不是正义。因为法律是可能的经验,是现实化的经验,是可重复实施的经验。德里达的另一种说法是,法律是可算计(calculation)的,而正义是不可算计的(incalculable)。算计这个概念是德里达经常使用的概念,它与“经济学”等概念一样,既具有字面的意义,也有它给予的特殊的哲学含义。“算计”即是说法律是可以按照现实的经验理解和运用,它可以通过制定可把握的、可实施的规则来执行,并且可以形成可见或可预见的结果或成效。例如,根据法律的条文,控方与辩方都有依据可循,法官也可根据法规做出明确判决,刑期都是可计算的,这些结果都可理解,可以预见或可以有明确的结论。但正义却不行,正义不可计算,不可比拟,也不会有明确的可确认的成效。
三、解构作为责任的双重运动
德里达关注主体的区分问题,公正与不公正也是被各种措施体制化的,解构这些区分,人的这一主体地位,例如,男人、女人、儿童、动物等等,德里达显然也看到在法与公正的实践中,并没有抽象的人类主体,公正承担主体本身就是被区分的。德里达指出,在关于正义的伦理—政治—司法以及公正与非公正的对立之前,解构并不让位于对虚无主义的响应。这也就是说,解构是要深入到这些实质问题的深处,才将其内在的对立揭示出来。德里达展开的解构更倾向于一种关于“责任”的双重运动,这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
其一,历史的和解释的记忆的任务置放在解构的中心。这并不只是哲学和词源学的或历史的任务,但是面对遗产的责任,也是对一系列的律令的解释遗产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解构已经抵押给对无限正义的要求。德里达这里特别提到“记忆”的问题,解构的责任是与记忆相关的,记忆也就是文化的历史遗产。责任总是有限定的,没有限定的责任在记忆之前就被历史文化的沉积物所渗透。语言与习惯用法对正义的限定,使得对正义阐述总是要转向他者的独特性,尽管它经常假装具有普遍性。说到底,“记忆”也就是语言、习惯用法、限定性等等,对记忆的解释的责任,就是去除那些限定。解构当然不可能还原什么本真性的正义观念,但解构具有责任去除那些在继承正义的决断之前的教条。
其二,解构呼唤对责任的提升。德里达认为,记忆之前的责任是一种调节正义和我们的行为、理论、实践、伦理政治决定的适当性的责任。责任的概念是与所有其他概念不可分的,诸如正当性、所有权、意向性、意愿、自由、意识、自我意识、主体、自我、个人、集体、决断和真实,等等。把解构与责任明确地联系在一起来考虑,这在德里达是一个重要的决断。解构总是被理解为拆除一切秩序和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力量,至少不负责任是解构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德里达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解释解构并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怀疑主义,解构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但在当时这种解释还是太空洞,现在,正是解构“法律”这个最有社会责任的事物时,解构显示出它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责任所在。解构要承担的责任是一种极其复杂、细致和深入的过程:那就是把迄今为止被各种虚假的概念和信念掩蔽的东西揭示出来,让人们看到事物的真相,看到事物更为本源的运作方式,看到事物的界限和不可能性。解构要追踪的就是事物真实性从而也是正义抵达的底线。按照德里达的设想,公理的信任和可信性要被解构悬疑,在这样的结构性的必要时刻,人们总是相信没有更多的空间留给正义。既不是为正义自身,也不是为向着正义的理论利益,没有这个悬疑的时刻就没有可能解构。这是一个单纯的时刻,如果这样的责任从来没有在教条的束缚中放弃它自己,它的可能性就会保留在所有责任实践的结构性呈现中,从而否定自己。从此,这样的时刻就颠覆了它自身,它变得更加苦恼。这样的悬疑的苦恼时刻总是开启了包含着转型的空间间隔,甚至司法政治的革命由此发生。正是解构把那些不可能揭示之后,留下正义可能抵达的空间。德里达特别指出,这种状况是不能被激发的,它不能发现它的时刻和它的冲动,除非是在正义的提升和补充的要求中。这也就是说,在对正义的要求处于并不充分的状况中时,不可算计的那种不对称性引发解构。德里达特别爱用“不可算计”(uncalculate),这个词也可以简要解释为“意外”,解构就是意外事件,所有的事情都规划算计得好好的,但解构的意外发生了。这就像中国话所说的那样: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就是解构的意外。这种意外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因为所有的可算计都包含着不可算计。法律给出的正义总是不充分的,法律的算计总是包含着不可算计。解构的责任提升就是始终处于这种不满足的呼吁中,就是要超出以一种名义给定的决定,解构的责任也体现于在那些被决定的语境中它有能力去发现它的力量,发现正义和正义的可能性[1]248-249。
德里达如此阐述解构的立场,解构与责任、正义的关系,这会让所有自认为对解构主义了然于心的人大感意外。尽管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里达的思想立场有更明显的转向,那就是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是180度的转弯,而是他早期思想的合理延伸,也就是德里达声称的解构始终具有的态度和立场。按照德里达自己的解释,解构一般以两种方式、两种风格发生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会相互嫁接,但两者还是有着明显的侧重点:一种方式是以论证和明确地非历史的、以逻辑形式悖论展开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更多地具有历史意味和记忆价值,显然是借助于文本阅读、严格解释和谱系探源而进行。后者无疑更接近现实化,与社会历史的政治实践更容易结合在一起。但德里达运作的解构总是这两者交错进行,所以,也使他的解构的现实指向性无论如何都还是包含着逻辑形式的那些层面。他更愿透过逻辑悖论的形式来看待社会历史实践。
后期的德里达越来越显示出他与列维纳斯的思想的内在联系,显然也意味着德里达更深地回到犹太教或希伯来文化的传统中。德里达从未在解构运作中明确地援引犹太典籍,他总是通过列维纳斯来进入犹太思想。这也说明他对犹太思想的当代化还是保持着一种警惕,他需要的是经过哲学转化的犹太思想。德里达在关于正义与法律的分离关系的看法,得益于列维纳斯关于他者的思想。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在《整体与无限》中表达的正义观:“……与他人的关系即正义”相当赞同。实际上,在德里达关于正义的思想中,正义始终是一个“他者”,这个他者是不可能被主体化、中心化的他者。它是无限的、不可算计的、反抗规则和外在于对称性的、异源异质和面向异地的。法律永远无法使正义转化到自身,相对法律的可算计、可被规则确认而言,正义就是它的他者。德里达谈到列维纳斯所说的“犹太人道主义”,其基础不是“人”,而是“他人”。这有什么区别呢?人总是普遍性的,主体化的,是可以自我确立的、最终具有强力的存在。而他人却是永远是个体,永远是一种有面容的存在,它是不能被那些普遍性的可算计的规范所同化的。
解构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是发现他者(他者的延异和踪迹),而解构与正义之所以可以被结合在一起,也是因为他者是其共同的基础。从逻辑的层面上来看,他者的踪迹即是解构的踪迹,解构就是那些被强制性地算计在一起的同一性的破解,那是不能“和而共同”的普遍性、规范、标准、同质化、进向,等等;从伦理的层面上看,正义永远是对他者面容的尊崇,要保持他者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让他者以存在者对存在的自我领会去存在⑨。就正义的本质而言,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就是把他人当作一个他者来对待。正是在这一点,法律无法做到。法律不可能保证一个他者的存在,法律就是用条文,用它的可算计性来对任何一个他者进行审判和判决,它并不管作为个人的他者存在有什么差异。他依据的是法律条文,它把他者的他者性抹去,让他者成为法律责任的一个承担者。并且,这样的法律适用所有的人,法律诉诸的平等是人人平等,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只有这样,才有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才有正义。
德里达从列维纳斯的“他人的权利”出发去理解法律面向正义的绝境。他人的权利也是“无限的权利”。“他者”是不能被自我规范的,不能被中心化算计的。他者的权利、无限的权力,从而也是他者的无限性——这其实就是德里达解构的根本要义。这样一个“他者的无限性”总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法律在普遍意义上的可算计性无疑时时刻刻与他者的无限权利相抵牾。在德里达看来,法律之所以可以普遍意义来实施它的算计,就在于以正义之名。而正义就此成为法律的本质,法律以正义之名行事;法律也就成为正义的现实化或在场,又正因为此,正义以强制性的形式实施和自我确立。解构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并找到它的自我[1]251。
四、解构的绝境与不可决断性
由此,德里达去思考三个绝境(aporia)。“绝境”的含义在于,法律在其实施中不可能达到正义,因为法律的实施总是要处于破坏其面向正义的可能。
绝境之一:规则的悬置。这就是说法律的决断总是要依凭规则,第一次规则的做出其实就是一次创造,以后就要依凭它。但每一次决断都不可能完全依凭这个规则,都要有所创造,而有所创造就是越出规则,每次都要赋予这种创造活动以正当性。本来法律的实施必须“有法可依”才是正当的,但真正的决断却依靠法官每一次有新的创造,这是对规则的毁坏,规则无法被原封不动地依凭和执行。法律的实施其实是规则的悬置。也就是说,以规则之名,也是以正义之名作出决断总是要超出规则。因此,德里达说,“绝对没有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此刻,我们能说一个决断是正义的。”[1]252
绝境之二:不可决断的幽灵。德里达认为,任何一个堪称正义的决断必须经受不确定性的历险。任何决断总是不完备,总是对一个特异性事物的决断。所以说到底,德里达这里还是以他者的“无限权利”来衡量决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法律的实施也就是正义的到来,无限的“正义观念”降临到眼前的事物,降临到某个事物之前,他必然对某个事物来说是不可承受的,因为正义被有限化,被现实化,他就是对正义的亏欠。在德里达看来,无限的“正义观念”是不可还原的,这就是说,正义是不可在某个时刻降临到某个事物身上,正义太大了,某个事物太小了。这并不在于某个个别事物是否有权利承受正义。德里达这里并不是轻视个别事物,相反,他是尊崇他者的无限权利,他者并不需要,也不应该在某个时刻以如此方式承载正义。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论德里达的意思:此一事物对正义的承载,也不可避免使另一个不在场的他者承载着不正义。而“他者”是不能被算计的,也不能被不正义算计。既然他者不能被算计,也不能被决断,那就是说,那些有罪或赦免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他者”,都被以正义之名决断,这样的“他者”在此一事件中,此一决断中,并不能承载正义,体现正义。例如,我们通常的说法,“伸张正义”,但那可能是使另一他者“蒙受”不正义之名。他者的无限权利是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剥夺的。如此情况也很复杂,德里达所论似乎在历史情境中可找一些事件和事例。例如,中国的土地革命镇压地主阶级,三反五反肃清反革命等运动,都是以革命的正义之名,农民阶级承载了正义,伸张了正义,他们获得了土地或地主阶级的财产;作为农民阶级的他者的地主阶级承载不正义,被以正义之名镇压,他们作为他者的“无限权利”在革命洪流中被洗劫一空。但革命自有革命的逻辑,革命叙事就把阶级压迫宣布为非正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之名就建立在革命的合法性和正义的名下。
不可决断性的实质就是他者的无限权利,就是正义是不可决断的。一切以正义之名作出的决断就不可能是正义的。德里达在这个意义上说出了一段极有震撼性的话:“对一种绝对在场的正义的确实性的所有前提的解构,本身就以一种无限的‘正义观念’为基础展开。这种观念之所以是无限的,是因为它不可还原;之所以不可还原,是因为它对他人有所亏欠;之所以在一切契约之前就对他人有所亏欠,是因为它已经到来,而他人的到来却是作为永远是他人的特异个体。对于怀疑论者立于不败之地的就在于,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正义观念’显然是不可毁坏的,这是因为它的肯定性品格,它对礼物的要求;这种礼物没有交易,没有疏漏,没有承认或报偿,没有经济的循环,没有算计和规则,没有理由,没有理性。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正义观念中辨别、确实是指控和辩解一种疯狂。也许,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神秘。对于这种正义,解构是疯狂的。对于这种正义渴望是疯狂的。在解构自我呈现为被学术界与现代文化界贴上‘解构论’标签之前,这种并非法律的正义就是解构运动,在法律中,在法律历史中,在政治历史中,在历史本身中发生了作用。”⑩[1]254
解构是以无限的“正义观念”为基础来展开,这一意思即是说,解构在面向正义时,并不考虑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正义是不可限定,可限定就不是正义,正义总是且永远是无限的。德里达这里谈到“无限的”也就是“不可还原的”(irreducible),这里的“还原”当然还有胡塞尔的“还原”之意,在这里意即不能回到事物本身,不能回到现实化和实体化,或者在这里的语境中,它不能被实施,不能作为法律或通过法律来实施。只要是作为正义到来的事件,这个正义就是对他人有所亏欠,你必然损害了另一个他者的权利,他者的无限权利。如此说来,德里达似乎否认正义的现实存在。就这一点而言,确乎如此。但这不等于德里达不追求、不肯定、不强调正义存在的意义。恰恰是把正义作为一种更高的存在,正如海德格尔对待人道主义的态度一样,海德格尔也认为正是把人道主义看成一种更高的存在,所以他不同意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说法(11)。德里达显然也不愿意把正义庸俗化,把正义看成是各种措施和法则的实施,他要守护的是正义的那种纯粹性,是正义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能的正义。一句话,或者是一种极端理想性的正义观念——一种弥赛亚意义上的正义。这倒很奇怪,解构主义的德里达何以要维护这样的正义观念?这样的正义观念有什么意义呢?
正如正义是法律的正义一样,正义也是强者的正义,是多数人的正义。德里达的正义则是守护他者也就是“少数人”的正义。正义只有在守护了他者的无限权利时才是正义,正义只有为他人时才是正义。但这是所有正义在其现实化时都不能实现的。正义在其每一次的此刻到来时,它总是会有一个差异的他者产生。正义到来了此一他者,必然要亏欠另一他者。而正义临幸的此一他者也就被主体化和中心化了,另一他者则必然要被剥夺。正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际法的遵循经常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途径,现今的政治家都爱说“双赢”,这是典型的自我与他者调和的观念,双赢似乎使双方都处于一种主体位置,在这里消除了他者的差异。但双赢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那些以正义之名为民族国家利益的奋战中,这种双赢经常也只能是自欺欺人。能获得双赢的只是政治家们,而受损的人民则不能幸免。在这些正义之名展开的实践中,总是有他者的无限权利被剥夺。“9·11”如此,反恐怖战争也是如此,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更是如此。或许人民,那些少数人,总是永远的他者,正义之名总是以对他们的亏欠的形式到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德里达才如此决然地对正义怀抱着如此偏执的信念。因此德里达会说:对于这种正义,解构是疯狂的;对于这种正义的渴望是疯狂的。这种并非法律的正义就是解构。也就是说这种不能被实施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然而,真正的正义是解构的,它是不可决断的,它不能到来,也不能被现实化。
绝境之三:阻隔认识地平线的紧急状态。所谓“认识的地平线”即是康德式的调节观念和弥赛亚观念,也可具体理解为指对正义的认识要在一个广阔的认识维度、知识平台上或历史反思视阈里展开。正义是到来的,是弥赛亚式的福音,它是人们在期盼中的到来,而不是人为的决断。在最低限度上,对正义的认识和决断总是要汇集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才可能做出合乎正义的决断。但正义的决断总是处于一种紧急或危险状况中,它并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不迫地做出审思和对全盘的把握。决断的瞬间是疯狂,所以德里达说“对于撕裂时间和违抗辩证法的正义决断尤其如此”[1]255。决断的紧急状况决定了正义不可能周全,它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它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的匆忙判断。也就是说,正义的决断总是一种匆忙的中断。它不是弥赛亚式的到来(降临),但也正因为此,正义被延搁了,正义的到来只是在未来。德里达写道:“正义可能有一个‘未来’(to-coming)。我严格地与‘将来’(future)区别的未来。那个‘将来’失去它的开放性,没有他者的到来的就没有正义,那个将来总是能再生产现在,宣告它自身或在场的自身在现在的改进形式中现身为将来。但正义依然保持将来,它本身就是将来,它必定将来,它就是将来。它以一个事件的非常维度不可还原地到来……‘也许’,对于正义我们必须永远说‘也许’。如果不是某些事件有可能,而作为事件超越了算计,规则,计划,期盼等等,正义作为绝对相异性经验就不可能呈现,但它却是事件的机遇和历史的条件。”[1]256显然,在正义的现实性这一意义上,德里达并未完全否定其必要性。德里达要思考的是正义在那些匆忙的决断中它是不周全的,但这些决断是正义尚未到来的时刻,是等待正义到来的时刻。因为这个决断,正义终将要到来。但正义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就降临在那些早已做出的决断上,德里达反对将来就是现在复制的未来,相反,德里达认为,正义的即将到来会使我们在随后的时间里对过去的决断做出重新估价。“政治化的每一步发展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再度解释先前已被算计被界定的法律基础”[1]257。这也就是说,那些决断总是迫使我们要将来更接近正义的情境中重新做出思考和回应,这就是正义必定到来之意。如此之正义,就像神意一样,它终将会使人类的事件更加接近正义。这又表达德里达对正义的态度如同一种信念,一种无限将来的正义终究会引领人类前行。但是这个正义似乎是太神秘了,它即不可显现,也不可算计,它只是“将来”,只是“也许”。但人类追求的那些信念:无限权利、自由、民主、公正、正义……事实上也是现实的,也必然是一种将来的信念。
德里达把解构引入法律和正义的领域,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我们先前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些概念、观念和准则,都受到全面的挑战。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是教会我们去颠覆和推翻业已构建着我们文明的那些秩序、制度和规范,而是让我们去思考它们内在的那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去思考人类要建构起一个共同体,人类要追求那些绝对价值的内在不可能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思考,我们才能看清人类更深刻和内在的困境。我们才不会那么盲目地、自以为是地算计人类一个个进步的程序,满足于一个个决断的“英明”或问题的“妥善解决”。很显然,德里达也因为关注了法律和正义这些更具有社会现实性的主题,他的后期思想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力量。这些主题都构成了后现代时代的法学、政治伦理学的崭新的出发点。在其本质意义上,德里达似乎并不相信我们人类已经建立起的这些思想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在他看来,这些思想的累积和运作,根本上是误入歧途,这样的致思方向当然是不可能解决其内在矛盾。当然,这也不是说人类可能有更好的出发点,德里达也不做如是推断。在他看来,今天我们思想的责任就是要在绝境中思考,在不可能性中思考,在不可能性中思考不可能性,这才是面对绝境的诚实态度。而问题的解决并非我们所能,那就只有等待,面向未来的等待才有“到来”的事件出现,那时可能问题才能解决。这样的态度看上去像是斯多噶主义的翻版,不过,德里达要我们老老实实在绝境中思想则是一种警醒,警醒问题的虚假解决。只要我们意识到身处绝境中,在思考不可能性,那也就是对不可解决的问题的最好解决。
[收稿日期]2007-07-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前两文都收入《写作与差异》一书,《签名、事件和语境》收入《有限公司》(法文版:Limited Inc,Paris:Galilée,1990;英文版:Limited Inc,trans.by Samuel Weber & Jeffrey Mehlman,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
②参见Nancy Fraser,“The French Derrideans:Politicing D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in Working Through Derrida,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ary B.Madis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pp.58-59。实际上,南希·弗朗塞在这里是引述和分析Christopher Finsk在Intervention一文中的观点。该文载Jean-Luc Nance & Philippe Lacoue-Labarthe(eds.),Les fins de L'Homme:A partir du Travail de Jacques Derrida,Paris:Galilee,1981。
③参见Jacques Derrida,Acts of Relig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本文有些引文段落参照《〈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的中文版(胡继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都作特别说明,如未做说明,均指英文版。
④中国学界的后现代法学研究还并不充分,在国际法学界,后现代法律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仅仅初露端倪,是一种思潮,没有变成现实。很显然,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德里达本人对法律的解构,是当代后现代法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德里达解构法学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解构主义法学,则是后现代法学的中坚力量。在欧美学界,宣称自己是研究后现代法学的人并不多见,较为突出的有施拉格(Pierre Schlag)、费尔德曼(Stephen M.Feldman)等人。他们主要被称作批判法学,但也可看作是解构主义法学。波斯纳是经济分析法学和新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也可归属于后现代法学。后现代法学最激进的思想还是解构主义法学,其关注的重点是通过语言修辞的解构来解构法律文本。参见於兴中《法学中的现代与后现代》,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1辑。
⑤此文是康德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也译为《权利的科学》)的第一部分。德里达在注释中引用了康德的话:“毫无疑问,这样的权利是建筑在每个人根据这条普遍法则而来的责任的意识上。但是,如果它确是这样的纯粹,它便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这种意识作为动机,并通过这个动机去决定意志的自由行动。为此目标,这个命题便建立在一种外在强制的可能性原则上,这种强制根据普遍诸法则,可以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并存。”康德又举了债权人责成债务人还债的例子以作说明,因为权利和强制都符合人的内在自由,所以“权利和强制的权限是一回事”。参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43页。德里达则不满足于这种“法的可强制性”与人的自由的结合与协调,他要继续自己的追问。参见Derrida,Acts of Religion,pp.233-234。
⑥Force通常译为力量,德里达的Force of Law也是被译为《法律的力量》。但德里达这里谈论的force还有强制性的意思,不过尚未达到暴力的强度和血腥,它只是以威慑力和强制手段来完成力量。力量总是客观的,而强力则具有主体性,法的力量也具有主体性,它总是与另一对象发生关系,与他者发生关系,它具有一种驯服对象的力量。所以,与violence相对,force译为强力更准确。
⑦蒙田的这句话德里达在多处提到过,例如在《类型的法则》一文中。
⑧罗尔斯依然可以说是康德的后裔,甚至还算是一位康德专家,因此他经常在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论述中大谈康德。罗尔斯要求的正义仍然基于自由与普遍性原则,而德里达恰恰要在已经被真理化的原则之外寻找“正义”。
⑨从这里也可看出,列维纳斯当初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列维纳斯对于海德格尔战后没有道歉始终耿耿于怀,但他的“他者”所具有的那种不可同化的差异性,无疑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者”的差异性的另一种表述。
⑩此段引文参照胡继华译文,并参照英文版有所改动。
(11)关于这一论述可参看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载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8-3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