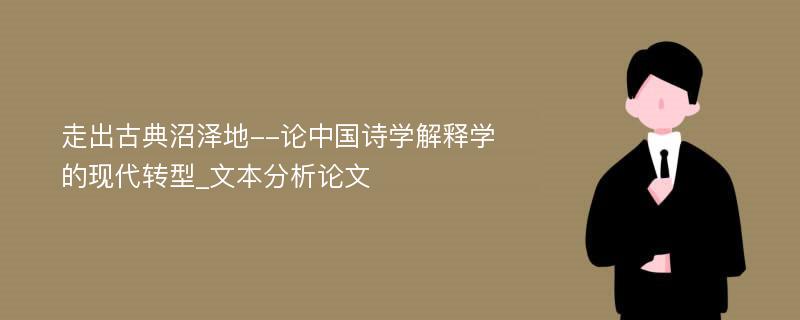
走出古典的泥沼——关于汉语诗学阐释学的现代转化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诗学论文,泥沼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观近20年中西比较诗学的进展,其不遗余力的探讨如果略加概括,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突出的价值目标:一个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重建问题;一个是在中西诗学对话中寻找某些可以相互理解的“话语模式”或称“共同的美学据点”,探讨某些“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 Poetics),确立或突出中国文论传统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价值和地位,一句话,中国诗学的世界意义问题。因此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存在着互相纠缠而又泾渭分明的两条对话的思路:一条是古今对话的思路,一条是中西对话的思路。围绕这两种思路的探讨过程,近年来陆续遇到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难点和困扰,譬如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关于原义的争论、意义的生成和阐释模式、中西诗学对话中的阐释的循环问题以及有关的对话原则和方法学的理论基础等等。这类问题本身并不直接涉及中国诗学的价值判断,而是有关与中国诗学发展相关的阐释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但是如果这一类问题不解决,则中西比较诗学的探索将会处处制肘,难以深入。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汉语诗学的阐释学理论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而在此一方面,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思想和方法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极富创造性的探讨角度和思索的理论基础。
一、怎样看待既有的诗学传统
比较诗学对中国诗学的现代解读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一种是把它视为封闭的、凝固的、不变的东西,在向另一种文化介绍这一传统的时候,不管对方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不管是否适合今日文学的发展需要,不加以任何的现代阐释和话语的转化,不敢动祖宗家法一根毫毛,一味的照抄照搬。只要是翻出几本古代文论的文本,搬弄几个“载道”、“言志”、“羚羊挂角”的术语概念,作几组罗列排比式的对照,来一番你现在才有而我家老祖宗过去就有的阿Q式解释,喊几句中国文化传统渊源久长,博大精深的口号,就以为展示出了一个“原装”的中国诗学的真实形态。这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努力,不仅无助于传统的弘扬和发展,甚至往往歪曲和损害了传统的形象和价值。在现代阐释学的意义上,文本照搬和考古式的对待传统,不仅抹杀了传统构成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传统作为一种从过去延续至今,又必然从现在走向将来的活的存在。就中国诗学传统而言,在数千年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曾经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而就其历史路径而看则体现为在历代的阐释下不断变化、扬弃、丰富发展的过程,以诗学中的言意关系范畴而论,从《易传·系辞》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到《庄子·外物》中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从魏晋“言意之辨”到《文心雕龙》的“文外之重旨”;从司空图的“言外之意”到后世各种与之相关的“神韵”、“性灵”、“境界”诸说,言意关系从解经学的观点逐渐变为诗学的范畴,从执著于言不尽意的困扰到对言外之意的自觉追求,均经历了一个历代不断加以创造性理解与阐释、融合与超越的过程,今天仍在不断发展之中。[①]如果只是执著于某一时空条件下的成说,不经过一番创造性的理解和超越,不仅不会有今日中国诗学关于言意命题的丰富内涵,恐怕这一认识连走出古典经学的圈子也有困难。因为即使是在王弼那里,“言意之辨”也主要只是一个关于《易经》阐释的义理问题。事实上,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地留存在以物化形式保留下来的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之中。在未经特定时代的主体去“阅读”和“激活”以前,传统的意义并不存在,传统的意义只能出现在现实主体与历史文本的对话和阐释中,只能不断生长在当代人的意识里。于是便少不了扬弃和发明,少不了话语方式的现代转换,否则就很难称之为传统,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意义,所以把历史理解说成是主体去接近一个自足存在的客体,就显然不是正确描述这种理解。事实上,在历史理解中总是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点,即朝我们走来的传统是在现在之中说话,我们必须在传统与现在这种调解当中理解传统,或者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把传统就理解为这种调解。”[②]
二、如何理解传统诗学理论的“原义”
如果承认阐释学对于传统的分析是符合传统在历史中的实际情形的分析,那么关于什么是传统诗学“原义”的争论便不难解决了。执著于原义与执著于传统的困扰均大同小异,历代文人出于维护经典“原义”的目的,极其强调一种“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即对经典的文本只作“注”、“疏”式读解,只转述而不加以发挥。经典只有一个,而注本却可以有成百上千。人们以为这样便可以有效地维护住经典的原义了,殊不知任何陈述都不可能是原样的再现,而是包含了理解主体的认识。“当你带着自己先在的经验结构和指向性去‘校、注、疏、述’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你的选择和判断,你对文本的任何处理行为都必然是一种阐释,是一个以‘原义’为起点,不断向着未来的意义积累和生长的过程。正是元典与注疏读解在历史中有机地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组合。你注六经时,不仅是经典在向你走来,同时你也在主动地向经典走去。经典的意义始终呈现为一个发明和运动的过程。”[③]如果说有什么称之为“原义”的东西存在的话,它只可能体现为一些最基本的生命困扰,一些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相关的言谈范围,一些由特定时空和语言环境所决定的意义的有限展开,而且随着视域的改变,它必定会在运动中生长、扬弃和丰富自己,这将意味着,它在历史的每一规定性的时空中只有以现代形态出现才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以“道”这一重要概念为例,它的原义在先秦铭文中只是“道路”之意,“一达谓之道,”此后随时代变迁和历代的阐释逐渐生出丰富的意蕴。《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遂有二元之分;《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渐融入“言谈”、“理性”、“虚无之道”等多种含义;后世则发展出“天道”、“佛道”、“理道”、“心气之道”、“万物之道”,以及近代之“人道”种种。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也成了诗学的主要价值目标,所谓“言志”、“载道”等等。《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既指万物本体、世界本质、社会发展规律的本体之道,也包含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等级制度等工具之道。待将“天人合一”视为文学应载之大道之后。“弘道”终于成了中国诗学之大法。而今人张隆溪在其著述《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中,则主要取其“道”的“理性”和“言谈”这两组与西方“逻各斯”概念较易对话沟通的层面来展开分析,使之既让对方有基本的理解,又在比较融合中产生洞见,这无疑为提升中国传统诗学为世界所认识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努力。[④]所有这些都无不证明,“原义”只有在现代阐释学的意义上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对于比较诗学而言,重要的不在于寻找一成不变的所谓诗学的“原义”,而在于如何去理解和追问这一久已被悬搁的观念,尽快走出古典诗学阐释理论关于原义的种种误区,从而对诗学意义的生成和阐释方式有更接近今日知识水准的全新理解。
三、中西诗学对话中“阐释的循环”的积极意义
现代阐释学在“阐释的循环”命题上与古典阐释学的认识不同,在于后者相信在整体与部分的依存与循环过程中无法做到“客观的理解”,无法寻找到文本的“原义”,从而成为恶性的循环;而现代阐释学则认为文本的创造者和阐释者都是“人”,他们的偏见和前理解都是作为“人”的局限性而不可避免。意义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无限趋向未来的过程,因此,加入到循环中去,就是理智地进入意义的不断动态生成过程,是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循环。就中国传统诗学而言,其过去的意义生成是历代的阐释主体对居于特定时空中的诗学文本进行不断阐释的结果,即有的诗学观念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相互对话、相互作用的动态生成物。前述关于“道”和“言意关系”命题的分析展开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相应的,则是在今日的语境条件下,在作为对象的传统诗学与作为主体的今人之间,在传统诗学文本与20世纪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背景之间,在中国诗学与世界其它民族诗学之间,一轮新的阐释循环的开始就绝非是一种学术上的随意选择,而是中西比较诗学对于这种历史要求的主动回应。这也将意味着,对中国传统诗学加以新的阐释和重建的意义,不仅是为着建设属于自己的当代文论话语,为着与当代世界文论主潮的平等对话,而且也是为着这一诗学传统本身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传统诗学薪火传递,生生不息的内在需求!
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无论是为着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还是为着在比较中寻求某些跨文化的诗学共相或所谓规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都是在努力追求中国的现代性这一世纪性主题的语境下展开。双方在现代世界中处境的历史落差反映在诗学领域,则表现为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话语的张扬和中国文论话语的退缩。在铺天盖地袭来的西方文论话语的喧哗中,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候愈来愈重,为着摆脱这一处境,中国传统诗学需要更新重建自己的话语,但是为着重建自己的话语,又不能不以大军压境的西方话语作为参照。于是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必然同时展开古今和中外的双重对话。也就是说,要更新重建必须依赖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交流,而要对话交流则我们的诗学话语又必须是可以相互理解沟通的现代理论话语,于是操作起来就显得腹背受敌,特别艰难。这一悖论实际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阐释的循环。从现代阐释学的理解去分析,我们所走进的这一循环虽然是无奈的选择,但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没有出路的。现代阐释学关于传统、前理解、视域和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和对话原则的一系列理论洞见可以启示我们,传统既然是一个在历史时空中运动着的活的存在,那么,所谓现代的西方理论同样也包含着关于西方诗学的过去的传统成分,包含着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古代文论思想;而被视为只属于古代传统的中国诗学经过20世纪的洗礼,经过王国维以来,或者说“五四”以来数代文论家的阐释,也未必不具有某些现代文论的因子;这就可能为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对话找到起点。除非你把最近这20世纪一百年的中国排除在传统之外,否则,你不能拒绝它加入对话和阐释的权利。而中西文论不同的前理解和视域差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必然是各自在过去的历史时空中探索文论问题的不同侧重和长处,这也为双方在融合过程中的交流互补提供了可能。双方尽管有落差,有不平等。但中西诗学只要坚持互为主体,互为参照的长期对话,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以各自的视域相互接触、试探和碰撞,并不断地反观自身,改进自身,不断探讨一种能够跨越双方诗学的新视域,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探寻中西诗学对话的中介性“话语”,相信中西比较诗学的价值预期就应该有实现的可能性。阐释学的原则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是理智地主动加入这一跨文化诗学的循环,我们就不仅不会丢弃自己的传统,而只会使传统得到趋于现代要求的提升。况且这还不仅是现代阐释学理论的论证,同时也为近20多年来,或者说自“五四”以来中西比较诗学的实绩所证实。
四、充分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对中西比较诗学的未来作出积极预期的时候,也应该对这一研究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的准备。不同的诗学体系的文化落差给双方视域的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人们尽管在理论上给予欧洲中心主义以普遍的批评,但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在实践中改变西方理论的强势地位。这是由近二百年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抢占的优势位置所决定的。你愿意以平等和互为参照的地位与别人对话,别人未必也会有这种意愿,而一厢情愿是不可能结成好姻缘的。这一切都需要长时期的争取和努力。古今中西多重视域的交叉和互为表里同样也给对话和理解制造了重重障碍,这将意味着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对我们的知识结构、学术深度和语言能力都必然有更高的要求;博古通今已是不易,学贯中西则更难,非如此,却又难有研究上的开阔眼界和穿透能力。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至今未能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找到比较适合的学科本体论的思想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从而导致研究工作总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倡导、问题的罗列、浮泛的比较、学科理论意义和价值判断的肯定等方面,很难再深入下去。处于这样的学科状况,与其作过多“学派”的呼吁,提出某类诗学“规律”和价值“普遍性”的许诺,满足于既有的一般性比较分析的成绩,倒不如把问题考虑得困难一点,深入一点。尤其应该回过头来,多作一些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学科本体论意义的思索和方法论原则的探讨;事实上,“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中,普遍性的机遇极少,在我们对知识的寻求中,普遍性的机遇虽多一些,但仍然有限。普遍性的最佳机会就存在于我们使用的方法中。”[⑤]如果中西比较诗学在实践中逐渐完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原则,而不是随意地、主观想当然地把一般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所谓方法和模式硬塞到中西比较诗学的头上,则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目标和价值预期也许会透过这些理论方法的运用而自然地浮现出来。在这一方面,西方阐释学从古典阐释学向现代哲学阐释学的成功转化,其在理论和方法意识上的创造性,对于中国诗学的重建无疑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广义地讲,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一种关于人及其所置身的世界的阐释学。同样,中西比较诗学无论从本体和方法上也可以视为西方诗学阐释学与中国诗学阐释学的交流和对谈。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两种阐释学存在着现代意义上的巨大发展落差。如前所述,西方阐释学在经过了创造性的探索之后,不仅实现了从一般方法论向哲学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而且使它的哲学立场和方法体系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动力和思维路径之一。在现象美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当然还有比较文学等理论中,都很容易见到现代阐释学的身影。而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诗学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来的命运一样,无可奈何地落伍了。她被拒斥在20世纪文论发展的历史机遇之外。作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持的汉语诗学阐释学,同样也错过了实现历史性和现代性超越的重要机会。这样就只能使汉语诗学阐释学理论仍然处在古典阐释学的思维泥沼之中。对“原义”的追求和对“正确理解”的渴望始终是它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文本的文字、音韵、训诂和考据不仅作为手段,甚至成为某一时期研究的终极目的;经典的注疏和转述不敢越雷池一步,文章义理的分析也只能代圣贤立言。在这里,不管是“述”或是“作”,都只是在古典解经学的意义上基于所谓原初意义的读解,以致在诗学思想和范畴概念的发展上循环传承,夹缠不清,很难理出头绪和看清历史演进的线索;要从中分清那些是有创造性的“新见”,那些是旧有的“陈说”的确相当困难。今人的视域在置入过去的文本视域之后,便陷入历史话语的囚笼和含混模糊的描述中。新的视域始终是一个迷离恍忽的影子,令人想见其真面目而不得,其结果只能是,整体的汉语诗学的价值意义构成和它的阐释学理论及方法仍旧停留在古典阶段,徘徊在现代世界的文艺理论主潮之外。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汉语诗学阐释学的理论方法中缺少向现代性转化的生长性因素,而是她很久以来一直缺乏这方面的历史语境和自觉意识。实际上,诸如中国诗学“有无相生”以及比兴隐喻的意义生成模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仰观俯察”、“优游涵咏”的意义阐释模式;[⑥]主体虚位、主客换位、“以物观物”的诗学关照方式;贴近个体生命感悟、追求言外领会的理论言谈方式等等,作为其特有的经验和前理解,都有可能在现代的阐释过程中被激活生长成为现代诗学阐释学的有机成分。譬如在理解了中国传统诗学的生成和阐释模式所具有的动态特征和生长性构成以后,从今日的视域去读解某一经典诗学文本(包括各种范畴、概念、术语等)时,我们在阐释的方法和层次上便可以试探某种新的意义深度探寻模式,即首先考虑文本本身在其原初的语义层面上说出了些什么意义;第二层则追问文本在与当时的语境关联中发挥出了什么意义;第三层将继续追问当时形成的意义作为理解对象在与历代理解主体(诗人、诗学家、一般读者等)的视域融合过程中又生长出多少新的意义,同时某些意义又是如何隐退或消失在历史的阴影下面;第四层则不妨从现代的视域去对融含上述三层意义的历史文本进行现代阐释,以今人的知识疆域和分析能力,我们不仅应该对历史形成的诗学意义理解进行一番清理和定位,而且能够继续发掘其深部结构和未尽之义,并通过文本的激活和再阐释,从而使历史传统以现代形态存活于当代生活之中,成为当代诗学话语的有机构成;第五层追问应是在比较诗学的层面上展开。作为民族诗学的传统在面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传统的追问时,许多曾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意义层面和价值结构都将面临被“拷问”、被“拆解”的尴尬境遇,但同时也会碰到被接受、被补充和“重构”新生的历史机遇。[⑦]在这一轮诗学的国际性阐释循环过程中,民族的诗学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成为可能,就每一具体的诗学文本而言,都无疑会开启一条无限敞开的意义生长之路。当然,上述阐释层次模式的区分是为着理解的方便和理论上的清醒,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可能是相互交叉,重叠并行的。这种尝试很可能既保持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优长,也体现出现代阐释学的开放性探索;既借鉴了现代西方阐释学的精神,也尽可能地去适应了汉语诗学阐释学的特定视域。在探索未来具有现代本体论特征的汉语诗学阐释学的历史路途中,类似的析解方法和阐释模式的尝试,其意义应该比匆忙地去强调双方的诗学价值比较,去呼吁地位的平等和席位的分配更重要得多。在这一意义上,比较确实不是理由,至少不是主要的理由和目的。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迫切课题与其说是要迅速地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要确立中国诗学的世界意义,倒不如说首先是要让古典诗学阐释学传统从历史徘徊的泥沼中走出来,经过艰难的中西古今对话,从而使其尽快从传统方法论向哲学本体论和现代方法论的层面提升。只有我们在关于诗学的思维和理解阐释路径方面有了革命性的改变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将中国诗学独特的文化视域和话语方式置入于现代理论的架构里面,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现代诗学视域的反复融合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选择扬弃,从传统中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生长点出发,全力去建构具有现代特征的汉语诗学阐释学,只有当这种努力成为诗学研究界自觉普遍的追求以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化和世界意义才会成为可能。这也许可以算是现代阐释学给予比较文学、尤其是给予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 陈跃红:《语言的激活:言意之争的比较诗学分析》,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四期,第104—106页。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1975年,英文版,第293页。
③ 陈跃红:《阐释的权利》,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一期,第50—51页。
④ 参见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Durham and London,杜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基本观点。
⑤杜威·佛克马:《东西方及其它地方的诗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北京,1992年,第1—2合期,第3页。
⑥ 可参见王宇根《“观”与“外”: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与诠释》,未刊稿,北京大学1995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⑦ 参见陈跃红《阐释的权利》,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