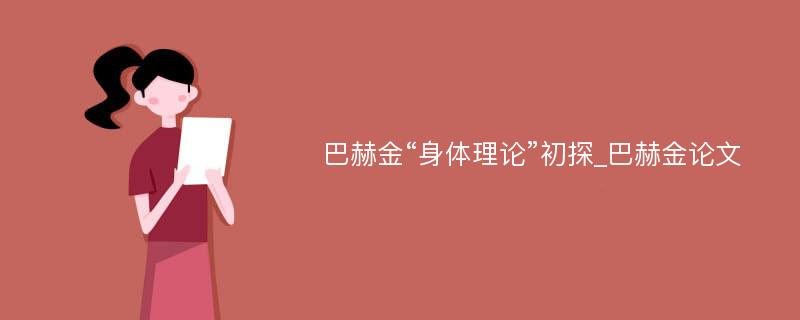
巴赫金“躯体理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躯体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6X(2007 )03—0018—04
躯体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本体性概念。在巴赫金的思想中被常常彰显的狂欢、怪诞等等范畴都不同程度地和躯体理论相交汇。巴赫金自诩为哲学家,一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围绕着哲学的基本论问题展开,即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躯体这一范畴统摄了我与他人、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我与他人、我与世界的一个交汇处。在这个意义上,躯体在巴赫金的思想中具有本体的性质。躯体在巴赫金的思想中牵涉的内容很广,从哲学、美学、文学、民间文化等多个层面构筑了一个以躯体为本体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正如巴赫金所说,现在应该“把躯体作为价值问题提出来”[1]。
一 内外躯体与巨大躯体
巴赫金一生都站在平民集体的立场上,我与他人关系是巴赫金用来沟通平等对话主体、建构共同存在的团结集体的重要维度。作为躯体理论的重要一维,如何把我与他人关系统一于躯体,巴赫金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躯体的把握上,巴赫金受到康德、柏格森等人的思想的影响。康德把人的感观分为内感观与外感观,时间是内感官的直观形式,空间是外感观的直观形式,从属于内外感观的时空直观形式是人用来把握事物先天能力。柏格森则把形象分为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外在的构成物质,内在的构成精神。康德和柏格森对巴赫金的重要启发在于使巴赫金认识到了人的内在与外在认知形式的不同。鉴于此,巴赫金把人的躯体也同样作了内外之分。内在躯体,指具体内器官的感觉、需求和愿望集中于内部中枢的总和,是自我意识的因素之一,其基础是“我”这一价值范畴。我对自我的把握、反思形成的对自我的认识都会构成内在躯体的因素。但巴赫金看到单纯拥有“自我”的内在的躯体不能构建出完整躯体。我可以直接感受自己的内在躯体,但我无法直接看到我的完整外表,因而需要从他人的审美旁观中获得我外在躯体的信息,“需要他人的认可和建构”。外在躯体的基础是“他人”这一范畴,只有他人利用其外位的优势,才能对我的躯体外在有一个整体的体验,同样我对他人而言也是一个他人,他人也通过我的超视体验来构筑自己的外在躯体。总体说来,“躯体作为价值在唯一而具体的世界里所占据的因主体而异的唯一位置。我的躯体基本上是内在躯体,他人躯体则基本上是外在躯体”[3]。 我要构造自己完整的躯体必然要统一自己的内在躯体与外在躯体。“而外形因素,……总有其内在的对应物”[4]。我要统一内在与外在躯体,也即是统一我与他人的关系,我要通过他人对我的外在完整体验结合内在的对应物,来建造一个完整躯体。这样,躯体问体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我与他人的主体间性问题,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躯体处交汇。通过内外躯体的划分与完整躯体的构建,巴赫金首先克服了意识和躯体的主客对立,把意识和躯体关系转化为你/我关系。我与他人的对话、交往、狂欢都是在彼此确证对方,在积极地建构对方的统一的躯体。躯体在巴赫金庞杂的思想体系中呈现出本体的特点。
对这种由我与他人关系构成的内外躯体的划分与统一,巴赫金认为有其历史的渊源。巴赫金追溯到柏拉图以前,认为古希腊罗马的鼎盛时期,“一切躯体的因素都为他人范畴所阐明,作为直接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被体验,内在的价值上的自我界定通过他人也为他人而从属于外在的界定,自己眼中之我融于他人眼中之我……”[5]。随着“狄奥尼苏斯酒神的出现”[6],个体自我内在的欲望膨胀,淹没了印证自我的他人视角,内在躯体与外在躯体的和谐开始被破坏,外在躯体开始消失。在伊壁鸠鲁主义思想中,躯体和精神的对立还没有尖锐化,无论躯体还是精神都统一在对躯体的各种需求和对需求的满足的基础上。“满足欲望或没有欲望,可以使人快乐”、“德行或道德使达到快乐或精神宁静的目的的一种手段”[7]。由于仅止于自我内部的欲望满足,巴赫金认为在欲望关系中,这类躯体还“带有他人积极价值的反照”[8],但也仅可称为“内在的躯体”[9]。在巴赫金看来,正是躯体萎缩到自我的内部感受中,精神才开始和躯体对立起来,而在此前的躯体依靠他人来设定之时,自我的精神是不反抗内外统一的躯体的(也即不反抗他人)。巴赫金认定,在斯多葛学派中,自我内部的身心对立开始出现,精神开始压抑内在躯体。斯多葛学派无视他人的存在,视“他人同我一样”[10],把内在的躯体需求视作错误的理性(巴赫金称之为“非理性”,强调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精神对躯体的征服。虽然巴赫金在分析斯多葛学派对内在躯体的压制时,把斯多葛学派和第奥根尼的犬儒主义学派混淆了[11],但巴赫金看到的这一趋势是正确的。巴赫金进而认为,这种对我的躯体的否定,在新柏拉图主义中达到高峰。“普洛丁,与我们同时代的哲学家,似乎为你生有肉身而羞愧。”[12] 新柏拉图主义以纯粹的自我体验为基础,始终如一地从价值上评价与领会人与世界,“一切事物(宇宙、上帝、其他人)仅仅是自己眼中之我,他们对自己地的评说是最具有权威和最终的结论,他人没有发言权”[13],同时由于自我的躯体需求不需要自我予以评价(这种评价只能他人来做),因而新柏拉图主义者表现出“对躯体的最彻底的否定:我的躯体对我本人来说不构成价值”[14]、“躯体作为肉体生命的载体,应该绝对加以否定”[15]。
由巴赫金的这一追溯,我们可以清楚地弄明白巴赫金的意思:我与他人的间性躯体的完美统一被内在自我欲望的膨胀而破坏,由此,自我在消灭他人之后出现,作为自我构成的精神和躯体的对立才真正开始,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对躯体的压抑之后,不是回复到尼采以来的学者主张的以欲望躯体压制精神自我(如果那样,人仍旧把躯体限制在一己之内),而是要重新引入他人之维,只有我与他人构建的躯体才能与精神达成和谐统一。但在构建躯体向度上,我与他人是只是单数的对位因素。在人与人的交往对话中,人群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躯体——这是巴赫金由个人的躯体引发出来的“巨大躯体”理论。巴赫金认为:“一切有文化的人莫不具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化于其间;不单是同人民,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中,不要有任何的距离、等级和规矩;这是进入巨大躯体。”[16] 这种巨大躯体是众多我与他人的复数关系, 有着人民共同体的意味。这种“巨大躯体”的象征有着基督教的渊源联系,旧约中的肉体就有“人民的集体的统一体”的内涵[17],新约中则视基督徒、基督与上帝为一体。这种肉体的一体化观念,给巴赫金的思想定下了“集体”这一基调。
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巴赫金一直把“集体”等同于“民间大众”,以民间这一集体去整合“官方世界”的统治阶级,最终使“官方世界”融合于“狂欢世界”。“巨大躯体”这一躯体观念本身就已象征性地预示着这一整合。同时,巨大躯体这一虚拟范畴也给了巴赫金躯体理论以一个理想指向,使巴赫金的整个躯体理论更富有体系性。巴赫金的思想的突出特色之一是始终以集体的声音说话,而这一集体的声音又极富有个性特点,只有在偶然的个体身上才会出现。这种貌似矛盾的集体性立场和个体化风格的对立,说明了“巴赫金对感性思想活力的强调与狂欢集体永恒性的颂扬,说到底最终是为了将个体融入到集体之中以获得永生”[18]。巨大躯体的这种具有集体性质的个体造型,为巴赫金的个体与集体完美融合的理想赋予了感性形式。这些狂欢世界中的个体,“它们超出了自身的个别性;在它们身上,个体的和包罗万象的因素仍融合在矛盾的统一体之中”[19]。这种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个体构造的巨大躯体也同样是个体的和包罗万象的因素融合一体的。巨大躯体是不脱离内外躯体建构的统一躯体,与任何个体躯体一样,需要我与他人积极主动去建构。我与他人的主动建构创造出我与他人的统一完整的躯体。民间大众的交互建构创造出一个完整统一、融合“官方世界”与“狂欢世界”的巨大躯体世界。个体间的对话是我与他人的建构行为,狂欢化的巨大躯体则是集体的积极建构行为。积极主动建构躯体,体现出个体利集体的能动创造性,唯有如此,个体和集体才会在巨大躯体中融为一体。
二 躯体与世界
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上,躯体是二者的融合体。在对待我与世界的关系上,躯体同样是我与世界的交汇体。在这种交汇中,我并不是脱离躯体的单纯心灵的自我,我与他人是躯体组成的二元因素,同样,我与世界也并不是脱离躯体的单纯心灵和外在独立的世界,二者是作为躯体重要构成因素的我与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我、他人、世界都参与了躯体的建构,完整的躯体必然包含我,他人与世界在内。在躯体与世界的沟通上,巴赫金则着眼于躯体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
躯体的开放性着重表现在躯体和外在世界的物质交流沟通之上。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探讨了民间文化中躯体的孔眼处的内涵。“被强调的部位,或者是人体向外部世界开放,即世界进入人体或从人体排出的地方,或者是人体本身排入世界的地方”[20],即人体的凹处、凸处、分支处和突出部:张开的嘴巴、阴户、乳房、阳具、大肚子、鼻子等等,一切和交媾、吃喝拉撒等交换功能相联系的部位都是躯体与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地方,也是世界进入躯体,躯体融入世界的地方。这种开放的躯体特点,消融了躯体与世界的明确分界线,“与世界相混合,与动物相混合,与物质相混合”[21],在开放、交换的世界,躯体与万物在彼此没有隔阂地相互吸纳。
同时,躯体在巴赫金眼中是未完成的躯体。不仅仅是我与他人对存在的躯体的共同建构未完成,而是在躯体中的物质更新交替未完成,躯体的生命始终在双重性、内在矛盾的过程中得以表现。这种未完成性常常表现出原始的辩证逻辑。例如怪诞躯体之一的怀孕的老妇。按照巴赫金的解说,这种躯体是“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一个是生育和萎死的身体,另一个是受孕、成胎、待生的身体……在一个人体上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程度突出另一个新的人体”[22]。这种新与旧、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的更替,需要躯体之外的世界不断融入躯体,躯体中死亡的成分不断回归到世界之中。这种躯体的未完成和躯体的开放性是完全一致的,正是由于躯体的开放,才可能使躯体处于不断更新的未完成之中。
躯体和物质世界具有天然的开放性的交换关系,“在这里,单独的身体和物质并非就是自己本身,并不等于自己本身,……他们代表着世界的不断生成的物质——肉体整体”[23],“人体代表和体现作为绝对下部、作为吸纳和生育的因素、作为人体的墓穴和怀抱、作为播种的田地的整个物质——肉体世界”。由于肉体的这些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因素,物质世界天然地汇入躯体这个中心[24]。由于躯体是自我与他人、物质世界的交汇载体,所以巴赫金曾经有过人与人平等交流融合,汇聚成“巨大躯体”世界的设想,所以巴赫金着重研究了民间狂欢世界这一具体现实存在而又符合“巨大躯体”象征性理想的时空状态。
三 作为价值存在的躯体
正统的中古世界观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缔造的。按照这种理论,所有物质都是依固定的顺序,自上而下排列的,所有的价值以其空间的垂直位置来决定。到文艺复兴时代,随着等级世界崩溃,人的躯体成为宇宙的相对中心。一切事物的价值开始以人的躯体为中心,向四周水平展开。巴赫金的躯体理论正是在文艺、美学、伦理等层面继续重建躯体的价值中心,在重建中不断冲决一切反躯体中心的旧等级秩序,因而表现出各种颠覆性的特征——而一切颠覆性因素都围绕着躯体理论的价值重建展开。
巴赫金建设的躯体理论,其核心是完整躯体的建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我与他人关系、我与世界关系交汇于躯体存在。时间和空间是在建构躯体中呈现出超时空的价值取向。在价值视野中时空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时空,而是富有情感意志色彩的时空。情感意志色彩是关乎他人的价值存在,时空中存在的躯体因而也无法脱离他人而存在。这种时空中存在的躯体具有明显的为他人而存在的伦理道德指向。这种道德指向使巴赫金的躯体理论不同于一味颠覆的肉体诉求——一味颠覆的肉体理论是把一切事物拉到动物的水平,而巴赫金的躯体理论是在颠覆的基础上重建“巨大躯体”。
作为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的合理组成部分,躯体的功能(死亡、性、吃喝等)分析,始终包孕着颠覆与建构的双重指向。对一个我与他人构建的完整躯体而言,躯体的任何功能表现都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都要在他者的参与中才能最终完成。死亡作为个体无法在时空层面上体验的结束,只能借助他人的超视来完成,更为关键的是只有在他人的情感意志关照下,个体的死亡才能真正作为一种价值存在被完成。同时,按照巴赫金的躯体理论解释,死亡蕴涵着新生,它是躯体与世界交互沟通的必要步骤。同样,单纯局限欲望满足的躯体的性并非巴赫金所阐释的性。巴赫金强调的是我与他人建构的完整的整体,而不是只是在性这一个单一维度上。巴赫金反对只停留于动物水平的性欲求。但在拆解旧的等级秩序,把以性为重要特征的躯体凸现出来了——这种突出更多的是对相关性的生育、交媾……和世界相交通的开口处的突出,表现的是躯体和世界的融为一体,在这种交融中任何等级秩序都无法阻碍。吃喝等躯体的生理功能表现也都在瓦解旧秩序的同时力求突出躯体和世界的一体,只有在这种巨大躯体中,一切隔阂交融相通的等级秩序才会被冲决殆尽。
身为文艺学家的巴赫金,阐释其躯体理论的载体是文学艺术。巴赫金注重挖掘文艺作品中的躯体主题。文艺作品的人学特旨契合于躯体的价值向度,为巴赫金挖掘文艺作品中的躯体内涵创造了条件。在拉伯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充满了躯体意象。文艺作品中躯体的夸张的生理表现只有在巴赫金躯体理论体系中,才能得到最为合理的诠释。无论是和狂欢文化渊源密切的怪诞艺术,还是镜像式的文艺形式、丑角地形学,在这些巴赫金所研究的文艺样式中,巴赫金总在力图诠释他对躯体价值的文化理解。巴赫金曾自认是哲学家,确切说是一个伦理学家,巴赫金的文艺研究某种意义上是在文艺作品中寻找他所认识到的哲学思想。巴赫金的躯体理论的文艺学应用,某种意义上是在文艺中发现他的关于躯体的思想,是在寻找文艺和躯体的密切联系。巴赫金的躯体理论对文艺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他在文艺中通过对躯体的寻找真正寻找到了人的存在价值——而且这一价值首先是从感性的躯体存在开始。
[收稿日期]2007—0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巴赫金躯体理论研究”(05JC750.47—99016)
标签:巴赫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