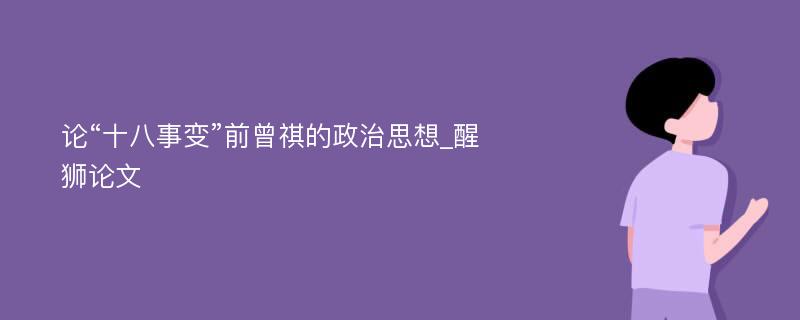
论九#183;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政治思想论文,一八论文,曾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青年党首领曾琦(1892—1951)是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因其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大陆史学界过去对其前期政治思想专门研究的不多。本文拟就九·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及其形成缘由加以讨论,这对于深入了解曾琦及正确估量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当属必要。
一
九·一八事变前,曾琦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不大,形成了其相对稳定的前期政治思想,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一)宣传国家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
这是他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曾琦根据自身对国家问题的理解,在当时大力提倡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主义。他结合世界和中国的情况,对国家主义的产生根据、基本精神,以及国家主义者的任务、宗旨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之所以陷于混乱,就因为守法观念已失,爱国信条未成,没有最高道德规范一切,所以卖国贼才敢于自私自利。1925年,他发表《国家主义者之四大论据》的讲演,提出信奉国家主义的“四大根据”,即第一,“世界大势论”。第二,“本国情形论”。第三,“社会道德论”。第四,“人类本性论”。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主义者,合国情顺潮流主义也。国家主义者救中国唯一良方也。欲救今日之中国,非国家主义不为功矣。并且进一步声称:欲中国政治上轨道,外交占胜利,社会得安宁,当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全民革命为手段,合四万万人之力,中国各民族合力同心才行。为此他大力宣扬“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强调国家的利益和作用,提出凡破坏国家者,国民应群起诛之,凡为国建设者,国民应群起而助之。指出国家可以要求人民作任何牺牲,人民对国家只有牺牲的义务。主张建立全民国家,实行“全民政治”。采用“普选”、“职业代表制”、“联省自治”、“妇女参政”等,建立“民治政体”;建议采取贸易保护、统一税则、开发本国实业等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
与此相关,曾琦还大肆抨击马克思主义。他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否定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早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他就反对用马克思学说指导学会活动,坚持把它办成一个纯学术性的团体。在留法期间,他给王光祈信中更称要研究蒲鲁东学说,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华的传播。并以《先声》周刊为阵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他表示不赞成马克思的“物质支配精神之说。”(注:《曾琦传记资料》(一)第103页,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政治重于经济。因一切经济制度,均可由政治权力变更之也。”(注:《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 186 页, 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党成立,曾琦在他起草的《建党宣言》中,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认为马克思主义太过注重阶级对立,提倡阶级斗争,主张劳工革命,是忽视了其他各界,减少了革命的势力,远不如国家主义“兼顾各方,易收实效”。而中国现实并不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他力主阶级合作,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曾琦看来,实行共产主义,必须具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在精神方面,须共产主义观念普遍,公共道德发达;在物质方面,须工业发达、交通发达。这两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均不具备,因此实行共产主义只能是“空想”。
(二)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
这是曾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1、反对共产党
曾琦自称是:“全亚洲反共最早而最力之人”。(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中共刚成立,曾就对其横加指责,说建立政党不符“革命的范围和秩序”,提出要从理论上澄清共产之邪说。1923年青年党建立后,他更激烈地批评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先后在《醒狮》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抨击中共是“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动摇国本”,“其祸实烈于洪水猛兽。”(注:《蔡元培与胡汉民之反共产论》,《醒狮》周报第46期,1925年8月22日。 )共产党“破坏国家;扰乱社会;勾结外寇;断送家土;毁灭国魂;废弃国旗;摧残教育;破坏生产;蹂躏法律;破坏党德。”(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表示:“共产党者,世界之恶魔也。”为此他力主消灭共产党,说:“吾人自始即认共产党为大敌,决心与之作战,成、败、利、钝、祸、福、毁、誉、得、失,举皆不计。”(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积极提倡“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注:《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这充分暴露了曾琦思想的消极落后的一面。
2、非难人民革命斗争
大革命时期,人民革命运动日渐高涨。1924年国共两党发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曾琦却指责国民会议运动是“乘机煽动,别有用心”,表示“吾人固万不能符合也。”(注:《醒狮》周报第15期,1925年1月17日。)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曾琦反对中共对工运的领导,反对工人举行罢工运动。说:“不宜轻用罢工手段”,以免“致使工厂歇业。”(注: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期,1925年9月26日。)1925年8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曾琦在《醒狮》周报上则公开主张:“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暗施操纵之术”;“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不宜让共产党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在军阀未倒,外患未消之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遽谈阶级斗争。”(注:曾琦《为上海总工会鸣不平》,《醒狮》周报第51期,1925年9月26日。 )这就是说共产党不要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人阶级也不要反抗资本家,不要搞阶级斗争。1926年6 月“万县惨案”发生,国内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强烈反对英国暴行,而曾琦却不以为然,声称:“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此外,他还提倡“求学救国论”,引诱学生、知识分子放弃革命的政治活动;攻击农会会员,反对蓬勃的农民运动等等。
(三)支持国民党“剿共”,反对蒋介石“党治”
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曾琦是矛盾的、复杂的。
1、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排斥其三大政策
一方面,曾琦自称对国民党向来具有同情,认为宗旨无大冲突,并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有三点与国家主义相合,把自己的国家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混为一谈。他表示:“中山生平所揭橥之三民主义,本不越乎‘国家主义’与‘社会政策’二大范围。三民主义实包括于‘国家主义’之中,何则‘民族主义’者,固所以求‘独立建国’者也;‘民权主义’者,乃所以伸张人民之权利,求平等生活于一国之内,而不受任何一阶级之专政,是乃‘民主共和之通义’,固犹在‘国家主义’之中也;‘民生主义’是明明为‘社会政策’之一种,亦包括于‘国家主义’之中者也。”(注:曾琦《悼孙中山先生并勖海内外革命同志》,《醒狮》周报第24期,1925年3月21日。)
但另一方面,曾琦又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跨入国民党。”(注:曾琦《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及忠告》《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曾说:“吾人之反对联俄容共,远在民国十二年国民党人最初动议之时,及十三年春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吾人乃加以痛切之忠告,猛烈的批评。”(注:曾琦《吾人七年来对于国家之二大贡献》,《醒狮》周报第223—225期,1930年10月10日。)“吾人断定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实具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其结果不惟妨害革命之成功,并使国民党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自本报出版以来,无日不以此警告国民党。”(注:曾琦《三年来吾人对于国人之贡献及所经历之痛苦》,《醒狮》周报第152—157期,1927年10月10日。)1924年冬,孙中山北上途径上海,曾琦由谢持介绍往见,劝孙中山“中止联俄容共”,“辩论良久,不欢而散。”(注:《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1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曾琦借机攻击孙的三大政策,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他指责孙中山先生“固执己见”,“晚年误收共产党,”(注:《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联俄联共无异引狼拒虎,引鬼入室,声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去海外华侨之同情”,“失却绅商阶级之同情”,“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注:曾琦《挽孙中山先生》,《醒狮》周报第24期,1925年3月 21日。)他离间国共两党关系,说:“始而利用,继而篡夺,终而打倒”(注:曾琦《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及忠告》《醒狮》周报第129期,1927年4月23日。)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策略的“三步曲”,“希望国民党……绝对不容党内有跨党分子,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贻赤化之讥。”(注:曾琦《吾人对于国民党之真正态度》,《醒狮》周报第106期,1926年10月16日。)
2、肯定蒋介石“剿共”,反对国民党“党治”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曾琦对国民党清党“不胜同情”,尤深“赞其勇敢”,希望国民党开除共产党后,必须和国家主义者及其他爱国团体通力合作,“庶足以竟全功而除后患”。他向蒋介石进言:“第一条,反共宜求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第二条,反共同时并须反苏,不可一面驱逐共产党,一面敷衍俄国。……第五条,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须知共产党之基础本在下而不在上,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何以制共产党之死命?”(注:曾琦《国共两党决裂后吾人对国民党之态度及忠告》《醒狮》周报第 129期,1927年4月23日。)公然鼓动蒋介石向广大工农群众开刀。
但是同时,曾琦对蒋介石利用法西斯组织揽权,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异己等行径又颇为不满,他撰文谴责国民党“专制”误国,腐败无能,指出专制政体,根本阻碍自由思想,违背平等原则,破坏博爱精神,使国家因之衰落,社会因之凝滞,公开号召群众走民治之路,摒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指责国民党“以对内而论,募采国债数逾六万万,正式税收不下十万万,加以苛捐杂税,合计数年来之收入总数约达二十万万”,国民党没拿这么多的钱为人民办好事,“只是在南京修了一条马路和一座坟墓,其他都用来打仗了”。“更就外交而论,则关税空有自主之名,法权徒存收回之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给国人带来的后果是“有害而无利,有罪而无功”。(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抨击蒋介石“假一党专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主张通过民主和改良等方法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制。
(四)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北伐战争
虽然曾琦有时也喊些反对北洋军阀的口号,但实际上他与封建军阀的关系颇为密切。客观的现实,使曾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注:《曾慕韩自订年谱》未刊稿。)于是为了达致理想,他本人时而投靠北洋军阀张作霖,时而托庇于孙传芳,时而依附四川军阀,助纣为虐,从事反革命活动。北伐之前,曾琦就曾为张作霖“创造”过民族、民权、民生、民德“四民主义”理论,出谋划策巩固张作霖的权力地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曾化名王奇,往来宁济之间, 充当孙传芳的机要秘书,(注:《五卅后两年来青年运动》,《中国青年》第161—162期合刊,1927年5月30日。)诬蔑攻击及破坏北伐。 当北伐军进占湖南后,曾琦竟说:“此次北伐,不惟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忧”,“世人虽震其声威,而予则敢断言其必败。”(注:《醒狮》周报第98期,1926年8月29日。)公开宣传北伐必败。 对于军阀吴佩孚的失败,曾则有兔死狐悲之感,声称人们“对吴氏有去后之思”,极力为穷兵黩武的反动军阀大唱挽歌。到1926年末,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进抵长江流域,严重威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所到之处,废除了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于是曾琦又纠集一小撮人掀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国旗”的运动,成立“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以示对抗。
(五)默认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社会主义苏联
曾琦对帝国主义侵略虽然也不满,亦讲过“外求独立”、“外不亲善”之类话,但实质上他对外却是默认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苏联。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的积弱积贫,除了封建政制的腐败外,就是外国列强侵略造成的。但曾琦却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替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他宣称:“近数十年来中国国权之丧失,非全由外人之侵略,而实多为国人放弃之事实”,不仅“清末如是,近十数年亦复如此”。因此,他反对人们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声言:当今世界“但有‘英吉利资本帝国’、‘美利坚资本帝国’、‘法兰西资本帝国’、‘日本资本帝国’而已,无所谓‘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并指责“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含有干涉他国”内政之意。(注: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醒狮》周报第2期,1924 年10月18日。)另外,他对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亦奉为金科玉律。说:“在革命中,我们对于外国一切之既成条约,均应照旧遵守,俟实力充足以后,再来收回一切主权,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381 —382 页,1957年版。)
与此同时,在“外抗强权”的旗号下,曾琦又把斗争矛头指向苏联。他声称:所谓“强权”,即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并特别强调来自帝国主义之外的“强权”,即所谓“非资本帝国而以武力临我者或据我之领土或强我奉号令”者(注: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醒狮》周报第2期,1924年10月18日。)。 他视苏联对中国的支援为侵略,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深怀戒心。他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式专制”,还赶不上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苏联是“既以金钱收买我国之无赖,又以军队参予我国之内争,推其意殆非赤化中国不可。”(注:曾琦《中俄问题专号辩言》,《醒狮》周报第40期,1925年7月11日。)
总括上述可见,九·一八事变前曾琦政治思想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其基本倾向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而又偏重蒋介石一方,总体上说是错误的;他反共反苏,宣传国家主义,否定阶级斗争,依附封建军阀,维护帝国主义,非难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制,这些政见,既不符合时代潮流,也不适合中国国情,最终只能导致曾琦作为一个不识时务的人物留在历史上。当然,曾琦的政治思想亦非毫无可取之处,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他宣传“民治”反对党治,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客观上也起到了揭露和削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作用,有利于当时人们对蒋介石以至国民党的认识。
二
九·一八事变前,曾琦持如此政见,原因何在?下面试析之。
(一)时代的产物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内容构成,都必然与产生它的时代背景密切关联。曾琦的政治思想亦然。曾琦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剧烈动荡,风云突变的时代。一方面,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民族危亡,人民处在异常痛苦中;另一方面,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尤其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华的广泛传播,中共的成立及其威望的不断提高,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这一切引起了当时曾琦的惶恐和焦急。他疑惧革命带来的后果,自1924年从法国回来后,他“目睹时艰,叹无产阶级势力之‘猖獗’,甚至‘占领’国民党,甚至把曾琦的同志冯自由,马素等通统都驱逐出党,自然曾琦等仇视共产党的程度与共产党在民众中势力的增长的程度为正比例。”(注:记者《国家主义是什么?》《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日。)兼之此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给曾琦认识中共的独立性蒙上了一层屏障。而中共仿效苏联的一些做法,更使他错误地把中共看作苏联的“附庸”而加以摈斥。于是他抓住各种机会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理论宣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对峙局面开始形成,在中国出现了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权,国内各派人物都面临着政治立场的抉择。而曾琦在这一选择中恪守“两恶相权,取其轻”,自觉地倒向国民党一边。在他看来,共产党的“罪恶”更大,威胁自己利益亦更大,所以他殷切希望国民党“剿共”成功,天下太平。但是这一切并没得到蒋介石的很好回报。由于蒋介石是一位权力欲极强的人,一旦大权在握,他就实行“党外无党”的方针,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并企图“吞并”青年党,要曾琦解散中国青年党加入国民党,“彻底反共”,“以竟全切”,这令标榜独立的曾琦十分恼火。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又监禁曾琦,下令拿办青年党,公开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改为“以党专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决不容许再有第二个党出来”,“不能让第二个主义如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派出来捣乱,来攻击革命的国民党消灭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称:“以党治国,就是以中国国民党治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革命唯一的革命党”,“只有用一个党一个主义来号召、来领导”才能挽救国家危亡。”(注: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蒋介石全集》上册第4页,第一编。 )这表明在国民党一党专制主义和思想统治政策下,其他政党、主义均不能存在。这大大加深了曾琦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矛盾,令其感到这时局难于忍受,不得不起来抗争,最终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琦只好努力地进行夹击中的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党治独裁。
(二)阶级本性的流露
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右翼的一员,曾琦的政治思想亦很大程度上体现其所属阶级的利益。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当它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束缚,国民党专制压迫时,它们是不满现状,主张变革,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之路的。故当时曾琦会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党治及独裁专政,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喊些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主张言论自由,对工农群众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同情。这体现出其资产阶级右翼思想激进的一面,传达了资产阶级右翼企图建立自己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联系,甚至依赖它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因而更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易同旧政权旧制度妥协合流、反对新生革命力量的弱点,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从这种阶级本性出发,曾琦与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尖锐矛盾。曾琦理所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得势,必‘共’他们之‘产’,必更陷他们于贫困,所以他们集其仇视与恐惧于无产阶级身上,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注:记者《国家主义是什么?》《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 日。)认为要“救人救家救国,甚至自救,便不可不坚决的反对共产党。”为了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曾琦必定会竭力反对中共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反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样从这种阶级本性出发,曾琦才会与国民党新老右派、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在反共反人民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尤其与同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国民党蒋介石更是宗旨接近。这一切均是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两重性的自然反映。
(三)个人经历的结果
曾琦出身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富宦之家,从小接受系统、严格的封建思想文化教育,打下了旧学的深厚基础。他“喜读古籍,好慕先贤,自幼已然,”(注:沈云龙《曾慕韩先生遗著》第39—232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尤其酷爱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曾国藩等学说,表示永崇陆、王之学以治心。他非常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甚至陷于其中难于自拔。以致当时代不断前进时,曾琦却仍然裹足不前,在如何救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道路的选择上,他依然注重中国过去的经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具备宣传、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反对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阶级,主张依靠现有力量甚至军阀力量。稍长,曾琦进入国内天主教耶酥会创办的震旦学院学习,并先后赴日、法留学数年,接受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对于西方的思想、政治、法律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尤其在留法期间,正值国家主义思潮在法国流行,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由18世纪末德国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提出的,主张对内用“国家至上”的口号压制阶级斗争,欺骗劳动人民服从剥削阶级的奴役;对外以“民族至上”相号召,实行狭隘爱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它与具有资产阶级右翼经济地位的曾琦有相合之处,故他当时很自然地接受了其中的立场和观点,正如《中国青年》所称:“法国在战后是反动的巢穴,曾琦等留学法国接受法国帝国主义的反俄反共的宣传,当然到了饱和的程度。”(注:记者《国家主义是什么?》《中国青年》第133期,1926年9月7 日。)从此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成为曾琦思想的基础和灵魂,他开始大力向国内推销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党治,倡导民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等,以阻止中国革命的蔓延和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言人。
收稿日期:1999—01—09
标签:醒狮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青年论文; 曾琦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历史论文; 孙中山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