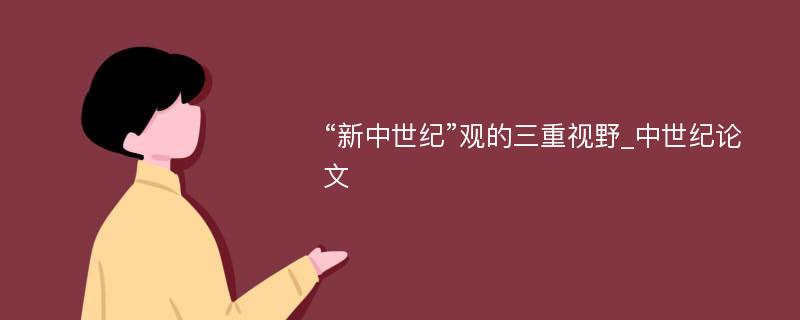
“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新中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4-090-095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知识界对“新中世纪”(new middle ages)的言说就不绝如缕。新中世纪的观念不仅仅存在于史学领域,而是出现在了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艺术、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这些言说的内容十分庞杂,想象与史实并存。虽然中世纪史家克里斯托弗·戴尔在运用新中世纪观作为著作章节标题时极力区隔与德国哲学流派的新中世纪观的关联性,[1]7但正如奥托·格哈特·奥克塞尔指出的那样,这些新中世纪观即使是对中世纪的想象,也与中世纪史研究有着隐秘的内在联系,“部分基于‘真实的’历史,但大部分基于某种中世纪诠释史”。[2]124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新中世纪观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为全面理解中世纪史提供一个参考。
一
笔者结合奥克塞尔等西方学者的分析,认为西方的“新中世纪”观主要有三重视野,一是乐观的新中世纪观,二是悲观的新中世纪观,三是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前二重视野是在部分史实基础上建构的中世纪意象,但是由于这种中世纪的想象“本身是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产物”,[2]128因而对西方学术思想和大众文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具有考察的必要。
乐观的新中世纪观把中世纪想象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整体的快乐时代,并且把新中世纪看作是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人类发展的下一个历史阶段。①这种新中世纪观主要存在于德国学界,但在美国、俄国、英国等国家的学界也不同程度存在,如俄国的别尔嘉耶夫、美国的丹尼尔·贝尔都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世纪式宗教的回归上。别尔嘉耶夫认为克服现代世界危机的途径在于对中世纪创造性的再发现,他称之为“新中世纪”。[3]丹尼尔·贝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中世纪观,但他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因此,“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回归”,“那就是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4]
奥克塞尔追踪了这种新中世纪观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从18世纪德国浪漫派的诺瓦利斯(Novalis)开始,到19世纪的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20世纪20年代的保罗·路德维希·兰茨贝格(Paul Ludwig Landsberg),50年代的罗马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80年代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90年代的迈因哈德·米格尔(Meinhard Miegel)。[2]122-123诺瓦利斯首开乐观新中世纪观的先河:“人类曾经有过光辉美妙的时代,那时欧洲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那时有一个基督世界安居于这块按人性塑造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的兴趣将这个辽阔的宗教王国的那些最边远的省份连接在一起。”[5]202诺瓦利斯选集德文版编辑也指出,人们并不认同诺瓦利斯对历史的理解,似乎他不了解中世纪基督教或教皇制度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这段包含在历史画面之中的内容并非真实的历史记述,诺瓦利斯也并没有存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5]199诺瓦利斯实际上是通过对中世纪似是而非的描绘来勾勒一个美好的未来,新中世纪将是“一个睁着神秘而无限的眼睛的新的黄金时代,一个预言的、创造奇迹和治愈创伤的、给人带来安慰和点燃永恒生命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和解时代”。[5]213诺瓦利斯之后,这种新中世纪观不断地在德国学界回响,就连社会学家滕尼斯也认为,共同体是个人与社会生活、家庭和亲属、邻里和朋友、村庄和城市的有机联系,而社会是由利益冲突和契约关系、由机械生产和经济变迁、由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由所有联系、忠诚和价值丧失形塑的人类机械关系的缩影。社会时代继起于共同体时代,现代继起于中世纪。[6]但现代文化正在不断衰败,因此滕尼斯呼唤新的共同体出现。这种新中世纪观最终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成为德国知识界为纳粹张目的工具。[2]135-137
悲观的新中世纪观把中世纪想象成为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停滞的黑暗时代,新中世纪就是一个应该竭力避免在未来出现的时代。这一观念的历史基础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所谓中世纪黑暗说,自彼特拉克开始,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都把中世纪视为一个黑暗时代,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860年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将中世纪作为文艺复兴的对照,[7]从而使中世纪黑暗说成为学术定论和大众常识。
1971年意大利哲学家罗伯特·瓦卡(Roberto Vacca)出版《即将来临的黑暗时代》。在这本著作中,瓦卡设想现代技术文化崩溃,导致社会和政治结构解体,世界重新封建化,权力在地方和地区水平上分配,民兵和自组织团体形成,流行病和大迁移复返,城市衰落。正是在瓦卡的新中世纪观的基础上,再加上意大利社会学家富里欧·科伦坡(Furio Colombo)的分析,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宣布我们的时代就是新中世纪。[2]1261977年国际关系研究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出版《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认为当代世界政治有向新中世纪发展的趋势。[8]1993年法国的阿兰·明克(Alain Minc)出版《新中世纪》把苏联的崩溃与罗马帝国的灭亡相提并论,认为欧洲正迈向分裂和混乱的新中世纪。[2]1232006年约翰·拉普莱(John Rapley)在《外交》杂志发表《新中世纪》一文,认为不但欧洲出现了新中世纪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新中世纪化,国家从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撤退,暴力私人化,黑帮接手地方经济和治安。[9]这种对未来新中世纪化的担忧在西方学界所在多有。
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是在旧中世纪观基础上形成的,旧中世纪观的基调是由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的,至今仍有影响力。旧中世纪观认为,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了中世纪时代,中世纪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萧条衰退,文化上愚昧停滞。当然,旧中世纪观也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亨利·皮朗、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等史学家都对传统中世纪观提出了质疑。正是在这一质疑过程中,在后现代哲学的启发下,新中世纪观开始形成。
笔者认为,在史学领域,新中世纪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颠覆了传统的中世纪文明兴衰观。
就中世纪文明的起源问题来说,霍吉斯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黑暗时代‘哥特人’的黯淡状态,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5世纪初期匈奴人阿提拉对富有的罗马文明所造成的天崩地裂般的后果之上。当然,这一观点是吉本那部不朽著述的基本观点,反过来它又成为19世纪史学家们孜孜以求加以详尽验证的对象。结果,研究古代世界的史学家们将5世纪作为他们研究的终点,而他们那些研究中世纪史的同行们,则把从那一时期开始的日耳曼人对西部欧洲的淹没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开端,这一框架模式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10]序言7而亨利·皮朗突破了传统学说的分析框架,在《中世纪城市》、《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等著作中,特别是《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一书中,提出了中世纪起源的“皮朗命题”。按照王晋新教授的归纳,“皮朗命题”的基本内容为:“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统治,但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上并不具有以往人们所赋予的那么巨大的意义;作为罗马世界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地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垮台和加洛林国家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10]序言3-4“皮朗命题”突破了常规的历史分期,打破了旧中世纪观的束缚,引发的争议至今余响不绝,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开放的论域。“皮朗命题”启发了历史动力学的新兴观点,形成了历史研究的物质生活取向。[11]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的《士兵和农民:7-12世纪欧洲的第一次飞跃》、理查德·霍吉斯(Richard Hodges)和大卫·怀特豪斯(David Whitehouse)的《穆罕默德、查理曼和欧洲的形成》、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的《构筑中世纪早期: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等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对中世纪起源提出了新看法,“皮朗命题”的基本要素也受到了挑战,如克里斯·威克姆将文献证据和考古成果综合在一起,将考察的时空范围放到400-800年的丹麦、爱尔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卢/弗朗西亚、西班牙、意大利、北非、爱琴海的拜占庭心脏地带和西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埃及,写成了《构筑中世纪早期》一书,对持续和断裂的考察更为全面,观点也更为平衡。与皮朗强调罗马世界的统一性不同,克里斯·威克姆强调,在400-800年间,罗马帝国的不同省份在贵族、城市生活和交换等论题上具有各自不同的经验,这些不同的经验随着时间不断变化。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农民社会或者家庭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国家形式发生了最重要的变化,在这些罗马-日耳曼王国,罗马国家不是在五世纪马上崩溃的,而是在400-700年间逐渐瓦解的(不列颠例外)。罗马国家的全部财政基础都瓦解了,政治权力的所有参数都被重建。[12]综上所述,虽然新的看法在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共同构成了更接近史实的关于中世纪起源的“新中世纪观”。
就中世纪文明的兴盛发展问题来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突破了中世纪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和突然”,因此,他提出12世纪就出现了文艺复兴,“在这一世纪,罗马式艺术登峰造极,哥特式艺术萌芽初露,方言文学蓬勃兴起,拉丁经典著作、拉丁诗歌和罗马法复兴,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大量希腊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创立。在高等教育、经院哲学、欧洲法律体系、建筑和雕刻、礼拜仪式戏剧、拉丁和方言诗歌方面,12世纪留下自己的印记”。[13]哈斯金斯的研究开启了对中世纪盛期的研究,此后一大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富有活力的新中世纪。
就中世纪的结束问题来说,克里斯托弗·戴尔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和社会变迁,否定了旧中世纪观描绘的经济衰退和贫穷落后景象,勾勒出建构新中世纪观的基本要素,认为“新中世纪可以归结为一个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时期,它经历了13世纪的商业化进程,它形成于14世纪危机的冲击,提升了适应变迁的能力——削弱的贵族,四处流动且较少受到限制的农民和生机盎然的工业和城市。这一时期的许多特征,从家庭结构到耕作方式,与盛行于16、17世纪的极为相似”。[1]40这样,戴尔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转型问题引发的结构性变迁,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从而将中世纪结束问题设定为一个开放的讨论平台,呈现出全新的学术样态。侯建新教授和龙秀清教授总结了近二十年英国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向,认为在农民与市场、城市化、农民日常生活、转型等重要问题上,都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的研究不仅改变了中世纪的面相,也使得农民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4]
二是新中世纪史学拓展了研究对象,将旧中世纪观没有关注的对象都纳入到新中世纪观聚焦的内容,从而使新中世纪观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当今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方兴未艾,后现代方法耳目一新,对史学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后现代史学极大地开阔了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视野,推动创立了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②威廉·帕登(William Paden)认为“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15]91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和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Gabrielle M.Spiegel)认为,新中世纪学在三个方面对中世纪进行了再发现,一是女性史和性别史的出现,从而使得学术关注点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的、家庭的和身体的领域;二是新文化史兴起,引发话语研究,历史学变成一种知识考古的形式;三是在语言转向的影响下,出现了把文献作为文本而不是资料来解读的转变,新中世纪学“不再是一门事物和行为的科学,而是话语的科学;不再是一种事实的艺术,而是事实的编码”。[16]694-697新中世纪学关注的内容也转向对异端的镇压、犹太人、犹太教-基督教关系、犯罪、儿童、大众文化、同性恋和其他边缘群体,曾经边缘化的主题成为新中世纪学关注的中心:乱伦、受虐狂、异装癖等等,新中世纪学还包括许多怪诞的主题:死亡、脓汁、传染、污秽、血液、落魄、屈辱、阉割、痛苦和尸检。即使在传统的封建研究领域,也开始逐渐强调暴力作为驱动封建机器的动力。[16]699-700由此可见,新中世纪学笔下的新中世纪观呈现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复杂多样的形态,完全打破了传统中世纪观的中世纪面貌。
二
在对新中世纪观的三重视野进行了简短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和延伸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新中世纪观之所以会呈现三重视野,与二元思考模式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中世纪意象从一开始就是想象与史实的杂糅。为了确立现代性,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了中世纪/文艺复兴、黑暗时代/觉醒时代、迷信/理性、团体/个人、落后/进步等一系列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17]xi“由于启蒙运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成为常识性话语。在启蒙运动的话语霸权主导下,中世纪就成为线性进步、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中世纪自然地等同于蒙昧无知、落后腐朽。”[15]92
但是在启蒙运动构建现代性的进程中,理性主义也迎来了自己的对立面——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将中世纪的北欧神话、骑士生活等视为构建浪漫主义意象的来源,从而开启了浪漫主义想象与史实的混合。就如同理性主义一样,浪漫主义内部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二元中世纪历史意象。正如以赛亚·伯林指出的那样:“一边是术士巫师,幽灵怪物,壕沟死人,围着中世纪古堡吱吱作响的夜蝙蝠,沾满血迹的鬼魂,吓人的沙哑嗓门,从一道道神秘而可怕的沟壑深谷向你扑来——另一方面,安详有序的中世纪宏伟景象以其比武盛事、传令使者和教士牧师体现了根本不可动摇的内在稳定。”[18]135浪漫主义的这两种不同意象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冲击了那些早期工业文明城市的日常现实。[18]136
在进入后现代之后,后现代主义又一次对现代性进行冲击,但后现代以后现代性来对抗现代性,以对“表象”(representation)的研究代替对“现实”(reality)的研究,[19]以多样性取代统一性,斯蒂芬·G.尼科尔斯(Stephen G.Nichols)认为,新中世纪学是一种对浪漫主义中世纪研究的修正运动,[20]弗里曼和施皮格尔也认为“他们复活了19世纪中世纪学的浪漫主义和反现代的魅惑”,[16]693让新中世纪史陷入了二元对立之中。当然,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张力中,新中世纪观才建构起摇曳多姿的多重意涵,从而让想象与史实的糅合成为新中世纪观的最重要特征。
(二)后现代主义给史学带来全新的分析方法,后现代中世纪史对新中世纪观的形成影响甚大。张乃和教授指出:“后现代影响下的新中世纪学更加强调特殊性,更加关注多样性,更加重视人的思维属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新中世纪学转变到了文化人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21]但是也要看到,后现代给史学带来了碎片化的危机,消解了史实的客观性,史学有被彻底颠覆的危机,后现代甚至已经宣布“历史之死”,[22]201因此,在运用后现代方法建构新中世纪观的时候,更要注意不能将想象无限放大,变成没有史实基础的想象,变成文学。正如法国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所言:“此时此刻,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历史已死’的呼喊固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找寻己身的映照。”[22]208
当然,后现代的新中世纪学虽然试图解构传统中世纪史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但它仍以中世纪命名自身,只在前面冠以“新”的界定,以示与旧中世纪观的差异,表明它仍接受传统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三分架构,没有摆脱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史学范式。况且新中世纪学“通过诉诸于文化‘他性’和拉伸时间并不能抹去或者解决作者/读者关系、真理与表象、作者意图与读者感受等重要争议,对严谨治学者来说,仍在几个前现代领域存在尖锐的挑战”。[17]122因此,追寻和复原历史真相仍是新中世纪学的紧要任务。近年来,邦尼·惠勒(Bonnie Wheeler)主编了“新中世纪”系列丛书,主要是对中世纪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强调妇女史,强调女权主义和性别分析。邦尼·惠勒指出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复原中世纪妇女的历史”。[23]因此,新中世纪观的基础仍然是历史事实。
(三)对中世纪的想象和偏见都是由于对中世纪的复杂史实没有全面了解,因此中世纪史研究只有在宏观和细微之处都得到推进,新中世纪观才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建构新中世纪观也不能完全剥夺想象的功能。一方面,不管是想象的新中世纪观还是基于史实的新中世纪观,都是“一种对中世纪的现代诠释”,[1]17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史学研究虽然不赞成把新中世纪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但想象的新中世纪观从深层次上看,也具有部分历史基础,特别在文学艺术领域,新中世纪观是在部分史实建构起的中世纪意象基础上的再创造,因而丰富了中世纪的意涵,成为西方学术思想和大众文化内在的一部分。抛开意识形态的层面,从学理上看,想象的新中世纪观是西方小说、绘画、电影等文学艺术的不竭源泉。如托尔金作为一名中世纪专家,[24]凭借对古代和中世纪神话元素的掌握,再加上瑰丽的想象力,创作出《霍比特人》、《魔戒》等畅销小说,并成为电影创作的绝佳素材,为没有神话的英国创造出了“英格兰的神话”。[25]另一方面,在建构新中世纪观的过程中,也不一定必须完全抛弃想象。马库斯·布尔(Marcus Bull)探讨了中世纪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史有时竭力突出疏离的形象,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繁忙的漩涡之上。公平一点来看,人们常说,研究历史达到先进水平的好处之一是能让人们看穿存在于公共领域的关于过去的错误观念和半真半假之处。另一方面,学术疏离思想也可能走得太远。如果真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快就会沦落为虚伪的装模作样,严重低估大众文化在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意义。向大众文化开放对你的学术健康并非错误,也无害处。”[26]因此,新中世纪史研究需要在想象与史实的张力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找到一条走出中世纪史迷雾的路径。
注释:
①Otto Gerhard Oexle.The Middle Ages through Modern Eyes.A Historical Problem:The Prothero Lecture[J].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Sixth Series,Vo.9,1999:124;19世纪以来兴起了中世纪村庄共同体的研究,一些人把村庄共同体和城市行会想象为生活品质如自由、平等、友爱的榜样,见Clive Dewey.Image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A Study in Anglo-Indian Ideology[J].Modern Asian Studies,Vol.6,No.3,1972:292.
②“New Medievalism”与“New Middle Ages”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按照王云龙教授的研究,“New Medievalism”历史学论域,应译为“新中世纪学”,在政治学论域,应译为“新中世纪化”,在公共性论域,应译为“新中世纪性”。(见王云龙.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J].北方论丛,2007(5)。)新中世纪学指的是后现代中世纪史学,“New Middle Ages”是指对中世纪的全新看法和观念,因而也包括新中世纪学呈现出的新中世纪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