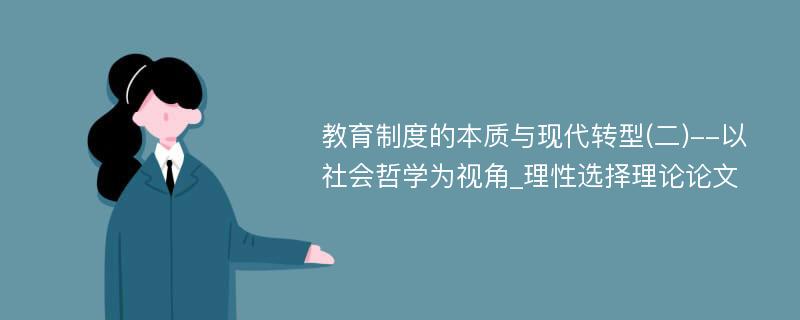
教育制度的本质与现代转型(下)——基于社会哲学的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3X(2004)02-0001-06
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把制度放到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去认识,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转型实质上是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和展示过程。社会转型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它被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的迅速、但又大致稳定的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关于社会转型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以人的发展为主线勾勒出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最具解释力。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精辟地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生产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34](p.104)马克思在此不仅勾勒出了人的发展的基本轮廓,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表明,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从第一大社会形态向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转变,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过程的实质,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随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转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创见性的理论。著名法学家梅因将它表述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35](p.97)迪尔凯姆表述为从“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到“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藤尼斯表述为从“社区”(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齐美尔表述为从“自然经济社会”到“货币经济社会”,[36](p.9)马克斯·舍勒表述为从“休戚与共的社会”到“竞争社会”,马克斯·韦伯表述为从“神魅化社会”到“合理化社会”。[37](p.6)社会转型,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传统社会如何发展自己,步入现代化行列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一个传统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问题。因此,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制度转型,并以制度的进步为突破口和目标,离开制度转型,尤其是社会制度的结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社会转型。另一方面,社会是靠制度来维系的,整个社会结构有秩序的运行都是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规范体系来实现的。正如凯尔森所说:“每一社会秩序、每一社会——因为社会不过是一个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是促成人们的一定的互惠行为;使他们不做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某些行为,并使他们做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其他行为。”[38](p.15)因此,离开制度谈社会转型,只能陷于空谈。从深层的意义说,社会的现代转型,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凸显,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这对新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需求。马克思曾提出并论证了生产方式的客观性对制度发展具有决定性制约作用的观点,他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强调了生产力作为经济制度发展动力的社会存在性,强调了在生产力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具体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分析原理的运行机制决定经济制度的发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9](p.33)从而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制度发展的客观条件。而新制度的出现,就能以其自身的规范功能来调节、限制各种矛盾之间的张力关系。总之,社会转型推动着制度转型,是制度整体性或局部性的转变。
就教育制度而言,教育制度转型的本质是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现代教育制度。与传统教育制度相比,现代教育制度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崭新的教育制度观念。传统教育制度强调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在传统教育制度中个人是消解于集体之中的,诚如沃尔特·厄尔曼所说:“个人为共同体或社会所吞噬,”[40](p.44)或者说传统教育制度只是制约个人教育行为的外在框架,与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无关,它回避了教育制度的主要问题——教育制度与个人的辩证关系。人们的教育选择和教育行为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一种是公共选择和集体行为。在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中,个人理性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公共选择和集体行为中,制度理性起着决定作用。对于个人理性来说,最大化的总是个人利益。与此不同,对于制度理性来说,最大化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集体利益或共同利益。而传统教育制度是崇尚集体教育利益和集体教育行为的,因此,其制度理性有三个缺陷:第一,它不是从教育的实际运行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而是某种先验的东西;第二,它不是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制度理性,而是建立在忽视、抹杀、削弱以至否定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制度理性。即在传统教育制度中,制度理性和个人理性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甚至是处于势不两立、有你无我的状态之中;第三,这种教育制度理性不是有限理性,而是完全理性。三者相互联系,同出一源。这就从根本上扭曲了制度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关系,使得“理性”的教育制度设计和教育制度运行,产生了非理性的教育制度结果。
现代教育制度则强调个人教育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教育制度归根结底来源于个人的教育利益追求和教育利益追求过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理性计算/估算)。现代教育制度是以个人利益为根基的,苏宏章认为:“各种社会制度的实质是利益制度,是为了一定阶级、阶层、集团和一定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不管社会制度的代言人使用何等漂亮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社会制度的这一实质。”[41](p.170)教育制度也是如此,总是来源于个人追求自身教育利益的(有限)理性活动。现代教育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一套竞争教育机会、权利的规则。每个教育活动的参加者,从政治家到一般公民,都通过这个舞台,利用这些规则追求自身的以及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教育制度界定为各种个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经过反复的谈判、争议、斗争而形成的教育契约。当然,现代教育制度并不是仅仅强调个人理性,而是强调个人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协调和统一。现代教育制度其实就是“N人博弈的均衡解”,[42](p.51)是博弈参加者多次博弈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博弈的参加者由不能控制他们的环境变成可以控制他们的某些环境,使选择合作的策略比选择不合作策略的预期收益要高,这样无疑可以改变个人的理性策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的反论,从而使个人理性和制度理性得到协调和统一。同时,现代教育制度并不是仅仅强调个人教育利益,而是强调个人教育利益和公共教育利益的相容性。现代教育制度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制度结构,既能为个人提供比较巨大的教育利益激励和比较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也能够为人们建立比较有效的教育利益约束和教育行为规范,从而在个人教育利益与公共教育利益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按照诺思的观点,“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p.225-226)这无疑表明制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判断和规定,它具有超出个人理性的力量,它对约束个人理性,维护和实现集体理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已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按张宇燕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因为希望别人都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实乃理性人之本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搭便车’”,所以“不管个人如何精明地追逐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也不会自发地出现。此时此刻,只有借助‘引导之手’(a guiding hand),或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才能求得有效的集体结果。”[43](p.169-170)现代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一套标准化、程序化的教育行为规则和社会心理机制。它是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建立的,它把一切教育关系和教育行为都纳入可计算的范围之内。这就使人们的教育行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可计算性。它不仅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测性,弥补个人理性之不足,而且可以在保证自然而有秩序地实现个人最大化教育行为的前提下,增进公共教育利益。托马斯·潘恩曾指出:“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相反,公共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总和。它是所有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个人的总和一样,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40](p.46)个人理性和制度理性求得协调和统一的现代教育制度,可以称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注:关于“自生自发的秩序”,哈耶克认为,亦可用“自我生成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等术语代替。参见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下),三联书店,1997年。)
传统教育制度在对教育关系和教育秩序的维持上,强调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强调权力运行机制的控制;现代教育制度强调要以教育法律等制度形式对教育秩序进行调整和维持,调节形式也由直接干预变为间接调控。也就是说,把原来政府的强制力用教育法律制度固定下来和体现在强制力行使的程序之中。把强制力法律制度化,用教育法律制度的形式来提供教育秩序,是现代社会教育秩序供给文明的标志。因为,在教育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强制力已经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化,不再是一种任意的强制力,而是一种稳定地发挥作用的理性化的强制力。我们知道,教育法律制度是以一系列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主要是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出现的。有了这些教育法律空间,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教育行为后果,都是可以自觉的和可以预测的。所以,教育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引导整个社会进入理性化的阶段,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理性的觉识来作出教育行为选择和对教育行为的后果进行理性的判断,进而使整个社会获得理性化的教育秩序。
当然,在现代社会,以提供教育秩序为目的的社会控制仍有两种途径:基于权力运行机制的控制和基于教育法律制度的控制。不可否认的是,强制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和维护教育秩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仍是有着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强制力的作用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有限,其适用范围与效能也愈来愈小。即便在今天这样一个强制力还是不可缺少的教育秩序保障因素的社会条件下,强制力也必须拥有教育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成为有效力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努力把强制力纳入教育法律制度的框架之中,而是让教育法律制度从属于强制力的行使,为强制力的行使开辟道路或加以欺骗性的掩饰的话,那么这种强制力不仅属于恶的强制力,而且正在引导着社会步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引导着教育步入失败的深渊。
传统教育制度强调不同教育制度间,不同教育价值观、偏好、趣味、利益等的对立,往往是站在一种教育制度立场上排斥另一种教育制度,以一种教育价值观、偏好、趣味、利益去排斥另一种教育价值观、偏好、趣味、利益。对此,伯林早在“自由四论”之中告诉我们:“一元论”(monism)是一种错误而且危险的思考,因为人类的价值理想事实上不只一个,而这些价值理想之间,未必能用同样的标准加以比较,甚至还会互相冲突对抗。[44](p.169-172)传统教育制度往往是特权的制度,它以维护现存教育秩序为首要价值取向,是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和社会身份的分配机制,是实质性的、道德化的、等级化的制度。因此,传统教育制度是不宽容的,不宽容在此意味着独断、专制、压迫、敌视和隔绝。现代教育制度则强调不同教育制度之间的宽容,它关注的主要是教育制度的公共性,自由、自由发展的人对自由、自由发展的他人的宽容。对于个人而言,宽容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精神,表现为对他人平等自由权利的尊重,表现为对他人不同思想与行为的理性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异的尊重。正如萨托利所说:“宽容之为宽容,是因为我们确实持有我们自视为正确的信仰,同时又主张别人有权坚持错误的信仰。”换句话说,“宽容尊重各种价值”。[45](p.53,62)它意味着转换视角,以相容性而非排他性作为处理人我关系的基准。对于教育制度而言,宽容精神主要表现为在制度上对社会不同成员、不同利益集团教育权利的尊重,对有关教育方方面面问题的不同意见平等相待,并提供一个彼此平等对话、交流、商谈,乃至教育思想争论的环境。
就现代教育制度是强制性或权威性的规则体系而言,现代教育制度是最不宽容的,它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并对违反和破坏教育制度的现象和行为给予惩处。然而,就现代教育制度所内含的精神实质而言,它又最具宽容的本性。正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宽容本性,才使现代教育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确立宽容的教育价值、形成自由教育秩序的基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教育制度是形成宽容的教育价值的生成机制。具体而言,现代教育制度的宽容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教育制度作为自由的制度,本身就是宽容的产物,是宽容精神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和展示。在现代社会,“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46](p.309)现代性是教育制度的存在方式,而现代性意味着教育制度存在方式不再是传统教育制度的那种两极对立专制一元的。生活世界与教育交往方式本身是多元的,人类的价值、信仰、立场在本质上也属于多元状态,伯林曾说:“我们必须了解生命事实上可以承载多元纷杂的价值,这些价值同样真实、同样绝对、同样客观,因此无法以某种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加以排序,或根据某种绝对标准加以评判。……这些价值之间,有的会与其他价值互不兼容,因为它们或者由不同社会、在不同时代所追求;或者在同一个社会中,由不同群体所追求。它们可能是整个阶级、教会或种族所追求的理想;也可能在同一个阶级(教会、种族)之中,为不同的个体所信仰。”[21](p.183-184)因此,具有不同价值、信仰、立场的个体彼此在商谈对话中如要达成共识,必须具有宽容精神。换句话说,相互独立的自由主体之间若是没有必要的相互宽容,作为各方共同约定、需要各方认同和遵守的现代教育制度,根本无从产生。
其次,从现代教育制度的形式特征上看,现代教育制度充分体现出教育制度的宽容意蕴。马克斯·韦伯在研究现代制度时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他从合理性的角度,把现代制度界定为形式合理性的制度,从而与以实质合理性为特征的一切古代教育制度(道德、教育习惯、教育习俗等等)区别开来。最能体现形式合理性特征的现代制度是“形式法律”,其基本特点是追求“最精确的、对于机会的可预计性以及法和诉讼程序中合理的系统性的最佳鲜明性。”[47](p.139)它是由逻辑上相互协调的一系列规则构成,通过严格的形式化司法得到实施。哈耶克认为,法律制度只有具有如下三个属性,才能保障自由或人的自由发展。第一,普遍性与抽象性。“一般且抽象的规则,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规则在本质上乃是长期性的措施,指涉的也是未知的情形,而不指涉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这种法律的效力必须是前涉性的(prospective),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48](p.264)第二,公知的且确定的。法律制度是一组规则,它能够为人们划出一个私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不会受到别人的强制,因此,也就是自由的。哈耶克曾引用冯·萨维尼的话说:“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获致一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的界线(the invisible border line),然而此一界线的确立又须依凭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48](p.183)第三,平等。法律制度应平等地应用在所有人身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不对人们作分类的工作,“一项法律可能只指涉相关的人的形式特征,因而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充分的一般性,然而它却仍可以对不同阶层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48](p.226)如果法律不得不作区分时,其原则是什么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亦即是说这种界分的合法性必须得到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某一群体中的人与此一群体之外的人的共同承认。”[48](p.266)马克斯·韦伯、哈耶克对制度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教育制度的宽容特质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教育制度是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是经过各利益集团的反复博弈而形成的一些成文的行为约束,体现在一定的教育法律程序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某种社会权力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或强制执行,不因具体情况的差别而有所变化。因此,教育制度在价值观上具有中立的性质,是对多元教育主体及其教育信念的整合机制,因而在本性上是宽容的。
现代教育制度的抽象性、确定性和平等性,决定了它的非人格化特征,它“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47](p.250)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一般精神是形式主义,它要排除官员在教育事务处理中的个人的偏好、专断和任意,使一切事务都成为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使一切教育行动都建立在功能关系上,具有“精确性、速度、清晰性、持续性、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力和人力消耗等等”的特点,[49](p.214)因而它亦是非人性的。现代教育制度尤其是教育法律制度是一种无差别同一性的制度,它不因执法者或行为主体的不同而变化自己的权威;是一种无差别的同一性行为规范,即它对众人一视同仁,并不因为行为主体的变更而变更自己的作用效力。现代教育制度只针对客观上存在的教育行为和教育事实,而不会因人而异,而且我们在制定教育制度规则时,事先并不知道谁、在什么情况下会使用它们,因而现代教育制度具有对事不对人的“盲目性”和“无知性”。因此,它一方面打破了特殊主义的羁绊、拘囿,可以作为自由主体相互预期的公共机制,同时又使一个人能够充分地保有自己的自由,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解决相竞争。”[51](p.252)
再次,现代教育制度所具有的“对物”性质,内在地包含着对他人的宽容。在现代社会,虽然自由主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合作、相互沟通的中介和渠道,这就是对物的共同依赖。现代教育制度正是通过中介化的物性关系,去调节相互独立和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它一方面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各人都能在自己的自由空间内思想和行动,不受他人的强制和压迫。哈耶克曾对自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personal freedom)的状态。”[48](p.4)在哈耶克看来,自由就是指一个私人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到强制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只有这样一个领域的建立,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是有自由的。但是,这样一个私人领域如何建立起来?什么东西可以保障这样一个私人领域?哈耶克认为,私人领域的建立所依靠的是一组普遍而抽象的规则,也就是法治。因为,法治意味着人人应服从法律并由法律统治。法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法治标定了人的行为范围的基本界限。在这一范围内他们享受充分的自由,法治保护这种自由免遭他人和政府的干预与侵犯。法治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及尊重个人主导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利,把安排个人前途命运的权利交给了个人自己,反对对个人的命运进行外在的(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干预、干涉和控制。法治有助于个人的自治与自我实现,选择生活方式,确定个人的奋斗目标。法治是个人自由的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它保障并增强了人的自主选择能力。
就教育而言,在现代社会,一切正式的、重要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都是法律的,一种教育制度只有取得了法律的形式,或者合乎特定社会的教育法律规定,才能成为普遍有效的教育制度形式。另一方面,由于现代教育制度具有客观的、公共的、形式性等特点,因此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人人都可以利用的社会工具。凭借这一工具,共同依赖于物的自由主体得以扭结起来,得以相互交流和沟通。就此而言;现代教育制度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独立于个人意志的、促进自由主体相互交往的交换机制,在人格化特征上,它是人与人之间获得相互宽容的保障。这是因为,在这种教育制度形式下,人们之所以能够相互宽容,是因为他们需要教育合作,而作为交换机制的现代教育制度又为这种基于竞争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一方面,由于可以交换的只是那些人们相互需要的东西,因此在这种交换机制下,不能交换的私人性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信念、个性被“悬置”起来,归个人自己保有,人们并不会因为他们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拒绝交流,这就使宽容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实;另一方面,这种交换机制又把教育利益、教育信念、教育价值观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需要的人们连接起来,使他们知道自己自由、自由发展的边界,能够各取所需,共荣共存,从而为宽容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传统教育制度是意志、权力;现代教育制度是规则、权利。前者的特征是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后者的特征是自由、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传统教育制度是人治的最好土壤,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人治。传统教育制度更强调教育法律意志的一面,因为制度是根据制度制定者的意志形成的。现代教育制度天然地要求法治。只有人的基本教育权利得到保障、公平的游戏规则和教育规律得到遵守,人们才有可能获得自由、自由发展的机遇。
最后,传统教育制度留给个人的自由和自由发展空间是有限的,现代教育制度不是单独地挤压和收缩主体自由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通过建立稳定的教育激励机制,使教育利益相关者通过相互间竞争促进个人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
(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