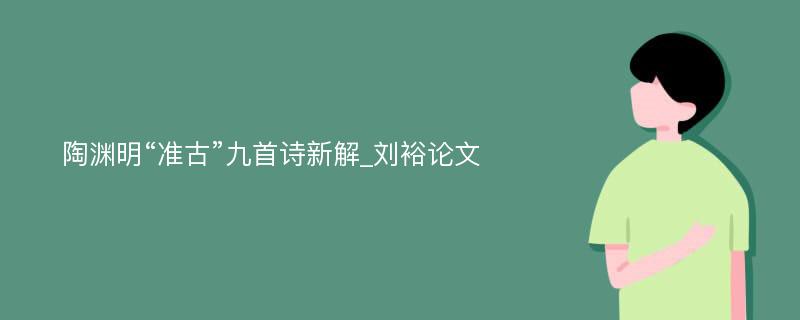
陶渊明《拟古》九首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拟古》九首是陶渊明集中的一组重要诗篇,关于其撰写的时间,逯钦立辑《陶渊明集》认为“九首当作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前后”:王瑶先生则认为“本诗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421)”,总之这组诗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时,论者对此多无异议。在风云变幻,王朝嬗替的晋宋之际,陶渊明写出这九首以“拟古”为题的诗章,当然不是无谓之举。魏晋以来,“拟古”之体向有两类,一类如陆机的《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何皎皎》、张载的《拟四愁诗》等,为严格意义上的模拟古诗之作,其命意、章法乃至标题都不出古人机杼而少有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性质上更接近于一种文学消遣。另一类拟古诗一般没有明确的标题说明所拟古诗的篇目,名为“拟古”,实不过是借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藉以抒发内心的慷慨愤郁之情,性质上相当于咏怀诗,冠以“拟古”之名,往往不过是为了避免在险恶的环境下直言当世之事而触发政治机网而已。陶渊明的《拟古》九首,正是属于后一种类型,其风格韵味上,也很接近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和嵇康的一些述怀诗。
陶渊明颇喜欢创作组诗,如《形影神》诗三首、《咏贫士》七首、《饮酒》二十首、《读山海经》十三首、《拟挽歌辞》三首等等。组诗中各诗诗意之间,也常有或显或隐的联系。《形影神》《咏贫士》等诗。内容结构上的逻辑联系自不待言;即便《饮酒》这一类诗,虽然表面上是如渊明自言“辞无诠次”,但细细阅读分析,同样可发现各诗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断续不定的微妙关联。《拟古》九首的情形,比较有类于后者,细玩九首诗意,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各篇在精神和寓意上的相互联系。亦可以说,这九首诗在顺序上颇有次第,诗人实际上是藉这九首诗,在内涵相互补充的反复叙写之中,展示回忆了生活中的一段经历过程,表现了诗人有关政治社会与人生的感慨。
具体而言,这组诗所回忆叙写的时间断限范围,上及东晋后期世乱方起渊明重新出仕的隆安元兴年间而下至渊明已归田十余年的永初前后,整个晋宋之际风云激荡的历史均包含在内;在叙写的方法上,则是以诗人自己的仕隐之迹及其间的心灵感受为主线,兼及晋末二十余年的政治、思想、人物,从中表现了诗人对纷纭世事的认识与批判。所以,作为以含蓄婉转的艺术手法,结合个人的身世遭际,回顾追忆晋末二十多年的政治历史并慷慨感怀之作,这组诗实际上兼具有抒情诗和史诗的双重性质。
诗人创作《拟古》九首的时间,正如前人所指出的,是在改朝换代的永初元年前后。当时,尽管不少人已将东晋的亡国和刘裕的代晋,视为“高秋凋候,理之自然”(《晋书·恭帝纪》),但政治上的气氛,仍不无紧张和微妙,此点从《通鉴》永初元年所载“宋王欲受禅而难于发言”,只得以“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暗示讽喻臣下劝进诸事中自不难体会,渊明诗所以用《拟古》之名,诗中凡言及时事者也多用比兴隐喻,当亦为此。不过当时刘裕虽然篡位,却尚未及用残忍诡诈的不义手段处置退位的晋帝,所以渊明这组诗,虽不无愤世之意,但涉及当时政治,语气上还是平静和缓,反思多于哀切,和后来的《述酒》诸篇不同。以下即结合史事,试将九首诗的诗意和内在联系作一钩引疏释:
第一首“荣荣窗下兰”: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多谢诸少年,相知不中厚;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此诗以兰柳起兴,而兰柳之意象颇有象征意味。逯注以为诗人是“以庭兰喻本人才德”,以堂前柳“隐喻曾祖勋德名望”,不无道理;从抽象意义上看,茂密繁盛的窗下之兰堂前之柳,亦可喻指一个人尚未受到外物损害的最初的素朴之质和高洁理想。不过诗中何以有“兰枯柳亦衰”的感叹?推想起来,当是隐含着个人经历中的一段将自己的素朴之质投入风尘世路后颇为失意的感受。参之史实,窃以为此诗应是为回忆感慨诗人在动乱初起的东晋隆安三年(399)到隆安五年(401)这段时间告别园林,重新出仕,任职于荆州刺史桓玄府中之事而作。渊明诗文中凡言出行或回归,本常于普通的意义之外,复具人生哲理上的含义,此诗言“行”、言“与君别”、言“出门万里客”、“兰枯柳亦衰”,同样一方面是实实在在地记述了诗人在这次出仕中远离田庐,缠绵人事,奔走川途,以至于形神枯损之辛劳;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一度感受到的“违己交病”,即由于种种自身或不得已的原因而使生活途轨与内心高洁本质疏离的精神飘泊过程的深自反省。从渊明在隆安中所写的若干感叹游宦行役之苦的诗中,我们也能够发现类似于“荣荣窗下兰”的困惑和苦恼,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栧新秋月,临流别友生。……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其诗在思想、情感、句意乃至词汇方面都与“荣荣窗下兰”十分接近;此外象《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的“行行循故路,计日望旧居”、“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句,也都是与之相类的感喟。大抵这些诗都是以出仕为“远行”“别离”“孤征”,对仕途言“倦”言“淹留”言“拘”,而以重返园林为身心之回归。“投冠还旧墟,不为好爵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正是所谓“多谢诸少年”的急流勇退,所不同者,仅在于一写实一寄意而已。
而除此之外,此诗在政治人事方面,似还含有一层很隐微的深意。盖当年诗人于乱世里重新选择出仕,并选择了在晋末一度政治声望很高,似乎有收拾河山的才力气度,且与先世不无瓜葛的桓玄为府主时,无疑怀有很深的政治期待,以为可藉此济世立功,一振祖德家声,功成身退。“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几句,颇能见出渊明出仕时的心境。然而这位府主的作为,却最终令渊明极为失望,意识到如果跟随其走下去,恐有覆家败德之虞。“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的诗句,即可看出渊明是深感桓玄的种种行事,不仅早已亏负其人当初扶佐晋室的允诺,也有违诗人自己选择出仕的初衷,所以“多谢诸少年”二句,或亦隐含有诗人对桓玄这种少年之辈(其实就实际年龄而言,作为桓温幼子的桓玄当时亦只刚过三旬而已)出言不信行为的批评责难在内。
第二首“辞家夙严驾”;
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非复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
此诗所叙写的内容,时间上与前一首诗联接紧密,正如逯钦立注中所言,“此诗是回忆元兴三年东下参与刘裕起义兵事写的”。诗中以汉末史事喻晋末之事,自拟田畴而暗指刘裕为曹操,辞意微妙贴切。按诗人在隆安五年冬因孟氏母去世离开荆州回到家乡守制,在此期间,桓玄从野心渐露到公然篡晋,尽失人心,出身北府的刘裕则由于击败孙恩卢循之功而声名大起。越三年后的元兴三年二月,刘裕从京口起兵讨伐桓玄,三月进入建康,被授使持节、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行镇军将军,渊明即在此后进入刘裕幕中担任镇军参军。渊明这次出仕,除去残存的用世之志,更多的是出于一些复杂莫名的考虑,迫于情势而不得不然。①而刘裕起兵虽有重安晋室之功,不得已入其幕中的渊明对他却深有戒意,在内心里划定了相处的界线,此即是诗中自比田子泰的出发点。《三国志》卷十一《田畴传》载,田畴本是汉末的一位节概之士,为人“好读书,善击剑”,有任侠之风。董卓强迫汉帝迁都长安,田畴曾作为幽州刺史刘虞的使者赴长安探问献帝(此点似和渊明在荆州时曾两度奉使至当时由司马道子把持大权的京城的经历有相类处)。又田畴居徐无山中,已有不仕之志,袁绍父子相继召辟而不行。然而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时遣使征之,田畴立即束装应辟,不待催候,且自言己之用意非他人所能识。此后田畴虽为曹氏掾属,却处处与之分途划界,对曹氏的封赏恩命,也一再坚拒不受。显然,这种态度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传统任侠之士功成不受爵的精神。而陶渊明对田畴的推崇,表明了他在晋末乱世中对士人操守节义的看重以及对刘裕其人的基本观感,也透露出他所以出仕刘裕的深意所在。要之,刘裕之于晋室,既有延祚续命之功,又怀篡政夺位之意,与当年既为汉相又为汉贼的曹操确有很多共同之处,古今也多将他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日正冷眼旁观的北魏拓跋焘崔浩君臣,即有“刘裕之平祸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的讨论(见《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为此,陶渊明对这一位府主的态度矛盾复杂,既出仕其幕下又与之深有隔阂,自不足怪,而如此心情,也正好与当年居曹氏帐下的田畴相通。若仔细体会这首回忆再次出仕之作中的情味并与“荣荣窗下兰”比较,还可以看出此诗情绪上已不同于前一首诗中多少显出的某种受欺于人的怨怼而是表现出相当冷静的自觉与无奈态度。想来是在这两番入仕之间,诗人已目睹了许多仕途上的云雨翻覆,有过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一番历练,在吸取了“兰枯柳亦衰”的教训之后,对世道人心的认识和实现理想的期待上,都已不再抱有过多幻想的缘故。
第三首“仲春遘时雨”: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非石,君情定何如?
此诗在时间和内容上也和前一首诗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所追忆的,仍是元兴三年刘裕起兵之事。如逯注所言,诗中“以二月春雷喻刘裕的二月举义兵”,实际上记述了从元兴三年到义熙元年期间刘裕的重安晋室之功以及诗人内心对此的复杂感受。按刘裕元兴三年二月从建康以东的京口起兵,三月,与桓玄战于江上,击败玄军,进入京城。《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载:“时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虽欲厘整,而科条繁密,众莫之从。”而刘裕入朝后,“斟酌时宜,随方矫正”,又“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这种情形,客观而言,正可谓“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此后,刘裕陆续消灭桓玄一派力量,到次年二月,奉迎被桓氏挟持西上的安帝回朝,三月,安帝兄弟反正。诗中“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的句子,应是隐寓了这方面的含义。不难看出,陶渊明对刘裕当年整饬朝纲,再造晋室的勋绩,始终保持了肯定称许的态度。尽管如此,此诗的末四句仍然十分耐人寻味,它们显示出诗人虽客观上肯定刘裕的功业,但从理智上也开始对自己的出处选择进行审视评判,在政治上的危机尚未迫临之时,已预见到形势的发展而决意归隐了。“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应是与《归去来辞》中的“田园将芜,胡不归”、“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诸句同意;而“我心固非石”二句,有很强的感情色彩,诗人在此用《诗·柏舟》之典,不仅寓含了毛《传》所云“言仁而不遇”的题旨,细忖之,其深意尚应有三:其一是承接前面有关安帝兄弟反正的诗意而来,藉此感慨晋末君臣易位,主昏臣乱的政治局势,也预示了以后仍将是强臣把持国柄,帝室不可复振的局面;其二是对当时官场污浊,世路黑暗,群小纵横,贤人君子正直之士志业难成的深深感愤;其三是诗人在黑暗现实与高洁理想不能相容的情势下不得不作出归隐田园,独善其身的拟择后的多重痛苦缠绵心情以及思绪虽萦折纡曲,去意则决不可回转的态度。
第四首“迢迢百尺楼”: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此诗风格苍凉激越,有浓重的沧桑之感,不仅对前一首诗末的复杂思绪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也是当年渊明最终选择归隐时更深哲学思考的展现。渊明所以回到田园,本由儒道两方面思想促成,即既是理想破灭的愤世之举,也是追求高蹈,复返自然的自觉选择。这首诗主要寄托了渊明后一方面的感慨,但由于时代的烙印,这种感慨无疑也包含了深隐的政治内涵。诗中,诗人登高远望,面对宇宙天地的浩浩茫茫,不禁对古往今来人间社会的攘攘纷争深觉悲悯。在亘古绵延的山川原野间,世上的一切都显得如此短暂和微不足道,那些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功名之士,最终所能留下的,只有累累荒丘,更何况还有人事的盛衰无常,政治的云雨翻覆。“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这是渊明在决定结束他的仕宦生涯时,对尘世功名追逐所得出的结论,而许多历史和现实的教训,深化了他对宇宙、人生若干问题的理解认识,也证明了他的归耕,并非率意的决定。然而,从这首诗里也能看出,尽管对世间的荣辱得失已经表现出了老庄式的超然与觉悟,但身处黑暗之世的诗人,内心依然充满了巨大的难以排遣的孤独,“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的诗句显示出来的心境,正和阮籍在《咏怀》中悲切感慨的“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那样一种深刻痛苦深深相通。
第五首“东方有一士”: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就留君住,从今至岁寒。
此诗颇有嵇康诗清峻旷逸的韵致,它采用寓言的方式,通过对上古高士的景慕之情,来表述诗人归隐之后的实际生活景况和精神世界,展示了诗人在高洁的理想主义信念操守支持下以贫为乐,自足于怀的固穷之志。此诗所描写的高人隐士,虽在思想志趣上兼有儒道两家的双重特征,但从诗中本用贫困长饥,“三旬而九食”的子思故事,而诗人欲追随此人,绝世独立,坚持松柏岁寒之节的叙写之中,不难看出其间依然更多地表现了诗人对儒学价值理想的追求与坚持。当然,由于诗人在玄学方面的不凡造诣,所以诗中隐者在精神上,也不乏道家玄虚之士恬淡、悠然、融然远寄的襟怀。渊明躬耕田园之初尝作《时运》四章,其第四章中有“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的诗句,情味颇与之相类,可以说,此诗在《拟古》九首中,是一篇渊明对自己归隐初期思想心态的归纳回忆之作。
第六首“苍苍谷中树”: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点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己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
有关这首诗的诗意历来有多种解释,论者通常认为或是写渊明不入白莲社事,如汤注:“前四句兴而比,以言吾有定见而不为谈者所炫,似谓白莲社中人也”。作为归田后生活的一番经历,这种阐释自有其道理,其内容放在组诗之中,也并没有什么抵牾冲突之处。不过个人认为,此诗用冬夏苍苍不畏霜雪的“谷中树”起兴,诗意实与前一首诗末的“从今至岁寒”相接,所忆写的一段经历,或许也应与渊明对固穷隐居君子之节的坚执有关。不难想象,在晋末纷扰之世,当渊明抱定固穷之志回到田园之后,由于声名和时势等因素,他的生活并未就此归于宁静,而促使诗人变易初衷的因素与机缘也并非再不曾有过,事实上,就在白莲结社的义熙九年,还有朝廷征他为著作郎的一番举措。此事虽因渊明的坚辞不就而作罢,但当时士人因受到权势的拉拢利诱而不能守其初衷者却不乏其例。其中,有些人尚不过出而讲礼兴学,为统治者粉饰太平;但另有一些人却完全投身政治漩涡,直接进入统治集团,为之出谋划策。渊明的朋辈中,这两类士人正复不少。无疑,当身边友人纷纷改弦易辙之时,渊明亦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劝诱,鼓动他再度出仕,这种劝诱有时甚至会显得很难推托。诸多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对渊明的躬耕之志显然构成了考验,诗人必须要对之作出回答,而这可能就是所以写这首“苍苍谷中树”的原因。本此,诗中“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四句,承接前篇“愿就留君住,从今至岁寒”的结尾,应为渊明自己独立人格的一种象征;其后四句大致是描述了诗人在多方游说之下,欲聊入临淄谈士圈中一游的情形。“厌闻世上语”,或可见出诗人不耐聒噪的无奈心情:“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事为古典,实际上应是暗指晋末一些士大夫在旧鼎将革,而新主大力标榜要“除其宿衅,倍其恩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来“礼辟名士”(《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八年),结恩信以收揽人心之际所表现出的犹如“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陶渊明《咏贫士》其一)那样不甘寂寞趋附新朝的态度。就实有的情况而言,诗人也可能是以“稷下谈士”喻当时一班受朝廷征辟而为新主充备顾问的著作郎等类人物。按《晋书·职官志》载:“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而所谓“撰名臣传”,亦多少有类于“著书言治乱”。这首诗的最后八句诗人似乎表白了自己本已决定离家一游,又抱怀疑深虑,以至放弃此次“出门”的一番内心经历,然而这未始不是渊明的故作狡狯之言。在一个不容许士人对统治者的拉拢表示出公开抗拒的政治形势下,诗人大概也只能以这种带寓言性质的庄谐参半的方式,委婉而坚决的表明自己不易初衷,无意追逐潮流,与统治集团合作的心迹。
第七首“日暮天无云”: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诗中写良辰美景,美人酣歌,然而却又言“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无疑是有很深的寄托。个人以为,此诗的托意并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生良宵不再,盛年易逝的伤感,而是深怀着对那些“稷下谈士”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虞,诗意乃与前篇相接。在“苍苍谷中树”中,诗人固是秉持岁寒之心,不为谈者的夸言所动,得以终守故辙;但相形之下,那些接受权势笼络,不甘寂寞出而应世的士人,虽一时显赫得志,为统治者粉饰天命,如美人乘良夜酣歌。然而一旦统治者不再需要,就有鸟尽弓藏之虞。而况政治波涛险恶,纵横捭阖,瞬息千变,不擅权谋的士人鲜有能在其中长久沉浮者,纵使得势,亦如云间之月,叶底之花,很快就将亏缺飘零。晋末名士如谢混、郗僧施,以至以后的谢晦、傅亮之伦,其命运莫不如是。诗中“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句所感慨的,当然也并非仅是自然方面的盛衰,《通鉴》晋安帝义熙八年载刘毅季父刘镇之闲居京口,有感于刘毅等之作为,对之有“汝辈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的喟叹,从刘镇之此言中,自不难见出“不久”一语在晋末政治风云变幻中常有的实际涵意。此外渊明《饮酒》第十七首中还有“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的诗句,反映了诗人对政治上失却故路,卷入漩涡之士前程的关注,其意也正与此诗相通。而从这首“日暮天无云”开始,《拟古》九首所叙写的视角,已从对往事的回忆完全转到对当世之事的感慨,在写出对世道的忧患之心后,又直接抒发了自己的愤世之意。
第八首“少时壮且厉”:
少时壮且厉,扶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中表现了秉性贞刚的诗人由于身处昏暗之世,知音难觅而感受到的孤寂愤懑。渊明内心,对当时的世道人心一向持尖锐批评态度,所作《感士不遇赋》的序中慨叹:“自真风告退,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而渊明刚直的个性和这种深刻的不遇之感,在此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诸句中,得到淋漓酣畅的表达。然而此诗的义蕴却并不仅止于此,从这首诗的前一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名臣之后的陶渊明在晋宋之际,尽管躬耕畎亩,其实并没有被当世遗忘,如果他愿意在新旧嬗代之时投靠新贵集团,也未必没有进身的机会。然而他却在穷愁老病中始终怀抱着“士不遇”的苦闷,其原因究是如何呢?第七首“日暮天无云”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一个问题,除去对儒学道义原则的坚持和对易代之际知识分子前途命运的担忧之外,渊明更有着类似“璋珪虽特达,明月难暗投”(郭璞《游仙诗》)那样为洁身保躯,以至不得不牺牲夙昔理想并深为之痛苦的复杂心情;此篇中的“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之句,则进一步透露出诗人对刘裕欺世篡位之辈的政治反感和不与之合作的坚决态度,从现实政治层面展示了渊明所以“不遇”的又一因素。而从此角度,这组《拟古》也最终从愤世切入晋宋易代的时事,显示出它们政治批判的本色与锋芒。
最后一首“种桑长江边”: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将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诗中,诗人直接对东晋的灭亡发出感慨。由于东晋政权早已腐朽以至名存实亡,而诗人在哲学上也具有很高的超悟与达观,故此诗言及东晋之亡,却并没有表现出孤臣孽子式的愚忠之情。纵览全篇,诗人运用比兴手法,以桑树托喻晋室,站在历史的高度,痛切深刻地反思了晋室所以覆亡的原因。尤其篇末提出了晋室的“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触到了东晋立国根基不稳,以至百余年来,始终国本不固,国运不昌的问题症结。诚然,在历史上,建国江东,号称中兴的东晋王朝,其政治始终没有摆脱西晋门阀专制下纲纪不立,政风浮竞腐败的覆辙,归根到底,也正是因为司马氏立国在本质上的无道非德,因而不能使国家基广根深之故,而渊明诗中针对此点而发出的浩叹,可以说是非常惋惜和沉痛的。尽管如此,诗人仍然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遭际和故国的盛衰兴亡联系到了一起,诗中“春蚕既无食,寒衣将谁待”的句子,隐隐写出了诗人在故国倾覆后所感受到的那种皮已无存毛将焉附的漂泊无依与失落怅惘。而组诗以这首感慨国事的诗作结,不仅显示了诗人于隐居中对世变的深深关切,实际上也透露了《拟古》九首的真正寄意所在。有关诗人从再度出仕到终于对政治彻底失望挂冠归隐,并从此拒绝统治者的征辟,坚守固穷之节的精神与现实经历及一再对卷入政治波澜的另一部分士人的命运深表忧虞的原因,也从中得到逻辑的解答。
注释:
①袁行霈先生《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论之甚详,可参看。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