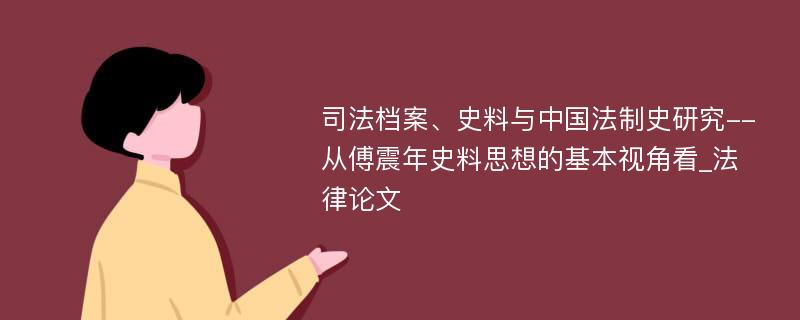
司法档案、史料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以傅斯年“史料学”思想为基本视角的略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视角论文,中国法律论文,司法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76-06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③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④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中的“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誌”[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⑤“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⑥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学界对司法档案为代表的法律史料的“价值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大致是过去法律史研究典范的一种矫正,[36]亦是传统中国“见之于行事”的史学传统的回归。[37]然而一切“旧”的学术典范都曾是“新”的,当对司法档案的研究已为人常见之后,研究者则应关注此一典范所要求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后更深远的问题。
傅斯年是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然经由他的分析典范和前文的简述,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史研究不易似也不可绕开“史观”。在史学、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单纯强调“史料”或“史观”都难免偏颇。余英时就曾说:“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38]故兼美二者才臻化境。当然,在司法档案的使用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甫成风气之初,重提傅斯年的史料学及其所倡的对史料的严格拣择、考据和规范性使用无疑更具意义。这是因为,司法档案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出场,并不意味完全“进步”的结果。黄宗智在大量使用司法档案后曾注意到:“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39]这确属经验之谈。对新的发现和研究,往往在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典范。至于具体运用档案的方法,大致属于“文无定法”之类,只有在长期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也许才能逐渐掌握需得之“法”。
①黄宗智法律史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②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
③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④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
⑤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
⑥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