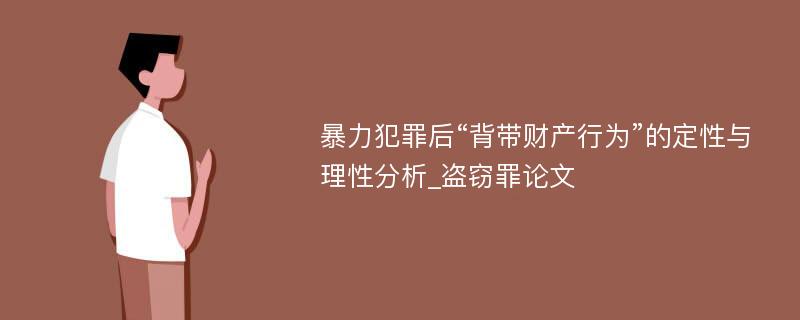
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及理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物论文,性及论文,理性论文,暴力犯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9)01-0036-06
一、问题的缘起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在实施侵犯人身的暴力行为如绑架、强奸、杀人、故意伤害等之后,往往“顺手”捎带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例如:
案例1.甲在一僻静之处,见一女青年乙走来,遂上前抓住乙用力往旁边一树林里拖,欲行强奸,乙奋力反抗,甲用拳猛击乙脸部将其击昏就地进行强奸。奸后,甲看到乙的手提包甩在不远处,捡起后发现包内有手机一部及现金千余等财物,据为己有。
案例2.甲使用暴力殴打乙,将乙强奸,待乙穿好衣服,惊魂未定之际,强行对乙搜身,乙不敢反抗,甲从乙衣服口袋中搜出一钱包,内有1000余元现金及信用卡若干张,非法占为己有。
案例3.甲伙同他人劫持乙到甲临时租住地,并打电话向乙家属勒索10万元,并威胁“不允许报案,否则撕票”。在非法拘禁乙的期间,甲强行将乙所带近千元的手表以及随身携带千余元现金搜去并占为己有。甲等人获得赃款10万元将乙释放。
案例4.甲男与乙男于2004年7月28日共谋入室抢劫某中学暑假留守女教师丙的财物。7月30日晚,乙在该中学校园外望风,甲翻院墙进入校园内。甲持水果刀闯入丙居住的房间后,发现房间内除有简易书桌、单人床、炊具、餐具外,没有其他贵重财物,便以水果刀相威胁,喝令丙摘下手表(价值2100元)给自己。丙一边摘手表一边说:“我是老师,不能没有手表。你拿走其他东西都可以,只要不抢走我的手表就行。”甲立即将刀装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对丙说:“好吧,我不抢你的手表,也不拿走其他东西,让我看看你脱光衣服的样子我就走。”丙不同意,甲又以刀相威胁,逼迫丙脱光衣服,丙一边顺手将已摘下的手表放在桌子上,一边流着泪脱完衣服。甲不顾丙的反抗强行摸了丙的乳房后对丙说:“好吧,你可以穿上衣服了。”在丙背对着甲穿衣服时,甲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甲逃出校园后与乙碰头,乙问抢了什么东西,甲说就抢了一只手表。甲将手表交给乙出卖,乙以1000元价格卖给他人后,甲与乙各分得500元。
案例5.2000年3月1日9时许,被告人计某因借钱之事与被害人林某发生争执进而发生厮打,在厮打过程中,计某用斧子、菜刀等凶器砍林头、颈部,致使被害人林某当场死亡。之后,计某进入林的卧室,搜得人民币5100元及部分衣物后逃离现场[1]。
上述案例中,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这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正确裁判,因此,有必要对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性质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以便刑法学理研究之展开以及满足司法实践指导之需要。
二、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定性之争讼
上述案例中,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暴力犯罪实施完毕后或者暴力犯罪不法状态持续过程中,行为人“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使得对案件认识与处理出现不同看法,具体来说:
在案例1中,对案件的处理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定强奸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理由是虽然实施暴力时,目的是为了进行强奸,但是暴力同时为其当场占有被害人财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其占有财物时,主观上具有利用暴力占有财物的故意,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分别定强奸罪和盗窃罪,进行数罪并罚。理由在于:定罪应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即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把行为的客观危害结果与其对该结果的主观认识和态度结合起来。就该案来说,甲对乙殴打与威胁,其目的在于对乙进行强奸,而非夺取乙的财物,因此,缺乏抢劫的故意。当然,甲的殴打行为客观上确实使被害人乙丧失反抗能力,从而为甲在无阻碍情况下占有乙的财物创造条件。但是,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把整个作案过程的两个阶段硬拉在一起,使暴力既作为认定强奸罪的根据,又作为定强奸罪根据,“一事两头沾”违反了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2]。基于同样的考虑,对案例2的处理也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主张定强奸罪与抢劫罪;另一种意见主张定强奸罪与抢夺罪。
在案例3中,对于案件处理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甲伙同他人劫持乙到甲临时租住地,并打电话向乙家属勒索10万元,并威胁“不允许报案,否则撕票”。甲的行为已构成绑架罪既遂。在非法拘禁乙的期间,强行掠取乙手表及钱物的行为正是利用绑架行为中暴力行为为手段,因此,应定为抢劫罪,并与绑架罪数罪并罚。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定绑架罪和抢夺罪,理由在于:甲在掠取乙手表及钱物时,并没有实施新的暴力或者威胁,将行为人实施绑架时的暴力行为作为后者强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的手段行为的话,违背了禁止对同一行为重复评价的原则,因此,后一行为应定为抢夺罪。第三种观点认为,绑架罪往往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勒索财物可以对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进行,也可以对被害人本人实施,因此,在绑架过程中,强行掠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可以视为勒索财物的行为,没有必要另外作出评价,全案只按绑架罪一罪处理。
案例4是2004年司法考试理论题。对甲趁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定性存在着不同看法,具体来说,一种观点认为,甲乘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成立盗窃罪。因为拿走手表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拿走手表已不属于抢劫罪中的强取财物的行为,即不属于因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压制或足以压制了被害人反抗而取得手表的情形。所以,不能将取得手表的事实评价在抢劫罪中,而应另认定为盗窃罪。另一种观点认为,甲乘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原因在于甲“在丙背对着甲穿衣服时,甲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的行为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甲“在丙背着穿衣服时、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丙的手表仅仅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脱离了丙视线,而不是丙对其放在桌上的手表注意上的失控。在只有甲、丙两人在场的房间内,甲仅在丙背着穿衣服时、乘机将手表拿走,作为智力正常的丙不可能得出手表不知去向的结论的。结论只可能有一个:手表是被甲公然非法占有。由于甲公开索要财物的行为在前,在甲已经对手表予以了高度注意的前提下,甲“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的行为不是秘密窃取,而是公然占有。也有学者从犯罪中止理论出发,认为犯罪中止具有时间性、自动性、有效性、彻底性等特点,要求行为人不仅要消极地放弃继续犯罪,而且还要采取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放弃”是行为人完全放弃了原来的犯罪,从而反映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的诚意和决心。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抢劫罪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成立要件,否则就不构成本罪。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甲乙共同抢劫的目的在于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甲“将刀装入自己的口袋”的行为只能视为对暴力手段的放弃,甲对被害人丙的威胁仍然存在;这种情形不能视为对抢劫犯罪目的的放弃;甲在丙背着穿衣服时、乘机将丙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走的行为,应当视为抢劫行为的继续;同时也表明甲并未彻底放弃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犯罪意图。因此,甲的行为不能视为犯罪中止,应当构成抢劫犯罪既遂。
在案例5中,对被告人计某故意杀人后又窃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计某的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计某杀人后拿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系以杀人暴力手段为前提,是故意杀人行为的后续行为,应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处理,只定故意杀人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计某到被害人家是为图谋钱财,将人杀死后劫取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上述案例主要围绕着行为人出于杀人、伤害、强奸等其他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之后再产生非法占有意图并夺走财物,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这不仅是理论上难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困惑。对上述问题,日本学者以及判例认识不一,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持盗窃说,如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认为,上述行为不是强盗,而是暴行罪·胁迫罪与盗窃罪的并合罪。不过,产生了夺取财物的意思后又进而施加暴行·胁迫,使抑压对方的反抗状态得以持续而夺取了其财物时,成为强盗罪。如果把先前的暴力、胁迫追认抢劫罪的手段,那就扩大了抢劫罪的范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3]。另一种观点持抢劫说,认为行为人虽然没有夺取财物的意思,但出于强奸或者其他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后,继而夺取财物,应综合全案来分析,应该认为有抢劫的故意,应成立抢劫罪。该说又因具体理由不同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利用余势说”,如日本学者藤木英雄提出“通过暴行·胁迫而压制了对方后,又产生夺取财物的犯意,从无抵抗的被害人那里夺取了财物时,只要可以认为犯人是利用基于此前的暴行所产生的不能抵抗状态,借其余势而夺取财物,就应认为是强盗”[4]。第二种是“不作为构成说”,认为由于行为人自己事先实施的暴力、威胁行为,使被害人处于抑制反抗的状态,行为人不排除这种状态,而实施的夺取财物的行为,同直接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夺取财物应该同样看待。第三种是“留在现场说”,认为行为人还留在现场,这本身就是一种抑制反抗的威胁,既然取得财物时存在这种威胁,当然构成抢劫罪。第四种是“持续说”,认为行为人和暴力、胁迫所产生的抑制反抗的状态,在夺取财物时还“维持”、“持续”着,这是构成抢劫罪的实质理由。第五种是“拟制说”,认为上述情形同一般的盗窃相比,可罚性程度更高;如果仅仅因为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后,没有进一步的暴力、胁迫行为,就否定抢劫罪的成立,这会造成处罚上的不均衡性,为此,有必要拟制其有抢劫的故意和行为[5]。日本判例对上述情况也存在不同态度。以强奸目的施加了暴力·胁迫,被害人由于恐惧而交付金钱,行为人接受金钱时,“是利用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恐惧状态,而取得对他人之物的所持,就等于是使用暴行或者胁迫而强取财物,其所为正符合强盗罪”。但强盗罪的定性是以强取财物的意思对被害人施加暴行·胁迫,抑压其反抗而强取财物,鉴于上述判例在解释上过于宽泛,因此,札幌高等法院判例认为,被害人以强奸的目的对被害人施加暴行、进行强奸后,从出于失神状态的被害人那里夺取了金钱的行为,成立盗窃罪。目前,在日本,上述行为认定盗窃罪为主流观点①。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6]:一种观点认为,即使后行的非法占有财物行为未实施暴力或暴力胁迫,也应定为抢劫罪,因为后行的取财行为是借助于先行的暴力或者胁迫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不能、不敢或不知反抗的状态进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杀人后又临时起意拿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主观上具备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和目的,客观上是秘密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侵犯的是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只要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盗窃罪的数额,就应当另行认定构成盗窃罪,与先行的杀人罪合并处罚。行为人的先行行为构成故意伤害,其后行的取财行为若是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或乘乙不知时实施时,应定为盗窃;若趁被害人重伤无力之机当着乙的面公然实施,从主客观统一上看属于抢夺性质。当然,后续取财的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盗窃罪或抢夺罪。总之,对于侵犯人身犯罪后未以暴力或暴力胁迫手段而非法取财的行为,不能定抢劫罪,理由在于这种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主客观特征,而只有在后续取财行为时又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方可成立抢劫罪。刘明祥教授也主张,对于实行暴力、胁迫之后才产生夺取财物之意思的犯罪案件,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总的原则是:夺取财物时若相伴有暴力、胁迫行为,就应该定抢劫罪,否则就可能构成盗窃罪、抢夺罪或做无罪处理。只是夺取财物伴随新暴力、胁迫行为,由于是以暴力、胁迫为基础的,因此,即便是比较轻度的暴力、胁迫(比如某种邪恶的表情、举动等),就能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效果,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手段[7]。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出于其他目的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之后临时起意当场占有被害人财物,即使该暴力在客观是为当场占有财物提供了方便条件,对后一行为也不应定抢劫罪[8]。
三、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理性分析
(一)对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认识
引发刑法学者和实务界对上述案例产生不同见解,主要在于对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认识产生歧义所致,因此,欲解决上述聚讼,首先应厘清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性质。
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发生场合有:第一,“捎带财物行为”发生在暴力犯罪刚刚结束或者暴力犯罪不法状态持续期间,前者如在实施强奸、故意伤害、暴力侮辱、强制猥亵等暴力行为之后,捎带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后者如绑架行为既遂后不法状态持续期间夺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第二,“捎带财物行为”发生在暴力犯罪刚刚结束之后,“捎带财物行为”是在“暴力犯罪”行为影响下实施的,即正因为先前的暴力犯罪行为使得被害人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状态下,行为人实施了“捎带财物行为”。前者如行为人采取暴力或者胁迫实施强奸、绑架等行为下,被害人因恐惧不敢反抗或者伤重不能反抗;后者如行为人杀害被害人顺便拿走被害人财产的情况。第三,“捎带财物行为”的性质为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属于侵害他人财产的行为。前者暴力行为通常为侵害他人人身的犯罪行为如强奸、绑架、伤害等行为,这与后者的“捎带财物行为”的性质则不同,如强奸行为后的捎带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如果前行为与后行为相同,则后行为被前行为所吸收,如行为人先实施了抢劫后的“捎带”行为,可视为抢劫行为。第四,“捎带财物行为”并非行为人事前预谋,而是临时起意,因此,行为人对“捎带”行为及其结果认识主观表现为“事后性”。总之,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侵害人身暴力犯罪行为刚刚结束之际或者不法状态持续期间,临时产生占有财物的意图并掠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二)对上述案例中处理意见的评析
在案例1中对案件的处理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定强奸罪和抢劫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这种观点有违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即认为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则是构成犯罪的各种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主观归罪与客观归罪都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相背。《唐律》就有记载:“诸本以他故殴击人,因而夺其财物者,计赃以强盗论,至死者加役流。”《唐律疏议》对此解释为“谓本无归财之心,及为另事殴打,因见财物,遂即夺之。事类先强后盗。故计赃以强盗论,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以先无盗心之故,赃满十匹应死者,加役流。若夺财物不得者,止从故、斗殴法……”,反映出封建法律的客观主义的以结果论罪的观念。对此,民国时期刑法学者赵琛认为:“强迫胁迫与强取之间,须互相连紧,不可分离。倘施暴剥夺人之行动自由后,临时起意,夺取财物,则意思行为各别,未可据以强盗论处。”[9]我国刑法通论也认为,作为抢劫方法的暴力是行为人为了排除或者压制被害人的抗拒,以便当场占有财物而采取的,即必须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联系性[10]。在本案中,甲预谋实施强奸行为并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意图,其占有财物的行为产生于强奸行为实施完毕后,属于临时起意。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暴力行为时其目的在于强奸,而非占有对方财物,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强奸后趁被害人昏迷之际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应属于盗窃行为,而非抢劫行为。第二,如果将行为人后续的劫取财物行为视为抢劫行为,即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或者胁迫行为既为强奸行为又为劫财行为的手段行为,也就是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事两头沾”,这也有违禁止重复评价法律原则。
案例2和案例1有类似之处,行为人先前实施了强奸行为,继而实施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但也有所区别:前者是被强奸后不敢反抗的情况下劫取财物的,后者是在被害人被击昏强奸后劫取被害人财物的。对案例2的处理,有学者主张定强奸罪和抢劫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实施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是否存在着暴力或者胁迫的问题,主张定抢劫的学者一般认为存在着暴力或者胁迫,而暴力或者胁迫来自先前的暴力或者胁迫,对此,我们认为有失妥当。理由在于:行为人先前的暴力或者胁迫行为目的在于实施强奸,非为事后的劫财行为,即使如此,也存在着重复评价行为的危险。我们认为,上述案例2应定强奸罪和抢劫罪。日本学者大谷实指出,如施加暴力使被害人难以反抗后,对被害人说:“有钱没有”并伸手在被害人的怀中寻找,取得金钱的场合,因为是在抵抗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的情况下实施的,因此,该行为可以考虑为胁迫[11]。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胁迫,是由先前强奸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新的精神强制,而行为人正是利用“新”胁迫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从而达到占有对方财产的行为,而且,这种新“胁迫”完全在当时的场景下转化为新暴力。正如有学者在分析该案件时指出,正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行为人强行搜身,即使不发出任何语言威胁,也是对被害人的无言威胁,暗示如果被害人敢反抗,必将再次遭受伤害[12]。日本通说与判例认为,出于强奸等其他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抑制被害人的反抗之后再产生不法意图并夺走财物定盗窃罪的主张,我们不敢苟同。通过以上对案例1和案例2的分析,我们知道,行为人在实施强奸等暴力行为后,继而实施劫取被害人财物行为的定性,可能构成盗窃罪,也可能构成抢劫罪,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具体判断。日本通说与判例一律按照盗窃罪处理,有失偏颇。
对于案例3中三种处理意见,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混淆了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罪与抢劫罪都以取得财物为目的;在客观上都可以表现为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在侵犯的法益方面,两者表现为同时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因此,两者具有近似性。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绑架罪是以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方法,并以被绑架人的安危为要挟,勒索财物行为的指向对象为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人,即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而不可能是被绑架人;抢劫罪则一般不表现为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而且其要挟的人及劫财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具有同一性。第二,绑架罪由于是将被绑架人作为人质向第三人索取财物,因此获取财物的时间不可能是绑架行为实施的当时,也一般不可能是当场获取财物。而抢劫罪只能是当场及在暴力、胁迫行为实施的当时劫取财物。此外,两者的犯罪主体、犯罪既遂标准、犯罪侵害的客体均存在不同。在案例3中甲在绑架罪既遂后不法状态持续期间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第三种观点并不正确。在案例3中,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即定抢劫罪正确,但不同意定罪根据,理由同前,在此不再赘述。
案例4的标准答案是,甲乘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应定为盗窃罪。尽管如此,有不少考生认为对甲的行为应作通盘考虑后,定为抢劫罪。我们认为,对甲趁机拿走丙手表的行为定为抢劫罪有所不妥。理由在于:首先,如果全案定抢劫罪的话,则甲持刀强制猥亵丙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呢?其次,从整个案件过程来分析,被告人的话语以及收起刀的行为,是在没有外在强制的情况下,行为人单方面中止自己的抢劫行为,应属于抢劫中止。再次,被告人持刀威胁被害人先前目的在于抢劫,而后持刀威胁目的在于强制猥亵。因此,从行为发展过程来看,甲的行为由先前的抢劫故意转化为事中的强制猥亵的故意,如果还是按照抢劫罪定性的话,则有主观归罪之嫌,即将事前故意当做事中故意来处理。最后,盗窃具有窃取特征,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标准,而不应以被害人主观判断为标准,在本案中,只要行为人在拿走手表的行为时认为采取的是秘密的方式进行即可,而不应以被害入主观感受为转移,即便丙当场发现了甲拿走手表,也应认定为盗窃。因此,通过对全案的分析,我们认为,对甲的行为应定为抢劫罪(中止)、强制猥亵妇女罪、盗窃罪。
在案例5中,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虽指控计某杀人行为,但对其搜走被害人数额巨大财物的行为,未指控为盗窃罪。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二审、复核法院在审理中不宜直接增加此罪名的认定,所以本案最终维持了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罪名的指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的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此规定表明了,抢劫罪的手段可以是故意杀人,但有所限制:“为劫取财物”。从时间上看,行为人劫取财物目的在前,故意杀人的手段在后;从手段与目的关系来看,故意杀人的手段服务于抢劫财物的目的,是为排除在劫取财物时来自被害人的反抗。因此,如果行为人因他故实施了杀人行为,尔后临时起意取走被害人财物,行为人的先前杀人行为与事后的取财行为之间并无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则不能认定为抢劫罪,只能分别定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在本案中,被告人计某到被害人林某处是为了借钱,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具有抢劫财物的故意和目的。当其遭到被害人的拒绝和责骂后,双方为此发生争吵、厮打,进而将被害人杀死,既非预谋杀人,更非劫取财物而预谋杀人,其杀人行为不是劫财的手段,也不是为劫财排除妨碍。计某在杀人后取走被害人财物不应定抢劫罪。因此,第三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此外,被告人计某杀人后又取财的行为是先后实施不同的犯罪故意支配下的两个独立的行为,而不是杀人行为的一部分,不能被杀人行为所包容或吸收。因其侵犯的是不同的犯罪客体,应分别定罪,数罪并罚。本案只定故意杀人罪有失准确、全面,与罪责原则相背离,因此应另定盗窃罪。
(三)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分析路径及结论
对于侵犯人身暴力犯罪后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定性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贯彻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后行的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符合什么罪的构成要件就定什么罪,而不能一律定为抢劫罪。具体分析的路径为:首先,判断行为人先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状态:是不敢反抗、不能反抗还是不知反抗;其次,判断行为人先前侵犯人身的暴力犯罪是否给被害人形成新的“威胁”并判断是否为行为人在夺取财物时所利用;再次,判断后续夺取财物的行为方式,是公然夺取还是秘密窃取,是否符合抢夺罪或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对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的定性,具体分析如下:
如果行为人先前暴力犯罪行为抑制了对方的反抗,被害人不敢反抗(仍然有反抗能力)从而形成新的“胁迫”,并为行为人所利用,公然夺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应以抢劫罪论处。
如果行为人先前暴力犯罪行为抑制对方的反抗,但是行为人并没有利用先前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新的心理威胁,而是采取秘密窃取方式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数额较大应定为盗窃罪;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不构成盗窃罪,案件只认定为先前暴力犯罪,后续取财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对待。
如果行为人先前暴力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如重伤倒地不能动弹),行为人当着被害人的面公然实施取财行为,如果“数额较大”的,则构成抢夺罪,如果取财行为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案件只认定为先前暴力犯罪,后续取财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对待。
如果行为人先前暴力犯罪行为使对方不知反抗(包括被害人昏迷或者死亡),行为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数额较大的应定为盗窃罪;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后续取财行为作为量刑情节来对待。
四、结语: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也在于逻辑
感受到时代需求、流行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论是公认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事们所共有的偏见,在决定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比演绎推理影响更大。鉴于此,美国法学家和大法官霍姆斯发出这样感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13]诚然,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可见,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分析暴力犯罪后“捎带财物行为”性质时所应秉持的基本原则与理念。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作出理性的分析,并指导司法实践。
注释:
①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大谷实等也持相同观点。参见[日]西田典之著:《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22页;[日]大谷实著:《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3版,第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