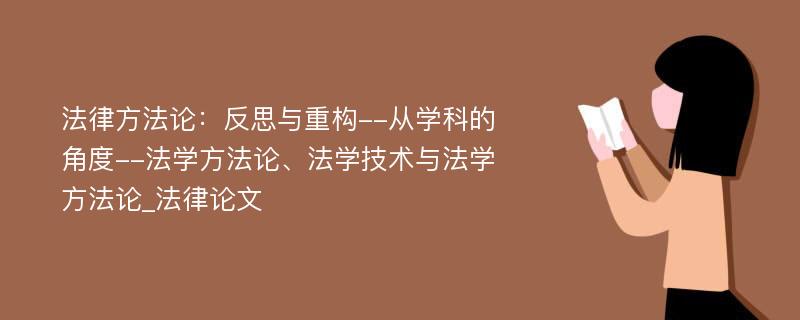
法律方法论:检讨与重构——以学科为视角——方法、技术与法学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法学论文,视角论文,重构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
方法、技术与法学方法论
胡玉鸿
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胡玉鸿,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学院博士生。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法学方法、法律方法以及法学方法论的讨论业已成为一种时髦。然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区分不同的概念是其前提,因为只有在概念明晰、范围确定的情况下,才会有研究上的同质性,也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平台。
在国内,对“法学方法论”一词原来有着较为明晰的概念框定,即将“法学方法论”视为在哲学意义上对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科学说明。就这个意义而言,“方法论”隐含着前提假定、立场指称、程序设计与科学说明的内容,构成“方法的方法”。然而自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的《法学方法论》以及德国学者拉伦兹的《法学方法论》引入大陆以来,“方法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蜕化成一种法律适用的方法,诸如法律解释、利益衡量、漏洞补充等,俨然成为了“法学方法论”的主干。
然而这样的理解是存在问题的。将法学方法论等同于法学方法或者法律方法,一方面使法学方法论降格到具体研究方法的层次,由此冲淡了方法论的理论意味;另一方面则仅突出了研究法律适用方法的重要性,使法学研究有可能演变为规则研究、技术研究。我们知道,就法学方法论而言,它必然在两个方面与具体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不同:一是法学方法论必然含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也就是说,法学方法论是一种主体意识非常明确的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律适用方法的体系建构。例如,自然法学派采用“价值分析”的立场,以公平、正义等“应然”观念来解构、批判法律制度,从而使“法律应当是怎样的?”成为一种立论的根本与分析的基点。同样,规范法学与社会法学则以实证的态度,(注:可以将规范法学与社会法学同视为实证法学,只是两者在“实证”的内容上有所差别。就规范法学而言,它是将法律规范视为一个完整的逻辑自足体,由此强调“规范内”的实证;但在社会法学看来,验证法律良善与否的标准并不在法律规范之内,而是在法律规范之外,因而必须将成本、效益等概念用来分析法律的正当性与完备性。)分别从规范的角度与社会的角度来证成法律的存在原理。两者共同的观念,都认为法学研究必须剔除道德、宗教的因素,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学真正成为科学。所以,就方法论而言,规范法学与社会法学标榜的是“价值中立”的价值判断,然而在实质上,它们仍然含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例如规范法学派对“基本规范”的预设以及社会法学派在“社会利益”上的偏爱,都难以证明它们真正做到了“价值中立”。二是法学方法论必须面对“人性假定”这一基本问题,而具体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则无须理论上的“负累”。法学方法论在严格意义上就是为法学研究找到一个基点、一个分析的逻辑开端,而这些又都只能从“人”本身进行追问。法学研究的终极目的,说到底,就是解决人与法的平衡问题,或者说,人如何适应法律而法律如何符合人性的问题,所以,法学方法论的路子是围绕如何建构“人的模式”而进行的。同样以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为例,自然法学派假设的人是“自然人”,即不依赖于国家、社会而先于国家和社会的生命个体,以自然权利的负载而进入政治社会之中,同样必须以自然权利的维系来检验国家、法律制度的合法与否;规范法学派则以“制度人”的假设切入法学研究的主题,将人定位为服从国家、尊重法律的法律主体,因而其主权、命令、制裁三位一体的法的定位才无懈可击;社会法学派则以“社会人”作为人性的基本预设,将人类的同感、克制、公益精神作为人的本质特性,因而要求人们服从社会利益而保障社会幸福才是那样的自然。总之,没有人性预设的方法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此而言,“方法论”与具体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后者只需在规则、技术的层次上解决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和如何制定、适用法律的问题。
“法学方法论”作为法学研究中方法的总体架构与体系,在其之下又可以分解成两种具体的、技术的方法:一是法学研究方法,也即学界常言的“法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这类方法是就法学的理论研究所采用的技术性方法,诸如我们常说的比较分析法、社会调查法、历史考察法、经济分析法等,其目的在于通过上述方法的使用,为法学理论的提出、检验、叙述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以使“法学理论”真正拥有一般性、抽象性、客观性、开放性、可检验性等外在特征,从而加强理论的解构力量与说服能力;二是法律生成与适用的方法,即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如何通过技术性的手段而得以成立,以及在实践中面对具体的个案如何适用。
就法律生成而言,它自然不是用方法或技术所能概括的,因为法律生成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关联着法律的内容与调整范围。然而,立法中必须有着成体系的“立法技术”,这是为了保证法律或法典前后一贯、逻辑严谨的必需规则。同样,习惯、风俗、价值理念认可为法律规范,法官通过解释创造新的法律,以及判例通过“识别”而与原有的判例在原则、对象、调整手段上的差异问题,也可以归入“立法技术”一类。只是由于这些规则的形成大多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因而常常作为司法方法对待而已。
就法律的适用而言,在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都存在着如何将法律的规定适用于具体的个案问题。只不过行政执法虽然也有着自己特有的个性,但就公正地作为裁判以及令人信服地相信裁决而言,其与司法十分类似。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迫行政官吏像法官一样思考和行动,否则,其裁决就有可能被法院所推翻。就此而言,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手段与行为方式基本类似。这些,国内学者统称为“法律方法”。(注:当然也不独国内学者如此。例如德国学者考夫曼即以“近代法律方法学说的历史发展”为题,阐述了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律方法的演进问题,而其内容主要也是法律发现、推论、填补漏洞等技术规则的阐述。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推理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6.)但笔者认为,与其称之为“法律方法”,倒不如用“法律技术”概括更为适当。原因在于:
第一,就语词本身而言,“技术”更为明晰地体现了司法的性质与特色。严格说来,司法的过程是一个由法律专家根据特有的专业规则处理事物(案件)、产生产品(判决)的活动。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就意味着法律的执行是一项非常人所能胜任的事业,它需要特有的素质、学说和经验。而“方法”,人们则多在认识论上使用之,意味着对事物的认识所必须采取的基本立场与基本态度。(注:例如经斯宾诺莎概括的笛卡尔“方法论原理”就包括四条基本准则:排除一切成见;找出能够用来建立一切知识的基础;发现错误的原因;清楚而且明晰地理解一切事物。参见:[荷兰]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M].王荫庭,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就此而言,“方法”一词过于宽泛,无法揭示司法特有的专业性质。实际上,即以国内学者常常言及的“法律职业”而言,也可知两词的使用场景。与“职业”相连的是“技术”而非“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法律职业技术”这个语词,但很难理解什么是“法律职业方法”。
第二,就司法本身而言,“方法”与“技术”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内容:(1)就个人的行为而言,“方法”可以指称法官对法律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对于解决案件这一活动来说,“方法”是法官为何会作出该种判决的认识前提,而“技术”则是在面临案件的解决之时,采用的具体解决纷争的手段与技艺;(2)就法官与同行的关系而言,由于“方法”主要是一种主体性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官会有对法律的不同认识,所以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分析问题的习惯自然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作为“技术”来说,则意味着它是相对客观的,因之可以成为“法官社会”通行的准则。正因如此,“方法”主要与个人有关,而“技术”则与社会有关;(3)就司法决定的作出而言,“技术”代表着一种相对固化、稳定的行为准则,是约束其他法官行为恣意的有效工具。例如“判例识别技术”,一方面要求法官必须遵循先例,另一方面则要求法官必须对先例与本案在事实、法律上进行比较,在此为法官所承认的规则就可以成为为法官所遵奉、同时又为社会所检验的行为准则,而“方法”虽然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然而它主要是用来认知法律本身的。
第三,从约定俗成的角度而言,“法律技术”一词早就在学界使用。例如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就有“法律技术”的提法,并将其解释为:“为达成一定政策目的而限制,或扩张侵权责任时而采的手段”,并将“法院如何解释适用法律,以促进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作为技术之一(王泽鉴先生的《侵权行为法》一书中,由于是从民事侵权角度研究法律政策与法律技术的关联问题,因而其定义主要是就侵权责任而言)。[8]国外辞书中,著名的《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其解释为:“法官和律师的实践技能,以及利用和应用他们的知识决定争议或得出其它希望结果的手段。每一法律实践的领域都有一套实践技能和方法。在决定争议中,有关的技术是:拟具诉状、取证、解释立法,以及掌握先例。”[9]由此而言,法律技术代表着法律适用中的实践技能,也是从事法律工作所必需的基本手段。如果将法律实践的过程进行划分,那么,它明显地包括两个基本的部分:一是知识的应用;二是技术的采纳。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它是通过司法界约定俗成的技术规则,寻求解决案件的方法或手段的一种必经流程。以此而言,法律技术保证了法律职业的某种“精英”性质,将未经此种“历练”的人排除在外;同时,它也有利于职业共同体相关传统与价值的建立与维系,从而形成法律权威的社会基础。
有关法律技术的具体内容,笔者将之分为八大类:一是法律渊源识别技术,即在规范重叠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个案最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的技术问题;二是判例识别技术,即如何运用先例,以及先例与现在的案件有矛盾时如何处理的技术问题;三是法律注释技术,即如何明确法律条款含义的技术规则问题;四是法律解释技术,即阐明法律意义的方法与准则;五是利益衡量技术,即如何确定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位阶上的优越性的技术;六是法律推理技术,即在个案解决中如何进行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技术问题;七是法律漏洞补救技术,指如何通过类推、目的限缩与目的扩张技术解决法律中业已存在的漏洞问题;八是法律说理技术,即作为官方决定的一方如何将其裁决理由告知相关当事人以获得对方的理解问题。(注:有关八类技术的具体内容,参见:胡玉鸿.法律原理与技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9.)考虑到“事实”与“法律”在司法场合中的两分,因而有关事实的采证(即通常所言的“证据规则”)技术不纳入法律技术的范围之中。
收稿日期:2002-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