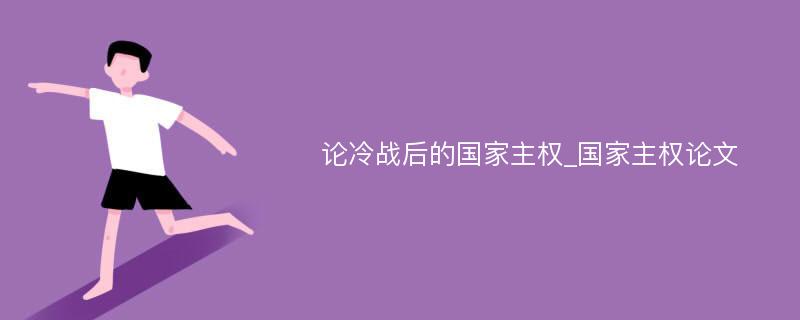
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国家主权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将冷战结束视为本世纪的第三个转折点。虽然国际法学界尚未在本学科作如此分界,但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新现象,的确给国际法学者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有些欧美学者甚至认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权概念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谨慎地重新考虑”,〔1 〕即:传统的主权概念亟待更新。
国家主权这一根深蒂固的国际法概念,为何在冷战结束后受到冲击?如下文所述,冷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某些新特点似乎是这些“冲击”的因素或源头。
冷战后东欧国家的分化与组合给国家主权带来了挑战。两德的统一、前苏联的解体、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分为二和前南斯拉夫的瓦解,使一些欧美学者得出如下认识:国家主权在冷战后受到民族主义趋势的严重影响;传统主权概念不再适应新的时代;主权已不再为非国家莫属的概念,而应以民族为其所属者。
冷战后国际凝聚力的明显增强对国家主权产生了挑战。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其它国际合作领域,能够较快地形成共识和决议,并果断地采取相应的行动或措施。这些行动或措施在过去的冷战时期则往往难以实现。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今的国际组织越来越频繁地撞击和侵蚀国家主权,甚至在某些方面实际行使着主权权力;因此,冷战后时代的主权概念至少应将国际组织包括在其内。
冷战后国际法的纵向发展尤为突出,从而对国家主权产生冲击。冷战后时代给国际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结果势必加速国际法的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继续朝着横向的领域延伸,另一方面纵向地深入到过去一直属于国家主权管辖的领域。于是,有学者断言:国际法将从“国家间法”发展为“世界人民法”。〔2〕
上述所谓的“挑战”或“打击”,概括地讲,涉及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国家主权与国际组织和国家主权与国际法三组关系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组关系均属国际法基本理论中的重大课题。因此,本文也许只能触其表面现象而难以及其深层问题。
一、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
在20世纪的后半叶,国际社会最基本的成员——国家,先后经历了两次巨变。第一次从60年代开始,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造成世界范围内殖民帝国的彻底瓦解。第二次从80年代末开始,在短短的几年内从原有政治领土分化出一系列新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两次浪潮的性质与特征以及所持续的时间大相径庭,但它们均与民族自决这一国际法原则密切相关,从而均对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冷战后的这次巨变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较大的震动,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的学术研讨热潮。〔3〕
的确,尽管殖民体系在冷战时期已经崩溃,但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倾向仍十分明显。冷战后主权国家的分化涉及的因素固然错综复杂,其中许多问题与国际法律密切相关,需要我们进行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例如,经联合国宪章宣称后由一系列联合国文件确认并完善的“民族自决”原则,是否适用于既存主权国家的民族、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或问:现行主权国家内的民族、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是否可援引民族自决权从该主权国家中脱离并建立新的独立国家?又如,民族自决原则,特别是其中所含的分离权,是否与国家主权相矛盾?
(一)谁有权“自决”
“民族自决”从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为一个法律概念,进而上升为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属联合国的贡献。联合国宪章第一(2 )条明确地将“民族自决”列为其宗旨之一。其后,联合国从60年代开始,先后通过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逐渐将“民族自决”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稳定下来。1960年12月14日,联大通过的第1514(XV)号决议,〔4 〕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宣称“所有民族”的自决权。但是,由于联大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当时西方国家的反对,“民族自决”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尚有争议。1966年,联大又通过了两个人权公约,〔5 〕其中第一条再次载入了“民族自决”。值得强调的是,这两个文件不仅用条约的法律形式予以表现,而且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更重要的是,1970年,联大第2625(XXV)号决议将“民族自决”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载入其中,且获一致通过。〔6〕不仅如此, 联合国国际法院先后在纳米比亚问题和西撒哈拉问题的两项咨询意见中明确断定:民族自决不仅仅是联合国主张和促进的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且是一项可主张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安全的权利。〔7〕
至此,尽管民族自决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已不再构成争议的焦点,但在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或谁有权主张“自决”这一问题上,各个国家及国际法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有关的联大决议宣称“所有民族”(all peoples)均有权“自决”,但从这些文件的上下文来考察,有权“自决”的民族限于三种类型:(1)殖民地民族;(2)受殖民和外国统治的民族;(3)受殖民剥削的民族, 最多还包括受种族歧视的新殖民统治的民族。总之,联合国确立的民族自决权只适用于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的民族以及实行新的殖民统治(如过去的南非)下的民族,不适用非殖民地之现行国家内的民族,因为:这些联合国文件均谴责旨在部分或整个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8〕
从民族自决演变为一项国际法原则的历史背景来看,上述观点似乎合乎逻辑,而且得到联合国有关实践的证实。例如,《非殖民化宣言》指出:“任何旨在部分或整个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均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国际法原则宣言》也明确宣称:“上述各款之规定(指民族自决的规定——笔者注),均不应解释为授权或鼓励整个或部分分裂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前联合国秘书长也曾经断言:“至于一个成员国的特定部分的分离问题,联合国的态度是明确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从未接受、也不接受,而且我坚信它将永不接受一个成员国的部分脱离的原则。”〔9〕
另一种观点则坚持,民族自决的含义,从其载入联合国文件之日起就超出了殖民地民族的范围,因为这些文件所指的是“所有民族”的自决权,而且有史料为证。印度政府在批准两个人权公约时曾经提出一项保留,即:自决将仅被理解为“在外国统治下民族”的一种权利。为此,当时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荷兰明确表示不同的意见。〔10〕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国的观点已成为主流派,并得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支持。后者在有关人权公约涉及民族自决的评论中明确表示:自决是所有民族的权利。〔11〕
虽然,民族自决权的广义解释已得到广泛接受,但是,自决权是否适用于一个国家内的土著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则是近年来联合国内外争论的一个新焦点。联合国土著居民工作组(The United Nations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WGIP)一直致力于《土著居民权利宣言》的起草工作,但迄今仍未拿出能被各会员国代表所接受的文本。分歧的根本在于:宣言中是否应明确规定土著居民的自决权;如果承认土著居民的自决权,其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工作组在1992年第十次会议上出示的宣言草案中曾写进了自决权,其文字表述为:“土著民族依照国际法享有自决权,并据此可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和组织结构,以及自由地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这一权利的组成部分为自主权和自治权。”〔12〕按照工作组主席兼报告人的解释,上述措辞的自决权是指其内部方面,不含有鼓励组建独立国家的任何意图。尽管如此,许多欧美学者和有关的机构并不认为上述解释能自圆其说,因为从宣言草案文字本身来看,土著居民自决权既包括对内自决权(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又含有对外自决权(externalself-determination)。〔13〕
就各国政府的立场而言,虽然一般都赞同土著居民有一定的自决权,但是尚无一个国家正式接受土著居民的对外自决权。因此,有些国家认为《土著居民权利宣言》中的“自决权”仍需缜密考虑;另有些国家坚决反对宣言载入“自决权”条款;还有的国家则主张宣言可写入自决权原则,但应将土著居民的此等权利严格限于对内方面。〔14〕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要就自决权的适用范围达成共识尚需时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就民族自决权概括出如下一些基本认识:第一,联合国倡导民族自决权的本意,无疑是为了促进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有权“自决”的主体,首先当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以及受外国统治、奴役或剥削的民族。尽管联合国有关文件的措辞为“所有民族”,但在80年代末之前,民族自决的实际运用主要是殖民地的人民和民族。
第二,国际格局在变化,国际法规范在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里,仍坚持民族自决权的传统适用范畴,不仅不符合联合国有关文件的字面含义,而且无法合理解释冷战后主权国家的分化、组合现象,更不能说明为何联合国还在致力于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自决权之文件的制订工作。
第三,承认广义的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国际法已确立或鼓励现行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享有当然的脱离权。必须明确: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离权,后者只是前者的具体内容之一。当代和未来的国际法,应提倡并协助各国充分保证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的对内自决权,而不是鼓励后者去实现对外自决权(脱离权)。只有这样,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原则才能既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定,又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在处理现行主权国家的分裂问题时,一向持谨慎立场。只是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国际组织的举止难免有武断之嫌,并且已招来越来越多的非议与抨击。
(二)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相矛盾吗?
80年代末以前,由于民族自决权主要适用于殖民地的人民与民族,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很少提出或引起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相矛盾的问题。究其原因,殖民地的人民和民族原来不是宗主国的国民,国际法赋予这些民族行使自决权,成立独立国家,既保证了此等民族充分的自主权和自决权,同时又不影响有关宗主国的主权,更何况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然而,在殖民地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现行主权国家内的民族自决权,则有可能碰撞该国的主权。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早有国际法学者断言:“主权原则从逻辑上排除了自决权。如果国际法要保证现行国家的主权,就不能又同时允许主权在自决权的名下受到侵犯。”〔15〕
其实,民族自决权有其丰富的具体内容。如果一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或部落行使的只是对内自决权,就不大可能危及其所属国的主权,因为这一部分权利(如政治参与权、自治权、自主权等)是在其所属国的管辖之下(依宪法程序)进行并实现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及其政府越是能充分保证其境内民族的对内自决权,其主权的完整性就愈加牢固。因此,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要维护其内部民族的团结和其外部统一的主权,就必须在立法、行政、司法、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确保其少数民族充分享有对内的自决权。当然,如果一个现行国家内的某一民族坚持以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方式行使自决权(对外自决权),其结果势必影响其所属国的主权,特别是领土主权。
可见,并非所有的自决权内容均与国家主权相抵触。真正对主权构成影响的只是自决权的对外一面(脱离权)。脱离权(或分离权)之所以与国家的主权相摩擦,是因为二者均与领土密不可分。维护已有领土的完整是一国主权的首要内容,而脱离权则意味着原来所属国领土的必然变更。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相矛盾之说,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可将自决权中的部分内容与国家主权的抵触,视为整个民族自决原则与国家主权的矛盾;更不可因此得出自决权与主权相互排斥的结论。
国家主权与自决权之间首先应该是一种相互并存的关系。国家主权是国际法首要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只要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分仍为国家,国际法仍主要是国家间法,国家主权原则将永远是这个社会及其法律秩序的核心。国家主权的这一核心地位并不因民族自决权的形成与发展而动摇。民族自决权也并不因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殖民体系瓦解的事实而失去其意义。只要国家管辖内存在有少数民族或部落,换言之,只要国家由多民族所构成,自决权就有其合法的生命力。
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之间还应该是一种彼此制约的关系。虽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但它同时又受其它国际法原则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又是主权者自己所施加的。民族自决权就是诸多制约国家主权的其它国际法原则之一。例如,国家依据主权原则对其境内的一切人具有排他的管辖权,但如果它对其少数民族的统治严重违反基本人权(如灭绝种族),有关的民族就可以行使自决权,从该国分离出来。至于民族自决权受国家主权制约的情形,则更为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决权是以国家主权为前提的。没有主权的国家,就无从谈论民族的自决,殖民体系瓦解后,情况更是如此。更何况民族自决权的实现(特别是对内自决方面)还取决于有关主权国家的准允。即使有关民族在行使脱离权时并不一定非取得原所属国的同意不可,但事实上只有得到国际社会其它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承认与支持的情况下,其脱离权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此外,笔者还以为,在全球殖民体系完全消失之后,民族自决权应该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一个外围规范。在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立主义势力高涨的情势下,正确认识主权原则与自决原则的主次关系尤为重要。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最近所呼吁的“世界社会的目标应该是防止国家的分裂;如果这不可能,也应以对公共秩序造成最低破坏的方式来处理。”〔16〕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协助国家抑制极端的民族主义,保证各国内社会的长治久安,从而赢得国际社会持久的安全与和平。近几年的教训表明:联合国及其它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如何处理这两项原则的主次关系,对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乃至整个全球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
二、国际组织与国家主权
许多欧美学者认为,自90年代以来,国家主权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上述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导致主权国家的破裂;二是国际组织这一新的“帝国”不断地在挖国家主权的“墙脚”。〔17〕谈到国际组织与国家主权的关系现状时, 有人还形象地把主权比作瑞士干酪(Swiss Cheese),〔18〕其中有被国际组织穿刺的形态各异的窟窿。有的把国家主权和国际组织的关系比作一张带有大小不同洞孔的白纸,其中纸好比国家主权,原本是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洞孔则如同被各种全球的和区域的国际组织所侵吞的主权成份。〔19〕
据有关统计,目前由国家或政府创建的国际组织已近2000个,平均每一个主权国家创立了10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而且,除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组织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第三代国际组织——国际组织间的组织(interorganizational organizations)。最重要的是, 国际组织的职权与活动已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是“无孔不入”。因此,从国际组织的发展、影响与作用来看,将本世纪说成是“国际组织爆炸的世纪”或云“国际组织是本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帝国”,并不显得夸大其词。
然而,现代国际组织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不当然构成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同样地,各种国际组织拥有广泛职权和其活动范围不断发展,并不当然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各国不可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处处威胁或损害其主权的国际组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国际组织,特别是象联合国这样的重要政府间组织,行使超越其章程的职权,这就不仅违反了包括该组织的组织法在内的国际法,而且会对国家主权造成损害或带来威胁。这种后果似乎在冷战后的有关国际组织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撞”
与前苏联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不同,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崩溃,不仅一直与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相随,而且先后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不同程度的介入,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共同体等。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在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与行动,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的确发人深省。
1992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当时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该组织中的成员国地位问题。该组织的执行董事会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从而决定停止其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资格;同时还决定:由波黑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等,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该组织中的财产和债务继承者。董事会还为五个共和国确定了各自的份额,并要求每一位继承者在一个月内通知该组织其是否接受所分配的比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决定,与其说是裁定一个主权国家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决定和宣告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存在。当一个国家处于内乱或武装冲突时,并在该国境内少数民族或几个民族纷纷要求独立的情况下,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审查成员国地位的方式作出原国家消亡并承认新国家的正式决定,这在冷战结束之前实属罕见。也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是否超越了其章程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它实质上影响现行主权国家命运之事实却毋庸置疑,更何况当时的南斯拉夫并未宣布解散,而仍在致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即使前南斯拉夫的瓦解已成事实,而且不存在任何国际法上的疑问,也应由五个新成立的主权国家自主并通过谈判协商或其它和平途径来继承前南斯拉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产与债务。
必须承认,在1991年夏季以前,欧洲共同体的立场是尽一切努力维持前南斯拉夫的统一。但是,从1991年11月起,随着前南斯拉夫内部局势的日趋恶化,特别是某些第三国过急承认新独立的共和国,欧洲共同体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其处理前南斯拉夫问题的过程中,“欧洲共同体南斯拉夫会议”(后被“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所取代)的一个仲裁委员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军师”角色。尽管该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咨询意见不仅对欧洲共同体的前南斯拉夫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确立和调整对前南斯拉夫的立场与行动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1991年12月16日,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发布了两项关于承认新国家的宣言,其中一项是关于指导承认前苏联和东欧的新独立国家,另一项则专门针对南斯拉夫。部长理事会还要求:凡是想获得承认的前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应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由后者就有关的申请者是否符合宣言中确立的各项标准发表咨询意见。为此,仲裁委员会还专门制作了“申请表”,并发送到各共和国,要求它们在递交填写后的“申请表”时附上各自的宪法副本和有关承诺的笔录。不久,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斯洛文尼亚均按时递交了各自的申请。仲裁委员会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就发布了其评估意见,即:第4—7号咨询意见。该委员会认为,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完全符合宣言中的国家标准,只不过强调后者的“马其顿”国名不能含有向另一国(意指希腊——笔者注)寻求任何领土的主张。至于波黑,委员会认为:“波黑各民族组建波黑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意愿尚不能断定已完全形成”,并建议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正如一位前南国际会议法律顾问所指出的,委员会的这一建议是一个“毁灭性”的动议,因为波黑宪法中没有全民公决的规定。〔20〕结果,当举行全民公决时,塞尔维亚人联合抵制。塞尔维亚人正是以波黑全民公决违反了宪法为借口,坚决主张成立其独立的国家,从而导致波黑地区战火连绵不断的复杂局面。关于克罗地亚,委员会断定它基本符合国家的要件,但其宪法的有关规定尚待完善。至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委员会于1992年3月18日裁定它已不再存在。最后,对于新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委员会裁定它不是前南斯拉夫的唯一继承者,只是五个继承者之一。
如果说上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的是间接手段(通过审查成员国资格)来干预前南斯拉夫命运的话,欧共体及其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则是赤裸裸地先确立国家的标准,然后审查并断定前南各政治实体的主权前途。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还有一定的组织法作依据,欧共体的举止在法律上则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尽管前南斯拉夫及其共和国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毕竟不是欧共体的成员。所以,欧共体的超常干预没有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组织借口。其次,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它设立仲裁机构来审查和裁定一个第三国及其有关当事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尤其是涉及主权这一重大问题,且事先不征得争端当事国(方)的同意,这在国际法上除了难于逃脱侵犯主权的责难外,是寻觅不到依据的。
尽管仲裁委员会的意见名义上仅与欧共体发生关系且属于“咨询”性质,但实际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咨询意见”应有的能量与作用。后来欧共体及整个国际社会对南斯拉夫问题作出的反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委员会的裁定密切相关。除前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有明显的影响之痕迹外,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对大多数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之独立的即刻承认,以及对个别共和国的延缓承认,都很难说不是受“咨询意见”的影响。
除了前南斯拉夫这一典型事件外,有的欧美学者还将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制裁措施也列入国际组织“硬碰”国家主权的事例。当然,撇开这类行动与措施的国际合法性,单就行动和措施本身而论,它们既然是直接针对有关国家的强制行动,就必须撞击和限制其主权。此外,国际组织在不事先征得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在一国设立“安全区”,无疑也是冷战后直接限制国家主权的强制措施。
(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软侵蚀”
上述“硬碰撞”的显著特点是:国际组织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并不事先征得东道国的同意。国际组织的这种公然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毕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软侵蚀”则司空见惯,而且呈现与日俱增的势头。“软侵蚀”的特点是:国际组织的行动与措施一般均事先征得有关国家或当事方的同意。其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地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在该国暂时行使主权权利。
欧洲联盟是主权权利持久地转让给国际组织的最突出典型。这个由西欧诸国扶植的“帝国”,不仅其内部组织结构形同主权者,而且在许多领域实际行使着过去属于国家的主权权利。从关税、贸易到整个商业政策;从劳动就业、人员流动到社会福利政策;从运输、农业、渔业、竞争到环境与科技发展政策;从司法协助到内务合作政策;从政治合作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总之,从内政到外交,欧洲联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或是排他的,或是与成员国并存或混合的。由于这种主权权利的转让具有持久性,且经国际条约固定下来,国际组织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所行使的职权,如同国家所行使的主权一样具有稳定性。
联合国是国际组织在其成员国暂时行使主权权利最突出的代表。例如,在会员国的国家重建方面,联合国自1988年以来,先后在纳米比亚、柬埔寨、索马里、萨尔瓦多、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南非和前南斯拉夫等国组织和实施国际监督下的民主选举。在上述这些国家中,联合国实际上是行使国家的主权权利,因为:一国实行何种政体、组成什么样的政府、以何种方式产生新政府,历来是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不过,一旦选举结束,新国家或新政府得以建立,联合国就将有关权利交还给相应的国家,并撤出其派驻机构或人员。所以说,联合国以这种方式行使有关会员国的主权权利只是暂时的。此外,有些学者还将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如人权委员会、防止种族主义委员会、妇女权利委员会等,要求会员国政府定期报告和答复有关状况和问题,均看成是“软侵蚀”国家主权的表现,因为这些涉及人权的状况和问题一向也是国家主权管辖的事项。至于有的学者还将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视为对国家主权的“软侵蚀”〔21〕则未免显得牵强附会。
三、国际法的新发展与国家主权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是一种横向的国家间社会。这种平面式的社会结构决定着国际法主要是调整主权国家间的横向关系。尽管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依旧,冷战后时代的国际法仍将主要是一种国家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动向,即:它越来越明显地朝着纵深的方向挺进。国际法不断地向国家管辖的领域渗透,使国家主权管辖的空间持续地缩小。
(一)属地优越权的缩小
属地优越权是国家主权的三大要素之一,表现为一国对内的独立权。其主要含义为:国家在其境内拥有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事物的权力,如制订与通过其认为适合其国情的宪法、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制订必要的法律、实施有秩序的国内社会政策等等。然而,国家的这种对内自主权已被国际法打了折扣。
尽管一国的立宪和政府组成并不受国际法的制约,但冷战后的实践显示:如果一个新独立的国家要获取国际承认,在国际社会赢得一席合法的地位,其宪法还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虽然欧洲共同体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独立所附的条件以及采取审查宪法的做法既不是一般国际法,也非国际习惯法,但是它开创的这个先例,不仅未曾遭到任何的责备或质疑,反而得到有关当事国的认同,尤其是得到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默许。这的确令人费解。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辩称前南斯拉夫问题是一个例外,但无论如何,由国际机构确立新国家的标准并评估和审查新国家的宪法之做法,不能不说是严重干涉了“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
如果说上述事例尚属特殊,那么国际法干预和限制国家的经济主权的事例则不胜枚举。仅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法律制度为例,我们就足以领略到国际法使国家的属地权缩小到何种地步。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所含的各项协定所触及的“大量政策领域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政策的排他领地。”〔22〕在货物贸易领域,成员国不仅不能随意制订关税税则,而且在实施各种非关税措施方面还得“小心翼翼”,就连一些“灰色领域”措施(如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等)也被限期废除和禁止使用。更有甚者,成员国在实施农业政策和补贴政策时不能不顾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的规定。即使是必要的技术标准和措施,如产品质量检验、原产地标准、卫生检疫、装运前检验等,不仅要有透明度,而且还必须符合有关的国际标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成员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政策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均必须遵守相应协定中的原则和规则。更使人们关注的是,一向为国内管辖的金融、保险、基础电信等服务行业,今后也要受制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它专门协定。最后,不可忽视的是,世贸组织刚刚立足,就“马不停蹄”地向国内管辖的其它领域进军,竞争政策、环境政策和社会标准已被该组织列为“新的贸易议事日程”(new trade agenda)。由此可以断定:在国家间相互依存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贸易领域,纯属国家属地优越权管辖的部门和事项似乎已萎缩了不少。
(二)属人优越权的缩小
属人优越权是国家对其国民享有的最高管辖权。然而,国家这一管辖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整体利益观念、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挑战。
国际人权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问题之一。在联合国的作用下,国际人权继第一代人权(个人的基本权利)、第二代人权(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集体人权)之后,已进入以和平权、环境权、发展权和人类共同继承权为标志的第三代人权概念的阶段。有专家断言:随着第三代人权概念的出现,国际法将出现一个新的主体——人类本身。〔23〕可以预测:如果人类整体作为国际法主体得到确立和国际公认,国家的属人优越权势必不再“优越”了,因为个人不仅只是以国籍作纽带而成为一国的国民,而且还同全球的个人一起构成人类的整体而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在当代和未来的国际法中,当国家的主权利益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无疑应服从后者。因此,除了国家的公民权利、民族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性别政策、弱者权利等须尊重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之外,国家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技术与发展政策和环境政策也应顾及到整个人类的和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共同继承权。国家不可为自身主权的完整而无视人类整体利益,因为此等“无视”有可能导致危及地区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国家不可为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不顾甚至破坏环境,因为一国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会殃及邻国和全球。国家更不可凭借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极地、国际海底和外空主张主权,因为这些地区或区域是人类共同的继承财产。
与国际人权法一样,国际人道主义法自纽伦堡和东京军事法庭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在战时保护无家可归者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安理会曾先后通过有关决议,在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境内建立安全区。在冲突地区设立安全区是一个新概念,其实践引起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国际法新问题:建立安全区或实施人道主义援助是否应事先征得东道国的同意?根据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1 )安全区的建立地点或人道主义援助的实施地点均在东道国领土上;(2 )安全区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济无家可归者,而这些无家可归者属于东道国的国民。然而,安理会通过的第688 号决议(关于在伊拉克建立保护库尔德人的安全区)并未征求伊拉克的同意。尽管这一决议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不少的争议,〔24〕但它毕竟曾经得到实施。冷战后的一系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措施似乎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如战争、大规模武装冲突、种族屠杀),国际人道主义措施并非必须征得东道国的同意不可。可见,冷战后时代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采取的措施对有关国家的主权构成限制。
四、结论:国家主权的辩证法
冷战结束后,不论一些国家的民族纷纷导致新的独立国家也好,国际组织及国际法越来越明显地渗透到(有时甚至是“粗暴地闯入”)国家主权传统的管辖领域也罢,均是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新现象。这些现象固然对国家主权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家主权构成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的核心之神圣地位。民族独立、国家分裂、国际组织职权膨胀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在国际法中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我们一方面不可被特定时期的突发事件和纷繁现象蒙住眼睛,看不清主权这块“基石”,另一方面又不可忽视“基石”周围的“气候变幻”及其影响。在当今国际范围内主权概念再度混乱的情势下,运用辩证法来认识主权的一些基本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主权的界定与属性不能含糊。历来的国际法文件、教科书、判例无不将主权与国家、主权与独立、主权与领土、主权与最高权等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有时相提并论。早在1928年,胡贝尔法官就指出:主权“在国家间关系中意味着独立。涉及地球某一部分的独立就是在这一部分行使一个国家职能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排除任何其它国家的”。〔25〕最近出版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仍将主权定义为国家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在国际平面上意味着在法律上不隶属于地球上任何其他权威的法律权威。〔26〕这是迄今关于主权概念的最新权威表述。可见,主权者,国家也,反之亦然。
正确认识主权概念,必须与国际法上的主体、自决权、组织职权等相关概念区别开来。虽然现代国际法承认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是国际法主体,但这些实体或群体并不享有主权。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不可与主权国家同日而语。同样地,尽管国际法确认具有宗教、文化、地理、语言和习俗等特征的民族享有自决权,但这种权利决不是主权,而且这种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主权者的承认与合作。类似地,虽然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享有广泛的职权,而且这些职权有时与国家主权发生碰撞,甚至有的职权还具有明显的超国家因素,但它们毕竟是国家赋予的职权,而不是主权,至多也只是主权含义中的某些具体权利。因此,仅根据冷战后出现的特殊现象而提出国家主权过时论、主权多元论或主权分散论,不仅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而且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状。
其次,国家主权是神圣的,但又不是绝对的。国家主权的神圣性是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正如梁西先生所生动描绘的,国内社会是一个“宝塔式”的社会,其中国家的主权表现为国内最高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威,没有这些国家的最高权威,国内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的神圣地位,是国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国际社会是一个众多“宝塔”林立的社会。由于在这个平面式社会里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威,所以就更需要坚持和维护彼此独立与平等的国家主权,彼此尊重主权。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少一些战争与冲突,多一些和平与安全;才能少一些强权与敌意,多一些平等与合作。
我们强调国家主权的神圣地位,并不等于将它推至极端。就像国内社会的任何人不可能有绝对权利和自由一样,国际社会的任何国家不可能享有绝对的主权。正如一位印度国际法学者所断言的,“现实生活给予国家绝对独立的程度并不比给予个人的独立程度高。”〔27〕而且,如同个人在社会的独立必须在法律约束之中一样,各国的主权独立也必须在国际法律范围之内。这一范围的首要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都要平等地受国际法的约束。国家主权之所以不可能是绝对的,还有国际社会内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这一根本的原因。现代科技和交通信息的高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愈来愈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一国的生存与发展还取决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谋求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就必须在一些领域适当限制国家的主权。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全球共同利益所必需的,而且是公认为国际法原则所允许的。
最后,主权的制约者恰恰是主权者自身。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制约国家主权或侵蚀国家主权的因素的确很多。有趣的是:归根结底,限制主权的真正“幕后操纵者”是国家本身。本文所涉及的限制主权的各种现象,大都是国家“自作自受”或“心甘情愿”的。以现行国家的瓦解为例,这实际上是国家努力将民族自决确立为国际法原则的结果。可以试想:如果国家不将民族自决升华为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有关民族想建立独立的国家也就找不出国际法的依据;即使擅自建立了独立国家,其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也会存在疑问。国际组织及国际法有情形也是如此。正是国家创立了国际组织,并赋予它们为实现其宗旨所必需的职权;正是国家不断制订和完善国际法来约束自己。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发现其主权受到过份的限制,它又会通过行使主权来调整有关的制约因素。一般都认为,欧洲共同体是限制国家主权最多的一个国际组织。然而,成员国通过缔结联盟条约注入了一个新的原则——从属原则,〔28〕其目的就在于抑制欧洲共同体权力不断膨胀的势头。
总之,我们不可因冷战后的某些国际特殊现象而渲染国家主权危机。其实,“国家主权并未怎么了”。只要这个世界还是“国际”的社会,只要调整这个社会的法还属于“国际”的法,主权将永远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掌握主权命运者将永远是国家!
注释:
〔1〕Thomas M.Frank,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Institutions,Clarendon Press,1995, p.3.
〔2〕Mohammed Bedjaoui(ed),International Law:A Chievement andProspect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pp,11-12.
〔3〕除了有关刊物上的论文外,有两次影响甚大的国际研讨会。一次是1992年8月27—29日在波恩举行的研讨会, 其议题为“殖民后时代的民族自决权”。另一次是美国国际法学会于1994年4月6-9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88届年会,其首要议题为“主权的转换”。
〔4〕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ance of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United Nations Yearbook,1960,p.49.
〔5〕Bruno Simma(ed),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A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62.
〔6〕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United NatedNations Yearbook,1970,p.788.
〔7〕ICJ Reports,1971,pp.16,31;1975,pp.12,31-33.
〔8〕Michla Pomerance,Self—Determination in Law and Pra-ctic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pp.14-15
〔9〕United Nations Monthly Chronicle,No.2,1970,p.36.
〔10〕Christian Tomuschat(ed),Modern Law of Self—Detetmina-tion,Martinus Mijhoff Publishers,1993,pp.2-3.
〔11〕Report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General Assem-bly Offcial Records,39th session,Suppl.No.40(A/39/40),p.142.
〔12〕UN doc.E/CN.4/SUb.2/1992/33.
〔13〕很多欧美学者认为,民族自决权应由两部分组成,即对内自决权和对外自决权。前者主要指自主权、自治权以及发展自我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权利;后者则主要指独立权或脱离权,即从原主权国家脱离开组建新的独立国家的权利。
〔14〕Christian Tomuschat(ed),Modern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Martinus Mijhoff Publishers,1993,pp.42-45.
〔15〕Christian Tomuschat(ed),Modern Law of Self—Determin-ation ,Martinus Mijhoff Publishers,1993,p.23.
〔16〕The ASIL Proceedings,1994,p.43.
〔17〕The ASIL Proceeding,1994,p.53、54.
〔18〕瑞士干酪是一种硬干酪,其中有形状各异并且位于不同方位的洞孔。
〔19〕The ASIL Proceedings,1994,p.52.
〔20〕The ASIL Proceeding,1994,p.36.
〔21〕The ASIL Proceedings,1994,p.38.
〔22〕Pitou Van Dijck & Gerrit Faber(ed),Challenges to theNew Worid Trade Organiz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p.16.
〔23〕Mohammed Bedjaoui(ed),International Law:A Chievementand Prospect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p.13.
〔24〕有一种观点认为,安理会的这一决议是越权行为,因为建立安全区是人道主义目的,而安理会的职权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无人道主义干涉权。参见Najeeb AI—Naruimi and Richard Meese(ed),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1995,pp.829-831.
〔25〕Record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Vol.2.p.838.
〔26〕参见《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中译本,第92页。
〔27〕R.R.Anand,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7,pp.86-87.
〔28〕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Union,Preamble,ArtsA(2),B(2);Article 3b(2)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