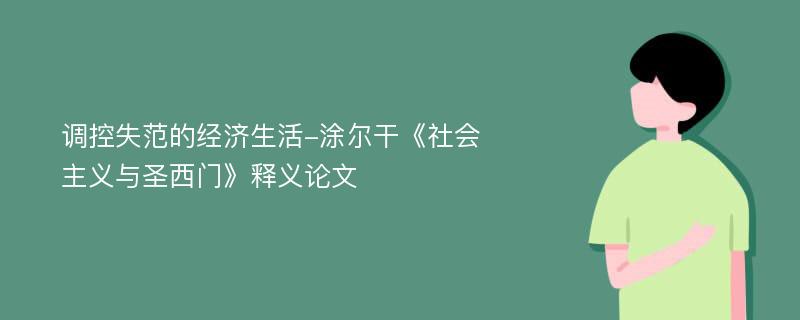
调控失范的经济生活
——涂尔干《社会主义与圣西门》释义
潘建雷
摘要: 社会主义学说是欧洲近代社会转型的独特思想产物,是19世纪初期集体良知对失范的经济生活的反应。涂尔干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事实”的考察既是“道德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这项研究也与宗教禁忌、家庭、财产观、契约等诸道德要素的研究一同构成了涂尔干现代社会转型可能性的研究系列。涂尔干试图通过呈现社会主义“最一般、最非个性化、最客观的特征”,分析那些促使圣西门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道德、政治、经济行为的新原则的社会压力,确诊催生社会主义的集体病症,检讨社会主义方案的利弊得失,为寻求恰当的治疗方法乃至社会的总体重建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社会主义;失范;圣西门;涂尔干
一、导言:社会主义与转型危机
社会主义学说是欧洲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降的欧洲社会,历经数百年商业复兴与海外殖民的量变积累,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爆发了产业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与社会改良运动。这一系列的革命与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着传统的封建—教会体制,资本扩张、政治权威衰落与道德价值紊乱等“集体疾病”接踵而至,新旧社会体系的焦灼呈现了一副极具时代特点的转型乱象。其中,资本扩张对社会结构与人心秩序的侵蚀尤为严重,用涂尔干的话说,“两个世纪以来,经济生活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膨胀。它从一种次要的、受人鄙视的、委诸下等人的社会功能,一跃成为首要功能……吸纳整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力量,成千上万的人都进入了工商业领域”。① Durkheim, Emil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 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7, p.12. 问题在于,当经济功能成为社会结构体的支配维度时,它本身却缺乏有效的组织与明确的规范,这使得“身处其中的人对道德只有微乎其微的印象,他们大部分的存在状态都远离了道德的影响”,生活在道德真空(moral vacuum)之中,倾轧无度,形成了强侵弱、富暴寡的极端悲惨景象。① 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71-275页。
社会紊乱的时代通常也是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正因为不稳定的集体组织不再能依据其天生的权威行使功能,才促使我们对社会事务进行反思。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欧美世界这场规模、深度、烈度都前所未有的转型在思想界引发了持久的惊愕与回响,不同人物与流派都试图就清理旧制度的瓦砾、促进新社会的发育提出各自的方案。社会主义便是这场社会性反思的独特产物或者说“显学”之一。按吉登斯的话说,社会主义是少有能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分庭抗礼的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理想学说)。③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理论的逻辑(第二卷)》,夏光、戴胜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07页。
取上一年没打过除草剂的豆科作物种植田的土壤50~150千克与育苗基质土50千克。土∶育苗基质=1.5∶1,加蔬菜复合肥硫酸钾(N∶P2O5∶K2O=12∶18∶15)50~100 克。
到19世纪后期,转型危机愈演愈烈,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相当一部分学者与社会改良人士都认定它是转型时代的济世良方,称之为“有关一般社会,特别是最文明的当代社会的性质与演化的科学学说”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青年时期的涂尔干也曾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一度与饶勒斯、梅奥等社会主义者过往甚密。据莫斯在《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初版序言中所说,涂尔干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就致力于以抽象与哲学的方法研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后来(1895-1896年)还在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开设了研究“社会主义”的课程,《社会主义与圣西门》这部著作就来自这些课程讲义。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的社会主义研究与时兴的观点有云壤之别,我们应当从涂尔干的道德科学研究与道德社会重建的总体计划来审视这项研究。根据涂尔干同时期撰写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等学术作品中的观点,社会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体,它的转型与重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各维度、各层次的“社会事实”及其演进规律做细致的科学研究,为此他制定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并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社会学年鉴学派”)对乱伦、自杀、犯罪、义务、宗教、财产、契约、国家、分类观念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事实”开展研究。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在涂尔干那里,这些看似无关的研究其实有相同的目的,如其所言,社会不是纯粹的抽象或理想,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事物,是一系列社会器官与社会事实的积累,即便是革命也不可能把社会夷为平地而重起炉灶。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因此,要想了解欧洲各民族的家庭、财产、政治、道德、法律与经济组织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和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必须研究过去存在过的大量制度和实践活动,寻找它们不同的历史变化轨迹,寻找决定这些变化的主要条件。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05页;第102页;第97页;第106页;第379-380页;第103页。 这些研究既是为了检验其“一切本质皆为社会”的观点,更要辨析这些要素的历史形式、演进轨迹及当下可能的发展方向与存在形式。涂尔干感慨,这类社会科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几乎没有多少进入正轨,就连最出色的研究都还处在基础阶段,但这却是解决转型欧洲的政治与道德危机,勾勒新社会蓝图的必由之路。他曾在课堂上批评同时代的政治家只关注表面、当下的社会状况,而不能用历史的眼光辨别“正在消失的历史残余”与“正在发育的未来种子”,他向学生说到,“只有当政治学的讲授像其他科学那样,欧洲的危机才能得以解决”。①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3、185、206页;第98、102、105页;第372-373页;第112-113页;第114-118页。
同时,随着卡夫卡思想上的成熟,他内心深处的犹太文化觉醒后,他内心中一直畏惧的父亲形象开始渗入上帝的影子,父亲的“惧怕”和作为犹太人对于上帝耶和华的“敬畏”是并生的,成为了卡夫卡精神上的绝对统治。卡夫卡甚至于这么说:“你对我吼叫的一切都不啻是天谕神示,我绝不会忘记它,它成了我判断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4]461-501
承上所言,经济生活的组织化与道德化是19世纪(转型初期)思想家着力的首要问题,而社会主义便是这种集体思考的产物。所以涂尔干指出,社会主义主要不是对社会事实的表达,相反它本身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社会事实(“物”),其本质是“受苦受难的民众自发与本能构想出来的社会重建计划”,是“那些最深刻感受到我们集体疾病的人们发出的痛苦呼喊和怒吼”。作为转型期的一种表达应然的意识形态与批判现实的学理说教,社会主义渴望凭借“从未存在或幻想的集体生活规划对社会秩序进行一次全盘改造”。②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1958, p.5-9;p.39. 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彼时普遍的集体情感的产物,只要相应的集体病症没有消除,这种学说就会持久不衰,“即便无药可治,人们也会一直寻求治疗方法,而且会不间断地产生寻求方法的人”。③ 如莫斯所言,涂尔干研究社会主义的初衷也正是要寻求治疗病症的方法,他试图通过呈现提炼社会主义“最一般、最非个性化、最客观的特征”,分析“那些促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与马克思等人倡导道德、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的新原则的社会压力”,确诊催生社会主义的那些集体病症(collective diathesis),检讨社会主义方案的利弊得失,为寻求恰当的治疗方法乃至社会的总体重建提供科学依据。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3、185、206页;第98、102、105页;第372-373页;第112-113页;第114-118页。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1958, p.5-9;p.39.
二、经济生活的组织化与道德化是转型时代的迫切需求
(一)社会主义:调控分散的经济功能
社会主义这种客观事实究竟由什么构成;它“最一般、最非个性化、最客观的特征”是什么?按《圣西门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定义”等文献,19世纪后期的社会主义流派多如牛毛,从胆小如鼠的“议会社会主义”到激进革命的“集体主义”不一而足,各流派各执一端,以至于在“确立社会主义的正常类型之前,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就是谬误的和反常的形式”。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3、185、206页;第98、102、105页;第372-373页;第112-113页;第114-118页。 对此,涂尔干运用了他倡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认为应当从外在视角对它们进行分类比较以归纳社会主义最普遍的特征。他指出,这些号称社会主义学说都在抨击当前经济功能的“分散”状况,并认为19世纪经济生活失范的根源在于,产业革命以来迅猛发展的经济功能长期游离于法律与政府决议等结晶化的集体意识之外,与指导社会机体的器官(国家)之间缺乏直接、明确、系统的沟通渠道,因而主张要尽快在工商业活动与社会指导性的意识机构之间建立某种联系。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3、185、206页;第98、102、105页;第372-373页;第112-113页;第114-118页。 这里所说的联系不是经济功能服从国家(社会的意识中心、“社会的大脑”、社会的认知与管理机构),而是在经济生活与国家之间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把经济活动提高到政治活动的层次,成为后者的主题。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3、185、206页;第98、102、105页;第372-373页;第112-113页;第114-118页。 据此,涂尔干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主张当下散乱的全部或某些经济功能应与社会的意识中心建立联系”①②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 1958, p.9. 的学说;它代表了“一种重组社会结构的愿望,要求重新安排产业结构在社会组织总体中的位置,使之脱离自生自灭的阴影,促使它得到良知的指引与控制”。③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 1958, p.26.
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期。这也是问题矛盾凸显的高发期。不仅治安问题多样,数量也增多。这对我国民警造成一定考验,这不仅仅要让民警承担更多的工作量,同时也要应对各种多发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的安全保障尤为重要,也为物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社会主义对经济功能散乱的批判与国家调控的强调这一普遍特征,还应强调以下几点:
这里要强调两点:首先,圣西门倡导的这场变革是世界范围的,如其所言,欧洲各国同属一种社会类型,实行相似的封建制度,尊奉相似的宗教神职人员,重大社会革新也往往引起超国界的连锁效应,封建制度的革命与基督教的失势就几乎同时在各国发生,因而法兰西的危机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治愈,当下的社会转型注定要引导大多数国家共同前进。⑦ 涂 尔干 :《孟 德斯 鸠与卢 梭》 ,李 鲁宁、 赵立 玮译, 上海 :上海 人民 出版 社,2006,第203-204页; 第223页 ; 他预言,产业社会将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一种超国家的国际产业委员会将推动产业体系扩展到全世界。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其次,作为一个敏锐的天才,圣西门的改革计划更多是原则性的预言,较之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性,他设计的社会主义蓝图与莫尔、康帕内拉等人勾勒的乌托邦一样苍白无力,而且迫不及待,所以涂尔干坦言,可以忽略圣西门社会主义蓝图的细节。⑨ 涂尔干 :《孟德 斯鸠与卢 梭》,李 鲁宁、赵 立玮译 ,上海: 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 第223页;
(2)经济功能自身尚未形成明确的器官(组织载体)作为立身之本。随着18世纪产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散乱的工场作坊渐趋集中化,经济生活的产业化形态渐趋形成,但彼时各经济领域的企业彼此独立,各行其是。尽管它们因经济交易与利益驱动产生物质层面的联系,但这些分散的企业就像器官的片段与材质,缺乏共同的目标,没有纽带使之结成统一的团体,用涂尔干的话说,“它们并不构成任何类的道德共同体”。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第132-134、155-157页;第131、374-375页;第132、375页;第375-376页。
大革命为何没能完成“立新”的历史使命?按圣西门的观点,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某些中间过渡,“律师-形而上学家”主导的社会体系便是封建-教会体系向科学-产业体系转型的过渡形态。从源起上说,律师以封建领主的代理人起家,后与产业界形成了更深的利益关联,帮助商人、劳工阶级摆脱封建法庭的控制;形而上学家脱胎于神学势力,后与科学家结盟,促成了个人良知的解放。律师与形而上学家新旧杂糅、模棱两可的特征,加之他们对科学与产业的绝大贡献,使之既能应对大革命前夜杂乱的社会状况,又获得了企业主与科学家的欢迎,因而主导了大革命的进程。律师与形而上学家确实摧毁了旧制度,但他们不具备建设新社会的能力。首先律师与形而上学的学说都源于旧制度,前者源自罗马法、国王法令与封建习俗,后者受到神学的深刻影响,都“渴望寻求得到超越时空的绝对解决方案”;其次,法律准则的固定性(更勿论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与产业生活的灵活性格格不入,法律捕捉不到产业生活的细微差别与变化,产业生活也不可能拘泥于固定的程序或教条的原理。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第190、305页;第275页;第209、211、213、219页;第284页;第245-246页;第249页;第222、237-238页;第213、214页。 正如涂尔干批评的那样,法国革命议会专注于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府,而完全没有触及社会危机的根源,即产业活动的无序状况。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第190、305页;第275页;第209、211、213、219页;第284页;第245-246页;第249页;第222、237-238页;第213、214页。
产业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共同组成产业社会的调控机构,成员来自产业与学术领域最有才能的人,它的权威基础与以往的政府截然不同。传统政府的权威基础源自作为共同信仰与传统的代表;产业社会治理委员会的权威源自指导产业生活的科学真理与实践知识,成员对它的信服不再带有任何强制性,用圣西门的话说,“旧社会体系根本上是人的统治,新社会体系则是原理的统治”。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按照圣西门的理想,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依据自身能力在社会有机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参与到各类相互联系的产业机构,在共同产业目标与调控器官的引导下,分工协作结合成有序的整体,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巨型的生产公司”或“经济功能体系”或“巨大的生产联合体”。其中,国家(治理委员会)作为“公共感觉的中枢”(communal sensorium)与“整合不同工商业关系的纽带”,负责调控生产与分配财富,在社会诸功能之间建立和谐协作的常规机制,尽可能获得最大的产出与和谐。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据此圣西门宣称,现代政治学的全部实质就是调控经济生活的“生产科学”。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按他的理想设计,既然世俗(经济)利益是产业社会成员追求的唯一幸福,且能理性有序的追求,那理论上经济生活最终可以自行有序运转,不需要任何外部强力与道德权威的干预。
1. 自由公社的解放运动:封建势力与产业阶级的地位逆转。11世纪前后,随着伊斯兰世界的衰退与欧洲的商业复苏,自由公社这种独立经济群体与社会器官应运而生,工匠和商人借助货币(银币)逐渐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监控,“公社成员开始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再受任何武力操控”。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在此后的数百年,随着经济活动向社会生活的深度渗透,自由公社也随之成为世俗世界的中心与规则的发源地。在此期间,产业阶级(industrial class:第三等级)从教会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独立司法审判权,尽管市政法庭最初受到了教会与领主的种种限制,但工商业事务的自决权完全归市政法庭,换句话说,产业阶级拥有了与其特点相一致的司法机构。⑤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起初,自由公社与封建领主、君主国家以特许契约与纳税的方式维持一种互不干涉的和平关系,封建国家根本没有意识到产业世界正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外悄然成长。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随着产业改良、技术发明与财富积累,自由公社扩张成了自由市镇,工匠与商人也转型为更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bourgeois),这直接影响到了政治关系的转变。自由市镇的资产阶级不仅要操控世俗的经济生活,还从影响国家战争动员开始向政治领域开拓。产业界的代表,从征税表决顾问,到预算审议权,再到排他性的预算表决权,最终接管了旧世俗权力的主要职能,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修正社会的前进方向与制度设置。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17-18世纪,新旧力量的矛盾开始凸显,英法两国率先爆发权力争夺,前者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联手遏制王室,后者是王室携手资产阶级架空封建领主,各国对封建制度的持续打击最终汇聚成以法国大革命为高潮的彻底颠覆。⑨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二)积极调控与自由放任: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的分歧
涂尔干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产业社会意识形态,是近代产业革命与生产方式变革的拥趸者,主张经济利益/经济关系将成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与集体存在的统摄性基质,而现代社会将演化成一个以功能依赖与利益交换为团结纽带的产业体系。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9、267页;第157-158、306页;第152、155、157页。 就此而言,社会主义与古典经济学这两大看似敌对的学说其实“具有一种很近的亲属关系”,它们都是典型的“产业主义”(industrialism);都认为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失范的经济生活,且“只能在经济生活之中并通过经济生活本身来组织经济生活”。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9、267页;第157-158、306页;第152、155、157页。
全省国土资源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省厅办公室)..................................................1-4
双方的分歧在于,经济学家彻底剥离了经济生活的公共属性,鼓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式的生产竞争与资源配置可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完美平衡与整体利益最大化;国家被限制为确保契约履行的消极“旁观者”,其职责是“防止个人对他人进行非法侵越,使每个人都能完好无缺地维护正当的权利范围”。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3、161、219页;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3页。 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大工业体制很难自动形成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平衡;因为人对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这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产品都有阈限。当市场限于特定区域时,生产者可以估算商品需求量,但在世界市场时代几无可能。而且,市场的广阔前景会激发生产者无止境的野心,使之尽力扩大生产。人的需要固然有一定的弹性,当某项产品超过集体需要阈限时,生产者可以开发更高端的产品,但劳动者的贬值与失业、先前投入的损失、剩余产品的降价出售等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这里要特别延伸讨论一下两种学说关于劳资矛盾的不同观点。相较古典经济学家的解决方案,涂尔干更认同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按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的根源在于他们作为经济世界一个构成部分尚不是成熟的社会成员,需要借助中介(资本家)参与社会,后者利用双方经济实力的差距,阻止工人获得与劳动等价的收益,不能获得更公正的待遇与更好的物质生活。所以,解决劳资问题的方法应当是让经济生活(工人代表)全部进入公共生活(政治国家)的视野,这样中枢神经(国家)就能充分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借助公共机构的力量限制乃至取缔资本家的中介作用,以社会指导机构(国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与评价者。⑤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 1958, p.26. 涂尔干坚信,只要经济活动与国家建立直接的关联,劳资矛盾与阶级斗争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所以他一再强调,劳资问题只是社会主义的次要关注点与现代健康经济秩序的一个小问题,而非本质要素或终极目标。⑥ ⑥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19、267页;第157-158、306页;第152、155、157页。
一言蔽之,在大工业时代,扩张的生产与有限的消费的精准平衡不符合科学与事实。①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社会主义者强调,普遍的过度生产引发了恶性的经济竞争,这是一场看不到对手的生死博弈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暴烈斗争,劳工近乎炼狱,雇主动辄破产,剩余利润的增加与贫穷苦难的加深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正相关关系;身处其间的人几乎都陷入一种“发烧”状态,个体与社会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即便是胜者也很难真正获益。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因此,他们呼吁必须改革重组当下的经济秩序,以国家为中心调控经济生活,以银行体系等为载体精确计算不同部门与地区的生产量与消费需求,以减少供需关系不平衡造成的周期性危机。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三、“封建-神学”向“产业-科学”的转型:圣西门的危机诊断
(一)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
圣西门(1760-1825)是涂尔干笔下社会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的人生与法国的思想启蒙、政治革命与社会动荡高度重合,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圣西门也宣称要继承百科全书派的思想衣钵,建立实证时代的“新百科全书”(新世界观)。在他看来,百科全书派的哲学与实证哲学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者重在批判旧式的宗教观念,后者致力于建立新时代的欧洲在道德、宗教、政治等领域所需的实证观念。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按照圣西门的实证世界观,万有引力定律是世界真正的原生规律,物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一切特殊规律都只是它的推论,而实证哲学的任务就是依据万有引力定律对诸种科学进行综合与统一,以重建世界统一性的共同信仰。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但圣西门发现,对物理学等特殊科学的系统化与一般化并不足以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宗教与政治信仰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释框架,在哲学的形式普遍性与科学的严格专业化之间还存在一个研究的空白地带,即“社会”;为此他主张把实证精神拓展到人和社会的领域,建立一门关于人与社会的新科学,即“社会生理学”(social physiology)。⑥ 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0-163页;第158-159页;第232、286页;第176-177页;第255、261-262页;第179-180、259页。
涂尔干认为,圣西门是第一个有清晰“社会观”并主张社会科学实证化的思想家,他明确区分了个体的“具体生理学”与集体的“总体生理学”,指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社会运行也不是意志任意或偶然的产物,它是一个巨型有机体或“组织化的机器”,各个部分都以不同方式作用于总体,总体的存在状态取决于各个器官履行功能的程度。⑦ 涂尔干在讲稿中多次就圣西门与孔德的“学术公案”表明立场,认为实证社会学创始人的殊荣应归于圣西门,而孔德及其门人后来不承认对圣西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有“剽窃”之嫌;当然也如孔德所言,圣西门缺乏学术耐性,随意修订改革计划,迫不及待地想用那些不成熟的实证研究指导实践,这也是二人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参见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7-190、206-207、220页。 与孔多塞等启蒙思想家一样,圣西门也坚信社会进步的规律是客观必然的,每个时代都能形成符合自身状态的社会制度。⑧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 1958, p.958, 101. 而社会生理学的任务便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当下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观察既有观念与利益的存在链条,区分发展的要素与历史的残余,辨析“为历史残余所遮蔽的未来”,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次序与社会进步的规律,以确定未来社会的具体形态。①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很多蔬菜的种子表面甚至内部,可能会感染很多的病原菌,如茄子的褐纹病、黄萎病、绵疫病、立枯病、猝倒病;辣椒的绵疫病、立枯病、猝倒病、炭疽病、细菌性斑点病、病毒病;番茄的疮痂病、叶霉病、早疫病、萎蔫病、花叶病;瓜类炭疽病、细菌性角斑病、枯萎病;菜豆炭疽病、叶烧病、锈病、花叶病等。由于带菌的种子又会将病原菌传染给幼苗和成株,从而导致蔬菜病害的发生和蔓延,因此,在播种前进行种子消毒是非常必要的。
(二)世俗与精神:中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主要维度
涂尔干盛赞圣西门是第一个认识到中世纪与现代的关联及公社的历史意义的人。在圣西门的笔下,中世纪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转型不只是影响了某些社会特征或统治机制的细节,而是孕育了包括自由公社与精确科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的胚芽与本质特征,彻底改变了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与组织原则,因而是研究现代的“最合适起点”。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呈现出“世俗—宗教”并立的特征,即把持武力与经济的封建制度与控制精神(教育)的教会制度。这一“双头”体系在10-12世纪达到极盛,与此同时自由公社(free commune)与精确科学这两种自成一体的革命要素,也在社会机体的核心结构内生根发芽,渐次引发了一场除旧布新的社会运动。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5)社会主义学说只是社会转型的思想反应之一。为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学说的独特性,涂尔干把社会主义与同时代另外两股“显学”做了比较,即共产主义与古典经济学。在涂尔干看来,这三种学说都是集体心智对19世纪前后生产方式遽变引发的病症的智识反应,“只是相似的集体良知的不同面向而已”,都针对经济生活的失范病症给出了自己的诊疗方案,也引发了相当程度的观念混淆乃至对欧洲各国的转型路径选择与现实的政制政策产生了干扰,为此涂尔干做了细致辨析。①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75、306页;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页。
最后,我们建议,一切与员工个人化相关的事情尽量回避,顾客体验感是顾客能感觉到的由餐厅释放的任何信号,不要片面的认为把产品、服务高标准严格了就能万事大吉,员工状态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你的餐厅品牌寿命!你们餐厅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2. 精确科学的发展:学者取代神职人员。公元8世纪以降,伊斯兰世界对欧洲进行了200余年的征伐,与铁蹄一同进入欧洲的还有学校,这孕育了一种与牧师类似的指导集体心智的群体,即学者。⑩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5、191页;第184-
185、192、202、206-207页;第192、193页;第193页;第198页;第224页;第197页;第193页;第193页。 学校与教会数百年都相安无事,到16世纪前后,学校孕育的反抗力量终于与旧的神学统治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斗争:(1)哥白尼、伽利略引领的科学革命,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对僵死的神学世界观产生了致命的打击;(2)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心智革命,他们倡导用个人的内省权利(right of examination)代替对教会的盲目信仰,这削弱了教士阶层对个人良知的控制权,更折损了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与社会的道德统一性;(3)17-18世纪,一大批学者作为智囊进入权力中心,成为王权的有力支持者与同盟者,在他们的推动下,大量向普通民众开放的专科学校(academy)应运而生;(4)科学的巨大效用使得从事工商业的普罗大众日益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经过两百多年的较量,学者逐渐取代了教士,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与知识权威,民众对学者形成了与原先对神职人员类似的敬畏。①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页;第196-197页;第218页;第199页。
(三)法国大革命:危机的总爆发
承上所言,从中世纪极盛期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旧体系向我们展现了一副持续走向衰败的历史画卷。在大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产业与科学的力量并没有以暴烈方式夺取世俗与精神领域的主导权,而是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公共活动的焦点与社会组织的中心自然实现的。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页;第196-197页;第218页;第199页。 但新旧体系毕竟有质的差别,很难共存,旧体系的世俗组织崇尚武力,精神力量主张脱离尘世的非理性信仰,而新体系的世俗组织崇尚生产能力,精神力量是关注现世的科学。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页;第196-197页;第218页;第199页。 这种矛盾到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已经避无可避,法国大革命只是矛盾的总爆发而已。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9页;第196-197页;第218页;第199页。 如圣西门所言,600年的市民社会革命与道德革命最终导致了政治革命,“如果有人坚持要为法国大革命寻根溯源,那就应追溯到公社解放和精确科学在西欧孕育之时”。⑤ Durkheim, Emile.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vin W. Gouldner.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Sattler. The Antioch Press, 1958, p.20.
的确,在大革命前夜,封建与宗教势力在政治体系中给专业人士(savant)与生产者(producers)让出了地盘,但这是苟延残喘式的妥协;新兴的产业力量依旧不能按自己的需求创造一种新的道德与政治秩序;旧体系的惯性(inertia:惰性)与新体系力量的软弱导致了无数的混乱冲突直至革命爆发。实际上,革命也没能彻底解决新旧体系的转换问题,用圣西门的话说,它摧毁了王室、贵族、教会等旧政治权威的基础,但没有明确权力归属;它赋予了良知自由以法理依据,却没有阐述一种让集体心智认同的新理性信仰;它根除了社会机体的主要纽带,却没有建立新的均衡机制;结果,革命非但没有缓和矛盾,还加重了混乱。转型的不彻底性与旧体系对新兴产业的持续阻碍,在一些国家造成了难以忍受的混乱,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没有议会席位,法国王权死灰复燃,这一系列现象都清楚表明1789年革命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以更紧迫、更焦灼的方式凸显。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0-202、208-209页。
(二)1670年—1724年,即著名汗王阿玉奇执政的年代,由于他卓有成效的施政,汗国势力不断发展与壮大,是土尔扈特国的鼎盛时期;
进气流量由微处理器根据不同的进水流量以及设定点温度来进行控制。通常经微处理器得到的进气流量,所能提供的折算热负荷只满足将热水加热达到所需的温升,并没有严格要求加热时间。在此,首先研究进气流量对加热时间的影响,同样将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数学模型导入MATLAB软件进行模拟计算,进气流量的范围参考文献[5]给出的进水流量以及温升达到40 K时所对应的进气流量以0.2×10-4进行划分,其余参数见表1,热水温升与加热时间的关系曲线如图5所示。
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它是在纯电动汽车上加装一套内燃机作为电力源的充电系统,其目的是减少汽车的污染,提高纯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可以直接由外接电源充电的重度混合动力汽车,而且电池容量较大可以靠纯电力驱动行驶较远的距离(目前我国的要求是综合工况下行驶50km),因此其对内燃机的依赖较少。在插电式混合动力中电动机是主要的动力源而内燃机作为备用动力,当动力电池能量消耗到一定的程度或电动机不能提供所需动力时才启动内燃机以混合动力模式行驶并适时向电池充电,如图2所示。
(3)经济功能尚未与中央调控器官(国家)建立系统性的联系。的确,国家已经为日常的经济生活确定了某些常规的交易类型,已经可以感受到经济生活的脉搏,但个人与企业依旧“可以通过相互约定随意摆脱”这类规定,而国家既没有明确的权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干预管理。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第132-134、155-157页;第131、374-375页;第132、375页;第375-376页。
四、“产业-科学”社会体系:圣西门的未来社会蓝图
尽管圣西门最先提出社会生理学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运用严谨的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的演化规律,而更多是出于兴趣探求他毕生思考的问题,即大革命之后的欧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体制。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圣西门告诫同时代的人,这场向理性与世俗时代转型的社会危机要想得到彻底,就必须以科学与产业为基础重建因旧制度的毁灭而混乱不堪的社会体制。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这是圣西门社会主义蓝图的要义。面对大革命之后持续动荡与新旧杂糅的局面,圣西门指出,社会均衡的重建要求所有的集体力量都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围绕同一个引力中心(center of gravity)运转,英国式的细节修补或妥协权宜是无济于事的,现实危机迫使社会做出选择:恢复旧体系或将新体系扩展到全社会。他疾呼,为了建设未来应当使过去成为白板(tabula rasa),根除封建与神学等历史残余物,以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唯一规范的(normal:正常的)存在形式,实现社会的彻底产业化与经济化,政治、军事等其他活动都要以之为模版,“以先验的方式设计产业制度”。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具体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改变世俗制度,使之能与那些摧毁了旧制度的新需求相一致;(2)确立一种共同的观念体系,作为世俗制度的道德基础。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1)经济活动(市民社会)的肯定性道德价值与政治生活(国家)的世俗化是社会主义出现的基本历史条件。经济活动要与国家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前提是集体良知要赋予两者类似的道德价值。经济生活作为现代世界的最主要维度,它的地位与价值并非与生俱来,在城邦与基督教时代的欧洲,政治与经济是道德生活的两端,国家是拥有至高尊严的宗教超验存在,而经济活动则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道德价值,与个人及财富相关的事物也很卑微。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第132-134、155-157页;第131、374-375页;第132、375页;第375-376页。 随着近代转型的深入,一方面经济领域的商业复兴与产业革命,使得经济活动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影响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18世纪的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使得政治生活的人文特征日益普及,宗教-封建国家逐渐向“公民国家”转型,民众的认可及其利益诉求的满足成为国家正当性的源泉,相应国家的功能也从战争治安转为经济调控。这种转变是社会主义学说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用涂尔干的话说,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国家的性质与功能转变的拐点,它催生了社会主义。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第132-134、155-157页;第131、374-375页;第132、375页;第375-376页。
我们应该坚信,只要老师能坚持不懈地对学生的预习进行指导和严格监督,日复一日,学生便能自觉养成较为良好的预习习惯,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必须教会学生如何预习,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世俗制度的改革
1. 产业社会的主体:两类劳动者
产业生活的独特目标是增强人对物的控制,致力于技艺、科学与产业的发展,为世俗生活生产尽可能多有用之物,所以有用物的生产者是产业社会唯一有用的人,即是说,劳动是产业社会人员遴选的唯一标准。⑩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3-204页;第223页;
第190、305页;第275页;第209、211、213、219页;第284页;第245-246页;第249页;第222、237-238页;第213、214页。 据此产业社会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物品的直接生产者(industrials,包括企业主与工人的产业从业者)与理论领域的生产者(学者)。其中,产业从业者是社会存在与运行提供必要条件的“基础阶级”(fundamental class),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并把国家意志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付诸实践,掌控无限复杂的经济情况。学者是
第190、305页;第275页;第209、211、213、219页;第284页;第245-246页;第249页;第222、237-238页;第213、214页。辅助性的次要阶级(secondary class),为产业提供科学知识的支持,甄别辨析产业运行的规律,为产业生活的实践者提供咨询;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一种与类宗教的精神与道德功能,用其缔造的共同原则调控人们的利益与情感。① ②③④⑤⑥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圣西门强调,这种世俗与精神并列的社会结构是历史性的分工框架的延续。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基督教会废除了希腊-罗马时代政教合一的体系,确立了精神与世俗的功能分工,使思想获得解放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形成了自由市镇与实证科学的并行发展的格局,产业社会也将延续这种社会结构。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3. 财产权的重构
(4)据上可知,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要求“以激进或渐进的方式使经济生活从现存的分散状况转变为组织状态”,使经济生活社会化就是使其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个人目的与自利目的服从真正的社会目的与道德目的,把更高的道德引入经济生活,实现经济力量的全面社会化。各流派的分歧在于调控的方式,包括具体机构是国家还是职业团体,职业团体的法律地位与权限,方式是暴力还是和平等。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1-132页;第132-134、155-157页;第131、374-375页;第132、375页;第375-376页。
2. 产业社会的调控机构:治理委员会或现代国家的作用
社会作为生产联合体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有效地组织生产,这就意味着生产工具应由最具使用能力的人掌握,所以应重构既有的财产权,使之与个人的能力、劳动形成机制性关联;然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迄今都没有“形成重构财产权的自然手段”,大革命也忽视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革命与转型尚未有所建树的主要原因之一。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尽管圣西门指责贵族、神职人员是“反国家”(anti-national)的寄生虫,主张应据自然法重构财产权,但他并没有像其巴扎尔等追随者那样要求取缔一切不以劳动与能力为基础的财产,以国家作为所有生产资料的管理者与个人财富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而只是提议用一种对经济活动最有利的方式确立财产权。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206、215-216页;第
210、216页;第228、231页;第126、141、217-219、229、267页;第218页;第233-235页;第285-286页。 他唯一认真讨论的财产权问题便是地产的改革措施,包括:(1)当土地使用权交给耕种者时应评估土地价值,双方均享增值收益,均担减产损失;(2)耕种者可以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土地改良的期权抵押,对所获资金有完全支配权;(3)鼓励推行土地银行制度,把地产转换成为契据,获得与动产一样的流通性。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从中不难看出,圣西门在做某种回避与妥协,如涂尔干所言,他只是试图通过对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一定程度的限制迫使懒惰的食利者参与生产,同时取消他们的政治权利,用法律严格监管他们,防止其拥有损害产业运行的能力,直至其消失殆尽。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二)道德的重建:新基督教
尽管圣西门也明言,19世纪初期的社会危机与多神的希腊—拉丁社会转型为一神的基督教社会的危机有相似之处,在这样一个新旧道德体系交替的间隙期,人们需要重建一种与新社会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但在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相信,在组织有序的产业社会中,利己主义与经济活动会自发遵循道德规则,劳动保障与交易自由等共同利益能促成所有生产者的联合与和谐,所以他一直希望以纯粹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构建一个稳定的产业社会。直到晚年的《论实业体系》(1821)与未竟之作《新基督教》(1824),他明确指出,必须确立一种新的道德教义克服泛滥的利己主义,因为经济领域转型形成的社会制度要想获得普遍的认可,就必须以根植于个人良知的共同信仰为基础,然而即便在设计最精巧的社会中,利己主义的离心功能也总是大于团结功能,随着古老的宗教信仰及相应的行为习惯的式微,它很可能引发社会的紊乱乃至解体。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这着实给圣西门出了一个难题:在他设计的产业社会里,经济活动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内容,人们只专注于明确、特定的当下利益,而这种经济活动本身却不能自发产生道德约束力,那就意味着要到经济活动之外寻求一种道德力量,构建一种世俗的、实践的道德体系或者说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它既要肯定世俗经济活动的价值,又能遏制泛滥无度的欲望。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这便是他的新基督教。
但在相互交流中,学生发现,可以根据格子的累加来“设计”图形,1格+1格,只有长方形,1格+半格+半格,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了,除了直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梯形以外,还可以拼成不规则图形(如图2);如果是半格+半格+半格+半格,那么又可以拼成不同的图形(如图3)。
圣西门指出,宗教的本质任务是向人们提供一种世界统一性的情感,为社会成员的团结提供精神纽带,并非一定要采取反对尘世的天国意象。从宗教的发展史来看,越接近源头,物化的仪式与实践就越重要,越往后纯粹道德性的信仰与戒律就越重要;他的“新基督教”就是要把基督教蕴含的道德力量从各种神秘观念与粗俗仪式中剥离出来,重塑其原初的单纯性。⑤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他宣称,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博爱”(philanthropy)精神,其首要目标是让所有阶级的信徒都集中关注道德,以弟兄相待,认识到救赎的途径不是传统基督教的禁欲,而是投身现世的共善事业。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现时代的博爱精神不仅是道德箴言,更要落实为有实际约束力的制度,引导世俗权力改善贫困阶级的处境,让一无所有的劳工或者说无产阶级尽可能多的分享劳动产品,从社会的组织化中获益,自愿依附并尊重社会,以消除贫困的方式实现两大阶级的和解与所有阶级的幸福。⑦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就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涂尔干指出,旧基督教的圣俗/心物二元论固然不适合全面世俗化的产业社会,但圣西门及其追随者也没有意识到,旧基督教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它把上帝置于人的欲望、利益与物质等世俗世界之外,这样上帝就可以作为一种反制欲望与利益的道德力,而在他们设计的世界里,上帝与尘世同质,精神与物质一体,又如何能成为一种高于后者的力量?换而言之,新基督教缺乏一种有效的神圣道德载体,这种致命的缺陷导致圣西门学派逐渐蜕变为一种神秘的感觉论与纵欲主义。⑧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6、289页;第215、
224、237页;第238-240、289-290页;第238-240、247、293页;第260-261页;第263页;第240-243、260页;第298页。
五、涂尔干对圣西门与社会主义的反思
在自由放任带来一切好处与缺乏调控而引发的所有危险之间,现代社会应如何抉择?① ②③④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5页;第132-133、273页;第273页;第144-145、270-271、274页;第99页。 这不是仅凭个人好恶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涂尔干所言,社会生活是一种永恒的变化作用,重要的是在经验事实层面确定它处在何种变化过程,未来它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预测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这就需要集体良知精确计算特定社会的欲望与道德、自由与纪律的权重比例,这便是其道德科学的主旨。
首先,涂尔干赞同圣西门等人以国家为中心调控经济生活的理念,认为经济领域的健康运行需要指导机构与不同经济部门的协作,规范诸如工作限量、职工收入等权利义务。当然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波动性与突变性意味着,经济调控应当是连续、变通、灵活、广泛的,而不是某种简单、僵化、幻想的方案可以胜任。②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5页;第132-133、273页;第273页;第144-145、270-271、274页;第99页。
其次,涂尔干不同意圣西门关于经济领域失范是旧制度作祟的判断,相反,19世纪后期西欧经济领域失范乃至社会总体危机的根源不是旧制度的阻碍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恰恰是圣西门极力主张的“经济活动与个人利益的彻底解放”。③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5页;第132-133、273页;第273页;第144-145、270-271、274页;第99页。 的确,经济活动与个人利益的彻底解放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严重摧残了人心秩序,导致了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这也正是涂尔干研究社会主义的最初关注点。
第三,如社会主义者所说,解决方法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温和派主张以收入调节与财富再分配安抚无产阶级,激进派强调彻底改变生产资料的阶级属性并交付集体运行。涂尔干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道德总体衰退致使经济活动没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古典经济学同样没有),就此而言,要想从源头上解决阶级矛盾,就应当重塑道德对欲望的有效约束。涂尔干以近乎道德说教者的口吻说到,贪得无厌是一种病态,不要妄想满足已经被社会成功激发的欲望,那无异于“达那伊得斯姐妹的无底水桶”。④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5页;第132-133、273页;第273页;第144-145、270-271、274页;第99页。 可见两派都没能抓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他们的改革方案既不能医治社会的病症,也不能成为社会重构的恰当基础。⑤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理论的逻辑(第二卷)》,夏光、戴胜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07页;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123、126-129页。
第四,尽管圣西门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尚未切中转型危机的根源,但涂尔干在诸多思潮中依然更钟爱社会主义,这不仅由于社会主义与法国的历史社会境况更契合,也因为他个人“从内心里反对所有阶级间或国家间的战争”,反对人对人的残酷剥削与倾轧,渴望一场有益于整个社会而非某一部分人的变革。⑥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65页;第132-133、273页;第273页;第144-145、270-271、274页;第99页。 实际上,涂尔干一直试图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纷争中寻找一条调和的途径,他的学说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社会主义某些原则来改造作为社会事实的个人主义:(1)重塑“社会主义”,赞同借助国家、职业团体作为调控性的道德组织,保护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尊严,剥离“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生产资料公有化、国家中心论等激进主张;(2)重塑“个人主义”,个人的权利、利益和尊严不再基于自然正当,而源自社会力量的支持与保护。⑦ 肖瑛:《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社会》,2008(2)。
第五,涂尔干对社会主义的借助并非圣西门学派式的道德宣讲或神秘主义,而是试图通过道德科学的研究,在经验有效性的层面上发现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及其组织载体,确定这些道德规范“凌驾于人们心灵之上的原因”,并把这些规范与组织载体作为社会重建的对象,以制约泛滥的利己主义与社会的过度世俗化。可以说,正是对社会主义的考察与反思,促使涂尔干思考必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发掘神圣的道德力量,探索构建以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道德个人主义)为信仰、以有限财产观、正义契约、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为实践礼仪的新社会(宗教)体系。
Regulating the Abnormal Economic Life——Interpretation on the Durkheim's “Socialism and Saint-Simon”
Pan Jian-lei
Abstract: Socialism was a distinctive intellectual product of modern transition of Europe, and the reaction of collective conscience against the anomie of economy.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ism represented by Saint-Sim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Durkheim's research program on “social fact ” . He attempted to present the most general, impersonal and objective feature, and analysed the social pressure that urge Saint-Simon to propose new principles for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ons. Therefore, he could diagnose the collective pathema that stimulated soicalism, rethink its reasonableness and find the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laissez faire and compulsive regul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isi for the trea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ism; Anomie; Saint-Simon; Durkheim(责任编辑:黄家亮)
基金项目: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青年项目“涂尔干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18XQN005)。
作者简介: 潘建雷,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北京,100048)
标签:社会主义论文; 失范论文; 圣西门论文; 涂尔干论文;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