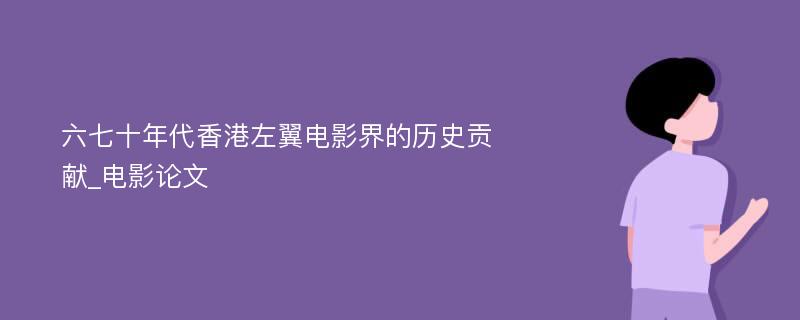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派论文,族群论文,香港论文,贡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5-0001-11 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心理开始转型,娱乐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大需求;同时,香港本土意识上扬,对左派文化极力排斥;再加上内地“文革”的政治影响,“长城”、“凤凰”、“新联”等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遭受了重大损失,从中兴走向了低谷。然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作用下,香港左派电影族群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烈的爱国意念、奉献精神、责任意识和创作热情,这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从未有过的。尽管曾经强势的左派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尽管香港左派电影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挂帅意识以及概念化等美学弊病,尽管左派电影产业被内地的政治运动和香港的政治迫害冲击得七零八落,但“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公司的统称)的影人们还是尽其所能,继续在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传播左翼文化,还是为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做出了一定的美学贡献和产业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颓势之中的左派影人还给中国电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至今仍被中国电影人所享用。 一、颓势之中的美学贡献 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美学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香港左派电影延续了香港电影文艺片中的人文脉流。香港影坛虽以商业类型片见长,但其中一直存在着文艺类型片的传统。香港文艺类型片较为特殊,其在创作上有西方国家艺术电影的某种理念,但在香港电影特殊的市场与文化氛围中,文艺片亦不可能进行非常自我的“作者”表述;其在选材上虽然不同于纯粹的商业片,而是以情感表现为主,但在制作模式、叙事手法和美学技巧等方面亦有强烈的类型特征,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香港电影的主要类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电影叠合在中国电影整体框架之中,中国电影中政治社会背景与个人情怀抒发相结合的创作模式也是此期香港文艺片的特色。这些影片或表达亲情伦理,或书写浪漫言情,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取向和政治理想。这种文艺片模式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中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数国产片、粤语片都在延续着该模式。6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新武侠片崛起,从此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电影取代文艺类型电影,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但文艺类型电影并未退出香港影坛,香港左派电影成为文艺片创作的主力,特别是这一时期在商业电影的挤压下,左派电影依然保持并延续着文艺片的脉流。这一时期“长、凤、新”摄制的《屋》(1970)、《大学生》(1970)、《肝胆照江湖》(1970)、《小当家》(1971)、《铁树开花》(1973)、《泥孩子》(1976)等众多影片,以深切的政治理想、清新的人文关怀以及感人的温暖人性在香港影坛竖起了文艺片旗帜,不但是对当时“邵氏兄弟”、“嘉禾”极其众多子公司等以血腥、搞笑、情色为主的商业电影的重要人文补充,提升了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而且延续了香港温情电影的脉流,使这一人文主义的涓涓细流在香港电影的滚滚商业大潮中从未间断。故此,香港电影才没有完全陷入商业电影的桎梏之中,并有了不断的超越。香港影坛的主体为商业片,香港商业片离不开其文艺片,文艺片滋养着主流商业电影的发展土壤,并为整体香港电影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在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影坛爆发了新浪潮运动,这次香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电影美学运动,便是在香港文艺片厚重的美学积淀下孕育而成的。而这一时期的香港左派电影,便是对香港文艺片的重要延续。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的创作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香港写实电影这一重要文艺类型的基础。虽然是“被改造”,但“长、凤、新”的大批一线创作者深入实际生活,他们创作的大量影片体现出了朴素写实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真情实感。其中的代表作《泥孩子》通过主人公素娟收留一个泥石流灾难劫后余生的小孩及为他找寻父母的遭遇,对政府的政策和官僚的办事作风作了尖锐的讽刺,表现普罗大众互相照顾爱护,共度时艰的美好品质。《泥孩子》出品于“文革”后期,可以看出,影片写的是住在安置区的基层港人生活,但写情写景都比较真切细致,摆脱了内地当时流行的“三突出”原则和刻意的阶级斗争观点。片中亦没有真正的“恶人”、“坏人”,对素娟也有不落俗套的心理描写,处处流露出一种温情主义。影片题材真实,手法上也参考采用了当年流行的灾难片模式,营造出危机逼近的紧迫感;片中插入飓风袭港的纪录片和实景拍摄的安置区日常生活,以之和厂景并置,高度逼真。真情和真实使其成为左派写实路线在20世纪70年代最突出的作品之一。影片表现出的关爱、清新和温情不但得到左派电影族群的认同,也为一般观众所接受。该片于1976年9月公映,三天就收得票房50万港元,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成绩。[1]此外,由“长、凤、新”给予经济支持的子公司——现代制片公司摄制的《半生牛马》(1972),亦是当时写实片的代表作。这部影片由著名粤语片导演李晨风执导,以散仔馆①的生活为题材,拍摄时力求写实: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主创当时曾往土瓜湾珠江戏院邻近的散仔馆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务求做到写实。《半生牛马》不单室内戏有真实感,街景也拍得很自然,看得出四周的行人没有注意到镜头存在。当时拍周聪与苗金凤在街上逃跑的镜头,是在佐敦道裕华国货公司楼上公寓,租下一间向着大街(弥敦道)的房间,可以望到对面的立信大厦,然后在房间内安置摄影机,从高处拍下。由于当年没有手提电话或对讲机这类通讯设备,导演与演员在商量好如何走位,及开始做戏的暗号后,便开始拍摄。虽然当时街上人来人往,但由于没有摄影机在场,加上演员的衣着打扮亦不起眼,拍完又马上离开现场,因此街景拍出来很有实感。[2]157 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香港文艺类型片的写实传统。20世纪80年代,香港影坛重要的、以写实见长的文艺片导演如许鞍华、张之亮、刘国昌、方育平、张婉婷、冼其然等人的作品,莫不受这种写实风格的影响。《半生牛马》被认为是后来著名纪实片《笼民》(1992)的先驱。[2]157这一时期左派电影的写实风格也影响到了香港电视美学的发展,如香港20世纪70年代轰动一时的著名电视剧《狮子山下》,亦借用了左派写实片的特性,“聪明地像‘左派’传统那样关注贫苦大众,让他们骂骂官商洩洩怨气,而又调和劝道,达到讨好小市民并为政府宣传之目的”。[3]231 其次,这一时期的左派影人的类型意识尽管受到了内地“极左”影响,但仍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类型片,对香港电影类型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一,表现为对武侠类型的贡献。武侠片是香港电影的最重要类型之一,“长、凤、新”继《金鹰》(1964)、《变色龙》(1965)、《我来也》(1966)、《云海玉弓缘》(1966)等武侠类型影片后,又推出了《双枪黄英姑》(1967)、《侠骨丹心》(1971)等以武侠类型为主的影片,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双枪黄英姑》,该片“是乡土侠义片,陈思思饰演逼上梁山的神枪女侠,在抗战时期领导绿林好汉大战恶霸、汉奸和日军,此片热闹生动,相当叫座”。[3]227 其二,这一时期“长、凤、新”还推出了有着自身特色的歌舞类型片,其代表作便是《双女情歌》(1968)、《海燕》(1970)等。当时“邵氏兄弟”等制片公司也推出了《香江花月夜》(1967)等多部歌舞片,但那些舞蹈的内容和形式是欧美式的或者是日本化的,且故事情节往往苍白无力或灰暗低沉。《双女情歌》、《海燕》则打破了这种类型常规,通过银幕向观众展现了健康的、富有中国民族色彩和现实基础的民歌或歌舞。《双女情歌》是一部以歌唱为主的表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撒尼族人生活的音乐故事片。该片的作曲草田收集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音乐资料,创作改编成了全片中20多首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歌曲,使当时沉醉于大量时代曲和欧美流行曲的香港观众听到了清新、动听的中国民歌。《海燕》中亦有各类中国民族歌舞七场之多,如“彝族青年”、“彩练双飞”、“长城颂”等,以及一个描写渔村生活,充满地方色彩舞剧的“上海女儿”。此外,《海燕》还叙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光明的故事,与歌舞交相辉映,使其避免局限于一般的歌舞纪录片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之后香港电影歌舞类型的表现内容。 这一时期其他类型片如《白领丽人》(1967)是香港电影中较早表现中环写字楼中职业女性的影片,夏梦等漂亮女星主演,具有相当的时尚性。《离婚之喜》(1967)也是白领夫妻斗气的喜剧,批评丈夫升迁发达后不顾情义,妻子宁愿去做贫苦工人。这些表现资产阶层的喜剧片对当时其他香港电影公司在喜剧片创作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讽刺喜剧《一磅肉》(1976)亦借题发挥,抨击时弊,以荒谬手法讽刺法律与奸商。这一时期左派喜剧类型片对香港电影影响最大的影片当推20世纪60年代“邵氏兄弟”新拍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1963),该片致使香港粤语电影再度红火。 自20世纪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摄制开始,直到70年代初,香港电影产业中粤语片与国语片产业一直泾渭分明。从产业特色到美学特色,两者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在不同的时期体现着不同的成就。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香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审美心理的变革,以及粤语片本身的诸多问题,香港粤语片产业开始萎缩,至1972年,香港全年投产的粤语片数量为零,几度辉煌的香港传统粤语片结束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香港电影的历史舞台。一年之后,一个成功的剧目——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终于再次掀起了粤语片的复兴,不同的是,这次复兴不是对以前传统粤语片产业兴旺时期的简单重复,而是开创了粤语与国语电影业合流的新型电影产业。 这部改变自同名舞台讽刺剧的影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在一个月的映期内就狂收560多万港元的巨额票房,在香港创下的票房纪录,超过了当年李小龙电影《猛龙过江》的53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该片的草根美学指向以及生动亲切的粤语对白,沿袭了传统粤语片的美学特征。它出品于“邵氏兄弟”的大型片场之中,是明显的“大厂体制”产物,具有鲜明的国语片产业特色。而且,它在制作过程中吸收了电视特色,据影片编导楚原回忆:“因为当时的EYT(即电视节目《欢乐今宵》)很受欢迎,我便想如果把没有拍过电影的EYT演员加进去,观众一定会喜欢的,所以我将一半EYT演员,混合一半邵氏演员,拍成了《七十二家房客》。”[4]影片成功地把电视建立起的艺员明星移植到电影中去,从而吸引了大量观众。这种模式随即被广泛采用,之后卖座的新型粤语片不但引入电视演员,而且某些具体情节直接取自电视,同时保持了电视情景喜剧的特色,其中《鬼马双星》(1973)、《香港七十三》(1973)、《大乡里》(1974)、《游戏人间三百年》(1974)、《多嘴街》(1974)、《新啼笑因缘》(1974)等,内容皆脱胎于受欢迎的《双星报喜》、《七十三》、《欢乐今宵》、《大乡里》等电视节目。这种新型产业融合了传统粤语片、国语片、新兴电视节目以及外国电影的诸种产业模式和美学手段,形成了与传统粤语片和国语片完全不同的新香港电影。新香港电影的出现使得粤语片复兴的势头很强,逐渐导致以后的国语片或其他方言的影片都有配粤语对白的版本。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电影在语言形态上全部统一为粤语。此后的香港电影便没有了国语片产业与粤语片产业这种明确的分别,而是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香港电影。 《七十二家房客》原为出自上海的舞台剧,其电影形态首推1963年“新联”和内地珠江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同名影片,当时很受欢迎;随后由“长、凤、新”排演、朱克导演的话剧版也很叫座。20世纪70年代初,此剧再由香港影视话剧团搬上银幕,轰动一时;最终“邵氏兄弟”再次翻拍,并致使香港电影产业和美学发生大变革。香港电影的这种美学和产业新变,是“邵氏兄弟”和其他影视企业对左派电影特色“活学活用”的结果,亦是香港左派电影对香港电影的重大贡献之一。 再次,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的美学贡献,表现为推出了众多优秀的纪录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许多表现当时社会风貌和民族文化的优秀纪录片被南方公司引进到香港,深受香港观众的欢迎。时值六七十年代,左派影人拍摄故事影片存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和资金压力,而选择纪录片拍摄则既安全,又会受到香港观众的欢迎,于是这一时期,“长风新”出品了多部优秀纪录片。这些影片在香港引起了较大反响,取得了较好的票房受益。如表现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万紫千红》(1974)当年票房突破了百万港元,成为较卖座的影片之一。同时,这些影片对之后香港和内地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时期“长、凤、新”出品的纪录片,前期主要是纪录乒乓球比赛的纪录片,如1971年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两部纪录国家乒乓球队访港的《中国乒团汇报表演》大型纪录片;1972年“长城”出品的记录北京举行的亚非乒乓球邀请赛的影片《友谊花开》及“凤凰”出品的表现广州新风貌的《欢乐的广州》等。后期纪录片在内容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录体育赛事的《杂技英豪》(1974)、《万紫千红》(1974)、《中国体操技巧比赛特辑》(1975)、《中国体坛群英会》(1976)等;另一类为表现内地风情的影片,如《春满羊城》(1974)、《白云山下谱新歌》(1975)、《武夷山下》(1974)以及《桂林山水》(1975)等。 这些影片探索出的独特艺术手法,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美学经验。第一方面,尝试对人物进行性格塑造,如对广州杂技团演出进行记录的《杂技英豪》中尝试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成为当时人物纪录片的先行者。譬如在“转碟”这个节目中,影片除了把拍摄重点放在演员折腰咬花这组动作上,也不忘记介绍主要人物形象。在演员咬花后,给了一个特写镜头,在这个镜头里,演员始终保持一种从容不迫、优雅镇定的神态。这样,观众不是单纯为杂技技巧而鼓掌,主要是为能表演出这样美妙艺术的演员而鼓掌。第二方面,这些纪录片都力图呈现厚重的历史感,如《万紫千红》虽以乒乓赛为中心,但其他内容如团体操、舞狮、武术表演,就占了全片的前半部,中间还拍摄了各国宾客到各地游览访问的情境,尽显中国内地文化。《杂技英豪》在介绍广州杂技团表演节目之前,先向观众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其中有出土文物画片、拓片,古籍文字记载,敦煌壁画的临摹画等,让观众对中国杂技艺术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有大致的了解。第三方面,这些纪录片在电影语言层面也进行了探索,甚至奠定了纪录片的某种镜语规则。《杂技英豪》运用电影的特殊技巧,把演员表演时快如电光的动作,如“钻地圈”的各种钻法、“大武术”的不同跟斗等,用慢镜头表现,让观众有充裕的时间看清楚其中的奥妙。在剧院里,观众观看杂技有顾此失彼之感,而电影则可以分别用近镜介绍,还能用分切画面的技法,让观众既清楚地看到底座表演,又能欣赏尖子的表演。其他如俯摄、仰摄等角度,更是剧院观众所不能看到的。充分发挥电影的特长,运用各式技巧,淋漓尽致地把杂技节目中的精华再现在银幕上,有助于消除剧场观看中存在的那种隔阂感,收到了在剧场观看难以得到的效果。而表现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中国体坛群英会》体现出了非凡的摄影功力和景别叙事能力,和当下的众多体育报道类纪录片并无大的差别。导演把歌舞表演《红旗颂》八幕的内容,作为一条主线,其中穿插了全运会各项体育活动,还有各地风光、军事表演、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专业歌舞团精湛的演出和中国登山健儿再次胜利登上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事迹等等。影片除了运用阔角度拍摄的大场面,充分表现出中国体坛的色彩缤纷、气势宏伟之外,还利用大特写及细致的描写手法,引人入胜。尤其是过去较少使用的“追踪摄影”、“慢动作”等手法,镜头运用稳健,恰当地拍出运动项目动作的高潮。同时,拍摄者敢于创新,如单杠演出,摄影师运用了从地面向上仰拍的镜头,利用场馆顶上圆形的灯饰,美化了单杠运动员潇洒自如的各种姿态。又如射击项目,一个镜头中同时表达了三个不同角度的画面,使观众在同一时间里看到了射击选手举枪射击同时中靶的精彩场面。 最后,这一时期香港左派影人拍摄出了一些颇具艺术价值和思辨价值的大片,为香港电影史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云海玉弓缘》、《屈原》(1974)便是其中的代表。《屈原》拍摄于“文革”后期,当时内地的政治氛围虽依然高压,但已有诸多松动的迹象,香港左派影人们也有精力进行更多的艺术思考。当然,政治影响根深蒂固,《屈原》的创作也无法避免某种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局限。 影片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考量屈原这一历史人物,刻画其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影片编剧也着重表现他的政治理想:看穿秦国“连横政策”不利于楚而加以揭露;提出变法改革。为了突出正邪之间的对立,影片对人物性格进行了一些雕琢和概括,集中刻画南后,将她典型化,表现她为了维护一己利益而反对变法,误国误民的本性。影片对婵娟和宋玉的刻画抛开历史而趋于符号化:一个不畏卑微,紧跟屈原,坚持爱国为民;一个则慑于权势,甘作小臣。影片的创作态度较严肃,在艺术层面精益求精,对历史和其他细节做了较多考证,在真实的基础上,力求庄严、华丽,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历史故事片。同时,影片富有深邃的思考,其深刻的思辨价值值得今人去重新读解。对此,有香港学者谈道: 此片筹拍于”文革“后期“四人帮”当权的一九七四年,由于长城、凤凰、新联和国内有着长远、密切的关系;”文革“政局的变幻不断影响着“长、凤、新”的制作路线。《屈原》写的是历史人物。但由于写到满怀壮志的屈原备受奸臣的压制、迫害,以致忠良被诬害打倒,奸人谗臣当道,颇有感怀于“四人帮”当道的时势,而为周恩来、邓小平被夺权,和无数忠良知识分子被迫害而悲伤、慨叹之意。影片改编,编导演方面都显得比较拘谨,人物塑造亦多少留有样板化的痕迹,但不掩那份迷茫、悲伤与悲剧感,这正是香港文化人面对“文革”思想感情的自己流露。[5] 影片由当时“长、凤、新”的重量级影星出演,阵容豪华,制作浩大,对道具、布景、服装、歌舞,主创都做过了一番考证,且都很讲究;影片思辨深刻,矛盾激烈,人物严谨,对白铿锵有力,场景大气,是一部能够在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制作影片。 二、左派强势文化的维系 除了上述美学贡献外,这一时期香港左派影人还做出了较大的文化贡献。“六七暴动”的历史事件和香港本土文化的崛起,使得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形成的强势左派文化愈来愈弱,直至被边缘化。尽管如此,香港左派电影族群从未停止过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左派文化传播,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这样的左翼文化依然没有消亡,这应当说是香港电影作品族群强力维系的结果。 1967年10月,以“新联”为主,左派电影人排演了粤语版话剧《红灯记》,在普庆戏院等左派戏院演出。1968年,“凤凰”出品了根据京剧样板戏《沙家浜》改编的国语故事片《沙家浜歼敌记》(编导:鲍方);“新联”则出品了根据同名京剧样板戏改编的粤语故事片《红灯记》(编剧:卢敦;导演:黄雄)。同时“长、凤、新”话剧团还在普庆剧院演出了话剧《沙家浜》。这也是经过学习改造和思想洗礼后回到香港的“长、凤、新”,以行动来表明紧跟内地政治风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决心。此番演出,导演为鲍方,主要演员分为A、B两组,A组为江汉(饰郭建光)、朱虹(饰阿庆嫂)、童毅(饰沙奶奶);B组为江龙(饰郭建光)、梁珊(饰阿庆嫂)、冯琳(饰沙奶奶);主要演员还有姜明(饰胡传魁)、石磊(饰刁德一)等。为了达到演出目的,大部分演艺人员在排演过程中都要按照剧本逐句理解,以阶级斗争为思想指导来详细分析角色,听取领导和其他人的意见,并写出思想汇报。 此外,在每年的国庆前夕,香港左派电影族群均要进行文艺演出,内地“文革”之后,这种演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就更为强化:1968年国庆节,“长、风、新”举行大型舞台剧《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公开演出;1969年,为庆祝国庆廿周年,“长、凤、新”举行《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大型综合演出。至1970年,“长、凤、新”将这种文艺演出推向了高潮,当年8月22—23日,经营“长、凤、新”院线的丰年娱乐公司主办音乐会,在普庆戏院演出,节目包括《毛主席诗词组曲》等。之后,“长、凤、新”参与了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举办的大型演出。“长、凤、新”参与演出,提供的主要节目为造型朗诵《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演出共分八组,分别将八个“革命样板戏”造型悉数搬上舞台。第一组:《工农兵》;第二组:《红灯记》;第三组:《红色娘子军》;第四组:《沙家浜》;第五组:《智取威虎山》;第六组:《白毛女》;第七组:《海港》;第八组:《奇袭白虎团》。此外,有粤曲演唱《主席声明》。王小燕、朱虹、王葆真、平凡、江龙、方平、梁珊、劳若冰、谢瑜、鲍起静、童毅等一线主力和众多年轻演员全部参与了演出。1972年,“长、凤、新”主办了“电影界庆祝国庆廿二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之后,每年9月15日到10月9日的国庆期间,“长、凤、新”都举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演出。这些演出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的,全港爱国机构、爱国学校都要排练节目参加演出,其中开场、闭场节目都是电影界主演的,中间则是其他爱国机构的节目。但是每次演出,港英政府都要严格审查节目,一些节目会遭禁演,港英政府在演出时都要到现场监督。 以上诸如在香港本土拍摄左派电影,将内地的“革命样板戏”搬上香港银幕,在港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的大型文艺演出,举行国庆纪念活动等等,都是左派电影族群在香港进行的左派文化建设活动,使左派文化在艰难环境中仍能延绵不绝,维持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除此之外,左派电影族群还多次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演出,努力在东南亚地区维系左翼文化。其中比较重要的互动有两次,第一次为1971年3月24日至4月1日,“长、凤、新”银星艺术团应马来西亚雪州华校校友会赈灾工作联合委员会邀请,在团长廖一原的率领下赴吉隆坡协助救灾(水灾)筹款演出,演出地点在国家体育馆。傅奇、石慧、江汉、草田、王葆真、王小燕、劳若冰、方辉、江龙、丁亮、张铮、冯琳、鲍起静、黎广超等参加演出。节目有大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男声独唱《我是个石油工人》等,女声独唱《千里草原把身翻》等,民乐合奏《草原新曲》等,大型舞蹈《大团结之歌》,手风琴合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男声表演唱《川江号子》等等,大部分节目具有较强左翼色彩。这次演出在当地造成了强烈的文化影响和政治影响,当地报纸《星洲日报》报道: 银星艺术团的这次演出,是阵阵的春雷,坚持健康文娱阵地的艺术团体,应该在它的鼓舞之下,继续加倍的努力发展健康文娱的活动,大长积极,健康和正派的文娱活动的威风,大灭黄色,灰色文化的霉气。我们诚挚地希望,通过这次演出之后,我们可以见到健康文娱的日益抬头,会有更多坚持正派艺术活动的团体出现,更加积极和广泛地推广健康的文娱活动,让我们的艺术坛一扫过去的颓废风气,尽荡群魔,开拓一个正派健康文娱活动蓬勃发展的年代。[6] 而当地1971年3月29日的《中国报》以《大马正执行新外交政策》为题,评说银星艺术团访问演出的政治意义。这次演出不仅显示出左翼文化的影响,更影响到了海外对新中国的重新认识及外交政策的调整。 第二次国际演出为1976年11月,“长、凤、新”银星艺术团应邀到菲律宾义演,演出人员基本上是1971年赴马来西亚的原班人马,演出节目更倾向于左翼。其中代表性的节目有舞蹈《彩绸舞》、《喜送粮》等,民乐合奏《早春》、《北风吹》等,笛子独奏《牧民新歌》等,钢琴独奏《快乐的女战士》等,男高音独唱《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等等。这次演出也产生了较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三、式微中的产业贡献 这一时期,式微之中的香港左派电影,对香港电影和中国电影的产业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种贡献首先表现在电影人才的培养方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还没有专门培养电影人才的学校或者机构,其电影人才的培养一般都是靠影视企业内部的培训机构。六七十年代,香港较有影响的影视培训机构是“邵氏兄弟”总裁邵逸夫担任重要股东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全名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TVB)主办的电视艺员培训班,该培训班培养了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钟镇涛、杜琪峰、林岭东、吴孟达、伍卫国、黄日华等日后为香港电影做出重大贡献的影人。该“无线电视台”艺员培训班在某种程度上是参照当时左派电影机构的培训方式而办的。 为了加强左派电影的实力,在内地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建议下,香港“长、凤、新”机构于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举办电影人才的培训机构。1968年,“长、凤、新”联合举办最大规模的一次演员训练班,包括部分工作人员共计25人。时值“文革”,培训班对学员的“背景”格外注意,成员主要来自香港、培侨、汉华、劳校等几家爱国学校及爱国机构。学员由李嫱、姜明负责选拔,李嫱、冯琳、唐龙、草田、吴世勋、童毅等“长、凤、新”的演艺人员担当不同的培训科目教师。培训班对学员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并制定有专门的培训方案《新演员训练规划草案》。前三个月学员主要是学习电影理论及基本知识,并参加国庆节目排练、演出;之后三个月则集中在清水湾片厂留宿实习,了解影片的制作程序。半年后,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有的被派往工厂去体验生活,有的则开始参与影片制作。一年之后,才将学员正式分配到这三家公司。左派电影的重要人物如方平、蒋平、鲍起静、向桦等演员,以及施扬平、吴沧洲、林炳坤等其他方面的演艺人才,都是出自此期培训班。此后的两年中,“长、凤、新”连续两次举办“长凤新新人训练班”,学员也是全部来自当时的香港爱国学校,先后培育出了张康达、平逸玲、徐佩斯、李颂华等演艺和管理人才。而“文革”期间重要的武侠片《侠骨丹心》(1971),就由多名“长、凤、新”演员训练班毕业的新演员参与演出。 “长凤新新人训练班”的成功举办,启发了香港其他演艺机构,这些机构认识到,在全港没有正规电影院校培养电影人才的情况下,这种企业内部的培训机构具有极大的产业意义。为加强实力,该培训班在和当时另一香港电视机构“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台”的前身)的竞争中占领先机。“无线电视台”于1971年联合“邵氏兄弟”举办第一期电视艺员培训班,许多日后为香港电影做出重大贡献的影人皆出自这一期培训班。学员毕业后大都和“无线电视台”签下合约,拍摄电视连续剧等各类电视节目。有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后,自1973年起,“无线电视台”开始更多地自制节目,成为香港最具竞争实力的电视机构,也引领了香港娱乐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左派电影族群的另一产业贡献,是1969年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内建成了清水街外景地。该外景地实际上是一条古装布景街道,由片厂的专业人员和普通职工自己动手、合力建成的。为了长期使用,清水街布景的设计及建造以坚固和实用为原则,以求其能经受风吹雨打。整个街道的布局,是一座两丈余高的城楼延伸出两排街道,既古色古香,又气派不凡。该片场后来不仅为左派电影公司所用,也被其他制片公司所用,成为全香港重要的片场之一。 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第三方面的产业贡献表现为院线业的开拓及内地纪录片的发行。以南方公司为主的左派电影发行、院线、放映业务虽在这一时期严重受损,但也尽量以各种办法维持经营,并努力开拓院线。由于内地电影和“长、凤、新”电影的创作颓势,“双南”院线需要发行、放映外语片来维持。作为龙头戏院的普庆戏院,开始与港岛区的龙头院线组成“普庆线”,连同一些地区的小戏院,以放映好莱坞八大公司及欧洲名片为主。高陞戏院在20世纪70年代初拆除,建成侨发大厦,而新戏院需要扩充进来。1972年,在原来戏院的基础上,南方公司在内地有关部门的资助与领导下,又为“双南”院线增添了新戏院——新光戏院。该戏院由中国银行在北角原商务印书馆馆址上投资改建的侨辉大厦内建成: 原计划是要作为双南院线在北角区的电影放映据点,同时兼演舞台戏。建造时由侨光置业公司陈康副经理及南方公司许敦乐两人负责统筹,中国银行港办总稽核潘静安兼任监督,并曾参考北京、广州等多家大型剧院。戏院内设有大型旋转舞台及化妆间,有第一流的放映机、音响、灯光设备,还有最新式的舒适座位。戏院大堂由名家文楼和许敦乐合作设计,采用汉白玉石及铜刻嵌镶,外墙白瓷砖孔雀蓝,新型、大方又具民族色彩,美轮美奂。[7]94 新光戏院落成后,在开幕式时却面临无片可放的窘境。南方公司以纪录片《新考古发现》救急,不料此片在港发行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从而带动了香港的中国文化考古热潮。对此,时任南方公司负责人的许敦乐如此回忆: 公映以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连映了三十九天、一千二百二十场。影片中的内容很快成了街坊、茶楼议论的话题……该片观众将近九十万人次,收入二百五十多万元,为中外纪录片收入的最高纪录。当时船王董浩云,听说有这样一部纪录片,也想见识一下。看完之后,他们都认为大开眼界,毕生难忘。[7]94-96 发行纪录片也成为南方公司之后的重要选择。该公司再次发行了《成昆铁路》等多部振国威的内地纪录片,再次在香港引起轰动。《成昆铁路》于1975年在双南院线公映,该片展现的是修筑成昆铁路的过程,该工程十分浩大,还要克服重重天险,很吸引观众,收到较好的效果。影片展现了成昆铁路完全由我国自己设计、施工,采用的钢铁也都是自己钢铁厂制造的,这就更加震撼国际,也被当时的香港观众所追捧: 中国人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个时候凡是以为祖国争光、扬眉吐气为内容的纪录片(如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比赛中勇夺冠军的纪录片)都能吸引大量观众。曾有一家专门放映国产电影的戏院的股东,初时看到国内建设水库的纪录片中有很多干部和工人、农民、解放军参加劳动,没有笑料又没有故事情节,于是就反对排映,认为“光是挖土、挑泥,有甚么好看?”。后来还是接受上映了,结果却是排队买票的长龙不断。[7]96 这些纪录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再次引发了香港社会探秘中华历史文化的热潮以及爱国热情,充分展现了内地电影及内地因素对香港电影和香港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对今后两地电影的互动也产生了较大的促进。 应该说,在这一时期特殊的困境中,香港左派电影族群选择了顽强的坚守,个人的境遇痛苦最终被对电影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所取代,在艰难的产业条件下,这一时期的“长、凤、新”体系仍创作了近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常被冠之以“极左”、“概念化”而遭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影片都是体验生活下的用心之作,体现着爱国主义层面下“长、凤、新”影人对电影的爱及坚守。这种爱没有商业考量、投机等杂念,没有个人私利,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爱。这种对电影的真爱,对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是“长、凤、新”影人留给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产业的精神财富。当下的中国影坛,更需要这种精神力量。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前后两个30年自然形成了内地和香港电影互动的两个阶段,前30年给人的印象是微弱的,而后30年是强劲的。然而正是由于前30年的潺潺细流打通了通道,才有后30年的滚滚洪流,而香港左派电影族群便是打通这一通道的唯一执行者。尽管有许多波折和痛苦,但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坚守,维系了香港和内地电影的产业、美学和心灵的通道。正是他们的坚守,才使两地的电影互动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没有彻底中断,这一时期的星星之火,最终使得两地电影互动在内地改革开放之时呈现出了燎原之势。 收稿日期:2014-06-17 注释: ①散仔馆为粤语,大意是指家庭小旅馆。标签:电影论文; 香港电影票房论文; 电影类型论文; 七十二家房客论文; 香港论文; 屈原论文; 香港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