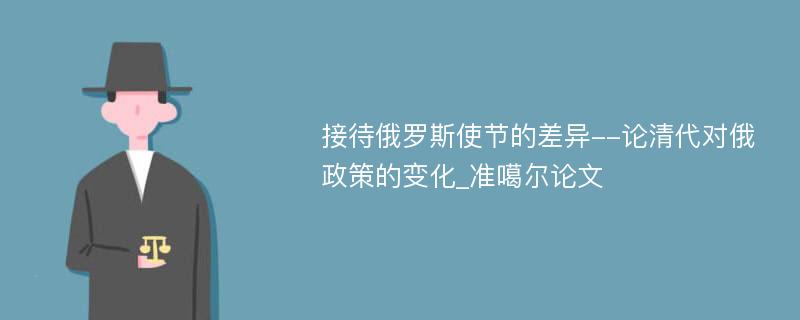
接待俄使之异:论清朝对俄政策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之论文,清朝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所谓“觐礼之争”,即因中西礼仪不同,外国使者不愿被当作中国皇帝的臣属,故不愿接受清朝安排的觐见礼仪。①过去的研究多指出冲突的起因不只是中外觐见礼仪的差异,更多是外人感受到不平等的歧视,故礼仪问题还隐有中外双方对国际秩序原理的不同看法。②对西方诸国的政治身份,《清史稿》虽失之简略,却概括了清政府对外交涉的观念转变。③《清史稿》指出,咸丰、同治朝以前,清政府视西方诸国如同属藩,但咸丰、同治朝以降,清政府不得不将西方诸国视同敌体之国,与之遣使缔约。事实上,俄国是第一个与清帝国使用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④可见《清史稿》的说法并不完整,有待商榷。同时,根据清俄关系的变化,可知清初诸帝理解天下秩序的局限性,必须另谋他策,将那些不称臣纳贡的化外之国,尽可能地纳入“天下秩序”。⑤
在与外国的交往之中,清帝国采取现实主义,往往视往来国家的动机与实力,调整其定位,再安排负责的机构与接待礼仪。清初诸帝吸取与传教士交往的经验,以特殊礼节,或站立,或握手,或屈膝不叩首。⑥对于俄国,清帝国视其为“敌体之国”,对等相待,故俄国使者未必都向皇帝行跪拜礼。这与过去学界主张的“天朝观”似有矛盾,⑦尤其是论及俄国使团的觐礼问题时,着眼于觐礼之争,或批判清朝君臣迂腐保守,或视俄国如同属藩,要求俄使遵行朝贡礼的成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⑧这些成果固有所见,却忽略清、俄两国并非宗藩关系,而清初诸帝对待俄国使团的觐礼问题,自有其现实的考量。因此,有必要考察清帝与俄国使团的互动,并观察顺治朝至乾隆朝对俄国的态度,借以分析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优礼俄国使团的意义。本文讨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对俄政策及其接待俄国使者的礼仪问题,说明顺治朝的对俄政策到了康熙中期已有转变,康熙、雍正皇帝皆采取对俄亲善的政策,故视俄国为“敌体之国”,优待俄国使者,不完全依照“朝贡礼”的方式强迫俄使行跪拜礼。不过,中俄关系的对等往来,在官方文书中多有隐讳,仍强调这些办法只是皇帝优礼俄使的恩德,以保持皇帝的体面,也回避俄国是否为属藩的问题。准噶尔问题解决后,乾隆中期对俄政策又为之一变,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皆否认曾优待俄使的先例,对外政策重回“朝贡礼”的路线,再搭配互市制度,将这些不称臣纳贡者归入“天下秩序”之中。⑨
二、遵用汉法:顺治朝拒见俄使的意义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与俄国的往来可谓密切,并留下了大量的官方档案、文书及信札。从这些资料可知,俄国曾提出平行国交的要求,始终坚持与清帝国平起平坐,也发生过俄国使者觐见清帝的礼仪冲突。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俄国派遣使者巴伊科夫(Ivanovitch Baikov),带着俄国沙皇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 й Миха йлович Тишайший)的国书,欲与清帝国建立外交管道。⑩使团出发前,俄国政府已听说中国礼仪繁琐,还会要求外国使者下跪,履行丢脸的仪式。(11)为了避免俄使受辱、维护俄国的体面,俄国沙皇颁下训令,命令俄使巴伊科夫觐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其他如亲吻礼仪、递交国书、呈送礼物等细节,也详列办法,不愿接受中国安排的礼仪。(12)据陈维新的研究,可知俄国使员须遵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并注意外交礼仪的问题,确保沙皇尊号的荣耀。一旦有折辱沙皇的礼仪问题,俄国使者宁可放弃觐见,也不可行损害沙皇荣誉的礼仪。(13)因此,巴伊科夫遵守沙皇训令,不愿先交出俄国国书,坚持觐见顺治皇帝,再面交国书,并声明自己是沙皇的代表,只能站立递书,绝对不行跪拜礼。(14)
顺治朝延续明代对外交涉的惯例,遵行“朝贡礼”,不愿变通觐见礼仪。因此,中俄双方对递交国书、觐见礼仪的看法,争执不下,反复谈判6个月,仍无法解决问题。(15)经诸王大臣部议后,理藩院只好驱逐巴伊科夫使团。(16)后来,巴伊科夫虽派人赴北京求情,并答应行跪拜礼,请求俄国使团能返回北京,觐见皇帝。(17)顺治皇帝虽不同意巴伊科夫重返北京的要求,仍让巴伊科夫携回致沙皇的诏书:“谕鄂罗斯国察幹汗曰: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劾忠顺,以副恩宠。”(18)从顺治皇帝的诏书内容,可知顺治朝的对俄政策,乃延续明代对外交涉的惯例,采取以上对下的书写方式,对俄国沙皇只称“察幹汗”,(19)要求俄国永远效忠,可知顺治皇帝认为俄国是归化中国的外夷,而俄国遣使递书的行动只是进贡方物。既然俄国已纳表归化,即是皇帝臣属,应视同属藩,俄使自然为贡使,故理藩院以“朝贡礼”相待。但俄使要求觐见、面递国书,已逾越属藩陪臣的分际。因此,理藩院若接受俄使的要求,等于让顺治皇帝自降身份,与沙皇平起平坐,才有驱除俄使的举动。
由于巴伊科夫使团迟迟未归,俄国沙皇担心中国扣留俄使,再次遣阿勃龄(Serkur Ablin)来华递书,并准备承诺今后俄国不再骚扰达斡尔地区,以换回巴伊科夫等人。(20)可是,当巴伊科夫等人回国后,俄皇立刻改换新国书,删去原先的承诺。(21)或许是鉴于巴伊科夫的失败,俄使阿勃龄不再坚持亲递国书,同意先将国书呈交理藩院,再觐见皇帝。可是,阿勃龄提出中俄应建立平等国交的要求,并指出中国既允许信奉耶稣教的国家来华传教,俄国也希望与中国建立国交,互换使节,让中俄两国商人可自由通商,希望清政府豁免俄国货物的出口税:“若干耶教国家已与中国发生外交关系,余甚愿与殿下永固友好,交换使节……甚盼殿下,准中国商人携各项货物到俄贸易,俄国货物中如有中意者,亦可自由输入中国,勿庸纳出口税。”(22)顺治君臣在意的是俄使的请觐与国书内容,不愿讨论俄国自由通商的要求。对顺治君臣来说,只有皇帝有权决定俄使能否觐见,觐见之事怎可出于俄使的要求。(23)而俄国国书日期采俄历纪年,违反“奉正朔”的原则。更糟的是,俄国沙皇竟自称大汗,对顺治皇帝只称“殿下”,而不是“陛下”。这些要求,让顺治皇帝大感不悦。(24)最后,诸王大臣会议以俄国国书不符合属藩表文格式为由,建议皇帝应驱逐俄使,退回贡物:“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表内不遵正朔,称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又自称大汗,语多不逊。下诸王大臣议,佥谓宜逐其使,却其贡物。”(25)顺治皇帝虽不满意俄国国书,但没有驱逐俄使阿勃龄,仍视同贡使,命理藩院设宴款待、查收贡物。(26)由此可见,俄方与中方的心态相同,皆视对方为臣属。但俄国沙皇分庭抗礼的心态,使顺治君臣相当不满,明令理藩院向俄使说明皇帝拒见的原因,并要求俄国不必再遣使递书,主动切断与俄交涉的管道。
三、敌体之国:康熙朝的对俄政策
经此挫折,俄国暂时不再派使来华,但沙皇仍有进占中国的野心,(27)先后占领雅克萨、尼布楚等地,甚至收容了战败叛逃的通古斯部酋长根忒木尔,威胁清帝国在黑龙江上游的统治地位。(28)俄国步步逼近,让康熙皇帝不得不派兵赴黑龙江一带防卫,并向俄国抗议,要求其交还根忒木尔,不许再骚扰边境。(29)但俄不但不遣回根忒木尔,反而派使者密洛瓦诺夫(Ignati Milovanov)前往北京,宣达俄皇密谕,要求康熙皇帝向俄国纳贡,成为俄国的保护国。(30)密洛瓦诺夫抵达北京后,似未拿出俄皇密谕,也没有向清政府说明俄人占领尼布楚的事实,甚至还向康熙皇帝行跪拜礼。(31)密洛瓦诺夫的恭顺态度,让康熙皇帝误以为中俄边界的冲突不是出自俄国政府主导,只是少数哥萨克边民闹事。于是康熙皇帝致信俄国沙皇,要求俄国约束哥萨克边民,不要再侵犯中国边境。(32)俄国政府虽未能解读这封信件的内容,但因当时俄国正与波兰作战,又有贵族引发的内乱,不愿再与中国开衅。(33)因此,俄国再次遣使来华,欲解决边境问题,但对清帝国引渡根忒木尔的要求,多有推托。(34)
康熙十二年(1673),俄国沙皇派遣尼果赖(Nikolai G.Spathary Milescu)率团来华,并指示尼果赖搜集沿途所见的各种情报,建立一条由西伯利亚到达北京的快捷通道。(35)康熙十五年(1676),尼果赖使团抵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由礼部侍郎马喇迎接使团,尼果赖却提出接待礼仪的问题,让马喇难以响应。(36)若按照“朝贡礼”的方案,尼果赖等人自然被当做贡使,而贡使入境,应拿出国书、表文,证明其使节身份。尼果赖却表明自己是沙皇全权代表,只愿与中国皇帝对话,并认为中国官员位阶太低,无权过问俄国国书。(37)同时,尼果赖也要求马喇先来拜会,否则不接受中方的邀请。礼部侍郎马喇虽未能得到俄国国书,但康熙皇帝仍允许尼果赖进京谈判,希望能解决哥萨克侵入边界的问题。(38)
尼果赖进入北京后,理藩院要求尼果赖先交出俄国国书,并要求尼果赖觐见皇帝时,需行跪拜礼。然而,尼果赖仍坚持向康熙皇帝面递国书,还要求觐见皇帝时,康熙皇帝必须站立,向俄国沙皇问安,表示两国平等。(39)就这样,因递交国书的仪式问题,中俄双方相持不下。(40)最后,理藩院采取折中的办法,在午门特设一张铺着黄绸的桌子(黄案),让尼果赖将俄国国书放在黄案上,由大学士转交皇帝。(41)对觐见礼的争执,尼果赖也有让步,同意向康熙皇帝行跪拜礼,(42)却提出12项要求。其中与中俄往来仪节有关的是,中俄往来文书以满文和拉丁文书写,并以双方对等的方式,中俄往来文书皆须写上双方君主正式的完整称号,还要求中国遣使俄国报聘。(43)对尼果赖的12项要求,康熙皇帝酌量接受,(44)并先后在太和殿、保和殿接见尼果赖,赐宴赏物,表示礼遇。可是,理藩院却提出引渡根忒木尔、俄使遵守中国礼法、俄国须约束边民等条件,尼果赖以为有损俄国尊严,无法答允,只好离京回国。(45)
围绕着觐见礼仪引起的纷争,最后以俄使尼果赖行跪拜礼收场,但康熙皇帝已察觉“朝贡礼”不可行于俄国的端倪,(46)并清楚俄国已有与清帝国对抗的实力。因此,康熙皇帝拉拢喀尔喀诸部以稳定漠南蒙古的秩序,并与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境,中俄关系暂时获得稳定。(47)然而,在准噶尔未平定的情况下,蒙古诸部多心存观望,不愿表态。(48)为了削减准噶尔的势力、防止俄国支持准噶尔,康熙皇帝认识到武力不可久恃,“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49)故倾向于与俄国友善,视为“敌体之国”,与之对等往来。(50)《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仍与准噶尔暗中往来,多有边民叛逃之事,让清政府相当不满。(51)
适逢俄国使团来京,理藩院曾向俄使伊台斯(Eberhard Isbrand Ides)提出抗议,要求俄国遵照条约,惩处边民,遣送逃人,并希望与俄国举行谈判,议定喀尔喀与俄国的疆界。(52)从俄使伊台斯的日记里,可见理藩院仍按接待贡使的方式,要求伊台斯交出国书、入住会同馆、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质问伊台斯呈交的国书不符格式的原因,甚至威胁伊台斯若不修改国书或收回国书,就要将使团驱逐出境。(53)伊台斯虽遭到理藩院的刁难,但因同意行“跪拜礼”,遂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并提出俄国的6项要求。(54)对沙皇的6项要求,理藩院只同意遣回俘虏,但驳回遣回逃人、互换使节、中国商人可出境通商等节。(55)由此可知,康熙皇帝虽视俄国如“敌体之国”,但在觐见礼仪上仍不愿轻易退让。当边境有事,理藩院对俄使退让空间较大,可变通觐见礼仪,不坚持跪拜礼的觐见礼仪;边境无事时,理藩院便寸步不让,要求俄使向皇帝行跪拜礼。
事涉中俄两国是否平等的礼仪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清帝国遣使俄国之时。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派图理琛赴土尔扈特报聘,欲说服土尔扈特出兵,与清政府连手征讨准噶尔。(56)由于图理琛等人将路经西伯利亚,不免要拜访俄国官员,将遭遇往来仪节的问题。与俄国沙皇颁布训令的心态相同,康熙皇帝也针对中俄往来仪节,指示图理琛务必遵行:(1)坚持报聘的对象是土尔扈特。俄国若主动派人接待,图理琛可与相见。若俄国不派人接待,图理琛也无须拜访俄国官员。(2)依照俄国的礼仪,与俄国官员相见。(57)(3)向“察罕汗”说明王道思想,表示中国绝不轻动干戈。(58)(4)不可让俄国官员转奏陈情。(5)不可收取俄国馈送的礼物;若无法推辞,酌量收取,再回送锦缎,不可让俄国官员轻视中国。(59)(6)留意沿途所见的俄国人民生计、社会民情及地理形势,查探俄国的虚实。(60)
康熙皇帝的6项指示,反映出康熙皇帝对俄交涉的原则是不卑不亢,尤其在与俄国官员往来的“相见礼”,明令图理琛以“入境随俗”的方式,采用俄国礼仪。(61)由于康熙皇帝不满俄使尼果赖的行径,批评尼果赖不尊重中国之礼,形同轻视中国,(62)又曾答应俄使伊台斯:“日后中国使臣出使俄国,当脱帽立于俄皇前,且依莫斯科之礼俗而行”,(63)康熙皇帝才会告诫图理琛必须尊重俄国礼仪,不可像俄使尼果赖那样失礼。后来,图理琛虽未能谒见俄皇,但成功探查了中俄边境的民情、经济及地理形势,也从四次与西伯利亚总督加格林亲王(Prince Matthew Fedorovich Gagarin)的会谈里,了解了俄国政治和文化,并趁机向加格林重申《尼布楚条约》的内容,要求俄国约束边民,不得私行越境。(64)
从《异域录》可知,图理琛与西伯利亚总督加格林的“相见礼”有以下特点。一是图理琛与加格林见面时,加格林以“执手叩请中国至圣大皇帝安”,(65)但不见图理琛如何问候俄皇,只知图理琛未用中国敕使出使属藩的礼仪。从加格林的“执手”举动来看,可能行“握手礼”,或蒙古式的“拉手礼”,绝不是下对上的“跪拜礼”,证明图理琛未将俄国当做中国属藩。二是当图理琛欲差人馈送俄官时,加格林以差人馈送不合于礼,希望图理琛亲自送礼。可是,图理琛认为亲送礼物之举,同样有碍中国之礼。最后,中俄双方以两国大体为重,决定互不送礼,避开馈送礼物可能造成的误会以及馈赠者的身份问题。(66)由此可知,图理琛与加格林皆坚持“名分秩序”,不愿触碰中俄孰尊孰卑的问题,故有互不送礼的共识,避免争执。
四、变通仪式:雍正朝的接待方案
由于青海蒙古新定,西藏、准噶尔又私下往来,时时蠢动,似有复起之势。(67)为了稳定中国西北的局势,雍正皇帝同样延续康熙朝的对俄政策,积极拉拢俄国,优礼俄国使者,甚至比康熙朝更进一步,同意遣使俄国,觐见俄国女皇。(68)雍正四年(1726)十月初八日,俄使萨瓦(Sava L.Vladislavitch)抵达北京,借祝贺雍正即位为名,实欲解决中俄边境的边界、通商、逃人等问题。同时,雍正君臣也殷勤款待萨瓦,希望俄国同意保持中立,不支持准噶尔部,以便讨伐策妄阿喇布坦。(69)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雍正皇帝对萨瓦相当宽容,不但亲手接过萨瓦呈递的国书,设宴款待,也向萨瓦保证中国与俄国的邦交关系,为中俄边界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70)清政府虽以“朝贡礼”接待俄国使者萨瓦,要求萨瓦行跪拜礼,但为了拉拢俄国,在仪式上也有变通之处,如俄国国书不再放在黄案上进呈,改由雍正皇帝亲接国书。由此可知,雍正皇帝刻意变通觐见礼仪,借由优待俄使的方法,表示皇帝施恩外夷,“以客礼待之”。(71)
中俄双方很快签订了《恰克图条约》,(72)划定蒙古与俄国间的疆界,也解决了逃人追拿、公文往来等问题,同时允许俄国商人每三年至北京贸易,开放中俄两国商人到恰克图交易。(73)雍正皇帝以为,俄国既享受通商优惠,应承诺保持中立,遂以俄国新帝即位为由,遣使俄国,让俄皇亲授承诺,不再支持准噶尔,亦不可收容逃亡者。(74)托时使团出发前,雍正皇帝特别指示托时:俄国乃中国的“敌体之国”,中国使团不应依循敕使出使属藩的方式,也不必奉有皇帝敕谕,只需带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的咨文:“按我大中国之例,凡派使外国均降敕谕。因我国与尔俄罗斯国原为邻国,今不再降旨,而仅派使臣前往。”(75)继托时使团之后,雍正皇帝又派德新另组使团赴俄,指示若俄国不提觐见之事,就不用主动拜见俄国女皇。若不得不拜见,必须向俄国官员说明中国使节觐见俄皇的为难之处,并命令德新觐见俄皇时,应行“内外王公相见礼”,只行一跪三叩礼(76):“拜见俄罗斯察罕汗一事至关重大……俄罗斯等若不提及拜见其汗之事,则我使臣亦无须提及拜见察罕汗一事。一俟事毕,即行索覆[按:索取俄国的回信]返回。设俄罗斯察罕汗差人来告知欲会见我使臣,则可告之……贵汗欲以会见,本使臣并非不愿拜见,惟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于何国,从无跪拜之例,故此于拜见贵汗之仪有所为难等语。设察罕汗差人来称务必会见,该使臣则可告以:按本国之礼,除叩拜我皇上之外,其次可拜见王爷等。我两国自相和好已有多年,实不与他国相比,贵汗既然务必会见,则本使臣等可按拜见我王爷等之礼[按:一跪三叩礼]拜见贵汗等语。”(77)从雍正皇帝的训令,可知雍正皇帝已考虑到觐见礼仪的问题,遂命令德新向俄国女皇行“内外王公相见礼”中的“宗室外藩贝勒相见礼”。(78)雍正皇帝虽未承认与俄国女皇平起平坐,仍保持天子的至尊地位,但从两次派遣使团赴俄之事,可见雍正皇帝考虑北疆未平的现实,刻意变通“朝贡礼”,积极拉拢俄国,也不再坚持将中俄关系纳入宗藩体制的框架之中。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1729年6月14日),作为中国第一个出访俄国的托时使团出发了。1731年1月14日,托时使团终于抵达莫斯科,并受到俄国政府隆重的接待,很快与俄国枢密院官员确定了觐见俄国女皇的时间、地点及相关礼仪。(79)1731年1月26日,托时使团在克里姆林宫,觐见俄国女皇安娜一世(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1693—1740,在位1730—1740),并在宫门外、宫门、谒见宫殿的入口分别受到三次欢迎的仪式。进入宫殿后,托时等人先将国书递交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再呈放在女皇面前的案上,与此同时,托时用满语说明出使目的。俄国女皇答词后,托时等人行一跪三叩礼,又退回呈递国书之处,再次祝贺女皇,重行一跪三叩礼,才退出宫殿,返回驻节的官邸,与俄官共同参与赐宴。(80)
继托时使团之后,德新使团也在1732年进入俄国。为了让使团参加俄国女皇的加冕典礼,俄国安排使团前往圣彼得堡。德新使团同样受到俄国隆重的接待,并与托时使团一样,德新等人也以一跪三叩礼觐见女皇。据何秋涛《朔方备乘》的考订,可知俄罗斯风俗不习跪拜,只以指扣眉,即如同叩首礼,而俄罗斯人对国君、尊长的敬礼,则是脱帽去裘,立地而叩。(81)然而,从托时等人的行礼方式,很明显不是依照俄国脱帽鞠躬的敬礼,而是以《礼记·聘义》诸侯交聘的原则,(82)兼采“宗室外藩贝勒相见礼”,于是托时等人向俄国女皇行一跪三叩礼。由此可见,为了歼灭准噶尔的势力,雍正皇帝的对俄政策,比康熙皇帝更为现实,不惜开创新例,将俄国视为“敌体之国”,与之对等往来,故两次派遣使团赴俄报聘,并准许中国使团行一跪三叩礼,觐见俄国女皇。
五、天朝的尊严:乾隆朝与俄国的名分之争
为了准噶尔问题,中俄关系再起冲突。清军大败准噶尔后,阿睦尔撒纳窜入俄境,寻求保护。(83)理藩院致函俄国枢密院,希望西伯利亚总督遣返阿睦尔撒纳,但枢密院以准噶尔不受清帝国管辖为由,拒绝遣返,使中俄关系变得紧张。(84)随着清帝国彻底平定准噶尔,中、俄势力面临正面交锋。因此,中俄边界的问题又浮上台面,再加上恰克图征收关税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85)让乾隆皇帝决定惩戒俄国,遂关闭恰克图边市,改驻军队,撤回所有中国商人,中俄形同绝交。(86)但恰克图贸易的关闭,让中俄双方在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必须赶紧谈判,解决闭市问题,恢复互市关系。(87)
为了重开恰克图贸易,俄国不得不再派克罗波托夫(И.И.Кропотов,1763年曾赴北京谈判)赴恰克图谈判,并主动向清政府示好,移走中俄边界的木栏,还同意清政府提出惩戒卡伦首领等要求。(88)对俄国的让步,乾隆皇帝感到满意,遂允许库伦办事大臣展开谈判,并命令库伦办事大臣不得对俄国退让,尤其是不能更改对俄国女皇“哈屯汗”的称号。(89)事实上,出于北疆安全的考虑,乾隆皇帝不愿破坏中俄谈判,仍想保持与俄国的互市关系。因此,乾隆皇帝的议和底线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斡旋空间,并不像清政府官方文书宣称的那样强硬。事实上,只要能解决准噶尔逃人与俄国女皇称号两项问题,乾隆皇帝就能得到台阶,同意开放恰克图贸易。(90)是故,如何称呼俄国女皇的称号问题,便成为《恰克图条约附款》讨论的重点之一。
据日本学者柳泽明的研究,乾隆朝对俄政策的灵活度体现于《恰克图条约附款》议定的过程,尤其是中俄双方如何妥协中俄草约上的用词和格式。(91)为了俄方、中方代表谁置于前,及“中国”一词没有抬头顶格等名分问题,中方代表瑚图灵阿、庆桂要求俄方改正,否则就离席回京,放弃谈判。(92)克罗波托夫不愿谈判破裂,赶紧修改草约,修改处有三:一是对中国皇帝的称呼,由“圣上”改为“皇帝陛下”,抬头顶格;二是对俄国女皇的称呼,由“女皇”改为“女皇陛下”,抬头顶格;三是将“中国”、“俄罗斯”皆抬头顶格。(93)可以说,克罗波托夫修改之处,正是乾隆皇帝最为在意的问题症结,宁可谈判破裂,也不愿退让。(94)
克罗波托夫拟订的草约,俄、满文两种版本却有不同的写法。在俄文草约里,中俄双方在意的国名、君主称谓,皆称陛下,也将“中国”、“俄国”二词皆抬头顶格。对俄文草约的写法,瑚图灵阿等人没有意见,似乎默许克罗波托夫的修改。但在瑚图灵阿交给俄方的满文草约里,“中国”、“皇帝陛下”、“侍郎”及“乾清门”等词皆抬头顶格,但“俄罗斯”和“女帝”等词却未抬头顶格,克罗波托夫同样默许满文草约的写法,也没有向瑚图灵阿等人提出抗议。(95)最后,比照俄、满两种版本的草约,可知清帝国不管俄文草约的写法,只要满文草约能按照属藩的表文格式,便同意签署《恰克图条约附款》。(96)
根据相关研究,可知乾隆朝的对俄政策,虽有务实的一面,不与俄国交恶,重开恰克图边市,(97)但也有形式的一面,乾隆皇帝强调名分问题,坚持中国尊于俄国,不再允许俄国的正式使团赴京谈判,(98)并销毁了雍正朝两次遣使、赴俄报聘的官方纪录,欲掩盖康熙、雍正朝视俄国为“敌体之国”、优待俄国使团的事实。(99)由此可知,准噶尔问题解决后,乾隆皇帝没必要再拉拢俄国,所以否定俄国曾为“敌体之国”的事实,对俄政策又重回“朝贡礼”,并禁止俄国使团赴京谈判,让中俄双方不必再为觐见礼问题争执。例如,嘉庆十年(1805),俄国派遣戈洛夫金(Golovkin)使团从库伦入境前往北京,但中俄双方因觐见礼问题僵持不下,嘉庆皇帝下令驱逐俄国使团,(100)可见乾隆朝以后,清政府坚持“朝贡礼”的方案,不再优礼俄国使团。不过,对俄罗斯的记载,乾隆年间仍可见到中俄往来的实况。例如,清代学者赵翼依据俄国不奉正朔、文书咨行,直指俄国是“敌体之国”,并非中国属藩之事实:“俄罗斯至今为我朝与国,不奉正朔,两国书问不直达宫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萨纳特[按:俄国枢密院],有事则两衙门行文相往来……其国历代皆女主,号察罕汗。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闻近日亦易男主矣。”(101)即便如此,为了贬抑俄国,凸显中国礼教的优越,赵翼竟听信民间传言,称俄国女皇迷恋托硕的男色,遂在床第上与中国订盟。
六、结语
清代宾礼的制礼原则有二,不但有适用藩部、属藩的“朝贡礼”,也有适用敌体之国的“客礼”。清政府对“华”、“夷”的认定,采文化上的定义,并据双方势力消长,变动藩部、属藩的认定标准,使清帝国的“边界”实有伸缩的空间。可以说,清帝国的对外关系相当富有弹性,往往视其对象的实力强弱或自身的需求与否,予以变通觐见礼仪,不像明代执著于“朝贡礼”。清初诸帝变通觐礼的根据,即来自汉代萧望之主张的“客礼”,(102)并将不愿称臣纳贡者归为“敌体之国”。因此,当俄国频频遣使、要求缔约建交时,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的应对方式虽各自不同,却反映了清朝接待俄国使团及其交涉政策的基本路线。
考察清初四帝与俄国的觐礼冲突可知顺治皇帝本醉心汉法,依据“朝贡礼”方案,视俄国使者为贡使,坚持俄国使者行跪拜礼,不惜驱逐俄国使团。康熙中叶以后,理藩院虽成功让俄国使者向清帝行跪拜礼,但因准噶尔叛变与中俄边界问题,康熙、雍正皇帝已了解到俄国不比属藩,无法强加“朝贡礼”,只能视俄国为“敌体之国”,与俄国对等往来,订约互市,让俄国不再支援准噶尔。由此可知,康熙、雍正两朝的对俄政策,采取拉拢俄国、分而治之的手段,切断准噶尔的补给,也防止俄国趁机侵入北疆,于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不惜牺牲“朝贡礼”的名分原则,变通俄国使团的觐见礼仪,允许俄国成为与中国对等的“敌体之国”。然而,当准噶尔彻底平定后,乾隆皇帝重新调整对俄关系,要求俄国遵守“朝贡礼”的规范,并销毁了雍正朝两次遣使、赴俄报聘的官方纪录,掩盖康熙、雍正皇帝曾视俄国为敌体、待以客礼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雍正皇帝虽视俄国为“敌体之国”对等往来,但通过理藩院处理对俄事务,回避中国皇帝与俄国沙皇位阶问题,并借“优礼”、“柔远”说法来解释康熙、雍正皇帝变通觐见礼仪之事,希图将“客礼”视为清政府优待俄使的权宜之计,以为如此便可无损于清帝国的体面。此外,从乾隆朝对俄政策的转变,可知清政府不再承认有“敌体之国”的存在,也摒弃了讲求对等位阶的“客礼”,清帝国的对外交涉体制只剩“朝贡礼”的单一方案,讲究天朝独尊的体面。同时,根据《大清会典(嘉庆朝)》“互市国”一类的出现,(103)可知清政府借互市制度,将不称臣纳贡者归入“互市之国”,作为“朝贡礼”的补充方案,借以完整“天下秩序”的缺憾。换言之,乾隆、嘉庆朝以后,当有外来者入华,清政府一开始会要求这些国家进表文、贡方物,将其使者视为贡使,试着让这些国家接受“属藩”的政治身份,成为清帝国的“外臣”。但当这些国家不愿称臣、进表、纳贡时,清政府便承认既有事实,不再设法将之变为“属藩”,但只允许通商关系,断绝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将之归入“互市国”的行列。
注释:
①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45页。觐礼之争,也包含中国使节觐见外国君王的礼仪争议。但中国若遣使外国,皆是敕使,不会与属藩国王发生觐礼问题。
②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5、10页;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年3月第78卷第1期,第35—106页;吴晓钧:《阿美士德使团探析——以天朝观之实践为中心》,新竹“清华大学”历史所2008年硕士论文,第49—56页;[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351页;George Thomas Staunton,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selected 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atrick Tuck,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0,p.118。
③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卷91《礼志十》。
④赵尔巽:《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19页。钱实甫指出,中俄关系显然不同于属藩,尽管清政府在礼仪方面不肯稍失天朝体制,但曾多次与俄国订立对等性的条约,因此俄国相关事务不归礼部管辖。
⑤John K.Fairbank & Ssu-yu Teng,Chí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107-112.费正清指出清帝国对欧洲各国的认识多有错谬,常混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法国来使。因此,费正清认为天朝观与朝贡体制维持的原因,可能是清帝国不了解欧洲各国的实况,才会视欧洲各国为属藩。
⑥赵尔巽:《清史稿》卷91《礼志十》。
⑦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费正清认为,中国远居亚洲,与世界主要文化中心隔阂,自成一文化体系,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中心观,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余外国皆蛮夷。因此,当西方各国使者来华时,中国视同朝鲜、琉球等属藩派出的贡使,为倾心王化而来。
⑧参见李齐芳:《清雍正皇帝两次遣使赴俄之谜——十八世纪中叶中俄关系之一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年6月第13期,第55、57—58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122—123页。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2005年博士论文,第2—4、116页。陈维新认为,在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仍认为俄国是属国,俄使是贡使。但笔者的看法不同,若清帝国只抱持天朝观,坚持封贡体制,便不会与俄国展开谈判,立约互市,也不会在觐礼问题上对俄使让步,更不会允许两国文书平行,由理藩院咨行俄国枢密院。
⑨参见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曹雯引用《(嘉庆)大清会典》的资料,主张清帝国曾试图将俄国纳入朝贡国的行列,但因俄国抵制,只好将俄国纳入互市国之列。
⑩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民国丛书》第2编28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11)[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2)刘民声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2页。
(13)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9—13页。
(14)[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15)苏联科学院编、厦门大学外文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1978年版,卷1,第74件,第177—178页。
(16)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limited,1919,vol.2,p.153.[俄]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版,第97页。俄国使团进入北京前,清政府派员出迎,并以皇帝的名义敬以奶茶,却被俄使当场拒绝,退回奶茶。进城后,俄使拒绝转递国书,要求当面向顺治皇帝递交国书。但理藩院不许。双方僵持不下,谈判半年,毫无结果,只好通知俄使离京回国。
(17)[俄]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雅斯尼科夫著,黄玫译:《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100—102页。根据俄国学者与王开玺的研究,可知巴伊科夫不愿无功而返,曾瞒着使团的其他成员,暗中派一名印度商人返回北京,向理藩院传话,表示自己愿意行跪拜礼,希望皇帝能允许俄国使团重返北京。
(18)《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五月乙巳。
(19)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圣训》,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3页。
(20)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厦门大学外文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第86件,第217页;第93件,第229页。
(21)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厦门大学外文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第96件,第231—232页。
(22)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7页。
(23)参见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72—74页。
(24)王和平:《从中俄外交文书看清前期中俄关系》,《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
(25)《清世祖实录》卷135,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
(26)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35,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
(27)参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王之相、刘泽荣译:《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1964年编印,第1件,第1页。
(28)参见[俄]巴赫鲁申著,郝建恒、高文风译:《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6、12—15、19—22、28页。
(29)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晓园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30)参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王之相、刘泽荣译:《故宫俄文史料》,第1件,第1页。
(31)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厦门大学外文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第141件,第283—287页;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75—79页。陈维新指出,密洛瓦诺夫可能修改了训令内容,删除了对康熙皇帝的不敬字眼,或可能是理藩院未将训令内容禀报皇帝,或耶稣会士故意不翻译那些不敬字眼。
(32)参见苏联科学院编、厦门大学外文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第183件,第380—381页。
(33)参见郝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档选译》,卷6,第6件Ⅱ,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2页。
(34)参见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8—19页。
(35)参见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vol.2,p.243。
(36)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8页。
(37)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45—46页。[俄]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14—115页。
(38)参见刘民声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第244—247页。
(39)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39页。
(40)参见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vol.2,pp.330-337。
(41)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40页。
(42)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121—126页;李齐芳:《清雍正皇帝两次遣使赴俄之谜——十八世纪中叶中俄关系之一幕》,第56—57页。王开玺认为尼果赖行三跪九叩礼,但李齐芳认为尼果赖只行鞠躬礼。笔者以为,尼果赖确行了三跪九叩礼,但态度傲慢,故意缓慢进殿,引起康熙君臣不满。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48—49页。
(43)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47—48页。
(44)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第141—142页。该书写有尼果赖提出的12条要求,亦附有康熙皇帝回复的答复,可见康熙皇帝对12条要求,直接拒绝者有4条,令部再议者有4条。关于康熙皇帝的拒绝理由不赘述,参见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89—95页。
(45)参见John 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vol.2,p.406;[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第110页。
(46)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
(47)参见[俄]齐米特道尔吉耶夫著、范丽君译:《蒙古诸部与俄罗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83—86、89页;[俄]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93—206页。
(48)参见庄吉发译:《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49)《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50)吴相湘:《清宫秘谭》,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版,第44—45页。
(51)参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10,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164—166页。
(52)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93—95页。
(53)[荷]伊台斯·伊兹勃兰特、[德]勃兰德·亚当著,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962—196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8—195、211—215页。关于伊台斯与索额图的争执,主要是国书格式与礼品收受的方式。
(54)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92页。
(55)参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88—89、94页。
(56)参见李齐芳:《清雍正皇帝两次遣使赴俄之谜——十八世纪中叶中俄关系之一幕》,第55页。
(57)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页。
(58)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1页。
(59)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4—16页。
(60)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7页。
(61)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10—11页。
(62)参见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第120—126、139—140页。
(63)朱杰勤编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海洋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
(64)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71—72页。
(65)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65—66页。
(66)参见图理琛著、庄吉发译:《满汉异域录校注》,第84页。
(67)参见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5页。
(68)参见《清世宗实录》卷60,雍正五年八月乙巳。
(69)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344页,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新归顺乌梁海人等逃入俄罗斯折;第1354页,雍正四年六月十四日都统查克旦奏报策妄阿喇布坦派兵三路来犯折。
(70)参见《皇朝文献通考》卷300《四裔考八》;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119—137页。
(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第1487—1489页,雍正五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右侍郎图理琛等奏报与俄罗斯使者议界折;第1494页,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喀尔喀副将军策凌奏报俄罗斯商对先行备马折之朱批。
(72)参见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国立”编译馆1976年版,第17—19页。
(73)参见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74)参见李齐芳:《清雍正皇帝两次遣使赴俄之谜——十八世纪中叶中俄关系之一幕》,第43—44页。
(75)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号224,第528页,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
(76)[日]野见山温:《清雍正朝对俄遣使考》,《福冈大学法学论丛》1961年12月第6卷第1期,第33—77页。
(77)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下册,号238,第550页,雍正九年六月。限于史料,未见雍正皇帝指示托时应用何种礼仪谒见俄国女皇,但对德新使团则有清楚训令,要求德新使团见俄国女皇时,应用拜见我王爷之礼,拜见俄国女皇。而托时亦对俄国女皇行一跪三叩礼,推测托时可能也得到类似的训令。
(78)来保:《钦定大清通礼》卷44《宾礼》,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页。
(79)参见Mark Mancall,"China's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1729-1731",Papers on 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55,vol.9,pp.86-87;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144页。陈维新指出,托时使团很可能没有向俄国政府解释一跪三叩礼的意义,也就是说,俄国并不了解一跪三叩礼乃外藩亲王拜见宗室贝勒的相见礼,而不是觐见皇帝的三跪九叩礼。
(80)参见Mark Mancall,"China's First Missions to Russia,1729-1731",Papers on 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55,vol.9,pp.87-88;[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第204—205页。
(81)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第12—12、17—18页。
(8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63《聘义》,艺文印书馆1965年版,第1—3页。
(83)参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13,第209—217页。
(84)参见赵尔巽:《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日]森川哲雄:《以阿睦尔撒纳为议题的清俄交涉始末》,《九州岛大学教养部歴史学·地理学年报》1983年第7期,第75—105页。
(85)参见《清高宗实录》卷680,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癸巳;卷710,乾隆二十九年五月乙卯;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
(86)参见《清高宗实录》卷797,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包遵彭主编:《中国近代史论丛——早期中外关系》第1辑,第3册,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39—44页。
(87)参见[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第174—176页。
(88)参见[日]柳泽明:《1768年〈恰克图条约附款〉与清俄两国的交涉》,《东洋史研究》2003年第62卷第3期,第1—33页。
(89)《清高宗实录》卷814,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丁酉。
(90)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16,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丁卯。
(91)参见[日]柳泽明:《1768年〈恰克图条约附款〉与清俄两国的交涉》,第24—27页。
(92)参见《清高宗实录》卷817,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壬申。
(93)[日]柳泽明:《1768年〈恰克图条约附款〉与清俄两国的交涉》,第24—25页。
(94)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第25—26页。
(95)[日]柳泽明:《1768年〈恰克图条约附款〉与清俄两国的交涉》,第25—26页。
(96)参见[日]柳泽明:《1768年〈恰克图条约附款〉与清俄两国的交涉》,第26—27页。
(97)参见[俄]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第177页。
(98)参见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第78页。
(99)参见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第145—148页。
(100)参见何新华:《威仪天下——清代外交礼仪及其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208—216页。
(101)赵翼:《檐曝杂记》卷1《俄罗斯》,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页。
(102)据《汉书》卷78《萧望之传》载:从汉宣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例子,可知天子权力有其限制,天下之内未必皆是王臣。萧望之主张,匈奴本为敌体之国,应将单于视为客臣,以客礼待之。
(103)《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卷31、52、53,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廖敏淑:《清代对外通商制度》,《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9—461页。
标签:准噶尔论文; 图理琛论文; 理藩院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尼布楚条约论文; 康熙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雍正论文; 历史论文; 清史稿论文; 中俄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