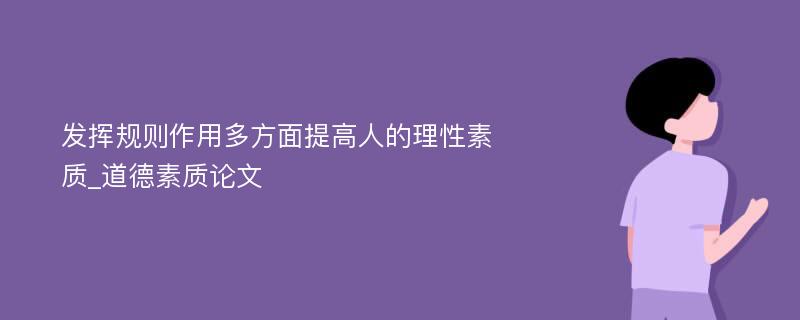
发挥规则作用,多方面提高人的理性素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方面论文,理性论文,素质论文,规则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个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从人的“理性素质”的角度出发,有利于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从规则同理性素质的关系着手,又有利于切切实实地提高人的理性素质、纠正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两点考虑。
一
邓小平同志90年代初几次谈到上海人的素质。1991年春节视察上海时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并鼓励上海的同志“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1〕1992年春节视察上海时他又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认为这是上海可以有一个较高发展速度的有利条件。〔2〕从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理性素质是人的素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他在谈到上海人的素质时用了“聪明”二字,不是偶然的;他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也同人的理性素质有直接关系。所谓“聪明”,就是理性素质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现代化过程归结为合理化过程,而合理化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工具合理化,一个是形式合理化,这二者的特定含义可以分别用上海人说一个人“聪明”时常用的两个词来说明,即“门槛精”和“拎得清”。“门槛精”,就是讲究窍门、讲究方法、讲究工具相对于目的的合理性。“拎得清”,就是懂得区别、懂得界限、懂得思维形式的合理性。现代化过程作为一个合理化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人们在思维、行动和社会组织系统上注重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
“拎得清”和“门槛精”,形式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常常是联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思维混乱、“拎勿清”的人,是难以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常常被当作“工具合理性”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形式合理性不仅和韦伯重视的工具合理性有关,而且和韦伯所忽视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合理性”也有密切关系。现代化之所以为一个合理化过程不仅和人们追求既定目标的手段有关,而且和人们对目标的设立本身有关。
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现代化之所以为合理化过程的理解。邓小平同志坚持我们的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与此相应,他要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3〕这些都同提高人的理性素质有密切关系。“有文化”这一条同人的理性素质的密切关系刚才已经提到了。现代文化的最重要部分是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技术的基础,而技术是服务于人的目的的理性手段或“门槛”;知识的掌握和增进又同人们思路清晰、有条理、善于概括抽象,也就是“拎得清”,是互为因果的。不仅“有文化”,而且“有理想”、“有道德”和“有纪律”,也同人的理性素质有密切关系。“有理想”:理想是层次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概念;一个概念混乱、抽象能力差的人无法真正做到“有理想”的。“有道德”:道德要求人们善于分辨善恶,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现代复杂社会对这种分辨能力、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的要求比前现代社会要高得多。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哪怕再善良,也无法履行现代社会中的种种义务,成不了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有纪律”:纪律的目的是让人们的行动有条有理,互相协调,以符合特定的目的、价值和理想。一个人理性素质不高,会表现为行为散漫、自我控制能力薄弱、无法遵守纪律,因而导致其行为缺乏应有的可预见性、可期待性和可协调性。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四有”新人的最重要素质就是在不同层次上以社会主义之“道”统率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系统性、条理性和目的性,这是一个人的理性素质的最高表现,也是整个社会的团结、有序和合理(合乎道理、合乎法理、合乎情理)的基本前提。
二
理性素质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要使得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首要条件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身上、自己心中的这种可能性,努力修养,日积月累,不仅变天性为德性,而且变天性为理性。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真正的德性是和理性分不开的。同时,由于人身上有种种可能性,因而光靠自己的努力而没有外界的教育和培养,也不能保证使人的理性的可能性而不是非理性的可能性变成现实。
教育和培养有两种形式,一是具体的、针对情境的,一是普遍的、超越特定情境的。以道德教育为例。比如一个叫李明的小孩偷拿了一个叫王强的小朋友的铅笔。老师对他说:“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对老师的批评,根据他的道德思维能力的高低,他可能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他的理解可能是“我,李明这次拿叫王强的这个小朋友的这支钢笔是不对的”,也可能是“任何人不经过同意拿属于任何别人的任何东西是不对的”,也可能(一般来说)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只有当一个孩子能把一个特定的情境和一条普遍的规则联系起来,他才一方面懂得了这条规则的含义,另一方面具有了“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待事情,即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的能力。
因此,在培养广义的人的理性素质(包括道德领域的理性素质)方面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要求空泛,不问对象、场合;一是就事论事,不问原则。以刚才的例子来说。幼儿园的老师如果对全班小朋友说:“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拿别人的私有之物”,小朋友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或者是因为用词太抽象、太普遍,他们理解不了;或者是因为没有针对性,小朋友们会纳闷,老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向他们宣布这条要求。但反过来说,幼儿园老师如果就事论事地对那个拿别人铅笔的小朋友说:“刚才拿某某同学的铅笔是不对的”,也起不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老师没有告诉孩子一条普遍规则的具体含义;在后一种情况下,老师没有告诉孩子判断一个特定情境的普遍标准,没有告诉孩子不仅擅自拿张三的东西是不对的,而且拿李四、王五等等的东西也都是不对的。只知道就事论事教育孩子的教师即使把学生管得服服贴贴,也可能培养不出普遍的道德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同样,只知道教学生如何做一件具体的事情,特定的实验和操作,但不教会学生在特定的实验和操作背后的普遍规则和普遍规律,也势必无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这里可以看出规则在素质培养、尤其是理性素质培养中的作用。全面地说,培养人的理性素质之所以必须发挥规则的作用,是因为规则有这样一些形式上的特点:
其一,公开性。规则一定是要颁布的;从原则上讲,是必须为制度所适用的对象所预先知道的。我们知道,合理的东西总能够为人们所公享、交流和相互衡量监督的东西。规则本身也有一个正确与否、合理与否的问题;如果把规则“秘而不宣”,则无法对规则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商讨和推敲。
其二,普遍性。规则必须是以全称命题的形式出现的。规则所适用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类个体。不管这个类多么小,它必须覆盖这个类中的全体,否则就不叫规则,而只能叫命令。规则常常有例外,但即使这个例外,也通常是在规则的表述中有所提及的。我们知道,人们的理性能力的重要特点是能够进行从个别和特殊上升到普遍,又能够根据普遍的规则对特定的情境进行判断和评价。
其三,稳定性。规则在制定、颁布以后,就具有了对于规则的制定者和颁布者来说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动。我们知道,合理的行动不能是朝三暮四、无法预测的。
规则的内容有各种各样,但只要是规则就有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或优点。从这些形式上的特点或优点可以看出,发挥规则的作用对于人的理性素质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规则提供的是一种合理的环境,在这种环境的熏陶、训练甚至强制之下,人们久而久之会把习惯转化为成自然,把外部的理性之物转化为内部的理性之物,真正成为具有高度理性素质的人。
三
但是,发挥规则的作用还有一个是不是恰当的问题。规则有不同的种类,忽视这些种类的区别,即使运用了规则,也无助于多方面的理性素质的培养。
规则大致可分为三类:博奕规则、技术规则和道德规则。博奕规则也叫游戏规则;人们常常把规则和游戏放在一起说,但其实并不能把所有规则都叫作“游戏规则”。
按通常的理解,游戏是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的,游戏规则是人们可以自由制定和修改的,违犯游戏规则常常是不必受到处罚和自责的——比如在足球比赛中,裁判没有发现球员犯规,这球就照踢不误;球员适当时候故意犯规,还是一种特定的技术技巧。
与游戏规则或博奕规则相比,技术规则是人们不能不遵守,不遵守就必然要受到惩罚的。球员犯规可以逃避裁判的眼光,技工违反操作规程虽可以逃避车间主任的眼光,却逃避不了自然规律的“法力”——技术规则的根据不是人们的约定,而是相应的自然规律。违反技术规则就违反自然规律;操作事故、安全事故是作为客观的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因违反技术规则的行为引起的,自我原谅和请求别人原谅都无济于事。把技术规则当做博奕规则,常常意味着把客观规律“视同儿戏”,害人害己。在有些情况下,这也是迷信的一种根源。比如在发生旱灾的时候供奉龙王或曝晒龙王,就是把大自然当做一位博奕的伙伴,甚至是一场不体面博奕的伙伴,想通过利诱或威胁的手段使其让步,逼其就范。培养人的理性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得人们知道技术规则和博奕规则之间的区别。一个“有文化”的人,不仅是一个懂得许多科学知识的内容的人,而且是一个掌握科学知识的精神的人,一个掌握获得和运用科学知识的方法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一方面学会了许多技术规则,另一方面学会了区分技术规则和博奕规则。
除了博奕规则和技术规则之外,还有一个大类的规则就是道德规则。道德规则的基础是所谓“实践理性”,就是人们对于行为规则的普遍适用性、正当性的判断能力。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康德以能否作为普遍道德律令来判断行为规则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讲以全人类利益为最高利益,是“实践理性”的不同表现。它们之间当然有重要区别,但在这里重要的是指出:道德规则和技术规则、博奕规则的依据和基础是不同的;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人的素质培养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不把道德规则混同于技术规则和博奕规则。
假如我们把道德规则混同于技术规则,就会认为道德规则象技术规则一样是以外在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因而是不变的(以前人们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并没有错,如果我们把“天”和“道”分别理解为“自然规律”和“技术规则”的话),因而违反它就象违反自然规律那样必然导致惩罚(旧时候人们的“天谴”“报应”等说法用在技术规则的违反上,也不错)。反过来,当人们发现违反道德规则并没有引起客观的因果性的惩罚,或遵守道德规则并没有引起客观的因果性的收益,也会随之而无视道德规则的约束——迷信是不足以使人趋善避恶的。
假如我们把道德规则混同于博奕规则就会只有对于规则的外部的保证,而没有对于规则的内部的保证。违反博奕规则也会遇到惩罚,但这种惩罚通常只是外在的,而且是可设法逃避或被赦免的。相反,违反道德规则即使人们没有发现、没有惩罚,一个真正视之为道德规则的人也会受到自己“良心”或“良知”的谴责。把道德规则混同于博奕规则,一个人会看上去循规蹈矩,实际上却可能并没有是非观念(所谓“良心”和“良知”)。因为他之所以循规蹈矩,可能只是为了不让同伴(相当于“队友”和“对手”)、上级和群众(相当于“裁判”)发现他“犯规”。
当然,博奕规则本身也是可以同道德有关的,在现代社会,或对于成人来说,“不能故意违反自愿加入的博奕的规则”本身,也是一条具有道德意味的规则——它涉及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作为成人,遵守诺言是一条基本的道德准则。对于一个组织的成员来说,只要加入组织是自愿的,只要他在加入时曾经宣誓遵守这个组织的规则即纪律,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不遵守这个组织的纪律,哪怕他后来是多么不想遵守。现代社会区别以往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法律规则在人们的生活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规则首先是一种纪律,即社会这个大组织的纪律。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广义的用法,加入一个组织就是加入一种博奕或游戏。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法律规则叫做“博奕规则”。但作为这种博奕规则的根据的不仅仅是约定(如证券交易法),而常常也可以是自然规律(如环境保护法),或实践理性(如宪法和刑法)。
上面分析表明,从哲学上说,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都和规则有关,它们分别同上面讲的三类规则(技术规则、博奕规则和道德规则)有比较特殊的联系。
再进一步说,“有理想”也同规则有关。在这里可以引进哲学中的又一个区别: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之间的区别。在康德那里,“知性范畴”是知识的构成性规则,因为没有了这些范畴在康德看来知识就无法成立;“理性理念”是知识的范导性规则,因为知识最好受这些理念引导,但不能说没有了这些范畴知识就不成其为知识。同样,“理想”和“纪律”作为规则对于人的行动的约束方式是不同的:纪律告诉我们必须做到什么,理想告诉我们最好做到什么。违反了纪律是要受处分的,但违反了理想则一般不受处分,至少不受同等程度的处分。遵守一个团体组织的纪律,对于这个团体组织的成员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通常情况下没必要特别褒奖,而符合理想,则一般来说超出了对这个团体的成员的起码要求,因而值得特别褒奖、鼓励和倡导。也就是说,在英雄模范和小人歹徒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注意纪律和理想之间的区别,会导致把违法乱纪的人仅仅看做不是英雄模范而已(假如有人说:“这个党员受贿,所以他不是一个优秀党员”,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把违背理想当作违法乱纪(假如有人说:“这个党员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应该把他开除出党”,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完成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的光荣任务。
四
规则不仅有种类上的区别,而且有普遍性程度上的区别。注意这种区别,也是恰当发挥规则在培养人的理性素质方面的作用的必要条件。
规则在普遍性程度上的区别可以从行为主体和行为情境这两个角度来考虑。
首先,从规则对于行为主体的约束面来看。规则对其有约束力的人的范围是有大有小的。规则作为规则是适用一个类的全部个体的,但这里所讲的“类”有大有小。比如《婚姻法》适用的范围是年满20岁的女子,年满22岁的男子,比《宪法》的适用面要小,和《党章》的适用面相比,可以说更大(多数男女不是党员)也可以说更小(不到婚龄的人也可以入党)。要恰当地发挥规则的作用,就要注意规则适用的行为主体的范围的大小,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邓小平同志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反对把适用于敌我矛盾的政策、法规运用于人民内部;他又再三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坚持凡在法律适用的范围内,没有特殊公民。做到这两条,不仅是一个政策水平问题,政治道德问题,而且是一个理性素质问题。随意扩大和缩小规则适用的人的范围,实际上等于取消规则,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个人的任性和武断。
其次,从规则所适用的行为情境来看。以本文第一节的例子来说。幼儿园老师如果对李明小朋友说:“你不许拿王强同学的这支铅笔”,她所颁布的是一条命令,而不是一条规则,因为规则所适用的行为情境都是一个类,而且通常这个类不只有一个个体。但如果她说“你不许拿王强的铅笔”,就接近一条规则了:只要是王强的铅笔,李明都不许拿。她如果说:“别人的东西你都不能拿”,就更接近于典型的规则了。
区别规则适用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情境的普遍性程度的高低,对于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在有些场合,普遍性程度低一些是必要的,或者是因为教育对象的理解能力不够,或者因为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比较特殊。但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应创造条件逐步提高规则的普遍性的程度,因为就其本性来说,道德规则的覆盖面是比任何其他规则都广的,因为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承认人作为人的人格的普遍平等;道德规则在原则上是不能因人而异的。邓小平同志曾专门讲过毛泽东同志是如何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对于我们理解规则的普遍性程度的问题很有帮助。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另一方面注意结合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要求。〔4〕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主要是指根据新的情况调整规则适用的行动情境的普遍性范围。比如,起初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后来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里“群众”的概念的外延显然大于“工人农民”。“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里的“一切缴获”的外延显然大于“打土豪”之所得的外延。此外,先前的“洗澡避女人”后来改为“不调戏妇女”,“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虐待俘虏”,也属于这种情况。在士兵觉悟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在活动范围较小的情况下,只能提出一些比较具体、比较直观的要求。但在士兵觉悟比较高的情况下,在活动范围比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仍然限于比较具体、比较直观的要求,就会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不对规则的普遍性程度作适当提高,邓小平同志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所不许可的许多事情,也就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一个人拿了小业主的东西,这是不是违反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纪律?殴打俘虏没有违反“不搜俘虏腰包”的纪律,这是不是允许?另一方面,这样也会妨碍了士兵认识他们之所以要做或不做一件事情的理由,妨碍他们提高行为的道德境界。假如有两个士兵,都做到了“不搜俘虏腰包”,但一个是仅仅认为搜俘虏腰包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一个则不仅知道搜俘虏腰包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而且知道这件事情之所以不对是因为这是虐待俘虏,而虐待俘虏是不对的,显然,后一个士兵的道德境界要比前一个高一些。当然,这位士兵的道德意识水平还有待于上升到“不得侮辱任何人的人格”、“要尊重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这样的水平。只有在这样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代的宪政国家。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掌握规则的普遍性程度不仅是为了适应人们的理性素质水平,而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性素质水平。正像科学知识的学习,一定程度的知识必须在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相应水平的时候才能传授,而一定程度的知识的传授本身也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样,一定程度的规则的施行必须与特定阶段的人们的道德意识水平相适应,但在人们的道德意识水平已经有了提高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原来低层次的要求的话,也可能妨碍人们的道德水平的提高。我们目前宣传的“七不”规范很具体,普遍性程度很低,但这些规范很好,很恰当,那是因为我们上海市民目前的公德水平还不够理想,先得从小事抓起。但上海市民的公德规范如果始终停留在“不随地吐痰”、“不说粗话脏话”的水平,也会限制上海市民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层次的提高。区分不同的教育对象,提出不同的规则要求;根据市民的德性水平和理性水平,提出恰当的规则要求,这是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技术规则也不能因人而异,但技术规则涉及的不是人的行动的正当与否,而只是人的行动的成功与否。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教会人们知道“成功的”不等于是“正当的”。所以讨论道德教育时,技术规则可以撇开不谈。
注释:
〔1〕〔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376、190页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