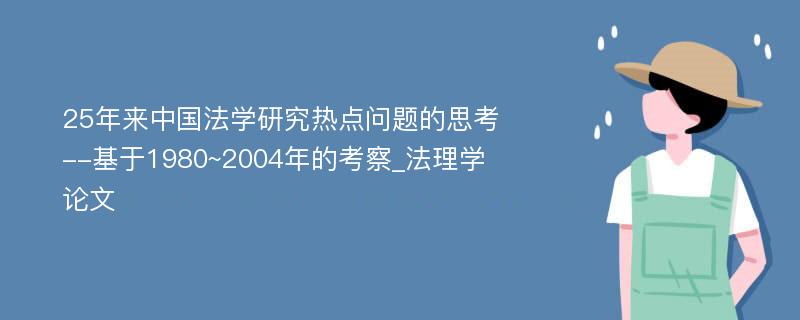
对25年来中国法理学研究热点问题的思考——立足于1980—2004年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理学论文,中国论文,立足于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07)02-0099-04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分析1980—2004年中国法理学界研究的主要问题,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诸侯大战”(1980—1988)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本就脆弱的法学理论几乎消磨殆尽,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都需要重新澄清、厘定;全员式地参与每一问题的讨论,这一点在相关资料的记载中表现得很明显,就是关于每一个问题的主要观点或不同论述至少有两个(对立),一般都有三个、四个乃至五六个。这主要是因为法学基础理论(法理学)框架还没有最终界定,学者们不得不四面出击,全方位的突破;学者们还没有或不能确定自己的理论方向或学科专长。
从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主要学术会议议题与当时政治背景的对照中可看出,学者们由于学科建设的需要研究、研讨了一些“纯粹”的法理学问题,但相当一部分问题与议题是围绕当时的政治话语展开的,或者是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而成为了问题。当然,这也正是学理界关注国家的法制进程、面对现实的本能反应。而且,这一阶段的问题和议题都不是对政治话语的简单认可,而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展开了不同的论述。这与后来的政治表态式的学术会议是不同的。
从这一阶段的“理论亮点”来看,大有理论无疆界之势,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提法的疑义、“应当以实施宪法为核心,不折不扣地按宪法的规定办事”,到对“判例法的优越性”的研究、对“我国法律实效不佳的原因”分析,鞭辟入里、细致入微,反映了学者们对现实的关切和理性批判的学术品格。
2.“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89—1991)
正是前一阶段“放马由缰”式的理论研讨,加之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姻缘际会,出现了1989年的“法学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从而导致了法理学发展历程中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阶段。之所以用“这里的”限定词,主要是与国际上的法学动态相比较而言,当然得不出“风景这边独好”的论断,只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用“黎明”一词的主要用意是,这并不是中国法学界失去的三年,学者们对法理学领域内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如“何谓权利”、“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关于立法发展战略问题”等,而且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代表还出席了两次国际法律大会。所谓“静悄悄”是指理论上没什么突破,也没什么让人掩卷长思、顿生慷慨激昂、痛快淋漓感觉之“理论亮点”。这是蓄势待发之前的准备阶段,为再一次的理论勃兴积攒力量。但“法学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学者们的学术热情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法学界不正视现实、喜欢宏大话语、言必称希腊的学术风气。
3.“春天的故事”(1992—1999)
从研究的主要问题看,与政治话语有关的问题和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往往并驾齐驱,这也可能是中国法学界“成熟”的标志之一。学术会议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态(特别是1993年)。这不仅与第一阶段虽也围绕政治话语展开研讨,但还存在学理思辨、理论阐述、进路分歧不同,也与第四阶段学者们有意淡化政治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一阶段的“理论亮点”反映了法律浪漫主义情怀,本文用“法律浪漫主义”这一词没有丝毫的贬义,这里所谓的“法律浪漫主义”主要包括两种倾向:一是对法律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如对人性的关注、对法精神的人文主义诉求、对法的最终功能是为人的“最优化生存”服务的阐述等;二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且仅仅是关注而已,是一种隔岸观火(站在西方法学理论的角度指点中国的法制及进程)、闭门造车式(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没有对现实的深入考察)的学术姿态,因而,他们对法律价值目标的追求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但并不是说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没有必要,学者保持一种超然的境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这是学者应有的一种学术品格)。特别是在法学界,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世俗化要求,学者们长期养成的注释现有法条的习惯,或者奉西方的经典论断为圭臬而不加论证的言说方式,使得独立思考、富有理想色彩的阐释显得弥足珍贵。
4.反思——回归(2000—2004)
这一阶段在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学术会议议题方面,有一个特点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几乎找不到政治话语,与以前各阶段、特别是与第三阶段相比,真是泾渭分明。这可能与学界就“法理学应多些知识、专业的成分,少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达成共识不无关系。
这一阶段的另外两个特点就是反思与回归。反思指对长期以来法理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又开始了新的研讨。当然,反思与回归并不能截然分开,反思即意味着要回归理论的本来面目。反思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理论亮点”中:“法理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从而给法理学研究以理论指导”;“必须对西方法律理论和制度可能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法的模糊性是法的绝对属性,法的确定性只在相对意义上存在”;“‘法治’与‘德治’、法律与道德在人的生存实践、实践目的、方式上有同一性。要从中国社会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二者相互关系契合的合理性”;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的主张存在“学理上的困境”及“法治中存在着悖论”等。
所谓回归除了上面提到的回归法理学理论本身外,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立场的回归。即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中国的问题,审视国际理论动向。第二,回归中国人的生活现实、生活场景。第三,回归人自身。也就是法律最终是为惬意的人世生活与和谐的人间秩序服务的,如果法律放弃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诉求,它也势必要为人所放逐,法律信仰更是无从谈起。第四,人性、人文关怀的回归。第五,法律知识分子自身品质、角色、地位的回归。“知识分子法律家的第一品质是捍卫社会良知,法律知识分子的第二品质则是把法律作为思考的对象而非前提,客观上使教授能够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阐释法律和法律制度,进而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和职业伦理。”需要强调的是,前面所说的各种回归只是一些学者的理论主张,只能说明在这些问题上有了学者们的意识自觉,能否成为学界的共识并付诸于行动还有待日后的观察。
二、法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
1.政治使命——政治、西学激活——学术自主性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不仅有极高的学术热情,而且把搞好学术作为政治使命来完成,因此,研究的范围很广泛,也少有政治忌讳。所有的问题都在研究、讨论之列。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进行,学者们对一些重大的、有现实意义而又比较敏感的理论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拘泥于本本。虽然也在倡导“双百”政策,但政治顾虑并没有彻底解除,甚至形成为一种学术惯例。表现在研究、讨论的问题上就是,在传统法理学理论领域鲜有新论,而所谓的学术灵感、创新,大都来自于流行政治话语或西方经典理论的激活。这种贴附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所谓理论,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而那些拿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现实的论述,也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经不起实践的推敲。21世纪伊始,法理学界呈现出了一种学术自主性觉醒的新气象,如果能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识,断言这开启了中国法理学的新时代也不为过。
2.“跑马圈地”——“坚壁清野”——“学术堡垒”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积极参与几乎所有的法理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整个理论领域纵横驰骋,可称之为“跑马圈地”。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理论界存在百废待兴的需要,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是为了达到对学科的通盘把握,从结果看是为选择自己的专攻方向做好了准备。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偏好,并且有意识地确立自己的学科专长。具体说就是在整个理论的视野之内,广泛搜罗与自己学科专长有关的所有知识,以夯实自己的理论优势,可称之为“坚壁清野”。这样,21世纪的学界便林立着众多的学术堡垒。
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在“跑马圈地”这一阶段,学者们采取的是短兵相接、直接过招的交流方式,是学界难得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了“坚壁清野”这一阶段,学者们一边忙于修筑自己的学术堡垒,但还得时不时地站在尚未修建完工的堡垒上,瞭望一下其他学者的建筑进程,相好者之间也偶尔呼应一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日渐减少。等到学术堡垒建成后,有人难免会走下堡墙,在城堡之内悠哉游哉。堡垒本应有的登高望远的功能不复存在,而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地面之上的“井”。从表面看,各种研讨会、交流会、学术讲座等络绎不绝,但往往是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姑妄听之,因为所研究的领域互不搭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鲜矣。
3.直面现实——“纯粹”法理——“软着陆”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研讨尽管政治色彩比较浓,但他们是直面社会现实的,他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政治色彩仍然比较浓厚的时代。学者们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解说,由此而来的理论的生命力且不说,但这样的一种直面现实的学术精神是值得肯定的。90年代伊始,学者们要么在传统的法理学领域内精耕细作,搞纯粹的从理论到理论的阐释,未免有些云山雾罩、语焉不详,甚至使人不知所云;要么就是译介西学成果,这本身很有必要,但如果以西方理论为判准而鞭批中国的现实,却是一种时空的错位,主体意识的缺失。笔者认为,法理学就是一门讲道理的学问,讲道理的关键是要让别人明白,如果以别人智识浅陋为由而不屑理论,也就发挥不了法理学的功能,达不到理论的目的。同样道理,讲道理就得心中明了听众的情况,面对中国人用中国的典故、常识要比引用“洋段子”效果好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法理学界与政界实现了良性互动,通过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尽管淡化了政治话语),对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可称之为法理学界的“软着陆”。
4.划界——注释法条——回归
中国是一个重道德、重人情的国家,但自清末以降,有识之士认为包括重道德、重人情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前进的藩篱,必须予以消除。因此,一讲法制(法治),学者们便首先给法律与道德、人情等划界,虽然适当的予以区分也未为不可,但“很多法学界人士”“明显地表示出一种非道德化的倾向”。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法理学便只能沦落为法条的注释、政策的解说词。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表现出了一种回归的趋势。
5.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拒弃——同情式理解——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立场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无知和排斥已经成为一种国民无意识的反应,但始作俑者是“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尽管在当时这种批驳是有必要的,但却造成了一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界继承了这一衣钵,甚至在学界这一时期的理论视阈中,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惊人地消失了。90年代法理学界开始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只是少数学者的“同情式理解”,始终未成为主流话语。21世纪的前五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在增强,但还是没有摆脱文化中心主义逻辑的制约。法理学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采取“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立场”这样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即把中国和西方看作多元世界文化中的两元,“皆应谦逊地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同时,要突出自己的主体性,就是“从自身所在的位置出发,无需也不能掩饰其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在中国文化主体寻求超越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不过是众多参照之一,世界文化的所有成员皆可作为借鉴的对象。”
三、结束语
从法理学界研究的问题入手来分析、总结学界的理论特点,一是想凸现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对哪些问题的论述是可以留之于后世、启发后学,对哪些问题的论述只是昙花一现、乏善可陈。二是想探寻一种新的法理学研究进路。邓正来先生在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文中指出,中国缺乏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究其根源是独立思考的缺失。这是中国法理学界的症结之一,应当引起足够的反思。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端,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问题的另一端,即“中国法学从何处出发”同样至关重要。中国的法学(特别是法理学),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即从研究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场景开始。就这一方面来说,有个别学者也在扎扎实实地做一些研究,但还远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况且若仅仅停留在对一些典型事件的法理学解说上,还是找不到理论的实践基石。也就是说在进行法理学的定性研究的同时,要开展定量研究,为理论的开展准备一些必要的资料。如人们经常脱口而出“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但究竟淡薄到了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如果进行相关的调查,用数据说话就更有说服力。中国也有这样的先例,只不过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没有看到其他类似的调查。当然,首先应该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及有关的数据资料。
总之,本文是以研究法理学历史的方式,仔细研读前辈们的理论观点,时有扼腕称道之处,也有痛心惋惜之时,所阐发的观点难免有主观、孔见之嫌,但也有置身于局外,再现了一番与历史谋面之后的真实之感。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回顾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是手段,反思及探寻中国法理学的新的研究进路才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