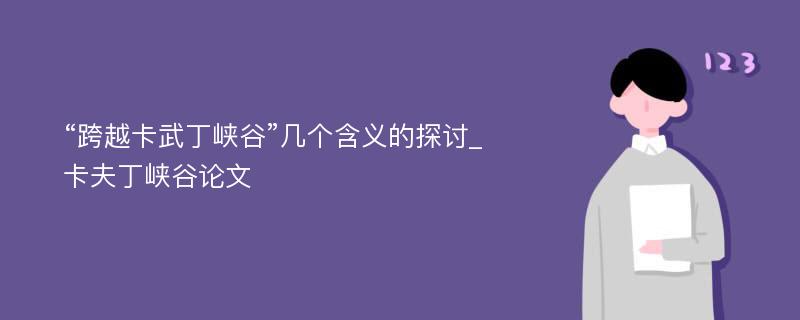
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几种含义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峡谷论文,含义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讨论的热点。究其原因,是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寻找理论上的“源头活水”。这本无可非议,而且实际上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活动。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客观地讲,有些观点是很有建设意义的,能给人以颇多的启发。但有些观点却不能让人苟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观点之间分歧较大,如同冰炭。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仅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还没有走出这一峡谷;另一些学者反唇相讥,我国早已走出“卡夫丁峡谷”已是不争的事实,说我国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一峡谷显然是无稽之谈。有学者认为,前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乃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极大地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另有学者反击,说这些“胜利”、“成功”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无联系。这些无谓的争论时至今日仍在继续。笔者之所以说这些争论是“无谓”的,是因为争论的双方没有站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来进行讨论。在所争论命题的基础性方面没有达成共识,或者说双方没有在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形成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一次地想起“熟知并非真知”这一名言。看来,真有必要来认真地讨论一下“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含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几种含义”的表述,而不是“几层含义”。“几层含义”的含义中的各个层面与总概念之间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几种含义”的含义中的“各种”与总概念之间并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几种含义”中没有总概念,或者说每一种概念本身就是总概念。与“几层含义”的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相似,“几种含义”的各种含义之间也是不相同的。纵览历史典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以及散见于国内的书籍、报刊、杂志等上的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文章,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理解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本文将对这几种含义作一简单的梳理并分别作出评析,以试图深化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含义一:典故意义上的含义
“卡夫丁峡谷”一词最早出自古罗马历史。卡夫丁峡谷地处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萨姆尼特河西南,今意大利罗马东南蒙泰萨尔基奥的阿巴亚一带。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21年,古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半岛扩张的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在卡夫丁峡谷,由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和提图斯·威图里乌斯·卡尔维努斯为统帅的5万之众的罗马军团,遭到意大利中部山区部落萨姆尼特人的伏击而战败,被迫通过把两支长矛插在地上、将第三支长矛横置其上、状如架在牡牛背上的轭的“轭形门”。这本是当时的意大利半岛上遣散战败者的传统方式,罗马人称之为“轭门下的遣送”(注: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44页。)。作为受困于卡夫丁峡谷的战败者的罗马军团在卡夫丁峡谷从长矛架设的“轭形门”被如此“遣送”,这一历史事件在罗马史上被认为是罗马人的耻辱。在这个历史典故中,本来作为地域性名称的“卡夫丁峡谷”被赋予了耻辱、灾难和波折的意思。通过“卡夫丁峡谷”就意味经受耻辱和灾难,跨越“卡夫丁峡谷”就意味着避免了耻辱和灾难。这种对“跨越卡夫丁峡谷”概念的解释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的一个附注里的解释。然而,这一本来无可厚非而且是极为准确地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解释却为后来我国某些学者对这一概念的混乱理解埋下了伏笔。
含义二:马克思意义上的含义
马克思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使用和理解无疑是源自于上述典故。据杨木先生考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曾先后六次用英、法两种语言使用和借用“卡夫丁峡谷”这一语词。马克思首次使用该词是在1853年7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东方问题评论”的《俄土纠纷。——不列颠内阁的诡计和诡辩。——涅谢尔罗德最近的照会。——东印度问题》一文里:“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后的退却,而是可以说通过卡夫丁峡谷。”1856年3—4月马克思在给《人民报》写的评论《小波拿巴法国》中又一次使用了该词:“布斯特拉巴表示愿意让那些被他折磨了4年之久的人们得到自由,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意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同意穿过没落帝国的furcae caudiane。”1881年2—3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和“三稿”中,共四次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中重复地借用了该词(注:杨木:《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
然而马克思使用这一语词的语境和时代背景是根本不同于古罗马人的,所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就与古罗马人的理解有差异。马克思不仅仅在“耻辱”、“苦难”和“波折”的意义上使用“卡夫丁峡谷”,他使用和借用“卡夫丁峡谷”这一语词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给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指明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这与我国学界某些学者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是由“跨越”和“卡夫丁峡谷”两个方面构成的。当然,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先后六次使用和借用“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跨越”一词。他在说到“卡夫丁峡谷”时,在其前面使用的是“通过”、“不通过”等词。显然,“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它是后人“赋予”马克思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一“赋予”本身,而在于这一“赋予”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赋予”,“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即便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它也是科学的概念。那么,“跨越”与“不通过”是否相矛盾呢?答案是否定的。《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是这么解释“跨”的:跨越、迈过。因此,“不通过”仅仅是“跨越”、“迈过”的否定性说法而已,“跨越”、“迈过”“卡夫丁峡谷”也就是“通过”“卡夫丁峡谷”。在此问题上,两者并无歧义,更没有如我国学者所认为的那种根本的原则性的不同。
马克思语境中的“卡夫丁峡谷”到底指什么?或者说马克思要强调的是“跨越”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在马克思先后六次使用“卡夫丁峡谷”的语境中,前两次(1853年和1856年)的确是在“耻辱”、“苦难”和“波折”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笔者认为这并非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真正要表达的旨趣。目前学界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解基本上是基于马克思后四次的使用,即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的“初稿”和“三稿”中的使用。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这里,因为在此份《草稿》中,我们能看出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在这个《草稿》中,马克思是这样使用“卡夫丁峡谷”的:“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437、438、451、129、326页。)。
从马克思对“卡夫丁峡谷”的这四次使用中可以看出,他在“卡夫丁峡谷”的前面都加了一个限定词——“资本主义制度”,这并非某些学者所说的同义反复。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这样说也许引起某些人的不满:怎么可能呢?当时的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中,马克思怎么还说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呢?既已处在“峡谷”中就不存在通不通过的问题。的确,俄国自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以来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尽管这种资本主义比较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献中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说,“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所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437、438、451、129、326页。)。恩格斯在其逝世前夕已经明确讲过,“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7、509页。)。史学研究表明:“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从60年代起,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农业经济也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注: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另据李宏图等先生的研究,1861年农奴制改革,“从内容和影响上看,这场改革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是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俄国在保留了许多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正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注:李宏图、沐涛、王春来、卢海生:《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当时的俄国既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显然不是俄国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点马克思也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马克思在其晚年思想中阐明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体并不是俄国,而是俄国农村公社。由于这并非本文的主题,故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中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很明显,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语境中要表明的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从而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成为“使俄国比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这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真实意图。
含义三:国内学者意义上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跨越卡夫丁峡谷”概念的理解,大致可简单归纳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解读,试图在“返本”的意蕴中来重释马克思;另一种情况是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在理解上的肆意引申和发挥,试图在“开新”的意蕴中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先看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制度层面,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下,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阵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二是生产力层面,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一旦完成制度跨越之后,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真正完成这一跨越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否则这一跨越是不会成功的。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二是指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及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灾难、不幸、痛苦和波折。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不仅如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还没有走出这一峡谷。这种说法所蕴含的意思是,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某一民族或国家就永远处于“卡夫丁峡谷”中,因此“卡夫丁峡谷”就是指资本主义因素。
应该说,上述四种观点中的前三种对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赋义”——一种不合理的“赋义”。直面马克思的文本,在他先后六次使用和引用“卡夫丁峡谷”这一语词时,前两次的确是在波折、灾难的意义上的。但马克思不是一个道义的谴责者,而是一位理性、严谨的理论家。虽然价值尺度也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发展的标尺,但他始终把价值尺度建立在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价值尺度脱离历史尺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成为历史的抽象。因此,马克思使用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含义更是在历史尺度意义上的。“卡夫丁峡谷”即指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灾难、波折和经济危机等与制度并非属于同一层面,前者只是后者的派生和后果而已。此为其一。其二,马克思在使用“卡夫丁峡谷”的语境中,并没有涉及生产力层面的通不通过问题,这显然是某些学者的“演绎”。马克思从不否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在讲到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并未说到生产力。这些学者联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不可逾越,便自然地杜撰出生产力的不可跨越性,把马克思在此语境中没有讲过的东西强行塞进来,犯了“结论先行”的错误。其三,把“卡夫丁峡谷”规定为“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那么,是不是说没有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就不必跨越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涉及到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是制度?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的看法是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陈郁等译,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康芒斯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注:[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6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页。);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凡勃仑把制度理解为“思想习惯”和“流行的精神状态”(注:[美]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页。)。上述学者在理解和界定制度的过程中,总是局限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出于自身研究的需要,往往因片面地抓住了制度的某一方面、因素而带有某种程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不仅仅是“规则”、“程序”、“规范”、“模式”,而且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3884页。)。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指“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3884页。)。而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指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机器大工业之前还先后经历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两个阶段;而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复杂性程度可把资本主义生产划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个阶段;按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性程度可把资本主义发展概括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试问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要跨越的是哪一阶段呢?实际上,制度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生产则主要相对于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力的技术性构成和协作性而言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域”是不同的。马克思所谓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跨越“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上述把“卡夫丁峡谷”理解为“资本主义因素”更是荒唐之极。纵观人类历史发展,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只有一种纯而又纯的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原始社会末期也已出现私有制形式,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原始部落。马克思早就告诉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是看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并不排除这个社会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以外还有其它的不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性质。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恐怕一直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因素”,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不矛盾,而且还可利用这些“资本主义因素”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上述观点不仅与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本意相左,而且也不符合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属于这种情况的学者立足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试图使用“跨越卡夫丁峡谷”来论证中国改革的艰辛和市场经济进程的困难。为了论证的需要便把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概念做了随意的引申和发挥。为了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几句引文:“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正跨越‘卡夫丁峡谷’,甚而出现了苏联东欧‘回归欧洲’的剧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上长期徘徊,主要难关在哪里,出路何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最大难关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顶住了内外的压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其伟大实践指明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出当前的困境,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金桥’”(注:梁云彤:《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主要难关与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看了这几句引文,我们的读者有何感想呢?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还要言谈“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呢?显然,这位论者所使用的“卡夫丁峡谷”既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理解,也不是上述第一种情况意义上的理解。这里的“卡夫丁峡谷”(笔者斗胆猜测,不一定是这位论者的本意)可能是指某一“障碍”、“沟壑”、“陷阱”,一旦跨过这一“障碍”、“沟壑”、“陷阱”即跨越了所谓的“卡夫丁峡谷”,就算闯过了难关,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出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解距离马克思的本意有多远,读者可以想见得到。讨论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当今学界提倡的学术创新、理论创新来。“返本开新”是一个好的学风,但“开新”并非脱缰的野马,没有限度。讲创新、“开新”并不是把马克思变成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看来“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的路途还很遥远。
标签:卡夫丁峡谷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