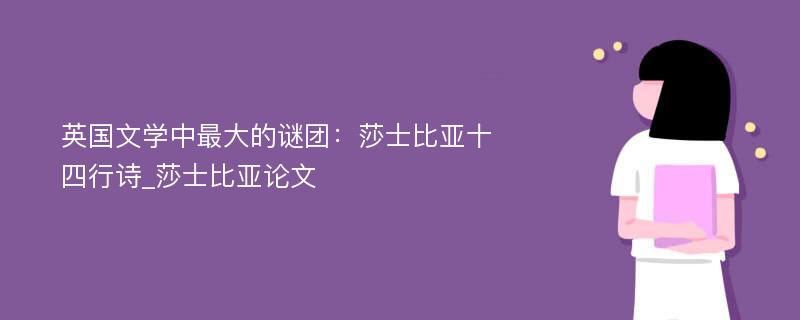
英国文学中最大的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英国论文,四行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其文学价值而论,是堪与他的最佳剧作相颉颃的诗歌杰作。莎学家斯托普斯女士(Charlotte Stopes)在1904年说:到了19世纪,
读者开始发现这些十四行诗的超绝的美,承认莎士比亚在发展抒情诗方面同他在发展戏剧方面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莎士比亚的艺术的完美,哲理的深邃,感情的强烈,意象的丰富多样,诉诸听觉的音乐的美妙,只有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才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种评价是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放在他的戏剧之上了。但这不是她的首创,在她之前的莎学家,如温达姆(Wyndham)在1898年就持这种观点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初出版于1609年。该年5月20日,伦敦书业公所的“出版物登记册”上,“一本叫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书”注册了,取得此书的独家印行权的出版者名叫托玛斯·索普(Thomas Thorpe)。同年6月初,这本书出售了。此书收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54首,依次编了号码,各诗之间互有联系,是一部系列组诗。这就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早、最完全的版本,史称“第一四开本”。
这些十四行诗的内容,按照18世纪末两位莎学家梅隆(Malone)和斯蒂文斯(Steevens)的解释(1780),大致是这样的:从第1到126首是写给或讲到一位美貌的贵族男青年的;从第127到152首是写给或讲到一位“黑女郎”的;最后两首与整个“故事”无关。这种解释一直广泛流传到今天。细分一下:第1至17首形成一组,这里诗人劝他的青年朋友结婚,以便把美的典型在后代身上保存下来,以克服时间毁灭一切的力量。此后一直到126首,继续着诗人对朋友的倾诉,而话题、事态和情绪在不断变化、发展着。青年朋友是异乎寻常的美(18-20首)。诗人好象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但对青年的情谊使他得到无上的安慰(29首)。诗人希望青年不要在公开场合给诗人以礼遇的荣幸,以免青年因此蒙羞(36首)。青年占有了诗人的情妇,但被原谅了(40-42首),诗人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不能忍受,但又不忍心离开这世界,因为怕青年因此而孤单(66首)。诗人对别的诗人、特别是一位“诗敌”之得到青年的青睐,显出妒意(78-86首)。诗人委婉地责备青年生活不检点(95,96首)。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诗人回到了青年身边(97,98首)。诗人与青年和解(109首)。诗人从事戏剧职业而受到社会的歧视,他呼吁青年的友谊(110,111首)。诗人曾与无聊的人们交往而与青年疏远过,但又为自己辩护(117首)。诗人迷恋一位黑眼、黑发、黑(褐)肤的卖弄风情的女郎(127,130-132首)。“黑女郎”与别人(可能就是诗人的青年朋友)相爱了,诗人陷入痛苦中(133,134,144首)。——以上的解释虽然受到过不少人反对,但逐渐深入人心,到现在已被大多数读者接受。
莎士比亚十四行系列组诗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十四行体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普罗旺斯民间,原是一种用于歌唱的抒情小诗,颇有些类似中国古代的“词”。它大约于13世纪被意大利文人采用;到14世纪出现第一位十四行诗代表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他的《歌集》包括三百多首用意大利文写成的十四行诗,抒发了对他所倾心的少女劳拉的爱情。从16世纪起,这种肇始于意大利的诗体向欧洲各国“扩散”,渗入法、英、德、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等国,产生了用上述各国语文写出的大量十四行诗。16世纪初,英国的两位贵族诗人托玛斯·崴阿特爵士(SirThomas Wyatt,1503-1542)和萨瑞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Earl of Surrey,1517-1547)把十四行诗形式引进英国。他们翻译成英文的彼特拉克十四行诗,被收入出版商托特尔(Tottel)在他们死后出版的杂诗集《歌谣与十四行诗》(1557)中。他们同时用这种形式进行英文诗歌的创作实践,成为最早的英文十四行诗作者。十四行诗以系列组诗形式在英国风行一时,则由菲力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在1591年出版的《爱星人和星》发端。这之后五年内在英国突然涌现出一大批十四行系列组诗作品。到1596或1597年,这种风尚突然终止。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十四行系列组诗的作者名单包括了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和次要诗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有:丹尼尔(Samuel Daniel,1563-1619)的《黛丽亚》(1592),康斯塔布尔(Henry Constable,1562-1625)的《黛安娜》(1592),洛其(Thomas Lodge,1558-1625)的《斐丽丝》(1593),德瑞顿(MichaelDrayton,1563-1631)的《艾狄亚的镜子》(1594),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小爱神》(1595),以及巴恩斯(Barnabe Barnes)、弗雷彻(Giles Fletcher)、帕西(William Parcy)、格里芬(Bartholomew Griffin)、托夫特(Robert Tofte)等人的十四行系列组诗。莎士比亚可能也是在这个十四行系列组诗浪潮冲击英伦的时期写作了他的十四行诗。1599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两首(第一四开本中的138首,144首)出现在一本被印作“莎士比亚著”的诗集《热情的朝圣者》中,出版者是杰加德(William Jaggard)。之后就是第一四开本在1609年出版。它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但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它的光芒终于把当年那些辉耀诗坛、风靡一时的同类作品掩盖了。
莎士比亚当时为什么不出版或不立即出版他的十四行诗?据莎学家贝文顿(DavidBevington)最近(1992)说:
莎士比亚可能有意推迟了他的十四行诗的出版日期,并不是由于他不重视这些诗的文学价值,而是由于他不希望被人们看作以写十四行诗为职业。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们中,写诗是一种高雅行为,一种骑士风格,一种消遣,用来愉悦朋友,或用来向女士求爱。出版诗集不太符合上流社会人士的身份。有些作者发现自己的诗作被盗印出版,都惊愕不已。16世纪90年代伦敦的青年才子们也模仿这种时尚。他们只求在同伙的小圈子内得到好评,不求在社会上扬名。莎士比亚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难以肯定。总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1609年以前一直没有出版过。出版时,十四行系列组诗的热潮早已过去。这部诗作在1640年以前没有再印过。
十四行系列祖诗的规模和写法给诗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新天地。典型的主题是爱情的追求中女主人公的高傲冷漠和诗人的悲观绝望,一而再地刻画小姐的美貌,召唤睡眠,声言诗歌的不朽等等。某些十四行系列组诗带有诗人自述的性质,或称“自传式”笔法,诗中的女主人公可以与实际生活中的真人对上号:如锡德尼写的是彭涅洛佩·里契夫人;斯宾塞写的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波依尔。在另一些组诗中,女主人公是诗人的女保护人,也有的全然是想象出来的人物。锡德尼的《爱星人和星》具有鲜明的戏剧色彩,直白的口语,整个作品十分生动有力;斯宾塞的《小爱神》富有音乐感,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性意象,蕴含着深沉的柏拉图式感情和基督教徒式情愫。德瑞顿的《艾狄亚的镜子》的独创性表现在另一方面:从不同寻常的事物如簿记、字母、天体数字等中间撷取意象,用变化多端的修辞和比喻使读者眼花缭乱。
莎士比亚的这一系列,尽管还是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十四行系列组诗的总的框架范围内做文章,却在很多方面完成了独一无二的创造。最突出的一点是:在这些诗中诗人致词的主要对象不再是所爱的女子而是一位男性青年朋友。莎士比亚强调友谊,这是非常新鲜的。在当时所有的十四行系列组诗中没有一部把大部分篇幅给予朋友而不给予情人。同时,诗中的“黑女郎”也与按照彼特拉克传统写出的女主人公大异其趣。还有一点,也许这点更重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包含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意蕴,比我们能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任何十四行系列组诗中所能找到的,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历史证明,在英国的十四行诗群山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一座巍峨的高峰;不仅在英国的抒情诗宝库中,也在世界的抒情诗宝库中,它恒久地保持着崇高的地位。
然而,这样一部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三百多年来,又被一层神秘的纱幕笼罩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人始终没有见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一代又一代的莎学专家和文人学士对这部组诗进行了难以数计的考订、研究探讨和论证。对它“聚讼纷纭”的论辩之繁、之细,在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中,除了《哈姆雷特》之外,无出其右!贝文顿说:这部组诗成了一个谜,“在全部英国文学中,恐怕没有其他谜引起这么多思考,产生这么少共识!”(1992)其谜底也许将永远沉埋在历史的烟雾中。
关于版本
前面已经说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初的、最完全的版本是1609年索普出版的第一四开本。但这个版本中有一些排印错误。全书共有诗2155行,排错的地方有大约36处,平均每60行有一处。卷首献词由出版者索普(即T.T.)出面,而不是由作者出面;献词内容含义不明。这些足以说明这个版本没有得到莎士比亚的授权,至少没有经过他的校阅。集子中第99首比规定的十四行多出一行;126首只有十二行;145首每行少去两个音节;最后两首与组诗无关,被有的人说成是古希腊警句诗的英译或改写,还有人否认这两首出自莎士比亚的手笔。集子中各诗的排列次序看上去似乎有些乱。因此人们怀疑这个版本并非根据莎士比亚自己编定的手稿发排。
公元1640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诗集,莎士比亚著》,出版者是本森(JohnBenson),其中收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46首(删去18、19、43、56、75、76诸首)及归在莎士比亚名下的1612年版《热情的朝圣者》及其他诗作。体例较乱。146首十四行诗的排列完全不按第一四开本的次序,而是打乱后重新组合成72首,分别冠以标题。第一四开本的献词去掉了。第一四开本中有些男性代词he及其所有格his都被改为女性代词she及其所有格her,这样,这些诗中的致词对象一律变成了女性。
本森编的本子在此后一个半世纪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10年纪尔登(CharlesGildon)的编本、1714年罗(Nicholas Rowe)编的莎士比亚全集中的十四行诗部分、1725年蒲柏(Alexander Pope)编的莎士比亚全集所收西韦尔(George Sewell)编的十四行诗、1771年埃文(Ewing)的编本、1774年简特尔曼(F.Gentleman)的编本、1775年伊文斯(Th.Evans)的编本、1804年敖尔吞(Oulton)的编本、1817年德瑞尔(Durrel)的编本,都以本森的本子为依据。1711年出版商林托特(Lintot)翻印1609年的第一四开本,标题页上竟印着:“这里154首十四行诗,全部是对所爱女子的赞美。”这说明了本森的影响。直到19世纪,诗人柯尔律治(S.T.Coleridge)还坚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是写给情人(女性)的。今天持此说者也还没有绝迹。
到了18世纪后期,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斯蒂文斯编《莎士比亚戏剧二十种》(1766),附有十四行诗,是用的第一四开本。卡贝尔(Capell)有一部未印的手稿,修订林托特翻印本,现藏三一学院图书馆,在序中抨击本森的本子。梅隆编有两种本子,第一种刊印于1780年,第二种刊印于1790年,后者作为他编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第十卷,两种本子均用第一四开本,均作了校勘。这两个本子对后来的影响都较大。19世纪初期的本子都是梅隆编本的翻印本。
到了1832年戴斯(Dyce)的编本倾向于恢复第一四开本的原貌,排斥了梅隆的校勘。以后的编本延续了这种倾向,如克拉克·赖特和奥尔狄斯·赖特(Clark and AldisWright)的“环球”本(1864)、他们的剑桥本第一版(1866)和剑桥本第二版(1893),罗尔夫(W.J.Rolfe)编本(1883、1898),都是如此。温达姆编本(1898)完全拥护第一四开本。也有另一种本子,如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编本(1899),改动第一四开本的地方过多,形成另一种倾向。
到了20世纪,许多版本都尽量保存第一四开本的面貌。斯托普斯的编本(1904),尼尔逊(Neilson)的编本(1906),普勒(C.K.Pooler)的“亚屯”版(1931,1943),里德利(Ridley)的编本(1934),基特列奇(Kittredge)的编本(1936),G.B.哈锐森(G.B.Harrison)的编本(1938),布什和哈贝奇(Bush and Harbage)的编本(1961),英格兰姆和瑞德帕斯(Ingram and Redpath)的编本(1964),威尔逊(Wilson)的编本(1966),布思(S.Booth)的编本(1977),都以第一四开本为底本。辛普逊(Percy Simpson)的《莎士比亚的标点》(1911)也完全赞同第一四开本。本世纪还出版了两种莎士比亚著作的“集注本”,先是奥尔登(R.M.Alden)“集注本”(1916),后来是柔林斯(H.E.Rollins)的“新集注本”(1944)。后者重印了第一四开本的原文,又将后来各家版本的异文加以集注,十分详尽,而且眉目清楚。本世纪的印本,已经摆脱了本森的影响。
W.H.先生是谁?“朋友”是谁?
1609年第一四开本卷首印有出版者索普(T.T.)的献词,原文如下:
TO THE ONLY BEGETTER OF
THESE ENSUING SONNETS
MR.W.H.ALL HAPPINESS
AND THAT ETERNITY
PROMISED
BY
OUR EVER-LIVING POET
WISHETH
THE WELL-WISHING
ADVENTURER IN
SETTING
FORTH
T.T.
梁宗岱的中文译文是:
献给下面刊行的十四行诗的
唯一的促成者
W.H.先生
祝他享有一切幸运,并希望
我们的永生的诗人
所预示的
不朽
得以实现。
对他怀着好意
并断然予以
出版的
T.T.
梁实秋的中文译文是:
发行人于刊发之际敬谨祝贺
下列十四行诗文之无比的主人翁
W.H.先生幸福无量并克享
不朽诗人所许下之千古盛名
T.T.
这里,献词是献给W.H.先生的。这W.H.先生到底是谁呢?
首先要弄清The Only Begetter是什么意思。Only一般解作“唯一的”,也可译作“无匹的”。Begetter可解作这些十四行诗的“促成者”(引起诗人写这些诗的那个人,也就是诗中的那位“朋友”),也可解作为出版者搜集到这些诗的原稿或抄件的人,即这些诗的“获致者”(这就不是诗中的那位“朋友”);前者把W.H.与“朋友”合一,后者把W.H.与“朋友”分开。梁宗岱和梁实秋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进行了翻译。
主张Begetter为“获致者”的注释家,代表人物是锡德尼·李(Sidney Lee)。他在《莎士比亚传》(1931年增订版)中断言,W.H.即威廉·霍尔(William Hall)。此人是个学徒出身的出版业从业员,可能是索普出版业合伙人。估计他为了满足索普的出版愿望,设法弄到了莎士比亚的这部诗稿。更早的时候,1867年,梅西(Massey)也把Begetter解作诗稿“获致者”,认为W.H.是威廉·赫维(William Hervey),此人乃第三任南安普敦伯爵亨利·莱阿斯利(Henry Wriothesley,Third Earl of Southampton,1573-1624)的继父,他的母亲的第三任丈夫。后来,1886年,弗里埃(Fleay)也持此说。到了1904年,斯托普斯更坚持说W.H.是威廉·赫维。她当然不认为索普的献词是献给诗中的美貌青年朋友的,她认为那位朋友是南安普敦伯爵。南安普敦伯爵的母亲于1598年与赫维结婚,死于1607年。斯托普斯设想赫维在亡妻遗物中发现了诗稿的抄件,便把它交给了索普。此说受到罗伯特逊(Robertson)等人的支持。但这派人的影响已越来越小。反对此说者,如斯密斯(Hallet Smith)诘问道:假如Begetter只是诗稿“获致者”,“那么出版者为答谢他而祝他永垂不朽,就太古怪了;隐其真名只用缩写,也没道理。”
另一位注释家尼尔(Neil)在1861年声称,他设想W.H.是威廉·哈撒威(WilliamHathaway),莎士比亚妻舅,生于1578年。尼尔说,莎士比亚晚年退休回到故乡后,可能想给这位妻舅一个惊喜,便把自己的十四行诗手稿交给他,让他去卖给出版商;因此“哈撒威完全可以被称为这些十四行诗的获致者、搜集者,甚至可以说,编辑者”。两年后,恰塞尔斯(Chasles)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现在已无人再提此说。
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有两位贵族成为他的无可怀疑的保护人。主张Begetter为这些十四行诗的“促成者”的注释家们,把这两位保护人当作W.H.先生(同时也是诗中的“朋友”)的候选人。其一是威廉·赫伯特,第三任彭布罗克伯爵(William Herbert,Third Earl of Pembroke,1580-1630)。他于21岁时(1601)继承爵位。莎士比亚在1589年至1592年间的剧作是由“彭布罗克剧团”演出的,这个剧团的保护人是威廉·赫伯特的父亲,第二任彭布罗克伯爵。莎士比亚的剧本1623年第一对开本就是献给彭布罗克的。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海明奇(Heminge)和康德尔(Condell)说,彭布罗克很珍视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十分宠爱他。W.H.这两个字母也与威廉·赫伯特的首字母相符。波登(Boaden)是第一位主张W.H.即彭布罗克的注释家,他倡此说于1832年。继起者有布赖特(Bright)、亨利·布朗(Henry Brown)、泰勒(Tyler)、柔林斯、威尔逊、T.坎贝尔(ThomasCampbell)等人。持异议者说,一个普通出版商称伯爵为“先生”(Mr.=Master)是不敬的;又说,这些十四行诗的写作日期较早,没有证据证明那时莎士比亚已与彭布罗克有交情;更有人反对说,1593年时,威廉·赫伯特只有13岁,莎士比亚在诗中竭力怂恿他娶妻生子,岂不荒诞!于是持此说者便设法把这些诗的写作年代往后移。1595年,威廉·赫伯特15岁,其父母逼他与伊丽莎白·卡瑞小姐结婚,他执意不从。此时,莎士比亚可能受到他父母的嘱托,写诗劝婚。这就是持此说者解释开头17首十四行诗产生的背景。
莎士比亚的另一位保护人是前面已提及的亨利·莱阿斯利,第三任南安普敦伯爵。他8岁丧父,继承爵位(1581),受财政大臣伯利勋爵的监护。16岁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年轻美貌,喜爱文艺;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恩宠,与埃塞克斯伯爵(Essex)过从甚密。后随埃塞克斯两度出征国外以寻求军功。1591年伯利勋爵要把孙女嫁给他,其母也劝他攀这门亲事以巩固家族的地位,但他推托不允。莎士比亚可能受其母之请,写第一批17首十四行诗以劝婚。南安普敦伯爵后受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未遂一案牵连,被判终身监禁。女王死后始获释放。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董尼》和《鲁克丽丝失贞记》都是献给他的,两诗卷首的献词表明了这一点。《鲁克丽丝失贞记》的献词尤其显出某种亲密程度,结束时祝他“幸福无疆”(all happiness),索普可能把它移用到了给W.H.的献词中,这也是W.H.即南安普敦伯爵的一个旁证。第一位主张W.H.即南安普敦伯爵的注释家是德瑞克(N.Drake),倡此说于1817年。继起者有詹姆逊(Anna Jameson)、威里(Wailly)、梅西等人。此说生命力很强,一直延续到现在,拥有较多的支持者。此说的一个弱点是亨利·莱阿斯利的缩写(首字母)是H.W.而不是W.H.,为什么要颠倒呢?另一个弱点是,1594年以后没有南安普敦伯爵与莎士比亚密切交往的文字记载。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说法。
在18世纪,莎学家法默(Farmer,1735-1797)认为,W.H.是莎士比亚的外甥威廉·哈特(William Harte)。但这位外甥于1600年8月28日才受洗礼(出生后三天),因而此说不能成立。另一位莎学家蒂尔辉特(Tyrwhitt,1730-1786)声言,W.H.是一位名叫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的演员。这个人是蒂尔辉特根据莎士比亚诗中的一些字词,牵强附会,假想出来的,没有事实根据。后来小说家王尔德(O.Wilde)还根据这一假想写成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章《W.H.先生的画像》(1889)。
肯宁汉(P.Cunningham)于1841年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朋友是一个半阴半阳的两性人。怀特(White)于1854年认为W.H.先生是雇莎士比亚为他写诗的人,并说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无诗才的人雇诗人做自己写诗的“助手”是当时的风尚。后来,布拉特(Blatt)于1913年断言:某一位W.H.先生,年迈而跛足,花钱雇莎士比亚写了这些诗。
1860年,邦斯托夫(D.Barnstorff)宣称W.H.实即William Himself(威廉·莎士比亚自己)!此说一出,受到多人的嘲笑和抨击。
最近,福斯特(Donald Forster)提出,"Mr.W.H."只是一起排印上的错误,索普本来写的是"Mr.W.S."即(Master William Shakespeare)(威廉·莎士比亚先生)。这样,Begetter就纯粹是“作者”了。此说与上一说颇似孪生子。但索普的献词中不仅提到:"Mr.W.H.",还提到"Our Ever-Living Poet"(我们永生的诗人),这里,索普向W.H.献上了“我们永生的诗人所许诺的不朽盛名”,也就是说,索普向莎士比亚献上莎士比亚给自己许诺的不朽的盛名。索普绕弯子说这些话,目的何在?
到底W.H.先生是谁,一二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主张W.H.为南安普敦伯爵的说法稍占上风,但对这个问题采取不可知、不必知、知亦无大助于理解诗作本身的态度者,仍大有人在。
与“朋友”有关的是男性同性恋说。这些十四行诗中对朋友常以“爱人”称,有时称之为“我所热爱的情郎兼情女”(第20首),诗中表露的感情非常热烈,几次提到别离给诗人带来的痛苦(第43、44、45首,等)。那朋友又有非常俊美的容貌。有些诗的歌颂对象是朋友(男性)还是情人(女性),不能确定。这就引起了一些注释家的异想。巴特勒于1899年首先提出,这些十四行诗表明,那位青年朋友勾引了莎士比亚,使之陷入男性同性恋的罪恶。瓦尔希(Walsh)于1908年、贾瑟兰德(Jusserand)于1909年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马修(Mathew)于1922年毫无根据地声称,本森在1640年重印这些诗时把诗中的男性代词改为女性代词,正好证明了1609索普的版本透露了男性同性恋的罪恶。吉雷特(Gillet)于1931年进一步说,那个危险的男孩使出了浑身解数,勾引、诱惑了这位极其敏感的、年长的诗人莎士比亚。这些说法受到了反驳和责难。赫布勒(E.Hubler)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包含的意义》(1952)中指出:
关于莎士比亚的性生活,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样的:18岁时他娶了比他大8岁的女子为妻,婚后六个月他做了父亲。一年又九个月后他再度做了父亲,这次生的是孪生儿。很明显,他早年的性生活完全是异性的,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同性恋者。
“黑女郎”是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所谓“黑女郎”。她并不是黑种人,只是黑眼、黑发,肤色暗褐。她不是blonde,即当时社会上推崇的白肤、金发、碧眼的美人。她富于性感,极具女性诱惑力,成了诗人的情妇。但她水性杨花。诗人对她是一片痴情,希图独占。当她投入他人的怀抱时,诗人便陷入痛苦之中。偶尔诗人也有内疚和对她厌恶的情绪。十四行诗的前半系列有几首(第35,40,41,42首)涉及诗人的朋友与诗人的情妇之间存在着私通的关系。后半系列中的第144首是一个关键,透露出“黑女郎”勾引了诗人的朋友;而诗人的反应明显地是为朋友担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嫉妒。看来要弄清“黑女郎”是谁比弄清那位朋友是谁更加困难。但有些注释家还是信心十足地提出了具体的人选。
恰尔默斯(Chalmers)在1797年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都是写给伊丽莎白女王的。W.H.格里芬(W.H.Griffin)于1895年认为“黑女郎”纯粹是想象中的人物。芒兹(Von Mauntz)于1894年认为这些十四行诗中至少有11首(第27,28,43,44,45,48,50,51,61,113,114首)是莎士比亚写给他的妻子安妮·哈撒威(Anne Hathaway)的。梅西于1866年声称这些十四行诗中有一个五角恋爱关系,牵涉到南安普敦伯爵和他的情妇(后来的妻子)伊丽莎白·维尔农(Elizabeth Vernon),彭布罗克和他的情妇佩涅洛佩·里契(Penelope Rich),还有诗人自己。诗中的女主人公时而为维尔农,时而为里契。
泰勒于1884年首先提出“黑女郎”是玛丽·菲顿(Mary Fitton)的说法。这一主张的前提是诗中的朋友必须是彭布罗克。玛丽·菲顿比莎士比亚小14岁。她17岁时来到伦敦王宫中,次年被伊丽莎白女王任命为近侍。19岁时嫁给61岁的内廷总管威廉·诺里斯(William Knollys)。彭布罗克伯爵与玛丽·菲顿的私情在宫廷里成为公开的秘密。菲顿23岁时怀孕。彭布罗克承认与她有两性关系。女王大怒。菲顿生了一个男孩,不久夭折。女王下令将彭布罗克监禁(不久释放),将菲顿逐出宫廷。菲顿是个水性扬花的女人,除了与彭布罗克私生一子外,还与里维森爵士私生过两个女儿。后来她又先后嫁过两个丈夫。泰勒提出玛丽·菲顿之说,得到很多人赞同。因为菲顿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太像诗中的“黑女郎”了。泰勒的主张在发表的当年即受到W.A.哈锐森(W.A.Harrison)的大力支持,后来(1889)又受到佛尼伐尔(Furnival)等人的认可。10年后,哈力斯(F.Harris)又著书支持泰勒的说法。萧伯纳于1910年以玛丽·菲顿为依据写成《十四行诗中的“黑女郎”》。但是4年后萧伯纳声称他不再相信“黑女郎”就是玛丽·菲顿,因为他见到了阿伯瑞(Arbury)肖像画上的玛丽·菲顿,她的皮肤是白皙的。
此外还有种种说法,如斯托普斯于1898年认为“黑女郎”不是贵妇而是有钱的平民之妻,她选中了出版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董尼》的出版商里查·费尔德(Richard Field)的妻子,法国人,并且猜想她是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克拉立克(Kralik)于1907年臆测说“黑女郎”在莎士比亚结识南安普敦伯爵之前就已经是莎士比亚的情妇了,后来她引诱了南安普敦伯爵,背弃了诗人。她的名字可能叫罗萨琳。诸如此类。但这些说法大都昙花一现就销声匿迹了。
“诗敌”是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若干首(至少9首,即第78-86首,或者更多,如第32、76首等)涉及一位(或几位)与莎士比亚争宠的诗人,被称为“诗敌”。这位“诗敌”究竟是谁,引起了许多探索和猜测。一种说法是,把“诗敌”看作一位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诗人。如梅隆于1780年声称“诗敌”是斯宾塞;波登于1837年认为是丹尼尔;柯里埃(Collier)于1843年认为是德瑞顿;卡特莱特(Cartwright)于1859年认为是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梅西于1866年也说是马洛;奥尔杰(Alger)于1862年主张是琼森(Ben Jonson);锡德尼·李于1898年认为是巴恩斯;斯托普斯于1904年认为是恰普曼(George Chapman);萨拉辛(Sarazin)于1906年认为是皮尔(George Peel)。
另一种说法是把“诗敌”看作不止一人。明托(Minto)于1874年即主张“诗敌”涉及许多人,其中主要的一人是恰普曼。亨利·布朗于1870年认为是戴维森(Davidson)和戴维斯(Davies);弗里埃于1875年和1891年两次发表意见,认为“诗敌”是纳希(Nashe)和马坎姆(G.Markam);A.霍尔(A.Hall)于1884年声称,“诗敌”是一群人,其中有德瑞顿,马洛·皮尔,纳希,洛其,恰普曼,巴拿比·里契(Barnaby Rich)等;温达姆于1898年声称,当年,
琼森、恰普曼、马斯顿(Marston)、德瑞顿等人组成一个相互标榜的小社团,其成员总是称赞圈子中人的作品,而漠视、嘲笑或者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
这些人就是莎士比亚诗中的“诗敌”。
关于“诗敌”,还出现过一些奇特的论点。如一位无名氏于1884-1886年撰文声称,“诗敌”是指意大利诗人但丁,因为莎士比亚在第86首十四行诗中称“诗敌”为spirit(精灵,幽灵,鬼),“可见此人不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活人”;又说,第86首中提到的“在夜里帮助他(“诗敌”)的伙计”是希腊的荷马、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古代诗人;同一首诗中提到的“每夜把才智教给他(“诗敌”)的、那位殷勤的幽灵”则是贝阿特丽采——但丁心目中的恋人,《神曲》中理想化了的女子。
有独无偶,G.A.利(G.A.Leigh)于1897年又提出新说法,认为“诗敌”是意大利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他与但丁不同,是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G.A.利找出了理由,十四行诗第78首中把“诗敌”称作alien pen(外国诗人。按alien可解作“外国的”,也可解作“陌生的”等),可见这是个外国人。G.A.利说,当时英国的文人们长期嫉妒着意大利文学对英国宫廷和上流社会的影响,而当时意大利诗歌的代表诗人就是塔索!
还有更富于想象力的论点。麦凯(Mackay)于1884年声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有好多首是出自马洛的手笔。麦凯指出,像第80首,其中称“诗敌”为“高手”,把他比作“雄伟的巨舰,富丽党皇”,而称自己是“无足轻重的舢舨”,如果把位置倒过来,“诗敌”是莎士比亚,作者是马洛,这才恰当;若是相反,那就不恰当。麦凯又说,像第86首,作者肯定是马洛,那是“宽宏大量、毫无忌妒之心的诗人马洛在高度赞赏和揄扬莎士比亚啊!”说来说去,这些十四行诗中的“诗敌”原来就是莎士比亚!而作者却是另一个人。
排列次序问题
本文开头曾介绍过广泛流行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故事”,这是梅隆和斯蒂文斯按照1609年第一四开本对154首十四行诗的排列顺序所作的解释。但第一四开本里,153、154首与前面各首无关;可以区分的两大部分里,有人发现存在着前后矛盾或不协调的地方,例如:嫉妒消失之后又突然出现;诗人受到朋友的抛弃而悲号,忽然又讲到友情的融洽无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有些诗前后紧密相连,有些诗前后无关;40至42首中不幸的三角关系,与后面“黑女郎”出现后诗中的三角关系,是不是同一事件,也令人猜疑。多数读者能够感受到整部系列组诗中故事进展的连续性,但仍然有人感到许多首诗越出了故事进展的正常轨道。索普的1609年版本未必可靠;本森的1640年版问题更多。梅隆于1780年恢复了索普版的排列次序,但并不能挡住对这些诗进行重新排列尝试的诱惑。
据柔林斯在《新集注本》(1944)中的不完全统计,在索普和本森的两种版本的排列次序之后,从奈特(Charles Knight)于1841年开始,到布瑞(Bray)于1938年为止,各种不同的重新排列产生过19次;有的学者如布瑞就重新排列了两次。这些重新排列大都伴随着对为什么要另起炉灶的解释。其后,从30年代末到现在,重新排列的尝试并没有终止。
写作年代问题
写作年代问题恐怕是这些十四行诗所引起的诸种问题中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其他问题将可迎刃而解,或至少可以较为明朗化,如“朋友”是谁,W.H.是谁,“黑女郎”是谁,“诗敌”是谁(假定他们都实有其人),也可以探知这些诗与其同时代作品的渊源关系。但是,最终精确地认定写作年代,却绝不是容易的事。
1598年,米亚斯(F.Meres)的《帕拉迪斯·塔米亚:才智的宝库》出版,书中赞誉了一百多位英国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并提到莎士比亚的“甜蜜如糖的十四行诗”“在知心朋友间流传”。可见,在索普的1609年版出现10年之前,这些诗已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学者们说,米亚斯讲的“甜蜜如糖的十四行诗”,可能只是后来公开出版的十四行诗的一小部分。
如果诗中的“朋友”是南安普敦伯爵,那么莎士比亚写这些诗开始于1591年,此年伯爵18岁,莎士比亚(27岁)可能奉伯爵的母亲之命写第一批劝婚诗。
如果诗中的“朋友”是彭布罗克伯爵,那么莎士比亚写这些诗开始于1595年,此年彭布罗克15岁,莎士比亚(31岁)可能奉彭布罗克的父母之命写第一批劝婚诗。
有的学者从诗中可能影射的历史事件来判定诗的写作年代。如第25首中有这样的句子:“辛苦的将士,素以骁勇称著,/打了千百次胜仗,一旦败走,/便立刻被人逐出荣誉的纪录簿,/使他过去的功劳尽付东流。”温达姆于1898年说,这些诗句“最恰当不过地写到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在爱尔兰的军事失利和随后的被捕”,而这次事件发生在1599年。因此,这首诗可能写于1599年或稍后。第25首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帝王的宠臣把美丽的花瓣大张,/但是,正如太阳眼前的向日葵,/人家一皱眉,他们的荣幸全灭亡,/他们的威风同本人全化作尘灰。”中国学者裘克安先生在他著的《莎士比亚年谱》(1988)中称:这首诗影射的是:“女王的宠臣、文武全才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因和贵嫔私婚被关入伦敦塔牢房,判处死刑,旋又获释,”从而指出这首诗写作于这件事发生的1592年。
第107首往往被认为是据以考证写作年代的关键。诗中有一句“人间的月亮已经忍受了月食”,被认为包含着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它引起注释家们的多种猜测。“人间的月亮”何指?“月食”何指?多数注释家认为“月亮”指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常被人称作辛西娅(月神)。“月食”象征灾难。有人把原文endured(忍受)解作survived(安然度过),如凯勒(Keller)于1916年认为,“安然度过月食”指女王过了63岁大关(当时欧洲人相信的占星学认为,人的生命每7年有一个关口,而63岁是最危险的大关)。据此,这首诗应写于1596年9月7日(女王开始进入64岁)或稍后。但还有另外的说法。G.B.哈锐森于1934年主张,“忍受了月食”指女王之死。那么,这首诗应写于1603年3月24日(女王逝世日)或稍后。但泰勒早于1890年即认为,“月食”不可能指女王之死,较合理的解释应是指埃塞克斯叛乱。1601年2月8日,埃塞克斯伯爵率党羽上街,企图煽动伦敦市民逼迫女王改变政府,否则要逮捕女王。结果叛乱失败,埃塞克斯被捕,2月25日被处死。据此,这首诗应写于1601年2月或稍后。
这首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无常,如今到了顶,变为确实,/和平就宣布橄榄枝要万代绵延”(橄榄枝象征和平)。这是指什么?巴特勒于1899年说,除了击败“无敌舰队”这件事外,这句诗还能影射别的什么事呢?那么,这首诗必定写于1588年,是年7月下旬,西班牙庞大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查尔斯·霍华德指挥下的英国军舰攻打,焚烧,追逐,130艘舰只在海战和风浪中损失大半;西班牙军队从荷兰过海向英伦登陆的计划也成泡影。英国大获全胜,在伦敦举行盛大的祝捷庆典。若按此说,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又大大提前了。仅此一诗的写作年代,有人判为1588年,有人判为1603年,相差15年。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猜测或设想。
“自传”说和“非自传”说
“自传”说和“非自传”说的论争,是这些诗所引起的诸问题中最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所谓“自传”说,并不是认为莎士比亚要用这部系列组诗来构成一部诗体自传。此说的主张者只是认为,这些十四行诗中涉及的人和事都是莎士比亚个人生活经历中真实存在的,诗中表达的感情是他的切身感受,因而这些诗带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而“非自传”说则认为莎士比亚创作这些诗与他创作剧本一样,诗中涉及的人和事是虚构的,或假托的。因此,一切试图从历史上找出真人真事来与诗中的人和事“对号入座”的学者和读者,以及虽不进行考证但确信诗中所写均实有其事的学者和读者,都属于“自传”派。反之,则属于“非自传”派。
1609年第一四开本出版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读者是否认为这些十四行诗里有一个“故事”,对它有什么看法,已不可考。1640年本森出版这些诗时把诗中代名词的性别改了,出于什么动机,也不可知。18世纪各种版本的编者对诗中人和事的关系不感兴趣。1769年,德国莎学家施莱格尔(W.von Schlegel)第一个指出:由于这些十四行诗所表达的是由真实的友谊和爱情产生的真情,还由于没有其他资料可供我们去了解莎士比亚的个人历史,所以这些十四行诗有价值。施莱格尔的评语被许多英美研究者引用,产生较大的影响。1818年,洛克哈特(Lockhart)发表他用英文译的施莱格尔的评语,说成这样:
通过这些诗篇,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这位伟大诗人的个人生活和感情。他写十四行诗时,似乎比他写剧本时更具有诗人的自我感觉。通过这些发自肺腑的作品去审视莎士比亚的性格,是奇妙而愉快的。要正确理解他的戏剧作品,必须认识这些抒情诗篇的极端重要性。
1815年,英国浪漫派大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称赞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说:“莎士比亚在这些诗中表达了他本人的、非他人的感情。”1827年,华兹华斯发表一首论十四行诗的十四行诗,说:“别轻视十四行诗,批评家!你冷若冰霜,/毫不关心它应有荣誉;莎士比亚/用这把钥匙开启了他的心扉……”。华兹华斯的观点仿佛一声呐喊,在莎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论者把施莱格尔和华兹华斯认作“自传”说的肇始者,把他们的观点称作“施莱格尔·华兹华斯信条”。
很快就有人发表反对意见。鲍斯威尔(Boswell)在他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821)中写道:
我满足于认为这些作品毫不涉及诗人或其他可以见到的个人的私事。这些作品仅仅是诗人幻想的产物,根据几个不同的话题写出来,以愉悦小圈子里的人们。
斯考托(Skottowe)在他的《莎士比亚传》(1824)中说,“要从这些十四行诗中去探索莎士比亚心迹的努力大都是做梦,是疯狂而荒诞的臆测……。”柯里埃于1831年认为这些诗是莎士比亚替别人写的代笔作品。戴斯于1832年认为,莎士比亚是以一个假想人物的身份来写这些诗的。后来的一些注释家们认为这些诗是戏剧抒情诗而不是个人抒情诗,形成“非自传”说,此说以柯里埃和戴斯的观点为滥觞。
“非自传”说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怀特,他于1854年提出:按当时的风俗,坠入情网的男子或其他人可以雇佣能写诗的才子为他们代笔写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取得酬金,这酬金就是他后来购买伦敦剧院的资金来源之一。科尼(Corney)于1862年认为,这些诗绝大部分都“仅仅是诗歌创作的练笔而已”,他说,如果认为这些诗带有自传性质,那无异于“对我们爱戴的诗人的道德品质进行诽谤”。在19世纪末,研究莎士比亚最有影响的学者锡德尼·李在几度突然改变观点之后,终于坚决地认定:这些十四行诗纯粹是常见的练笔之作,没有任何自传的意义。他在《莎士比亚传》1897年伦敦版中说:除了第153、154两首之外,“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坦陈了他的心灵的经历,尽管语意是隐晦的。”但是锡德尼·李在这之后,在同一年出的该书纽约版中,把这些话突然改为:
这些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文学练笔而写成的。这些诗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幻觉或个人自述的印象,可以用作者的经常起作用的戏剧创作本能来加以解释。
欧美的许多诗人和作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德国诗人海涅在1876年认为,这些诗“是莎士比亚一生中种种境遇的可信的记录”,深深地反映出“人类的悲哀”。英国作家卡莱尔在他的名著《英雄与英雄崇拜》(1840)中说:
我说莎士比亚比但丁更伟大,因为他真诚地战斗过并且战胜了。不用怀疑,他也有他的悲哀:这些表明他的心愿的十四行诗清楚地说明:他涉过多么深的水,为了生存,他在水中游泳挣扎。
美国作家爱默生于1845年演讲时说,“阅读这些十四行诗谁不发现诗人莎士比亚在其中揭示了友谊与爱情的真谛,揭示了最敏感而又最具智慧的人的思想感情的困惑?”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大诗人、新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布朗宁(1812-1884)不同意华兹华斯的观点,说:“‘莎士比亚用这把钥匙开启了他的心扉’——真的吗?如果是,他就不像莎士比亚!”另一位重要的英国诗人斯文本(A.C.Swinburne,1837-1909)于1880年针对布朗宁的论点反驳说:“不,我要大胆地回答:没有一点不像莎士比亚:但毫无疑问,一点也不像布朗宁!”
这个论争一直延续到当代。《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1974)中,斯密斯为《十四行诗集》写的序中说:“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否带有自传性质是不可知的这种观点,很难永久不变。这种观点依仗的是呆板的学院式原则,即:没有充分证据来证实,就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这个看法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贝文顿在他编的《莎士比亚全集》(1992)中为《十四行诗集》写的前言中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曾作为内心的呐喊而打动过许多读者……然而,这种表达感情的力量可能是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天才的赞扬,却未必能作为他本人感情卷入的证据。”这个观点又偏向于“非自传”说了。
对这个问题,笔者也有自己的倾向性。笔者认为这些十四行诗不可能不带有自传的性质,或者,不可能没有自传的成分。尽管不能确定诗中的具体人物和事件,但不能因此就判定这些诗都是文学虚构。抒情诗与剧本不同,与叙事诗也不同。如果认为这些诗出于摹拟、假托或虚构,那么这些诗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具有真诚性。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也不可能通过无病呻吟达到如此杰出的抒情诗高峰。不是真诚的思想感情怎么能打动千百万读者的心灵!笔者在1955年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本新一版所写的“内容提要”中指出:
这些十四行诗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们透露了莎士比亚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个人历史的一部分,读者将从其中窥见这位伟大诗人戏剧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若干方面。
这个观点至今未变。
对于这些十四行诗的思想蕴含和艺术造诣,西方评论家中给予高度评价的也不乏人。本文一开头就引了斯托普斯的一段评语。这里再选录三则以示一斑:
美国诗人昂特梅耶(L.Untermeyer)在本世纪40年代初说:
人们可以对这些十四行诗所包含的“故事”提出疑问,对这些诗的系列顺序表示怀疑,但不可能怀疑这些诗的思想深度和感情强度。除去那些看上去太普通、太随心所欲的十四行诗外,这里有一座小小的诗歌宝库,唱出了欢乐与绝望的最高境界。爱情与失落,忠诚与欺骗,情欲导致的烦恼与音乐的治疗功能……这些题目形成一个个对比,为总的主题服务。这些诗具有天才作者奇迹般的创造力量,它们创造出两个世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浪漫然而可以认识的世界,和想象中的无实体的然而更加恒久的世界。
J.A.恰普曼(J.A.Chapman)于1943年说:
没有任何其他英国诗歌比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唱出更好的进行曲来。因为这些诗永不变暗淡,永远新鲜;充满着戏剧活力和兴味;富于智慧,成熟完美。诗中有大自然;有爱的激情;有表达这种激情的神圣的语言;还有许多老人的睿智……
又说“这些十四行诗的内涵小说是不可穷尽的”。
更早些,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有这样的评价:
说到高度的完善,风采,优美,我不知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有哪一种能达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水平:这些诗使人们不得安宁: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困惑……(注:引自贺拉斯·特罗贝尔(Horace Traubell)著《瓦尔特·惠特曼》(1914年版)。)
笔者毕竟孤陋寡闻,还没有见到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思想和艺术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价的专门论著。本文介绍的西方学者对这部诗作的考证和论争,延续了二百多年,引起了轩然大波。论争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掩盖了这部诗作本身的光芒。某些注释家穿凿附会的论证,花费了读者宝贵的时间。本文只想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西方学者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进行考证、研究、论争的概貌,并不想把读者引进繁琐考证之兴趣的歧途,“在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评论中,比之于在对他的其他作品的评论中,有着更多的蠢话。”这是钱伯斯(E.K.Chambers)在1930年作出的估计。这看法对我们认识西方某些莎学家的论证,至今还有启发意义。斯密斯在本世纪70年代初说:“目前读者阅读这些十四行诗时把主要兴趣放在其文学品质方面,似乎已成为可能。”这话令人惊讶,也令人沮丧,但也稍稍给人以宽慰,因为透过历史的迷雾,这部经典名著本身的光芒已经显露出来。
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论文; 英国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