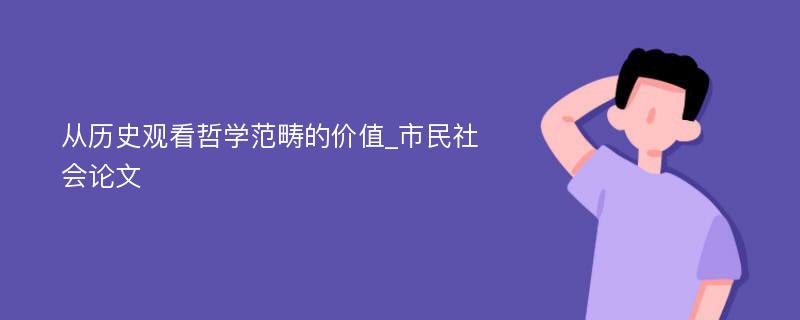
从历史维度审视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范畴论文,哲学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13)02-0011-08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已经作了相当多的阐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维度。但毋庸讳言,现有成果大都是一种静力学的或曰静态的考察,即把价值范畴当作一种不受历史约束的永恒不变的抽象规定加以确认,脱离特定历史语境提出并解决问题。我认为,这种研究方式不符合马克思的运思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价值的历史展现性质,从而妨碍了对其本真性的揭示。
一、关于价值范畴,怎样提出问题才恰当?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以“劳动”为例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①此话颇值得仔细玩味,其中最要紧的在于马克思提示了一种运思的方法论原则,即“抽象的规定本身”也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并且只有被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性。因此,马克思认为“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那么,我们也同样应该把价值范畴看作“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它也“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按照马克思“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只有把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当作一种历史的规定加以追问,才是恰当的;非历史或超历史地提出问题,都是不恰当的。
人们虽然提出了“价值”的“属性说”、“实体说”、“关系说”等等,但并未真正理解它们都是在什么意义上才成为真理,亦即使它们具有真实性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我们不能抽象地说哪种阐释方式是恰当的,哪种阐释方式又是不恰当的。问题仅仅在于必须给出各种阐释方式之适切性的历史条件,以及做出某种阐释的历史理由。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真实的,从而才有意义。只有从历史维度上对价值范畴加以阐释,才能恢复它的本真性的含义。马克思式的“历史地思”,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
从本体论上说,正如蒂利希所言:“价值只能从表现于存在中的‘在’(being)的基本结构中导出。”③对本体论的元问题——“存在(Being)是什么?”——的追问,究竟是沿着“本质”(essence)一途还是沿着“实存”(existence)一途而展开的争论,难道这仅仅是取决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吗?问题在于,人的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本身又源自何处呢?离开了人的“亲在”(Dasein)—在马克思语境中,“亲在”不过是人的实践的建构活动本身——所塑造的历史,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答案,由此决定了回归历史维度成为本体论赖以重建的契机。“本质”和“实存”的区别,在本体论意义上成为“存在”的不同维度的分野,在人本学意义上则成为人的存在本身的不同维度的分野。而本体论结构不过是人本学结构的反思性把握而已,因为哲学就是人为自己的存在立法。但它一经产生,就遮蔽自身的根源,人们因此遗忘了它同人的历史存在之间的脐带般的本然联系。在人的存在的层面,“本质”与“实存”的分裂,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意味着人的异化的历史生成。如果说理性(“是”)对应于“实存”,那么价值(“应当”)则对应于“本质”。作为绝对的形式,价值乃是抽象普遍性的修辞,它因此而变得空洞,被表征为应然的规定。作为相对的形式,理性则是基于人的经验存在对实然世界的把握方式。当然,从更始源的意义上看,人的存在的这种分野及其带来的后果,归根到底植根于人的实践结构——普遍性品格和直接现实性品格的内在矛盾。实践基础上的人的本质与实存的分裂,展现为人的个体与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尘世”与“天国”、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一系列矛盾。这才是价值问题得以历史地发生的坐标。从逻辑上说,它们都不过是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悖论展开了的形式,进而构成理性与价值分裂的历史根源和学理根据。
二、理性与价值的关系之历史维度
一般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休谟最早对“是”与“应当”做了自觉而明确的划界。休谟说:“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或伪”④。真伪判断只能是事实判断。在休谟看来,道德准则“不能由理性得来”,因为“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⑤。他因此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区别并不是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完全不活动的,永不能成为像良心或道德感那样的一个活动原则的源泉”⑥。与真伪判断不同,善恶问题属于价值判断。休谟实际上区分了“理性”同“价值”这样两个不能相互归属、不可通约的范畴。为什么到了休谟那里才提出“是”与“应当”的自觉划界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是历史本身成熟到足够程度的一种意识形态表征罢了。只是到了近代,纯粹的理性⑦才真正被确立起来。与此相应地,价值也成为一种经过反思而被把握到的自觉形式。
马克思“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是”与“应当”的划界本身所依赖的特定历史语境,意识到我们自己究竟是在说什么,所说的到底又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理解,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之思、一种本体论式的反思功夫。只有如此处理问题,才能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经过古希腊理性主义的过滤,犹太教演变为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上帝”不过是“逻各斯”的神格化。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这种原始的融合终于解体,从而终结了。因此,从根本上说,价值同理性的分裂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或事实罢了,它在本质上属于现代维度。实际上,当“价值”被作为一个自觉的问题提出时,就意味着价值同理性的分裂及其对立已然在历史基础层面上实际地发生了。对价值的反思性的把握本身,就构成这一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修辞。
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理性的世界越来越物化为一种没有任何价值负荷的、敌视生命的领域,而价值的世界则越来越灵化为脱离任何实存而孤立存在的空洞形式,以至于变成一种虚伪的装饰物。这就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分裂的历史现象。正因为如此,宗教这一价值的标志物,只能使人醉心于虚拟的满足而无法使人得到真实的满足。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构成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的理由。马克思说得好:“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⑧处于宗教异化中的人,其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这里所谓的“现实性”,应该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被领会。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本质与实存的分裂,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不具有现实性。
马克思还进一步揭露了宗教的历史根源,指出:“政治国家的成员之所以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⑨因此,“彼岸世界的理论”就是“宗教”⑩。但是在基督教那里,自由这一绝对价值却变成一个遥遥无期的空头支票。正如马克思所言,对自由的渴望“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则消失在天国的幻境之中”(11)。因为“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但“相反地,在国家中……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12)。所谓“非实在的普遍性”,亦即那种脱离了特殊性、从而不再以特殊性为中介的抽象普遍性,它规定了人的“天国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宗教不过是与市民社会分裂、从而外在于市民社会的政治国家成员的灵化形式。它构成价值的一种可能的载体,却沦为“天国的幻境”。康德把宗教作为道德的基础,认为上帝、永生和积极的自由构成使道德赖以成立的三个悬设。这正是“价值”在历史上得以凸显并被人们自觉地把握到的秘密所在。
作为价值的人文形态之一,道德何以在历史上受到排斥并因此沦为独立的存在?这就不能不回到造成这一格局的世俗基础,即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这三者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大致地说,它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它们彼此不是简单的等价关系。有了商品经济,未必就有市民社会;有了市民社会,未必就有资本主义。二是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发生学联系。就是说,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足够成熟之时,必然会孕育出市民社会;同样地,当市民社会成熟到足够的程度,也必将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三是资本主义构成商品经济的最高历史阶段和最完备形态。
商品经济对于道德的拒斥,构成理性与价值分裂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商品经济为理性精神提供世俗基础,两者具有内在的、原罪般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作为商品经济的最发达、最典型、最充分的形态,资本主义生产(13)变成了“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14)。科学乃是理性精神的最典型的人文形态,它因此成为马克思说的“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其次,商品经济本身正是孕育人的理性精神和理性能力的土壤。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交换所实现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分离,实质上不过是“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15)。因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16)。商品交换把使用价值这一特殊性规定“过滤”掉了。因此,商品交换过程也就是达到可通约基础(17)的过程,它无疑是一种“简化”。“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18)。人的存在方式归根到底孕育着人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学意义上,人的抽象思维这一理性能力,不过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实际抽象的内化形式罢了。而理性只有以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再次,商品经济所需要先行设定的人格是斯密所谓的“经济人”,它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具有权衡利弊得失能力的主体。权衡利弊得失的能力亦即“会算计”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正因此,黄仁宇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称作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社会。
市民社会对道德的解构,既是近代以来理性与价值紧张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也是这种紧张的一个突出的历史表现。市民社会成员争得的“市民权”意味着什么呢?它说到底不过是作为商品经济前提的自由。关于这种自由,马克思一语中的:“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19)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财产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相反地,我的意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体现在财产中’”(20)。也就是说,是私有财产决定了人的意志自由,而不是意志自由决定私有财产。因此,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成了意志的主体,意志则成了私有财产的简单谓语。在这里私有财产已经不是任性的特定客体,而任性反倒是私有财产的特定谓语。”(21)作为市民权的自由,不过是私有财产这一客观的占有关系支配下的主观任性而已。因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是“占有”。而“私有财产的权利是jus utendi et abutendi[任意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22)。马克思还进一步揭露道:“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23)市民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不过是马克思所谓的“私人任性”罢了(24)。这就勾画出来了市民社会的反道德性质。只有遵循道德律才能获得必然性。作为对人之为人的固然之理、本然之性、当然之则的背离,任性不过是受制于外在规定的表现,从而是偶然性支配的结果。黑格尔对此早就做了透彻的揭示,他指出:“我既然具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来规定自己,也就是说,我既然可以选择,我就具有任性,这一点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自由。”(25)人们对于自由的俗见,并未超出任性的范围。而任性又意味着什么呢?“任性的含义指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26)真正的自由是由内在必然性规定的,而不是由外在的他者规定的。由他者规定的东西,只能是偶然之物。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偶然性一般讲来,是指一个事物存在的根据不在自己本身而在他物而言”。(27)而“任性的内容是外界给予的,并不是基于意志本身,而是被意识到以外在环境为根据的。就这种给予的内容来说,自由只在于选择的形式,这种表面上的选择,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因此也可看成只是一种主观假想的自由”(28)。由外在的他者决定,这一情形恰恰是商品经济所塑造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典型特征。从表面看,商品生产者对于顾客偏好的迎合;从深层看,商品经济对人的肉体存在(29)的肯定,都是这种特征的体现。因此,市民社会成员不过是“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而且“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30)。由此决定了我们对于任性的世俗基础,只能在以商品经济为根源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真正的意志自由一旦被任性所取代,就不可避免地违反道德律及其基础之上的基于内在必然性而成立的自由,从而沦为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形式上的自由”或“主观假想的自由”。这种所谓的自由,只能是一种伪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市民社会成员只能是“偶然的个人”(31),而这种“偶然存在的人”(32)必然表现为“任性”。
此外,市民社会还造就了利己主义者。黑格尔已经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3)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34)。在对市民社会所做的批判性分析方面,马克思显然是继承了黑格尔的有关思想,他同样指出:“市民社会成员”无非就是“利己主义的人”(35),因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36)。市民社会“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37)。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命运。在这样的“世界”,道德必然丧失掉赖以立足其上的根基和地盘。当然,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分歧,不在于对市民社会条件下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分裂及其对立的揭示,而仅仅在于对这一对立的根源所做的解释,以及超越和扬弃该对立的可能路径。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将其诉诸实践所建构的历史本身的成熟,而非任何超历史的想象。
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孕育出来的现代性,具有排斥道德的性质。早在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即已孕育着了。资本主义历史发生的前提性条件就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萌芽恰恰生长在管制的空白地带。皮朗甚至说“自由是市民的第一需要”;“自由成为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38)。其实,对于市民阶级来说,自由并不具有形而上学含义。“市民阶级最不可少的需要就是个人自由”,但“他们要求自由,仅仅是由于获得自由以后的利益”(39)。然而,“事实必须变成权利”。在11世纪前后的欧洲社会,新兴的市民阶级甚至抛开捍卫封建主和贵族利益旧有的法律秩序而另搞一套(例如皮朗提到的最迟在11世纪初产生的一种萌芽状态的“商法”之情形),这一方面显示了他们的自组织能力(这构成了自治传统的发生学根据),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市民阶级使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诞生出来(40)。亚当·斯密称对于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运用为“最神圣的人权”(41)。如同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样,“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42)因此,恩格斯总结道:“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43)正如阿隆所说的,“剩余价值不需要主人和奴隶、领主和农奴的划分,但需要劳动者的法定自由,契约的自由。按照市场的规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4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自由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但这种自由值得剖析。这种自由的最初发生,可以让人们看清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之所以成为道德的一种解构力量,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了。弗里德曼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英国、美国以及在较少范围内的欧洲大陆,人们能未经任何政府或类似政府当局的同意而从事他们所企求的任何行业或职业。”(45)到了19世纪,对自由的约束已不再区分正当与否、合理与否,而是一概地予以拒绝。连“职业执照”的颁发都在拒绝之列。由此不难窥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的实质。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它需要有市场自由,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46)。正是以这种“自由”为条件,人的欲望表达为任性且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传统社会伦理规范对于人的肉体存在的约束被逐步地解除了。这正是道德失效和受到腐蚀的重要历史因素所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任人的贪婪乃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正是这一点,在韦伯的《经济通史》中被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得以建立的6个基本条件之一。
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吊诡和悖谬现象,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47)而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已经沦为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变成了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的物化形态。不仅如此,理性还渗透到经济过程。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实践把货币单位转变为合理的成本——利润计算的工具,计算的最高成就是复式簿记。”(48)这种“计算”不仅反映出背后的功利动机,而且“计算”本身的价值中立性也排斥道德的正当性。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无非是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修辞。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49)。恩格斯也讽刺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50)。经济学说到底不过是自然逻辑在人间的应用。大自然没有多余之物,因而是最节约的;而经济的本义,就是节约。因此,自然逻辑最符合经济学规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何以能够启发达尔文揭示生物学规律这一科学史事实了。经济学一定是排斥道德的。恩格斯批评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认为它“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51)。他甚至说:“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52)。
总之,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历史上孕育并强化了理性精神,促成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的相继发生,这些变革不仅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而且有一条明晰的理性线索贯穿其中;另一方面也在历史上剥离了宗教和道德,使其变成一种日益游离人的世俗世界的唯灵论的抽象形式。这就是理性与价值的分裂的特定历史语境。对于价值范畴的理解和把握,不能不回到这个基础上来。惟其如此,才是一种“历史地思”。
三、从历史上看,价值理想是一把“双刃剑”
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看,为什么把价值预设为终极目标的理想主义往往导致悲剧性的后果?这是一个令人沉思且不容回避的问题。抽象的价值目标倘若脱离了历史的条件,就有可能导致灾难。价值作为被人通过意识而自觉地掌握的理想目标的规定,它本身却是一把“双刃剑”。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理想的确立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它的实现也同样依赖于历史本身的成熟。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历史条件尚不成熟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实际的历史为其创立者准备了必要条件的产物。马克思也谈论理想社会,它作为价值目标的规范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3)提供批判尺度,从而引导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超越现存的一切。二是它要求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从后思索”,这表征为马克思所提示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即“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4)。所谓“社会的人类”,也就是“合乎人性的人”(55)。显然,同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市民社会不同,实践的唯物主义立足于理想的亦即人性实现了复归的社会。
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无疑都追求价值目标,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诉诸人的实践基础上的历史本身的发展。倘若脱离了历史基础,价值目标就将面临着沦为“乌托邦”的危险。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价值目标的人的解放,归根到底不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而是历史领域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马克思认为,对人而言,“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56)。因此,“‘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57)。人的解放作为最高价值理想,只有变成历史本身的现实存在时,才能获得其充分的意义和真实性。它意味着人的本质与实存、理性与价值、历史与道德之统一的实现和完成。
以“取消货币”为例,马克思说:“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必须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58)“取消货币”当然是价值理想的诉求,因为货币所代表的商品经济制度是一个有待被超越的阶段,不超越这个阶段,就无法过渡到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在“取消货币”问题上,马克思提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历史地“取消”,一是人为地“取消”。前者显然是基于历史本身的逻辑和历史本身的成熟,是人类历史“自己构成自己”的运动。后者则违背历史本身的节奏,无视历史本身的成熟,对货币采取机械否定的态度,这是一种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59)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看,这也是值得作出深刻反省的地方。马克思坚决拒绝那种“唐·吉诃德式”的否定。因为在他看来,“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60)所谓“抽象否定”,就是那种不包含任何肯定于自身、不是把肯定作为自身的一个内在环节的否定,从而是机械的否定。为什么说这种否定是一种“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呢?因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1)。任何无视历史进步的否定,都必然是违背“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的,从而是“非自然”的。所以,马克思反对那种在前私有财产的水平上否定私有财产的做法,尽管它符合抽象的价值目标的诉求。
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作为“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只有“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才能够“生成”。这意味着,“历史的全部运动”,就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62)。马克思认为,那种脱离历史基础的、仅仅满足于空洞的价值目标的取向,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仅具有欺骗性,而且会阻碍历史的真正进步。因为“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63)。这种仅仅基于道德理想而实现的虚幻的超越,不可能达到“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而只能陷入“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64)。
按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了避免价值“乌托邦”悲剧,我们不得不忍受历史发展中的必要的“恶”。尽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5),但仍然需要肯定它的历史解放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6)。而生产力的积累,恰恰为人的历史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恩格斯也揭示了文明社会的道德代价,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被“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他进而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67)正因此,恩格斯同意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的动力的命题。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交换时指出:“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68)没有超越,没有价值理想的引导,从而把现实本身理想化,就不能不导致保守主义立场。这是一切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所共有的致命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种脱离历史基础的超越就是正确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恰恰就在于离开历史基础,去寻求一种与历史无关的理想,其结局不外乎走向道德感伤主义。马克思对这两种极端立场,均持否定态度。我们从中不难体味出马克思对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所秉持的历史主义态度。
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追求道德的纯粹性一旦脱离了历史的基础,就有可能导致相反的局面,即走向道德的反面。胡克说:“极权主义的文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罪恶的错误的历史上合法的继承者,而且还被认为是对于这种不能持久的传统的道德上合法的反动。这种文化显示出对人们心灵的一种值得令人赞赏的关切,但是走上了错误的救世道路。”(69)在这一点上,足以体现出对于历史的理性主义态度及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的辩护。
在一定意义上,理性与价值的关系可以转换为“知”与“信”的关系。“知”与“信”的关系本身,也只有被纳入历史的坐标中才能得到透彻的理解。然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把一个“信”(believe)的问题当成是一个“知”(know)的问题来处理。这种做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以历史本身的成熟为基础的统一,而是一种无视历史基础的混淆。从西方哲学的嬗变看,许多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超历史地混淆了这二者的区别。我们需要仔细甄别,“知”与“信”的统一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康德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搁浅,即陷入必然与自由、自然律与道德律的背反,就是因为他未曾想到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解释。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触及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这种统一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规定,它只能在历史的展开及其完成中得以实现。在现象学意义上,它表征为一个不断生成和展现的过程;在完成的意义上,它又表征为积淀着以往的全部历史财富的最终结果。马克思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70)只有作为“历史的全部运动”的结果,它才是可能的。尽管在措词方面还残存着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痕迹,但此时的马克思无疑已经奠定了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全新基础。从马克思的观点看,那种把理性与价值抽象地对立起来并加以孤立地论述的做法和立场是多么地狭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③马斯洛主编:《人类价值新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
④休谟:《人性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8页。
⑤休谟:《人性论》下册,第497页。
⑥休谟:《人性论》下册,第498-499页。
⑦这里所谓的“纯粹”,并非指不包括任何经验的成分,而是指不包含任何信仰或价值的成分。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13)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页。
(17)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可通约的量”、“本质上的等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0页。
(2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页。
(2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7页。
(27)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1页。
(28)黑格尔:《小逻辑》,第302页。
(29)对于“人”而言,人的肉体存在并不具有内在的意义,因为它虽然是人赖以存在的前提,但却不能成为人之为人的理由。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作为感性的东西,我本身是外在的,是空间性的和时间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51页)。
(3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4页。
(3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09页。
(3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0页。
(38)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7页。
(39)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6页。
(40)它的历史后果,就像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页)。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对于政治国家的排斥和挤兑。
(41)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5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6页。
(44)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
(45)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31页。
(46)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7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4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9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5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65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6页。
(6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80页。
(6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7页。
(6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6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1页。
(6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3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页。
(69)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1页。
(7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1页。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